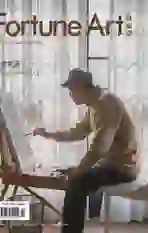《气球》,错位的第五代气息
2021-03-30俞冰夏
俞冰夏

中国始终没有出现第七代导演,代际定义和作者导演的身份因为资本介入而加速失真。当今作者导演,如万玛才旦一般精通上世纪知识分子电影语言的不多,他受阿巴斯的影响之深,注定使得他在电影行业的道路要走得比年龄比他还小一岁的贾樟柯困难得多。万玛才旦的藏族身份在中国大陆电影的语境下显得如此异域、异化,然而他的电影能真正吸引的文艺片观众,对全球本土化(glocal)这样的时髦观念精通得很,也能从根本上明白人类之间的共性远超过文化差异。万玛才旦最近的两部长片《撞死了一只羊》和《塔洛》是主体性泛滥的电影,藏地风貌只是其背景,驱动发展的是人作为个体寻找自我,或寻找某种线索的路径,其宗教意味,或处于国土疆域远界的疏离气味,是主体意识的一部分。我忘不了《撞死了一只羊》里作为面店老板娘的索朗旺姆在给金巴倒酒时极魅惑的眼神,它不是纯真的,因此是真实的。《塔洛》里的剪发更是如此,其中晦涩的情欲、对自我的隐秘怀疑,都是万玛才旦电影最为吸引人的地方。
新片《气球》则不同,我惊讶于在2020年,能看到如此浓郁第五代导演气息的叙事。你也许可以说是故事驱动了这部电影的表现方式,但娄烨对毕飞宇《推拿》的电影表现,找到了把第五代集体叙事“翻译”为第六代个人主义气质的方法。这不是说集体叙事没有价值,也不是说张艺谋《一秒钟》这样的电影在今天就完全过时(毕竟电影是种大众艺术,它理应是集体大过个人的),只是它也许淡化而非辅助万玛才旦的电影语言。当片尾,一只只气球升天,用最字面意义的方式点了电影的题时,我在空荡荡的电影院里,不得不认为这要不是对院线和制片人的某种妥协,就是中年人对自己的妥协。无论如何,它是一声叹气,虽然可能还不至于是一声哀叹。
在今天的中国影视行业,想要拍个院线片,不妥协是不可能的,最直接的妥协是价值观上的,毕竟那最不值钱。这是现实,苛责从业者毫无意义。某种程度上万玛才旦面对的困难要超过很多其他导演,倒不仅仅是因为藏语电影带来的文化差异,而是因为他从来是个叙事节奏异常缓慢的导演,他的叙事速度更接近实验影像。没有哪个第六代导演抵达过万玛才旦在这方面的高度,放眼国际,我还能想到阿彼察邦和蔡明亮,剩下的恐怕都活跃于美术馆。在这方面拒绝妥协的结果是,《气球》不得不从故事上走入俗世,讲起了随便哪个中国老百姓都能理解的基本家庭伦理故事,并不得不把时间转回到90年代。或者说,比起他的其他电影项目,这个故事更能让投资方看懂。再也没有《撞死了一只羊》里两个金巴在卡车里无厘头的荒诞对话,也没有《塔洛》里粗颗粒黑白画面和肆意、放空的大量留白。《气球》里属于万玛才旦的闪光点,那些超出观众预知的部分,是在两个小男孩身上。除此以外,它的精致与中规中矩,也许对其他导演是进步,对万玛才旦则不一定。
第五代叙事的根基是一个字:穷。人为了钱能做出些什么,这是源远流长的现代主义话题。看《气球》,你首先意识到“气球”这个词对藏语来说是舶来语。它以汉语普通话的形式夹杂在句子里。气球在这部电影里的象征意义,从一开始就很字面。电影的开头在我眼里是它最精彩的片段,金巴扮演的男主角骑着电瓶车一如阿巴斯《随风而逝》(很难否认这部电影对万玛才旦视觉风格几乎定型般的影响)的开头,慢慢盘转到父亲身边。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在老父亲与男主角的对话当中被亲情糊弄过去,这种糊弄,人类有所共情,两个孩子则在一边把从父母枕头下偷来的避孕套当气球吹,人生的轮回概念不用转世的佛教仪式看待,也就是这么回事,生老病死是朴素的生活原理,唯物还是唯心是之后的选择。
男主人公的形象是傳统家庭掌门劳动力。男人朴实、勤恳、能干、顾家、孝顺,有时脾气暴躁,偶尔酗酒。女主人公的形象是传统家庭妇女。女人朴实、勤恳、能干、顾家、温婉,有时对未来没有信心,偶尔为自己的苦命唏嘘。这对夫妇是传统家庭叙事的范本人物。另外几个次要人物——在县城上学的大儿子,害怕拿不出学费,干活非常卖力,显然在未来会成为自己父亲的翻版;因为情伤出家做尼姑的小姑子;虔诚、笃信转世的父亲,也都是典型现代主义文学人物。唯一的岔路是小姑子写小说的文艺青年前男友,两人为何交恶电影并没有完全交代,作为观众,猜测基本是男人因为追求理想而远走他乡,年轻时没有能力把理由成功解释给女人。
万玛才旦讲究意象,从早期作品《静静的嘛呢石》开始就对用物作为符号渲染意象有几乎宗教般的虔诚。在电影里的雕琢意象有点像在生活里塑造仪式感,两者的心理源头恐怕也一致。《气球》里,红白气球与红事白事的对应,动物借种与人类借种的交错出现,停电和火焰熄灭之中的文明冲突,最后老父亲的去世与女人因为避孕套被孩子偷走,又一次怀孕直接发生在转世的时间框架之中,这些意象的处理直白、易懂,视觉效果也精致到位,粗颗粒画面和不稳定的相机视角很少出现,长镜头拍得又美又稳。如果不是因为故事落俗,这无疑是他在美学价值上最接近《随风而逝》的作品。
但我们也要讨论这个故事。在2020年看这部电影,观众几乎无法避免会带着今天流行的意识形态,把视角聚焦在女人身上。索朗旺姆身怀红气球的电影海报具备属于今天女权主义的视觉权力。然而这既不是个2020年的故事,也和性别政治关系不大。《气球》里这对夫妇在主体意识上的缺乏(也就是“传统”),使得我们不得不把他们的行为逻辑归结于“生存所迫”和“传统文化”。意外怀孕后,女人想要堕胎,原因也不是她要追求更自由独立的人生,而是因为穷。就像女人烧了妹妹前男友的书,并非因为对伤害妹妹的男人有女权意义上的恨,而是害怕妹妹为了追求浪漫,失去生活基本保障。影片发展到第三幕的关键阶段,男人发怒打了女人,女人坚决去了医院,家庭伦理开始歇斯底里升级,女人至此的形象,完全是张艺谋电影(不管是《红高粱》还是《归来》)里巩俐经常扮演的形象,传统中国女性受苦受难的形象。至于之后的开放式结局,好像一声不加解释的叹气,恐怕听者各有各的认知。
把万玛才旦放在大陆电影的语境下看也许不公平,对藏族文化有念想的人,容易把万玛才旦电影里日常生活的仪式感等同于肃穆和光明,之后我们面对一个凝视异族文化的目光是否具备充足知识的问题。没去过藏区,如何能理解《气球》?此类身份政治的呐喊已成为常态,但我总相信,我们读来自全世界的书,看来自全世界的电影,目的是为了不再大惊小怪,以便对人性的认识能回归本质——而非倒过来,扮演所谓“人类学家”的角色,假装不明白穷对人的创伤是全球通用的,用小布尔乔亚的想象把穷人几千年来磨炼出的对付穷的方法供起来统统当美的东西处理。万玛才旦之前的电影在展现藏族生活以外,依然能捕捉独一无二的主体意识。《气球》放弃了这些,恐怕是令人遗憾的。
更令人遗憾的是,《气球》奔向主流的尝试并没有换来太好的票房收益。当今的电影市场对小资本电影可以说环境万分亿分恶劣,几乎没有存活空间。我们当然不是真的没有第七代导演,他们是郭敬明、吴京、韩寒、沈腾,以至于谁也不好意思用第几代来称呼人了。有电影理想的人如何在这个时代存活,这问题太难,无法回答。而纵然《气球》有令人遗憾的部分,它恐怕依然是2020年最好的大陆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