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母的慈爱
——怀念我的母亲资华筠
2021-03-30王蕾
王 蕾
译林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图书《百年名家散文经典:母亲》中,收录了我的母亲资华筠曾经发表的一篇文章《严母的慈爱》。这篇文章也曾收录在她2004年出版的散文集《过电影》中。借着这个机会,我重读了母亲当年所写的这篇怀念外婆的文章。一转眼,母亲离开我已经有六年了。我一直很想写一篇文章怀念我亲爱的母亲,虽然我心中思绪纷繁,真到写时,又不知该从何落笔。

傣族舞蹈《白孔雀》(独舞),首演于1959年,摄于1981年

“豆蔻”年华首演《飞天》,摄于1954年
每当我端详母亲的照片时,母亲的形象就会在我的眼前浮现。很多记忆就如同电影里的片段,在我脑海中交错闪过。母亲是著名的舞蹈家、学者,当她在舞台上表演“飞天”时,母亲美丽高贵如仙女下凡;当她端庄地坐在台上发言,在电视里接受采访的时候,母亲又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学者。在生活中,母亲身上既有教导我时体现的严厉的家长气质,又有搂着我在沙发上聊天、斗嘴的家常范儿。在我与母亲共同度过的时光中,有着太多温馨和难忘的回忆。我们是母女,也是最好的“闺蜜”。
童年时,在别的小朋友眼里,我的母亲是位有名的艺术家,因此他们都很羡慕我,我却偷偷地羡慕他们。那时我的理想妈妈,是一位能让我随时撒娇的妈妈,也是一个能在生活上细致照顾我的妈妈。但我的母亲总是很忙,同时又是个不折不扣的“严母”。母亲对我的期望值很高,因此对我显得过于严格,有时甚至让幼小的我觉得她有些不近人情,因此就有点怕母亲。那时候我比较胖,母亲怕我有肥胖症,带我看过很多医生。她为了防止我发胖,总是不许我多吃零食,特别盯着我不许吃巧克力,必须严格按她给的食谱吃饭。在学业上,母亲把我的日程安排得很满,我从5 岁半开始练习弹钢琴、学习舞蹈,上小学后每周末跟老师学习唐诗宋词、英文课程。有几次我生病了,她一边给我洗漱,还一边让我背拼音,一点儿也不放松。我练琴时经常被骂得直掉眼泪;考试得了96 分也得不到妈妈的表扬,还被问那4 分扣在了哪里;她帮我复习功课时,着急了还“骂”我笨……我小时候甚至怀疑,这真是我亲妈吗?

本文作者儿时与母亲的合影
童年时有个小插曲让我记忆深刻。那时的我非常淘气,总是喜欢和小朋友在院子里疯玩。有一次,我从很高的台阶上摔下来,把膝盖磕破了,流了不少血。当时母亲带我到中央歌舞团的医务室治疗,医生用水清洗我的伤口,母亲却一再要求医生用碘酒。医生觉得会比较疼,怕我忍受不了。但母亲坚持这样做,她认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毒,避免感染。晚上,我以为我的膝盖受伤了,可以偷懒不练钢琴了,谁知母亲一点儿不“可怜”我,到了规定的练琴时间照样监督我练琴,还说定好的日程不能轻易改变,要求也一点儿不能降低,小手指翘了,就还要“打手”。当时,我心里很是不满。但现在想来,这件事体现了母亲独有的教育我的方式。母亲关心我的身体,坚持要彻底消毒伤口,以避免创伤给我的身体造成其他的影响。同时,母亲也不因为我的身体情况而溺爱我,依旧对我严格要求,意图培养我坚忍不拔的意志。
不过,母亲虽然对我严格,但她也很民主,她经常鼓励我表达对人和事物的看法。每次母亲带我去看她的演出,回来就一定让我给她的表演打分,认真听我的点评。后来,我也是她文章的第一读者。她经常学我的语调重复我对她的评价:“妈妈,我觉得您今天的表演不够酣畅……”我们家中的气氛一直非常自由。我高中毕业就希望能去美国读大学本科,她和父亲都很支持。母亲一直鼓励我自由地追求自己的梦想,不给自己设限,是她让我相信我的未来有无限可能。
我有一个大大的旅行包,里面满满当当地装着我留学期间父母与我之间往来的书信。当时是90年代初期,没有如今这种便捷的通讯条件,所以我大部分的零花钱都用来和父母打越洋电话了,电话里说不完的就写在信里。每一封母亲写给我的信的开头都是“亲爱的蕾”,信尾也都会写上“妈妈爱你和想你”。那时我一个17 岁的女孩,只身来到千里之外的美国,十分想家,我每次看到父母的信都会哭。后来,等父母的信成为我留学生活中的精神寄托。信里点点滴滴都有父母的爱、期许和关心。现在的我偶尔拿出来看看,还是非常感动。

2010年,资华筠先生与她的博士生合影
回味从前,我很感谢母亲在我儿童时期是个严母。她从小培养了我良好的学习习惯,她教导了我去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教会我坚持、保持如一的标准,教会我要过自律的生活……如果没有这些理念的支撑,我在留学期间和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也不会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也不会成就今天的我。她的民主,给予了我自由的空间,培养了我对事物的好奇心,这大概就是所谓“养成”教育吧。她还启发我从小要拥有发现美的眼睛,在人生旅途中不断自我唤醒、激发、联想、创造;告诉我作为女性不仅要追求美,更要自尊、自强,拥有独立的价值理念,坚持追求和实现自己的梦想。一直到现在,我在做事情时还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母亲的话,以及母亲教导我的点点滴滴。
在我成年以后,母亲越来越像一个慈母了。她很开明,我们相处得如同朋友,可以随时随地像“闺蜜”一样聊天,可以分享彼此的各种小秘密,坦诚彼此的意见、观点。我有时问她:“为什么您小时候对我那么严厉,现在又对我这么宽容?”母亲回答说:“我那时要磨砺的是你的品质,要培养你的学习习惯。有了这些做基础,现在的你完全可以把握自己的人生。”我的“闺蜜”母亲非常可爱,我穿的衣服、我拿的手袋都会引起她的兴趣。她常常问我:“这件衣服也适合我穿么?”“你这个手袋好看,我有时出席场合也可以拿拿,先给我用吧。”每次出席重要活动,母亲也会在穿戴方面征求我的意见,我是她的小“造型师”。每年生日,母亲都会让父亲包个大红包给我。记得有一次我过生日前,正在海外出差,看到一只手镯,很是喜欢。正好母亲打电话来,知道我的位置后,母亲说:“你买吧,回来我给你报账,算我送你的生日礼物!”之后每逢生日,我都会戴上这只手镯。只要戴上它,我就能够感受到母亲对我沉甸甸的爱。我出差频繁,总在天上飞来飞去。经常飞机在机场刚落地的那一刻,我就会接到母亲的电话。我在外工作时,也会接到母亲的短信,关心我的身体和工作进展。她总是盼着我能早点回家。在我从职业经理人转换到自主创业的过程中,母亲给了我各种支持,鼓励我跟着自己的内心走,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她常常用我小时候学的李白《将进酒》里的诗句鼓励我:“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她总是说:“没事,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妈妈都永远支持你!”当我在事业上取得一些小成绩时,母亲总是很开心地同我分享喜悦。听父亲说,母亲也经常在背后表扬我,不在我面前说是为了不让我太过骄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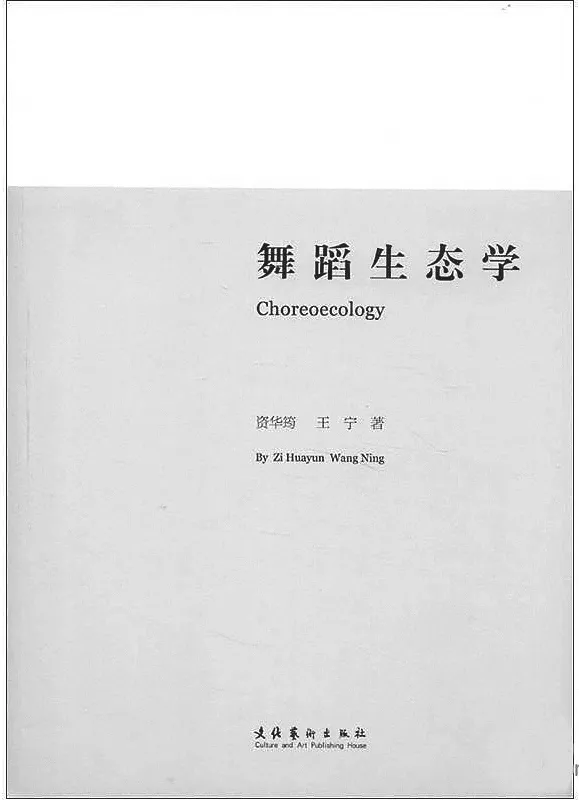
资华筠、王宁著:《舞蹈生态学》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也开始逐渐认识了家庭之外的母亲。我发现母亲对我严格的教导来源于她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而她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则来源于她对艺术、对学术孜孜不倦的追求。对于母亲来讲,艺术就是一切,即便是她罹患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之后,也依然坚守自己的梦想。
母亲是一名舞蹈表演艺术家,在51岁的时候,她接了吴晓邦先生的班,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开始从事学术理论研究。她就职演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不是来上任,而是来上学的。相信只要自己想学,任何时候都不晚。”母亲认为舞蹈学科的本体研究基础理论薄弱,所以自己要在学术上“啃硬骨头”。因此,母亲以自己多年来在舞蹈实践中的困惑和思考为基础,在语言学家、自然科学家的帮助下,从研究舞蹈之生成、发展与其诸多环境因素的关系出发,选择了舞蹈生态学这一课题进行研究。在母亲的努力下,她于1991年出版《舞蹈生态学导论》。1999年母亲卸任舞蹈研究所所长以后,仍主持过国家、院级重点课题。2010年,母亲荣膺中国艺术研究院首届终身研究员,成为当时舞蹈界唯一的终身研究员。但母亲并未止步于此,2012年她又推出了全新修订版的《舞蹈生态学》。《舞蹈生态学》在研究方法论上为舞蹈学界作出了重要贡献,把舞蹈理论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具有开创性和开拓性。这门新兴学科也因此得到广大舞界和学界同仁的认可。正如母亲在《舞蹈生态学》发布会上的发言里所说:“这本专著可以说是我毕生实践积累和思考研究的成果。舞蹈生态学研究是我从舞蹈演员走上学术研究岗位的一个艺术研究课题,它缘起于我30年表演各种民族舞蹈的经验和困惑。《导论》出版于1991年,虽然很不成熟,但得到了各科专家的帮助指导,令我终身受益。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实践检验,得到舞界、学界的认可,我自己的思考也日渐成熟,决定重新撰写舞蹈生态学……由于患白血病8年,白内障日趋严重又不宜手术,因此三年多的写作是在与‘双白病’做斗争中进行的,一度靠定期住院输血维生。身体衰弱不支与思维的空前活跃,奔涌形成反差,是信念和友情支持我坚持下来……舞蹈学科的建设任重道远,让我们以高度的紧迫感和坚定的信念为之共同奋斗!”每每想到母亲的发言,我就会想起我陪伴母亲度过的病中时光,也能想起她在病中也从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的坚韧精神。
母亲与慢粒性白血病抗争的十年间,主治医生一直提醒她不能过于劳累,也总叮嘱我要监督母亲好好休息。作为女儿,我也希望母亲可以更长久地陪伴在我身边,有更多时间一起去分享简单的亲情时光。我觉得她在事业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不用再那么较真地为事业拼搏。但母亲有她自己的追求和信仰,她对艺术奥妙永不止息的探寻,她的纯粹、勤奋和顽强不息的精神感动了我,我也开始全力支持她的工作。我经常帮她整理电脑里的文件,帮她发送电子邮件。为避免母亲用眼过度,我会随时帮她念一些手机里的短信。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更加理解母亲,心疼母亲。她因为免疫力低和供血不足,眼睛常常出血,还一度感染病毒性神经炎,非常痛苦,但她一直坚持工作。她的坚持既是出于她生病后对生命的珍惜,更是出于她对舞蹈学科建设的激情和信念。这是她的选择、她的追求,她愿意为之奋斗,让生命更加璀璨。
同时,患病并没有使母亲停下追求的脚步,反而使她本身就具有的助人之心更加热忱了。母亲罹患慢粒性白血病后,由于年龄关系,不能采取移植骨髓的方法彻底治疗,她却鼓励我给红十字会捐赠骨髓样本,希望我的骨髓可以帮助到其他需要帮助的人。母亲就是这样的人,从小就鼓励我帮助他人,把好东西分享给别的小朋友,此后也一直支持我做公益活动。母亲曾经是中国红十字会的理事,我刚刚参加工作有了自己的收入,她就引导我和她一起支持“春蕾计划”,我们俩一直资助四川贫困山区的两个女孩上学,直到她们高中毕业。我在北京举办帮助湘西贫困地区年轻妈妈们的公益活动时,母亲也给予了我最大的支持。2008年,我参与策划了一项公益活动。母亲那时虽然已经生病,却仍然亲临现场。汶川地震后,母亲第一时间捐款,并且主动提出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人的保护问题。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和“非遗”专家,母亲多次强调非物质遗产保护中,最为关键的一环便是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在地震后,母亲第一时间致电四川省文化局副局长杨莉,向她询问羌族非遗传承人的情况,建议震后应关注羌族文化传承人保护问题。母亲还在2009年9月初亲自到四川汶川映秀镇看望羌族民间艺人、非遗传人。在她的倾心帮助下,羌族文化传承人纪实录的项目得以在文化部和国家非遗保护中心的关注、支持下,论证、立项并获得专项经费。母亲在担任第五届至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的30年间,一贯关心民生及弱势群体。《人民政协报》曾以“大侠资华筠”为题在头版刊发报道她的文章。母亲的很多优秀提案都被收录在册,比如,母亲建议为见义勇为立法,在天安门广场为普通民众修建公共厕所,在奥运会前呼吁要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她一生助人无数,为我树立了真正的榜样,母亲教会了我心中要有大爱,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母亲指导博士生和博士后的工作也大都是在她生病期间完成的,她把每个学生看得都很重要,为每个学生都操着心。我很少陪母亲参加学术活动,只有两次,由于母亲身体不好,我必须陪同她参加。一次是2014年夏天母亲的最后一个博士生答辩会。当时她的白血病已经向急性发展,血小板急剧下降,但她坚持一定要先完成学生的答辩会才肯住院治疗。她说学生比天大。另外一次就是2014年11月5日,《舞蹈生态学》获得第九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特等奖,我陪同母亲参加当代中国文艺论坛及颁奖典礼。那时母亲非常高兴,特别跟主治医生请假,我便陪同母亲赶赴苏州参加典礼。因为她当时血液的各项指标都很低,血液循环又不好,走路都有些困难,但母亲一贯好强,她坚持不坐轮椅,也不要我扶她上台。母亲在台上说:“我们都是艺术洪流中的一滴水,力求是纯净的,是真切的,是优秀的……” 当时坐在台下的我,看着母亲,激动又骄傲。母亲的情怀和精神永远鼓励着我,不断追求向上,在人生的任何时候,都期待着能遇到更好的自己。从苏州领奖回来后,母亲因病情急性发作再度入院,一度抢救闯过一关,各项体征也平稳了。可谁知,病势又有反复,最终人力不可逆转。那天,我陪了母亲整个白天,临时需要离开医院去办事情,母亲摸着我的手说:“我没事,你走吧,晚上在家好好休息,明天再来。”我放心不下,晚上又回到病房,看到母亲在特护的协助下坐在床上吃东西,她让我回家,还跟我飞吻……那是母亲昏迷和离别前跟我的最后互动。

汶川地震后,资华筠前往震区看望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2010年,与父母及来宾在资华筠舞蹈艺术生涯60 周年庆典现场合影

母女情深
斯人已逝,但关于母亲的记忆却愈发清晰。我与母亲共同经历的点点滴滴,都被照片定格了下来。每当我思念母亲的时候,我就会看看她的照片,尤其是我与她共同拍摄的照片。记得我在留学期间的第一次寒假,回国看望父母,母亲有好几个晚上跟我睡在一张床上,紧紧地搂着我。那个寒假我们拍了一张紧紧拥抱在一起的合影,这张照片后来还收录在母亲艺术生涯60 周年纪念册《甲子归哺》中,题为“母女情深”。母亲在给我的那本册子扉页上写下:“To Leilei, love you forever, mom 妈妈永远爱你!”多希望时光永远定格在那一刻!今天我又像往常一样在母亲的照片前放上一束她喜欢的鲜花,照片里的她对我宠爱地微笑着,我心中感觉暖暖的。母亲给予我的爱会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陪伴着我,让我永不孤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