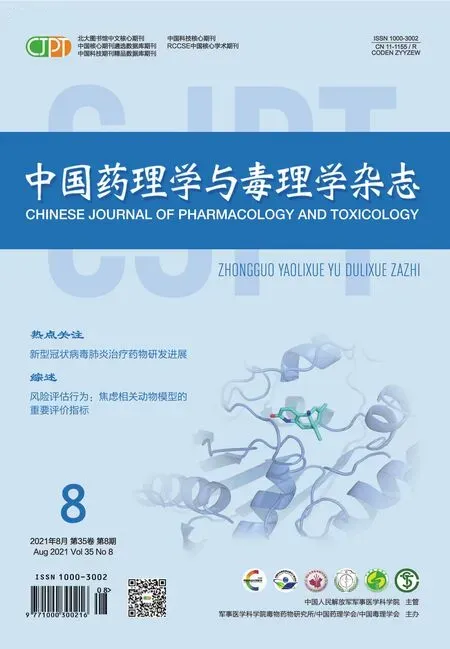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潜在靶点研究进度
2021-03-28谢冠博
谢冠博,韩 笑,吴 宁,李 锦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毒物药物研究所,抗毒药物与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神经精神药理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50)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是一种个体因受到超常的威胁性、灾难性创伤事件的刺激,从而导致的延迟出现并长期持续的精神障碍。PTSD症状主要包括创伤后恐惧体验的长时间反复出现(闪回)、持续回避创伤事件相关的刺激和警觉性增高等。PTSD已成为重大灾难性事件后发病率最高的精神类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和唐山大地震后PTSD的患病率平均为10%,乌鲁木齐特大爆炸事故后PTSD的发生率高达78.6%[1-2]。在这次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大疫情中,Lancet Psychiatry发表了对冠状病毒肺炎导致的PTSD的研究,报道其患病率为32.2%[3]。我国新冠疫情期间,中学生PTSD症状群筛查总阳性率为10.6%[4]。PTSD相关症状严重影响着患者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而其与抑郁、焦虑和药物成瘾等其他精神类疾病的共患病率高达约50%[5],使得PTSD成为一种重大精神类疾患,给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安全隐患。遗憾的是,目前临床尚无抗PTSD的特效药,美国FDA批准的2个临床治疗PTSD的一线治疗药物(舍曲林和帕罗西汀)均为5-羟色胺重摄取抑制剂类(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SRI)抗抑郁药,存在有效率不高(<60%)、起效延迟和不良反应严重等问题[6]。为此,深入研究PTSD的发病机制、寻找新的潜在治疗靶点、探究新的治疗策略,对提高PTSD的治疗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阐述相关神经递质、内源性大麻素系统(endocannabinoid system,ECS)、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ypothalamus-pituitary-adrenal,HPA)轴和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等与PTSD的关系入手,对治疗PTSD的潜在靶点进行综述,以期为PTSD治疗药物的研发提供新思路。
1 与PTSD相关的神经递质
1.1 5-羟色胺
5-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5-HT)是脑内一种重要的单胺类神经递质,参与调节抑郁、焦虑、情感障碍等多种精神类疾病,其与PTSD的关系也被广泛研究[7]。战后患有PTSD士兵的血浆中5-HT浓度低于健康对照组[8]。动物研究也发现,在单一延长刺激模型(single prolonged stress,SPS)中,PTSD大鼠前额叶皮质的5-HT及其代谢产物5-羟吲哚乙酸水平显著降低[9]。目前临床上用于治疗PTSD的SSRI类药物是通过抑制5-HT转运体(serotonin transporter,5-HTT),升高突触间隙的5-HT水平达到治疗目的。但是这类药物普遍存在起效延迟、治疗效率低、引发认知功能障碍和性功能障碍等问题,于是一些研究转向了针对5-HT受体参与机制的研究。5-HT受体有7种亚型,包括5-HT1(5-HT1A,5-HT1B,5-HT1D,5-HT1E和 5-HT1F受体),5-HT2(5-HT2A,5-HT2B和5-HT2C受体),5-HT3,5-HT4,5-HT5(5-HT5A和 5-HT5B受 体),5-HT6和5-HT7受体。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对于5-HT受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5-HT1,5-HT2,5-HT3和 5-HT6受体亚型。目前研究认为,5-HT1,5-HT2和5-HT3受体与焦虑和恐惧等情绪反应关系密切,5-HT6与认知相关[10]。临床研究表明,与安慰剂联合心理疗法相比,采用3,4-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3,4-methylenedioxymethamphetamine,MDMA)(间接激活5-HT2A受体)联合心理疗法能显著降低PTSD患者的PTSD评分,表现出安全有效的抗PTSD作用,目前此疗法已处于Ⅲ期临床试验阶段[11];非临床研究发现,选择性5-HT重摄取抑制剂、5-HT1A受体部分激动剂和5-HT6受体完全激动剂盐酸羟哌吡酮(代号:YL-0919)在2种PTSD动物模型(大鼠时间依赖敏感化模型和小鼠短暂电击模型)中均能显著改善PTSD样行为,并增强PTSD大鼠的认知功能[12];低剂量的5-HT2A受体激动剂赛洛西宾(psilocybin)能促进条件性恐惧记忆的消退[13];PTSD大鼠背侧海马注射选择性5-HT3受体激动剂SR57227,能剂量依赖性地促进情景恐惧记忆的消退[14]。虽单纯抑制5-HTT的药物治疗效果不够理想,但5-HT不同受体亚型可能成为PTSD的治疗靶点。
1.2 多巴胺
多巴胺(dopamine,DA)是脑内含量最丰富的儿茶酚胺类神经递质,参与调控奖赏、动机、运动和情感等多种生理活动,与精神分裂症和药物成瘾等精神类疾病密切相关。DA作用于脑内DA受体发挥作用,DA受体包括D1样(D1和D5)和D2样(D2,D3和D4)受体。文献报道,DA与PTSD患者的核心症状——恐惧体验长时间反复出现相关,且D2和D3受体基因突变与PTSD高发病率相关[15]。临床研究发现,在观看创伤性视频后,PTSD患者脑脊液中DA的主要代谢产物高香草酸浓度下降[16],DA受体激动剂KB220Z能显著改善PTSD患者的噩梦症状[17]。非临床研究发现,急性足底电击可显著增加大鼠前额叶皮质DA神经元的活动[18],这种急性增高可能是机体处于自我保护状态的一种代偿性增高。而在经历一系列创伤性刺激一段时间后,大鼠前额叶皮质和杏仁核DA水平显著下降[19]。在小鼠SPS模型中,全身给予选择性DA受体激动剂(激活D2和D3受体)罗替戈汀和普拉克索能显著改善小鼠PTSD样症状[20]。全身给予第二代抗精神病药阿立哌唑(D2受体部分激动剂)能促进PTSD模型小鼠恐惧记忆的消退,且该作用与增加PTSD模型小鼠杏仁核DA水平有关[21]。临床及非临床研究表明,DA参与了PTSD病理过程,提示可以DA系统为靶点,通过提高DA水平或增强DA作用,进而发挥抗PTSD作用。
1.3 谷氨酸和 γ-氨基丁酸
谷氨酸(glutamic acid,Glu)能神经元是脑内主要的兴奋性神经元,γ-氨基丁酸(γ-aminobutyric acid,GABA)能神经元是脑内主要的抑制性神经元,在正常状态下两者在脑内保持动态平衡。应激状态下,脑内不同脑区(如海马和杏仁核)Glu释放增加[22],导致脑内Glu与GABA之间的调节失衡,进而引发各种精神障碍[23]。研究发现,Glu系统的激活对PTSD的发生发展(恐惧记忆的形成和再巩固)过程非常重要[24]。在此过程中,Glu是主管编码长时程记忆的关键神经递质。Meyerhoff等[25]发现,PTSD患者的右侧海马Glu高表达,而右侧的前脑岛GABA低表达。动物实验结果表明,采用谷氨酸受体N-甲基-D-天冬氨酸(N-methyl-D-aspartic acid,NMDA)非竞争性拮抗剂氯胺酮能显著缓解大鼠的 PTSD样行为[26]。Li等[27]研究结果表明,在小鼠短暂电击模型中,给予能增强GABA能神经传递功能的药物(苯二氮类药物地西泮和抗癫痫药丙戊酸钠),可显著抑制小鼠的僵住行为和焦虑行为。上述结果表明,靶向Glu能神经元(即下调Glu水平)或GABA能神经元(即上调GABA水平)的药物,可能具有治疗PTSD的作用。
1.4 去甲肾上腺素
去甲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NE)参与机体的恐惧和焦虑反应,PTSD患者过度警觉、易激惹症状与NE活性增高有关[28]。临床研究表明,PTSD的持续性和严重性与经受创伤性刺激时NE能神经元长时间激活有关,在经受创伤经历刺激后,给予β-肾上腺素受体拮抗剂普萘洛尔能降低罹患PTSD的风险[29]。动物研究表明,在听觉条件性恐惧实验中,大鼠恐惧记忆提取后,杏仁核单次给予异丙肾上腺素能增强恐惧记忆的再巩固和抑制恐惧记忆的消退,而杏仁核给予普萘洛尔能阻断异丙肾上腺素致恐惧记忆的增强[30]。提示抑制中枢NE能神经元过度活跃的药物,包括降低NE释放的药物(如α2受体激动剂可乐定)和阻断突触后肾上腺素受体的药物(如α1受体拮抗剂哌拉唑嗪或β受体拮抗剂普萘洛尔)等,可能具有治疗PTSD的作用。
1.5 乙酰胆碱
乙酰胆碱(acetylcholine,ACh)是脑内最先被发现的神经递质之一。文献报道,胆碱能神经元能调控巴浦洛夫条件性恐惧的学习和消退[31]。非临床研究表明,在电刺激训练前,全身给予毒蕈碱型受体的特异性拮抗剂东莨菪碱能减轻啮齿类动物条件恐惧记忆的获得,且在重新暴露于该环境时能显著降低其恐惧反应[32]。在电击刺激后,海马或杏仁核局部注射东莨菪碱,72 h后能减轻大鼠恐惧反应;然而,全身或局部脑区给予烟碱型受体特异性拮抗剂不能减轻小鼠的恐惧反应,可能是因为与条件恐惧记忆相关的内源性ACh是通过毒蕈碱型受体介导的[31]。在PTSD大鼠模型中,在单一连续刺激1 d后,乙酰胆碱酯酶(acetylcholinesterase,AChE)活性升高使Ach减少,从而使恐惧记忆降低,而7 d后AChE活性降低,ACh增多,恐惧记忆增强[33]。上述结果表明,毒蕈碱型受体拮抗剂或靶向AChE可能是抗PTSD的治疗策略。
2 PTSD与内源性大麻系统
内源性大麻素系统(endogenous cannabinoid system,ECS)直到1992年才被发现,它参与众多精神类疾病的发生发展,包括焦虑、成瘾和抑郁症等。该系统由3个部分组成:内源性大麻素,大麻素受体(cannabinoid receptor,CB)及产生和分解内源性大麻素的酶。内源性大麻素主要包括N-花生四烯酰乙醇胺(N-arachidonoylethanolamide anandamide,AEA)和2-花生四烯酰甘油(2-arachidonoylglycerol,2-AG)。CB有CB1和CB2 2种亚型。临床研究发现,PTSD患者血液中AEA和2-AG水平低下[34],2014年报道显示,PTSD患者可通过吸食大麻缓解症状[35];许多患有PTSD的退伍军人也使用大麻或其衍生物来控制PTSD症状[36]。动物实验结果表明,大麻二酚可显著抑制PTSD模型小鼠恐惧记忆的提取[26],还可促进大鼠恐惧记忆的消退[37]。采用CB1受体激动剂局部注射到与恐惧记忆密切相关的脑区(杏仁核、前额叶皮质和海马),可损害啮齿类动物恐惧记忆的获得和提取,增强恐惧记忆的消退,进而发挥抗PTSD样作用[37-38];采用AEA降解抑制剂能减少啮齿类动物的恐惧行为[39]。上述证据均表明,ECS参与了PTSD的病理过程,作用于ECS的化合物如CB1受体激动剂和AEA降解抑制剂等可能成为抗PTSD的潜在靶点。
3 PTSD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
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HPA)轴是神经内分泌的系统,调控机体应激反应,其与PTSD的关系很早就被关注和研究[40-41]。HPA轴涉及的神经内分泌激素包括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ortic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CRH)、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ACTH)和以皮质醇为主的糖皮质激素(glucocorticoid,GC),GC可与GC受体(glucocorticoid receptor,GR)结合而发挥作用。临床研究表明,PTSD患者HPA轴功能紊乱,血液和尿液中皮质醇浓度降低,CRH水平增高,淋巴细胞中GR表达增加,GR呈高敏感性状态。GR的敏感性增加会导致GC对HPA轴的负反馈抑制增强,最终表现为体内皮质醇持续低下的状态[42]。临床试验表明,创伤后立即给予低浓度皮质醇,能降低PTSD的发病率或者减轻PTSD的症状[43]。同样,动物实验表明,大鼠创伤刺激后1 h给予皮质酮,能显著降低PTSD样行为(降低恐惧记忆提取,促进恐惧记忆消退)[44]。给予GR拮抗剂RU40555能抑制PTSD模型大鼠的情景恐惧反应和长时程增强损伤[45]。上述证据表明,调控HPA轴功能(如给予皮质醇和GR拮抗剂等)有望成为治疗PTSD的潜在靶点。
4 PTSD与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s,BDNF)是体内含量最多的神经营养因子,BDNF与其特异性酪氨酸激酶受体B(tyrosine kinase receptor B,TrkB)结合后,参与调控神经突触可塑性及神经元存活和死亡。文献报道,BDNF-TrkB通路与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和强迫症等多种精神类疾病密切相关,且在PTSD发生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该通路的改变会影响情境恐惧记忆的的获得和消退,这可能成为PTSD发生的原因[46]。临床研究表明,PTSD患者血液中BDNF水平显著低于健康者,且BDNF可作为PTSD患者诊断的潜在生物学标志物[47-48]。非临床研究表明,PTSD模型大鼠海马和皮质的BDNF水平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49-50]。全身给予小分子TrkB激动剂7,8-二羟基黄酮能促进束缚应激诱导的PTSD模型小鼠恐惧记忆的消退[46]。以上研究结果表明,靶向BDNF-TrkB通路、调控BDNF水平或将成为治疗PTSD的潜在靶点。
5 其他
神经肽Y(neuropeptide Y,NPY)是广泛存在于中枢和外周并维持内环境稳态的激素,与应激反应相关,通过与其受体(Y受体)结合发挥作用。临床研究表明,PTSD患者血浆和脑脊液中NPY水平显著低于健康者,而抗精神病药物能增加患者的NPY水平[51]。非临床研究表明,在SPS模型中,PTSD大鼠鼻腔内给予NPY能防止高警觉反应(PTSD的核心症状之一)[52];PTSD大鼠的基底外侧杏仁核给予Y1受体激动剂Leu31具有抗PTSD的作用,表现在促进PTSD大鼠恐惧记忆的消退、降低惊吓反应行为[53]。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作用于NPY系统的药物(增加NPY表达)可能具有抗PTSD的作用。
胍丁胺作为一种内源性活性物质以及候选神经调质,具有重要生理学功能,并且外源性胍丁胺具有抗抑郁、抗焦虑和改善精神分裂症的认知障碍症状等作用[54]。有研究表明,胍丁胺可能参与应激反应和焦虑相关精神障碍的神经生物学调节机制[55]。非临床研究表明,在大鼠时间依赖性敏感化模型和小鼠短暂电击2种PTSD常用模型中,胍丁胺可抑制损害恐惧记忆的获得,具有预防PTSD形成的作用[56-57]。提示胍丁胺有可能成为治疗PTSD的潜在药物。但其对已形成的PTSD是否具有治疗作用,如是否促进损害恐惧记忆再巩固或恐惧记忆消退,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6 结语
PTSD是重大创伤事件后发病率最高的精神类疾病,人们对其认识较晚,对其病理机制和治疗药物的研究相对滞后,目前尚缺少安全高效的治疗药物。PTSD病理机制不仅涉及多种神经递质和激素系统功能紊乱,还涉及神经营养因子、神经肽异常等。本文对与PTSD发生发展相关的神经生物学部分因素进行概括,在与PTSD相关的神经递质中,虽然靶向5-HTT的药物效果不佳,但靶向5-HT受体其他亚型具有改善PTSD相关症状的作用;同样,增强DA能神经元功能、调控脑内Glu和GABA水平的动态平衡、降低NE能神经元功能等均具有抗PTSD的作用;基于PTSD病理机制之一——HPA轴负反馈增强,调控HPA轴恢复正常状态可能是PTSD的治疗策略之一;上调ECS水平以及BDNFTrkB通路功能同样在改善PTSD的相关症状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另外,这些潜在靶点可能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协调,最终起到预防或治疗PTSD的作用。但是,目前关于PTSD的发病机制认识较少,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其发病机制,探索新的治疗靶点,同时基于现有的假说和研究结果,结合光遗传学、化学遗传学、在体电生理等神经生物学技术,开发新的抗PTSD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