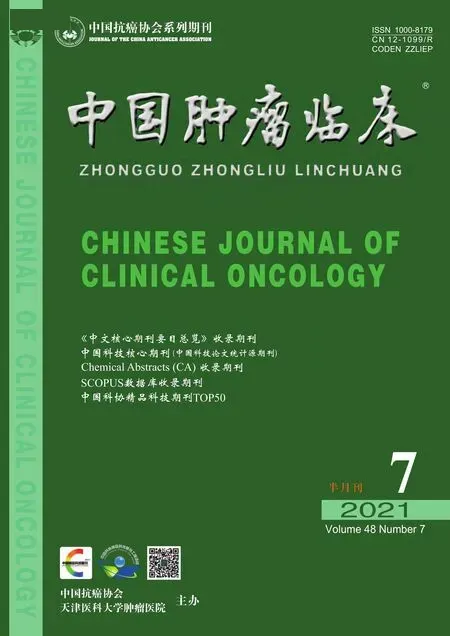调控固有免疫防治肺癌转移的研究进展*
2021-03-27于盼姜怡阙祖俊罗斌田建辉
于盼 姜怡 阙祖俊 罗斌 田建辉
最新研究提示,2020年肺癌导致死亡在所有恶性肿瘤中的占比下降至22%[1],这得益于20年来肿瘤综合治疗手段如手术、放化疗、分子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飞速发展。尽管如此,肺癌仍是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而复发转移是导致肺癌患者预后不良的主要因素,转移防治成为降低肺癌患者死亡率和延长生存期的关键。目前,仍缺乏广为接受的转移防治理论与高效的防控手段。免疫治疗的出现为肺癌治疗领域开启了新的篇章,多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ity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的临床应用使部分肺癌患者获益,但仍存在大量对免疫靶向治疗不敏感或发生免疫耐受的肺癌患者,制约了肺癌防治效率的进一步提高。研究发现[2],在肺癌肿瘤组织中,T 细胞和B 细胞占主导地位,分别占浸润性免疫细胞的47%和16%,固有免疫细胞占比相对较少,其中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NK)4.5%、巨噬细胞4.7%、粒细胞和单核细胞9.3%、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s,DCs)2.1%、肥大细胞(mast cell,MC)1.4%,尤其是NK 细胞和巨噬细胞占比明显低于非肿瘤肺组织,提示固有免疫细胞可能与肺癌转移相关。
1 固有免疫紊乱与肺癌转移密切相关
固有免疫紊乱在肺癌复发转移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临床研究发现,肺癌患者外周血中的单核细胞、中性粒细胞以及细胞毒受体转录水平与患者的总生存期相关,且肺癌患者与健康人的NK细胞水平差异尤为显著。与健康人相比,早期肺癌患者外周血中NK 细胞数量较高,杀伤型CD56dim亚群、CD16和NCR水平较高,表明癌细胞激活NK细胞发挥免疫监视作用[3],随着病情进展,NK细胞无法完成免疫清除和免疫平衡,随即发生免疫逃逸导致转移。原发灶免疫细胞的鉴定分析提示,高比例的CD68+巨噬细胞/单核细胞与肺癌患者的低死亡风险存在相关性,且巨噬细胞含量超过4.5%的患者生存期显著延长[4]。固有免疫细胞还可影响转移前微环境的形成,原发灶肿瘤细胞通过各种髓系祖细胞群体、细胞因子、可溶性因子、细胞外囊泡介导次级器官重编程,招募中性粒细胞、肺泡巨噬细胞等,为肺癌转移创造“肥沃的土壤”[5]。由此可见,固有免疫系统在转移发生中具有重要作用,对其开展深入研究有望为转移防控提供创新性思路。
2 固有免疫细胞的肿瘤免疫机制
固有免疫应答是免疫系统激活的第一步,通过非特异性识别激活对癌细胞的即时反应。固有免疫细胞主要包括NK细胞、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DCs、MC、固有类淋巴细胞(innate-like lymphocyte,ILL)和天然淋巴样细胞(innate lymphoid cell,ILC)等。
2.1 NK细胞
NK 细胞是固有免疫系统的关键效应细胞,在肺癌及转移中发挥重要的免疫监视和免疫清除作用,其细胞毒性由激活性受体和抑制性受体信号之间的平衡决定[6]。激活性受体主要包括NKG2D、NCRs(NKp46/NCR1、NKp44/NCR2、NKp30/NCR3)等,可识别肿瘤细胞表面MICA/B、ULBP 等配体;抑制性受体主要有NKG2A、KIRs 等,识别HLE-A 等配体[7]。NK细胞主要通过下述几种途径杀伤靶细胞:1)抗体依赖的细胞介导的细胞毒作用(antibody-dependent cell-mediated cytotoxicity,ADCC),由CD16 介导识别肿瘤细胞表面CD19,触发细胞毒作用[8];2)释放穿孔素、颗粒酶,穿孔素在肿瘤细胞膜表面形成孔道,颗粒酶经过这些孔道进入细胞,进而溶解肿瘤细胞[9];3)死亡受体介导途径,形成Fas-FasL、TRAILTRAILR 激活casepase 3 死亡级联信号,诱导细胞凋亡;4)释放IFN-γ、TNF-α等细胞因子,抑制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s,Treg)、髓源性抑制细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MDSC)等抑制性免疫细胞,同时增强适应性免疫功能,直接或间接杀伤肿瘤细胞[10]。NK 细胞还存在转移特异性的免疫监视作用,对诱导上皮间质转化的A549 细胞具有更强的细胞毒敏感性[11]。
2.2 巨噬细胞
巨噬细胞是肺组织中最丰富的髓系细胞之一,由单核细胞分化而来,可分为肺泡巨噬细胞和间质巨噬细胞两类,在周围环境影响下极化为M1和M2两个亚群,其表型和功能截然不同,这种极化作用具有可塑性[5]。M1型巨噬细胞被IFN-γ、TNF-α等Ⅰ型细胞因子极化,可产生TNF-α、IL-1α/β、IL-6和COX-2,并大量表达NO以产生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表现出抗肿瘤活性。相反,M2型巨噬细胞受IL-10、IL-33及Ⅱ型细胞因子诱导,产生IL-10、TGF-β等,发挥免疫抑制作用[12]。巨噬细胞可由VEGF、CCL2、M-CSF和TGF-β等因子诱导进入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成为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r associated macrophage,TAM),是TME中含量最高的免疫细胞[13]。其中M2型TAM占主导地位,通过表达免疫抑制分子或招募Treg、MDSC等形成免疫抑制TME,可促进肿瘤细胞生长、血管生成和免疫逃逸,TAMs浸润增加与肺癌预后不良相关[14]。
2.3 单核细胞
单核细胞可分为经典的炎性单核细胞和非经典的巡逻单核细胞(patrolling monocytes,PMOs)。原发灶招募炎性单核细胞协助TAMs的浸润,从而发挥免疫抑制作用;而非经典的巡逻单核细胞具有吞噬和清除肺血管中介导转移的肿瘤细胞外泌体的作用[15]。PMOs可通过募集和激活NK细胞发挥免疫监视作用从而防止肺癌转移,研究发现缺乏PMOs小鼠的NK 细胞抑制性受体NKG2A/CD94 表达增加,激活性受体Ly49D表达减少[16]。由此可见,单核细胞并非直接与肿瘤细胞作用,而是通过与TAMs、NK 的交互作用影响免疫微环境。
2.4 中性粒细胞
中性粒细胞主要通过诱导肿瘤血管生成及免疫抑制促进肺癌转移,合成转移关键生长因子转铁蛋白,并调控抗肿瘤免疫细胞ROS 水平形成免疫抑制微环境从而促进肺癌转移[17]。中性粒细胞外猎网(neutrophil extracellular traps,NETs)是由细胞外中性粒细胞DNA 纤维组成的网络,能够结合肿瘤细胞以促进肺癌转移[18]。由肿瘤细胞招募浸润成为肿瘤相关中性粒细胞(tumor-associated nuetrophils,TANs),可经IFN-γ 和GM-CSF 诱导分化为粒细胞和抗原提呈细胞(antigen presenting cell,APC)的复合表型(CD11b+CD15hiCD10-CD16int/Low),交叉呈递肿瘤抗原从而增强T细胞的抗肿瘤免疫作用[19]。
2.5 DCs
DCs是协调抗肿瘤细胞免疫的关键APC,通过偶联MHC分子将肿瘤相关抗原(tumor-associated antigen,TAA)呈递给T 细胞,主要有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plasmacytoid dendritic cells,pDCs)、经典树突状细胞(classical dendritic cells,cDCs)、炎性树突状细胞(inflammatory dendritic cells,inf-DCs)亚群[20]。pDCs一方面分泌IFN-Ⅰ、IFN-α/β发挥抗肿瘤作用,另一方面分泌TGF-β、IL-10、IDO等抑制性因子并表达抑制性配体,抑制T细胞的杀伤作用;cDCs在激活CD8+T细胞抗原结合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是IL-12的强大来源,可显著增加化疗敏感性和细胞毒性T 淋巴细胞(cytotoxic T lymphocyte,CTL)的细胞毒作用;inf-DCs是一种特殊的亚型,在肺癌中的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21]。
2.6 MC
MC是变态反应的主要效应细胞,通过Toll样受体等启动即时免疫应答,释放促/抗炎介质、生长因子及共刺激分子等,可通过TNF-α诱导T细胞增殖,或表达HLADR发挥APC作用[22]。目前,MC与肿瘤细胞的作用机制尚未明确,有待进一步研究揭示。研究发现,肺癌细胞外泌体中的细胞因子可以增强MC的迁移能力,促进TNF-α、MCP-1的释放,发挥抗肿瘤作用;然而MC被激活后发生脱颗粒释放的类胰蛋白酶(tryptase)、PGE2、TGF-β、EGFR和IL-8等将影响血管生成、组织重塑和抑制免疫,有利于肺癌转移[23]。
2.7 固有类淋巴细胞
ILL 包括自然杀伤T 细胞(natural killer T cell,NKT)、γδT 细胞、B1 细胞和边缘区B 细胞。目前,肿瘤免疫相关的ILL 主要是NKT 细胞和γδT 细胞。CD1d 限制性T 细胞被称为NKT 细胞,对神经鞘糖脂Ag-α 半乳糖基神经酰胺(α-GalCer)具有强反应性,活化的NKT 表达穿孔素、颗粒酶、FasL 及TRAIL 等,表现出类似NK细胞的抗肿瘤细胞毒作用,同时激活M1型巨噬细胞和DCs以间接启动适应性免疫的抗肿瘤免疫应答[24]。γδT细胞具有独特的TCR结构,兼具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的特性,具有肿瘤细胞杀伤活性,并表达趋化因子受体,促进肿瘤细胞归巢,然而其抗肿瘤作用受到TME的调控[25]。
2.8 天然淋巴样细胞
ILC 是近年来新发现的固有免疫中独特的细胞类型,在调节TME的免疫反应中具有重要作用[26],主要可分为ILC1、ILC2 和ILC3 3 类,均具有抗/促肿瘤的双重作用。TME 中的TGF-β 可诱导NK 细胞转化为促血管生成和具有免疫耐受特征的ILC1,而ILC1又可分泌IFN-γ 从而发挥抗肿瘤作用;ILC2 通常被认为与MDSC 的免疫抑制功能有关,然而在IL-33 的作用下具有抗肿瘤免疫反应;ILC3 可产生IL-22、TNF-α 和IL-8 等促炎细胞因子,还可诱导间充质基质细胞表达ICAM-1和VCAM-1,从而促进白细胞浸润;不同类别的ILC 在特定的细胞因子诱导下可发生转化[27]。
3 固有免疫细胞在防治肺癌转移中的临床应用
大量研究显示,固有免疫细胞具有抗/促肺癌转移的双重作用,目前针对固有免疫细胞的临床应用多处于基础研究阶段。NK细胞和TAMs分别作为固有免疫中唯一的效应细胞和TME中含量最丰富的细胞,将是未来肿瘤免疫疗法的研究热点。此外,固有免疫细胞过继疗法、单克隆抗体、肿瘤疫苗等也为肺癌转移的免疫治疗带来了新的研究策略。而单核细胞、中性粒细胞、肥大细胞在肺癌转移固有免疫中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具有成为生物标记物的潜质。
3.1 靶向固有免疫细胞抑制肺癌转移
鉴于不同的固有免疫细胞分别具有抗/促肺癌转移的作用,当前针对固有免疫细胞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方向大致分为3类:1)促进抗肿瘤免疫细胞的激活从而增强抗肿瘤免疫应答作用,如细胞因子疗法;2)减少或阻断抑制性免疫细胞的招募和激活,间接增强效应细胞(CTL、NK)的细胞毒作用,如ICIs;3)过继细胞疗法,即在固有免疫细胞表面链接表面嵌合抗原受体,使其具有更强的靶向性,如CAR-NK。
现阶段,靶向NK细胞的免疫疗法在调控固有免疫预防肿瘤转移中占据主要地位,尤其在血液肿瘤中开展了大量临床试验,但在肺癌等实体瘤中的疗效仍有待研究[28]。IL-15 及其受体激动剂是目前肺癌临床应用安全性最高的细胞因子,以NK细胞为靶点的单克隆抗体如抗KIR(IPH2101,lirilumab)、抗NKG2A(monalizumab)等也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29]。最新研究显示,NK-92、CAR-NK 等细胞过继疗法可有效控制肺癌转移。针对γδT 和NKT 的过继细胞疗法对肺癌动物模型的肿瘤生长具有抑制作用,但临床疗效有限[30]。
TAMs与肿瘤浸润性CD8+T细胞的物理接触抑制了T细胞的抗肿瘤活性,因此抑制TAMs的介导作用(包括耗竭、重编程、靶向功能分子)是靶向TAMs防治肺癌转移的途径之一[31]。此外,利用封闭抗体阻断CCR2、CSF1R、IL-1β、MARCO可以减少TAMs的募集、存活、分化和极化,从而改善TME的免疫抑制状态[32]。DCs作为T细胞的重要APC,提高其抗原呈递能力、开发DCs疫苗是防治肺癌转移新策略,临床肺癌晚期患者应用个性化的肿瘤相关抗原mRNA转染的DCs疫苗后总体存活率较高,且未见不良反应[33]。
3.2 作为生物标记物评估肺癌预后
外周血中固有免疫细胞和相关因子的监测可为肺癌患者预后评估提供新思路。免疫治疗前检测外周血中NK 细胞活性可预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治疗反应,基线NK 活性与无进展生存期呈正相关,且敏感度达80%,特异性68.4%,是有效的免疫治疗预测工具[34]。肺癌患者的放疗疗效受到外周血中性粒细胞数目的影响,尽管放疗前的中性粒细胞比例与预后无关,然而中性粒细胞可增强对放疗的抵抗力[35]。tryptase+MC浸润是肺癌转移潜在的预后生物标志物,瘤内tryptase+MC 高密度与肺癌淋巴结转移显著相关,与总生存期、无进展生存期存在相关性[36]。可见固有免疫细胞具有成为肺癌转移生物标记物的潜力,但有待进一步研究。
4 结语与展望
肺癌转移导致的死亡人数常年位居所有恶性肿瘤之首,其主要原因是肺癌的复发转移未得到有效防治。目前,肺癌免疫治疗主要针对以T淋巴细胞为代表的适应性免疫,由于靶点蛋白表达的制约、自发性和获得性耐药的出现,以及较为严重的不良反应,靶向T细胞的免疫疗法治疗实体瘤疗效遭遇瓶颈,促使研究者们将重点开始转向固有免疫调控,研究发现免疫清除、免疫平衡和免疫逃逸组成了动态变化的免疫编辑过程,而固有免疫应答发生于病原体入侵的0~96 h,可见低效的固有免疫应答是导致免疫逃逸的重要原因之一[37],因此近年来肺癌免疫治疗的研究热点逐渐从适应性免疫向固有免疫转换。
NK 细胞作为固有免疫的唯一效应细胞,具有类似CD8+T 细胞的特性,且细胞毒作用更强,免疫原性更低,是固有免疫细胞中最具潜力的研究靶标[7,38]。相反,TAMs 作为TME 中占比最高的免疫抑制性细胞,有一定的促转移能力[13],未来亟需筛选关键信号通路和免疫抑制因子,研发抗体阻断剂,积极开展临床转化研究从而开发靶向TAMs 的抗肺癌转移免疫疗法。而其他固有免疫细胞由于存在不同表型或与CTL间的交互作用,兼具抗/促肺癌转移的作用,需进一步研究明确细胞间作用机制,进而开发高效的临床疗法。
研究发现肺癌患者早在根治术前已经发生远处器官的转移,其实质是体内潜伏的癌细胞和免疫功能代表的抑癌力量的动态博弈过程,在国医大师刘嘉湘“扶正治癌”学术思想指导下,田建辉提出“正虚伏毒”为肺癌转移的核心机制[39],其中“正虚”是以机体的免疫衰老、免疫逃逸为基础的免疫功能紊乱为主,而“伏毒”是潜伏在外周循环系统或转移靶器官的癌细胞(如循环肿瘤细胞、肿瘤干细胞、播散肿瘤细胞、休眠肿瘤细胞、衰老肿瘤细胞等)。当机体正气亏虚时,表现为免疫监视和免疫清除效率下降,正虚不能遏制伏毒,则潜伏的癌细胞失去制约,从休眠期进入增殖期,最终形成影像学可以检出的病灶而确诊为临床发病。课题组临床研究中发现肺癌患者外周血MDSC、Treg、循环肿瘤细胞(“伏毒”)是肺癌转移亚临床状态的重要因素,提示了固有免疫在转移中的重要作用。研究组建立了以世界首株可稳定传代的人肺腺癌循环肿瘤细胞系(CTC-TJH-01)为基础的转移特异性研究平台[40],发现调控NK细胞可抑制尾静脉注射CTCs 小鼠模型的肺转移率(数据待发表)。该平台已用于肿瘤免疫领域研究及新药筛选,期望提高肺癌转移研究的转化效率。
综上所述,肺癌转移仍然是制约肺癌总体防控效率的关键,由于转移的发生是机体“正气”和“伏毒”的相互制约过程。提示针对转移的研究要积极采用系统生物学思维和各种组学技术从更大尺度和更多维度揭示其时空演变规律。为此我们要传承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和以人为本思想,融合现代肿瘤免疫学的精华,创新肺癌转移的防治理论和研究体系,完善肺癌转移转化研究体系,不断提高肺癌转移的防控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