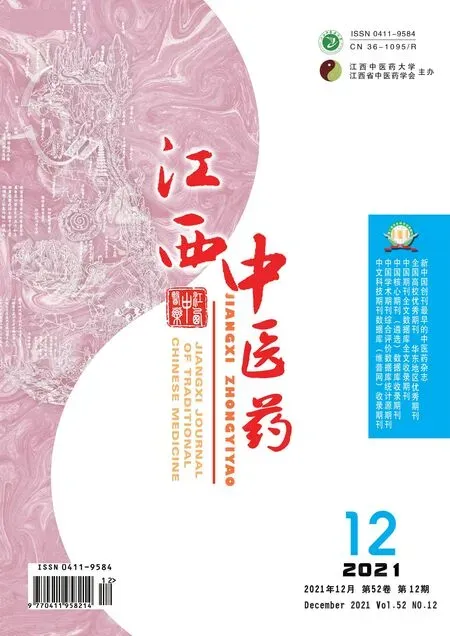魏江磊治疗痹证经验探析
2021-03-27夏振威魏江磊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上海0805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上海00
★ 夏振威 魏江磊(.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上海 0805;.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上海 00)
中医认为痹证是由风、寒、湿、热等外邪侵袭机体,闭阻经络,阻碍气血运行,导致筋骨、关节、肌肉等疼痛、重着、酸楚、麻木或关节屈伸不利、僵硬、肿大等症状的一类疾病;对应于现代医学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魏江磊教授是上海市名中医,师从国医大师任继学、颜德馨,擅于治疗临床疑难杂症,有多年治疗风湿顽痹患者的临床经验,且疗效确切,现对其经验探析如下。
1 病因病机
1.1 正气亏虚为本 《内经》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痹证患者,必有正气不足,风、寒、湿等外邪才有入侵之机;感邪后正邪交争,正气充盛能驱邪外出,而正气不足,邪气留恋胶着于筋骨肌肉之间,痹阻经络,脉道涩滞故而引起疼痛等各种症状。正如《类证治裁·痹证》曰:“诸痹良由营卫先虚,腠理不密,风寒湿乘虚内袭,正气为邪气所阻,不能宣行,因而留滞、气血凝涩,久而成痹。”经脉痹阻、气血不通畅日久,则脏腑失荣;正气亏虚若明显,邪实入里,可成脏腑痹,因此正气亏虚是痹病发生及病情演变的根本因素。
1.2 诸邪致痹,“瘀”邪为要 风、寒、湿、热、痰、瘀等邪气入侵留恋于肢体筋脉、关节、肌肉等处,致经络闭阻,不通则痛,是痹证的基本病机,因此可以说诸邪皆可致痹证,故有医家或从风、寒、湿,或从湿热,或从痰热等论治。王清任提出“痹证有瘀血”说,魏老师宗于此观点,认为痹病不管因何邪而起,从其影响气、血、津、液运行输布,闭阻经脉,致络脉瘀滞开始,瘀邪已是核心病理要素并贯穿始终[1]。这也与田雨、夏璇等诸多现代医家的认识不谋而合[2-5]。魏老师强调此瘀邪,不仅是脉络脏腑等组织中停滞的有形瘀血,更要注意血液运行迟缓,血流不畅的病理性的血瘀状态,二者互为因果,相互影响,要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动态认识,深入理解。
结合现代医学理论,所谓“血瘀”就是由于血瘀和血管的流变性质异常产生了“血行失度”或血液循环障碍并导致全身或局部血行低下或功能紊乱的疾病状态[6-7]。痹证发病后,经脉痹阻,痰瘀互结,血液处于“浓、黏、聚、凝”的高凝状态,可引起全身或局部的血液循环和微循环障碍,而产生疼痛、结节等一系列症状。因此治疗痹证时应特别重视瘀邪,当病情进展,迁延难愈,甚至内舍脏腑,变阵丛生时,则是瘀邪作祟。
1.3 “脉络瘀滞”为病机关键 魏老师认为传统医学对其病机的认识已经非常确切,痹病早期治疗效果尚可,一旦病程日久,为何会迁延不解?对其病情演变详细分析,可知在痹证将成而未成之时,依靠适当药物及自身的康复能力往往能驱除风、寒、湿、热等致病之邪,血脉通畅,则病情得以缓解;如致病之邪长期存在或治疗不当,出现痹证,络道阻滞,血滞为瘀,津停为痰,此时再单纯依靠祛风散寒或清热之药则往往难以奏效,而血脉不畅通,外邪亦难以祛除;痹证日久,痰瘀胶着不化,正气若不足,病邪可由经络累及脏腑;邪气不散,又会加重正气损耗,生机衰退,气血失常,最终表现为气血亏虚为本,而痰瘀胶结为标之象。
由魏老师对痹证的病程分析可见,痹证的演变离不开瘀血为患,祛邪更赖于血脉通畅。因此可认为“痹者闭也”即气血不通之意,病机中“脉络瘀滞”是关键病机,治疗上应注重活血通络。
2 临床治疗
2.1 扶正祛邪兼顾 根据病因可知正气亏虚是痹证发病的内在条件,而外邪是诱发因素。因此魏老师在治疗中强调扶正祛邪兼顾,行标本兼顾之法。针对本虚,痹证初发,腠理疏松,卫表不固者,处方中常加桂枝、白芍调和营卫或加黄芪以益气实表、防风祛风散邪;病程稍长,气虚痰瘀已成者,加苍术、白术燥湿健脾,川芎、丹参活血化瘀;病程较长,肝肾亏虚者,或加附子、肉桂温补肾阳,或加地黄、鹿茸填补肾阴,或加杜仲、巴戟天补肝肾祛风湿。针对标实,重在祛除风、寒、湿、热等外邪,其痛游走不定,谓之行痹,治当祛风,一般选用羌活、独活,重者加用蕲蛇;其痛冰冷刺骨,谓之痛痹,重在散寒,轻者选桂枝、细辛,重者改为川乌、草乌;其痛重着固定,谓之着痹,胜湿为上,常规用茯苓、薏苡仁,不效重用半夏、苍术;其痛灼热,谓之热痹,当需清热,一般可加知母、芍药,重者改生石膏、络石藤等。
2.2 活血通络为主 基于外邪侵袭机体,导致气血闭阻,而成痹证的认识,血瘀是痹证起病后发生发展的重要病因,“脉络瘀滞”是关键病机,魏老师认为活血通络应是治疗核心点。在多年治疗疑难杂症,运用活血通络法实践中,魏老师追根溯源,钻研古训,对活血之法有深刻领悟,认为完整、科学、有效的“活血”应涵盖理气、化瘀、通络三要素[8]。
理气者,盖气血相生相用,血赖气之推动、固摄、生化,正如《本草纲目》曰:“气者血之帅也。气升则升,气降则降;气热则行,气寒则凝”,《血证论》曰:“人身之生,总之以气统血”。因此,活血当先理气,气机通畅才能为活血通络法提供先机,魏老师认为理气不是指单纯意义上使用理气行气之药,一切消除影响气机通畅的原发及继发因素都可以归为理气,如寒凝气滞而温煦推动、热灼气散而清热收敛、痰瘀涩气而破血逐痰、气虚血瘀而补气行气等治法都应该属于理气范畴。因此,治疗痹证,尤其病程较长者,魏老师反复强调不应只重局部病邪,应着眼整体状态,化瘀即重在消除瘀邪,主要是改善血瘀状态,即血液在脉道中运行迟缓、阻滞、凝聚的状态。针对瘀血成因,魏老师认为活血化瘀,一者要调畅气机,正如上所述,气机失调必然影响到血液运行,因此应用补气行气、调整寒热等措施调畅气机是化瘀的重要条件;二者适当加用活血药物,改善血液运行,防止血瘀影响气机运行及血瘀状态加重停滞脉络脏腑而成瘀血。通络即祛除瘀血,保证血液通道的畅通无阻。正如《医论十三篇》曰:“譬如江河之水,浩浩荡荡,岂能阻塞,惟沟浍溪谷水浅泥淤,遂至壅遏。”血瘀重,停滞脉络或离经之血、污秽之血积存体内而为瘀血,只有通过破血散血才能消除瘀血,保障脉络通畅。
3 临床用药特色
魏老师治疗的各种痹证中以久病、顽症居多。《临证指南医案》指出:“久病入络”“风湿客于经络,且数十年之久,岂区区汤散可效”“治则须以搜剔动药”。对于病久难愈患者,魏老师特别推崇虫类活血药物,认为其属血肉之品,功擅通络,运用得当,能有效改善络脉而止痛。另外对于顽症,常规药物效果不理想时,非大毒之药不能起沉疴。
3.1 虫类活血药
3.1.1 全蝎、蜈蚣全蝎、蜈蚣二者均有息风镇痉,攻毒散结,通络止痛的功效。《玉楸药解》记载全蝎:“穿筋透节,逐湿除风。”《医学衷中参西录》曰:“蜈蚣走窜之力最速,内向脏腑,外向经络,凡气血凝聚之处,皆解开之。”在血脉瘀阻,脉道闭塞,疼痛明显时,二者协同使用可显著增强通络散结之力,病情严重者改为粉剂以增强疗效。
3.1.2 蕲蛇蕲蛇祛风,通络,止痉。《雷公炮炙论》曰:“治风,引药至于有风疾处。”《本草纲目》记载:“其能透骨搜风,截惊定搐,为风痹、惊搐、癞癣、恶疮要药,取其内走脏腑,外彻皮肤,无处不到也。”魏老师认为其不仅有很强的活血通络之力,而且祛风之效甚佳。治疗行痹症状时隐时发,走窜不定者,可直达病所,为活血药之先锋。
3.2 大毒药物
3.2.1 马钱子马钱子苦、寒、有大毒,具有散结消肿、通络止痛之功效。张锡纯对其倍加推崇,《医学衷中参西录》记载其:“开通经络,透达关节,远胜于他药也。”现代药理研究发现其具有抗炎、调节免疫及镇痛作用[9-11]。因其毒性较大,常提取有效成分应用于中成药,而鲜有医生临床使用,魏老师却常用其治疗诸多疑难杂症,如类风湿关节炎、偏头痛等,收效甚佳。对于痹证,魏老师认为其是止痛之王牌,对于病程较久,疼痛明显,常规用药效果不佳者,用之立竿见影,但为避免其毒副作用,应避免轻易使用且每日用量应严格控制在0.5 g以内,可胶囊包裹吞服,亦可合诸药煎服。
3.2.2 雷公藤雷公藤味苦、辛,性凉,大毒,《滇南本草》称其“入肝脾十二经,行十二经络”,具有“治筋骨疼痛,风寒湿痹,麻木不仁,瘫痪痿软,湿气流痰”等功效。现代药理研究雷公藤可通过多靶点、多途径调节免疫,广泛应用于免疫系统疾病,有“中草药激素”之称[12]。在临床中,魏老师治疗免疫指标明显异常的患者,常加用雷公藤多苷片(10 mg/片),每日4~6片。待症状明显缓解,免疫指标稳定后逐步减量至停药。
4 案例举隅
李某,男,53岁,已婚,自由职业者。2018年1月11日初诊。患者因“臀部及下肢疼痛5年余,加重伴活动受限1年余”就诊。患者年轻时曾于东北工作,当时因年轻气盛,寒冷天气冬泳,曾出现腰背部及关节疼痛,经治疗调养症状缓解。近5年患者右侧臀部及下肢出现钝痛,麻木不仁,且日益加重,最初考虑坐骨神经痛,经针灸、理疗后改善不明显,详细检查诊断为类风湿,先后采用针灸、西药、中药等多种方法治疗,仍时轻时重。近1年症状较前明显加重,上楼梯及下蹲受限,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多处求诊无明显疗效。后由朋友介绍,来我院求诊。入院症见:臀部及下肢酸胀疼痛明显,屈膝及下蹲困难,疼痛部位可触及小结节,压之痛甚,无畏寒发热,无口干口渴,小便清长,大便每日1行,舌暗淡,苔薄白,脉沉细涩。查体:双侧髋关节周围、股四头肌等处有压痛,右侧明显;双下肢有少许结节,压之疼痛明显;无关节畸形,因疼痛活动有不同程度的受限。辅助检查:髋关节X线影像检查:可见髋关节间隙毛玻璃样改变。类风湿因子:阴性。中医诊断:痛痹(寒滞血瘀证);西医诊断:风湿性关节炎。具体药物如下:制川乌6 g,制草乌6 g,细辛3 g,肉桂3 g,延胡索12 g,仙茅15 g,巴戟天30 g,徐长卿15 g后下,白芍15 g,丹参15 g,全蝎粉2 g,蜈蚣粉2 g,川芎10 g,甘草6 g。另加用生马钱子0.3 g,硏粉吞服,每日1次。7剂,上方加水煎3次。嘱1、2煎口服,第3煎用于足浴,期间注意保暖,避风寒,适当活动。二诊,服药后自觉腰骶部关节有温热感,关节疼痛酸胀减轻,疼痛仍较前明显,纳尚可,大便通。舌暗,苔薄白,脉涩。考虑阳气稍复,但瘀血仍较甚。故宗上方加蕲蛇3 g,加强活血通络止痛之效。再进7剂,用法同前,仍嘱生马钱子0.3 g,胶囊包裹吞服,每日1次。三诊:服药后关节疼痛稍减轻,活动已较前便利,但双膝以下有恶风之感,二便调,舌淡,苔薄白,脉弦涩。继续服用上方,14剂。四诊:关节疼痛已明显减轻,但冷风吹袭时有刺痛感,余无不适。上方去白芍、徐长卿,加黄芪30 g、防风10 g,益气固表。注意保暖,继续足浴。后续治疗宗上法,2018年3月21日因头痛再次就诊,追问详情,述服药后上述诸证消失,唯双下肢结节压痛点偶有不适。舌淡,苔薄白,脉弦。建议加强锻炼,调摄得当。
按: 该患者年轻时寒邪侵袭发病,因正气尚足治疗调养后很快缓解。 但随着阳气虚衰,痹证再发,且病程日久,寒、湿、痰、瘀,阻滞经络,闭阻血脉则疼痛。本已虚、邪尚盛,因此在治疗时扶正祛邪兼顾,采用仙茅、巴戟天、肉桂温补肾阳,川草乌、细辛祛除寒湿之邪,而本病脉络瘀滞明显,旧血不去新血不生,使用全蝎、蜈蚣粉重在破血散血,芍药养血活血顾护阴液,川芎、延胡索调畅气机以助行血,疼痛明显,加用马钱子粉以缓解疼痛。 用药后阳气得复,症状改善。但瘀血仍较明显,加用蕲蛇以增强通络活血之效,后宗上法反复调理两月有余,后正气充盛,邪气得散,病告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