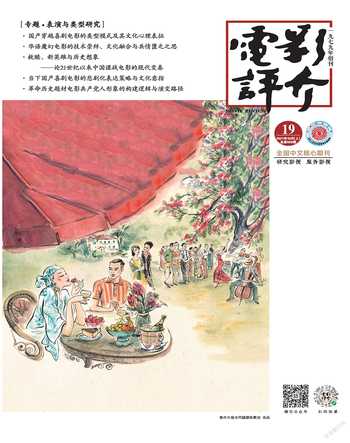《困在时间里的父亲》中的感官叙事与疾病隐喻
2021-03-27王小静吴蕾
王小静 吴蕾
《困在时间里的父亲》在悬疑光影中,梳理出一个关于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动人且无奈的故事。曾凭借《沉默的羔羊》(乔纳森·戴米,1991)荣获第64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著名演员安东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因在《困在时间里的父亲》中炉火纯青的表演再次荣获第93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同时《困在时间里的父亲》还获得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可谓是该年度奥斯卡的最大赢家。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关注,很多电影中都有涉及,比如韩国纯爱电影《我脑中的橡皮擦》(李宰汉,2004)就讲述了女主角患病之后男主角的不离不弃;电影《恋恋笔记本》(尼克·卡萨维蒂,2004)的故事设定也是相伴终生的爱人,即使其中一个人开始遗忘,另一个人总会不厌其烦地讲述他们曾经的故事,即使记忆真的抹去了,也要在重复中制造新的回忆。这些电影大多从照顾者的角度展开叙事,主题多与爱情相关。《困在时间里的父亲》以患病的父亲为叙事主体,通过他的引导展开情节的建构。也正是因为父亲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使得他的叙述具有不可靠性,本片因此呈现出“悬疑”的效果,碎片化的記忆拼接宛若迷宫般混乱。但随着故事接近尾声,一切又逐步清晰。镜头的调度、演员的表现、重复的情节等都在缓缓进行中迸发出巨大的动力,观者对于亲情、自我、生命也有了更多的思考。
一、从舞台剧到电影的文本深化
《困在时间里的父亲》是导演弗洛莱恩·泽勒(Florian Zeller)的第一部影视作品,他最初为人熟知的是他作为小说家和剧作家的身份,这部电影就是他根据自己于2012年原创的同名舞台剧《父亲》改编而来的。自古希腊以来,尽管戏剧不断演变发展,但对于“崇高”的追求几乎是一以贯之的,这其中当然也少不了剧烈的冲突。近情近理的剧作创作即使打破了传统的“三一律”,由于戏剧一般在剧场中演出,还是会受到空间的局限。除了演员激情的表演,场次的转换、道具的改变、旁白等各个环节必须配合默契,才能使剧情高度凝练集中,观众才能在有限的观赏时间中接近事件的真实状态。即使故事不是一天之中、一个场景、一批人,戏剧也必须遵循规律,在这样的背景下戏剧呈现的故事是宏大的,缺乏细节的捕捉,形式往往大于内容。戏剧有不同的“幕”,电影文本细化为导演剧本,也就是分镜头脚本。内容包括镜头号、景别、摄法、画面内容、台词、音乐、音响效果、镜头长度等项目,更为精细化。电影给了导演更广阔的发挥空间,灵活多变的镜头语言、不同场面的拼接更为直观地使观众在视觉观看中达到心理认同。即使电影不像戏剧以追求庄严、崇高、典雅、完美为旨趣,但也不缺乏艺术感受力和震撼力。其中很大的原因在于导演对于剧本文本的打磨。文本创作是戏剧也是电影的基础,在其他艺术形式还未成型之前,文本必须是形象性与理性、情感性与认知性相互渗透的。《困在时间里的父亲》故事源于弗洛莱恩·泽勒的外祖母,故事背景从最初的法国迁移至英国伦敦,人物与文化背景的改编,使得文本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又以一种全局意识构建社会理性,兼具个人情感又能达到普遍的智性输出。即使在看似碎片的画面拼接中也能抓住故事的核心讲述者,并在他们的对话和不同的视角呈现中把握故事的脉络,感悟时间与生命。
影片中最重要的角色莫过于父亲安东尼和女儿安妮,他们共同构成电影的两个叙事角度。托多罗夫(Todorov)说过:“在文学中,我们从来不曾和原始的未经处理的事件或事实打交道,我们所接触的总是通过某种方式介绍的事件。对同一事件的两种不同的视角便产生了两个不同的事实。事实的各个方面都由使之呈现于我们面前的视角所决定。”[1]在故事的前半部分,父亲占据着叙事的中心,观者对于故事的了解来自父亲视角,父亲对女儿的指责甚至让观者误解安妮可能是个不太孝顺、只想继承财产的自私的人。随着情节的推进,父亲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这一事实开始显露,父亲的叙事开始变得不可靠,也正是这种不可靠加深了电影对于观众的吸引力。观者半信半疑地跟随安妮的叙事角度不断窥探父亲患病的细节,却又对于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一切充满了好奇。女儿的无奈、父亲的敏感在彼此交织中呈现不同的境遇和困惑,不同的事实背后是不可逆的衰老和仍将继续的生活。在父亲患病的这个事件里,不同的情节铺排打破了时空的界限,不同视角的穿插使故事事实与价值判断出现矛盾,也就能够更为客观地展现故事内核,观者也可以在质疑中形成与电影的有效互动。尤其是电影中对于相同情节的一次次重播,借助不同的视角对混乱与不合理进行解释。例如,父亲沉睡时,女儿是受不了折磨掐死了父亲,还是轻轻抚摸父亲的面庞;父亲听见女儿和男朋友在争执把自己送入养老院时对安东尼脸部的镜头聚焦,和从正面记录的全景聚焦。同一场景换个角度往往得到的信息是不同的,这种镜头的调度符合情节的进展,是功能性的结构设置,也是叙事意义的延伸。以“我”这个第一人称视角展开的故事也更好地凸显出人物的形象,使观众更为接近文本所要传递的价值观念。
二、突破封闭空间的感官叙事
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中,故事空间最开始是指背景,强调外部空间可以使人物及其行动具有似真的效果。从最基础的层面来说,背景的呈现往往能增强观者或者读者的视觉化理解,增强代入感,使故事更具有可信性,人物形象更加鲜活。结构主义叙事学家普遍认为,空间对于叙事作品具有非常重要的结构意义。一方面,空间给人物提供了必需的活动场所;另一方面,空间也是展示人物心理活动、塑造人物形象、揭示深层意蕴的重要方式。《困在时间里的父亲》的叙事空间在三个空间中,包括父亲的公寓、女儿的公寓、养老院的房间。这三个空间的布局结构非常相似,尤其是父亲的卧室,如果不仔细观察基本很难区分,甚至可能会以为只有女儿公寓这一个活动空间。为了突破看似封闭且单一的空间,导演不仅注意画面的色彩转换,而且借助有限空间里的相似物件设置悬念、给出线索。空间被结构化和整理的地方,就能获得解答谜题的一个锦囊。父亲安东尼游走于公寓中的各个房间,又在不经意中留下痕迹。仔细寻踪可以知道,安东尼的公寓呈棕色系,安妮的公寓是灰蓝色,养老院则是清冷的蓝色系。公寓中的灯具、家具、墙面的装饰画都有不同。例如,安东尼公寓的壁炉之上挂着小女儿露西的画作,而安妮公寓的墙面上无装饰;安东尼的卧室虽然朝向一致,但养老院的床及床头的装饰画、窗外的景色都是不同的。在时空错乱的迷雾中,揭示的不是恐怖的故事真相,而是安东尼因为患上阿尔茨海默病所陷入的人生困境。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影片中的走廊,安东尼总是在走廊中留下背影,每一次在走廊尽头,当他打开门,就仿佛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推动故事进展。在有限的空间中,走廊承担了叙事的桥梁作用,成为叙事空间的转换枢纽站。当安东尼得知女儿及其男朋友要把他送入养老院,愤怒走向走廊尽头,打开门,他已身处养老院阴冷的蓝色世界,这种视觉的流动性极具诡异感,又能带给观众直接的心灵震撼。记忆术的核心其实就在于视觉联想,即把记忆内容和难忘的图像公式编码以及入位——在一个结构化的空间中的特定地点放入这些图像。从这种地形学的特点到把建筑物当作记忆的体现只有一步之遥。这也是空间作为记忆术的媒介朝向建筑物作为记忆的象征的一歩[2]。伦敦的公寓是导演精心设计的,各种色彩、道具的存在都是对时空切换的按钮,看似狭小的空间拥有无限的存量,记录着安东尼流散的记忆,也共享着每个参与者的感官知觉和生活经验。
除了视觉的建构,电影的配乐也在极力延溢空间的边界,依靠听觉加强感官叙事。最初的电影是没有音乐的,其实连声音都没有,当时还不具备把声音加入画面的技术。后来即使有了音乐,音画也是分离的,音乐是在放映现场配合演奏的,直到有了同步的声音,现场演奏的音乐才逐渐被淘汰。发展到今天,大部分电影中都有配乐,各大颁奖礼也会有和音乐相关的奖项,音乐成为电影艺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电影配乐和主题曲来自两种途径:一种是由音乐家专门为某部电影创作的音乐;一种则是借用已经问世的音乐。这其中既有流行乐,也有古典乐或者爵士等各种类型。好的音乐能助推一部电影的成功,能够达到相互成全的作用。就如宫崎骏的电影基本都是久石让创作的钢琴曲,彼此辉映。音乐能够告诉观者某个场景或者时刻所具有的意义,还能推动故事发展,形成强烈共鸣。在《困在时间里的父亲》这部电影中,音乐共出现3次,3首来自歌剧的曲子神圣又神秘,每一次的响起都在揭示着安东尼不同的人生轨迹。电影伊始,在安妮穿梭街道回到公寓的过程中,播放的是英国皇室御用作曲家亨利·普赛尔(Henry Purcell)创作的《冷之曲》,歌声停止,安东尼出场,戴着耳机的他形容枯槁,就如歌曲所暗示的那样走入了人生的寒冬,像一座骄傲的孤岛。第二次音乐出现在厨房中,伴随着意大利作曲家贝里尼(Bellini)的咏叹调《圣洁的女神》,安东尼踉跄着起舞,轻松且愉悦,这时候的他平和、饱含热情。只是短暂过后,一个陌生男子保罗的出现马上又把电影拉回了一种不知所措的惊恐之中,这种反差其实也为后面安东尼真实的状态埋下了伏笔。从医院回家的段落采用的配乐来自法国作曲家比才(Bizet)的歌剧《采珠人》中的咏叹调,无论是坐在车中的落寞还是音乐突然的卡壳,都在昭示着生命的裂痕已经出现。音乐作为感官刺激或刺激感官的一种符号系统,与画面信息让人处于从现象到本质的入口或过程中,并在渐入佳境中踏入关于安东尼个体生活的普遍本质和意义探索之中。
三、个体求索指向生命法则的疾病隐喻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把个体意识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三个维度。“本我”追求快乐,注重现时的享受,受先天的本能和欲望控制;“自我”则较为现实,受制于“本我”,又起到调节作用,行动力较强;“超我”则受到社会各个方面规则的制约,遵循道德原则。也就是说,主体并没有恒定的本质,它受到意识和无意识两方面的影响。作为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人,意识尚是被分解的,在不同时间、环境呈现的意识状态会有偏差。作为一个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安东尼显然试图掌控自己的意识,即使记忆力在慢慢衰退,生活变得混乱,他也想保持“自我”,甚至完成“超我”。但事实上,安东尼的意志已经不完全受自己控制了,他情绪化、刻薄、多疑、脆弱。当安妮给他找来新的护工时,最初他表现的礼貌、风趣,符合“超我”的规范,但没一会儿他性情突变,开始数落安妮,甚至诋毁安妮搬进自己的公寓是想要继承自己的财产,而事实上他是住在安妮的公寓。他的“自我”越是突出,就越接近“本我”的野蛮,也就是人尚未开化的状态。情绪的狡黠与顽固战胜了理性和经验,意识受控于直觉,主体抛弃了社会和历史,逐渐生物化,无法以原有的样态继续存在下去。阿尔茨海默病打破了主体的完整性,像病毒侵入般腐蚀主体的身体机能,摧毁主体的精神系统。个体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博弈,想要对于“自我”存在的确认,演员安东尼·霍普金斯在大量特写镜头下通过不着痕迹的表演展现得淋漓尽致。电影中出现两次安东尼找手表的情节,其实也是安东尼想要试图掌控自己与现实的联系的一种隐喻。“找”其实是安东尼对于“自我”的一种确认,是想对自己活在当下的一种明证;“手表”代表着时间,是世界运行的秩序。阿尔茨海默病打破了时空的运行准则,使得安东尼不知道自己身处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尤其是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当他怀疑护工、怀疑保罗拿了自己手表的时候,其实就暗示着他其实已经走入時间的迷宫,被时间控制。安东尼·霍普金斯将内心戏与表演场景重合,契合主人公的慌乱,是电影与生活的真实统一。而时间最终指向的则是死亡。弗洛伊德指出,“开始认为人类正在可怕的死亡驱力的掌握之中憔悴凋萎,而这一死亡驱力就是自我释放到自己身上的一种原始受虐欲”[3]。虽然电影结局还未提到死亡,但受困于疾病的安东尼已经被死亡驱力所包裹着。最后,安东尼对着护士说自己想要找妈妈,依偎着护士的他回到孩童模样。本能的需求超越思想的满足,自我变成一个可怜的实体。对于生命价值的确认回归有知之前的状态,最终只是在挣扎中指向死亡的悲剧。
生老病死,没人可以逃过这一生命的规律,人的一生在健康之外总会伴随着疾病。比起癌症,阿尔茨海默病的攻击性不算强烈,但却更加考验一个人的能力,毕竟这是一个耐心和时间的混合体,也就难免要与伦理联系起来。伦理的范围由浓厚的关系决定,有亲密也有疏远。与道德不同的是,在伦理语境下的人是一个实体词,更具有个性。在疾病隐喻的背后,电影更加注意对于道德的解绑、对于个体的尊重。在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中,困在时间里的不仅只有父亲,还有女儿。也许有人不理解安妮最后把父亲送到养老院的安排,但这样的剧情却更体现出导演的功力。道德是一种必要的善,决定父母要抚养子女,子女要赡养父母。而伦理则是在原则上选择的善,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可以选择的关系。当然这种选择往往是具有转移性的,有义务但不强制。安妮的第一次离婚其实就与父亲有关,包括后来与男朋友的争论,都可知她从未放弃自己的父亲,即使父亲心里更在乎死去的女儿露西,安妮也是默默承受并选择理解。父亲进入养老院她会给父亲写信,假期从巴黎回来,与父亲散步、交谈,安妮其实就是整部电影压抑氛围中温暖的代表,不张扬,平凡却充满力量。生活永远处在不确定的状态中,伦理的价值不仅在于打通社会里消极情感转化为关爱和关心的通道,而且在于承认并肯定每一个人独立的自我价值。个体受制于自然规则,也囿于情感的牵连,个体的理性仍有决定的主动权。在“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传统理念之外,导演或许也在告诉观众每一片叶子都有凋零的时候,人同样如此受制于生死命题。自然界的一切都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有凋零就会有新生,微不足道却也独一无二,个体的价值不会轻易消失,活过即存在。
结语
电影是文本感知的特殊分享,是平凡世界的特别构成。完整的电影文本不仅是一种再现,而且是直接的感官体验。《困在时间里的父亲》把故事置于纯粹而有限的空间,借助多个维度的视角一步步揭开一个家庭的不幸。以个体的感受为出发点,记忆与想象、现实与虚幻没有清晰的界限,生命在时空混淆中运行。时空的视听转换加之饱满的故事情怀恰如其分地相融为一体,混乱的碎片在故事的推进中才一点点得以拼凑。从当下出发,跟随电影的视角,使故事在发生于回忆的时刻移位、变形、扭曲、更新,有限空间延溢出无限的可能。在公寓中游走暗喻疾病压制下个体对于自我的寻找,意志与意识的拉扯,暴露出生命的脆弱,也展现出善良的美好。疾病是人类难逃的劫数,或大或小,或早或晚,如果无法避免,那就勇敢并坚强地直面它。时空轮回,个体的困境总会消解在时间的齿轮之下,伦理的最终追求是对自我的关爱和对别人的成全。所以,不必沮丧,生命之花仍然值得绽放!
参考文献:
[1]王泰来.叙事美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27.
[2][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59.
[3][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