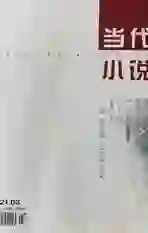离散与告别
2021-03-26徐龑鹏
徐龑鹏
如果要为过去的一年罗列几个关键词,“离别”會是排名很靠前的一个。离别容易让人们伤感,并且带来持续性的魂牵梦萦。正因离别如此平常又如此蚀骨,构成了历来文学创作的重要母题之一。刚刚结束的2020年如此特殊,有亲人朋友的永别,有曾在各行业留下辉煌成绩的先辈们逝世,也有一些人不知为何彼此失散。2021年1月份见刊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对被离别包围的生命体给予了不同形式的温暖关怀。
阿华的《月亮出来亮汪汪》(《广西文学》2021年第1期)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失散的故事。叙事者“我”的爹出家为僧,留下“我”与外公相依为命。年幼的“我”不因失孤而倍觉孤单,因为有小伙伴霜妮儿陪伴在身边。霜妮儿是一个13岁的脑袋不太灵光的女孩子,家庭圆满,以放羊为乐。不久之后,霜妮儿的父亲三斤半患重病离世,作者写道,“很久以后,我一直记得霜妮儿扶着村口的老槐树,哭得撕心裂肺的样子。”小说虽然在三斤半去世不久就结束了,但故事的意涵却远不止于此。叙事者“我”的父母亲先后离去的惨痛经历,作者有意将其从文本中隐去,而用大量的篇幅铺写三斤半去世前霜妮儿一家幸福的生活和去世后霜妮儿状态的变化。“我”的故事与霜妮儿的故事如此相似,无法不将霜妮儿的经历当作是叙事者“我”本人经历的隐喻。小说中不断出现的“孤独”一词,既是霜妮儿的心境,也恰恰是作者未加着墨的“我”的心境。“孤独就是我的影子,它时刻跟着我,我一个人在树林里捡桑树叶的时候,它是树上的鸟鸣。我一个人去河边扔鹅卵石的时候,它就是水里围着落叶转的鱼。”正因为小说围绕“生离死别”这一主题多重的嵌套与延宕,才需要我们对文本的不断追索。被离别的个体并不只“我”和霜妮儿两个人,文中从未出场的父亲恰恰构成了“离别”这一主题最深处的核。父亲出家为僧的缘由颇为耐人寻味,小说借他人之口道出其中玄机,“我娘的离去对我和尚爹的打击太大了,我娘在生下我不久就因病去世了,这让我和尚爹伤心欲绝。他在家里不能看见我娘留下的任何东西,觉得哪件东西上都有我娘的气息,每次看到这些东西他都会发愣,都能看出一汪泪水来。”父亲因母亲的“死别”而灰心丧志,选择出家为僧,与作为女儿的我“生离”。小说的主题因此有了双重的含义,作为个体的我们既是被他者离散的主体,又无形中建构了他者的离散经验。
裘山山的《失踪的夹竹桃》(《山花》2021年第1期)在故事设置上比《月亮出来亮汪汪》简省得多,但对“离别”这一主题的呈现却不遑多让。小说以陈淑芬突兀的长辫子作为开端,勾起读者继续追索的欲望。随着故事的深入,陈淑芬奇特的长辫子的谜底也一层层揭开。陈淑芬的老汉儿曾是川剧团拉二胡的艺人,因为双目失明赋闲在家。为了给老汉儿解闷儿,陈淑芬用她的长辫子作为拐杖带老汉儿四处拉二胡表演。陈淑芬将头发留成巨大的辫子,不仅平时生活多受影响,天气热的时候也会散发出一股酸臭的味道,这一切都是为了给老汉儿尽孝心。直到有一天,父女二人在回家路上被拉板车的撞倒,老汉儿死掉了,陈淑芬的长辫子被卷进车轮子里,受伤住院。陈淑芬出院后,将头发剪短,一直到初中毕业都是短短的寸发。故事很简单,作者按照时间顺序娓娓道来,没有旁生枝蔓和另起波澜,但在平淡中却蕴含着亲切动人的力量。小说以“失踪的夹竹桃”为题,借“夹竹桃”隐喻陈淑芬剪掉的辫子,而陈淑芬将剪去的辫子与老汉儿埋在一起,“失踪”传递出对离去亲人不舍的缅怀与哀伤。离别作为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也许并不需要极其高明的技巧或者形而上的思想凝练,直笔写出,平淡中寄寓的巨大的情感张力刺激着读者心湖深处久难平静的记忆与之勾连呼应。
张毅的《两个人的山谷》(《青年文学》2021年第1期)对离别这一主题做了别样的探索,寄寓了作者对人性温情的赞同和褒扬。苏子林的儿子苏诺意外离世,将器官捐献给一个叫周小苏的年轻人。而被移植的苏诺的肾脏以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将苏子林和周小苏吸引到一起,两个孤独的灵魂因为器官产生了莫名的连接,共同守护着苏诺出事的山谷。因为器官移植使逝者在被移植者身上以某种方式复活,并且给予逝者亲人以精神上的安慰和补偿,选取类似题材结构故事、创作小说并不罕见,且容易陷入滥情的套路。但《两个人的山谷》对这一“元叙事”进行了不同以往的改写。苏子林清楚地知道周小苏是儿子肾脏器官的获得者,但却没有将其点破,两人仅仅以雇主雇员的关系在文本中共存。小说以雪崩夺走苏诺的生命开始,以下了三天三夜的铺天盖地的大雪作结,绵亘一切的大雪使得文本呈现回环往复式结构,仿若生命是一个循环再生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作者对结尾的处理消解了这一常见题材的感伤滥情因素,对雪落的声音与藏地诸种物象的描摹,渗透着宗教式的解慰。
阿郎的《正月初六》(《当代》2021年第1期)可以放置在东北书写的文学场域内进行观察。正如同“铁西三剑客”或者“新东北作家群”的部分文学实践一样,犯罪与贫困同样构成了《正月初六》这部短篇小说得以运行的相互震荡的两极。东北书写因其对改革开放后全国范围内的经济腾飞使得东北重工业没落这一悖论式存在通过艺术创作的反复诘问,具有鲜明的在地性和时代特征。在小说结尾,罪案告一段落,叙事者声称这一案件为自己的文学创作积累了素材,但写的不是犯罪小说。研究者讨论东北书写习惯于将思索停留在旧工人群体因经济没落而被时代所抛弃,但阿郎的写作却更进一步。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案件,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贾洪斌长期囚禁在家,性欲因抑制而没有宣泄的途径,意欲对母亲“犯浑”,被亲哥哥用斧头劈死。作为一部以犯罪、破案来结构故事的小说,《正月初六》并没有着力于制造悬疑、刺激的剧情。贾洪斌被杀案以及文中一闪而过的盗窃案,叙事者似乎都在引导读者思索背后的经济原因。
佟琦的《毕业那年》(《山西文学》2021年第1期)将视线聚焦在年轻人身上,年轻人也许比较少地直面死亡逼近眼前的考验,但朋友的失散所构成的分离尤为轻易与无名。故事同样很简单,叙事者“我”毕业回到北京,租了一所房子专心搞创作,老同学谢谣来北京,“我”邀请她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故事没有丝毫戏剧性,在谢谣与“我”同居的一段时间,两人有过一段相互慰藉的露水情缘,然后谢谣飘然离去,故事戛然而止。整个故事的发生发展如同《聊斋志异》中的鬼魅狐妖与书生的一夜情缘,又如同徐 的《鬼恋》,不知因何而起,又莫可名状地终结,如坠梦中。似乎表征了当下部分年轻人的生活。乘坐现代性这趟不断加速的列车,我们会发现,人生体验竟然奇异地分裂成完全相反的两极。亲密关系的建立与分离,对有的人而言,愈发艰难与刻骨;相反地,另有一些人,似乎很轻易地走在一起,又很轻易地失散。《毕业那年》通过对年轻一代易聚易散的书写,淡化了“离别”这一主题的沉重与崇高,为我们提供了多元观察的异质性视角。
凡一平的《裁决》(《人民文学》2021年第1期)將“离别”与“重逢”反复纠葛的关系通过婚姻这一人类共通的话题进行讨论。小说以覃桂叶和她的两个老公蓝茂与韦加财绵延二十六年的婚姻纠纷为时间线索,以顶牛爷两次相反的裁决为主轴,串联起三个人相互羁绊的一生。顶牛爷第一次将覃桂叶判决给韦加财,覃桂叶因此度过了无爱又饱受责打的艰苦的二十六年。蓝茂选择坚守在覃桂叶身边,终于等来二十六年后的第二次裁决。顶牛爷目睹覃桂叶艰难的一生,怀有歉疚,在第二次裁决时将覃桂叶判给了蓝茂。《裁决》对于覃桂叶和蓝茂之间横跨二十六年的坚守的书写,提供了不同于《毕业那年》之中轻易离散的另一种思考的角度。但对这貌似大团圆结局的背后细加审视,不免带出更深层次的疑惑,发生在70年代之后的三人的婚姻纠葛,为何要如此乖乖听令于他者的摆弄?命运作为悲剧的超越性力量并未在文本中出场,决定三人悲欢离合之一生的纯粹是人力。小说因此传递出一种特殊的无奈与恐怖。相较于《毕业那年》中年轻人满不在乎的主动分离,《裁决》中的蓝茂和覃桂叶因自身的软弱和愚昧所导致的分离苦痛,则很难激起读者心中的共情。小说对顶牛爷的安排也颇具戏剧色彩,顶牛爷因为错将覃桂叶判给韦加财内心备受煎熬,终成心病,才导致他下决心推翻自己以往的判决。顶牛爷之所以这么做并非彰显正义,当然民间判决婚姻丝毫无正义可言,完完全全是垂死之人的自救之举。小说因此完成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戏谑地嘲弄了看重感情、相依相守的传统美德。对顶牛爷最后判决时的神态描写,“他坐在一张龙椅上,被四个人扛着,像坐在轿子上,高高在上,沐风而来。”这无疑大大加重了作者讽刺的砝码。
大解的《遥远的回声》(《民族文学》2021年第1期)是一篇写给成年人的童话。在这篇小说里,人们可以在云彩上采撷露珠;可以沿着山顶走上天空,却不可以离开大山去看平原和大海;梦境可以变成现实,人们可以拾捡流星,吃下去就能变成神仙;河边的鹅卵石可以孵化成小鸡。大解延续了少数民族作家对“万物有灵观”的尊崇和实践的书写传统,并伴之以奇妙神异的想象。这不禁启示我们,在面向成年人的严肃文学创作中,汉族作家在多大程度上忽视了非现实的童话/神话写作对现实生活的意义以及文学写作的丰富性。王德威曾论述“幻魅叙事”作为瓦解、抵抗历史宏大叙事的正当性的异质性力量,为我们提供思考历史与现实的另一种可能。《遥远的回声》中,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一个完全闭锁与外界不相连接的山村,山村中的人无法走到外面,他们与山外人唯一一次可能的联系是流星来的那一夜,隔着河流相互喊话,声音却“被掠过河面的清风吹得四散,本来是一句完整的话,却变成了零散的颗粒”。山村作为桃花源式的存在,不是村民们有意避世的选择,更像是上帝刻意将其与世隔绝,如同推倒巴别塔之后,言语不通、星散的孤岛族群。小说的题目《遥远的回声》在文中指的是山里的人们向着远处遥遥呼喊,声音却从天上反射回来。从另一个意义上理解,小说塑造的桃花源世界,不也正是世俗中狼狈不堪的我们发出的沙哑呼喊所收到的上帝的回声。小说以奇妙瑰丽的幻想故事,反观现实中人类艰难蹒跚的处境,通过回溯与复活人类历史的童年时代天真美丽的幻想传统,在现实中打开了一道缝隙,为我们提供了一处暂时的精神栖息地。
曾剑的《母亲生日快乐》(《满族文学》2021年第1期)延续了自鲁迅开启的乡土小说的“返乡”情节。故事背景不脱“返乡”写作的窠臼,通过对故乡人事物的今昔对比中,生发作者结构故事的逻辑。如果说《故乡》是按照“归乡——离乡”安排情节,串联人物,那么《母亲生日快乐》也无疑如此。连《故乡》中出场的人物形象如杨二嫂、闰土等,也能在银山媳妇、聋二身上找到隐约的影子。叙事者“我”作为在部队服役的军官,返回贫困脏乱的故乡时显得格格不入,并且通过叙事者的眼睛观察到的故乡的人,皆蒙上了一层野蛮愚昧的影子。作者通过描写母亲几次过生日时出门“躲生”串联起母亲愁苦的一生,“返乡”的书写在这里不单具有思恋故土的情节,而是对母亲的赞歌。故事在给母亲过七十大寿时到达高潮,困守故乡的二哥因为给母亲祝寿的红包太少被邻里讥讽,上演了一出闹剧,破坏了母亲的生日宴。而叙事者“我”在这场闹剧中袖手旁观,任由事态恶化,仿若与己无关的外乡人。题目“母亲生日快乐”在文本中实际上是母亲生日不快乐,标题与文本的悖反产生出情感的张力锋利地批判了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的疏离。小说结束时,“我”与妻子离开故乡,与母亲作别,对双方来说,场面的激烈与悲苦仿佛终生不会再得相见。小说对“离别”这一主题给出了大多数成年人的回答,也许并不存在什么强制性力量介入阻碍两个人见面,见面的计划也始终在日程表上排期,但生活中总是有事情耽搁,慢慢等待时间的耗尽。
盘文波的《逃逸》(《朔方》2021年第1期)是一篇有关失踪、寻找的小说。故事背景设置在偏远小城镇瓦城,聚焦本应处于现代化边缘的人群如何被现代化的力量所裹挟与伤害。甘奶奶的孙子甘大列意外车祸身亡,负责此案的警察林光华因为没有头绪将其搁置,瓦城的自媒体闻风而动,造谣不作为的林光华与案情有涉。小说中的人物仿佛激流中的小舟,被舆论重重捆绑,不能自主。故事虽然发生在一座虚拟的小城,但作者的现实针对性跃然纸上。如果不是自媒体散播谣言所引发大众热点,警察局不会再重提此案,甚至可能将其无限期搁置;而又正是自媒体的蜂拥而至,只顾及流量和噱头带来的经济效益,无人在意甘奶奶所求的真相和对警察林光华的污蔑和伤害。故事的结局和现实生活中那些转瞬即逝的热点一样,热度一过,就无人关注曾经发生的事情,甘奶奶的正义始终没有彰显。小说借邻人之口将自媒体行业比作“炒股”,股市见涨才会引来关注。警察林光华顺水推舟,指责自媒体才是“肇事逃逸者”。这部小说暴露了现实生活中涉及我们每个人的关键问题,执法部门的懒政和民间自媒体进行监管的逐利性。甘奶奶的遭遇既可以发生在瓦城,又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每一座城镇。小说将一出亲人离散的惨痛悲剧,放置在同舟一命的现代时空中进行戏谑与摆弄,借此启发读者若干现代性的反思。
王奇兰的《童年对话》(《萌芽》2021年第1期)是一篇在文体上介于小说与散文之间的作品。作者王奇兰在2020年第二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是一个新锐作家。《童年对话》追忆父与子两代人的童年故事,形成对话呼应关系,传递出作者在成长过程中的生命体悟。作者以温情脉脉的视角带领我们回到“我”的童年,不厌其烦地讲述日常的琐屑往事,这些故事相互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只是让读者静静体悟时光缓缓流逝的哀伤。父亲的童年时光依旧如此,平平常常,静水流深。读完这篇小说,仿若看了几分钟侯孝贤的电影。在作者回忆往事时,时间的流速并不着急,但却因其始终不停地前行,故人逐渐消散,泛黄的语境下沉溺着一丝哀婉。当“我”从回忆中走出时,父亲的血脉仿佛若有若无的胶质一样延续到“我”的身上。“他曾讲述过的那些故事,一些是讲述给人们听的,外面的世界,一些却是总对我重复的,他曾走过的道路。前者完成了我对世界的期待,而后者完成我对世界的理解。我要到很久以后才意识到,什么构成了衰老的他和年幼的我对话的语言。”成长是一个不断与过去告别的过程,告别一些习以为常的认知,告别单纯,更加要告别曾视之为珍宝之物,然后走上父亲曾走过的路,祖祖辈辈曾走过的路,也许这就是人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