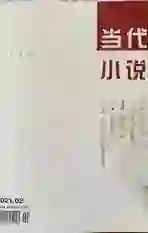每个周五的夜晚(短篇小说)
2021-03-26王威
王威
很快我就知道了,这是个不让人省心的女人。
那天,我刚搬来德村现代城45号楼三单元1201室,她端着一小笼包子就敲开了我家的门。看着她足有一米八的个子,我有点吃惊,不过我没要她的包子,我不习惯跟人这样打交道。她并没有因我的拒绝而退缩,而是爽快地说,哥,你叫我大个就行,我在德村大酒店干后勤部部长,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我极少听到有女人这样称呼自己,我点了点头,右手始终扶在防盗门上,好随时关上它。大个没有被我的姿势阻止住,她左手端着我拒绝了的小笼包子,右手指划开掌中的手机屏幕说,哥,你手机号多少?我加你微信。那一刻,我在心里有点烦躁,早知道搬来会遇见这么个女人,我还不如一直住在和小梨租的筒子楼里呢,虽然那个屋子刮风的时候老是呜咽,让人瘆得慌,可总比身边有个聒噪的女人强。
小梨是我女友,上个月她到日本打工去了。她说五年后回来,到那时如果我没有结婚,她还爱我,那她就嫁我。我冷眼看着她进进出出办理各种证件,无力阻挡。最后她乘飞机离开了筒子楼,离開了我。她发誓说,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买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坚决不再住这些破烂筒子楼或者肮脏地下室什么的。她前脚走,我后脚就搬出来了,我承受不了里面哪哪都有她的影子。
我在大学城当老师,教古代汉语。小梨是我学生李培城的表姐。那天他说,老大,今晚我请表姐吃饭,你一起吧。我说,吃什么名目的饭?他说,今天表姐生日。我以前听他说起过这个远房表姐,老家安徽的,这几年一直在诸城工作。我说行。于是我就见到了小梨。刚见面时,小梨从餐桌后站起来对我说,崔老师,我叫小梨,梨花的梨。看着小梨的鹅蛋脸、小酒窝,我脑子里忽然出现了明朝文学家王世贞的《玉蝴蝶》:
记得秋娘,家住皋桥西弄,疏柳藏鸦。翠袖初翻,金缕钩月晕红牙。启朱唇、金风桂子,唤残梦、微雨梨花。最堪夸,玉纤亲自,浓点新茶。
平日里我是个讷言的人,很少跟人聊古诗词,更别说第一次见面就这么卖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见到小梨我会这样。过后李培城搂着我的肩膀说,老大,你是不是看上我梨表姐了?我很认真地说,我好好想想。
吃饭的时候,看着低头认真切蛋糕的小梨,我又重复了一遍这句:“启朱唇、金风桂子,唤残梦、微雨梨花。最堪夸,玉纤亲自,浓点新茶。”多么美好啊!我很动情。小梨哧哧笑,说我炫耀,欺负她没文化。虽然这么说,可我朗诵的时候,她不错眼珠地盯着我,脸都涨红了,像个得到奖赏的小女孩在压抑着兴奋。我就是从这刻起笃定自己喜欢上了她。
小梨在龙城市场开了一家出租婚纱的店,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租出去五六十套。可她说,即使这样,她也没攒下多少钱。
我们同居后,她问我一个月可以拿多少薪水。我说出一个数字,小梨没有评论,只是怜悯地抱了抱我就做饭去了。我们认识一个礼拜就同居了,这似乎不太符合我对爱情的认知,可小梨说两人的时间不在一个频道上,不同居怎么知道合适不合适。我连连点头。
小梨去日本前的最后一晚,我们吃的炸秋刀鱼,是小梨从市场带回来的。她一块一块仔细地剔除鱼肉里面的细刺而后塞进我嘴里。跟她一起吃饭,我会想起母亲,我小的时候也是被母亲这么惯着。惯着惯着我就变成了一个不闻窗外事的废物,除了读书考试,其他什么也不懂。当一盘秋刀鱼吃尽,小梨用吸油纸撸着手指上的残油说,我说的你都记住了?我对着小梨点点头说记住了,其实我不知道她让我记住什么,我只觉得满腔悲凉,这是继母亲抛弃我后,第二个女人抛弃了我。所不同的是,母亲再也不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而眼下这个女人还会回来,带着满行李箱的钞票,趾高气扬地跟旁人结婚生子,顶多带着怜悯的情怀拥抱我一下说,你还在这里呀。我忍受不了自己想这些,站起来出去了。小梨在我身后追问,你去哪里?我脱口而出,我要搬走。小梨以为我说玩笑话,因为学校分配给我的宿舍早就被用作他途了。
搬到德村现代城的第一个早上我就睡过头了,因为我从来没有睡过这么舒服的床。昨晚睡之前我还以为自己会失眠,会为自己的处境悲伤,想不到头刚粘在枕头上就失去了意识。大个的高跟鞋在楼道里发出清脆的敲击声,叫醒了我。我今天没有课,想睡个回笼觉,可高跟鞋在我家门前停住了,我警惕地把头离开枕头几寸,听外面的声音,很快,高跟鞋又敲起来,越敲越远,最后是电梯开启的声音。
德村现代城是德村的回迁楼,刚交房不久。签完租房合同,房东给我钥匙的时候说,是崭崭新的楼哎,我自己都舍不得住给你住,你就偷着乐吧。我握着钥匙一声没吭。德村远离市中心,自从大学城搬到这里,它也进行了大规模拆迁,然后就天天眼看它起朱楼,眼看它宴宾客,完全没有了村落该有的样子。早知道可以这么租房子,我就带小梨出来住了,何必住那个刮风呜咽的破筒子楼,最终把她住到日本打黑工去了。小梨争辩过,说她不是打黑工,她是正规的劳务输出。不管是什么,反正是漂洋过海离我远去了。
大个在我家门口放了两双一次性拖鞋,她发微信告诉我说没花钱,是从酒店里拿的,她还说,昨天下午给我送小笼包子,看到我在家里穿皮鞋戴着鞋套,那样不舒服。小梨也这样批评过我,不过她从不拿拖鞋让我换,任由我穿着鞋套在她身边转来转去,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随你便。我没有开门去拿那两双印着红色“德村大酒店”字样的一次性拖鞋,也没有给大个回复微信。
中午我点的外卖是秋刀鱼,吃得卡住了嗓子,用醋用馒头用苏打水统统试了一遍,最后我也不知道刺掉下去了没有,反正喉咙里老是觉得有东西横在那里。不管它了,我赌气把整块刀鱼放在嘴里嚼啊嚼,边嚼我想起还从来没有给小梨读过《玉蝴蝶》的下阕:
嗟呀!颠风妒雨,落英千片,断送年华。海角山尖,不应飘向那人家。惹新愁、高楼燕子,赚人泪、芳草天涯。况浔阳,偶然江上,一曲琵琶。
系主任打电话来,市古诗词协会有个古典诗词大赛点名让我去当评委,问我要不要去。我说我没有空,然后就挂断了电话。其实系主任知道我不会去,他的心里早应该有了一串人选。
我用消毒液把家里清洗喷洒了一遍。我喜欢消毒液的味道,让人感觉干净和安全。晚饭我蒸了几片腊肉,腊肉是姐姐前天从湖北老家给我寄来的。每年的四月份,姐姐都会给我寄腊肉来,是她亲手腌制的。切开红若胭脂白如玉,让我心醉。我两年没有回老家过年了,因为小梨让我在诸城陪她。我问过一次她的父母呢,她为什么不回安徽陪他们过年,她质问我是不是不想陪她过年才问这些有的没的,我赶紧转换了话题。姐姐电话中说不回来就不回来吧,母亲不在了,家里的老屋快坍塌了,住着不安全。
姐姐寄来的腊肉我还没吃一半,就知道大个为什么对我殷勤有加了,我觉得她这是提前致歉。周五晚上我从学校回来,背着笔记本电脑,抱着一摞书刚从电梯出来,迎面一阵劈头盖脸的爵士乐就把我整晕了,我以为自己下错了电梯,音乐是从大个家传出来的。随着另一部电梯门的开启,有几个男女嘻嘻哈哈从里面出来,像看怪物一样上下打量我几眼,然后推开了大个虚掩的房门。
我没有吃晚饭,我被爵士乐烦扰得心神不宁。就在我要去找大个谈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大个找上門来了,她端着一盘车厘子非得塞给我。我不明白这个女人,为什么每次见面都要给人送东西,我义正辞严地拒绝了。我直白地说,我不喜欢吃别人的东西的,也不喜欢被人打扰。说完我看着她,希望她明白我的意思。大个看我真心不要车厘子,就往自己嘴里塞了一颗,满不在乎地说,教授,我知道你在大学城当老师,我以后就叫你教授吧。我一声没吭。教授,我每个周五晚上都会在家里举行舞会,如果你喜欢呢,也可以参加;如果不喜欢呢,我会补偿你噪音损失,比如送你需要的东西,或者给你点钱。没等我想好怎么回答,大个又往嘴里填了一颗车厘子说,就这样,转身走了。我感觉头痛,索索地痛。
我一晚上没睡,直到凌晨两点他们才散。听着他们在楼道里乱七八糟的脚步声,我身心俱惫。我想从房东那里要回租金,回筒子楼住,反正那里租期还没到。与这惊心动魄的爵士乐相比,现在筒子楼里的风声呜咽对我来说简直是天籁,具备着自然美学的力量。
听到我要退房租,房东很吃惊,她说我简直是异想天开,她让我拿出租房合同学习一下,她没空跟我胡扯。我在电话里的沉默大概是让她动了恻隐之心,问我为什么想搬走,我没有说大个周五晚上对我的影响,我不习惯背后谈论别人。
白天不上班的时候,我做了一个调查。这栋回迁楼,整栋楼33层,可住在这里的只有不到十户人家。原德村村民现在基本每户手里都有好几套回迁房,他们根本住不过来,往外租赁又没有那么大的客源,只有闲置。大个钻了这个空子,每周五晚上在这里开舞会。我也想过周五去学校住,去酒店住,可是这些都不是解决实质问题的最好途径。自从小梨走后,每当遇见什么事情,我总会想,如果小梨在会怎么解决,于是小梨在脑海里告诉我说,你去跟那个女人谈谈,告诉她如果不彻底解决就报警。不管是找大个还是报警,我都不是很情愿,我就想小梨这个说法也不一定能解决掉问题。
最近这几个周,每当周五晚上在外面溜达得不能再溜达时,我会顶着喧闹的爵士乐躺在远离大个家的次卧地板上读古诗词,当然读的最多的是《玉蝴蝶》。
同是写女人,王世贞的这首与白居易的《琵琶行》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如果不是因为小梨,我都不会过多关注它。可是在每一个周五的夜晚,我却一遍遍诵读它。我似乎看到小梨站在我面前为我出新的主意,你咋不过去给她把音响砸烂呢?停了一会儿,她又笑嘻嘻地说,或者,爵士乐比起“一曲琵琶”也差不到哪里去啊。说着我看到她捂嘴笑,我张口结舌。
实际上,每晚十二点以前小梨是没有空跟我说话的。她在一家中国餐馆端盘子传菜,弓着腰轮流在各个餐桌前用简单的日语请客人点餐,只有十二点坐上电车后,她才会跟我语音说上那么一两句。这一两句里面隐藏不住的疲惫让我不忍心跟她多说什么,所以更多的时候,我都是在脑子里跟小梨说话,让她给我出主意。
我决定找大个正式谈谈,在喧嚣的音乐激扬下,我或许会增添更大的勇气。于是这个周五晚上的十一点钟,爵士乐到达高潮的时候,我敲响了大个家的门。这是我第一次敲别人家的门,以前有小梨,这些事根本用不到我出面。门开了,激烈的喧嚣声和浓烈的烟酒味倾泻而出,呛得我后退了一大步。大个家的客厅是我家客厅的三倍大,屋子里除了投影仪发射出白炽的光,其他是昏暗的。大个像棵风中的树,在酒精的指挥下歪歪扭扭走向我说,教授,进来玩玩啊。我说,可以小点声吗?大个在门口站定,双手扶在门框边上低头看着我说,可以呀。这个姿势很诡异,像是她把柔软颀长的身子挂在了门框上。她答应得这么痛快,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她随手按开了顶灯,屋子里立时大亮了,音响停了,所有人静止在原处看着我们。灯光下,大个的脸色绯红,上面浮着一层妩媚的笑,她轻声说,这样可以吗?我这才发现,大个的眼睛圆圆的,像个纯洁无瑕的女童那样看着我。一瞬间,我内心对她充满了感激,我说,谢谢你……我发现自己居然不知道大个的名字。我尴尬地说,怎么,怎么称呼你?大个像在端详一个犯错误的孩子,忽然放肆地笑起来。她一笑,屋子里的音乐重新开启,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这晚我是在学校的阶梯教室度过的。听着教室外虫子的鸣叫,我很长时间没有入睡,也不知道小梨回到住处了没有。
第二天黄昏,我在客厅喝茶的时候,大个在外面敲门。为什么我知道是她敲门?因为她边敲门边自报家门,教授,是我,开一下门,教授……我揣测她是为昨晚的事来送东西给我道歉的,我决计不开门,不接受她的道歉,说不定她会因为内疚而改了呢。
敲门声持续了很长时间。我烧水煮茶,把喷壶里的消毒液喷洒了一遍卫生间,又把卧室的床单整理得没有一点褶皱,当这些都做完的时候,我开始用肥皂使劲搓自己的双手。敲门声终于结束了。
手机屏幕一闪一闪的,大个给我发微信说,哥,我肚子疼。这几个字让我心头一喜,报应!继而我为自己这恶毒的惊喜而羞愧。怎么能这样呢?她一个女孩子也不容易,这如果是小梨在日本肚子疼需要帮助呢?一想到小梨,我没有摘鞋套就跑出了屋子。大个像一堆散乱的衣服瘫在我家门旁。我很慌乱,我想打电话问问小梨怎么办。大个仰起蜡黄的脸说,送我去医院。
大个是喝酒导致的胃肠炎,在医院待了一周。她住院没给我添什么麻烦,一律是酒店负担的陪护,反倒是让我获益不少,那就是这个周五的舞会没有开成,我既舒心又为舒心羞愧。这种情况下,对于小梨不怎么联系我,我也不太纠结了,我知道小梨忙得没有白天黑夜。我们俩语音的时候,我问过她,我们的年龄也不是太大,为什么要这么急火火的挣钱呢?她把我的句子修改了一下说,我们的年龄也不是太大,为什么不去急火火地挣钱呢?我无言以对。我想用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古诗词,只有在那里面,我才会明白世界存在的意义,即使数百年前的《玉蝴蝶》散发的光芒,也能映照进我的内心,让我感动和思念,那时的人儿是多么美好。这样想着,我就想大个永远住在医院就好了。不只舞会这一件事,还有她高于我的个子、过火的热情都不是我能忍受的,可是我不得不继续忍受,因为她周六回来了。
大个回来的那个深夜,我对着手机跟小梨诉说这些心理活动。小梨坐在电车上边吃着店里发的盒饭,边听我絮叨,忽然我耳边没有了声音,我说喂,小梨,怎么了?几秒后,小梨笑嘻嘻地说,继续说啊。我听出她的声音里有浓重的鼻音,我的情绪低沉了下去,也许我天天这样怼大个,是因为想念小梨也说不定呢。小梨说,东子,你再读一遍《玉蝴蝶》我听。我沉默了一会儿,挂断了电话。一股突如其来的悲伤抓住了我。我不知道其他人的恋爱是怎样的,为什么到我这里,就变得这么难呢?
我们学校只能算个职业大专,里面的学生大多是中考无望才来的这里,所以上课时你在讲台上讲自己的,他们在讲台下玩他的,互相不干涉,尤其是我的古汉语课,他们简直就是听天书。李培城跟我说,老大,上课意思一下就行了,同学们都听得心烦,尤其你讲高兴了,居然还拖堂,真无知!我说城子,自从小梨去了日本,我就只有课堂了。李培城同情地看着我说,老大,你活得太无味了。
警察上门调查大个,我没有吃惊,因为在大个家跳舞的男男女女都不像好人,当然我没有跟警察说这些,我只是说我跟大个不熟悉。警察又问每周五跳舞的事情,我摇摇头说不了解。虽然周五的舞会让我受到了极大的影響,可是我觉得这件事除非大个自己说,我没有资格去说她的私事。陪同警察一起来的是个戴红胳膊箍的大爷,那么大年纪的一位老人,居然满脸坏笑说,她干那事方便,不管是酒店还是她这个回迁房,都有地儿。我脸一红,想赶紧退回自己房间。警察吆喝住了我,让我在记录本上签个字,我仔细看了一遍那些字,都是警察问我回答的。我这才知道大个叫朱宁,我认真地在上面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大个过了一个礼拜才回来。我不知道这期间她去了哪里,也许被警察拘留了,反正她不在家我很开心。这次回来她没有敲我的门,我是通过高跟鞋判断她回来了。李培城晚上带着一条鳜鱼来找我,他说,老大,超市刚进的货就被我遇到了,赶紧烧了它,我们俩喝两杯。我就琢磨怎么烧这条鱼,厨房里除了那块腊肉什么也没有。就在这时,大个来了,她砰砰敲门喊,教授,是我,大个。李培城正蹲在矮柜前找花椒,他看了我一眼,疑虑地说,怎么会有个女人?我梨表姐知道不?我只得过去开门,让李培城看看。
大个端着一盘饺子进来了,一副很熟稔的样子。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李培城解释,李培城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看我和大个的表演。大个看着我手中的鱼说,吆!鳜鱼啊!然后第二句是跟李培城打招呼,帅哥,你好!李培城淡淡地点点头,关上橱门站了起来。大个说,这是我们酒店今天刚实验的新品,新蒜饺子,给你尝尝。我刚要推辞,李培城礼貌地接过去了,接过去以后他说,你家有烧鱼的调料吗?对于这一招,李培城很得意,他后来说他是故意留大个在这里吃饭的,以便观察我跟她有没有事。
大个几乎把她家冰箱里的肉菜都搬到我家来了,这晚,饭桌上就跟过年一样热闹。她清蒸了鳜鱼,凉拌了秋葵,清炒了上海青,红烧了排骨……厨房里全是嗞嗞啦啦的煎炒声。李培城在厨房给她打下手,啧啧赞叹说,姐,谁娶了你真是烧了八辈子高香。我坐在沙发上装作看书的样子,其实在偷眼看厨房。大个最后一趟回家,拿了一块桌布和两瓶红酒过来。看着餐桌上精美的桌布和丰盛的酒菜,我有点不知所措。李培城微笑地看我,表情莫测。
我不喜欢喝酒,跟小梨一起的时候,顶多喝点花雕。这晚我什么也没喝,吃完半勺米饭就放下了筷子。大个跟小梨不同,她不管我吃不吃东西,她只顾着跟李培城喝酒,喝得云天雾地,两瓶红酒见底后,两人拜把子成了兄弟。拜完把子李培城直接倒地打起了呼噜。大个还努力保持着形象,僵硬着身子坐在餐桌前。我说我得收拾房间了,你回吧。
大个一声不响地看着我来来回回收拾桌子。我不再理她,不是因为警察曾经调查过她,或者我们对于每周五的夜晚有分歧,而是我不擅长跟人打交道,尤其是女人,还是个个子比我高的女人。当我把屋子全部收拾干净,用消毒水拖完地以后,我发现大个在哭,我疑惑地看着她。大个说,教授,你是不是特瞧不起我?从你第一次搬来就瞧不起我是不是?我脑子里把第一次见大个到今晚快速扫描了一遍,没有任何瞧不起她的片段。我说我们都不熟悉,怎么会存在瞧起瞧不起呢?大个没有管我的解释,她用纸巾擦着泪水说,我从小都习惯了你们这种眼光。我内心想,什么眼光?女人怎么这么麻烦!
小时候由于个子高,我受到了无数捉弄,长大后因为个子高,不管男人女人都不喜欢跟我在一起,看我就像看个怪物,就连第一次见你,送你东西,你都跟躲避毒药一样躲开。
李培城被自己的呼噜呛着了,他坐起来剧烈地咳嗽。大个递给他一杯水,看他喝完。李培城喝完看了看她说,大个姐,你哭啥,谁欺负你有我。说完倒头又睡了。我敢保证,明早李培城都不会记得他们曾经拜过把子。可是大个由于这句醉话,居然重新哭起来。她边哭边说,我讨厌大个这个名字,可是我不得不让你们这样叫我,好显得我不在乎。
我感觉有点厌烦。看到我冷漠的眼神,大个在沙发上换了个姿势停止了哭泣。屋子寂静下来,我刚要站起来重新找点活干,她忽然说,哥,警察来调查我都知道,谢谢你护着我。我想说我没有护着你,可终究没有说出口。沉默了一会儿,我忽然说,你读过王世贞的《玉蝴蝶》吗?大个愣怔了一下说,什么玉蝴蝶,泰国佛牌吗?
我有点振奋,开始给大个讲《玉蝴蝶》中的“微雨梨花”,讲“浓点新茶”,最后讲到小梨。大个把脸用纸巾擦干净,安静地听我讲。她说小梨为什么去日本,就为了挣钱?我没有回答她。这个夜晚,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沉浸在古诗词中,任由小梨独自去日本打工是多么自私。
第二天是李培城把我弄醒的,他说老大,你怎么也睡这里了?我看了看自己躺在沙发上,大个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李培城没有忘记大个,可他忘记了跟大个拜把子的事,他说老大,那个高个女人叫什么?我看手机上有小梨的留言,很疑惑她怎么凌晨两点了还不睡?小梨在微信上说,东子,日本理发好贵啊,我打算留长发了。我回复说,等你长发及腰,回来我娶你。小梨没有回,她打了两份工,上网时间有限。被李培城在旁边问急了,我胡乱说,好像叫张宁或者李宁。其实她叫朱宁,这是李培城走后我想起来的。
周五晚上,大个的狐朋狗友如约而至。我用消毒液把门口地垫喷了一遍后,又鬼鬼祟祟地把电梯间和按钮面板喷了一遍。这个周五,夜晚喧嚣得跟以往没有什么不同。第二天我起来都中午了,头昏脑涨的,再这样下去可不行。
大个对我的到来很吃惊,甚至有些不知所措。客厅里还残留着昨晚的凌乱,红色的高跟鞋一只躺在门口,一只站在窗下,她红着脸收拾东西。我没有地方坐,尴尬地站在那里。从我站的地方能看到窗外大片的晚霞,如一匹绚丽的锦缎。我说你看窗外的晚霞。大个直起腰看了看窗外,没有做任何表示,又匆匆抱起沙发上的衣服进了卧室,几次下来,客厅终于空旷下来。她招呼我坐下,我就近坐在了门口的椅子上。
本来一切进行到这里我还占据着主导权,可是当我亮出手中的书时,大个忽然笑喷了。她笑着为自己的失态道歉说,教授,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笑你。我拿的是一本《诗经》,这是我最推崇的古典书籍了,可以这样说,《诗经》是文学的祖宗,没有它,中国文学将是荒芜的。我说你读过它吗?就这么一句,我彻底失去了主导权,大个在我面前不再惊慌失措,恢复了她往日的模样。
她接过书把书页翻得哗啦哗啦响,边翻边笑。她说我从初中毕业后就再也没摸过任何一本书,你今天来算是给我开了眼界。我说,朱宁,你不要自暴自弃,等你读书多了,你会明白,这个世界广袤无垠,红尘四合,烟云相连,山川万物和方寸之间皆有它存在的道理,比如你我,比如你跟舞会……大个像只灵巧的猫咪,当我沉浸在说教中时,她慢慢靠过来,把她冰凉柔软的手从我后衣领伸了进去。我打了一个激灵,我承认被吓住了,任由她像母亲搂孩子那样把我搂在怀里,手在我的脊梁上游走。我越挣扎她抱得越紧,就像在赌气或者搏斗。大个身上散发出一种好闻的栀子花味。当她用那双圆圆的孩童般的眼睛盯着我,当她温热的脸颊贴在我腮上,当她柔软的双唇捉住我的嘴时,我僵在了她的双臂之间。她喃喃自语,教授,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山川万物和方寸之间吗?我的内心被巨大的情欲和悲伤蚕食着,让我不能控制,惧怕到瑟瑟发抖。大个抱紧我试图让我安静下来。
大个把我从书本中的旖旎世界,拉到了现实中的旖旎世界。完事后,我哭了。大个怎么也想不到我会哭,她惊讶地说,你是男人不?这种事都是女人哭,哪有男人哭的?我踩着地板上那些凌乱的衣服,赤裸着不洁的身子开门回家。我在楼道里遇见了保洁,这个戴红胳膊箍的老头吃惊地望着我,以为我疯了。这没什么好羞耻的,如果能把肉体抖擞下去,我情愿只用灵魂走回去。大个在我身后喊,我以后不在家开舞会了还不行吗?都听你的还不行吗?
那一晚,我用遍了家中所有能用来洗涤的东西,肥皂、香皂、洗发液、洗衣粉……只为了洗澡。天亮的时候,我全身已经没有一块好皮肤了。站在花洒下面,我丝毫感觉不到水的冷热。
记得秋娘,家住皋桥西弄,疏柳藏鸦。翠袖初翻,金缕钩月晕红牙。启朱唇、金风桂子,唤残梦、微雨梨花。最堪夸,玉纤亲自,浓点新茶。
一切结束了。
结婚前夕,李培城陪我和朱宁拍外景婚纱照,休息的时候,他问我,老大,我给你当伴郎不?我说,随你便。他说,给你当伴郎,对不起我梨姐;不给你当伴郎,对不起你。朱宁用食指戳他,你们这些读书人,净弯弯绕,说起来你跟我还拜过把子呢,就是为了我,也得当这个伴郎。说着朱宁蹲下把我裤角上的枯草拿掉了,顺手掸了掸。李培城笑起来。李培城的笑干凈明亮,像那年的我。
责任编辑:孙孟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