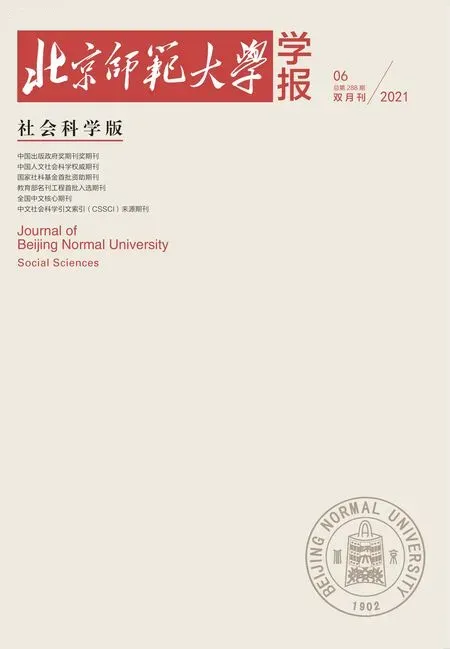论“诙谐书生”形象的生成、传播与文化构因
2021-03-26潘超青
潘超青
厦门大学 国际中文教育学院、海外教育学院,厦门 361005
“诙”与“谐”古而有之,二者合成词最早见于东汉班固《汉书·东方朔传》,又《汉书·叙传》言“东方赡辞,诙谐倡优”(1)班固:《汉书》,卷一百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58页。,用来形容东方朔之类的滑稽文人。读书人在民间文艺中常被塑造成诙谐形象,因其滑稽、迂腐之言行被扣上“酸腐”的帽子。“酸”作穷酸、尖酸解,指作品中的读书人因家贫不大方,好不合时宜地挑刺、讥讽他人而显得滑稽;“腐”为迂腐、陈腐,指文人因墨守陈规不知变通,常闹出笑话,本应体现礼仪教化的文人形象由此被拉下圣坛。书生形象多酸腐,但并非不正面,而是稳定地呈现出一种诙谐、滑稽的喜剧气质,在民间文艺中形成一种智识者形象趣味化的倾向,即以调侃的心态来看待文人,以诙谐化的方式来塑造文人,以喜剧性的形象内涵来影响人们对智识者的认知和态度。
已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一特殊形象,分别从形象学、故事类型的角度来探讨其戏剧渊源、文化意义和喜剧特质。戏曲学中关于宋杂剧的“酸目”戏的研究也为诙谐书生形象的溯源提供了重要的参考(2)参见牛刚花、陈继华:《宋杂剧金院本“酸目”新谈》,《四川戏剧》,2013年第9期;杨挺:《宋杂剧金院本戏医说药考》,《四川戏剧》,2014年第7期;杨挺:《宋杂剧耍秀才考》,《四川戏剧》,2015年第9期。。然而,从戏剧形象到文学形象发展演进的路径尚不明晰,对民间文化本源性和持续性的建构力量亦重视不足,尚未有系统梳理这一形象渊源流变的研究出现。本文尝试在中国古代诙谐文化发展的整体视域下,考察民间文化在诙谐书生形象生成、演进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诙谐书生形象是如何生成的,又怎样在民间文艺中传播、演化,进而在文人创作中形成稳定的形象类型,这是本文想着重探讨的。
一、诙谐书生形象的艺术生成
典籍记载的诙谐人物可上溯至先秦。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淳于髡、优孟、优旃在宫廷中为君王消遣娱乐,所谓“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3)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97页。,借助身处君侧又能言善辩,起到了文士般问政进言的作用。武帝时宫廷文人东方朔,因其出格的言行及富有滑稽意味的文赋作品,被扬雄称为“应谐似优”,枚皋、郭舍人、司马相如也都是汉代著名的滑稽人物。魏晋文人更是冲破礼教束缚,以不从俗流的戏谑言行树立起特殊的文化形象,所谓“魏晋滑稽,盛相驱扇”(4)刘勰:《文心雕龙》,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71页。。这些人物多是史录记载,虽为民间文艺提供了艺术想象的底本,但仍不同于有意识塑造的文艺形象。唐代开始出现以儒生为对象的戏弄样式,民间以娱乐性的演艺将儒教及文人视为戏谑调侃的对象。《旧唐书》卷一七《文宗纪》中记载了在宫廷正式场合上演戏弄圣人的杂戏,虽被斥责驱逐,但此类“戏儒戏”已不足为奇。唐代儒释道三教并立,儒家虽是正统,却也只能在释、道的夹缝中求发展,并没有在社会各阶层取得独尊的认同地位。戏儒短剧的盛行,在三教并立的文化环境下突破了尊崇儒教的文化意识,也以戏弄之风初步形成了此类表演的审美风貌,为后续借助市民文化而兴起的宋金杂剧诙谐演艺提供了可能。
如果说唐代以儒生为戏,开辟了新的戏弄类型,那么为文人形象注入稳定的喜剧特质,并推动其以类型化形象固定下来的,则在于宋金戏剧。宋代民间文化兴起,商业化的市民演出最大程度地吸纳各种伎艺的优势,形成了民间诸艺交流、融合的文艺生态,推动生成集歌、舞、剧于一体的成熟的戏剧样式——杂剧。杂剧最突出的审美意趣就是诙谐,所谓“全以故事世务为滑稽”(5)《〈都城纪胜〉:外八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7页。,“大率不过谑浪调笑”(6)夏庭芝著,孙崇涛、徐宏图笺注:《青楼集笺注》,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第44页。,是以资欢笑的“诙谐之技”,谈的都是杂剧的诙谐意趣,而宋金杂剧整体上的诙谐氛围奠定了诙谐书生形象的基本特质。
《官本杂剧段数》和《院本名目》收集杂剧、院本剧目时有着明确的“类”意识,首先以伎艺形式划分,其次依据脚色或内容排序,其中有一类“酸”剧与文人形象有关。“酸”剧主要有:
《褴哮负酸》、《食药酸》、《眼药酸》、《急慢酸》、《秀才下酸擂》、《四酸逍遥乐》、《合房酸》、《麻皮酸》、《花酒酸》、《狗皮酸》、《还魂酸》、《别离酸》、《三缠酸》、《谒食酸》、《三楪酸》、《哭贫酸》、《插拨酸》、《酸孤旦》、《四酸擂》、《四酸讳偌》、《四酸提猴》、《酸卖俫》、《是耶酸》、《怕水酸》。
什么是“酸”?明佚名《墨娥小录》卷一四《行院声嗽》云:“秀才,酸丁。”“丁”为附加词尾,或作“俫”。明代《六院汇选江湖方语》云:“酸子,乃秀才弄耍老子者。”明胡应麟《庄岳委谈》云:“世谓秀才为措大,元人以秀才为细酸。”(7)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一,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58页。“细”,含文弱俊秀意,与“细旦”之“细”类同。酸、细酸、酸丁、酸俫指的都是秀才。那为什么称秀才为醋大(措大)呢? 唐末苏鹗在《苏氏演义》中有过解释:“醋大者,或有抬肩、拱臂、攒眉、蹙目以为姿态,如人食酸酣之貌,故谓之醋大。大者广也、长也,篆文大象人之形。”(8)苏鹗:《苏氏演义(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0页。以人食醋后窘态来命名秀才,姑且为一家之言,但透露出该称呼有戏弄、调侃之意。宋人“恬于习玩,每闻以此称之,辄指为轻己”(9)洪迈:《容斋三笔》,卷二,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第345页。。时人嘲笑文人,多以“醋大”(措大)来称呼。《唐阙史》记录了唐末宦官、儒臣的一则趣事,说当时的宦官首领派亲信去尚书省打探消息,得到了一个“醋大知之久矣”的回报。书中释:“中官谓南班,无贵贱皆呼醋大。”(10)高彦休:《唐阙史》,《大唐新语(外五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38页。说的是无论贵贱,一律用“醋大”之谑称来指代文官群体,含有明显的贬义。《能改斋漫录》亦载有宋太祖赵匡胤轶事一则:
太祖尝与赵普议事,有所不合。太祖曰:“安得宰相如桑维翰者,与之谋乎?”普对曰:“使维翰在,陛下亦不用,盖维翰爱钱。”太祖曰:“苟用其长,亦当护其短。措大眼孔小,赐与十万贯,则塞破屋子矣。”(11)吴曾:《能改斋漫录》,上海:中华书局,1960年,第302-303页。
在帝王看来,只要能为其所用,给点钱不算什么,武将出身的宋太祖赵匡胤骨子里对文人的轻侮之意可见一斑。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还记载了一则赵匡胤称陶谷为措大的趣事。
陶尚书谷为学士,尝晚招对,太祖御便殿,陶至望见上,将前而复却者数四,左右催宜甚急,谷终彷徨不进,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顾左右取袍带来,上已束带,谷遂趋入。(12)欧阳修:《归田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页。
陶谷几经催促却只肯在殿门外止步不前,直至太祖着好礼服,陶谷方才进前拜见。对此,太祖笑称“此措大索事分”,就是说,“这个读书人拘于礼节,真是没事找事!”元杂剧《救孝子》中的书生杨谢祖的母亲听说儿子想要弃儒去作“令史”时,马上坚决反对,说:“哎!你个儿也波那,休学这令史,咱读书的功名须奋发,得志呵作高官,不得志呵为措大。”(13)臧晋叔:《元曲选》,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757页。由这几则材料可见,“醋大”和“措大”都是当时广泛使用的戏称,用于讽刺文人的穷酸、迂腐、拘礼、无能,无论是朝堂君臣还是世俗百姓,倘见不惯文人的酸腐作态都会用此来称呼对方。
杂剧剧目可以形象类型来命名。对于“酸”剧有两种理解,一是脚色义,如“旦”、“孤”,因为“酸”是民间对穷秀才和落魄文人的称谓,所以“酸”剧就是秀才剧。郑振铎将“褴哮负酸”、“秀才下酸擂”、“急慢酸”、“眼药酸”、“食药酸”五本视为一类,并解释为“盖述秀才们的事以为笑乐者”(14)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57页。。“酸”剧又不完全是秀才剧,其中有一类与医生职业有关(如《食药酸》、《眼药酸》),当然,古时医者也可归于广义的知识阶层。还有一类“酸”不似名词,而是用作动词(如《合房酸》、《麻皮酸》、《花酒酸》、《狗皮酸》、《还魂酸》等),因此,胡忌认为“酸”一方面指“以‘末’扮秀士念文句”,相当于表演形式;另一方面表示多以穷酸之态呈现的秀才(15)胡忌:《宋金杂剧考(订补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10、115页。。刘晓明认可这种说法,认为“酸”有两种含义。一是作为人物的“酸”,即所谓酸丁、儒酸;二是作为表演艺术形式的“酸”,凡以“酸”为尾名者皆为此类(16)刘晓明:《杂剧形成史》,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24页。。不学无术的文人,其文章诗作难登大雅之堂,却常作酸诗酸文,以酸话逗笑尤为多见。《南唐书》载,“(韩)熙载性懒,不拘礼法,常与(舒)雅易服燕戏,猱杂侍婢,入末念酸,以为笑乐。”(17)马令:《南唐书》,卷二二,《舒雅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47页。“入末”即“入抹”,化妆扮演之意,“酸”为酸腐书生写的谐谑逗笑之文,即以化妆扮演的方式,以酸俗诗文来进行一段诙谐、滑稽的表演,博人一笑。宋初钱熙曾撰《三钓酸文》(18)文莹:《玉壶清话》,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59页。,《梦粱录》记录杭州夜市“有李济卖酸文”(19)吴自牧:《梦粱录·元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6页。,都属于此类笑料。
除了“酸”剧,《官本杂剧段数》和《院本名目》中还有一类“哮”剧也与秀才有关:
《双拦哮六幺》、《双哮新水》、《三哮卦铺儿》、《三哮揭榜》、《四哮梁州》、《三哮上小楼》、《三哮文字儿》、《双哮采莲》、《三哮好女儿》、《三哮一檐脚》、《褴哮合房》、《褴哮负酸》、《褴哮店休妲》、《哮卖旦》。
关于“哮”的含义存在很多说法。“哮”多与“褴”联系,如《褴哮合房》、《褴哮负酸》、《褴哮店休妲》,周贻白认为“哮”为“褴哮”的简称,“哮”取咆哮之义。胡忌不赞成此说,他指出“哮”如取“喧嚣”义,则并非人物称谓,同列剧目的“旦”、“孤”、“酸”都有脚色义,“哮”也不应出此范畴以外。胡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哮”所指,但认为“‘哮’亦属于男性人物无疑”(20)胡忌:《宋金杂剧考(订补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10、115页。。有研究者认为“哮老”即“醋”,“醋”即“酸”,“酸”即“秀才”,由此推知“‘哮’可能是市井江湖对秀才一类读书人的另一种俗称,缀以‘哮’的剧目的内容当与秀才书生有关”(21)景李虎:《宋金杂剧概论》,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05页。。本文同意此观点,首先,剧目中,“哮”在剧目中多用作主语,未呈动作和表现义,当是人物名称;其次,冠有“哮”的剧目,从剧名上看多与书生有关,如《三哮揭榜》、《三哮文字儿》、《褴哮负酸》,且与“酸”同列,也提示了“酸”与“哮”的内在联系。结合《行院声嗽》的释义,“醋”或是“醋大”的简称,指秀才,“哮”当亦指秀才,“褴哮”即褴褛衣着的贫困书生,与所谓“穷酸饿醋”不谋而合。
在“酸”剧和“哮”剧之外,金院本中还有专门的秀才家门,名目有十:
《大口赋》、《六十八头》、《拂袖便去》、《绍运图》、《十二月》、《胡说话》、《风魔赋》、《疗丁赋》、《牵着骆驼》、《看马胡孙》。
以上剧目从篇名来看不乏戏谑之义,其中已出现以“风魔”来形容秀才的《风魔赋》,《胡说话》想来也是用秀才的酸话诨语来耍笑,前文所述的《哭贫酸》似与秀才以家贫卖惨博取同情有关,《疗丁赋》更是堂而皇之地咏赋“钱”,对穷酸秀才来说自有一番反讽意味。院本名目“诸杂大小院本”中还有《花酒梦》、《穷相思》等,或亦属以思念异性之情态谑浪打诨(22)杨挺:《宋杂剧金院本戏医说药考》,《四川戏剧》,2014年第7期,第28页。。这些连同舞队《耍秀才》、题目院本《呆秀才》共同构成了宋金杂剧中秀才剧的基本内容。
对秀才书生调侃式的称呼,借助杂剧的戏弄手法,形成富有喜剧意味的固定形象。宋杂剧无存本可考,北京故宫现存两幅绘有宋代杂剧形象的绢画,周贻白和廖奔都进行过考证,认为其中一幅描绘的就是官本杂剧《眼药酸》(23)廖奔:《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164-167页。。画中绘有两人,一人为兜售眼药的江湖郎中,身上挂有成串的眼珠子,冠前、挎袋上亦有眼球装饰;另一人为市井打扮,右手食指指着右眼,好似在说自己眼睛不适。此角色手执一杖,摞起袖子的手臂上有“点青”,背后插一破扇,上有一草书“诨”,明确了其为打诨角色(24)扇上书有一草体字,模糊不清。周先生判断是个“净”字,从而认为插扇者由副净扮演,江湖郎中则是由副末扮演的酸。而廖先生认为扇面草字为“浑”字,副末色打诨,插扇者为副末,江湖郎中由副净扮演。两者对角色看法不同,但都认为此画描绘的是官本杂剧《眼药酸》。。二人组合符合宋杂剧的表演形式,《梦粱录》卷二十“伎乐”条云:“且谓杂剧中末泥为长,每一场四人或五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两段。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或添一人,名曰装孤。……大抵全以故事,务在滑稽。”(25)吴自牧:《梦粱录·元宵》,第190页。杂剧的五人团队中,表演集中在副净和副末之间,副净的职能是发乔,装呆弄痴,副末的职能是打诨,嘲弄戏耍,二者之间构成了发乔与打诨的固定逗笑模式。《青楼集志》和《南村辍耕录》中都云:“末可扑净”、“末可打副净”,必要的时候可以道具“嗑瓜”来敲打副净,强化喜剧效果。绢画中,副末色“手执一杖”即是杂剧表演常用的“嗑瓜”,想必是副净色郎中做了什么出格的事,配合“酸”的形象特色,或是自作聪明地兜售眼药,或是言语尖酸惹怒了副末色扮演的市民,被当头一棒。“酸”剧和“哮”剧都以戏弄秀才为主,《耍秀才》、《呆秀才》、《风魔赋》等剧目名称也可见“戏弄”含义。
梳理戏剧的早期形态,从唐参军戏发展到宋金杂剧,核心的戏剧手段是“戏弄”。“戏弄”的对象众多,上至皇帝、高官,下至老妪、走卒,遍布社会各个层面,在金院本的“家门”中就有14类不同身份和行业的人群,秀才只是其中一类。虽然杂剧人物庞杂,涉及社会方方面面,但无论是什么形象,都是由副净和副末来表演,不管派生出多少的人物形象类群,都跳脱不开戏弄性脚色的功能限定,即发乔和打诨的固定模式,必须在脚色功能的定位下完成表演。就如同后世成熟的脚色行当,净可扮演各种形象,但都要服从净的声口,以净的脚色规约来扮演。据此推想,酸、哮剧的创作初衷并非为了塑造秀才形象,而是早期戏曲诙谐性表现手法与人物形象类群相遇和的结果,体现了脚色制形成过程中,功能性与类型化相碰撞所产生的艺术创造力。民间文人形象自此打破了现实形象的限定,被赋予了诙谐、滑稽的性格气质,并深植于民间戏剧形象图谱中,伴随着戏剧与其他民间文艺的交流而传播开来。
二、诙谐书生形象的发展与传播
早期戏曲形象在宋杂剧整体的诙谐氛围中获得了形象特质,通过不断吸纳、融合相邻伎艺的资源来丰富诙谐意趣的表现。同时,杂剧诙谐片段和戏剧方式也以各种形态加入民间文艺的交流融合,不仅戏曲、话本等口传伎艺中出现了诙谐书生形象,杂谈小说、民间故事、文人笔记等书面文学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形成一个借助戏剧诸艺推动发展的传播路径。
首先,宋杂剧诙谐片段短小灵活,可被直接用于各种戏剧结构中。如元佚名《张公艺九世同居》杂剧二折,剧中四秀才应试的关目隐现金院本《四酸擂》。剧中,两个滥竽充数的秀才来应举,想蒙混过关,恰好碰上想作“一头儿买卖”的贡官,彼此你来我往,酸言酸话,笑料不断:
(贡官云):兀那两个是甚么人?(张狂云):是应举的秀才。(贡官云):你来应举,会吟诗么?(张狂云):会吟诗,会课赋,丢了斧子拽的锯。(贡官云):这壮士,你来应举?(李柰云):学生我来应举。(贡官云):你会甚么武艺?(李柰云):我十九般武艺都会。(贡官云):只有十八般武艺,偏你十九般,那一般呢?(李柰云):我会打筋斗。(26)《张公艺九世同居》,《孤本元明杂剧》(无编者),卷一,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
后来又添两酸,凑成四酸比试应举,后来者学识渊博,为偶然出现的考官所赏识,此“擂”才见分明。虽是多人表演,但对话的两人言语之间保持了副净装痴、副末戏耍的古朴样式,可供一窥院本《四酸擂》的面貌。又如《吕蒙正风雪破窑记》,现存是明人改本,当是由宋、元人剧作承续而来。据南戏改编的明钞本《彩楼记》第八出“夫妻归窑”,似院本名目《合房酸》的戏剧方式,叙吕蒙正夫妇二人婚后入居破窑,家徒四壁却爱粉饰,明明是瓦窑门低进不去,却称之为“礼门义路”,需“鞠躬施礼,摇摇摆摆”,土坯房环境简陋,却托词“平生爱住泥土房,就地安排胜书堂”,还给一穷二白的家里安上“风扫地”、“月点灯”等“景致”,足见书生酸腐之气。
灵活运用诙谐关目有效地增添了戏剧的诙谐意趣,但滑稽短剧之类的片段还是游离于剧情主线之外,直至元代发展出成熟的戏剧形态和故事编演,有关文人的诙谐片段才真正获得形象意义。元杂剧塑造了一批诙谐书生形象,集中在表现男女爱情的三十余部戏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西厢记》中“风魔书生”张生,完全颠覆了社会文化对读书人形象的设定。他性格跳脱,忽喜忽忧,或张狂或低落,忽自吹自擂,忽束手无策,既有读书人的迂腐和傻气,又带有年轻士子的冲动鲁莽,“酸”与“狂”共同构成了其别具一格的“风魔”性格。
张生的“酸”首先表现为一股“呆气”、“傻气”,不管是实际行动还是内心幻想,都与文人的清雅睿智相差甚远。他初见莺莺便日夜牵念,“昨日见了那小姐,到有顾盼小生之意”,颇有些自作多情,但也不失可爱。初次见红娘,自报家门之后,突然冒出一句“并不曾娶妻”,立即被红娘抢白“谁问你来?”红娘奉老夫人之名来请张生,人家“请字儿不曾出声”,张生“去字儿连忙答应”。为赴约,张生还非常认真地打扮自己,“皂角也使过两个也,水也换了两桶也,乌纱帽擦得光挣挣的”(27)王实甫:《西厢记》,王季思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第66、68、7页。,还请红娘当镜“照照”自己,“小生客中无镜,敢烦小娘子,看小生一看何如?”还配上舞台上“来回顾影”的扭捏姿态,惹得红娘嗔怪,唱起:“来回顾影,文魔秀士,风欠酸丁。下功夫将额颅十分挣,迟和疾擦倒苍蝇,光油油耀花人眼睛,酸溜溜螯得人牙疼。”(28)王实甫:《西厢记》,王季思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第66、68、7页。凌蒙初批曰“酸得妙,自是元人宾白”(29)凌蒙初:《西厢记》,第二本第三折张生白之眉批。。张生之“风魔”还表现在其“癫狂”,不寻常地唐突莽撞,完全没有读书人的庄重姿态。他在佛殿初见莺莺便惊呼:“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业冤”(30)王实甫:《西厢记》,王季思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第66、68、7页。,听其答话,惊为天籁,急于表白,但碰到挫折便惊慌无措,进退失据。老夫人赖婚,只许张生、莺莺以兄妹相待,张生备受打击,却是“低首无言自摧挫”,既可怜又无奈。《闹简》一出,莺莺请红娘传书给张生,却瞒了红娘,连红娘也以为是坏消息,张生听了犹如晴天霹雷,当下跪哭在红娘面前,“小生这一个性命,都在小娘子身上”(31)王实甫:《西厢记》,王季思校注,第107、107-108页。。可等到展读小姐的信柬,风魔劲又上来了,欣喜若狂,说:“呀,有这场喜事,撮土焚香,三拜礼毕。早知小姐简至,理合远接,接待不及,勿令见罪!”(32)王实甫:《西厢记》,王季思校注,第107、107-108页。大悲大喜之间,将张生的风魔个性鲜明地刻画出来了。如张生这般,元杂剧中的书生普遍带有迂腐之“酸”和天真之“傻”,有着非常强烈的喜剧色彩。如《金钱记》中的韩翃为了追求柳眉儿,在王府中贸然撞人被吊打一顿,为接近柳眉儿甘做王府的教书先生,终日把玩定情信物,结果被发现再次被吊打。虽才高八斗却为情痴傻,每每做出傻事遭到惩罚却让人心生笑意。《曲江池》中的郑元和初次见到李亚仙几乎不能自持,几次三番的坠鞭动作将其急于求成而又不得的内心焦灼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极富喜剧效果。《百花亭》中的王焕为能与贺怜怜相见,“费心机,恨不得钻天掘地”,不惜屈尊装成卖梨条的小贩。《金线池》中韩辅臣因误解不辞而别,回来向杜蕊娘求和却还摆谱犯酸,被抢白后不顾斯文赶紧道歉,最后还拿出撒泼耍赖的架势要求好友府尹“公堂解决”,强词之下颇能显示他无计可施的窘态。由宋杂剧演化而来的诙谐片段已融入到元时杂剧的整体剧情中,人物之间不再是刻意的戏弄调笑,也不仅为了博人哄堂,在形成诙谐、热闹的喜剧气氛的同时,更兼有刻画人物性格、助推情节发展的功能。
诙谐书生形象在民间演艺中不断发展,形象的定型和传播还借助了民间艺术的类型化特点。民间曲艺处于广泛交流的文艺生态中,同一题材、形象在不同艺伎中反复出现,杂剧、院本、话本、戏文、笔记小说、历史传记等,大多数都有所本,几乎没有一本是作者杜撰的(33)参见罗锦堂:《锦堂论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第99-112页。。要使市井民众更易于理解和接受,都趋向清晰的结构线索、鲜明的形象塑造、简明的语言风格以及故事类型的高度重复。故事类型学研究指出,在民间故事中“变换的是角色的名称(以及他们的物品),不变的是他们的行动或功能”,这就使我们有可能根据角色的功能来研究故事(34)〔俄〕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7页。。以元杂剧为例,形象设置往往依据其形象身份有所分工,女性往往是故事核心,功能上是被欺压、被侮辱的;权贵官员出场总是欺压百姓,是灾难的发动者;老年角色(父母或虔婆)多为感情发展的障碍等等。爱情故事中的男女形象定位更具元代特色,女性无不积极、自主,推动事件发展,男性多缺乏主见、进退失据。不同形象类群具备不同的功能,而功能的一再重复则强化了形象的类型化意义,不仅在编剧、演剧上更具效率,也符合市井百姓在民间文化塑造下的阅读期待和审美反应。诙谐书生形象多出现在爱情戏中,起到配合和衬托的作用,逐步成为一种典型形象确立下来,为后世文学作品、市民文艺所不断效仿。
明清小说大都经过世代累积,特别是戏曲化的过程。所谓“戏曲化”,指的不仅是故事内容纷纭递变的演进,同时还有艺术手法潜移默化的影响。《梦粱录》、《醉翁谈录》均记载了民间说唱、南戏、杂剧对作家的影响,吴自牧言“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35)吴自牧:《梦粱录·元宵》,第194页。,罗烨言民间戏曲“遣高士善口赞扬”、“使才人怡神嗟呀”(36)罗烨:《醉翁谈录》,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5页。,无不说明民间戏曲的表现形式为百姓喜闻乐见。基于民众的审美需求,文人作家认同戏曲的形象类型和叙事手法,推动此类形象在舞台表演和文本书写中得到进一步强化。民间故事、杂谈小说、文人笔记中逐步出现结合剧情的诙谐形象,甚至发展出专门的文人笑话。此类短小精悍的文人笑话成为文人创作进一步深化的基础,围绕书生的迂腐性格、浅薄才学和窘迫境遇,发展出不同的笑话类型。
首先是以读书人迂腐迷信为笑料,因文人所恪守的陈规与现实环境不相符而产生滑稽感。如宋代陈正敏《遁斋闲览·谐噱》载有秀才“应举忌落字”的小故事。秀才犯忌落第,不喜用“落”字或音似,常以“安康”取代“安乐”,后派仆人看是否高中,仆人也只能回答“康了”(37)原文为:柳冕秀才性多忌讳,应举时同辈与之语,有犯“落”字者,则忿然见于词色。仆夫误犯,辄加杖楚。常语“安乐”为“安康”。忽闻榜出,亟遣仆视之。须臾,仆还,冕即迎问曰:“我得否乎?”仆应曰:“秀才康了也。”后明代冯梦龙编纂《古今谭概》迂腐部第一《忌讳》也收入,名“秀才康了”。张贵胜辑《遣愁集》卷一《绝倒》,也有“柳冕忌落”,似由《遁斋闲览》演化而来。。读书人饱读诗书,却受困于陈规,为避忌讳想尽办法,在人前求全体面,却暴露了虚弱本质,闹了笑话。第二类以读书人不学无术、死读书来制造笑料。如明万历刊刻《续金陵琐事》下卷《书低》载有一则书生趣事:秀才借用僧房读书,书童反复取来典籍给他,他却都抱怨过“低”,僧人以为是不满于经典,原来居然是嫌拿书当枕不够高(38)原文为:友人谈戏语,讥秀才云:一秀才赁僧房读书,惟事游玩而已。忽未午归房,呼童取书。童持《文选》视之,曰:“低”。持《汉书》视之,曰:“低”。又持《史记》视之,曰:“低。”主僧大诧曰:“此三书,熟其一,足称饱学。俱云低者何也?”试窥之,乃取书作枕耳。见周晖:《续金陵琐事》,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238页。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成书的陈皋谟辑《笑倒》(系《增订〈一夕话〉新集》第三卷的一部分)中的《书低》引用了该故事。乾隆四十六年(1781)刊刻的游戏主人辑《笑林广记》卷一《书低》亦转抄了这则,文字略有改动。这一故事类型,现当代仍在天津等地流布,如《少爷读书》(见《天津民风》第8辑)《秀才索书》(见《民间笑话大观》)。。所谓的饱学之士悠哉混日子的窘态被拿来揶揄逗趣。大量故事通过白字、错字、取名等来讥讽书生学艺不精,如《解愠编》卷一《聂字三耳》,写一个书生写字多误落,“阝”该右不右,该左不左,反复被责罚,后有一个聶姓者托写首状,直接被吓退了(39)原文为:一书手写字多误落,遇造册时,将“陈”字着“阝”于右。被官责二十。书手性愚,误凡“阝”俱当在左,后又将“郑”字着“阝”于左,又被官责二十。后有聶姓者托写首状,书手大呼曰:“我因两耳,一连打了四十;若与你写状,岂不送了我性命!”见乐天大笑生辑:《解愠编》,《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127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53页。冯梦龙辑《广笑府》卷一《聂字三耳》,近人憨斋士篆辑《笑林博记》卷四《聂字三耳》,与此相似。诸如此类的故事还有康熙年间刊刻的石成金撰《笑得好》初集《笑话一担》,讲了一个秀才乱起名的故事,清光绪八年刊刻的小石道人辑《嘻谈录》卷上《喜写字》、《读白字》等亦属此类。这一故事类型,当今仍广为传播,上海等地流传《白字先生》、《读白字》、《错别字先生》等,湖北、广东等地流传《秀才取名字》、《笑话一担》等,河南、山西等地流传《求你别写》、《爱写字》等。参见《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8年。。第三类围绕书生的穷酸和爱面子。如《笑林广记》中的《咬饼》就是个颇具趣味的故事。穷酸老师饥饿,用咬出个月亮来哄骗孩子的吃食,这本身就很好笑,偏偏碰上不舍得食物的纯真孩童,师生抢饼,居然把孩子手指咬伤了,更增笑料。老师没有他法,只能以停课来安抚孩子,想来平时也自知上课无趣,邀买也没有本钱,还不惜自辩为狗,穷酸之窘态跃然纸上,妙趣横生(40)原文为:一蒙师见徒手持一饼,戏之曰:“我咬个月湾与你看。”既咬一口,又曰:“我再咬个定胜与你看。”徒不舍,乃以手掩之,误咬其指,乃呵曰:“没事没事,今日不要你念书了,家中若问你,只说是狗夺饼吃,咬伤的。”见徐如江、徐侗:《明清通俗笑话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7页。。
从民间文艺到文学书写,诙谐书生形象逐步摆脱爱情戏中的角色定位,体现出更具文人特点的诙谐性格,为丰富叙事文学的人物形象塑造提供了素材。明清文学谐谑之风盛行,文人搜索民间故事笑话加工润色或亲自创作,官场、市井、儒林无不可戏谑,笑话这类短篇叙事所勾勒的诙谐书生形象,几乎成为白话小说中文人形象的主要面貌。《儒林外史》中,有为宴请精打细算的胡三公子,宴请前买鸭子怕不够肥,拔下耳挖来戳戳鸭脯上的肉,买馒头也随意赖账,硬要用两个钱买三个钱的东西,临了还把剩下的骨头果子装回家。西湖雅集,本是风雅之事,与胡三公子的寒酸小气相联系,让人忍俊不禁。还有尚在丁忧的范进去汤知县处打秋风,饭前各种忸怩作态,为遵制反复挑剔餐具,最终还是忍不住吃了个大虾元子,原先居丧守制的道学形象瞬间瓦解。再看临终前不忘灭掉多余灯芯的严监生,坚持着伸着两个指头,等着赵氏掐灭一个灯芯方才安心咽气的场面令人哭笑不得,也使之成为古代文学中最经典的吝啬鬼形象。他们虽然有着各种性格弱点,却无一不是以诙谐可笑的面貌示人,喜剧性的塑造手法在成熟的叙事文学中自然蕴含着写作者更深的创作意图,但从形象发展轨迹看,构成形象最核心的“诙谐”意趣自形象生成时就已深植其中,借助民间文艺圈共享故事和形象类型的创作手法,完成了从口头传播的民间文艺向文人书写的书面文学传播发展的进程,最终成为稳定的文学形象类型。
三、诙谐书生形象传播的社会文化构因
自宋杂剧整体性的诙谐氛围奠定书生形象诙谐化的基础,经过了游离性的滑稽短剧片段、融入戏剧表现的形象塑造手法、民间文学中的笑话短文单元、有意识的文人形象塑造等发展阶段,最终成为稳定的文学形象类型。这一形象能经久不衰,一方面体现了民间文艺寻求突破创新、不断自我完善的艺术生成力,另一方面也与社会文化需求密不可分,不同创作主体的文化需求为诙谐书生形象提供了持续演进的动力。
艺术形象首先是社会形象的反映,唐宋元三代正是文人地位跌宕起伏的历史阶段。隋唐之后,随着门阀制度的逐渐瓦解,更多士子通过科举获得了社会体系内的上升途径,文人地位整体上是提高的,宋代更是平民阶层知识者的黄金时代,但就普通读书人来说,通过科举出人头地的希望仍然渺茫。隋朝以初策登第为荣,唐宋科举取士,春试及第称进士,乡试不中则只是秀才,久居为秀才者被视为无能之辈,平民阶层事实上累积了大量出仕无望也无一技之长的文人。元代时政剧变,停开科举长达80年,儒生们失去“四民之首”的地位,更失去了政治上的进身之阶,社会地位骤降。元代郑思肖《所南集》中称“七猎八民九儒十丐”,与谢枋得《叠山集》中“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虽略有出入,但是“儒”的地位低下,仅比乞丐高一级,却是事实。元代民间亦有俗谚曰:“生员不如百姓,百姓不如祇足”(41)李继本:《一山文集·与董涞水书》,李伸:《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79页。,“小夫贱隶,亦皆以儒为嗤诋”(42)余阙:《青阳先生文集》,卷四,《恭泰父文集序》,《四部丛刊续编》,集部,影印明刊本,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失去社会地位的儒生为人所轻视,百姓更容易地看到了读书人软弱、可笑的另一面,而将他们塑造成文艺作品中被戏弄、揶揄的对象。
将形象诙谐化作为一种平民的文化意趣,首先体现了凡俗百姓对喜乐生活和精神愉悦的追求。宋元杂剧与市井文化息息相通,所体现的滑稽诙谐已经超出了单一伎艺的范畴,代表着中古民间文艺最主要的审美取向。无论是凡俗市井的题材内容、刻意弄丑的形象造型还是插科打诨的戏剧手段,无一不朝着娱乐大众的方向努力,这是市民文艺特点所决定的,也提示我们应从精神满足的层面来理解形象的诙谐性。对“笑”的追求是人们基本的情感需求,与人们追求快乐的内心需求相契合,“笑本身所包含的解脱之感,这是自然人力图摆脱社会束缚与传统习俗的一种解放。”(43)〔英〕阿·尼柯尔:《西欧戏剧理论》,徐士瑚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第251页。喜剧以艺术之轻松抚慰了人生之沉重,诙谐书生形象是有趣的,有妙趣横生者,亦有鄙俗粗陋者,无论形式怎样,百姓都喜闻乐见,在丰润人心、平衡社会情感、满足文化需求方面有着特殊价值。
其次,就书生形象而言,对智识者的调侃戏弄最初反映着民间文化的心理需求。大多数仕途无望又不与农商相类的书生秀才生活能力低下,却因为掌握知识而具有心理上的相对优势。普通人对他们一方面羡慕尊崇,另一方面又心存抵触和不满。在民间文艺中,通过贬低更高阶层来弥补内心的缺憾,是常见的一种心理补偿方式。戏弄那些文化阶层高于自己的书生文人,既可以寻求欢乐,又可以反衬出一个更高大、更有自信的自我形象,人们通过会意一笑,发泄了对现实的不满,释放了心理压力,从而获取内心的平衡。而这种“贬损”又是有一定尺度的,攻击文人的弱点或包含歧视意味的戏谑虽然降格了对方,但从社会心态上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很难真正“好笑”起来,因此,诙谐化就成为一种无伤大雅又能降低其优越度的有效手法,在民间戏俗同构的文化氛围中广为传播。
当诙谐书生形象由民间文化进入文人书写,依然保留着诙谐的表现,但文人笔触包含着更为审慎的态度。诙谐化手段往往是单向度的,即底层文化对智识阶层可抱有戏弄、调侃的态度,后者却很难以相似的方式去表达好恶,因为面对弱小于自身的阶层,任何一种调侃意味都容易滑向恶意。当文人以诙谐手段塑造文人形象时,难有单纯的“好笑”,一方面出于同为知识者的感同身受,选择文人作为调侃的对象,以玩笑的形式揶揄、作弄,在刻画具体形象时不免带有自我意识的投射,戏谑之余也寄寓着同情。另一方面,文人的诙谐始终表达着基于严肃立场的价值取向,知识者的人性弱点只是世风浮薄的代表,“不以庄言责之,而以谑语诛之”(44)吴敬梓:《儒林外史·闲斋老人序》,济南:齐鲁书社,1994年,第50页。,对其戏谑嘲讽实质上延续了传统的文学讽喻功能。从文人所辑录的历代俳优做戏的记载不难看出,单纯的诙谐表演并不多见,几乎都关涉世态时事,对此类诙谐演艺的价值认定,始终在于“寓谏净于诙谐中”。而对如范进之类悲剧性人物的诙谐化塑造,则代表着写作者更警醒的艺术选择。寓庄于谐,发警世之言,基于文人主体创作的需求,诙谐成为一种创造性意义建构的有效手段。也正是在文人笔下,诙谐书生这一民间文化孕育生成的艺术形象得以提升文化品格,成为兼具审美意趣和社会价值的形象类型。
从宋杂剧的“酸”剧、“哮”剧,元杂剧的“风魔书生”,到明清小说笔记中各类“酸腐文人”,诙谐书生形象一脉相承。此类形象的滑稽性源于古代文人在现实境况中反映出的酸腐个性,作为文艺形象的“酸”最初来自宋金杂剧中脚色装痴弄丑的特点,具有“丑”的形象功能,是戏曲早期脚色的功能性遗存。杂剧形象在宋元与民间文化融合交汇,暗合了底层百姓对知识文化者的态度,并在戏曲形象类型化的过程中固定为滑稽形象留存下来。单元化的喜剧形态易于进行艺术移植、组合、加工,推动杂剧的诙谐片段和戏剧方式融入其他民间文艺类型中,形成了一个借助口传戏剧向书面文学发展的传播路径。民间文学延续了早期戏剧的诙谐形象,一方面说明了此类形象深受百姓喜爱,是民间自主的文化选择;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民间文艺的艺术生成力。戏剧艺术因子与社会文化心理需求相结合,共同缔造了诙谐书生形象,并使其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在文化脉络中延续,持久地发挥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