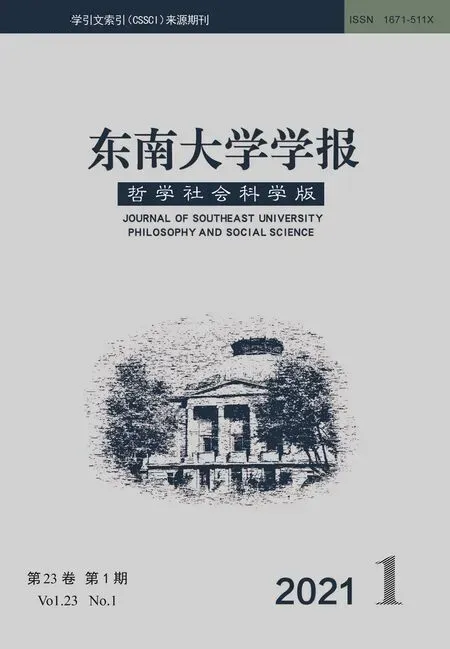智能投顾监管的国际经验及其借鉴
2021-03-26朱紫涵
朱紫涵,余 涛
(1.上海交通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0030;2.东南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一、引言
方兴未艾的智能投顾业务或许是引领我国金融创新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但是其飞速发展的现实并不能掩盖其所面临的监管法挑战。传统的投顾业务分为投资咨询服务和资产管理服务,二者实行分类管理,采用不同的市场准入和监管标准,因为投资咨询服务引致的风险较资产管理服务更低,故而投资咨询服务的准入门槛以及合规负担较后者也更低。而智能投顾使投资咨询服务和资产管理服务在事实上合而为一,那么到底是将传统投资顾问服务的监管规则和资产管理服务监管规则叠加适用于智能投顾,还是单独为智能投顾寻求一套独立的监管规则,这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对前述问题进行思考的一个惯常路径是根据“穿透式”监管的需要,把传统投资顾问和资产管理业务中体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体制与规则适用于智能投顾。不过,根据学术界和实务界的乐观描述,智能投顾所拥有的“智能”不但和人类“智能”一样具有独立自主性,而且能够比人类智能更强大和完美。此时再把基于有限理性而生的人类规则移植到智能投顾主体之上,势必会出现规则供应与需求不匹配的情况。这就使智能投顾监管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不适用人类中心主义的规则,那么智能投顾所带来的金融风险便无法得到控制;如果适用人类中心主义的规则,那么智能投顾的规则需求又将得不到满足。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一个常见的研究结论就是“既要防风险,又要促创新”。然而,这种价值组合除了能提供绝对正确的价值说教以外,并不能为实践提供真正有效的监管策略(1)彭岳:《互联网金融监管理论争议的方法论考察》,《中外法学》2016年第6期。。
面对这样一种监管困境,我们可以借鉴哈特的理论来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哈特认为,法就是第一性义务规则和第二性规则的结合。其中,第一性义务规则是一个原始社会群体对自己的标准行为模式的一般态度,它由若干关于人性和生活中最明显的公理性事实所支撑。这些地方性规则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它仅仅是某个群体所适用的单独标准,无法自然地推广开来。对其他群体来说,这种地方性的合乎人性和公理事实的标准就具有不确定性。为了克服这种不确定性,就需要引入第二性的承认规则(2)[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93-100页。。智能投顾监管可以被看成是哈特所说的原始社会,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在这个原始社会中提炼出群体成员对自己标准行为模式的一般态度,方法就是寻找该原始社会中的人性内涵以及公理性事实。
本文选取了美国、英国、加拿大三国关于智能投顾监管的实践,将它们视为智能投顾监管的“原始社会”,以考察它们在实践中所形成的行为标准。之所以选择这三国作为考察对象,是因为它们在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具有典型的代表性(3)李经纬:《构建中国智能投资顾问领先模式——基于市场需求与全球实践》,《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后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将简要介绍美国、英国、加拿大的监管实践,并对它们的做法进行评析;第三部分将提炼出对我国有借鉴意义的经验;第四部分是结论。
二、他山之石:智能投顾的国际监管经验之简析
(一)美国的监管构造:自律监管和官方监管的协同作用
智能投顾最早于2010年左右起源于美国(4)Megan Ji, “Are Robots Good Fiduciaries? Regulating Robo-Advisors Under the Investment Advisers Act of 1940”, Colombia Law Review, 2017, 117(6), p.1544.,不过美国并没有针对智能投顾监管的专门立法。美国金融业监管局(Financial Industry Regulatory Authority, FINRA)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的相关规定和实践构成了美国当前的智能投顾监管体制,前者属于自律监管,后者属于官方监管。
1.FINRA的监管:以智能投顾平台底层算法和投资组合的监管为中心
2016年3月,美国金融业自律监管机构FINRA发布了《关于数字投资建议的报告》(Report on Digital Investment Advice),本意是在不创制任何新规则的情况下,对服务数字化背景下的经纪人(broker-dealers)之监管提供监管和从业指引。FINRA在报告中倾向性地将经纪人与智能投顾进行类比,并宣称该报告虽然主要适用于对经纪人的监管,但其中的监管建议也可能会对智能投顾的监管提供有益借鉴。故而,学界也将FINRA的报告视为智能投顾的监管依据。FINRA在报告中重点强调了两方面的监管内容:第一,对智能投顾平台底层算法的监管;第二,对投资组合结构的监管,包括对该投资组合结构中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问题进行防控(5)FINRA, Report on Digital Investment Advice (2016-03)[2020-12-23], http://www.finra.org/sites/default/files/digital-investment-advice-report.pdf.。
关于算法的监管,FINRA的基本逻辑是,因为算法是整个智能投顾的底层驱动力,是为投资者提供服务的关键,智能投顾平台一定要保证算法的输入和输出具有逻辑一致性,能够完成智能投顾平台所设定的任务或目标。FINRA将监管算法的任务交给了智能投顾平台本身。这实际上是在强调,智能投顾平台要想从事智能投顾服务,其必须具备技术上的可行性。不过,FINRA并没有列出智能投顾平台应该能够达到的算法技术标准。
关于对投资组合结构的监管,FINRA重点列出可能出现利益冲突的两种情形:雇主和客户的利益冲突风险,公司和客户的利益冲突风险。其中“雇主”是指智能投顾人员,即在智能投顾机构中为投资者提供服务的个人。这种利益冲突在需要人工辅助的智能投顾服务中有存在的可能性,如果是完全自动化的智能投顾,就不可能存在雇主和客户的利益冲突。“公司”是指智能投顾平台或机构,这种利益冲突风险存在于所有智能投顾中,因为即便智能投顾发展到高度智能化的阶段,客户也始终都绕不开与智能投顾机构的直接接触。FINRA认为,对投资组合所涉利益冲突进行化解的关键是要让独立于该业务的人员对投资组合进行审查。
总之,FINRA并没有创设任何新的规则,它只是对原有监管规则或手段进行了重申。这说明FINRA倾向于将智能投顾纳入到传统的监管体制之中。
2.SEC的监管:以注册义务和信义义务为中心
SEC在2017年2月23日发布的投资者公告中明确表示:“尽管智能投顾提供的是自动化的服务,但是在美国,它们必须遵守SEC层面或州层面的、与投资顾问有关的证券法律。”(6)原文为Although the services that they provide are automated, robo-advisers in the U.S. must comply with the securities laws applicable to SEC or state-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ers. See to SEC, Investor Bulletin: Robo-Advisers (2017-02-23) [2020-12-23], https://www.investor.gov/additional-resources/news-alerts/alerts-bulletins/investor-bulletin-robo-advisers。在联邦层面,对智能投顾进行监管的主要法律是《1940年投资顾问法案》(Investment Advisers Act Of 1940)。根据《1940年投资顾问法案》的规定,智能投顾相关主体应遵循如下规则:
(1)市场准入监管——注册义务规则
《1940年投资顾问法案》第202(a)(11)条在界定投资顾问时,着重强调了投资顾问是提供投资建议服务的主体。这似乎说明,投资顾问的业务只包括提供投资建议服务,而不能涉及资产管理服务。不过,该法案第204(b)(3)(A)条规定,投资顾问所管理的财产数量(assets under management)、杠杆的使用情况等都是需要在年报或者其他报告中体现。这说明,投资顾问也可以经营资产管理服务。在美国,不管是投资咨询服务,还是资产管理服务,都是特许业务。某个主体想要经营此类业务,必须获得相应的资质,获得资质的方式就是在监管部门进行注册。
《1940年投资顾问法案》第203节详细规定了投资顾问的注册要求。《1940年投资顾问法案》第203(c)(1)条规定,任何一个想注册成为投资顾问的主体,必须向SEC提供与投资顾问有关的如下材料:①名称、组织形式,投资顾问成立的法域,总部所在地、主要营业地、派出办公室,投资顾问及其伙伴、管理人员、经理等人的名称和地址,员工数量;②教育背景,过去十年的业务关系,投资顾问自身及其与业务伙伴、管理人员、经理等主体的当前业务关系;③所从事的投资顾问业务的实质,包括提供建议和发布分析报告的方式等;④经过第三方审计机构审计的资产负债表或其他财务报表;⑤与客户资金和账户有关的投资顾问权限的本质和范围;⑥投资顾问的报酬基础;⑦投资顾问是否具有注册资格;⑧主要业务是否包含投资顾问业务的声明以及投资顾问业务的主要部分是否包含投资管理业务(investment supervisory services)的声明。
(2)业务经营的监管——信义义务规则
《1940年投资顾问法案》并没有明确规定投资顾问对客户负有信义义务,投资顾问所负的信义义务规则是判例法演绎的结果。1963年SEC诉Capital Gains Research Bureau, Inc.(以下简称“Capital Gains”)案是投资顾问信义义务规则生成的开端(7)Steven D. Irwin, Scott A. Lane, Carolyn W. Mendelson, “Wasn’t My Broker Always Looking Out for My Best Interests? The Road to Become a Fiduciary”, Duquesne Business Law Journal, 2009, 12, p. 44.。在该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衡平法上的欺诈之含义要比普通法上的宽泛,主观上的欺诈意图并不是成立欺诈行为的必要成分。而且,立法者在《1940年投资顾问法案》中的意图应该像其他证券法律一样,被解释为“避免欺诈而实施”,不应该过分强调欺诈规则的技术性成分,而应该强调欺诈规则的救济性(remedial)成分(8)William Alan Nelson II, “Broker-Dealer: A Fiduciary by Any Other Name?”, Fordham Journal of Corporate & Financial Law, 2015, 20(3), p.645.,所以,作为投资顾问的Capital Gains公司应该向投资者全面、真实地披露它的投资建议对其自身营业所生之效果的信息(9)SEC v. Capital Gains Research Bureau, Inc., 375 U.S. 180, 181-197 (1963).。从本案的原意来说,它主要解决投资顾问领域中的欺诈认定问题,尤其是强调反欺诈制度存在的目的。从解释论的角度来看,该案例是通过目的解释的方法,扩大了反欺诈规则的适用范围,以更加切实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在彼时,该案仅仅是对美国证券监管极为重视投资者保护的理念的一种延续和具体化(10)Katelin Eastman, “Restoring Confidence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Advocating for A Uniform, Rules-Based Fiduciary Standard”, Pepperdine Law Review,2014, p.12.。后来也有其他法院采取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论证逻辑。不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虽然表露出了投资顾问负有信义义务的态度,但毕竟这不是该案所认定的重心。
该案之所以会被认为是赋予投资顾问信义义务的第一案,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历史解释的方法,详细考察了《1940年投资顾问法案》的立法材料,发现当时就有人主张投资顾问负有信义义务。其二,本案争议的焦点与信义义务所要着力解决的利益冲突问题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该案中,Capital Gains的投资建议同时服务于两个目标:一个是为了Capital Gains自己在短期的股票价格涨跌中赚取差价;另一个是为了投资者在长期的股票投资中赚取收益。在这两个目标中,Capital Gains利用自己向投资者提供投资建议的便利,很容易在投资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向投资者推荐那些能够让Capital Gains自己赚取短期利益的投资机会,这被认为是利益冲突。在之后的系列判例中,投资顾问信义义务的内涵不断被深化和细化。
在判例法的基础上,学界认为在信义义务规则下,受托人(投资顾问)必须:①确保所有的投资建议在他们的知识范围内是准确、完整的;②避免并披露所有潜在的利益冲突;③明确披露所有的费用和佣金细目;④提供符合客户理想目标、具体目的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建议(11)Matthew Frankel, The Fiduciary Rule: Pros and Cons (2017-02-03)[2020-12-23], https://www.fool.com/retirement/2017/02/03/the-fiduciary-rule-pros-and-cons.aspx.。从理论上说,信义义务包括勤勉义务和忠实义务。所谓勤勉义务是指投资顾问在向客户提供服务时,要像一个谨慎的人在为自己服务时所具有的勤勉程度去为客户服务,即要求投资顾问“事人如事己”。所谓忠实义务是指投资顾问在为客户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应当以客户的利益作为自己行为和行动的最高准则,当自己的利益与客户的利益出现冲突的时候,自己的利益必须让位于客户的利益,即要求投资顾问“不得损人利己”。一般来说,信义义务只是给特定的情境提供了一个一般的分析框架,至于义务的具体内涵和行为范式,需要根据特定情形进行具体分析。这就意味着,即便智能投顾相关主体对投资者负有信义义务,但是这种信义义务只有在智能投顾特定的情境下,根据具体的细节才能确定。
3.对美国智能投顾监管体制的简评:强烈的务实主义风格
美国对智能投顾的监管呈现出两大特征:(1)美国监管层和实务界将智能投顾经营者界定为投资顾问,将其纳入现有的证券法监管体制。比如,SEC认为智能投顾应该注册成为投资顾问。美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智能投顾机构Betterment也宣称其是在SEC注册的投资顾问(SEC-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er),其严格遵守《1940年投资顾问法案》和SEC的信息披露要求,以履行其所肩负的信义义务(12)Betterment, Disclosures [2020-12-23], https://www.betterment.com/legal/.。(2)监管文件以通知或报告为主,保持了一定的试探性。一般来说,作为自律监管组织的FINRA会根据现实情况,及时向相关的业务经营者提供针对各种问题的合规通知、指导、公告、监管报告等(13)FINRA, Rules and Guidance [2020-12-23], https://www.finra.org/industry/rules-and-guidance.。这些内容都是对现实情况的及时回应,但它又不是意在对市场施加强监管,而是提醒市场主体充分注意和防范潜在的风险。在面对智能投顾实践时,SEC也仅仅是发布了相关的公告,向市场提示了相关的监管要点。这些做法充分说明监管者对当前智能投顾业务的监管采取了一种较为务实的试探性态度。事实上,不仅监管机构采取了试探性的态度,司法机关也是如此。比如,在号称智能投顾第一案Green诉Morningstar, Inc.中,美国东部大区联邦法院并没有就智能投顾本身的争议展开分析,而是从民事诉讼法的角度去分析原告是否享有诉权(14)Green v. Morningstar, Inc., 2018 WL 1378176.。法院这种避开实体法而选择程序法审案的做法,实际上也是一种试探性策略的体现,其原因可能是法院认为当前的智能投顾实践发展尚不充分,过早的公力干预将有可能限制智能投顾的多样化发展。但SEC和法院的这种试探性态度又不会让智能投顾完全脱离控制,因为内涵灵活而丰富的信义义务会将智能投顾机构和人员的创新行为或试错行为所带来的负面外部性进行灵活约束。
(二)英国的监管构造:一般监管和特殊监管的双层构造
英国既有的智能投顾监管体制可以被分解为两块:一块是由《欧盟金融市场指令II》(Markets in Financial Instruments Directive II, MiFID II)构建的监管体制;另一块是由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FCA)创新计划所构建的监管体制。前者可以视为英国智能投顾的一般监管体制,后者可以视为前者的例外或补充。这两种监管体制在逻辑上形成了一般监管和特殊监管的双层构造。
1.英国智能投顾的一般监管体制:对欧盟监管体制的转换性适用
受英国脱欧的影响,《欧盟金融市场指令II》并不会完全适用于英国市场,但是FCA有权将其中的监管规则选择性地适用于英国。目前,FCA明确表示会将MiFID II所规定的措施运用至英国市场的有两项内容:
第一,关于佣金支付规则。《欧盟金融市场指令II》严厉禁止投资公司通过捆绑式佣金安排从经纪人处获得投资研究报告。不过,在投资经理利用其自有资金或者与客户资金相区隔的“研究支付账户”(research payment account)向经纪人支付佣金时,其仍然可以从经纪人处获得投资研究报告。该规则的主要目的是禁止利益冲突,因为捆绑式佣金安排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投资者,在投资经理与经纪人的交易中,很容易发生投资经理与经纪人合谋侵害投资者利益的问题。如果将投资经理与经纪人之间的交易所涉资金与投资者的资金切断,那么就可以有效解决利益冲突问题。FCA明确表示,其将接受这一规则。
第二,关于最佳交易原则(best execution)。《欧盟金融市场指令II》贯彻最佳交易原则的主要方法是强化交易的透明度,尤其是强化不同投资经理在不同地点执行质量方面的透明度。评估其执行质量的因素包括提供服务的价格、执行事务的成本、执行事务的速度、执行事务的可能性。执行质量与投资经理之间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循环过程。投资经理会根据执行质量来选择营业地点;反过来,投资经理又需要按照要求披露其相关的营业信息,这些信息又会被吸收到下一轮的执行质量评估中去。对投资者来说,执行质量透明度使他们有机会在不同的执行方案中进行选择,以筛选出最能符合自己利益的投资策略。FCA表示,最佳执行原则将会被应用至英国市场。
2.英国智能投顾监管的特殊体制:以促进科技创新为中心的监管实验主义
英国智能投顾监管特殊体制是由FCA于2014年推出的“项目创新”(Project Innovate)建立起来的。该计划的目的是强化FCA作为一个富有远见的监管者的角色,促使英国成为一个吸引各类科技公司和金融服务的市场。简单地说,“项目创新”计划大致可以被分解为三个层次:其一,向那些在提供金融服务方面的奇思妙想打开大门;其二,孕育新的金融服务提供者;其三,寻求一种安全的、可持续的服务提供方式(15)Michael Huertas, “The UK FCA’s Regulatory ‘Sandbox’: Any Lessons for the EU?”,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 Law and Regulation, 2018, pp.50-51.。
作为“项目创新”计划的一部分,FCA成立了“创新中心”(Innovation Hub),致力于帮助新业态或既有业态中的初创企业降低产品、服务费用,提高产品、服务质量,以造福金融消费者。“创新中心”的工作有两项:其一,直接为创新者提供指导,比如,当创新者对监管政策有疑义时,可以直接寻求创新中心的帮助,以减少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其二,对政策或相关程序进行识别、评估,并作出相应的调整,以支持创新。在这一点上,FCA通过多种措施深入地与创新者进行互动,真正从创新者内部去了解和搜集创新者的政策需求,进而对现有的监管规则进行调整(16)There is Little that Bureaucrats Hate More than Innovation: the FCA Opens its Innovation Hub (2014-10-29)[2020-12-23], http://www.osborneclarke.com/insights/there-is-little-that-bureaucrats-hate-more-than-innovation-the-fca-opens-its-innovation-hub/.。FCA“创新中心”所采用的最为著名的监管方式就是始自2016年6月份的“监管沙盒”(Regulatory Sandbox)。
与“创新中心”并行的一个计划就是FCA的“建议部门”(Advice Unit)。成立“建议部门”的直接动因是《2016年金融咨询市场评估》(Financial Advice Market Review 2016)的规定。从宏观上说,FCA是英国智能投顾的监管主体;从微观上说,“建议部门”则是英国智能投顾的直接监管主体(此处是指在特殊的监管体制语境下)。“建议部门”与“创新中心”的关系在于,前者更加专注于对金融科技的监管,后者在补充前者的基础上对各种创新的金融活动都提供监管帮助。
“建议部门”的基本工作原理是:由智能投顾申请成为“建议部门”项目中的一员,“建议部门”对申请人遇到的全新监管难题进行解答,以降低政策不确定性给申请人带来的风险。
一般来说,某个公司如果想加入FCA的“建议部门”计划,必须首先考虑自己所从事的行业是否属于FCA所列的创新行业。如果不是FCA所列的行业,那么“建议部门”不会向该申请人提供监管反馈。
“建议部门”的反馈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向相关公司发出的。这就是说,“建议部门”向申请人发出反馈存在一个前置程序,它包含两层意思:其一,只有申请人解决不了的全新的监管难题,才能向“建议部门”求助,否则的话,“建议部门”不会向其提供反馈。其二,申请人在寻求监管反馈的过程中处于主动地位,“建议部门”处于被动地位。申请人必须用既有的监管规则对自己的业务模式进行评估,“建议部门”不会主动对申请人的业务模式进行评估。如果申请人没有成功加入“建议部门”项目,“建议部门”也会给申请人提供反馈,阐明申请失败的原因以及补正措施,或者将申请人移送给FCA的其他部门,比如“创新中心”项目。
3.对英国智能投顾监管体制的简评:实现了金融安全与金融创新的有效平衡
英国一般监管体制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与利益冲突有关的问题,其倚重的手段也是信息披露,这与其他国家的传统投顾监管体制并无本质区别。英国智能投顾监管体制的亮点就在于由“建议部门”试验出来的监管规则。但是,FCA尚未对“建议部门”已提供的反馈进行体系化整理,由“建议部门”摸索出来的新的监管经验在短时间内尚难以被制度化。
抛开经验制度化的难题不谈,我们对入选“建议部门”项目的主要考核指标进行分析后可知,“建议部门”所把握的关键点有:服务于边缘消费者,真正的智能化,解决真正的、新的监管难题。这意味着英国特殊体制对智能投顾的监管着重追求科技创新,促使智能投顾经营者将智能投顾打造成真正的科技金融。
总之,英国智能投顾的主要特征是:(1)监管主体单一,FCA在监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我们可以从理论上将英国智能投顾监管体制分为一般体制和例外规定两部分,但是具体实施这两种监管体制的主体都是FCA。(2)设置例外规定来缓和一般监管体制对金融创新的抑制作用。英国的一般监管体制实际上将智能投顾机构和传统投顾机构完全等同地监管。但是考虑到智能投顾可能的创新性,FCA创设了例外监管体制,以进一步激发和强化智能投顾的创新性,从而为金融创新预留空间。这两种体制较好地缓和了风险防控和金融创新之间的张力(17)许多奇:《金融科技的“破坏性创新”本质与监管科技新思路》,《东方访学》2018年第2期。。
(三)加拿大的监管构造:业务和人员的类型化规制
加拿大证券监管管理局(Canadian Securities Administrators, CSA)于2018年6月12日出台的《全国监管机构31-103:注册要求、豁免和持续注册人义务》(CSA National Instrument 31-103: Registration Requirements, Exemptions and Ongoing Registrant Obligations (“NI 31-103”))是监管智能投顾最重要的依据。其主要内容如下:
1.智能投顾业务的监管:推行分类注册主义
关于智能投顾平台是否有明确的业务范围,加拿大法律对此并没有规定。平台可以选择经营资产管理业务,也可以选择经营投资咨询业务,也可以二者都做。CSA在2015年9月24日发布的《关于投资组合管理人在线建议的指南》(Guidance for Portfolio Managers Regarding Online Advice)中认为,加拿大的智能投顾提供的是自由支配的投资管理服务(discretionary investment management services)。所谓“自由支配”是指投顾服务的主体在资金管理、信息咨询等方面享有自主决定权,前者是传统的资产管理业务,后者是传统的信息咨询服务。所以,加拿大的智能投顾包含了传统的资产管理和信息咨询服务两个方面。不过,不管中介机构具体从事什么业务,它们都必须在相应的监管机构进行注册,只有进行注册以后才能从事相应的业务。之所以要求中介机构进行注册,是因为作为守门人的监管者要确保服务提供者的适格性——有能力、有资质向投资者提供相应的服务。
NI 31-103大致将中介机构分为三类:经销商(dealer)、投资顾问和基金管理人(18)Dominique Payette, “Regulating Robo-Advisers in Canada”, Banking and Finance Law Review, 2018, 33(3), p.432.。在资本市场上,所有的中介机构最终都必须在前三种机构中选择一种或多种进行注册。如果一家中介同时涉足两个或三个领域,那么它就需要同时注册两个或三个身份。未经注册而提供中介服务的,则属违法。总的来说,加拿大智能投顾服务提供者被归在投资顾问一类。这也就意味着,所有想提供智能投顾服务的主体都必须在相应的监管机构注册成为投资顾问。因为加拿大的证券监管属于地方性事务,所以智能投顾服务者想跨省份提供投顾服务,需要同时在相应的省份完成注册。
2.智能投顾人员与平台的分离监管主义
智能投顾服务提供者包含两个主体:一个是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比如某个智能投顾平台;另一个是提供服务的个人,即智能投顾人员。这两类主体在提供投顾服务前都必须注册,分别接受监管。将这两个主体置于智能投顾领域,个人被称为投顾代表(advising representative),平台被称为证券投资组合管理人(portfolio manager)。每一个智能投顾平台都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投顾代表为其工作。
对个人来说,注册要求大概包含三方面:(1)一般能力要求(General proficiency requirements),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该个人要通过特定的专业考试,比如加拿大投资基金课程考试(Canadian Investment Funds Course Exam)。(2)教育和经验要求(Education and experience requirements),即提供服务的个人必须拥有为投资者提供适格服务的教育背景、培训经历和工作经验。投资顾问的种类比较多,不同种类的职位对个人的资历要求也不一样。(3)自律监管机构的成员资格要求(Membership in a self-regulatory organization),比如提供智能投顾服务的个人如果还同时提供交易商服务,那么该个人在成为交易商之前,必须在加拿大投资业监管组织(Investment Industry Regulatory Organization of Canada)注册成为会员。
对平台来说,注册依据是NI 31-103第7部分的规定。比较特殊的是,NI 31-103并没有从正面规定机构进行注册时所应满足的条件,而是在第8部分的“注册要求豁免”(Exemptions from the requirement to register)中详细规定了三类中介机构的注册要求豁免情况。我们可以将NI 31-103的注册规定要求总结为简化的正面注册清单和详尽的负面豁免清单相结合的监管方式。不过,NI 31-103没有详细规定注册要求,并不意味着这些机构(平台)不用注册或者根本不存在注册要求。事实上,更为详尽的注册要求体现在各省、特区的证券监管规定中。机构想从事相应的中介服务,必须满足地方性监管规定。
3.对加拿大智能投顾监管体制的评析:强烈的保守主义风格
加拿大当前的智能投顾是人工和机器的结合体,它们都是由投顾代表和投顾服务在线中介机构(平台)组成,其中投顾代表在智能投顾服务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比如,平台利用网络在线问卷来判定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资产状况、投资目标等,以完成了解客户(know your customer, KYC)的合规要求。通过网络问卷自动生成的KYC报告并不是平台作出投资决策的最终依据,因为只有KYC报告再经过投顾代表审核以后,方能成为平台的决策依据。同样地,平台在线生成投资策略以后,也要经过投顾代表审查,在确保投资适当性的情况下,才能够具体实施投资计划。在这个意义上,智能投顾被看作是传统投顾的延伸,它并不是彻头彻尾的新事物、新业态。于是,加拿大监管者在承认技术中立性(即鼓励投顾技术创新)的情况下,完全地将传统投顾的监管体制移植到智能投顾领域,这也就决定了加拿大在智能投顾监管方面较为保守的监管风格。CSA把智能投顾与传统投顾几乎完全等同起来,将传统投顾的监管体制(人员监管和机构监管)无差别地运用于智能投顾的做法,虽然有助于控制智能投顾所蕴含的潜在风险,但是其同时有可能把智能投顾所蕴含的创新性给扼杀了。
加拿大的监管体制还存在另一个致命缺陷就是监管的碎片化阻碍了统一市场的形成。加拿大的证券监管被认为是地方性事务,由省政府或地区政府的证券监管机构进行监管。之所以会形成此种局面,主要是因为《1867年英属北美法案》关于联邦政府和省级政府的分权规定。《1867年英属北美法案》区分了两个概念,一个是省级财产和民事权力,另一个是联邦商业贸易权力,前者属于省级政府的事权范围,后者属于联邦政府的事权范围。在加拿大的证券监管史上,联邦政府和省级政府多次发生过争夺证券监管权的情况,但是,这些纷争始终是以联邦政府失败而告终。于是,在加拿大就形成了13个省或地区分别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的情况,如果某一证券营业主体要跨境从事证券业务,该主体必须分别向所涉及的省或地区的证券监管部门申请。这种分别申请、逐一注册的监管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全国统一证券市场的形成。智能投顾业务属于新式证券业务,它需要有足够大的市场方能支撑其逐步发展;而且,互联网的跨疆界性质很容易使智能投顾业务在事实上形成跨省或地区经营的情况。为了拓展市场和顺应互联网跨疆界的特性,智能投顾业务经营者必须逐一在不同省、地区的监管部门进行重复申请,这必定会大大增加经营者的合规成本,进而增加智能投顾业务经营者的创新创业负担。
(四)小结:智能投顾监管的实用主义哲学
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对智能投顾的监管都体现了强烈的实用主义哲学意味。这三国的监管者都或明或暗地承认“新的真理总是一种进行调和的中介,总是便于过渡的缓冲器”(19)[美]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6页。。这就意味着,智能投顾不可能是一种开天辟地、完全颠覆传统投顾的业态,对它的监管必须在承继传统投顾监管体制的基础上,逐步过渡到适合于智能投顾监管的体制上去。之所以要如此,是因为“我们对事物的各种基本的思想方法是远古祖先们的发现,它们经历此后所有世代的经验还能保存下来”,人类的“其他阶段可以在这个阶段上移枝接叶,但是永远不能代替它”(20)[美]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95页。。实际上,这样一种实用主义态度与作为智能投顾监管规则的法律的特征也具有契合性。法律具有保守性,其并不喜欢过于变动的现实,这体现在它总是基于不断沉淀的事实来总结具有稳定性的行为范式和规则,而无法基于不确定的未来提炼出能够预测未来的规则(21)苏力:《反思法学的特点》,《读书》1998年第1期。。以“缓冲器”的思路去监管智能投顾,它会驯服过度变动的实践,进而为基于传统体制的“移枝接叶”提供更多的可能性。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正是在坚持传统投顾监管的大前提下,对各自智能投顾展开了各具特色的监管。
三、经验借鉴:域外智能投顾监管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认为,美国、英国、加拿大对智能投顾监管的实践值得我们重点借鉴的内容有:
(一)应注重监管价值和监管手段的多样化
在我国,智能投顾业务属于证券投资基金的范畴,所以,与证券投资顾问服务和资产管理服务有关的规范性文件都可以作为我国智能投顾监管规范的法源。据笔者梳理,此类不同类型、层级的规范性文件多达二十几项。这些规范性文件主要有:《证券法》(2019)、《证券投资基金法》(2012)、《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2014)、《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1997)、《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6〕99号)、《中国证监会基金监管部关于基金管理公司向特定对象提供投资咨询服务有关问题的通知》(2006)、《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2010)、《关于加强对利用“荐股软件”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监管的暂行规定》(2012)、《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管理暂行规定》(2012)、《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2013)、《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2014)、《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2015)、《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2016)、《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审批暂行规定》(2017年12月7日修正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2018)、《国务院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2018)、《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规范》(2012)、《关于规范证券公司与银行合作开展定向资产管理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2013)、《关于拓宽证券投资咨询公司业务范围的通知》(2015)、《证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子公司管理规范》(2016)。
这些庞杂的监管规范始终严格坚持的一个监管原则就是严格坚持审批制。这种监管追求所导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看似庞杂的监管规范要么是对其他规范意涵的简单重复,要么是对“严格坚持审批制”的细化。由此而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将事前的行政审批裹挟成为对智能投顾监管的最重要措施:事前监管靠审批,事中事后监管还是靠审批。为了避免事中事后出现风险,监管者往往就会设置较高的审批要求或较严格的审批条件。这样一来,只有少数主体才能够通过审批;即便通过审批的主体,也只有极为有限的营业空间,进而也就减少了引发金融风险的可能。这种严苛的监管设计当然能够很好地控制金融风险,但是这种简单的监管设计不仅抽空了智能投顾监管规则本身应有的丰富内涵,更在事实上固化事前审批就是进行金融监管的灵丹妙药的错误印象,最终可能扼杀智能投顾市场应有的创新性。
相反,国外的监管价值追求和监管手段就较为丰富灵活。比如在美国,对智能投顾的监管可以概括为:事前监管靠注册,事中事后监管靠信义义务,这是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达到平衡的结果。在智能投顾语境下,智能投顾经营者在SEC进行注册,在功能上类似于我国监管者所强调的审批或批准,但是SEC并没有完全或者主要依赖准入注册的方式对智能投顾的经营风险进行防控,而是以信义义务为中心,对智能投顾经营者或人员施以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的要求。信义义务属于判例法规则,它本身具有很强的延展性和灵活性,能够适应复杂多变的现实之需要。这种灵活性的规则,也意味着法律规范对智能投顾经营者和相关人员经营或从业权利的尊重,为这些主体进行各种试错创新行为提供了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在智能投顾经营过程中引入信义义务规则是有利于智能投顾业态发展的,因为“权利是市场存在和发展的前提”(22)邱润根:《金融权利视角下民间金融的法律规制》,《法学论坛》2015年第2期。。信义义务规则的延展性在有利于智能投顾主体和人员进行创新试错的同时,也可能会危及投资者的正当权益。
那是否意味着SEC的监管规则偏重于金融创新,而忽略投资者保护呢?否。原因是,一方面,SEC在监管过程中有权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向被监管者发放停止令。如果SEC发现智能投顾相关主体的行为偏离了信义义务的要求,对投资者权益造成损害或有可能造成损害时,它就可以向被监管者发放停止令。停止令的发放将对被监管者经营行为产生重大不利影响(23)2008年11月23日,SEC根据《1933年证券法案》第8A节向美国曾经最大的P2P网贷公司Prosper发布了停止令,原因是Prosper没有履行《1933年证券法案》第5(a)节和第5(c)节规定的证券发售注册义务。彼时,Prosper误判了SEC介入的决心,其选择继续与SEC对抗,谋求对SEC的停止令进行上诉。直至2009年7月13日,Prosper在对抗无果的情况下,才正式关停了其平台,对业务模式进行全面整顿。相反,LendingClub从一开始就没有选择与SEC进行对抗,它在2008年4月7日主动关停了其平台并对业务模式进行调整;2008年6月20日,LendingClub决定向SEC提交注册声明;2008年10月13,LendingClub重新开业。正是因为LendingClub的这些合规举动,使它在原美国最大、最为知名的P2P网贷公司Prosper还在与SEC对抗时,一举逆袭而成为美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最先上市的P2P网贷公司。Tao Yu, Wei Shen, “Funds Sharing Regu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Sharing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Logic of China’s P2P Lending Regulation”, 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 2019, 35(1), p.53。。另一方面,如果这些主体的行为不符合信义义务的要求,那么很可能会招致投资者的集体诉讼。在行政监管和市场约束的情况下,智能投顾营业者和相关人员不能只顾着创新业务模式和业务内容,他们还得思考这些业务模式和内容该如何满足信义义务的要求。这样一来,来自市场的压力不仅可以激发智能投顾经营者和投顾人员不断地创新业务内容,而且还能不断地创造出满足信义义务要求的各种措施,这在客观上会同时促进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手段的创新。
对我国来说,监管者应该放弃唯金融安全论的价值追求(24)邢会强:《相对安全理念下规范互联网金融的法律模式与路径》,《法学》2017年第12期。,将金融安全和金融效率价值统合起来,利用多种监管手段(25)刘沛佩:《我国证券市场智能投顾发展的监管思考》,《证券市场导报》2019年第1期。,对智能投顾的准入和经营采取不同的监管方式。尤其是在智能投顾业务经营过程中,我们可以引入美国对智能投顾监管的信义义务规则,充分激发智能投顾的经营者和相关人员的创新创造力,而不是寄望于利用严苛的准入门槛将智能投顾的经营行为死死地限制在极为有限的空间内。
(二)应以英国的监管模式为借鉴对象
美国主要是通过监管者表态的形式将智能投顾纳入到既有的监管体制之中。这种模式在理论上为创新监管体制预留了空间,但实际上损害了监管体制或规则应具有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让从业者处于不确定的合规风险之中。从业者为了谨慎起见,往往都会顺应监管者的号召,主动将自己宣称为是监管者所期待的那种行为主体。比如,Betterment在其经营宗旨中就向公众宣称:“我们是一个受托人(fiduciary),这意味着我们将以你的最大利益而行事(We’re a fiduciary, which means we act in your best interests)。”(26)Betterment, Our Commitment [2020-12-23], https://www.betterment.com/mission/.在这种氛围下,美国的监管体制和规则几乎没有创新之处。相较于美国,加拿大的监管者更为保守。CSA明确表示,传统的投顾监管规范将被全部运用于智能投顾领域,而且每个智能投顾平台必须配备足够的智能投顾人员,确保在线智能投顾程序所生成的投资建议都有一个对应的人工投顾来进行审查。在加拿大的监管语境下,智能投顾机构或在线程序被当成是传统投顾的工具或手段,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智能投顾人员。
在科技金融监管领域,一个常见的监管弊病就是“不同的游戏+相同的游戏规则=游戏玩完”(27)Sofia Ranchordás, “Does Sharing Mean Caring? Regulating Innovation in the Sharing Economy", Minnesota Journal of Law, Science & Technology, 2015, 16(1), p.414.。这也是遭我国学者广泛批评的一点。比如,有学者认为我国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一个重要失误就是用传统金融监管的方式来监管互联网金融,最后把“互联网金融”监管成了“金融互联网”(28)彭岳:《互联网金融监管理论争议的方法论考察》,《中外法学》2018年第6期。。如果沿用美国和加拿大对智能投顾的监管思路,最终的监管结果很可能是把具有创新性的智能投顾监管成了“传统智能投顾+智能技术”式的业态。
相较而言,英国的监管体制值得我国借鉴,尤其是FCA所采用的监管沙盒的做法值得我们深入学习(29)参见郭金良《我国智能投资顾问发展的法律挑战及其监管应对》,《江海学刊》2019年第6期。。监管沙盒意指在风险受控的环境下暂停与消费者或者投资者等有关的法律法规的实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创新者的合规要求,为创新者提供一个极为自由和宽松的创新环境,让创新者在这个受限的“盒子”内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进而实现金融创新。待监管沙盒中的项目成熟以后,监管者再把此类项目的模式进行推广,并据此修订相应的监管规范。由此便完成了一轮由项目创新到规范创新的过程。从本质上讲,监管沙盒是风险受控式的创新,它平衡了促进创新和防控风险的双重需要。这对打破我国金融监管领域中“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思路。
(三)应将资产管理服务纳入智能投顾的营业范围
国外智能投顾的业务范围都呈现出投资咨询服务和资产管理服务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基于规模经营的成本效益考量以及提高金融业国际竞争能力的需求,1999年11月,美国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标志着其放弃了坚守66年的金融分业经营体制。这对世界各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世界各国的金融经营体制逐渐由分业经营转向了混业经营。以1999年为分界点,我国金融业的分业经营监管体制在此以后有所松动。从2000年左右起,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都积极探讨和推动不同的银保合作方案(30)何光辉、杨咸月:《银行保险与我国分业体制下的银保合作》,《上海经济研究》2001年第7期。。2008年1月16日,原银监会和保监会正式签署了《关于加强银保深层次合作和跨业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强调规范银行业和保险业之间开展的深层次合作,进一步提高跨业监管的有效性。这是我国自1994年确定金融分业经营和监管体制以后,官方首次明确放松了金融分业经营和监管的体制(31)郭田勇:《金融监管学》,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4年,第90页。。2018年3月21日,我国原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成立银保监会,这可以被视为我国金融混业经营和监管的里程碑事件。在金融混业经营的大背景下,智能投顾的营业范围也应该符合这一趋势。
然而,在我国现行监管体制下,投资顾问服务和资产管理业务还是坚持分业经营和监管的原则。比如,根据我国证监会的规定,同时符合下列3个条件的,则涉嫌非法证券投资咨询:“(1)行为主体不具备证券投资咨询资格。具体包括:①未取得证监会批准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许可的机构;②未取得证券投资咨询从业资格,或取得证券投资咨询从业资格但未在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执业的个人。(2)向投资者或客户提供涉及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投资建议服务,辅助客户做出投资决策。投资建议服务内容包括投资的品种选择、投资组合以及理财规划建议等。(3)直接或间接获取经济利益。”(32)证监会:《证券投资咨询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规定》(2018-11-09)[2020-12-23],http://www.csrc.gov.cn/pub/hainan/xxfw/hngzjx/201811/t20181109_346530.htm。也就是说,即便具有经营资产管理业务的智能投顾机构,在没有获得相应批准的情况下,其也不能经营投资顾问业务。反之亦然(33)《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2013)第4条规定:“证券公司从事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资格。未取得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不得从事客户资产管理业务。”。
鉴于国际上投资顾问和资产管理业务混业经营的趋势,我国也应该允许智能投顾同时经营投资顾问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以发挥混业经营所具有的规模效应。这一点也为我国学界所坚持。有学者认为,我国应该修改《证券法》(2019)第161条,扫除智能投顾的准入障碍,即允许全权委托(即资产管理);如果将智能投顾的业务范围严格限制在投资咨询范围内,那么智能投顾将成为“伪智能”(34)李文莉、杨玥捷:《智能投顾的法律风险及监管建议》,《法学》2017年第8期。。
四、结语
在法与金融的关系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的LLSV理论认为,金融市场的发展受到法律的制约和促进,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障(35)参见沈伟《法与金融理论视阈下的上海金融法院:逻辑起点和创新难点》,《东方法学》2018年第5期。。这即是说,智能投顾的发展水平取决于智能投顾监管制度,智能投顾监管制度设计得好,智能投顾业态发展就会好。本文通过对世界上在智能投顾监管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监管经验的分析,大体上勾勒出了在智能投顾监管方面所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希望本文的研究对我国构造出符合智能投顾发展要求的监管制度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