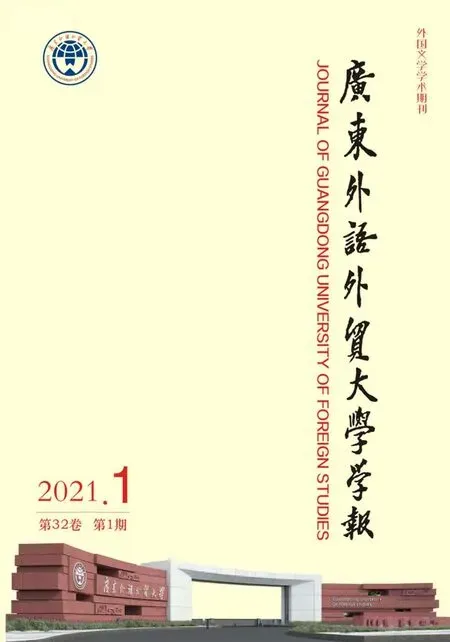“悖谬”表象之下的战争隐语
——论《潘多拉之匣》的叙事策略
2021-03-25孙萌
孙萌
引 言
《潘多拉之匣》(パンドラの匣,1945)是作家太宰治(Dazai Osamu,1909-1948)在友人日记的基础上改写的一部书信体小说,于1945年首次发表在《河北新报》上。若从这部小说创作时间来看,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作家文学创作中期与后期的分水岭。这篇小说以书信体的形式记叙了于战争时期身患肺病的“我”在一个名为“健康道场”的疗养院里所闻所见所感。纵观国内外先行研究,对于太宰治本人及其作品的研究不胜枚举,基本上集中于其中期代表作《奔跑吧!梅洛斯》,后期代表作《斜阳》《人间失格》等作品。以《潘多拉之匣》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寥寥无几。在为数不多的先行研究中,日本文学研究界对《潘多拉之匣》的评论呈现出了褒贬不一的局面,而中国学界对这部小说的解读主要基于叙述者对战后社会乐观的叙事判断(周婷婷,2015:113-115),对于文本中贯穿故事首尾充满悖谬之处鲜有研究者提及。而作品中的种种“悖谬”正是与太宰治本人的战争体验最息息相关的部分,文本中的时间及场景、疾病,包括登场人物在内虽都有原型可寻,但太宰治却以此作喻,将种种原型上升为带有隐喻色彩的、看起来充满“悖谬”的隐语符号,在进行文化管制的特殊时期,隐含地传达自己对于战争以及战后社会的态度与立场。
这部小说以独特的叙事方式、紧凑的结构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寓意深刻的“少年成长史”,同时也在创作手法、创作题材等诸多方面为日本战后现代小说的创作开辟了新的可能。本文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考察贯穿整个文本的“悖谬”意识,试图更为全面地解读《潘多拉之匣》的双层文本,揭示经历过战争时代、却又游离于战争之外的特殊战时共同体的内在意识形态。
悖谬的“发生”:时间的错位与战争节点
小说《潘多拉之匣》全篇采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策略,在表层文本中营造出一个看似可靠的叙述者表象。然而,若进一步探究这部小说的潜藏文本,便会发现,随着回顾性叙事的展开,越来越多的不可靠叙述不断涌现,不合理的悖谬之处也浮上水面。正是因不可靠叙述者造成的种种悖谬的“发生”,才使得在表层文本中每一组看似矛盾且错位的时间,与战时共同体记忆深处的战争节点完美地契合在一起。
在表层文本中的文体选择、叙述技巧及章节构成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可靠的叙述者。首先,就文体选择来看,实际作者①在“作者的话”这一章节中就已挑明了文体——这是一个“少有先例”的“书信体小说”,但这篇作品作为书信接受者的“你”是缺席的。书写者与接收者之间交流的可能性自始至终都是隐含在书信体小说叙事中的重要前提,虽然在作品中这样一种可能性并未被取消,但作者却将其隐而不表。其次,在叙事技巧上,叙述者有意引导读者关注患病的“我”被送到疗养院之后的心理变化,以及在疗养院中遇到的人和经历的事,甚至不惜花大量篇幅描写“我”与“竹姑娘”“麻儿”之间复杂而矛盾的感情线。此外,小说的章节标题也似乎暗示着“我”作为一个经历过战争的人在战后成功地重塑自我、适应社会的历程:首章标题(除‘作者的话’之外)使用了“开演”二字,并且开篇第一段话便表明了适应的成功——“新时代的帷幕已经拉开了,而且是我们的祖先未曾经历过的崭新的时代”(太宰治,2016:27)。之后每章的标题均以疗养院内的人和事物命名,这使整篇小说看起来就像是一部“明朗”的成长记录,探讨“我”在经历过绝望之后如何重生希望,进而怎样达成自我认同的。这篇书信体小说虽然是事后叙事,但隐含作者把所有读者严格把控在“我”身体经验发生的感受之内,把读者直接带入到故事发生的那个瞬间——“那一天/那个时刻-某一天/某个时刻”。这样一来,一方面由于叙述者就是书信书写者“我”,从而不会像回顾性叙述者那样美化或丑化某段事实导致叙述的不可靠;另一方面,隐含作者与叙述者的关系也变得难以界定,读者很容易认为隐含作者和叙述者在价值判断或道德判断上基本一致,从而把“我”当成一个可靠的叙述者。
然而,在挖掘潜藏文本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事实/事件轴”(the axis of facts/events)与“伦理/判断轴”(the axis of values/judgment)上,叙述者“我”一方面暴露出复杂的人格,另一方面又对此毫无意识,使两条轴线上的不可靠性相互交织。例如书信的上半部分中,“我”毫无顾忌地表露了自己对于“麻儿”的喜爱,并经常说诸如“竹姑娘没有一点女人的魅力”之类的有关“竹姑娘”的坏话,可在最后一章中,“我”却坦白自己其实是喜欢“竹小姐”的。再例如“我”不断地赋予“新男性”种种定义,并且从一开始“我”就以“新男性”自居,但是到了后来,“我”的所作所为越来越偏离“新男性”的轨道。叙述者“我”被隐含作者置于聚光灯之下,若读者对其言行与举动进行一番抽丝剥茧,便会发现叙述者在“事实/事件轴”与“伦理/判断轴”上存在着诸多不可靠性。
在不可靠叙述者“我”的叙述里,“我”发病到病重直至坦白病情,这样一种看似清晰明了的时间线,均以杂乱且充满着悖谬的“无时性叙述 ”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现在/以前-那一天/某一天-那时/某时”代替了具体的时间节点,并形成了多次重复。
在第一章“开演”中,叙述者“我”采用了倒叙(flashback)的方式,向所有读者表明自己的身份——肺病患者,且“现在”的“我”对于疾病的事情“已经忘在了脑后”。“现在”正是新时代帷幕拉开的时候。也正是在此章中,叙述者把第一个“空白”的时间符号安插在文本中:
只不过是某一天,某个时刻,圣灵潜入我的内心,眼泪流过脸颊,独自哭泣了许久,渐渐地身体变得轻飘起来,头脑也仿佛变得清晰而透明了。从那时起,我变成了另一个男人。在此之前我一直隐忍着,但此时我马上告诉了母亲:“我咳血了。”(太宰治,2016:28)
显然,“某一天”时间起点发生在已经“对于疾病丝毫不以为然”的现在的时间起点之内, 叙述者通过运用这样一种“内倒叙”(internal flashback)的方式,把书信那头的“你”与书信之外的“我们”安置在通往历史的路口,在网络不住的杂乱线索与纷纭的过去之中,作者与叙述者一同提问:“某一天”具体指的是哪一天?“某个时刻”到底是哪个时刻?而“那时”又意味着什么?
在回忆过去和面对现在的交谈中,答案渐渐浮上水面。“我”通过回顾“我”的病情这面“后视镜”来反复体认,反复验证那悖谬的、交织在一起的“某一天”“某个时刻”“那时”的时间坐标。“我”最初因为发高烧而引起肺炎,好转过后又患了胸膜炎,因此“我”只能作为一个“多余人”游离于“让人眼花缭乱的速度飞快旋转着的”世界之外,面对亚洲的“冲绳决战”,面对“美机对日本内地狂轰乱炸”的国家之忧虑,患肺病且病情不断加重的“我”,“完全无能为力,只是惊慌失措”,在追求着绝对同一性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国家意识之下,“我”这样的“多余人”,由于“身体”的缺席,从而失去了“人生价值”,只能在农田里干活。“第三天深夜,半明半醒之中,我便止不住地咳嗽起来,肺部也咕噜噜地作响”,此时“我”突然清醒,产生一种“咳血”的预感,并且咳出的血也验证了“我”预感的真实性。第四天,“我”感觉到快速恶化的病情,甚至想要就这样死去。就在第四天的凌晨,“血不断涌上来,眼睛,耳朵仿佛都在喷血。大约吐了两杯左右后,终于不再吐了。我用木棍儿将血被染红的土盖住……正在这时,传来了空袭警报”(太宰治,2016:38)。就这样,叙述者“我”通过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中的“经验自我”(empirical self),不断把答案拉到所有读者面前。结合先前“我”的叙述,便可得知,“我”从发病到“咳血”的这段时间线,与二战末期战况的发展时间线是平行的。1945年夏,日本在冲绳等地的疯狂抵抗导致了大量美英盟军官兵伤亡;8月6日和9日美军对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造成大量平民和军人伤亡;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在战时国家下,每一个国民理应都要尽到“国民之责”,“我”却因肺病而“缺席”于这块国民版图,这样一种疏离感使“我”只能去等死;那天本应赴死的“我”,在听到天皇的玉音放送(宣告战败)之后,却“变成了另一个男人”,并向父母承认,“我昨晚咳血了”。由此可见,作者安排叙述者安插在文本里的第一个“空白”的时间符号——圣灵潜入“我”内心的“那一天”与“那个时刻”,指涉的无疑是“战败之日”。悖谬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衍生出来的。
某一天的某个时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也应该知道的吧。就是那一天啊,就是那一天的正午啊。就是我用那可谓奇迹般的天赐之声哭泣着向你道歉的那个时刻啊。(太宰治,2016:28)
此时,第二个“空白”的时间符号出现了——虽然叙述者用着同样的“那一天”“某一天”的话语来叙述,但却变成了“不可靠的”“悖谬”的指涉。东乡克美(東郷克美,1999:46)曾指出此处的“那一天”有可能是作者笔下的“开战日”的隐晦表现。太宰治于1942年在《妇人公论》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十二月八日》的小说,其中对“开战日”有这样一段描写:“我安静地听着那句话,突然感觉到,自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此时,有一束光打在了我的面前,身体的每一寸都似乎便得透明且轻飘了。又或许是这样一种感觉——圣灵的神圣气息拂面而来,竟化作了一片花瓣,恰好降落在了我的心底里。从明天开始,不只是我,整个日本也会驶向新的航道”②(太宰治,1998:16)。伊藤整在《十二月八日的记录》中也有极其相似的表述:“我站在被那句话笼罩之下的屋子前面,时而停留,时而踱步,某一刻我突然感觉到自己从头到脚好像都焕然一新似的”(伊藤整,2011:100)。由此推测,若是把这个第二处的空白时间符号当作开战时间节点的指涉,也有其合理性。
“现在/以前-那一天/某一天-那时/某时”通过作者的叙述者“我”无意识回忆(unconcious memory)相互重叠,相互交错,作者这样一种倒叙的方式以近乎蒙太奇的手法打乱了故事原本的发展顺序。若从整体上把握文本开头部分,可发现其叙述手法以整体倒叙为主, 以局部倒叙为辅, 漫长的过往与正在进行的现在被自然且巧妙地揉杂在一起。具体来说,叙述者“我”在写给“你”的信中,叙事时序变化不定,甚至多次出现“空白”的时间符号,这些符号又与“我”的肺病发作与痊愈交织在一起。“我”尝试着用线性的叙事时间来说明自己患病时以及患病后的故事,却又试图在暗流中加入能够呼唤起隐含读者共同记忆的、超脱于疾病本身之外的战争隐语。因此导致文本中的时序时而重复,时而断裂,以一种变形的、悖谬的形式与意义的世界合二为一。“那一天/某一天-那时/某时”形成了多次重复,而“我们”却能明了其中的顺序,因此,这些“空白”的时间符号虽然因其“不确定性”体现出明显的“不可靠”,却包括了隐含读者所认同的一些信息:“我们”正是被这样一种叙述方式呼唤起共同记忆的群体,可以是被叙述者邀请的真实的书信接收者,更是可以在故事脉络中自由穿越叙述空间的、拥有相似身体经验的战时共同体。换言之,体现在无时性叙事中的时间悖谬使得不可靠叙述者“我”与隐含作者,以及所有“作者的读者”在“战争体验”这样的身体经验上达成了一致。
悖谬的“在场”:异质空间与异化的个人
战争给一个国家民族带来的文化创伤是难以言说的,战争文学因其题材的残酷性和极限性更是饱受诟病,但文化创伤因其自觉性、主体性和反思性的特点,还需要创伤者探究苦难的存在和产生的根源(任宏智, 2020: 67)。二战后的日本文学作品中,大部分作家笔下的战后民众生存空间以一种近乎残酷的、血淋淋的“伤疤”的形态展现在所有人面前,或以惨绝人寰的受害者叙事、或以残暴无情的加害者叙事,总归都会毫不保留地揭示出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国家创伤”(national trauma)。而《潘多拉之匣》中的空间构建却恰恰与之背道而驰,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可以发现文本中无一处关于惨无人道的战争描写。在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日本文坛被战争题材的国策文学充斥着,太宰治却似乎绕道而行,奥野健男也指出,“太宰治对战争无视以及否定是他一贯的态度”(曾婷婷,2018)。在发表于战败之时的《潘多拉之匣》中,有关于作者的战争认识以及战后的社会适应,其实是隐藏在文字之下的,隐含作者通过赋予文本中空间的悖谬性与异质性,并将登场人物进行一番异化,暗示读者不能简单地把文本中由原型改写的空间放在“真实”的维度上,而是要把这个空间看作是一个被叙述者符号化的产物。换言之,隐含作者以文本中异质空间与异化的个人为镜,折射出充斥着整个文本的悖谬意识之下,于战争洪流之中既无法顺流而下遵从时代变迁、又不能逆流而上抽离自我的“多余人”画像。
在《潘多拉之匣》中,叙述者“我”向父母坦白了咳血一事之后,便被父亲送入一个名为“健康道场”的疗养院,这个疗养院是为了应对战争中粮食和药品的不足而建立的,结构上分为“新馆”和“旧馆”两栋。“健康道场”是“奇妙”的地方,第一点在于其存在的奇妙性,在战争中有很多医院被炸毁抑或因为物资不足等原因而被迫关闭,而这个疗养院却在能保证所有入院患者一日有营养三餐的前提外,还能让专业的医护人员(文中名称‘补习生’)带领每一位患者每日都有计划地进行康复运动。第二点在于其治疗方法的奇妙性,“健康道场”的场长独创出一个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忘记疾病”,也就是说,只要把肺病一事抛在脑后,肺结核便可得以治愈,而文本中运用倒叙的叙述者“我”在书信一开始,便告知了读者——“六个月我就痊愈了。以后再也没有咳血,连血痰也没有。疾病的事情我已忘却”(太宰治,2016:41)。第三点,在于其患者的奇妙性,“我”以及疗养院中的每一名患者都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身份标签”:“我”是一个“啾啾地大声鸣叫着,嬉戏着”的“云雀”;“我”旁边名叫松右卫门的“有威严”的“果敢家”成了“越后狮子”;木下先生因为经常哼唱《都都逸》之类的俗调,加之“轻轻扭着屁股”的走路姿势,因此被大家叫做“都都逸”;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充满书卷气且瘦瘦高高的被大家称为“笔头菜”的男人。
需要注意的是,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我”口中的“患者”都是存在于疗养院中“新馆”里的男性人物,“我们”的绰号在这个空间中变成独属于自己的符号。在国家高唱着“男性气质”征兵之时,患病的“我们”犹如失声者只能于边缘之外流离不定,但这些绰号的存在使“我们”在入院之后重建了一个更能被自我所认同的身份标签。龙迪勇在《空间叙事学》中指出,空间本身是历史或时间的产物,空间的特定历史总是与人物的典型性格或人物的“主体性”相互关联(龙迪勇,2015:260)。在这里,作者在文本中有意将人物塑造与空间描写相结合,“健康道场”这一空间设置的异质性,首先从贴在登场人物身上的标签中就可发现,从战时到战后这段特殊的时间里患了肺结核且入住到“新馆”的“我们”是拥有相同患病经验的共同体。而“我们”想要丢弃的究竟是自己变为“新男性”之前的身份,还是一直与“我们”的患病时间相平行的战争记忆呢?
文本中种种不可靠叙述都指向其空间的异质性与悖谬性,时刻提醒着读者这样一处空间设置的背后,印刻着的是有关以“病人”的身份存在于战争生态之外的身体话语。文本中与每个人物都紧密相联的“肺结核”,因多发于战争时期在兵营里集中训练的士兵中,所以在二战末期成为极易传染的“战争病”之一。这部作品最终版完成于1946年二战之后的时间节点上,战败不仅仅造成国家经济崩坏、社会秩序混乱,也致使肺结核的发病率达到顶峰,更为雪上加霜的是,相当一部分医院被迫终止运营造成了病床数量在短时间内急剧降低(见图1)。
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的肺结核疗养院从“为生活贫困者增设的、防止进一步感染的机构”变更为“收治传染源患者的机构”,在太平洋战争时期疗养院曾因战局的恶化一度陷入停滞状态,到了1945年可以说是日本结核疗养院的“冰封时刻”。就当时的社会背景而言,战后日本整个国家都陷入了粮食资源紧缺、社会秩序崩坏的困境,像“健康道场”一样能保证每一个患者的一日三餐,甚至绰绰有余的疗养院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部作品是太宰治根据木村庄助的实际病榻体验改写而成的,无论是战争时期患肺结核的叙述者,抑或是让每个人都想要丢弃原本身份的“健康道场”,都是可以追溯到原型的。“健康道场”的原型是位于东大阪市的孔舍衙健康道场,在1942年太平洋战争开战的第二年便因战争原因被迫关闭,作者通过改写,将“健康道场”作为一种想象的载体,在想象性建构中,“道场”成为神圣的地方,成为“大家团结一心,为了战胜结核,从早到晚努力修复身体的地方”。这样一种建构除了承载想象,更激起所有隐含读者的战时身体经验的共鸣:所谓“过去”其实是“过不去”的彼岸,“我们”如同困兽,在天皇制之下的战争枷锁中动弹不得。在“健康道场”里,“忘却疗法”代替了实际的“大气·疗养·安静”疗法,简单的医护人员与病患之间的关系也变成了一种“战友同盟”式的,彼此用诸如“在做呢?-做呢。加把劲啊!-好嘞!”(太宰治,2016:60)这样一种激发战场斗志的激励性话语来维系彼此的特殊关系,而类似于士兵锻炼法的、不合常理的例行“腹肌锻炼”让“健康道场”这个空间变得复杂且荒谬,并逐渐异化——看似彼此矛盾的多个空间被并置在一个维度,不仅这一凸显了其多元性和包容性,同时也将多个不同类型的空间以一种隐喻的方式重组到一起,生成新的意义。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架空了原本真实存在的空间,用悖谬意识填充出一个多层次、多向度的意义空间,从其暗流中浮现出来的矛盾与冲突中看,患病的身体成为构建异质空间中共时性事件构成的唯一通道。
在不可靠叙述者“我”的笔下,异质空间不仅使身为“多余人”的自我身份得到内化,还通过特殊的时间叙事构建出一条能与隐含读者心照不宣的意识地带,这种内化使“我们”转变为拥有独特身体经验的“战时共同体”——“我们”每一个因疾病被战争排除在外的“多余人”,都在以介入现实的方式“参与”战争。这样一来,在与现实相悖的异质空间中,“我们”的身份与命运想要被重新定义:“我们”究竟该何去何从?这样一种反思,使得表层文本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充。叙述者“我”从故事的开篇到结尾都重复着近乎相同的话:“从那天开始,我感觉就像乘上了一艘新造的大船”。被“我”符号化的“大船”在文本中重复出现了26次,加之诸多关于“新男性”的嵌入式叙事,表层文本用直白的话语告诉读者:“我”已经成为委身于“新造之船”的“新男性”。但充满悖谬的异质空间与时间线却道出了只有“我们”能彼此互通的隐语:在用架构出来的空间想象标记出的每一处清晰明了的战争坐标上,“我们”只能是战争中的“多余人”,战后的“败北者”。因为异化,“我们”获得了一个绝佳的存在场域,同时也失去了突围的可能。
悖谬的“主体”:患病的身体与战争集体记忆
碎片化的记忆片段构成了叙述者“我”患病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中悖谬且明显被打乱时序的记忆片段中可以看出,“我”与书信那头的“你”以及“健康道场”内的“我们”心里,都存在着同一种“独特的”战时国家意识。当“我”通过扩音器听到美军进驻消息时,“突然涌上来一股难以名状的极度悲伤之感”(太宰治,2016:122);越后狮子一边批判着投机思想,一边大声呼喊着“天皇陛下万岁”;花宵先生在察觉到患病的“我”焦虑不安之后,安慰我“只要安心在这里生活,就一定能痊愈,然后就可以为日本的重建贡献一份力量”(太宰治,2016:306)。这样看来,“我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答案不言自明。“我们”虽然因病变成了战争中的“多余人”,但“健康道场”的存在却让我们不断地介入现实。肺病既是战争中“我们”的“记忆在场”,同时又是“身体缺场”,可以说,“我们”作为被疏离于战场之外的人,对于战争唯一的记忆便是“疾病”。1944年,太宰治发表了名为《散华》的短篇小说,“肺病”在其中也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作为登场人物之一的三井与《潘多拉之匣》中的“我们”一样,因肺病导致战场中的“缺席”。对于“肺病”元素的借用,不仅与太宰治本人因患肺浸润而被免除军队征用资格的经历有着切实联系,也包含了他作为一个国民,对于国家、对于时局的态度隐语。
在此基础上,一个不断试图介入现实却又不可能存在于现实的“健康道场”,与其说是一个空间意义上的“乌托邦式的存在”,不如说是一个时间意义上“填补缺口”的存在。1945年初,昭和天皇曾提出“以战求和,维护国体”,希望通过战争胜利来维护国体,并坚信“这场战争只要坚持就能够获胜”(龚娜,2017:41),哪怕以造成大规模人员死伤为代价去维护天皇制也能够接受,但随着德国无条件投降以及冲绳战局的变化,加之美国连续对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造成大面积伤亡,昭和天皇做出了“圣断”:在8月15日《终战诏书》中,昭和天皇声称,通过“圣断”终结战争的结果在于“朕兹寄信赖于可护持国体,忠良之尔等臣民之赤诚”(龚娜,2017:42),确信“神州之不灭”,应着眼于国家之重建。这样一来,“圣断”政策起到连接战前战后的桥梁作用。文本中“健康道场”这一意义空间承载着从战时到战后厚重的意识形态,“新式”则是其中最重要的方向与目标:每个人都在这里试图重建一个“新式”自我,哪怕这里的每个人都是“多余人”、都不曾参与战争。作者看似执拗地不断反复着有关“新式”的话语,实则将批判的锋芒对准以国家重建为目标的“圣断”政策。
道场场长所提倡的“忘记疾病”的治疗方法,从某种层面上说,隐喻天皇作出“圣断”决策之后,日本为了规避战争记忆与责任,忘却战时军国主义,跨越到民主化、反军事化的“新式日本”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文本前半部分中,“我”与“你”虽然都不约而同地宣告自己对于“新式日本”构建的决心:“我们的生命已经奉献给了某个人物,不再属于我们自己了,因此,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轻松地委身于这艘所谓天意的大船上,这是新世纪的勇气”(太宰治,2016:107),但在文本的后半部分中,这样一种忘记过去、直接迈向彼岸决心却遭遇败北,正如越后狮子所言:“到昨天为止,它是古老的,但是在今天,它是最新的自由思想。……我要是没病的话,现在就恨不得站在二重桥前,高声呼喊天皇陛下万岁”(太宰治,2016:107)。文本中这样一种保守派宣言的回归,不仅在表面上指涉战败之后民众自发前去皇宫前二重桥广场上高呼“天皇陛下万岁”的事件,也凸显了隐含的作者独特用意,这样一种叙述方式使不可靠叙述中的杂乱扭曲的时间线与悖谬的空间再度交融,叙述者“我”用凌乱重叠的碎片化陈述,使文本呈现出一种共时性的空间效果:“我”在开战与战败的时间点与其空间坐标点上随意穿梭。这样一来,开战之时日本国民齐声呼喊着的“天皇陛下万岁”,与败战之后民众对摆脱战争责任的“救国英雄”天皇再次呼喊的“天皇陛下万岁”穿梭交叉在一体。而被“那一天/那个时刻-某一天/某个时刻”这样一种叙述方式呼唤出的战时共同体最后一次被邀请进来,那些试图忘却但又不能忘却的战时记忆,以及想要驶向但又不能到达的战后彼岸,在这穿梭与交叉中愈见明朗,跃然纸上。
战后时期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历史的车轮推动着(抑或迫使着)每一个人直面重建起来的“新式”的社会秩序以及道德体系,通过文本中的种种不可靠叙述,作者也被邀请进来,一起诉说着一个问题:“我”(战时共同体)的疾病真的通过“忘记疾病”而痊愈了吗?答案是否定的。进一步挖掘的话,这个问题又或许是:“我”(我们这一代人)真的已经在占领政策与国家要求之下,做好准备去游过这条“暗流”通向战后的“彼岸”了吗?答案似乎也是否定的。1945年8月15日,天皇自宣布战败之后便走下神坛,日本人对天皇的忠诚观念瞬间崩塌,国民身份认同也极度萎缩。在传统价值观崩坏之际,以德田球一与志贺义雄为代表的日本共产党人在《赤旗》复刊后曾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打倒天皇制,建立基于人们意愿的人民共和政府”(陈月娥,2019:104)。太宰治对此现状,借越后狮子之口批判:“在日本,如今还在攻击昨日的军阀官僚,这已经不再是自由思想,而是投机思想”(太宰治,2016:263)。对于同时间段在“民主、自由”思潮中高涨的天皇战争责任问责,太宰治本人依然坚持“要无条件把天皇作为伦理道德的模范”,在其他文学创作中,心向天皇热烈的爱意也处处可见。在《苦恼的年鉴》中,太宰治曾说道:“我如今梦想的境遇,是以法国伦理思想家的言说为基调,将天皇作为伦理道德的模范,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无政府主义的世外桃源之中”(太宰治,1998:205)。可以说,在民主主义袭来的浪潮中,战场缺席的“我们”这种“多余人”,即使曾经作为“局外人”旁观时局风起云涌,但“我们”仍旧难以跨越这条新与旧之间无缝衔接的“暗流”,天皇对国民身体的烙印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要铭记自己的身份,而身份的认同却又凝结成天皇制枷锁之下的想象共同体。这是枷锁与禁锢,是无法言说的却又“公开”的秘密,也是太宰治本人文学创作的局限性所在。
结 语
二战以日本的法西斯无条件宣布投降而结束,在经历战败体验之时,许多作家都选择以直白的叙事方式描写战后废墟般的日本。如无产阶级作家宫本百合子笔下的《播州平野》,从战争导致的家庭破碎景象直到潜藏在民众内心深处的心理创伤,每一处似乎都在还原着日本的战后实景。而太宰治却用一种看似“疏离”的叙事方式,在另一端描绘充满着矛盾与悖谬的时间与空间,不去描写战争的残酷,不去揭示被战争泯灭了的人性,也不去批判军国主义的罪恶,而是用病态的身体经验去把握表面上看似缺席的战争体验,借不可靠叙述者之口中的看似杂乱的“事件”去揭开战后社会民众的共同弱点与伤疤,从“局外人”的视角去介入开战直至战败的整段战时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在《潘多拉之匣》中,潜藏文本对表层文本中的战后民众的自我认同问题与“自我”对战后社会的适应问题形成补充,又构成一定程度上的反写和纠偏。换言之,文本中的显性情节聚焦于患病的身体突破困境重生希望这一主题,而隐性进程③则围绕着天皇制之下战后民众生存困境展开,两种不同的矛盾同时并行,且互为补充。这样一种巧妙的文本设计,通过太宰治“炫技”式的写作技艺,使作品中矛盾性与复杂性以“悖谬”的形式浮上水面,构成了太宰治文学作品独特的悖谬美学。
太宰治在创作《潘多拉之匣》这部作品时,虽然有原型可据,但种种悖谬使原型中的“肺病”与“健康道场”变成一个特殊的战争记忆途径。而记忆是人类赖以建构自我身份的重要认知活动,也是一个包含着“想象的真实”的行为,在连同真实作者在内隐含作者、叙述者一起诉说肺病患者作为“旁观者”的战时及战后体验时,“想象的真实”在叙事行为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验。在对特定时间的暗示性指涉上,叙述者“我”的记忆叙事一方面揭露了不可靠叙述中的种种悖谬意识,将过去已然成形的战争印象(时间/空间)之所说变成开放性的言说:另一方面使所有拥有集体记忆的战时共同体由静态的回忆,转向动态的记忆言说,并在“疾病已经痊愈”的“现在”这个时间点上,在保证与战争以及战后社会之间有一定留白的空间点上,重新审视天皇制之下战时共同体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与想要挣脱却无法挣脱的战争枷锁。
注释:
①本文所使用的“实际作者”和“隐含作者”的概念,均引自韦恩·布思.1983.小说修辞学[M],华明,等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②[日]太宰治「十二月八日」,太宰治『太宰治全集6』より,ちくま文庫.1998:16。本文所有日文文献,若无特别注明,均为笔者翻译。
③申丹在其《何为叙事的“隐性进程”?如何发现这股叙事暗流?》中曾定义,隐性进程是“与情节发展呈现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走向,在主题意义上与情节发展形成的一种补充性或颠覆性关系”(2013:47)的叙事暗流。“隐性进程”以其贯穿叙事进程的始末,以及探究过程所引发的“逐步增强的审美愉悦”和“不断深入的主题思考”而区别于莫蒂默(A.K.Mortimer)提出的“第二故事”。“隐性进程”与显性情节的“并行性”又使它完全不同于传统文学批评中的“象征意义”或“隐匿情节”(申丹,201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