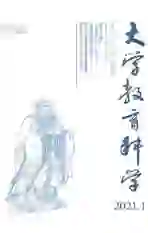意义世界视域下课程思政的价值旨归与根本遵循
2021-03-24聂迎娉傅安洲
聂迎娉 傅安洲
摘要: 课程思政蕴含着教育构建学生意义世界的内涵,凸显了学科知识内在的丰富意义,呼吁在重视知识“价值”与“意义”的过程中回归大学生的精神成长,从精神向度上丰富了对课程育人的理解。意义世界视域下,推动课程思政走深走实,需要从回归知识的价值性、回归知识的情境性、回归学生的主体性三方面着力,切实在促进学生的精神成长上发挥作用;需要以“以文化人”为根本遵循,明确育人目标、文化内容和化人方法,让文化有机渗透课程思政建设的全方位、全过程,使课程学习体验转化为个体的价值追求和精神成长。
关键词:课程思政;课程育人;意义世界;精神成长;以文化人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1)01-0071-0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国别比较视域下‘课程思政育人支持体系研究”(19YJC710053);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课程思政理念下通识课程与思政理论课同向同行研究”(2018SCG213);同时受浙江省高校思政名师工作室(伍醒)支持。
2020年,我国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下简称《指导纲要》),明确全面推进高校所有学科的课程思政建设,并就行动方案做出了国家层面的整体设计和全面部署。《指导纲要》指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就是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角度,这要求把教育教学作为最根本的工作,凸显课程知识内在蕴含的丰富意义,真正实现从培养“单向度”的人到培养“完整”的人的转换。
一、课程思政呼吁课程回归意义世界
马克思的人学理论不仅揭示了人生存的事实世界,还“在思想的自我反思和实践的不断超越中为人类生存创设了一个专属人类的意义世界”[1]。因此,意义世界形成于探寻存在本質、价值和思考人自身存在意义的过程中,旨在满足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需求。课程思政契合了教育构建学生意义世界的理念,是教育存在价值的一种人性解读。它关注到课程教学中侧重事实层面“是什么”的问题偏向,认为应进一步追问价值层面“意味着什么”“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学生意义世界的生成。
(一)课程具有构建事实世界和意义世界的双重属性
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出发,教育是人的一种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是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和作为实践客体的活动对象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人既要在实践中认识和改造世界以满足生存需要,又要在从事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反思活动的意义,二者共同致力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教育的本质就在于提升作为实践人的价值,是主体人的再生产”[2]。课程,作为从学科专业角度对知识进行分类基础上开展的一种教育实践,内在地蕴含着帮助学生认识事实世界和构建意义世界的双重属性:一方面要引导学生认识事实世界,将课程知识作为客体性存在,教授学生有关客观事实的知识和规律,以及认识和改造物质世界的方法与能力,使其学会怎样生存;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建构意义世界,将课程作为承载情感与价值、蕴含历史与文化的中介,启发学生思考客观世界对主体生命的意义、追求何种意义以及怎样去过有意义的生活等,使其思考为何生存。课程知识这种鲜明的教育属性,不是仅局限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或者某一类课程,而是指将所有课程作为教育实践的载体,在知识学习过程中浸润价值问题,并上升到对价值的追问和意义世界的构建,达成专业话语体系和价值话语体系的有机融合,由此在课程教学中实现事实世界和意义世界的有机衔接。
(二)现代化使高校课程趋“事实”远“意义”
科技发展及现代化带来的专业细分和职业分工,使高校在承担教学科研职能的同时,还要肩负对学生开展实用知识和专业技能教学的重任,以满足社会高速运转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由此,科学知能在学校课程教学中的核心地位被牢固确立,这里的知能是指中立的、价值无涉的逐渐学科分化的知识技能。这种知能观在实用主义哲学的裹挟下,“表现出强调知识的经济和社会功能,强调知识的实用性的倾向”[3],高度契合时代发展对大学走出纯粹科学、服务社会的呼声。由于人们希望在课程中习得在未来生存实践中所需要具备的“有用”知能,提高改造物质世界的能力,高校课程也因此逐渐转向客体化知识教育和技能培养。即课程按照现实社会的物质需求来培养人,即使德育课程传播的也主要是客观抽象的、脱离生活情境的道德知识与道德科目,而非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选择和理想信念,陷入“知性德育”的囹圄。在这种教育实践中,课程逐渐趋“事实”“工具”,远“价值”“意义”——知识以客体化、工具化方式存在,被视为认识和改造外部世界的工具,脱离了知识内在蕴含的文化价值和精神意义,忽视了主体人在改造世界的同时对自身意义世界的建构。知识的学习和主体的精神成长相分离,导致大学教育“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因此,人被异化为物质的附庸,“在教育中只被看成是未来的生产力、未来的人力资源”[4],成为“单向度”的人或工具人。
(三)课程思政强调课程中意义世界的构建
现代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关注物质需求和经济增长,到关注人的主体需求和全面发展的转型,教育也相应地从关注物质的、经济的外在客体,转向关注精神的、文化的主体。不论是已故钱学森院士对于“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困惑,还是北大钱理群教授对于大学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忧虑,都反映出我国学者对近代工具理性发展使课程陷入重知识与技能、轻情感与价值的反思,以及对大学课程脱离习得主体“意义世界建构”的担忧,归根结底反映的是课程育人中意义世界的缺失。我国课程自古就蕴含“诗书礼乐以造士”的思想,西方的“经验论”“唯理论”也彰显了课程具备建构知识、技能与理智的多重内涵。在现今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多元文化激烈交锋、社会思潮交织激荡的时空背景下,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完整”的人,要求“将课程话语的焦点从课程知识的掌握问题转向课程知识的意义问题,即敞亮知识所蕴含的意义世界,关注知识对于人的生存意义的指引和生命境界的提升”[5]。课程思政中的“思政”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简称,其目的是将一定的价值观念内化为理想信念与精神追求,外化为行动自觉。课程是思政的载体,通过在整体设计和教学实施中挖掘思政元素,并系统、有机融入课程教学,进入知识的意义世界,把价值引领建立在课程知识的基础上,丰富价值引导的知识底蕴,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时间和空间,旨在从供给侧满足学生成长成才的精神文化需求,“促使个体在教育过程中形成具体的、稳定的价值选择与判断能力,以个体的发展推动社会的发展”[6]。
二、以促进学生精神成长为价值旨归
事实世界意蕴下,高校人才培养主要聚焦高效的知识学习这一主题,无论是课程教学改革还是培养模式革新,学生发展皆以学习知识、提高技能为中心,呈现出鲜明的专业化、实用化和技术化特征。但是,大学却从未停止过对“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培养人”的思考。20世纪中叶,《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呼吁现代大学不仅应发展专业教育,还应关注培养“完整”的人。我国学者也提出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应该“改变知识本位,尤其是专业知识本位的狭窄单一教育观”[7]。在此背景下,课程思政要求所有课程在学科分化基础上寻求“思政”价值方向的统一,澄清了课程在意义生成过程中回归大学生精神成长的内在价值诉求。
(一)促进学生精神成长的价值内涵
全球化时代复杂交错的政治文化,使人们不得不反思高等教育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按照物质文化需要培养人的外在化教育“突出量化的手段和技术角度,使得对学习过程的处理过分强调经验客观、价值中立而简单化”[8],消解了知识所蕴含的价值与意义。这导致课程知识与价值、课程学习和个体意义相互分离,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使课程教学陷入“只见知识不见人”的困境,而解困之举的关键在于反思课程育人。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首先是一个精神成长的过程,然后才成为科学获知的一部分[9]。循此理路,课程育人首先在于促进个体精神成长,这不仅凸显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和学生成长的主体价值,还内含课程必须转向学生内在的、自发的精神成长之意蕴。换言之,课程育人不仅要关注客观知识的认识论价值,还要关注学生成长的本体论价值。
课程思政反映了一种将思政寓于课程之中的教育理念,它将知识视为“有待发育的精神种子”[10],通过引领学生进入知识所蕴含的丰富意义世界实现精神成长。首先,知识不只是中立的客观性内容,它还是特定文化价值在教育教学中对知识进行选择、组织和创造的结果。课程史上从“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到“谁的知识最有价值”的理性思辨,关于知识与价值关系的反思和追问从未停止。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价值是指“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意义关系”[11],知识价值就是作为客体的课程知识满足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的程度。这种价值性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在古代教育中主要表现为满足人纯粹的精神需求,在现代大学中则主要表现为功利性、实用性。因为知识总是服务于某种社会目的,“所有的知识生产都是受着社会的价值需要指引的,价值的要求已经代替求知的渴望成为后现代知识生产的原动力”[12]。其次,知识不只是普遍的对象性内容,它本身不仅“是探究的产物、结果形态”,还内在地蕴含着过去探究、创造、研究、发现、建构的过程与方法,是未来探究行动、方法以及过程的原材料[13],堪称人类的文化遗产。知識从生成、探究到传播的整个过程,都受到文化的影响,与一定文化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息息相关。我们只有充分理解课程知识的内涵,将对意义世界的追求转化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相适应的精神价值,才能在课程知识和个体精神之间建立内在的文化共生关系。
(二)促进学生精神成长的内在逻辑
知识蕴含的丰富意义使学生通过课程实现精神成长成为可能。以此为导向,课程教学应从致力于学科体系和知能习得,转向在课程中获得知识价值和个体意义。这并非否定知识学习,特别是专业知能的重要性,而是要求将课程知识理解为“人类参与这个世界过程中创造性涌现、生成的产物”[14],在传统知能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导学生参与知识选择、知识习得和知识应用等过程,从课程中获得个人经验,因为“意义不是内在于课程之中的,而是个人赋予其上的”[15]。
首先,课程知识具有主观选择性。知识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创造的,选择哪种知识才能避免远离人文关怀与生命关怀,才能更适合精神成长?传统课程知识观视域下,人们将课程与知识的结构关系、知识的社会经济价值作为知识选择的标准。但这显然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知识环境。随着人类进入“知识爆炸”时代,知识选择不再以实用作为唯一标准,最迫切的任务是“反思科技理性的缺陷,探寻人性的真实需要”,人与知识的关系也由此转向“探寻和构建知识育人的意义关系”[16]。例如,在最基本的关于体力劳动经验性知识的学习中,也可以渗透对劳动重要性的省思,进而追问劳动对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意义。
其次,知识习得具有意义相对性。既然知识学习是个体在理解知识、掌握知识、占有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激发兴趣、启迪智识、发展思维,使知识“成为个体精神和人的意义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17](P61)的过程,那在知识和人之间建立起的意义关系便是因人而异的。在课程知识的有序供给中,这种相对性体现在既要推动学生克服个体局限,学习普遍知识,又要使其在与知识的对话和交往中实现知识内化,不断丰富发展自身意义世界。如此,学生便不是从属于知识,而是在知识习得过程中实现了精神参与。
最后,知识应用具有个体差异性。知识应用是学生主体内在意义外化的过程,学生通过对知识的学习,将“一般”知识内化为“个别”知识,并在具体实践中通过行动运用知识。这需要承认学生个体经验、情感、态度等要素在知识运用过程中的价值与意义,在课程实践中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从被动学习者转化为知识发现者、知识探究者和知识创造者,实现从他者促学到自我教育的转向,通过对知识的追问、对实践的创生和对意义的探究等行动达成精神成长。
(三)促进学生精神成长的三个“回归”
知识蕴含的丰富意义解释了课程滋养个体精神成长的内在逻辑,也丰富了课程思政的内涵,为结合专业知识分类推进课程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拓宽了实践思路。但囿于工具理性主导的现代大学课程模式中,量化评价很难测量知识所蕴含的精神价值,以及知识对人的文化教育意蕴。因此,学科知识转化为个体的智慧与美德还迫切需要解决知识与价值分离、知识与情境分离、知识与主体分离三个问题,促进知识文化性的回归。
一是回归知识的价值性。知识并非中立的,所谓的普世价值实为伪装了的意识形态。古今中外,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的[18]。具体而言,几乎所有的课程都可以做到知德双栖,思政课程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非思政课程要在既有课程框架和知识结构基础上挖掘知识的价值意蕴和文化基因。如文史哲课程可在专业知识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知识传播强化价值引领,达成知识和价值的同频共振;理工类课程中则可以渗透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体现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和服务国家的科学伦理,激发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二是回归知识的情境性。知识具有地域性和文化性,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关系作用的产物,体现着特定区域或者特定文化影响范围内人们的生产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知识合法性的来源既不能离开对特定历史情境和文化背景的分析,也不能离开对知识主体立场和偏好的分析。这表明,知识只有在特定的时空和文化背景中才容易得到认可,有效的知识传递需要建立在不同主体互动沟通和达成一致的基础上。因此,知识学习需要具体化、本地化、情境化,课程思政就是呼吁根据不同学科特色,从“课程所涉专业、行业、国家、国际、文化、历史等角度,增加课程的知识性、人文性”,促进教材中普遍性原理知识转化为学生的个体认知。
三是回归学生的主体性。知识承载着情感、态度和价值。英国哲学家波兰尼曾指出,任何知识都是客观性和个人性的结合,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饱含个人寄托和融进了识知者的热情的个人参与过程”[17](P54)。我国历来有因材施教的传统,即根据学生差异化、个性化的成长背景、知识结构、学习能力和个体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学生知识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理性认知、心智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与认识对象的对话和交往,引导学生走向深度学习,因为“学习如果只发生在知识的表层就难以达成德性养成的目的”[19]。学生只有通过浸润知识所蕴含的价值与意义,才能整合自身的思维、情感、价值和行为,生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当下,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已形成基本共识,课程思政实践探索已涉及文史哲、理工农等12个学科门类,主要推进方式是结合学校学科优势开设课程思政特色课,建设课程思政示范课,挖掘专业课程中的思政案例和知识框架中的思政内容等。在意义世界视域下,课程思政可理解为一种新的课程观,浸润着对课程知识要素价值性进行筛选和实现价值实践的迫切需求;也可理解为一种教育观,“蕴含着对现行课程制度的反思和课程应然状态的新时代设想”[20]。如此,思政元素可理解为一种精神元素,各类课程要实现同向同行,必须在促进学生的精神成长上发挥作用。
三、以“以文化人”为根本遵循
促进学生精神成长,核心在于培养学生自觉超越生存的文化精神,因為文化是涵养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育人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21],这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内在要求,也是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创新发展的新路径,为进一步推进课程思政提供了新的增长点。促进学生精神成长,必须以“以文化人”为根本遵循,科学回答以文化人的课程释义,明确育人目标、文化内容和化人方法,将文化有机渗透课程思政建设的全方位、全过程。
文化可以理解为“人化”,人既创造文化又受到文化规范。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2]。人类在物质生产实践中形成了稳定的生存方式与特有的文化模式,这种生产方式和文化模式被人们所接受,并反过来约束和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就是文化的生成与传承。学校是人们系统接受教育的场域,课程是特定文化价值在教育教学中对知识进行选择、组织和创造的结果,这使得课程与学生个体间建构了一种内在的文化关系。课程可以借助知识实现个体精神养成,进而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现实场域中获得文化价值的认同。因此,教育的本质就是以文化人,即用文化的内容和文化的方法,使课程学习体验转化为个体的价值追求和精神成长。
(一)在课程文化自觉中反思育人目标
以文化人要求在教育目标上使人成“人”。文化与人的劳动实践息息相关,它“起因于人的现实需求,归于人的现实生活,成于人的生存方式”[23](P148)。这里的人既可以指某一时空背景下作为一个群体创造文化的人,又可以指在劳动实践中接受文化规范并追求个体发展的人。从育人视角来看,既有教育模式倾向于培养“单向度”的人,我国传统儒家教育思想培养的是“道德人”,西方中世纪神学培养的是“神性人”,后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价值主导下学科课程培养的是“经济人”和“工具人”,这极大地消解了人的文化属性。在当下的高校课程实践中,教育对象是成长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青年学生,他们的学习过程中中西文化交织,专业课程精细化,实践教学开放化,学习和生活方式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等特点,以文化人就要在尊重学生的内在需求与成长规律的基础上,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24],“用教育对象自己在劳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生存方式培育其自身”[23](P146)。这要求作为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课程体系承载相应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即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以满足培养“完整”的人的基本要求,更好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思政”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德育词汇,强调的是立德树人,凸显了立足本土教育实践进行课程改革的中国视野。“课程思政”是我们通过课程文化自觉,建立全课程教育共同体,在中西文化对话与冲突中不断反思课程育人、探寻教育价值的一种本土课程方案。它既要服务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凸显学校育人特色,又要服务于立德树人这一根本目标,凸显课程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主体性意识。如,在上海高校推出的“中国系列”课程中,东华大学依托纺织学“双一流”学科开设“锦绣中国”课程,上海中医药大学依托与医学相关的三个“双一流”重点建设学科开设“岐黄中国”课程,不仅立足学校特色专业和优势学科,而且主语都是“中国”,讲述学术沉淀背后的历史、文化、哲学等要素,让学生在了解中国、读懂中国中增强文化自信。
(二)将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教学建设全过程
以文化人要求促进课程内容的有机融合。课程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具有促进学生精神成长的育人功能,目前比较普遍的做法是将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追求嵌入课程知识结构和实践体验之中,增强思政教育的文化蕴涵。历史上,不论是孔子修订六经,还是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都是将受教育者的学习体验与文化滋养紧密相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文化育人经历了满足青年学生文化需求、积极开展高校第二课堂、丰富创建大学校园文化、培育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的发展阶段”[25],從基本走向上越发注重内容融合贴近学生生活体验,文化传递上重视政治引领和价值引领。《指导纲要》指出,要以学生为中心,“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等重点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这并不是指简单地把该部分内容叠加到既有的课程知识框架中,而是要在深入挖掘二者内在统一性的基础上,结合专业特点和课程类型实现思政元素的课程教学融入。如,2020年中国经历的抗击新冠肺炎之战,是所有中国人亲历的大事件,也是一个特殊的“思政”课堂。面对疫情,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科学精准施策等,是思政课讲清楚中国之治,引导学生坚定四个自信的生动案例;面对疫情,医护人员的挺身而出、逆行出征可以融入医学类课程,作为医德医风、医者精神教育的典型素材;面对疫情,科学家快速应变,开展病毒检测和疫苗研发等科技攻关,可以融入理工类课程,作为培养学生探索未知、勇攀高峰责任感,激发学生科技报国使命担当的重要催化。如此,通过挖掘课程内容中的思政元素,将其渗透在课程目标、课程大纲、课程教学与课程评价的各个方面,可以在学习中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达成知识与价值的同频共振。价值是文化的核心内核,不管是人文知识、社会知识还是科学知识,都不是价值无涉的,学科分化背景下更应该贴近学生专业学习与生活实践,深入挖掘课程文化中的思政元素,增强课程教学中知识文化要素与人的精神需求之间的互动,激发学生学习的内生动力。
(三)“四维”推进助力课程思政育人润物无声
以文化人注重方法的潜移默化。以文化人的“化”有教化、感化、润化、转化、美化、涵化、化解等意,突出的是一种方法论,强调运用文化的力量影响人、规范人、培育人。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26]。它的突出特征是潜移默化,将教育者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渗透到课程要素中,引导受教育者在学习过程中自发接受熏陶,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从课程物质文化维度,一方面要利用好课堂教学主渠道,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为学生学习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另一方面要综合运用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通过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实习实训等活动丰富课程文化载体,以优质产品和文化活动增强文化知识的价值引导。从课程精神文化维度,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教学中的落细落小落实,激发深层次的情感共鸣,促进人的精神成长,指引学生理解生活的意义并追求有价值的生活。从课程制度文化维度,要通过课程顶层设计凸显价值导向,在课程体系、课程内容、教材建设、教学方法改革中有机融入思政元素与文化内涵,辅之以科学的教学管理制度、科研激励制度和行为规范制度等,利用文化的整合力构建全课程、全方位的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强化课程思政的组织实施。从课程行为文化维度,要倡导知行合一,贴近学生生活,通过知识认知、情感认同、行为参与的逻辑理路,将理性认识与价值认同转化为具体的行为。例如,在爱国这一核心价值的指引下,开展关于国旗、国歌等标志性符号和重要节庆纪念日的仪式教育,开展典型爱国人物事迹的学习等,培养学生关注、调研和分析现实社会民生问题的意识与能力,激励学生主动投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
课程思政自2014年提出至今,已从上海学校的地方探索,发展为全国推广的教学改革,再提升为落实立德树人的战略举措,肩负着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任。新形势下整体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不是要把所有课程上成显性思政课,而是要构建一个涵盖工作体系、教学体系和内容体系的德育系统工程。课程思政拓展了学科知识内在蕴含的丰富意义,呼吁课程回归意义世界,切实在促进学生的精神成长上发挥作用。这需要从根本上遵循以文化人规律,将思政教育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大学教育的全课程,融入课程教学建设的各要素,落实到课程编制的各方面,贯穿于课堂教学的各环节,真正实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法制人、以行带人。
参考文献
[1] 张懿,夏文斌.马克思的意义世界理论探析[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05): 45-52.
[2] 鲁洁.通识教育与人格陶冶[J].教育研究,1997(04):16-19.
[3] 伍醒.知识演进视域下的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迁[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128.
[4] 鲁洁.边缘化 外在化 知识化——道德教育的现代综合症[J].教育研究,2005(12):11-14+42.
[5] 苏鸿.意义世界视野下的课程知识观[J].课程·教材·教法,2007(05):9-13.
[6] 孟庆楠,郑君.基于“课程思政”的高校课程转化:价值、目标与路径[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3):139-145.
[7]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专题研究组.走向2030: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之路[J].中国高教研究,2017(05):1-14.
[8] 李金碧.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的反思与范式重构[J].教育研究,2017(04):49-54+116.
[9] [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3.
[10] 郭元祥,吴宏.论课程知识的本质属性及其教学表达[J].课程·教材·教法,2018(08):43-49.
[11] 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86.
[12] 石中英.知识性质的转变与教育改革[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1(02):29-36.
[13] 张华.课程与教学整合论[J].教育研究,2000(02):52-58.
[14] Deborah Osberg, Gert J. J. Biesta, The Emergent Curriculum:Navigating a Complex Course between Unguided Learning and Planned Enculturation[J].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2008(03):313-328.
[15] 施良方.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37.
[16] 郭晓明.知识与教化:课程知识观的重建[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02):11-18+41.
[17] 郭晓明.课程知识与个体精神自由[D].南京师范大学,2003.
[18]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5-6.
[19] 伍醒,顾建民.“课程思政”理念的历史逻辑、制度诉求与行動路向[J].大学教育科学,2019(03):54-60.
[20] 聂迎娉,傅安洲.课程思政:大学通识教育改革新视角[J].大学教育科学,2018(05):38-43.
[2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78.
[22]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8.
[23] 王振.新时代以文化人重要思想的理论蕴涵[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04).
[2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网.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EB/OL].(2020-06-01) [2020-06-03].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 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
[25] 冯刚.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28.
[26] 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149.
The Value Significance and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in the View of the Meaningful World
NIE Ying-ping FU An-zhou
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contains the connotation of education to construct students meaningful world, highlights the inherent rich significance of subject knowledge, calls for returning to the spiritual growth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process of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value and meaning of knowledge, and enriches the understanding of curriculum education from the spiritual dimen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eaning world, to promo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we need to focus on three aspects; returning to the value of knowledge, returning to the situation of knowledge and returning to the subjectivity of students, so as to play a role in promoting the spiritual growth of students. It is necessary to fundamentally follow the law of cultivating people with culture, define the educational objectives, cultural contents and transforming methods, infuse the culture in the versatile and whole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and transform the curriculum learning experience into individual value pursuit and spiritual growth.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curriculum education; the meaningful world; spiritual growth; cultivating people with culture
(责任编辑 黄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