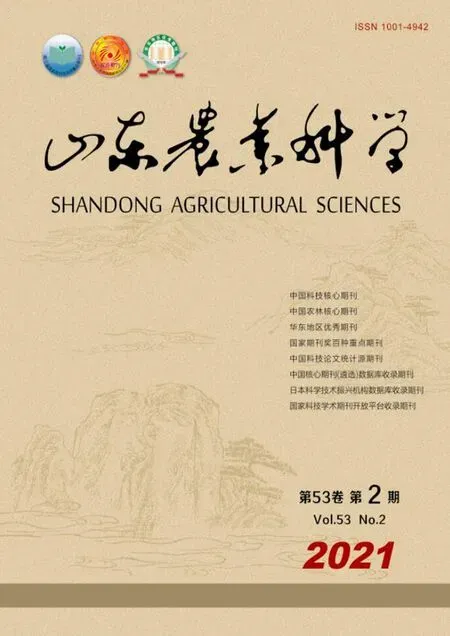基于CNKI和WOS的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知识图谱研究
2021-03-22赵光明王萍
赵光明,王萍
(曲阜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山东 日照 276826)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人类活动和生态过程变得更为复杂,多尺度生态风险的出现使得和谐人地关系遭受破坏[1]。土地利用格局、深度和强度不断变化,土地利用类型趋于多样化[2,3],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大气和水体污染、土壤沙化、物种灭绝等地域性和累积性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4]。生态学的研究已从二元生态链(生物—环境)转向三元生态环(生物—环境—人类)和多元生态网(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5],土地作为一个社会自然综合体在多元生态网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土地利用是指人类为获取一定的经济、环境或政治福利(利益),对土地进行保护、改造并凭借土地的某些属性进行生产性或非生产性活动的方式、过程及结果[6];既是人与土地耦合关系集成的动态系统,又是人类开发、利用、改造自然环境最直观的表现形式之一[7]。生态风险和生态风险评价的内涵不断延伸、转化[8,9],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研究已成为近年来生态学等领域的热点话题之一。1992 年美国国家环保局(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将生态风险评价(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ERA)定义为“评估暴露于一种或多种压力因子后,可能出现或正在出现的负生态效应的可能性过程”[10]。生态风险评价为风险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的同时,也为土地利用定量评估带来了新思路[11,12]。
目前国内外对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研究多集中于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评价部分,有两种主要模式:一是基于源-汇景观理论的传统风险,合理设计源-汇景观空间格局,促进非点源污染物质的再分配,Walker[13]、王金亮[14]、许学工[15]等做了相关研究;二是从景观生态学的视角入手,构建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景观生态风险指数,建立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型与体系,揭示景观生态风险的时空演变规律。相对前一种模式,该模式不仅重视对区域生态风险的定量评价,还侧重于分析风险时空分异特征以及特定空间格局对生态功能、过程的风险表达[16]。
国内外针对具体的研究区域已有不少关于土地利用生态风险领域的研究成果,是时机采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对土地利用与生态风险这个交叉研究领域进行定量化评析。本文基于CNKI(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和WOS(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借助CiteSpace引文分析软件,对土地利用生态风险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从文献数量年度分布、关键词频次、聚类分析等方面探究该领域的研究主题变化和前沿发展,明确研究热点、知识演变、演化路径和未来趋势,以期对土地生态领域及其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参考。
1 数据来源与方法
为客观展示国内外土地利用生态风险领域的研究前沿,数据样本分别取自于中国知网知识网络平台CNKI和美国Clarivate Analytics公司开发的科研信息检索平台WOS数据库中的核心合集(包括SCI-EXPANDED、SSCI、CCR-EXPANDED和IC)。时间跨度设为2001—2018年,并根据需要去除了重复、偏离主题的文献。
CiteSpace是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计算机与情报学终身教授陈超美博士使用Java开发的一款用于科学计量分析、挖掘潜在知识的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17],其主要依靠绘制出的科学知识图谱,并结合文献计量法通过文献数量分布、关键词频次等信息可视化来展现土地利用生态风险领域的知识演变、发展脉络和研究热点。
2 可视化分析
2.1 文献数量年度分布
在CNKI数据库中选择高级检索,检索主题为“土地利用”并“生态风险”;在WOS数据库中选择基础检索,检索主题设为“land use AND ecological risk”或“land use AND ecological risks”,分别获得有效中文文献720篇和外文文献1883篇,并进行文献数量年度分布统计(图1)。2001—2004年国内文献数量增长缓慢,学术界开始关注土地利用生态风险领域的研究;2005年文献数量增加到10篇以上;此后13年间,仅2008、2010年文献数量略有下降,整体上一直处于平稳增长状态,表明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研究持续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但重视程度不够,需要进一步开展突破性相关研究。相较之下,从2006年起,国际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研究一直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年均发文量高达134.5篇,基本上呈线性增长的态势,表明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研究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已成为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和全球变化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同时表明,国际研究仍是该领域的“领头羊”,中国不是主导研究力量,但已是主要研究力量。由于学校购买的WOS数据库中核心合集仅有2006年至今的文献,国际文献数量存在一定缺陷。
2.2 研究机构与作者
从表1看出,国内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研究机构分布相对分散,发表论文较多的机构为中国科学院大学、新疆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大部分作者的研究成果相差不大,发表论文最多的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张永福(7篇)。排名前10的研究机构中有4所师范类院校,接近一半的贡献力量来自于此,这与国内大多数师范类院校开设的相关专业、方向(土地资源管理、公共管理、地图学和地理信息系统等)和硕、博士点关系密切。

表1 国内排名前10研究机构与作者频次统计
从表2看出,相较国内,国际研究同样没有高产作者,但值得关注的是, Univ.Chinese Acad.Sci.(中国科学院大学)是发表论文最多的国际研究机构,发表172篇论文,占总发文量的45.7%,该研究机构可视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研究的核心力量。其次是发表33篇论文的US Forest Serv.(美国森林服务公司),占比8.7%,排在第3位的是发表28篇论文的Beijing Normal Univ.(北京师范大学),占比7.4%。中国科学院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的发文量之和占国际高频研究机构总发文量的一半以上;国际排名前10研究作者分布中,中国作者有7人,发表论文总计41篇,占国际高频研究作者总发文量的69.5%。由此可见,国内土地生态领域的科研成果大量外流已成为普遍现象[18],中国学者才是国际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研究真正的“主力军”。

表2 国际排名前10研究机构与作者频次统计
2.3 关键词频次
关键词是对论文的高度概括和总结,聚焦了研究者关注的核心,对论文关键词的提炼和系统归类,通常能够真实地反映某个研究领域和对象的研究价值[19]。高频关键词的引入,更是成为辨识该领域发展方向和前沿热点的重要参考依据。关键词共现分析相比文献的共被引和耦合分析,其得到的结果更加直观明了,即研究者可以直接利用共现分析的结果,对所研究领域的主题进行分析[17]。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能反映其在整个关键词共现网络中的重要程度,代表一定时期内该领域核心的研究主题[20,21]。分别选取国内外研究中前30个高频关键词,有助于反映土地利用生态风险领域的发展方向和前沿(表3)。
国内研究中关键词主要分为四类:①“生态风险评价(中心性高达0.58)”方面的关键词,频次之和共占所有关键词频次总和的25.5%,主要含有“生态风险评价”“风险评价”“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等关键词,代表了国内土地利用生态风险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前沿。②土地利用及景观格局变化方面的关键词,频次占31.5%,包括“景观格局”“土地利用变化”“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土地利用方式”“空间分析”“景观指数”“空间自相关”和“时空分异”等关键词,如田鹏[22]、许凤娇[23]和汪翡翠[24]等利用多期土地利用数据研究生态风险时空特征变化,程文仕等[25]基于生态风险的空间异质性研究土地整治优先序。③“生态安全(中心性高达0.52)”方面的关键词,频次占20.3%,围绕 “生态安全”“重金属”“土壤”“土壤重金属”“多环芳烃”和“污泥”等,多从生态毒理学的角度针对土地利用进行生态健康评价,评定人类健康的潜在危害[26]。④“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技术方面的关键词,频次占8.2%,注重各类信息技术与数学方法相结合,剖析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时空变化特征。

表3 高频关键词统计
国外研究关键词频次分析:①“climate change(气候变化)”“biodiversity(生物多样性)”“management(管理)”和“conservation(保护)”等关键词频次均超过160,共占关键词频次总和的30.3%,反映了国际土地利用生态风险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②中心性大于0.10的关键词,有 “biodiversity(生物多样性)”“landscape(景观)”“heavy metal(重金属)”“pattern(模式)”“vegetation(植被)”“extinction risk(灭绝风险)”和“adaptation(适应)”,是目前国际土地利用生态风险领域的研究核心和热点关注。③“ecosystem(生态系统)”相关研究的高频关键词较多,且频次均高于50,主要有“ecolsystem service(生态系统服务)”“vulnerability(脆弱性)”“adaptation(适应)”和“resilience(恢复力)”等,表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以及生态系统脆弱性、适应性、恢复力等研究是土地利用生态风险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④风险源—风险受体方面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包括“heavy metal(重金属)”“forest(森林)”“soil(土壤)”“ecosystem(生态系统)”和“sediment(沉积物)”等,频次均介于60~100左右。由此可见,重金属、沉积物、杀虫剂等污染物是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罪魁祸首,危害涉及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农田、水域、森林等)。⑤“China(中国)”和“United States(美国)”的频次同样很高,说明中国和美国已成为研究者选取研究对象和研究区域的热点关注,研究者多以此开展相关实验研究等实证分析。⑥“model(模型)”“system(系统)”和“pattern(模式)”,共占关键词总频次的9.1%,说明该领域多进行定量化的模型研究和模拟研究。此外,“agricultural soil(农业土壤)” “urban(城市)”“social ecosystem(社会生态系统)”和“surface soil(表层土壤)”等关键词同样频繁出现,未来的研究重心或将转向农业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系统及复合生态系统的生态风险评价、生态管理和驱动机制等方面[27,28]。
2.4 聚类分析
CiteSpace软件中的聚类分析是指在关键词共现网络的基础上,展示共现关键词之间的亲疏关系,并依据它们的亲疏关系程度进行聚类[29]。根据表3高频关键词统计和图2所示的聚类情况,国内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研究主题可划分为两大聚类集群(图2)。
集群1由“#1风险评价”“#3生态风险评价”“#4生态风险”“#8地理信息系统”和“#9风险管理”构成。国内土地利用方面的生态风险评价研究较晚,从健康风险过渡到环境风险再向生态风险转移经历了近20年的漫长演变历程[30],目前尤以土地利用变化生态风险评价研究居多。生态风险研究能够为风险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同时伴随GIS和RS等新技术手段的开发与应用,结合土地统计分析和生态风险指数等方法研究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相关文献不断出现,其主要通过构建CLUE-S模型、PSR模型等关系模型对地类转变、土地损毁和土壤侵蚀等引起的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进行评价,为区域生态风险预测及管控提供决策支持,进而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优化配置、生态系统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的整体统一。
集群2由“#0低丘缓坡”“#2红寺堡区”、“#5土地利用/覆被变化”“#6土地利用变化”和“#7城镇化”构成。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方面的问题层出不穷,人地关系矛盾日益突出[31]。因此,从县域、市域和省域等不同尺度出发,基于遥感影像数据研究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或土地利用变化生态风险的实证案例研究越来越多,其主要对景观结构、土地用途、植被覆盖率等地理空间信息进行分析处理,探索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及其时空分异和空间冲突,如李月月[32]、何莎莎[33]等分别以长汀县和扬州市为研究区进行的相关研究。而低丘缓坡作为土地综合利用的后备开发资源,广布于我国东南沿海和武夷山区,已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空间扩展的重要选择[33],未来可能会在农业农村发展、土地用途管制和国土空间规划中扮演重要角色[34]。同时,作为生态移民安置区的典型代表,红寺堡区是近5年来国内学者关注的典型研究区,生态移民对迁入区土地利用的深广度、类型、景观破碎度、异质性和多样性等的影响逐渐得到重视[35,36]。
国际研究划分为三个聚类集群(图2):
集群1-风险源,由“#1 climate change(气候变化)”“#5 phoshorus(磷)”和“#7 surface sediment(表层沉积物)”构成。气候变化是全球变化的最大诱因之一,同时也给土地利用带来了巨大的生态挑战。气候变化对土地利用的直接影响一般表现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对土地的影响,如暴雨洪水对土地的危害(以农田为例):土壤流失加剧、毒害物质堆积、土壤结构破坏等;间接影响表现为气候变化迫使农田作物的播种期、收获期和全生育期发生变化以及种植界限的变更,从而影响以土地为载体的生态系统内生物间及其与环境间“流”的传递(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37]。而氮、磷循环是从微观尺度研究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重要切入点,以磷、氮等为代表的营养元素含量超标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风险因子[38],氮磷污染不仅造成湖泊、水库等水体的水质变差、鱼虾及其他生物大量死亡,还会胁迫小区域范围内物种多样性空间格局变异和生态系统多样性“换血”。另外,针对表层沉积物中的重金属元素(铅、镉、汞、砷、铬等)和有机污染物(多环芳烃、卤代烃等)的空间分布、生态风险评价及其来源等方面的研究,是近年来江河、湖泊和海域表层沉积物研究的重点。无机污染物中重金属所占比重较大,其在生物体内累积、沉淀后的危害相当大。因此,预防重金属中毒需从源头抓起。将空气、泥土、食物和水中重金属含量控制在安全范围内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生态安全问题现已上升到国家高度,如习近平于2014年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39]。
集群2-风险受体,由“#2 home range(家域)”“#4 vegetation(植被)”“#8 transmission(传递)”和“#1 biodiversity(生物多样性)”构成。单风险受体向多风险受体和复合风险受体的转变过程与城市化发展的演化过程相契合,风险受体的选择已从个体、群落、植被、家域、保护区等小尺度扩展到森林、河流、景观、生态系统等中、大尺度,土地利用生态风险领域的研究方向也从景观生态风险研究发展到区域生态风险研究,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动态变化对自然植被分布、动物栖息地、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将更加明显,生态系统中生物和无机环境的耦合关系也会更加复杂[40]。家域中动物的生态需求、活动路线和生境选择对生态过程的影响为土地利用和森林景观的生态风险研究提供新的视角[41]。植被类型在土壤形成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改变土壤物理结构、化学成分等)。一方面,植物根系可以固土锁水、提高土壤抗侵蚀力、优化改良土壤;另一方面,森林砍伐、火灾对植被盖度、覆盖率产生不同程度的生态效应,成为定量研究森林生态系统覆被演替的重要切入点。
集群3-风险评价,由“#0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生物多样性保护)”“#3 North America(北美)”“#6 forest management(森林管理)”“#9 remediation(修复)”和“#10 England(英国)”构成。美国、澳大利亚、荷兰、德国、加拿大等国都对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评价的框架和指标体系做过相关研究,基本路线为结合内梅罗指数法、相对风险模型(RRM)、景观格局指数等风险评价方法,进行问题表述、问题分析、风险表征[42,43],美国和英国已成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相关领域重点关注的研究区所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利于全球土地生态的平衡与可持续,已发展为当今国际学术界重点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对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的保护研究已得到世界各国的积极响应。森林具有保持水土、涵养水源、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一旦遭受破坏将会波及整个地球生态系统。森林管理一直处于国际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相关领域的研究前沿,森林生态风险研究正逐渐成为森林范畴内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热点前沿。而当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出现或即将达到临界值时,就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减少风险损失。生态修复方式与技术(生物、物理与化学修复及工程技术)的快速更新与推广,使土地短时间内恢复其原有的生态价值变为可能。

图2 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
2.5 时区图
时区图是从时间维度上研究文献关键词年度分布的一种表现方式,侧重于展示某年首次出现的关键词,有助于某领域的演进路径研究,以后再次出现将在之前年度区间进行累加。如图3所示,国内外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主题演进分为三个阶段:
起步探索阶段(2006年之前),国内关注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思想来源与理论方法,从地理学、景观生态学和土地科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界定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研究范畴、方向,可称为基础层;国外主要涉及风险源-风险受体[如“community(群落)”“forest(森林)”“habitat(生境)”和“landscape(景观)”等]方面的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评价,强调自然风险源对生态系统管理、恢复及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机制研究。
稳步发展阶段(2007—2013年),国内出现了大量实证研究,涉及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依托条件(“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生态系统服务”)、技术层(“地理信息系统”“遥感”)、理论层(“模型”与“指标体系”,“风险评价”与“风险管理”);国外研究注重化学污染物对生态风险的危害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包括“water quality(水质)”“management(管理)”“heavy metal(重金属)”和“pollution(污染)”等问题,围绕土地-生态系统的研究:“resilience(恢复力)”“vulnerability(脆弱性)”“adaptation(适应)”及其对策(“conservation(保护)”、“management(管理)”、“restoration(修复)”),这与关键词频次分析的结果基本一致。
快速发展阶段(2014—2018年),国内开始关注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风险源(“多环芳烃”等)、多尺度的生态风险(“景观生态风险”等)及“评价模型”和空间分析(“空间冲突”等)等多个方面。国际研究内容不断细化,如风险源从“heavy metal(重金属)”到“trace metal(痕量金属)”。从农业、社会、自然及复合生态系统视角下探索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spatial distribution(空间分布)”及“desertification(荒漠化)”“environment change(环境变化)”和 “ecological impact(生态冲击)”等问题,“health risk(健康风险)”研究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3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系统梳理了CNKI和WOS数据库中2001—2018年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有关文献,针对生成的知识图谱及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探索出该领域的知识演变、研究热点和演进趋势。结果表明:①国内土地利用生态风险领域的研究虽已初具规模,但整体发展较为缓慢,而国际研究日臻成熟。②国内的研究热点为“生态风险评价”“景观格局”“土地利用变化”和“生态安全”等,国际的研究热点为 “climate change(气候变化)”“management(管理)”“conservation(保护)”“biodiversity(生物多样性)”和“land use change(土地利用变化)”等。③国内外研究各自形成了主题关联的研究集群,国内分为区域性研究和技术性研究两大集群,国外分为风险源、风险受体和风险评价三大集群。④国内外的研究发展具有相似的阶段性特征,皆可分为2006年之前、2007—2013年、2014—2018年三个阶段,国外研究相对发展较早、内容更为深入。
从文献数量看,近年来国际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研究已步入发展的快车道,而国内还停留在平稳增长阶段,未来期待更多学者和研究群体的投入关注。大量科技成果外流已成为普遍现象,不利于国内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研究的长期发展。从关键词频次看,国内外皆重视景观生态风险研究,主要从landscape(景观)尺度研究土地利用变化、景观格局、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过程,通过构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指数、评价模型和评价体系进行生态风险分等定级,解析多源风险的综合生态空间表征,进而提出土地可持续利用和降低生态风险的对策建议。结合关键词频次和聚类集群看,重金属与多环芳烃相关研究是国内外的共同关注点。国内更注重土地利用变化对人地关系的影响,而国际侧重于从风险源-风险受体方面对生态风险进行评价。
本研究文献数量有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研究主题的客观性,但也致使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关键词选取上按照国内、国际文献中关键词频次的前30位,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低频关键词不重要,它们成为未来的研究热点亦有可能。今后应多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耦合研究,多视角、多尺度、多层次的共同考量,研究对象和主题紧密契合国家发展战略需求,提出适宜的风险响应策略与制度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