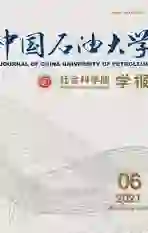《红楼梦》中的疾痛隐喻与女性形象建构
2021-03-17陈晨
陈晨
摘要:疾病在文学之中并非单纯的病理学现象,它所表征的是背后的整个社会文化体系,是阐释空间与意义生成的载体。一部《红楼梦》,也是一部女性的疾病史。探寻她们的疾病之因,必须深入到其精神心灵世界的内部,她们情感无所依托的孤寂、爱欲无从排解的苦闷造成了身心的割裂,心理上的痛感与身体的病态互相作用。疾病不仅与女性的个体性格有密切之联系,父权文化所规定的社会性格也是促成女性病痛的重要导向因子。噬心腐骨的女性病痛有深层的社会根源,在父权与皇权所控制的婚姻机制与价值观念之下,女性的生存与精神空间被严重挤压,生命惨遭蹂躏,深陷疾病的漩涡之中沉沦。女性被病痛与现实所凌虐,死亡成为自我维护与清净解脱之地,她们在自恋与自虐的复杂心境中走向死亡,也是对既定命运范式的微末反抗。
关键词:《红楼梦》;女性命运;疾病隐喻;性格倾向;社会根源;死亡叙述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21)06-0096-07
《红楼梦》①中的女性疾病被当作修辞或“以他物之名名此物”的隐喻加以使用,其中渗透着作者对疾病的想象、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以及对社会文化与组织制度的批判与思索。女性在与世界、社会、他人的碰撞之中体验着疾痛之感,这又与她们的性格、命运轨迹相纠缠。女性身体成为被压抑的基本场所,其中纵横交错地写满了性别规范、权力话语与社会规约,使她们时常陷于疾病的囚笼之中无法挣脱。“身体不是私人性的表达,而是一个政治器官,是宇宙的和社会的实在之镜像,反映着人的病相、毒害和救治过程。在身体这个位置上,人们可以审美地、社会地、政治地、生态地经验世界。”[1]沉重的女性病体,传达出了其内心的痛楚与不安,凝聚着她们生存的血泪,镌刻了父权文化与所处时代带给她们的烙印与创伤,描绘出那一时代之中女性绝望哀伤的处境与支离破碎的人生。形态各异的群体病像是当时社会文化背景之下集体女性惨痛命运的真实写照。
一、“情天欲海”与疾病隐喻
人类的情感需要与生命欲求皆在正常的人性范围之内,但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之下,情感与欲望并不允许被自由表达,女性被要求是缄默无言的。爱欲无可纾解,于是人的心理遭到撕裂,在与情感欲望的抗争之中病倒了。正如弗洛姆所言:“基于人类存在的特殊性的基本生理需求必须以某种方式得到满足,否则人就变得不正常,这就好像他的生理需求必须得到满足,否则就会生不如死。”[2]青春期少女生动鲜活的情感与生命律动受到了严格的压制,她们在个体自我与传统社会伦理规范之间痛苦挣扎,被社会文化环境与道德规范挤压、碾磨甚至无情绞杀。
作者对于林黛玉这一主要人物的刻画至少有一半是在疾病书写中完成的。黛玉之疾伴随着间歇性的发烧、咳喘、吐血,应属于逐渐加重的肺结核。在文学作品与社会文化中,肺结核含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它经常被当作“爱情病”来使用,患病之人承载了文化所附加给她的这些隐喻。爱情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如火般的热情,而肺结核的特性之一即是间歇性的发热。“结核病的发烧是身体内部燃烧的标志:结核病人是一个被热情‘消耗’的人,热情销蚀了他的身体。”[3]20黛玉常示人以孤高冷傲之态,实则对他人与外部世界有着浓烈的情感,她对贾宝玉之情尤为炽热,在第三十四回中,宝玉遣晴雯给她送来旧帕,她便悲喜愧惧,五内沸然,“浑身火热,面上作烧,走至镜台,揭起锦袱一照,只见腮上通红,自羡压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萌”。她对宝玉缠绵婉转而又热情似火的感情恰好与肺疾中的发热症状产生可置换的意义。
在父权的重压之下,女性的情感无从表露,婚姻不能自主,她们的身心遭到了双重凌迟,疾病成为表达宣泄情感的途径。“依据有关结核病的神话,大概存在着某种热情似火的情感,它引发了结核病的发作,又在结核病的发作中发泄自己。但这些激情必定是受挫的激情,这些希望必定是被毁的希望。”[3]21宝黛二人情意相通却受制于道德伦理规范,无法言说内心的情愫,肺结核强烈而明显的病症表现极好地传达了病患者的情绪起伏与情感波动。在第五十七回中,宝玉因紫鹃的试探之言急痛迷心犯了痴病,黛玉听知后,“哇的一声,将腹中之药一概呛出,抖肠搜肺,炽胃扇肝的痛声大嗽了几阵。一时,面红发乱,目肿筋浮,喘的抬不起头来”。寶玉的言行状态总能引发黛玉强烈的病体反应,这是黛玉表达炽热情感的途径与方式。龄官对贾蔷亦有着憨痴而执拗的情意,她在花叶繁茂的蔷薇架下,触景生情画下一千个“蔷”字,细雨湿衣而恍然不知。身份低卑的戏子与贾府的公子相恋,其中的阻碍比宝黛更甚,这同样注定是爱而不得。精神上的忧郁痛苦,心理上的煎熬折磨,让龄官患上咳血之症。当个体私人化的情感表达与传统的社会规范、道德准则、价值观念产生冲突,她们只能以病态之躯表达、宣泄并与之抗衡,但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战争之中,她们不可避免地被推向毁灭的绝境。
在人类的爱恋之中必然夹杂着欲望的成分,甚至欲望可以脱离爱独立存在,但在中国古代的道德语境之下,欲望二字是不能被提及的禁忌。然而,爱与欲本就是健全人性的一部分,即使受到外界的强力压制,也并不能被彻底消除。较之其他女性,林红玉对情爱的态度更为大胆,当她在对贾芸有意之时,故遗手帕,牵惹情思。但在礼教森严的大观园中,她仍然要小心躲避、压抑感情,心中惴惴不安、神魂不定、烦闷异常而终成一病。在第二十六回中小丫头佳蕙问及红玉的病因,她却答:“你那里知道我心里的事。”红玉之病源于对于贾芸的缠绵情思不得发露。欲望在无意识的海洋之中往来奔腾,犹如巨石下的岩浆随时要奔涌而出。来自生理的原始本能与外部道德规范的重压,女性心灵与身体成为两种力量争夺对抗的战场,她们的心理无可避免地遭受千疮百孔的伤害,从而外发为身体上的疾病。
《红楼梦》对于疾病的描写是虚实相间的,某些疾病表现出明显的病症,而有些疾病却更侧重于内在的象征意味。薛宝钗为先天之症,“我这是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幸而先天壮,还不相干,若吃寻常药,是不中用的。”
(第七回)但在前八十回中,她一直身体清泰,病情从未发作。此处作者借由宝钗之病引出了疗疾之药冷香丸,这二者非全然实写,而是隐含着深刻的哲理意蕴。何为热毒?脂评曰:“凡心偶炽,是以孽火齐攻。”[4]187情感太过炽热也是一种疾病,而冷香丸的功效是为遏制宝钗之情。宝钗并非纯然的冷美人,她原本也属于“风流冤孽”之一,要为情为欲所困所扰,但因冷香丸的缘故,宝钗有着寻常女子所难及的冷静克制,故二知道人批道:“宝钗外静而明,平素服冷香丸,觉其人亦冷而香耳。”[5]
但冷香丸却也只有遏制之效,并不能完全消除宝钗的情感欲望,所以她也有少女扑蝶的活泼情态,有对金玉良缘的期待以及对功名事业的热忱。在这孽海情天地与功名利禄场中,她也难以做到全然不动心意,故太平闲人道:“于极热场中,但着一‘冷’字,便是一服清凉散,奈何宝钗服而不服也?”[6]她终是要经历一番人世的磨练才会有最终的了悟,但冷香丸的警醒之意却不能忽视:“既治体病,更治心病。同样也是对宝钗的警示与点化。”[7]宝钗之病寄寓了作者的宗教关怀,冷香丸不仅点化宝钗,更为渡脱大观园中所有女性乃至人世芸芸众生。冷香丸药方乃癞头僧所赠,其中所隐藏的宗教象征意旨并非游谈无根。《中本起经》:“凡人为恶,不能自觉。愚痴快意,后受热毒。”[8]人生于世,利害相争,沉迷于物欲与情欲之中,终日忧思辗转难安,内心昏沉郁热,人之心灵精神饱受心火焚烧熬煎,不得清宁解脱,此之谓热毒缠身,众生皆在病痛之中。
二、性格倾向与女性疾痛
性格的倾向性是个体思维与行为之根源,《红楼梦》中女性的疾病与其性格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荣格认为,性格“意味着一种基本的倾向,它制约着整个心理过程,建立起习惯性的反应,因此不仅决定着行为方式,还决定着主观经验的性质”[9]。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也指出:“性格结构即决定了一个人的思想和观念,又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10]78言行定于性情,性情影响事态,性格本身即可以是一种致病因素,它通过影响人的情绪与行为走向而引致疾病的产生。如,内抑型人格常压制自己的负面情绪,消极的情绪无法得到排解,更易在忧郁悲伤中患病;外倾型人格争强好胜,不满足于既有的成就,易因过于劳累对身体造成重负而患病。《红楼梦》的女性病体之中明显带有性格所印刻的痕迹,这不仅包含着个人性格的心理动力导向与脆弱成分,还体现为社会性格结构对女性的驯服。
尤二姐屬于典型的内抑型性格,她因无见识决断,贸然搬入贾府,使自己置身于危险之地;后又因性格软弱,面对凤姐的欺辱、秋桐的挑衅,一味忍气吞声。但一再的忍让却只能换来更大的委屈,心中的气愤抑郁不能发出,气血不能调和,必定外发为病。“那尤二姐原是‘花为肠肚,雪作肌肤’的人,如何经得这般折磨?不过受了一月的暗气,便恹恹得了一病,四肢懒动,茶饭不进,渐次黄瘦下去。”作者对尤二姐这一人物的塑造是与尤三姐对比进行的,尤三姐的性格与尤二姐截然不同。在第六十九回中,尤三姐捧着鸳鸯宝剑入梦,指出了尤二姐的性格弱点,“你一生为人心痴意软,终吃了这亏”,并为二姐提出建议,“将此剑斩了那妒妇”。若是处在同等境遇之中,以尤三姐之性格,绝不会让王熙凤如此凌辱,势必与之拼个鱼死网破。尤三姐被柳湘莲误会,并非患病而终,却是自刎而亡,这也正符合三姐的性格特征。但她们的生存空间本就十分狭小,可选择的反抗手段也极为有限,尤三姐有强烈的反抗意识与玉石俱焚的胆气与魄力,尚能以身殉志,尤二姐面对欺辱却无反击之力也无反击之心,只能任由他人摆布,终于走向毁灭之路。
尤二姐的性格前后出现了明显的逻辑断层。前尤二姐背弃婚约、风流淫乱,并非良善之辈;后成为贾琏的妾室,凡事退让、贤良淑德。这与其说是人物自身性格的转变,不如说这是男性权力系统希望她们所拥有的性格特征:温和柔弱、卑顺缄默。弗洛姆认为人之性格,除个体性格之外,还有社会性格,“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个性范围……社会性格指的是同属于一个文化时期绝大多数人所共同具有的性格结构核心”[10]82。尤二姐的后期性格是父权社会所精心培育的,是在当时社会文化背景之下,男性意欲加诸到女性身上的性格。她们毫无怨言地接受自己的境遇命运,甚至认为罪有应得;女性的感觉经验被刻意忽视,她们的存在只为服务于男性的需求。女性的自我独立意识被有意无意地过滤了,这种性格固然符合男性的性别统治,但女性的身体心理创伤就只能由个人承担,疾病之发是女性个体性格与社会性格相冲突的结果,也是压制内心情绪以迎合社会性格的外发表现。曹雪芹虽然比同时代的作者站得更为高远,但文本之中男性的权力渗透却是清晰可见的,“但凡男人写女人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11],这可解释尤二姐的前后性格何以出现断裂,也可解释为何女性只能在疾病之中自戕自戮,一路跌向死亡的深渊。
男性通过改造女性的个人性格、培养社会性格,以更好地维护现有的性别结构,从而加强操控统治,如果她们在很大程度上违背社会性格就会遭到贬斥。晴雯病情的加剧与其被赶出大观园有直接的联系。权力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哪怕如大观园般的清净女儿之地也成为权力运行的机制构成。被男性权力收编的每一位家族成员都成为监视控制者,违背社会性格之人自然容易被挑出、疏离乃至抛弃。晴雯个性张扬、言语尖刻、行为放肆,与父权文化背景下所要求的女性社会性格极度不符。“虽说‘贤妻美妾’,然也要性情和顺,举止沉重的更好些。”(第七十八回)与晴雯相比,袭人不断将自我驯化为与男性管理者所控制的社会更为相符的性格,受到王夫人的青睐以及权力系统的嘉奖。晴雯的被训斥、被污名、被抛弃乃至病重而亡的过程凸显了性别权力管理者的威慑手段,以此告诫其他女性其应该遵循的规范与应该养成的性格。
个体性格是王熙凤这一人物形象的重要构成因素,也是其疾病的深层诱发因子。王熙凤机智聪慧、杀伐果断甚至狠毒无情,这些特质很难与女性病态的身体相联系,但在前八十回中正面侧面描写熙凤之病,足有十余次之多。在第十四回中,王熙凤料理秦氏之丧,几乎一夜未眠,脂批曰:“此为病源伏线,后文方不突然。”[4]241王熙凤生性要强,家中事务皆要包揽在身,她虽然可以在这一过程中施展自己的执政理家能力,但也暗示了劳累过度已然埋下病源。在第五十五回中,熙凤小产成为其病情显露与加剧的重要节点,而小产之因似也与其过度操劳有关,“刚将年事忙过,凤姐便小月了”,依其素爱揽事的性格,“年”这一重要节日前后的事务,她自然不可能缺席。小产虽对女性身体有严重的损害,如果静心修养本可逐渐恢复,但她却从未停止筹谋计划,一月之后身体尚未恢复,就重新理事。“谁知凤姐禀赋气血不足,兼年幼不知保养,平生争强斗智,心力更亏,故虽系小月,竟着实亏虚下来。”身体上的劳累与心理上的算计不断耗损凤姐的心力以致积劳成疾。
个体的行为模式一般由性格所决定,王熙凤属于争强好胜的外倾型人格,她希望在人际关系与事务处理中居于主导地位,享受处理解决事务带给她的成就感以及他人的称赞与尊重。表面看来,熙凤独揽家政大权,风光无限,实际她亦处于族权与夫权的压迫之下,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极力争取支配权,只有如此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她内心的抱负与向外部世界拓张的欲望。但她用尽手腕、耗尽心力也未获得其所期待的尊重,邢夫人说她“自家的事不管,倒替人家去瞎张罗”(第六十五回),丈夫贾琏对她也不满已久甚至不乏恨意。在七十一回中,邢夫人当众奚落凤姐,勾起其旧症,竟成血崩之势,之后她的身体每况愈下,以至于中秋赏月之时也只得卧病在床,自此病势已经无可挽回。于前八十回作者埋下的伏笔来看,王熙凤极有可能因病而亡。从第五十八回的小产到第七十二回的旧疾爆发,如若她万事不管,调养身心,或许最终的死亡与疾病无关。但她的性格决定了她需要在支配与征服的过程中获得满足,甚至不惜以损伤身体为代价,而环境的挤压又导致了其病情的加剧。
三、病體铭刻:社会制度的牺牲者
在女性的疾痛之中,她们真实的命运得到了展现,父权文化中的社会组织制度是其遭受痛楚熬煎的深层根源。中国古代社会是壁垒森严的等级制度,家国同构的特征使得等级制度在家庭之内强烈地发挥作用。在性别等级之中,男性居于统治地位;在社会等级之中,皇帝位于政治权力系统的最顶端;在家庭等级之中,男性家族长享有对女性的绝对支配权。女性在皇权、父权与夫权的多重压迫之下暗无天日,她们的天空如此之低,空气如此稀薄。婚姻中的一夫多妻制度使得妻妾的身心与物质利益皆不能得到满足,从而造成家庭内部女性之间的互相倾轧。她们不会结盟共同对抗让其陷入黑暗永夜的男性权力,反而成为男性之刀彼此残害。女性被限制在闺阁内院之中,满足男性的欲望并为之生育子嗣,皇权、父权与夫权的合谋销毁了女性具有外在开拓性的本质,让她们的精神在压迫与凌辱之中委顿,她们的身体在病痛之中消陨。“父权制文化秩序中身体作为女性的象征,被损害被摆布,然而却未被承认。”[12]
不合理的妻妾制度是女性患疾的重要原因,她们或在病痛之中抑郁而终或不堪凌辱自戕而亡。香菱温柔娇憨,惹人怜爱,虽然身世飘零,却始终天真明媚。当她得知薛蟠将要迎娶夏金桂时还兀自雀跃欣喜,但当她置身于妻妾制度的罗网之中,终于不堪金桂、宝蟾、薛蟠的多重欺凌折磨,“对月伤悲,挑灯自叹”,病情加重,“今复加以气怒伤感,内外折挫不堪,竟酿成干血之症,日渐羸瘦作烧,饮食懒进,请医诊视服药亦不效验”(第八十回)。由此可见,香菱之病此时已经到了药石罔效的地步。在后四十回中,续作者为香菱安排的结局是难产而亡,这并不符合作者原意,与第八十回文中所提及的香菱之疾是相抵牾的,“因血分中有病,是以并无胎孕”。而香菱的判词也预示着她的结局:“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第五回)
爱情具有独占性的特征,但在妻妾制度之下,正妻并无权力阻拦丈夫纳妾,女性无力与男性权力相抗衡,却将报复的矛头指向同类,“这种怨恨没有施发到造成这种不平等现象的男性身上,却施发到同是受害者的女性身上”[13]。尤二姐也是在残酷的妻妾斗争中身患重病,在她搬入贾府之后,王熙凤为将之铲除无所不用其极,在贾母处搬弄是非,利用秋桐的嫉妒借刀杀人,对其施加物质精神的双重虐待。
当然妻妾之间斗争的触发因素不仅是源于情感上的嫉妒,更是为了守住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与利益所得。王熙凤对贾琏的情感尚在其次,但尤二姐的出现却极有可能威胁她的地位与利益。在中国宗法制度下,子嗣对家族的影响至关重要,这涉及家族财产的继承问题,产嗣的行为使得女性的生存多了一重保障,也使之成为既得利益者。王熙凤在贾府之中虽拥有一定权力,但尤二姐温柔貌美,颇得贾琏之心,又极有可能为贾琏诞下子嗣,这于她而言是极大的威胁,所以必要除之而后快。一方面,妻子虽居于正位,但若失去丈夫的宠爱与庇护,其地位岌岌可危;另一方面,妾室在正妻的压制之下,反抗的余地非常微弱。双美与共大多只存在于男性作者的文学想象中,在现实社会中,此类情况属于极少数,这需要两者同时拥有高超的品格与淡泊名利之心。妻妾之间的斗争是一场零和博弈,双方几乎不存在合作的可能,“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第八十二回),妻妾之间的和睦共处不过是男性一厢情愿的想象。
由于文中对贾元春着墨不多,加之她的判词极为模糊,可做多种释义,所以关于元春之死,红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后四十回续作者为元春安排的结局是重病而薨,这也符合这一人物命运的因果逻辑。贾元春自幼入宫,因才华品行“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 (第十六回),身份地位尊贵至极,哪怕家族中的长辈也要向她行跪拜之礼,此时她已有了皇权的笼罩加持,在男尊女卑的父权社会中,只有极少女性可以获此殊荣,贾府也因此在朝廷之中有了倚靠与庇护。但元春内心却一直有着不可轻易与人言的忧闷与悲苦,惆怅与寂寥。元春省亲之时,她哽咽垂泪,对贾母王夫人等称皇宫为“不得见人的去处”(第十八回),这一语之内含藏了多少怨与悲,“元春的贵妃身份使她在骨肉至亲面前也只能如此‘怨而不怒,哀而不伤’”[14],极为克制的表达已然如此,想见元春心中的忧苦更甚。
元春之殇既有家族长为家族利益发展牺牲子女幸福的怨,又有被锁于寂寥深宫的悲,还有处于斗争漩涡之中的疲惫。对于权力上层的人而言,“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15]。贾府曾享“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第十三回),但元春个人却无可避免地成为家族利益的牺牲品。所以她对其父贾政说:“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第十八回)身为家族之长的贾政并未有任何情感的回应,他需要她扮演好元妃的角色以支撑贾府的富贵风流。皇宫之内是比寻常女子闺阁更寥寂的所在,表面的光艳繁华,终究难敌高墙之内行动不得自由的无奈。元春不但要承受难以排解的落寞,失去自由的绝望,还要日夜思索如何固守皇帝的宠爱,如何在宫内斗争之中立于不败之地,正所谓“得宠忧移失宠愁”。元春并非忽得暴病,而是早有预兆,“每日起居劳乏,时发痰疾” (第九十五回),这是她在宫内的生活与身体状态,省亲之时的哽咽而诉是她悲郁情感的流露,她在多重忧思悲怨中耗损身心,饮恨而终。引发元春之疾的忧思悲怨背后是男权与皇权对女性生存空间的挤压,她们没有自由选择婚姻的自由,个人的情感不被珍视,鲜活美好的生命终于为社会制度所吞噬。
四、死亡叙述中的女性病体
疾病之中的女性常伴随着自我意识的萌发与对死亡的思考。“死亡才是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16]当疾病体验与死亡感知相连接,女性的个体意义也得到了彰显,“死亡感知是构成独特性的因素;正是在对死亡的感知中,个人逃脱了单调而平均化的生命,实现了自我发现;在死亡缓慢的和半隐半显的逼近过程中,沉闷的共性生命最终变成了某种个体性生命”[17]。她们在疾痛与死亡之中自我发现、自我维护,也通过这一方式抵御社会权力系统对自身意志与生命的侵袭。
在病痛的凌迟与现实的蹂躏之下,衰残之躯已经成为自我灵魂的樊笼,她们对于死亡有种异乎寻常的执著。黛玉时常以死为念,“左右打算,不如早些死了……自今以后把身子一天一天的糟蹋起来,一年半载,少不得身登清净”(第八十九回)。黛玉带着内心的哀痛与创伤倔强而孤傲地离开人世。死亡于她而言是对既定生命范式的否定,她不愿接受家族与社会对她个人命运的安排,可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女性反抗的空间如此狭小,死亡仿佛是她们唯一可以选择的自我拯救与反抗方式。在第二十六回中,红玉被佳蕙问及病情时也表露出这种观念:“怕什么。还不如早些死了倒干净。”死亡作为反抗的话语出现,这或许是她们生命中言说“不”的最后一次表达,但是她们依然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以自我的身体殉葬。
死亡是女性所建构出的清净王国,那里没有尘世的污垢与满目的疮痍,故黛玉、红玉等皆认为死亡反而“身登清净”,她们是要在生命的余烬之上重建新的希望。她们未必没有面对死亡的忧愁疑惧,否则黛玉葬花之时也不会发出“未卜侬身何日丧”的感慨,但现实的风刀霜剑与秽垢不堪已经让她们失望至极,于是将身心寄托于彼岸并将之视为安顿之所,不必在现世的沟渠中挣扎。对于在病痛与现实社会之中饱受折磨的女性而言,死亡并非幽暗狰狞之地,而是清静解脱之所。
从病痛走向死亡,其间甚至伴随着女性的自我虐待与自我戕害,颦卿绝粒是对现实不满的宣泄,是绝望中的迁怒,近乎疯狂的举动恰恰表达出她内心的无望与彷徨。黛玉所代表的是因情感遭受重挫,心灵陷入抑郁与苦闷之中的女性,她们希望通过追寻死亡的方式摆脱现世的折磨。对身体的处置也是她们所能享有的唯一话语权力,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她们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时刻承受着身心灵肉不能统一的痛苦,只能通过自我毁伤获得一点所谓的主动权,这是一种绝望的反抗。
晴雯因容貌风流出挑而被王夫人等视为媚惑宝玉的狐狸精,因不堪其辱恹恹而病被驱逐出府,临终之前,她怀着满腔的委屈、不甘、愤懑与桀骜将自己的指甲齐根铰下。《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18]在中国儒家文化语境下,人对自己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极为珍视,决不会轻易损伤,只有在处于极度悲伤或表达某种决心之时才会主动为之。自我毁伤的行为成为女性话语表达的途径,“我太不服”,这不甘而愤恨的呐喊指向的是整个社会男性权力系统,暗示着女性在自我意识觉醒过程中与男性社会相斗争所付出的努力,她们的死亡也因此被赋予一种崇高而悲怆的意义。
当女性个体的精神情感被撕碎蹂躏,身体自然不可能完好无损,甚至疾病也无法成为她们的退路与逃避空间,生命中充满了惨切的伤痛与绝望,死亡就成为唯一的选择。尤二姐在妻妾斗争之中不堪凌辱而病体缠绵,但终是丧失了生的希望吞金自尽;纯真娇痴如香菱也被欺凌折挫而患重疾,日渐羸瘦郁郁而终。在不合理的妻妾制度中,家失去了庇护的意义,反而成为争夺宠爱与利益的战场。她们的生命被疾病一步步蚕食,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在她们上空;但相较之在命运与社会编织的罗网之中被慢慢绞杀,死亡反而是一种解脱。“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19]自我毁灭的决心中流露出对现实人生的绝望,与其在尘世之中忍受身心崩离之苦,不如死而后快。
由疾病到死亡的书写,真实再现了女性的生命之痛,她们在社会的挤压蹂躏之下身心遭受重创,只能以死亡表达对现实人生境况的反抗,这是女性疾病经验中的自我升华。女性以死亡作为自我维护与解脱之径,甚至反叛之工具,似乎颇具讽刺意味,但这确乎是她们唯一能做的选择。女性生命中的绮丽欢乐只是昙花一现的幻象,仿佛只有惨切的悲哀才是一直存在的。她们自我怜惜而又自虐自戕,看似矛盾的行为却是复杂情感心理的表达。
五、结语
疾病是时代与社会所施加在女性身上的魔咒,《红楼梦》中的疾病书写也大多与女性有关,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的隐喻,是父权社会将女性凌折得千疮百痍,而男性的身体与精神却完好无损。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在男权社会之中,女性从未作为健康而完整的人活着,她们始终是病态的、刻满伤痕的。“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的控制。那些权力强加给它各种压力、限制或义务。”[20]但有一类女性却身心安泰,或是已被男性权力收编,成为男性权力统治与运作的组成部分,自然也為权力系统所庇护,如贾母、王夫人等;或是已经丧失自我意识并认同了既定命运的女性,如袭人等。
女性病体不仅是个体化的生理状态,还是社会文化的映射,它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女性的疾病成为被描写与被言说的对象,承载了各种指涉与隐喻。女性在疾病中的个体生命体验与身体状态,并未在寥寥数语中被带过。她们所承受的疾病,或激烈而极端,或逐渐噬人心骨,或浪漫哀愁,或怪异污秽,身份地位各异的女性却不约而同地遭受着疾病的痛楚。女性身体的疾病与死亡形态,表现出父权文化对女性的压抑与凌虐,她们的集体病痛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作者将女性病体与个人内在情感冲突、个体性格与社会性格、社会文化制度的联系加以考察呈现。精神的凌虐损伤着身体,病痛的身体又腐蚀着精神,病精神与病身体相互作用,共同将女性拉向绝望的深渊。
《红楼梦》的作者身为男性,处于男性权力系统之内,却对女性的内心世界与命运处境有着深切的关注,并以其特有的同情与悲悯展现了那一时代女性的集体苦难,揭露了男性权力与社会制度禁锢戕害女性的事实,体现了作者的文化焦虑与终极人文关怀,这也是其深刻性与先进性所在。
注釋:
① 本文涉及《红楼梦》原文引用,皆出自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 下文若无特殊情况,引用自该书的原文 ,不再注明出处。
参考文献:
[1] E M 温德尔.女性主义神学景观[M].刁文俊,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476.
[2] 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蒋重跃,等译.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30.
[3]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4] 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
[5] 一粟.红楼梦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92.
[6] 冯其庸.八家评批红楼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170.
[7] 梅新林.《红楼梦》哲学精神[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121.
[8] 昙果,康孟详.中本起经[M]//高楠顺次郎,等.大正藏:第四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5.
[9] 荣格.荣格性格哲学[M].李德荣,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70.
[10] 埃里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M].张燕,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11] 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3.
[12] 玛丽·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M].胡敏,译.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359.
[13] 姜跃滨.中国妻妾[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223.
[14] 张锦池.红楼十二论[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282.
[15]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91-92.
[16]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315.
[17] 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M].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93.
[18] 汪受宽.孝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
[19] 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21.
[20]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2:155.
责任编辑:曹春华
Abstract: Disease is not a simple pathological phenomenon in literature. It represents the whole social and cultural system behind it and is the carrier of interpreting space and meaning generati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is also a medical history of women. To find out the causes of their illness, we must go deep into the inner world of their spiritual world. The loneliness that their emotions are anchorless and the depression that their passions cannot reconciled have resulted in the separation of their body and mind. The psychological pain and the sickness of their bod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Disease is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to womens individual personality, but also to the social personality stipulated by the patriarchal culture. There are deep social roots for womens pain. Under the marriage mechanism and value concept controlled by patriarchy and imperial power, womens living and spiritual space are severely squeezed, their lives are tragically ravaged, and they are sinking into the whirlpool of disease. Women are abused by illness and reality, and death becomes a place for self-preservation and purity. They go to death in the complex mood of narcissism and self-abuse, which is also a minimal resistance to the established fate paradigm.
Key word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female destiny; metaphor of disease; personality tendency; social roots; death narration
3693500589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