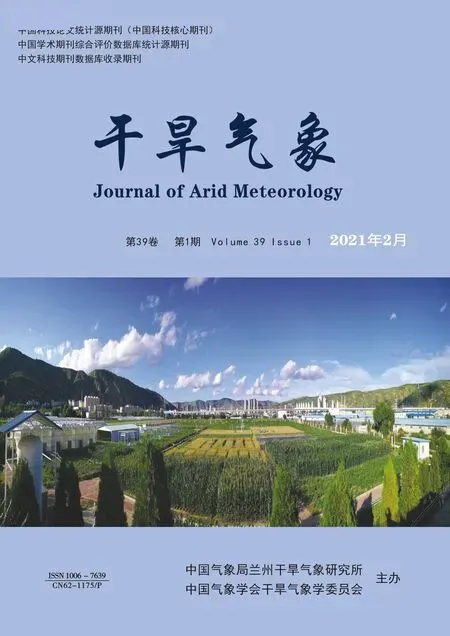1961—2018年青海高原极端气温指数时空变化特征
2021-03-16冯晓莉多杰卓么李万志申红艳陈冀青
冯晓莉,多杰卓么,李万志,申红艳,陈冀青
(1.青海省气候中心,青海 西宁 810001;2.青海省黄南州气象局,青海 同仁 811300)
引 言
近百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气候变率增大,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趋于增多,给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1-4]。因此,开展极端气温事件变化规律的研究,对于更好地应对极端气候和防灾减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青海高原是世界大气水分循环的重要生态调节区和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占青藏高原面积的三分之一,其气候变化会对该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造成影响。近年来,高原气候整体呈变暖趋势,气温及地表温度升高导致冰川融化、冻土消融、生物多样性发生变化[5-8]。青海高原平均海拔3000 m以上,自然气候条件恶劣,发展农牧业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较多,比如作物发育期提前加大了春季霜冻的危害,局地高温干旱对农牧业带来较大损失,低温事件减少导致病虫害增加等[9-11]。可见,极端气温的变化会增加农牧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对该地区农牧业环境的影响尤为显著,因此,研究该区域极端气温变化有利于提高气象预报对农牧业的服务水平和力度,对及时调整农牧业种植结构和生产布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很多研究从全国以及不同区域尺度分析极端气温事件的变化特征,发现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中国大陆极端暖事件增加、极端冷事件减少[4,12-16],其中北部地区尤为明显[12-15]。极端气温变化对气候变暖有很好的响应,气候变暖突变发生前后某些极端气温指数如暖昼(夜)日数、冷昼(夜)日数、冰冻日数、霜冻日数发生频率表现出明显差异[17-18],而且青藏高原、云贵高原、阿尔卑斯山、喜马拉雅山脉等高海拔地区气温变化幅度的区域差异性可能与海拔和纬度有关[19-30],因此,选择合适的极端气温指数对高原极端气温事件的时间变化规律进行系统分析,并从纬度及海拔的角度探讨高原极端气温变化的空间差异性及敏感性,对高原气候变化归因有一定参考价值。
鉴于此,本文利用青海高原49个气象站点1961—2018年逐日最高和最低气温资料,选取8个极端气温指数,采用累积距平、线性倾向估计、M-K突变检验、周期分析、相关分析以及集合经验模态分解等方法,对青海高原极端气温指数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探讨极端气温变化的空间差异性及敏感区,以期为高原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青海高原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31°N—39°N、89°E—103°E),海拔1658~6824 m(图1)。按照气候变化特点,将青海高原分为4个生态功能区:柴达木盆地位于高原西北部,站点平均海拔2946.3 m,属于戈壁荒漠地带,植被覆盖度小;环青海湖地区站点平均海拔3121.2 m,降水较多,属于农牧交错带;东部农业区站点平均海拔2304.9 m,温湿适宜,农业资源丰富;青南牧区为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站点平均海拔3926.4 m,降水多、温度低[31-32]。

图1 青海高原地形及气象站点的空间分布Fig.1 The topography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over Qinghai plateau
1.2 资 料
选取1961—2018年青海省50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点的日最高、最低气温资料,对其进行极值检验和时间一致性检验以确保各站点资料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经过整理,最终确定49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点的逐日最高、最低气温资料用于计算极端气温指数。
1.3 方 法
采用世界气象组织及世界气候研究计划气候变化检测与指数联合专家组(ETCCDI)推荐的8个极端气温指数[33],根据其不同内涵,将这些指数分为相对指数(TX90P暖昼日数、TN90P暖夜日数、TX10P冷昼日数、TN10P冷夜日数)、持续指数(WSDI暖持续日数、CSDI冷持续日数)、极值指数(TXN最高温极低值、TNX最低温极高值),通过分析这些指数反映极端气温不同方面的变化(表1)。

表1 极端气温指数的定义Tab.1 Definitions of the extreme temperature indices
采用线性倾向估计方法研究极端气温指数在时间变化中升降的定量程度,并对其进行显著性检验[34-35];利用累积距平和Mann-Kendall检验方法进行突变分析[36];对极端气温指数序列进行集合经验模态分解(ensembl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EEMD)得到不同时间尺度分量,计算各分量的能量谱密度及方差贡献率,反映不同时间尺度分量的平均周期及其对原序列的影响程度[37];用ArcGIS绘制不同极端气温指数倾向率的空间分布,计算各极端气温指数倾向率与站点所在纬度和海拔的相关系数,探讨极端气温变化的空间差异性。
2 结果分析
2.1 极端气温指数的变化趋势
图2为1961—2018年青海高原不同极端气温指数距平年际变化。可以看出,1961年以来,青海高原极端气温相对指数的变化十分显著(P<0.001),暖昼和暖夜日数分别以11.8、16.6 d·(10 a)-1的趋势上升,冷昼和冷夜日数分别以-10.1、-19.3 d·(10 a)-1的趋势下降;暖持续日数和冷持续日数分别呈显著增加和显著减少趋势(P<0.001),气候倾向率分别为1.4、-1.6 d·(10 a)-1;极值指数均以0.4 ℃·(10 a)-1的趋势显著上升(P<0.001)。通过比较可以看出,青海高原极端气温指数倾向率具有昼夜不对称性,夜指数(暖夜、冷夜日数)变化速率大于昼指数(暖昼、冷昼日数),即最低气温的升温速率大于最高气温。近几十年来,昼夜增温速率的不对称性可能与云层覆盖有关,云量的增加减弱了夜间辐射降温的效果[38];GAO等[39]利用数值试验分析表明温室效应会引起日最高和最低气温升高,从而使暖事件增多、冷事件减少。从不同极端气温指数的累积距平曲线来看,极端气温暖指数(暖昼日数、暖夜日数、暖持续日数、最高温极低值、最低温极高值)均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特点,极端气温冷指数(冷昼日数、冷夜日数、冷持续日数)则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除冷持续日数外,其余指数的累积距平曲线在1990年代中期达到最大值或最小值,冷持续日数在1980年代中期达到最高值,之后持续偏高,至2000年后呈缓慢下降趋势。

图2 1961—2018年青海高原不同极端气温指数距平年际变化Fig.2 The annual variation of different extreme temperature indices anomaly over Qinghai plateau during 1961-2018
2.2 极端气温指数的突变特征及周期分析
采用M-K非参数检验法对各极端气温指数序列进行突变点检验(图3),可以看出,暖昼日数、冷昼日数、最高温极低值、最低温极高值、暖持续日数在1996年前后发生突变,其中暖昼日数、最高温极低值、暖持续日数的突变点出现年份略早于冷昼日数和最低温极高值;突变发生前,各指数的UF曲线在0.05信度线之间呈波动式变化,处于不稳定状态,至1990年代中后期,UF曲线超过0.05信度线,表明冷昼日数突变后显著减少,暖昼日数、暖持续日数、最高温极低值、最低温极高值突变后显著增加。

图3 1961—2018年青海高原部分极端气温指数序列的M-K检验Fig.3 The M-K test of some extreme temperature indices series over Qinghai plateau during 1961-2018
由于气候系统具有非线性、非平稳性以及层次性,许多大小不一的时间尺度构成了多层次结构,在极端气温指数的长期上升和下降趋势中包含了多种变化周期。对极端气温指数序列进行EEMD分解时,将扰动白噪声与原始信号的信噪比定为0.01,集合样本数取1000次,最终得到4个固有模态函数(IMF1、IMF2、IMF3、IMF4)以及长期趋势分量RES,计算各分量的平均周期及方差贡献率(表2),可以看出,各极端气温指数序列在年际尺度上表现出准3 a和5~6 a的周期振荡;在年代际尺度上,各极端气温指数表现出10~15 a、24~31 a以及更长时间尺度的周期振荡。这与申红艳等[18]研究指出青海高原极端气温变化存在3~8 a的年际周期,以及13、17、27 a的年代际周期特征基本吻合。对各分量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大部分极端气温指数序列以准3 a周期变化最显著。不同时间尺度分量对各极端气温指数序列的方差贡献率表明,以准3 a周期为代表的年际振荡(IMF1)以及长期趋势项(RES)两者累计方差贡献率在63.5%~93.6%之间,其中暖持续日数和最高温极低值的准3 a周期振荡对原序列的影响程度最大,贡献率在50%以上。

表2 1961—2018年青海高原极端气温指数序列经EEMD分解的各分量平均周期及方差贡献率Tab.2 The average periods and contribution rates of each component of EEMD analysis of extreme temperature indices over Qinghai plateau during 1961-2018
2.3 极端气温指数倾向率空间分布
图4为1961—2018年青海高原极端气温指数气候倾向率的空间分布。可以看出,1961年来,整个高原地区所有气象站点的暖昼(夜)日数呈显著增加趋势(P<0.05),冷昼(夜)日数呈显著减少趋势(P<0.05),东部农业区暖昼日数气候倾向率较大,暖夜日数增加最快的站点主要分布在东部农业区和柴达木盆地,冷昼(夜)日数减少幅度最大的站点主要分布在柴达木盆地;大部分区域(占总站数的98%)暖持续日数呈显著增加趋势(P<0.1),倾向率在0.7~2.6 d·(10 a)-1之间,增加幅度最大的站点主要分布在青南牧区;各地冷持续日数呈减少趋势,显著减少的站点达84%(P<0.1),倾向率在-6.7~-0.5 d·(10 a)-1之间,减少幅度最大的站点分布在柴达木盆地;青海高原气温极值指数均呈上升趋势,以最高温极低值和最低温极高值为序,呈上升趋势的站点分别达96%、100%,其中通过显著性检验的站点分别达71%、98%,最高温极低值和最低温极高值上升幅度最大的站点主要分布在柴达木盆地和东部农业区。

图4 1961—2018年青海高原极端气温指数倾向率的空间分布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climatic tendency trends of extreme temperature indices over Qinghai plateau during 1961-2018
总体上,极端气温冷指数(冷昼日数、冷夜日数、冷持续日数)在柴达木盆地减少最明显,大部分极端气温暖指数(暖昼日数、暖夜日数、最高温极低值、最低温极高值)在柴达木盆地和东部农业区增加最显著,暖持续日数在青南牧区增加最快(表3)。研究指出自然或人为改变地面状况会造成气温的变化[40-42],因此,极端气温变化的地区差异性很可能与地表植被覆盖和人类活动有一定联系,柴达木盆地主要以荒漠戈壁为主,植被覆盖度小,比热容小,升温快,李林等[43]研究指出柴达木盆地是青海高原变暖最显著的地区;东部农业区植被多、覆盖度大,但该区域聚集全省70%以上人口,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增加可能是引起显著变暖的主要原因[3]。

表3 1961—2018年青海高原不同区域极端气温指数倾向率的平均值Tab.3 Mean values of the extreme temperature indices trends in different areas over Qinghai plateau during 1961-2018
2.4 极端气温指数倾向率与海拔和纬度的关系
极端气温指数倾向率在空间分布上具有差异性,其经向差异并不明显,气象站点所在纬度和海拔高度可能是影响高原极端气温变化敏感性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图5和图6分别为青海高原气象观测站点1961—2018年8个极端气温指数倾向率与海拔和纬度的散点图。可以看出,暖昼日数、暖夜日数以及极值指数倾向率与海拔呈负相关,而与纬度呈正相关关系,其中最高温极低值和最低温极高值倾向率与海拔(纬度)的负(正)相关关系通过0.0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高原极端气温暖指数的增加速率随海拔的降低和纬度的增加而加快。冷夜日数和冷持续日数倾向率与纬度呈显著负相关性(P<0.05),表明高原极端冷事件减少速率随纬度的增加而加快。另外,青海高原极端暖指数(暖昼日数、暖夜日数、暖持续日数、最高温极低值、最低温极高值)正倾向率以及冷指数(冷昼日数、冷夜日数、冷持续日数)负倾向率最大的站点分布在2000~3500 m的低海拔带及35°N以北的高纬度地区(图5、图6),可见,极端气温暖(冷)指数在高纬地区比高海拔地区增加(减少)更快。

图5 1961—2018年青海高原49个气象站点极端气温指数倾向率与海拔高度的散点图Fig.5 The scatter plots between linear trends of extreme temperature indices and elevations at 49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over Qinghai plateau during 1961-2018

图6 1961—2018年青海高原49个气象站点极端气温指数倾向率与纬度的散点图Fig.6 The scatter plots between linear trends of extreme temperature indices and latitudes at 49 meteorological stations over Qinghai plateau during 1961-2018
3 结论与讨论
(1)1961—2018年,青海高原极端气温暖指数(暖昼日数、暖夜日数、暖持续日数、最高温极低值、最低温极高值)均呈显著增加趋势,极端气温冷指数(冷昼日数、冷夜日数、冷持续日数)呈显著减小趋势。青海高原极端气温指数倾向率具有昼夜不对称性,即夜指数变化速率明显大于昼指数。
(2)暖昼日数、冷昼日数、暖持续日数、最高温极低值、最低温极高值在1996年前后发生突变,其中冷昼日数和最低温极高值的突变年份略晚于其他指数。各极端气温指数序列表现出准3 a、5~6 a、10~15 a、24~31 a以及更长时间的周期振荡,其中以准3 a周期变化最显著,暖持续日数和最高温极低值的准3 a振荡周期对原序列的影响最大。
(3)近58 a来,极端气温冷指数在柴达木盆地减少最快,除暖持续日数外的其余极端气温暖指数在柴达木盆地和东部农业区增加最快,植被覆盖度和人类活动可能是引起上述地区极端气温显著变化的原因。
(4)高原极端气温指数倾向率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纬向差异和垂直向差异,大部分极端气温指数倾向率的绝对值自低纬向高纬、由高海拔向低海拔地区递增,极端气温暖(冷)指数增加(减少)最快的站点均分布在2000~3500 m的低海拔区及35°N以北的高纬度地区。
近几十年来,高海拔地区变暖的海拔依赖性研究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一些研究认为高海拔地区升温幅度比低海拔地区快[19-25],还有研究认为高原升温的“海拔效应”具有不确定性[26-30],高原地区气候增暖海拔效应的不确定性往往归因于高海拔地区气象观测站稀少、研究时段不同、所用数据不同等。为降低这种不确定性,有必要利用空间分辨率较高的MODIS卫星遥感数据,结合地面气象观测站资料,对高原极端气温变化的海拔效应进行深入研究。另外,气温的变化会影响植被物候期、生长能力以及植被的碳吸收和碳消耗[44-45],青海高原作为气候变化的敏感区,气候变化的微小波动都有可能引起生态系统的强烈响应,因此,不同区域自然生态系统对极端气温变化的响应特点和机理也是未来的研究重点。
DOI:10.1029/2003JD003651.
DOI:10.1016/j.gloplacha.2009.03.017.
DOI:10.1007/s11442-012-0936-z.
DOI:10.1007/s00704-014-1286-9.
DOI:10.1038/nclimate2563.
DOI:10.1016/j.gloplacha.2010.01.020.
DOI:10.1007/s12583-010-00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