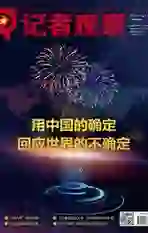城市隐秘角落的拾荒江湖
2021-03-15杨文滢
杨文滢



拾荒者或废品从业者,时常被称为“捡破烂的”。在普通人眼中,拾荒并不是体面的工作,甚至算不上一个工作。但实际上,从垃圾称重、计量、辨识材料到寻找货源、渠道,这个工种非常专业,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
据统计,在全国668座城市中,有拾荒者230多萬。在北京,拾荒者多达10万之众。广州市供销合作总社的数据显示,目前广州约有10万人从事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工作,每年回收的再生资源产值超过i00亿元。这些默默穿梭在街头巷尾的身影,对城市环境清洁作出的贡献不容小觑。
自上海之后,目前已有46个城市相继实施垃圾分类,政策的推行迟早会影响到拾荒这个行业,但面对体量庞大的城市生活垃圾,我国专业的回收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拾荒这个生意依旧生生不息。
难以统计的“江湖”数据
一个个看起来肮脏不堪、人人避之不及的垃圾桶,装着一个拾荒江湖。从拾荒老人到废品收购站,再到垃圾分拣站、垃圾交易市场,人们眼中无用的垃圾,会几易其手,最终变成财富。
根据住建部此前披露的信息,全国有1/3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垃圾围城带来的首要问题是土地、水、空气等污染,影响人体健康,致使呼吸道疾病、痢疾、癌症等疾病发病率明显提高。其次是资源浪费。垃圾填埋场使用的土地,填满后成为一座垃圾山,彻底丧失使用价值,不能盖房子,也不能用于绿化。垃圾中混有大量玻璃、金属、塑料纸等可回收利用资源,不分类直接填埋也导致资源严重浪费。因此,对城市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是非常重要也很必要的。
相关数据显示,中国目前近一半的铜、超过一半的纸和将近30%的铝都来自于可循环再用的废品。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统计,在2001年至201 1年.间,金属回收再利用为中国节省了1.1亿吨煤炭资源,并减少了90亿矿产资源的开采。同样在这十年间,中国大力回收铝废料,因此减少释放5 52亿吨二氧化碳。
这些数字必然与拾荒者相关,他们付出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分拣、分类、收集、运输,使可回收物重新成为生产原料。
而对于刚刚涌入城市的农村人而言,拾荒行业或许是个好选择。不需要特别技能,也不受户口、学历要求的限制,只要付出劳动总有一点现金回报。
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曾任北京市政市容委副总工程师王维平研究拾荒者队伍20余年,为城市垃圾治理提供对策。他所撰写的《关于北京市生活垃圾资源回收利用和相关产业问题的调研报告》中提到,2016年北京通过垃圾处理厂处理和拾荒者处理的垃圾体量基本相同,均为760万吨左右。处理每吨垃圾需要500元人民币,如果没有拾荒者队伍,北京当年的垃圾处理支出将增加38亿元。
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工作是由各区环卫局、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层层推进的。也就是人们看到的,市政的垃圾车到每个社区将垃圾桶内的垃圾进行统一回收处理。但事实上,在市政垃圾车和环卫工人抵达垃圾桶的时候,里面有价值的垃圾已经被分完了。
王维平指出,目前各大城市垃圾处理系统建立的过程是滞后于垃圾的产生的,没有纳入的部分流入了非正式的系统,而可回收资源的分散性分布特征,让资源回收的成本增高,拾荒者把这些本来是零价值的废物重新赋予了价值。
人们丢弃的垃圾通过前端收集、终端转运、后端处理最终抵达再生资源企业。这三个环节承载起了一个拾荒“江湖”。
由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由不同职能部门负责,这个江湖中的绝大部分环节,无法通过企业财报、纳税记录或是其他官方渠道具体统计。而且拾荒群体由民间自发产生,整体文化素质偏低,政府难以统一收编。
没有数据、缺乏监管,并不代表这个江湖不存在。
靠捡垃圾,能把孩子“送”上大学?
城市中的拾荒者多数是进城务工人员,他们在亲戚朋友的介绍下加入拾荒行列。初级的拾荒者只是翻翻垃圾桶、垃圾点,其次是蹬三轮沿街收购、搬运废品旧货的拾荒者,再次是不必四处奔走,坐等收购的站点负责人。
从低级的拾荒者变成大型回收站的老板或是进入再生产业链的并不多,但从沿街捡垃圾开始,慢慢买了自己的三轮走街串巷收废品,进而开起自己的小回收站的人并不在少数。
魏姐的一天是从凌晨四点开始的。
相识的人叫她“大个子”。每天早晨四点半,她都要开着三轮车到20公里外的杭州市中心收垃圾。延安路是杭州规模最大的商业街,在她眼中是块宝地。西北有几个规模巨大的老小区,社区开放,只要三轮车停对地方,早晨六七点就可以完美躲过交警和社区的检查。
保洁、环卫工人、保姆都是提供废品的主力,还有早早起来遛弯儿的老业主,颤巍巍提着两小袋塑料瓶交给魏姐,换一顿早点钱。
“老人们还是有勤俭节约的习惯,你别看他住着这地方几百几千万的房,还是愿意囤东西或者在小区里顺道捡一些废旧物品,舍不得白扔。”
魏姐是安徽亳州人,18年前买了三轮车,和她一起进城的二十多个老乡到处翻垃圾桶扒垃圾桶,做着最末端的垃圾回收。
一开始他们承包了周边写字楼、大厦产生的垃圾。优势是稳定,没别的拾荒者争抢,问题是必须天天到,而且扣除承包费也赚不了多少。后来她就专注老小区的垃圾回收营生。
平时只要魏姐到达社区西边的小门,一两个小时就能收四五百个塑料瓶,放到三轮车上有一米多高。隔三差五,社区会有卫生检查,社区管理员就会撵人,魏姐的应对之策就是起得更早,只要在八点管理员上岗前搞定,就不会有差错。
进入市区,“魏姐们”经过改装的三轮车就成了交警重点关照的对象,超载和违规进入专用车道经常被罚款。最近扣车少了,三五十罚款更多了,很多拾荒者把交警的行为看作是对他们不得已违规的默许,也或许是对他们为减少城市垃圾所作贡献的理解。
回到自己经营的站点,魏姐就会叫上堂哥和老乡帮忙,把废品集中送去回收市场。五六百斤的垃圾固定在车上,要站在板凳上,一人扶着,一层一层垒,十三四个编织袋堆叠,压得三轮车吱呀响。
几十年下来,魏姐把两个女儿送上了大学,一个还读了研究生。虽然奔波、辛苦,但“为孩子,也为了自己”,她很满足,也很自豪。
时代见证下的拾荒致富产业
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废品收购,1955年供销合作总社专门成立了废品管理局,统一管理全国的废品物资回收工作。转入市场经济后,以供销、物资系统公有制为主体的回收行业垄断格局被打破,个体户成为回收行业的主体。
拾荒产业,在上世纪80年代,迎来了黄金期。
拾荒者从偏远、贫瘠村落来到县城,终日穿梭于垃圾桶、垃圾楼、工厂垃圾车间,一心仰赖城市的垃圾发家。
1985年,15岁的河南固始辍学少年乔保锋北上拾荒,旁人避之不及的一座座垃圾山,是他求之不得的聚宝盆。3年后,18岁的乔保锋就拥有了百万家产,成为北京昌平一带赫赫有名的“破烂王”。
经历着同样财富故事的,还有福建小伙林秀成。1990年代,恰逢中国工业化加速时期,他日夜蹲守在钢铁企业门口,赶着上前收下运出的废弃材料。
赚得第一桶金后,机缘巧合下,与三明钢铁厂合作成立了多元化的三安集团。2020年胡润全球富豪榜中,他以360亿元人民币身价名列其中。
外行眼里不值一文的废物,经过成千上万的积累成了撬动财富的有力杠杆。
放眼当前,相关数据显示,一个一线城市每年被丢弃的瓶子约有20万吨,约80亿个。绝大部分塑料瓶身是PET材质,这种材料是制作涤纶的重要原料,而瓶盖则是PP材质,又叫聚丙烯,可广泛运用于汽车、电子电器、纺织、建筑等多种领域。
塑料瓶在垃圾回收站的毛料回收价大概在2000多元一吨,而通过分类、破片、压缩后的价格可以达到4000元~6000元一吨。
废旧泡沫塑料的利润更加可观,市场上回收泡沫塑料一般以1.5元每公斤成交,而塑料泡沫制品厂的收购价格达到了3000元每吨,虽然中间环节很多,但利润依然不小。
曾因稀土价格猛涨,强磁的回收价格从每公斤60元飙升到每公斤400元,这其中价格变化,是随便将废旧收音机丢在垃圾桶中的人们所不了解的。
城市里开车往返于收购站与垃圾处理工厂的吴师傅,每月刨去卡车加油和房租等日常成本,收入将近2万元。
对垃圾打包站和垃圾处理站来说,获利则更高。以废纸打包站为例,据估算,假设每天收货50吨且毛利润在0.1元一公斤,一年的收入约为140多万元。
这样规模的垃圾打包站一年的场地租金约25万元,如果有能力开一个能容纳30家~40家打包站的垃圾场,每年光房租利润就是一笔巨款。
但随着垃圾分类政策的稳步推进,拾荒产业也逐渐受到不小的影响。
都市里的拾荒者,该何去何从
长期以来,不少聚集在城市边缘郊区或城中村的废品回收、处置作坊都存在着手续不全,缺乏安全、消防设备等问题。很多废品回收站常年都堆满了捡来的垃圾,脏乱繁杂,环境恶劣。而且长期在无防护的条件下和垃圾接触,也很容易患肝炎、痢疾等传染病,给社会公共卫生埋下了重大隐患。
随着垃圾分类政策及理念的推行,不少地区都针对违规的废品回收站进行了整治、关停。
北京于2020年5月1日起,全面开启“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并要求关停所有位于城区主干道的废品回收站,鼓励市民推行“互联网+回收”的模式,西城区还率先施行APP预约回收、定时定点回收、上门回收等方式。
2020年1月初,呼和浩特监管部门在联合执法排查中发现玉泉区商户私自焚烧的废弃物涉及废旧电器外壳、电路板线、机械部件、生活废品、包装废弃物、建材废弃物、废旧汽配件等多达7大项20余种,随即要求自行整改并搬迁至指定区域。
西安灞桥区也于2020年摸排再生资源回收站80余家,对违规的回收站全部进行清理、注销;重庆市江北区于2020年5月重点查处无从业资质的废品回收站,并拆除多处回收站的临建……
在城市管理触角不断延伸及地租高涨的大环境下,废品从业者们只能越搬越远,不断远离现代文明。
王维平表示,北京拾荒者人数在2014年、2015年到达最高峰,有17万人,现在还剩不到10万人。随着人口控制和外部市场等诸多因素变化,近年来各大城市的拾荒群体都在不断萎缩。
浙江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雪锋提出,垃圾分类本质是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置,而拾荒是一种谋利行为,对居民环保意识的提升没有作任何贡献。因此,这种垃圾减量的方式是不值得鼓励的。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宋国君也认为,在城乡差距很大,社会的保障不是很充分、管理不到位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这样一个群体。城市拾荒者提供的社会功能应被另一种更加文明、更加现代化的方式替代。
2020年,零点有数发布的《强制垃圾分类前后拾荒者生境研究报告》中表示,目前国内以及各城市的垃圾分类相关政策规定多作用于居民、社区居委会与物业公司、城市环卫清运系统、垃圾处理终端等重点主体上,相对而言对于拾荒者与其构成的非正规垃圾处理体系较少提及。
在目前的政策环境下,国家与各地方对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总的要求是专业化、市场化、规范化、全民化。对拾荒者、拾荒行为则没有明确要求。
在当下的环境下,拾荒者未来一段时间仍会继续存在。但垃圾分类政策、管理要求会给拾荒者的工作、生活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受政策影响最大的人群是部分单一收入来源的捡拾类拾荒者,其他类型的拾荒者所受影响有限,整体的回收体系链条尚未发生断裂。
2020年实施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应及时制止翻拣、混合已分类的生活垃圾的行为。这样的政策,会给拾荒者们带来或多或少的影响,但也可能会反作用于城市正规垃圾处理体系,造成可回收物处理压力的增加。
截至去年,万宏俊在北京经营废品打包站已经3年。前不久,附近的站点都被通知关停。但仍有人不甘心,继续住在原处标着6元一天的集装箱板房里,观察着有无重开的可能。
对他而言,去留之間也很矛盾。彻底离开,需要转让60多万购买的打包机器,再想回来未必有资金再重新投入。
他希望政府能够出面规划一些土地,把现在几乎都处于灰色地带的废品回收业正规化,利润可以少一些,至少能稳定下来,踏踏实实再干几年。
李军和他的老乡是重庆干废品回收较早的一批人,近几年一半的人也转了行,开车、去印刷厂、回老家的都有。他也想过离开,但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老家地少,辛苦一年挣一万块,除了化肥、农药,各种生活花销,剩不下多少。”他无奈地说。
在南京拾荒30年的老王,一大早又徘徊在新街口商业区附近,他打量着匆匆路过垃圾桶的行人,心里默默盘算着:“转转,前面还有好东西……寄回老家的钱今年终于可以盖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