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汉塞“陰燧取火”考
2021-03-15陈松梅何双全
陈松梅 何双全
(1.四川警察学院,四川 沪州 646000;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30)
2014年以来史语所简牍整理小组出版的《居延汉简》图版更清晰、释文更准确,为汉简研究提供了更完善的资料,但我们在使用时发现部分释文仍存在问题。如简5.10:
官先夏至一日以陰隧取火,授中二〓千〓石〓官在长安、云阳者,其民皆受,以日至易故火;庚戌寝兵不听事,尽甲寅五日。臣请布臣□昧死以闻。(5.10)①
据表格对比发现,“除”“陰”字形虽相似,但也有区别,二者区别在于右侧偏旁的下部,“陰”字右侧下部为“山”“土”“厶”形,竖划与左右两侧是相连的,笔划间具有合聚性、封闭性。“除”字右侧下部多为“小”形,竖划与左右两点并不相连,笔划间具有分散性、开放性。简文的“”虽竖笔下部有向左侧很短的撇划,应是竖笔向左的延笔,因其右侧下部竖划与左右两边完全相连,笔画间仍具合聚性、封闭性。故“”应为“陰”字而非“除”字。
简5.10 属于“元康五年诏书册”的一枚,“元康五年诏书册”是大庭修先生简册复原的成果之一。⑦为便于理解,现将此诏书引用如下:
御史大夫吉昧死言:丞相相上大常昌书言:大史丞定言:元康五年五月二日壬子日夏至,宜寝兵、大官抒井、更水火、进鸣鸡、谒以闻布当用者。
□臣谨案:比原泉御者、水衡抒大官御井;中二〓千〓石〓令官各抒别火。 (10.27)官先夏至一日以陰隧取火,授中二〓千〓石〓官在长安、云阳者,其民皆受。以日至易故火;庚戌寝兵不听事,尽甲寅五日。臣请布,臣昧死以闻。 (5.10)制曰:可 (332.26)元康五年二月癸丑朔癸亥,御史大夫吉下丞相,承书从事下当用者,⑧如诏书。 (10.33)二月丁卯,丞相相下车骑将〓军〓中二〓千〓石〓、郡大守、诸候相,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少史庆、令史宜王、始长。 (10.30)
三月丙午,张掖长史延行大守事、肩水仓长汤兼行丞事,下属国、农、部都尉、小府、县官,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守属宗、助府佐定 (10.32)
闰月丁巳,张掖肩水城尉谊以近次兼行都尉事,下候、城尉,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守卒史义。 (10.29)
闰月庚申,肩水士吏横以私印行候事,下尉、候长,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令史得。 (10.31)
这八枚简共同构成“元康五年诏书册”,同出土于地湾(A33)即肩水候官,元康五年闰月丁巳(四月六日)此诏书由汉代张掖郡肩水都尉府下达到肩水候官,并于闰月庚申(四月九日)下达到肩水候官所辖部隧,此诏书册是肩水候官的存档文件,由上奏请诏文和诏书行下文两部分组成。简5.10与10.27共同构成上奏请诏文,上奏内容是长安、云阳两地的各级政府机构、官吏在夏至日前后要完成三件事:一是“比原泉御者、水衡抒大官御井”,为疏通水井行改水之事。二是“官先夏至一日以陰隧取火,授中二千石官、二千石官在长安、云阳者,其民皆受,以日至易故火”,意在元康五年夏至日前一天以陰燧取火,并将新火发给两地吏民,以便在夏至日来临时改行新火。⑨三是“庚戌寝兵不听事,尽甲寅五日”,意在元康五年四月庚戌至五月甲寅这五天内不行兵事、政府停止办公、官吏放假五天。
因诏书前已言改水之事,所以确定简5.10的“陰燧”与改水无关,应与改火有关。而且简中的取火“陰燧”与传世文献所记取水“陰燧”并非一物,“陰燧取火”与“陰燧取水”并非一事。传世文献中的“陰燧”又名“方诸”“阴鉴”,多为铜制方镜,用于取水。而简文的“陰燧”用于取火,二者的功用明显不同,应指代不同器物。二者出现时间也不尽相同,“陰燧取水”的最早记载见于《淮南子集释》卷三:“‘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高诱注:‘方诸,陰燧,大蛤也。熟摩令热,月盛时以向月下,则水生,以铜盘受之,下水数滴。先师说然也’。淡春堂案:诱自序云:‘自诱之少,从故侍中同县卢君受其句读,诵举大意。又云:‘深思先师之训,为之注解。’卢君者,植也。诱所云‘先师’当是卢植。”⑩卢植是东汉时人,其生卒年是从汉顺帝永和四年至汉献帝初平三年(139~192年)。那么,传世文献所记“陰燧取水”也应出现于东汉以后。而简文的“陰燧取火”早在汉宣帝元康五年就已存在,远远早于传世文献“陰燧取水”出现的时间。[11]
汉代取火工具主要有“金燧”“木燧”。《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四:“《礼》有‘金燧’‘木燧’皆取火之物,故以燧名火也。”[12]《江文通集汇注》卷七:“阳燧要景”,注:“《淮南子》曰:‘阳燧见日则然而为火出。’注:‘阳燧以金为之,持以向日,燥艾承之,寸余,则得火。’”[13]《五礼通考》卷六三:“取火于日故名阳燧,取火于木为木燧者也。”[14]可知,取火于日的“金燧”又名“阳燧”。而简5.10的“”燧并非“阳燧”,因为从字形上看,“”与同简“阳”的写法差别较大,故此“燧”不是取火于日的“阳燧”,而是另一种取火于木的工具“木燧”。而“”与“木”的写法完全不同,“”燧应是“木燧”之外的另一种称呼,可能为“陰燧”。
同时“木”有“阴木”“阳木”之分,《周礼》卷四:“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郑司农云:“阳木春夏生者,阴木秋冬生者,若松柏之属。玄谓阳木生山南者,阴木生山北者,冬斩阳夏斩阴坚濡调。”[16]为适应万物生长规律,简5.10夏季改火所用的“燧”应采自于“阴木”,“燧”即是“阴木”做成的“木燧”,加之其佩戴于右侧、出火于木,皆属阴,“燧”为“陰燧”无疑。
因“陰燧”为“木燧”,“陰燧取火”即是“钻木取火”。《礼记集解》卷二七:“‘左佩金燧,右佩木燧。’郑注:‘金燧取火于日,木燧钻火也。’”[17]简文的“陰燧取火”是为了在夏至日行改火之事,以“钻木取火”的方式行改火之事,文献中亦多有记载。《尸子》卷下:“钻燧改火。”《论语集解》马融云:“《周书·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梄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钻火各异木,故曰改火也。’皇疏云:‘改火之木随五行之色而变也’。”[18]《汉书·魏相传》:“天地变化,必徭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识,不得相干。”[19]通过以上文献资料可知,四时变出火之木及夏至前“陰燧取火”都顺应了万物新旧更替、阴阳交替的规律。
二十世纪初以来西北地区出土了大量木质取火工具,比较典型的有:1906年在楼兰遗址发现1件钻木取火器,取火板和钻木棒用细毛绳联结在一起(见图一);1979 年在敦煌马圈湾地区出土1件取火器(79D.M.T4:012),柳木制成,形制为长条形木块,两侧有钻眼孔,一侧8 个,另一侧2个,孔底有灼烧的焦痕(见图二);1987 年此地又出土1 件钻木杆(87D.M.T12:031),红柳削成,一端齐平,一端有榫头,或许与取火器配套,为钻木杆(见图二)。[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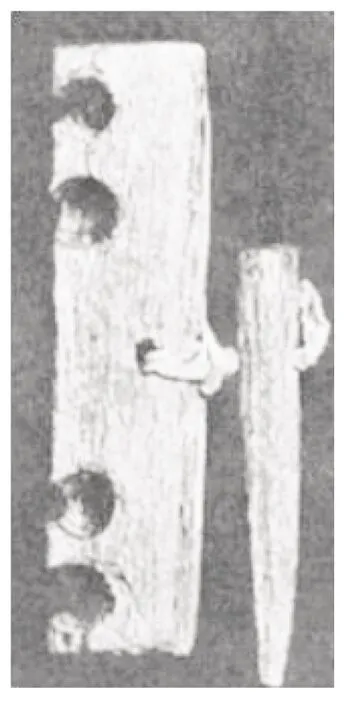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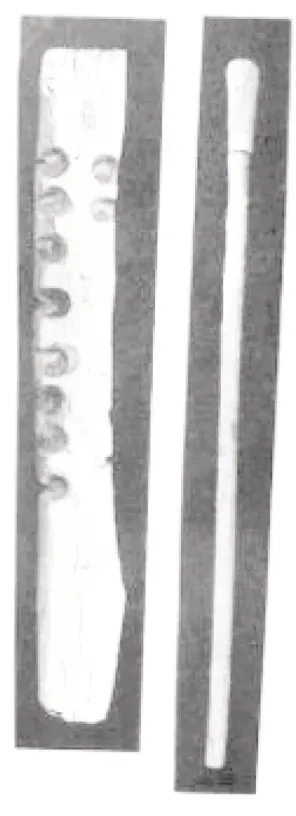
图2
取火工具作为边防守御器的一种,简文也有记载:
卅井降虏□
出火椎钻二 (305.17A)
出火遂二具 (505.10)
守御器簿……出火燧二具…… (506.1)
长椎四 出火具各一 烟□□ (敦煌691)
据此可知,“出火椎钻”“出火遂”“出火具”是汉代西北边塞的取火工具,由钻木杆和出火板(如上图所示)两部分组成。实物的出土,说明河西汉塞确实存在过“陰燧”“陰燧取火”,或可成为夏至前改火“陰燧取火”的物证。
综合“元康五年诏书册”的内容、夏至先一日“陰燧取火”行改火之事的合理性、考古出土实物及相应字形的对比分析,简5.10的“”释为“陰”文从字顺。由此可以确定“”燧即“陰燧”,也称“木燧”。“陰燧取火”即是“钻木取火”。
注释:
①简文参见史语所简牍整理小組:《居延汉简》壹,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年,第9页。简后的未识字“□”,因无此字文意已通,而且据图版简面遗留的墨迹可能是简册字体的延笔,故“□”应删。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页。
③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8页。
④于豪亮《于豪亮学术文存》,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2页。
⑤裘锡圭《裘锡圭学术文集》(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7页。
⑥史语所简牍整理小组《居延汉简》(壹),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年,第9页。
⑦[日]大庭脩著、徐世虹译《汉简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18页。
⑧应将“承书从事,下当用者”间的逗号删除。因“者”是中心词,是“承书从事者、下当用者”的略写。
⑨[汉]司马彪《续后汉书》(第四),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74页。
⑩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73页。
[11] 于豪亮先生通过传世文献的记载和作者所处時代,认为“陰燧取水”的说法大概出现于东汉时期。具体论述为“因为高诱师卢植、卢植师马融,马融曾注《淮南子》,是不是高诱关于方诸又名阴燧、即是大蛤之说本于马融呢?即使此说本于马融,马融是东汉时人,比简文所记元康五年(61年)晚得多。时代变迁、词义变化,不能据此否定阴燧取火即钻木取火之说。”参见于豪亮《于豪亮学术文存》,第182 页。
[12]《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上、中、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55页。
[13][明]胡之骥注、李长路、赵威点校《江文通集汇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61页。
[14][清]秦蕙田《五礼通考》,《钦定四库全书》清光绪二十二年梅城望龙阁陈氏刻本。
[15][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27页。
[16][唐]贾公彦《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
[17][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第727页。
[18][周]尸佼撰、[清]汪继培校正《尸子》,湖海楼刻本。
[19][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139页。
[20] 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县文化馆《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0期,第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