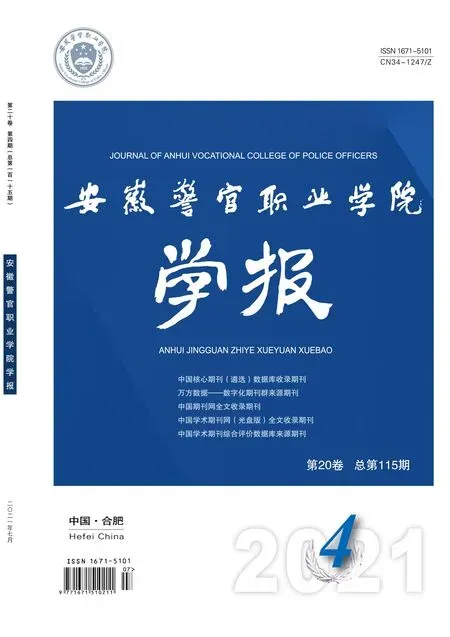诬告陷害罪之实体要件再解读
2021-03-13周云,张兰
周 云,张 兰
(四川大学 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7)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243条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由此而确立了我国诬告陷害罪之实体要件。然而,实务中在适用该规则时,对该罪的构成要件部分内容却产生了许多争议,例如,其不法构成要件要素之行为是单数还是复数?其侵犯的法益究竟属于人身权利抑或司法秩序?关键词“事实”该如何解释等等。而这些实体问题的不同解释,往往关系着行为人之行为的“罪”与“非罪”。但法律与相关司法解释对此却未加以厘清,从而埋下了“同案不同判”的隐患。且法律规范内容理解上的歧义,还影响其指引功能的发挥,导致实践中诬告陷害事件频频发生。因此,现在亟需对诬告陷害罪的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以及有责性进行再解读,界分其中争议问题,以期对完善该规范有些微之作用。
一、诬告陷害罪之构成要件符合性
构成要件符合性并不是整体的判断,而是需要法官在面对刑事个案时,具体判断案件事实是否具备构成要件的各个要素,不存在离开构成要件要素进行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可见,构成要件要素是否具备以及对其内涵的界定,影响着行为人的罪与非罪。而由于诬告陷害罪之部分构成要件要素尚存在争议,因此,下文将对这些争议内容进行讨论。
(一)“单一行为”抑或“复合行为”
依据不法构成要件所描述的行为数,犯罪类型可区分为单行为犯与双行为犯。其中,单行为犯系指不法构成要件所描述的行为仅属单一的犯罪,例如只有杀害行为的杀人罪;双行为犯又可称为复行为犯,系指在一个独立构成要件中兼顾两个以上行为的犯罪,例如包括强制手段与劫取财物两个行为之抢劫罪。[1]区分行为之单、复数,对于正确判断行为是否满足构成要件之该当性具有重要意义,若某一犯罪的构成要件描述之行为为复数,那么只有单一的行为就不符合该罪之构成要件,终被认定不构成此罪。例如行人A夜晚下班回家途中,巧遇B正实施暴力抢劫C的钱包,C在情急之下,为避免钱财之损失,把其钱包丢向远处,恰落在A的脚下,A出于非法占有之目的捡起C的钱包逃之夭夭。本案中,对《刑法》第263条之行为单复数的判断,影响着A的行为是否构成抢劫罪。《刑法》第263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抢劫罪之构成要件中,包括两个行为,即物理或心理之强制手段,与取得他人财物行为。设行为人的行为只满足前者或后者,都将不构成抢劫罪。因此,上述案例中,行为人A只有取得他人财物的行为,而没有针对被害人C实施强制行为,故行为人A并不构成抢劫罪。至于A是否成立犯罪或成立什么犯罪,则属于另一个层面之问题,本案中,A的行为符合盗窃罪之构成要件。可见行为之单复数判断问题至关重要。
对于诬告陷害罪不法构成要件所描述之行为数的判断同样关乎某一行为是否成立此罪,因此,对诬告陷害实体要件之分析,绕不开对此问题之厘清。《刑法》第243条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有学者认为,诬告陷害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复合行为,由捏造事实行为与告发行为结合而成。[2]按照此种观点,要构成诬告陷害罪,行为人之行为必须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捏造他人行为构成犯罪之事实,二为向对行为人的自由有限制或剥夺权之国家机关告发。缺少其中任何一行为,将不满足构成要件之该当性,不构成诬告陷害罪。若此种观点正确并在实务中适用,将会违背罪责原则,带来一系列之负面后果,使刑法保障人权之目的难以实现。例如行为人D为了诬告陷害E,意图使E受到刑事追究,捏造E贿赂之“犯罪事实材料”,打算向纪委监察委员会“告发”。不料在途中,不慎将其“材料”遗失在举报之路上,恰巧E的仇人F捡到。由于对E心生怨恨已久,故F遂拾到的此份“材料”后,明知内容不实,仍呈交至纪委监察委员会,使E受到立案追究。不料最后东窗事发……。若按照上述之诬告陷害罪为复数行为之观点,由于F没有实施捏造E贿赂之犯罪事实的行为,其只有告发行为,因此,F的告发行为并不符合诬告陷害罪之构成要件,不构成此罪。但纵观此案,被害人E已经被立案追究,很有可能其人身自由还遭受了剥夺,即《刑法》第243条保护之法益受到了侵害,但却没有侵害行为?这显然有悖罪责原则。
本文认为,对某犯罪的不法构成要件所描述行为是单数还是复数之判断,不得只停留在文义解释层面,而应当结合该罪名之设置目的与该法条在整个法律文本中的地位进行解释,即应进行目的解释与体系解释。首先,《刑法》第243条之保护法益为人身权利。由于犯罪行为之本质就是侵害刑法所保护法益之行为,没有侵害法益之行为不可能构成犯罪。[3]因此,想要判断某一行为是否属于诬告陷害罪之犯罪行为,必须要看其是否侵害了被害人之人身权利,不应把目光局限于文义表面所包括之行为;其次,要对被害人之人身权益造成侵害,其诬告行为必须使得有关机关对被害人采取一定之措施,例如暂时剥夺其自由;若诬告行为并没有致被害人的人身权益遭受损失,则被告人之行为就很难定义为刑法意义上之诬告陷害行为。我们以上面所举的例子观之,行为人D只有捏造E犯罪事实之行为,由于客观原因,没有实施向有关机关之告发行为;可见,行为人D的行为并没有致被害人E之人身权益遭到有关机关的侵害,故其行为不应构成《刑法》第243条之诬告陷害罪。与之相反的是行为人F之行为,虽然其没有捏造E有犯罪事实,但其向有关机关之告发行为致使被害人E遭到立案调查,人身权益受到侵害,F之行为已经构成了诬告陷害罪。因此,通过目的解释我们可以发现,诬告陷害罪之不法构成要件所描述之行为应当是单数而不是复数行为,其不法行为应是向有关机关之告发行为,并不包括捏造犯罪事实之行为。
为了进一步论证诬告陷害罪之行为应只包括告发行为,而不涵盖捏造行为,我们可以将其与《刑法》第246条之诽谤罪进行比较分析。由于此两个法律条文同属于《刑法》第二编第四章,从广义上来说,两者保护之法益都为公民人身权利,且两者之构造上基本相同。诽谤罪之规定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而诬告陷害罪为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由此可以看出,两者在客观行为构造上基本相同,只是两者都包含的“事实”内容有所差异。因此可以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得出结论。对于诽谤罪不法构成要件所描述之行为是单数行为还是复数行为。传统的刑法理论观点认为,其应包括捏造虚假事实与在公众场合散布两个行为,[4]只有捏造虚假事实或在公众场合散布虚假事实行为的,不构成诽谤罪。随着网络诽谤现象犯罪行为的频频发生,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9月通过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其中解释第1条对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行为具体化为三种类型,第三种类型为明知是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情节恶劣的,以“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论。由此可见实务中也主张了诽谤罪不法构件所描述之行为应为单数行为,而不是复数行为,即主张虽没有捏造虚假事实之行为,但只要有散布虚假事实行为的,依然构成诽谤罪。尽管有声音称该条《解释》将“散布他人捏造的虚假事实”解释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属于以解释之名行类推解释之实,超出了刑法原意,不具有国民可预测性。[5]但本文认为,我们在判断不法构成要件所描述之行为为单数或复数时,应当要看其是否侵害了刑法保护的法益。显然单一的散布他人捏造的虚假事实行为对被害人的名誉造成的侵害与既捏造虚假事实又散布该事实之行为,对保护法益的侵害程度没有什么差别。有学者主张可以将“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解释为“利用捏造的事实诽谤他人”或者“以捏造的事实诽谤他人”;并且《刑法》第246条使用“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这种表述看似重复,实际上是为了防止将误以为是真实事实而散布的行为认定为犯罪,亦即是为了防止处罚没有犯罪故意的行为,而不意味着诽谤罪必须由复数行为构成。[6]本文赞同这种观点。同理,由于诽谤罪与诬告陷害罪两者的行为构造基本相同,故这里关于诽谤罪行为单复数之观点可以运用到诬告陷害罪中,从而可以进一步论证诬告陷害罪不法构成要件描述的行为应为单数行为,并不是复数行为。对于《刑法》第243条中的“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可以解释为“利用捏造的事实诬告陷害他人”。因此,虽然没有伪造证据材料,捏造犯罪事实之行为,只有向有关机关告发之行为,依然构成诬告陷害罪。
(二)捏造事实中“事实”之解释
诬告陷害罪的构成要件中,另一重要的问题是对捏造事实中的“事实”该如何解释,以及其界限问题。《刑法》第243条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此行为构造表明,行为人捏造的事实,必须能够使他人受到有关机关的刑事追究。因此,这里的“事实”并不是“生活事实”,而应当仅局限于“犯罪事实”,否则将难以使他人因捏造的“事实”而受到有关机关的刑事追究。实务中,公职人员经常被诬告为“在开展工作中存在优亲厚友谋取私利问题”,“心胸狭隘,借反腐泄私愤”,甚至有被举报“存在向一位村党支部书记‘打招呼’”。由于这些捏造的事实并不属于犯罪事实的范畴,最多只能算是个人工作作风问题,难以该当诬告陷害罪规定的“事实”要件,故不构成诬告陷害罪。界定清楚诬告陷害罪中的“事实”是犯罪事实之后,我们还需要对什么是事实进行解释,才能算是真正掌握何为“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避免陷入误区。“事实”是指现在或过去的具体历程或状态,并且具有可以验证其为“真”或“伪”之性质者。[7]也即是说“事实”是可以根据一定的证据资料来探究其真实与否的,例如,G诬告H在某时某地收受他人贿赂,打算为其谋取不正当利益。由于这一诬告事实是属于过去的具体历程或状态,且可以查实真伪的,因此,其属于“事实”概念范畴。与“事实”概念相对应的是“意见”,其是指纯粹的价值判断或单纯的意见表达,欠缺可资检验真伪的性质,甚至可以说,“意见”是见仁见智之“个人品味”问题。例如实务中存在的诬告他人心胸狭隘、接受精神贿赂……。这些流言蜚语都很难评价成为“事实”,至多算是单纯的价值判断,即属于“意见”之概念范畴。但即使是属于类此的流言,实务中还是有许多部门出于保险起见,对被诬告者做出相应的处理,如本文引言中所述若不能立刻澄清的,上级将径直选择从备选名单中剔除这名干部,或是终止相关任用程序。这样的处理方式是混淆“事实”与“意见”的表现,将“意见”当作“事实”,若不改变此种观念,无疑将会对被诬告者的权利造成侵害,还将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因此,在实践中,当有关机关接到有关控告、检举他人的材料时,首先应判断材料所指的是“事实”还是“意见”,若为后者,则不需要启动相应的程序来进行调查核实,即是说“事实”与“意见”之判断起着过滤的作用,将不符合诬告罪所要求的事实排除。特别是在有关对公职人员的诬告陷害审查中,若收到的材料明显属于“意见”类,例如心胸狭窄,打招呼……,可以不中止对该工作人员的升迁考察程序,不将其从备选名单中剔除等。
(三)侵害之法益:人身权利抑或司法秩序
保护法益是刑法目的之一,故从反面来说,犯罪行为的本质就是侵害法益之行为。而在因果关系与客观归责理论中,判断该当不法构成要件中不法后果是否归责于行为人时,法益亦成为重要判断的标准。由此可见,对某一刑法条文所保护之法益的正确定位至关重要,甚至于关系到行为人之行为是否构成此罪。诬告陷害罪的侵害之法益是被害人之人身权利,抑或司法秩序在学界中有不同的声音。有学者认为,将诬告陷害罪侵犯的客体局限于公民的人身权是不妥当的,因为诬告陷害行为也会附带侵犯国家的正常司法秩序,[8]故主张诬告陷害罪之客体为复合客体。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诬告陷害罪保护的法益是被害人之人身权利或司法机关的正常秩序,即虽然诬告行为只是对此两种法益中的一个造成侵害,如只侵害了司法秩序,而没有损害被告人身权利的,依然构成诬告陷害罪。本文认为,要对诬告陷害罪的法益进行探讨,必须要从该法条在整个刑法文本中的体系位置进行解释,从上述可知,我国《刑法》第243条处于第二编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根据诬告陷害罪在刑法文本中的体系地位可知,其保护之法益为公民的人身权利,并不包括司法秩序。虽然任何诬告陷害行为都必然附带侵犯司法活动,但这只是客观事实,而不是法律规定。[9]故,诬告陷害罪保护的法益是单一法益,即只是被害人之人身权利。若某一诬告陷害行为只是侵害司法秩序,没有侵犯被害人人身权利的,并不构成诬告陷害罪。
二、诬告陷害罪违法性之阻却事由
“刑法上的违法性是判断行为是否值得处罚的要件,按照结果无价值论的观点,刑法的目的与任务是保护法益,没有造成法益侵害及其危险的行为,即使违背社会伦理秩序,也不能成为刑法的处罚对象”。[10]也即,行为人的行为符合该当性与违法性指要件,但由于侵犯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亦不能发生犯罪之结果,应当成立不能犯而不具有可罚性。[11]由于诬告陷害罪成立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的可能性太小,所以本文主要针对被害人承诺着重讨论,其余不再赘述。
违法阻却事由中有重要的一项为“因法益性的阙如阻却违法的事由”,即得被害人承诺。因被害人承诺有一定构成要件,必须符合其要件方能阻却违法,诬告陷害罪可能使被害人人身权甚至生命权受到侵害,所以在此讨论有一定必要性。
首先,我国刑法不承认被害人对其生命权的承诺,通说理论都认为,即使被害人承诺行为人可以随意杀害自己使其丧失生命权,但是行为人仍然构成故意杀人罪。所以对于被害人承诺行为人构陷其故意杀人罪而导致被害人被司法机关强制剥夺其生命,被害人的承诺也不能构成违法阻却事由,行为人仍构成诬告陷害罪。
其次,被害人承诺仅限自身能够处分之法益,对国家利益、他人之利益等都无法承诺。[12]但对于诬告陷害罪,有双重客体说,也即被害人人身权与司法秩序之法益,即使被害人承诺行为人可以侵犯自身权益,但由于诬告陷害罪特殊性,伴随着司法机关因诬告行为而开启刑事诉讼程序,其司法正常活动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对此,被害人承诺是否能成为违法阻却事由,亦属争论点之一。[13]就此问题而言,本文认为诬告陷害罪的客体是单一客体,即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因其所处位置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所以对于被害人承诺自己人身利益的行为,当然可以成为诬告陷害罪的违法阻却事由之一。
再者,被害人需具备认识能力与行为能力,主要是以年龄与精神状态作为辨认标准。因被害人承诺将有损自己的利益,所以对此主体条件要求较高,必须具备认识能力与辨认能力,并且做出的承诺是客观真实的,不受任何胁迫与欺骗的,对后果能够清楚地认识。因此,本文认为应当要求被害人同时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不仅要求有认识能力,还必须具备行为能力。
三、诬告陷害罪之有责性
构成要件符合性与违法性是有责性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当行为人的行为符合客观犯罪事实构成时,才能对其犯罪的主观状态进行考察以确定是否应当对行为人进行非法的责难。有责性不是指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或再犯可能性,而是指其主观故意或过失状态,下文将详细论述有责性方面的几个争议问题:
(一)主观故意
诬告陷害罪之主观为故意并没有争议,故不值得去大书特书。然而,若主张诬告陷害罪属于上述之单行为犯,即不需要有捏造犯罪事实,只需要有告发行为就该当构成要件之行为;那么就需要注意一个重要的问题——主观真实,亦即虽然客观上被诬告人并不存在犯罪事实,但实施告发行为的人认为有相当的“客观证据材料”判断被诬告者有犯罪之嫌疑。此时,有必要探讨诬告者主观状态。显而易见的是,主张诬告陷害罪为复合犯的观点并不存主观真实的问题,因为,既然捏造犯罪事实与向有关机关告发行为是诬告陷害罪必不可少的两行为,那么诬告者主观上就不会发生主观认识上认为犯罪事实必然为真的问题。诬告陷害罪之主观真实问题,关系着公民的检举、控告权与被告发人之人身权利之间的权衡。此外,对于主观上虽属于故意诬告陷害他人,但其捏造的犯罪事实却偶然符合被诬告者实施的犯罪行为。例如,赵某素与李某有仇,为了让李某陷入“麻烦”,故捏造李某曾经有盗窃的行为,并向当地的公安机关进行告发,在该机关对李某采取强制措施并立案侦查时,却发现其竟曾经在某年月日实施入室盗窃。在此案例中,赵某主观上是出于故意陷害李某,并以使其受到刑事追究为目的,而捏造其以为客观并不存在的事实,却不曾料到李某曾实施过该盗窃行为。此时,对李某的行为是否认定为诬告陷害?本文认为,李某的行为难以评价为诬告陷害。根据三阶层理论学说,对于某一行为能否评价为此罪,需要从不法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进行逐步判断,这一渐次的判断过程,也是一个由客观到主观判断过程。因此,对于赵某的行为,客观上并不存在诬告他人的犯罪事实,既然在客观阶段已经将其行为排斥在犯罪之大门外,就不需要再讨论其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诬告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否则一意孤行地认定赵某的行为属于诬告陷害的话,无疑将会导致主观归罪,将有悖于罪刑法定之刑法原则。
(二)主观目的
对于诬告陷害罪是故意犯罪已无异议,但对于其是否能够由间接故意构成犯罪却无定论。部分学者认为诬告陷害罪可由间接故意构成,因实践中存在行为人散布谣言任被害人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本文不同意上述观点,这是混淆了诽谤罪与诬告陷害罪的界限,上文已经论述过诬告陷害罪最重要的在于告发、揭露行为。本文在此讨论主观目的旨在否定诬告陷害罪主观构成不存在间接故意,而是存在主动追求犯罪结果的发生。由于诬告陷害罪是目的犯,所以在诬告陷害罪有责性层面,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主观目的,其是指某些故意犯罪所要求的主观要素,这些故意犯罪也称之为目的犯。对于目的犯,主观要素除了要求故意外,还必须要具备特定的目的,否则不成立此罪,由此也可得出诬告陷害罪不能由间接故意构成的结论。刑法条文中表明在故意之外,仍需具备特定目的之条文一般表述为“意图”、“以……为目的” 等,例如《刑法》第263条规定的“以牟利为目的,制作、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其就表明犯罪事实要能涵摄第263条之规定,主观上除了具备故意要素之外,还必须具备牟利之目的。因此,《刑法》第243条规定中,“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的表述也说明要构成诬告陷害罪,除了具备故意之外,必须还要具备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的主观目的。这也是区分诬告陷害、错告及检举失实有效判断方法,虽然行为人客观上告发的事实与真实存在的客观事实有一定的出入,但由于其主观上并没有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的目的,此时就不能把告发行为评价为诬告陷害罪,应属于错告或检举失实。
四、结语
诬告陷害罪在实体法构成要件存在的理论争议, 间接造成诬告之低成本,对被诬告者造成很大之影响。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重塑其实体要件来解决问题。在实体要件中,首要须判断的是不法构成要件,通过对《刑法》第243条进行目的解释与体系解释,我们可以得出诬告陷害罪应当属于单行为犯,而非复数行为犯,并且其保护法益是人身权利,而非司法秩序。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如何界定“捏造犯罪事实”中的“事实”,特别要注意其与“意见”的区别,前者是指现在或过去的具体历程或状态,并且具有可以验证其为“真”或“伪”之性质者;后者是指纯粹的价值判断或单纯的意见表达,欠缺可资检验真伪的性质。实体层面其次需要判断的是违法性,即被害人承诺的利益范围及主体要件,即使是被害人自己的人身权利,法律对此亦有限制,如果不满足被害人承诺要件,那么违法阻却事由也即失效;最后,需要注意的是,诬告陷害罪是目的犯,不存在间接故意成立诬告陷害罪,即存在意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之目的,因此,欠缺此目的的,应属于错告或检举失实,不构成诬告陷害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