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汉学家对李白道教诗歌的跨文化阐释
2021-03-11卢婕
卢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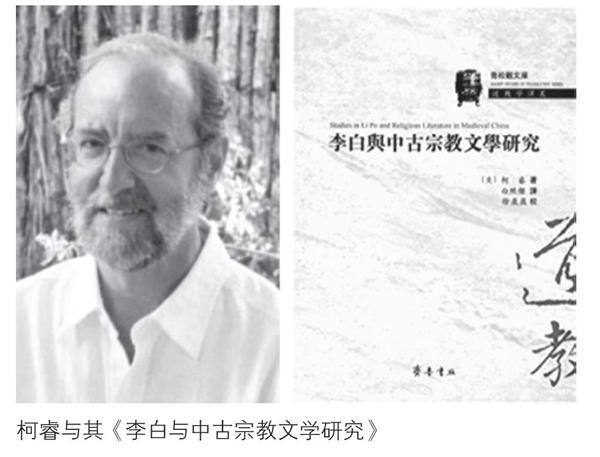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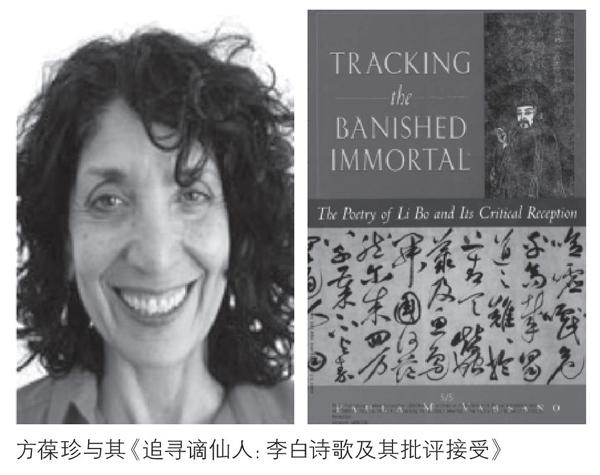

摘 要:美国学者柯睿和方葆珍通过跨文化阐释的方法,深化和补充了西方读者对李白诗歌和中国道教的认识。柯睿以文学—宗教学的跨学科视野,复以将人文与自然科学结合、学科交融的阐释方法为西方读者分析了李白道教诗歌的用语和意象;方葆珍以“以译释义”和“以中释中”译释结合的阐释方法,力求最大化地保留李白诗歌的道教内涵和形塑李白作为“道教诗人”的形象。他们对李白道教诗歌的跨文化阐释不仅促进了李白诗歌在海外的经典化,还有效地推进了中国道学的西传。
关键词:跨文化阐释;李白;道教诗歌;海外汉学
“所谓跨文化阐释,就是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从一种文本向另一种文本、从一种能指向另一种能指的转换;就是用另一种文化、另一种语言、另一种文本、另一种能指来解释、补充或替换原来的文化、语言、文本和能指。”[1]无论是“西学东渐”,还是“东学西渐”,跨文化阐释都是世界文学艺术和文化思想相互交流促进、互构共融的一种有效的策略。李白,作为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诗人之一,他的作品自然是海外汉学家进行跨文化阐释的重要对象。在致力于李白诗歌研究的众多海外汉学家中,美国学者柯睿(Paul W·Kroll)和方葆珍(Paula M·Versano)的研究视角尤为独特——柯睿不仅注重以文学-宗教学跨学科视野考察李白道教诗歌的用语,甚至还以人文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李白道教诗歌意象进行跨文化阐释。方葆珍除了以“以译释义”的方法对李白道教诗歌内涵进行跨文化阐释外,还以“以中释中”的研究方法,分析中国文学和道教传统对李白诗歌的重要影响。他们对李白道教诗歌的跨文化阐释不仅促进了李白诗歌在海外的经典化,还有效地推进了中国道学的西传。
一、学科交融: 柯睿对李白道教诗歌的跨文化阐释
美国唐代文学研究专家、科罗拉多大学波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荣休教授柯睿主要从事中古中国文学、语言、历史和宗教研究。他在对李白诗歌的跨文化阐释中,从中古道教的视野挖掘李白诗歌在用语和意象等方面受到的影响,颠覆了西方世界对李白的一贯认识。柯睿发现在大多数西方学者的研究中,李白通常是一个“自由不拘、生活散漫的醉汉,拥有即席创作赞扬类似‘嬉皮士生活方式的诗篇的才能”的中国诗人。[2]1918年,英国学者弗莱彻(William John Bainbrigge Fletcher)在翻译李白诗歌时对道教内容进行了“文化过滤”。以《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A Song of Lu Shan)的译文为例,弗莱彻将“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译为“Trough Five Sacred Mountains to wander,/In search of some beautiful hill,/No distance could ever yet daunt me/ The joy of my lifetime is still/ Across famous mountains to ramble”[3]。原文中李白不辞劳苦到五岳“求仙访道”的道教徒形象在译文中荡然无存。从译文来看,西方读者能够了解的李白只是一个爱好游览观光,乐于“在路上”的嬉皮士形象。直到2012年,美国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杰罗姆·西顿(Jerome P. Seaton)教授在《明月白云:李白诗选》(Bright Moon, White Clouds: Selected Poems of Li Po)一书中仍然把李白刻画成一个嗜酒的“cowboy-swordsman”(西部牛仔剑侠)。由此可见,一个世纪以来,李白作为“诗人”“酒仙”和“剑客”的形象在西方文化中广为接受,但是他作为“道教徒”的身份却鲜少有人关注。但是,柯睿通过通读李白一千多首现存诗歌和一百余篇散文,发现“李白的很多诗歌都是‘道教的,在严格意义上与道教(Daoist religion)相关”[4]。通过将李白诗歌纳入道教语境和理蕴中细致考察,柯睿深入发掘了道教对李白诗歌的重要影响,深化和补充了西方世界对李白其人其诗的理解。
(一)以文学与宗教跨学科阐释李白道教诗歌语言
在《李白的超越性诗语》(Li Pos Transcendent Diction)一文中,柯睿注意到道教对李白诗歌语言措辞的重要影响。他从李白诗歌与中古道教文书之间的互文性出发,为西方读者恢复了李白诗歌的道教涵义。
以《上元夫人》为例,柯睿先以白话阐释了诗歌的表层意义:“上元是什么夫人?独能获得王母的娇美。高举的和顶上的——她的三角发髻,她剩余的头发松散地垂到腰部。作为外面的披风,她穿着一件绿色的毛皮制的锦缎,身上穿着一件红色寒霜的长袍。她用手引领嬴姓的小姑娘,闲适地与她以箫管吹奏凤凰的叫声。她们以眉毛交流,两个人无拘无束地大笑,接着忽然之间,她们在风的尾迹之中滑翔而去。”[5]接着,他更是从《汉武帝内传》和《茅山志》等道教文献中找到了关于上元夫人的描述:“夫人年可二十余,天姿清辉,灵眸绝朗。服青霜之袍,云彩乱色,非锦非绣,不可名字,头作三角髻,余发垂散之腰际,戴九灵夜光之冠,带六出火玉之珮,垂凤文林华之绶,腰流黄挥精之剑。”“上元夫人服赤霜袍,披青毛锦。”因此,通过比对李白的原诗和这些道教文献,柯睿发现李白关于上元夫人的服饰和容貌的描写明显受到了道教文献的影响。“嵯峨三角髻,馀发散垂腰。裘披青毛锦,身着赤霜袍”中提到的“三角髻”“青毛锦”和“赤霜袍”等用语并不完全出自于李白的个人想象。柯睿为西方读者指出:为了让信徒在个人存想中明确辨认出他遇到的是哪一位神仙,道藏文献细致地列述出了诸位道教神仙的外表,尤其是服飾。因此,在李白描写上元夫人这位女仙时,他别无选择,只能在诗歌里保留下道藏文献里对其外表的描述。
又如,在《登峨眉山》和《颍阳别元丹丘之淮阳》中,李白两次用到了“锦囊”一词。在前者中的“泠然紫霞赏,果得锦囊术”被柯睿阐释为“孤傲淡然,观赏者紫烟,我确然已经获得锦囊小包中的技术”;在后者中的“我有锦囊诀,可以持君身”被阐释为“我拥有锦囊的秘要,其可以用来护持先生您的身体”。对于这个重复出现的选词,柯睿同样以文学—宗教学的跨学科研究进行了追根溯源。最后,他在《汉武帝内传》《茅君传》《洞真上清青要紫书金根众经》等道教文献中找到了类似的表达。根据这些道教文献的记载,西王母拥有的是一个内藏《五岳真形图》的“紫锦囊”。因此,柯睿认为,在第一个例子中,李白“凭借通晓‘锦囊之‘决,才能登上峨眉,领略峨眉崇高庄严的奇景”;而在第二个例子中,“他慷慨地奉献出这些隐秘的教诲,与即将远走的朋友分享,以确保后者自身的安全。”
从柯睿的跨文化阐释来看,他与其他研究李白诗歌的海外汉学家最大的不同在于——在柯睿眼中的李白不是一个典型的“儒家”诗人,甚至也不是一个“道家”诗人,而是一个十足的“道教”诗人。因此,除了以上提到的例子,柯睿还挖掘到以下李白诗歌用语与道教文献的联系:首先,柯睿指出在“朗咏紫霞篇,请开蕊珠宫”(《至陵阳山登天柱石,酬韩侍御见招隐黄山》)中提到的“紫霞篇”其实是喻指《黄庭经》,而“蕊珠宫”则源于《内经》第一章中的内容——“上清紫霞虚皇前,太上大道玉晨君,闲居蕊珠作七言,散化五形变万神:是为黄庭曰内篇。”其次,在解释“清晨鸣天鼓,飙欻腾双龙”(《玉真仙人词》)的含义时,柯睿更是难能可贵地为西方读者指出“鸣天鼓”其实是一种道教信徒在存想过程中的实践:四颗门牙有目的地叩击发出共鸣声以召唤超越性存在的神灵。再次,他还发现在《游泰山六首》中出现的“流霞杯”源于《抱朴子内篇》中的记载;而在《登太白峰》《飞龙引》《上云乐》等三首诗歌中提到的“天关”也有其道教渊源:一部简称为《灵书紫文》的早期上清经有专章讲述“披天关上法”。最后,柯睿还用李白在《奉饯高尊师如贵道士传道箓毕归北海》《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凤笙篇》等三首诗歌中反复使用的“玉京”一词,来证明道教文献对李白宇宙观的重要影响——在灵宝经传统中,太清、上清和玉清被大罗天所环绕。而根据《无上秘要》记载,“玉京山”就在大罗天,因此“灾所可及”。一言以蔽之,柯睿从道教视野出发,精研李白诗歌中的选词与道教文献的联系。他的研究为西方读者了解李白诗歌独特的风格打开一扇新奇的窗口:正是受到神奇瑰丽和飘逸脱俗的道教文献用语和神话世界的影响,李白的诗歌才呈现出豪迈奔放、语言奇妙、清新飘逸、想象丰富、意境奇妙的“浪漫主义”的特色。
(二)以人文与自然科学结合阐释李白道教诗歌意象
在对李白诗歌中频繁出现的“紫霞”“紫烟”或者“紫冥”等意象的跨文化阐释中,柯睿先是以西方自然科学的方法介绍了气象学家所谓的“紫光”这一“非同寻常的、可被科学定义的、但宏伟庄严的大气现象”[6],然后,他又以语文学的研究方法介绍了中文中的“紫”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情感意义,并由此而引发出对于李白诗歌中各种颜色词汇的数据统计。在日本学者花房英树的《李白诗歌索引》的基础之上,柯睿发现李白诗歌中使用最多的颜色是白色,其次是青色、黄色,接着便是紫色。考虑到白色和青色也是杜甫、王维、孟浩然、李贺、卢照邻以及骆宾王等唐代诗人作品中高频率出现的颜色词汇,因此,他认为尽管白色和青色是李白诗歌中使用最多的两种颜色,但它们并不见得是李白最青睐的颜色。接着,通过统计以上诗人对其他颜色的使用频率,柯睿发现只有李白和卢照龄的诗歌中有如此高频率的“紫色”,而且碰巧卢照邻也与李白一样信奉道教。正是基于这种严谨的数学统计结果和李白与卢照邻的巧合之上,柯睿开始思考李白诗歌中的“紫色”与道教之间的密切关联。
柯睿发现李白的诗歌中一共出现了127例“紫色”。而在这127例中,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与“紫霞”“紫烟”和“紫冥”等描述大气或天空的景象相关的。客观地说,无论是“紫霞”“紫烟”,还是“紫冥”,这些物象本身是纯自然的,但是,一旦它们被写进诗歌之后,就被打上了李白的思想烙印。通过对李白诗歌的文本分析,柯睿发现,李白频繁地将“紫霞”“紫烟”和“紫冥”作为一种道教文化符号或者道教意象,以表达自己对道教神仙之境的向往。
比如,在《寄王屋山人孟大融》中,李白写道:“我昔东海上,劳山餐紫霞。”柯睿对此的解释是“我,很久之前,在东海之上,在劳山上服食紫色的霞光”。对于一般的西方读者而言,这样的解释显然只会让他们感到一头雾水;因此,柯睿为之补充了必要的道教常识:李白在服食了“紫霞”之后曾遇到过蓬莱仙岛上的仙人安期生。紧接着,为了避免西方读者对“紫霞”的误读,柯睿强调道:紫霞并不是一种强烈的致幻剂,而是“上清选民的太阳养料”。在道教文献《真诰》中记载了一位被称为“九华真妃”的上清女仙说过的话:“日者霞之宝,霞者日之精。”因此,对于道教徒李白而言,他相信餐食霞光可以强身健体,甚至得道成仙。除了介绍“紫霞”是道教徒修行时服食的“养料”之外,柯睿也注意到它的另一种用途:一种可供攀乘的东西。比如,在“澹荡沧洲云,飘飖紫霞想”(《春陪商州裴使君游石娥溪》)、“我有紫霞想,缅怀沧洲间”(《春日独酌其二》)、“泠然紫霞赏,果得锦囊术”(《登峨眉山》)和“若恋幽居好,相邀弄紫霞”(《送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其一)等诗句中,柯睿为西方读者指出:“对李白而言,‘紫霞象征着那些超越世俗的和在此乏味无光的俗世之上的生命的存在区域。‘道教的实践有助于去往那里。”[7]简言之,对于李白而言,“紫霞”就是他心中所向往的道教仙境,一个理想世界。有了柯睿这些在道教视野下的诗歌阐释,即便是对中国诗歌和道教并无了解的西方读者,也可以理解“紫霞”与“道教”之间的密切联系了。
除了“紫霞”之外,“紫烟”也与道教密切相关。柯睿发现在很多诗歌中,“紫烟”与“紫霞”其实是一种同源物,只是颜色稍淡。出于押韵的目的,诗人有些时候就用“紫烟”作为“紫霞”的替代词。同时,他还敏锐地发现,相比“紫霞”意味着纯粹的道教仙境而言,“紫烟”是一种道教仙境与世俗世界相接时产生的迹象。比如,在《送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其一中,李白写到作为相门之女的女冠李腾空“素手掬青霭,罗衣曳紫煙”。另外,在《明皋歌奉饯从翁清归五崖山居》中,李白见到一位隐士“身披翠云裘,袖拂紫烟去”。然而,通过细读柯睿的论证,读者不难发现,促使他形成这一观点的重要因素是他对光学这一自然科学的了解。柯睿结合了满晰博(Manfred Porkert)在《对中国一些哲学-科学基本概念及关联的研究》(Untersuchungen einiger philosophisch-wissenschaftlicher Grundbegriffe und Beziehungen imm Chinesischen)一文中提出的观点,[8]解释道:“想象光谱是一条线或者弧(例如,一道彩虹),红色和蓝色位于相反的两个位置(头和尾)。将之看成一个圈,红和蓝便毗邻紧贴。因此,连接它们的紫色,是‘宇宙整体或者全体,是毫不衰退的力量,因此也是复归的统一体,回归宇宙之道的色彩艳丽的本质。”[9]
又如“驾鸿凌紫冥”中的“紫冥”也是一个非常生僻且富于道教内涵的词语。柯睿认为“冥”实际上暗指“投下黑暗的、黄昏暮色的、昏暗深邃的光……在道教语境里,紫冥指凡夫肉眼无法看到的国度。这一图景所暗示的是凡人或俗人的视角”[17]。方葆珍将“驾鴻凌紫冥”译为“Riding a wild swan to mount the purple dark”,从一方面突显了道教神仙世界的神秘性和超越性;从另一方面,则提醒读者注意到其虚无缥缈、难以捉摸的特质。
方葆珍对李白诗歌的翻译非常注重保留其道教内涵。她以翻译为手段对李白道教诗歌的跨文化阐释,为李白诗歌和中国道教在英语世界实现正向传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二)“以中释中”阐释李白道教诗歌神仙形象
除了翻译李白《古风五十九首》的多首诗歌之外,方葆珍还对这些诗歌做了必要的阐发。她将李白的道教诗歌放置在中国诗歌和道教的传统中,引发西方读者思考这些诗歌中的神仙形象所承载的李白的道教信仰。
比如,在方葆珍对《古风》其七的分析中,她认为李白微妙而有效地两次变换了讲述者的身份。第一次是从“客有鹤上仙,飞飞凌太清”里呈现的中立的为神仙作传的作者身份,转换为“扬言碧云里,自道安期名。两两白玉童,双吹紫鸾笙。去影忽不见,回风送天声。我欲一问之,飘然若流星”里呈现的神迹见证者身份,然后再从见证者身份转换为在“愿餐金光草,寿与天齐倾”中呈现的毫无机会得遇仙人的普通凡人身份。诗歌的主体部分是李白以目击者身份对神仙世界的精细描述。在一篇名为《由此及彼:寻找早期中国诗学中的主体》的论文里,方葆珍曾谈起过她对中国诗歌的印象:“在中国,自然景物本身就是一张纵横交错的网,交织这普遍的和个人的感受以及语言的和视觉的暗示。当诉诸语言时,这些景物反映出诗人瞬间的情思和内在的天性。”[18]因此,在方葆珍看来,李白诗歌中描述的见证者在神仙世界中看到的“碧云”和“流星”当然也不仅仅是自然景象,而是诗人情思和内在天性的反映。那么,“碧云”和“流星”到底反映了李白什么样的情思和天性呢?方葆珍并没有立即在文中给出答案,而是转而分析了这首诗与中国以“游仙”为主题的诗歌传统的关系,以及诗中“安期生”这位道教神仙在中国道家和儒家中的形象。
首先,方葆珍认为《古风》其七深受屈原《九歌》游仙诗的影响。尤其是李白以第二个身份进行叙述的部分可以明显地唤起人们对《九歌》中的“萨满”(shaman)的回忆。在《九歌》中,萨满也是有幸短暂地一睹神仙的真容,然后无助地眼看着他们凭空消失。在最后一联中,李白又一次变换身份,以“顿呼”(apostrophe)的形式直接向读者发言,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于长生久视的向往。无论是将《古风》其七纳入游仙诗的范畴,还是指出李白对于永生的渴望,方葆珍都在尽力引导西方读者思考李白的宗教倾向。其次,对于诗歌中将“安期生”作为李白表达神仙向往的对象,方葆珍考据了《列仙传》对安期生的记载,向西方读者介绍道:安期生在秦朝时期卖药于东海,秦始皇与他交谈三日三夜。以后他邀请秦始皇数年后到神仙居住的蓬莱山去寻访他。但是,后来据秦始皇派出的使者报告,他们在海上遭遇到巨大的风浪却没有到达蓬莱仙山。除此之外,她还介绍了司马迁对这个故事的记载,并指出司马迁增加了关于安期生“合则见人,不合则隐”的性格特点。正是基于这两处中国古典文献的记载,安期生在中国化身为一个理想的儒家和道家的混合体;因为无论是从儒家的还是道家的立场来看,他坚定拒绝服务暴君秦始皇的行为都是值得赞扬的。至此,方葆珍通过阐释《古风》其七,水到渠成地引导西方读者认识到李白创作这首以“古风”为体裁,以“游仙”为主题的诗歌的动机:通过不同身份(诗人、目击者、凡人)的视角描写道教神仙和神仙世界,表达诗人(李白)关于道教理想的坚定信念。
从以上内容来看,在分析李白的《古风》其七时,方葆珍并不是一味采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术语和方法“强制阐释”李白诗歌的道教内涵,也没有通过解构、变形、过滤李白诗歌中的道教内涵来适应西方读者的“前理解”。相反,她是通过将李白的诗歌放到以楚辞为代表的游仙诗传统、以《列仙传》为代表的道教传统和以《史记》为代表的儒家传统中进行解读,在中国的文学传统和文化视角下对李白诗歌进行生命体验和资料考据并重的跨文化阐释,最后使李白的道教思想倾向得以彰显。对于西方读者而言,中国道教的教义、仪式、神仙信仰和宗教理想与其本土宗教迥异。如果要令西方读者真正理解李白的道教诗歌和接受他作为“道教诗人”的新形象,阐释者就务必需要扩充西方读者对中国道教文化的了解。圆凿方枘,固会龃龉而难入;但如果榫眼够大,榫头的进入便自然不会有不适。为了扩充西方世界对李白、对道教、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方葆珍曾于1983年作为同济大学的美国高级进修生前往李白的多处遗迹,考察其行踪和思想来源。她对中国语言文学的精心专研,加之能结合其在中国的广泛的“田野调查”,这便为“以中释中”阐释李白道教诗歌奠定了基础。
三、结论
对李白诗歌的跨文化阐释热潮在海外汉学中经久不衰。许多学者都曾尝试以不同的视角和方法来阐释李白诗歌,以帮助这位中国的“诗仙”在英语世界获得“来世生命”。但是,由于中西文化模式的巨大差异,李白创作的那些与道教相关的诗篇在跨文化阐释过程中却常常陷入“南橘北枳”的窘境。为了减少李白道教诗歌进入异域文化的阻力,不少海外学者曾经采取“削足适履”的办法,以变形、扭曲、过滤的阐释方法,改变李白道教诗歌的原貌以期获得西方读者的认可。但是美国学者柯睿和方葆珍却独树一帜,采用了学科交融和译释结合的阐释方法,最大化地保留了李白诗歌的道教内涵,形塑起李白作为“道教诗人”的形象。他们对李白道教诗歌的跨文化阐释不仅促进了李白诗歌在海外的经典化,还有效地推进了中国道学的西传。由此可见,学科交融和译释结合的跨文化阐释是助推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的有效策略。
注释:
[1]李庆本:《跨文化美学:超越中西二元论模式》,长春出版社2011年版,第196页。
[2][4][7][9][10][17]柯睿著,白照杰译《李白与中古宗教文学研究》,齐鲁书社2017年版,第8—9、21—37页,第3页,第69页,第59頁,第72页,第71页。
[3]W. J. B. 弗莱彻:《英译唐诗精选》,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年版,第18页。
[5]Kroll, Paul W.“Li Pos Transcendent Dic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86 (106):99-117.
[6]Kroll, Paul W.“Li Pos Purple Haze”.Taoist Recourses, 1997 (7.2):21-37.
[8]Porkert, Manfred. “Untersuchungen einiger philosophisch-wissenschaftlicher Grundbegriffe und Beziehungen imm Chinesischen”.Zeitschf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t, 1961(2): 439-440.
[11]Versano, Paula M. Tracking the Banished Immortal: The Poetry of Li Bo and Its Critical Recep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179.
[12]王宁:《翻译与跨文化阐释》,《中国翻译》2014年第2期,第5—13页。
[13]王承文:《中古道教“步虚”仪的起源与古灵宝经分类论考——以<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为中心的考察》,《中山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73—95页。
[14]Schafer, Edward. Pacing the Void: Tang Approaches to the Stars.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15]Owen, Stephen.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134.
[16]Schipper, Kristofer. “A Study of Buxu:Taoist Liturgical Hymn and Dance”. Tsao Pen-Yeh & Daniel P.L.Law ed. Studies of Taoist Rituals and Music of Today,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1989:110-120.
[18]方葆珍、张万民、张楣楣:《由此及彼:寻找早期中国诗学中的主体》,《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三十五辑)——中国文论的思想与主体》2013年第4期,第20—43页。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四川李白文化研究中心“基于李白诗歌的中国道教文化海外传播”(LB20-B05)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5批面上资助课题“唐代道教诗人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影响研究” (2019M65347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教授
四川省社科院与四川大学联合培养在站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