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生产中的《兄弟》
2021-03-10冯玉华
冯玉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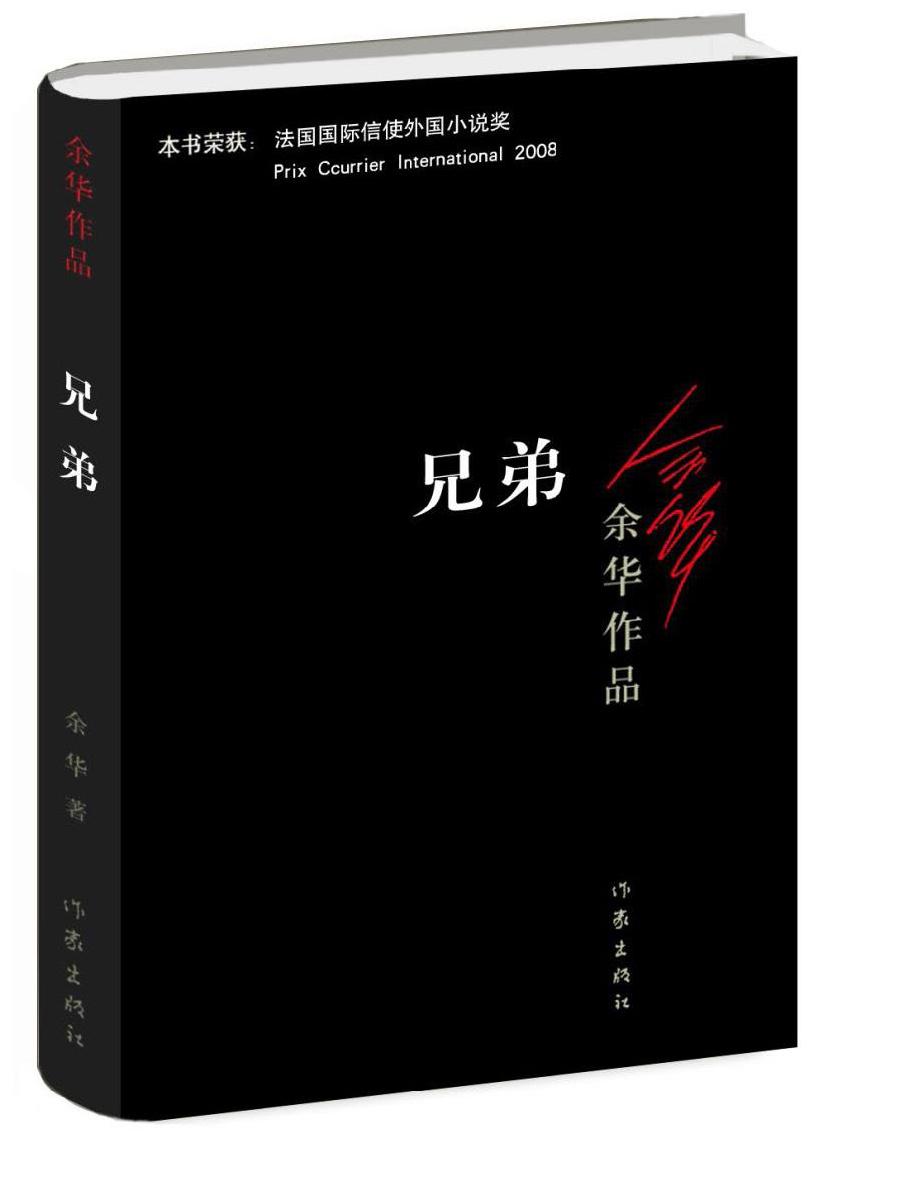

摘要:在社会形势不断变化的背景下,我国文学生产机制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变化,《兄弟》作为余华于200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从侧面印证了生产机制变化对文学造成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通过对文学生产相关内容进行调查,重点探讨当代文学生产中的《兄弟》,从商品化生产背景和文学生产背景两个方向分别分析,以供相关人员参考。
关键词:文学生产;兄弟;商品化生产背景
《兄弟》这部长篇小说是著名作家余华在两年时间里推出的作品,向读者展示了当时的环境并使用狂欢式的写作手法勾画了社会众生相,受到了读者的喜爱。但在此过程中,主流文学界却对《兄弟》进行批判,这与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具有直接关系。
一、文学生产相关概述
文学生产主要是指一种物态化生产,通过将作家创作的文本以物质载体的形式变为文学读物的生产。不同于文学创作,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生产,是一种创造性活动,而且,文学创作的主体是作家个人,需要大量的物质基础,受外界打扰较少。但是,文学生产是一种社会性集体活动,组织机构是开展该活动的必需条件之一,在文学生产过程中涉及出版环节,且受社会因素和物质因素的双重影响。
二、探讨当代文学生产中的《兄弟》
(一)当代商品化生产背景下的《兄弟》
《兄弟》是当代作家余华创作的长篇小说,于2005八月首次出版,共分为上、下两部,2008年,《兄弟》获第一届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但在《兄弟》出版起,外界对其的态度使得该小说长期处于争议之中,形成该争议的主体分别为主流批评界和读者市场,前者主要对《兄弟》进行批判,而后者则是接受,但不可否认的是,自出版至今,其销量已高达百万册,而形成如此矛盾局面的主要原因即当前的商品化生产背景。“出版”是连接作家与读者、市场需要与文本制作之间的中介,是整个文学生产流程的核心。《兄弟》文本是文学生产结果,但在对其进行理解时,主要是对叙事所表达意蕴的理解,这需要透过成形的文本进入文本诞生前对《兄弟》进行解读。实际上,《兄弟》成为破百万销售量的畅销书并非偶然结果,它不仅蕴含着余华个人精神活动的成果,更是作者与出版方、市场博弈的结果。在有关《兄弟》的争议出现后,余华一反常态,不仅接受媒体采访,还将《兄弟》称为自己写过最成功的作品,而这制造出了很难一言以蔽之的文学现象,但从实际批判和争议来看,在对作品进行解读的基础上,还涉及余华的影响力。在该长篇小说创作以来,由于余华自身影响力,以及于2004年与上海文艺出版社签约,使得其成为签约作家,而该举措在文学市场以及业内造成很大反响。主要是因为该举措打破了以往传统观念中出版社与作家之间互相独立的关系模式,在以往关系中,作家是不受物质制约的,为此,其作品往往具有“纯粹性”和“独特性”的特点,可以说,是超越物质、现实的精神支点。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文学出版主体由国家所有和管辖,相对于文学出版最终获得的经济效益,其更加注重出版文学传达的思想观念,并非以物质利益为出版前提。在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文学出版体制改革,涌现出以稿酬为生的专栏、职业作家,商业化特征与生俱来,这导致这类作家被划分为“通俗作家”,其创作的文学作品与纯文学不同。而在余华成为签约作家后,打破了“通俗作家”与纯文學作家之间的界限,这便是出现争论的原因之一[1]。
上海文艺书版社总编曾谈到过,“余华是一名实力派作家,更是年轻读者的偶像。”余华的影响力主要产生于《活着》,该篇小说的影响力奠定了余华在文学市场中的地位,从出版社的角度去看,出版社在注重余华实力的同时,更为注重的是余华的市场影响力和号召力。由此可见,在当前市场背景下,文本所具备的文学性与市场性存在矛盾关系,从现状来看,“原创+实力+营销”是成为畅销书的三元素,但实际上,这是一种理想的畅销书运作模式,但是,出版社正是看中了余华《兄弟》这篇小说潜在的市场影响力,在以《兄弟》为核心而展开的运作,是双方合作的市场操作行为。简单来说,对于出版社而言,通过对成名作家进行签约,能够对作者作品进行垄断,进而能够更加宽泛地选择并制作畅销书,同时也可以要求作家进行营销配合,《兄弟》即其中之一;对于作家而言,与出版社合作能够扩大读者群以及获得市场回报。
不仅如此,在《兄弟》这一长篇小说出版后,以该小说为核心出现的文学市场现象中,引起广泛关注的因素之二是版税。《兄弟》自2005年出版以来,于2006年其销售量就已经近百万册,余华曾说过,2006年是他创作生涯中收入最高的一年,上海文艺社支付的版税就已经超过了一百万。在商品化生产背景下,《兄弟》成为百万畅销书的原因之一是开展了大量的媒体宣传和巡回签售等活动,通过对《兄弟》进行营销和运作,在短时间内就凝聚了极高的市场人气,成为读者关注的热点事件。而在该情况下,《兄弟》不仅成为畅销书,连带余华创作的其他文学作品以及出版社都获得了极高的人气,出版社因而成功打造了自身的品牌形象。《兄弟》分为上、下两册分别出版的目的则是深入到文本内部进行的一场品牌营销活动,而《兄弟》就是这场营销活动中的核心品牌。在此过程中,出版社以“未完待续”的方式给读者带来心理期待,给营销成功奠定基础,而余华作为将“文革”背景下的故事描写的深入人心的作家,读者会对以“文革”为背景的《兄弟》具有极高的期望和兴趣,上下册的分开出版则加剧了这份期待,进而形成热点话题。连续不断的话题炒作使得读者以及媒体都十分关注《兄弟》下册,也进一步带动了《兄弟》上册的销售量,在上、下册互相刺激的情况下,《兄弟》成为百万畅销书[2]。
(二)文学生产背景下的《兄弟》
如上所述,文学生产包含着作家叙事意蕴以及意识形态,余华在对《兄弟》这一长篇小说进行创作时,由于其签约作家的身份,在其具有作家这一身份的同时,也在《兄弟》中附着了一定的营销性质。具体体现为余华认为《兄弟》分为上、下册出版是正确选择,在《兄弟》出版后引发的众多争议中,最大的争议即分册策略。主流文学评论家曾说过,“文学作品如产品一般,可以分批生产,一部长篇小说竟然可以人为地被腰斩为两部分而分次出版,《兄弟》的出版完全是充分准备之后‘做出的畅销书写手。”在主流文学界来看,《兄弟》的分册出版无视了文学的创作规律,是一个生硬的、为了营销宣传的市场举措。但是,分册出版并非仅仅取决于作家或是出版社,更取决于《兄弟》这一小说的内容表达,以及对《兄弟》意蕴传达的作用,这与作品内容具有极强的密切联系。
余华在《兄弟》封底写下这么一段话,“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连接两个时代的纽带就是这兄弟两人”,由此可见,余华在创作《兄弟》时,其写作立场十分明确,通过有意识地将两个时代进行连接,完成逻辑对应的同时也揭示了分册出版的原因。而这需要明确余华的创作初衷,余华坦言,1995年就开始了《兄弟》的创作,但由于1995年的中国与过去的中国变化太大,使得《兄弟》创作中断。但在其接受欧洲记者采访时,余华从这位记者对中国时代变化的提问中找到了《兄弟》的创作思路,这就是《兄弟》曲折的创作背景。如果余华所说为其真实想法,这意味着余华不想沿着世俗口味一路写下去,进而做出了具有自己想法以及带有批判含义的判断。
从《兄弟》文本内容中人物命运来看,李光头象征着那个时代的世俗欲望,在作者的叙述过程中,没有对其进行批判和讽刺,更多的是对李光头的默许和无可奈何。纵观李光头的一生,李光头成功树立了自己“成功人士”的形象。在人性如此复杂的李光头这一角色身上,作者通过有意无意地表现“存在即合理”这一理念对李光头的人性、行为进行解释,对其欲望进行回避。以《兄弟》这部书中的某一情节为例,在对十四岁的李光头因为偷看林红屁股而被抓住游街这一情节进行处理时,作者没有对李光头人性中的恶进行深化,也没有将其作为切入点对人性黑洞进行演绎,而是通过强化李光头无赖、泼皮的特质,将一件原本十分羞愧、为人所不齿的事情理直气壮地转化成一场交易,换来了五十六碗三鲜面。而且,在与李光头交易的世故,居然还是一些体面的人,赵诗人、刘作家等,在该情节的描写中,将具有悲剧性的事件转化为具有荒诞性质的喜剧情节,通过李光头与前来交易的人的对比,相较于真小人,交易的成人则向读者显示了另一方面的丑陋。由此可见,在余华强烈的荒诞意识下,大部分读者不会对人性进行深层思考和探讨,在戏谑的情节中,只是留下了当街游行的反省空壳,这不仅塑造了人物形象,还兼顾了大众的阅读心态。不仅如此,在对该情节进行描述时,其使用的叙事角度是“我们刘镇”,没有将叙事者指出,但其强烈的存在感给读者带来了当下的鲜明气息,也就是通过充满欲望信息的众生相对该情节进行描述,使读者带着“我们刘镇”的视角看待整件事情,让读者体会特有的世俗气息,直观地看到刘镇上的丑闻、暴力、绯闻等奇闻逸事,并将作者的价值期盼以原生态的方式呈现给读者[3]。同时,余华最擅长细节描写,当其对暴力、罪恶等场景进行描写时,在“我们刘镇”的视角下,那些场景只是场景,也许惹人流泪,也许惹人发笑,但这仅是供人观赏之后的结果反应而已,在该视角下,不可能产生超越刘镇这个故事的反思,也不可能产生另一种理解历史的方式,读者仅仅是以一种参与者的方式对《兄弟》进行阅读和理解。在该情形下,人性的洞察与批判转变为对现实戏谑式的宽容。正是在该叙事方式下,当“我们刘镇”这一视角结束后,出现独立声音对整个事情乃至时代进行评判时,群众运动消解个体存在这一意义的现实立场和价值会被取代,进而成为《兄弟》这篇小说的主旨。因此,在该层面上,这部小说将过去几十年来中国人百感交集的复杂经验简化为善与恶的斗争,隐喻着那个时代下人性的迷失与这个时代下人性的复归[4]。
当大众对一件事情和现象进行批判时,其标准大多为道德伦理,虽然是最为有效的一套标准,但在《兄弟》这篇小说中可以看到,即便是最为简单的善与恶之间的斗争,也出现了断裂。具体而言,在《兄弟》上册中,余华将对那个时代的批判和评价渗透到文章中,并将暴力、心灵折磨、饥饿以及殴打等常规意义上的恶进行描述,呈现给读者。相应的,凸显出来的善也是常规意义上的善,有宋凡平带来的家庭温暖亲情和正常伦理,也有李兰的羞耻感以及苏妈扶危济贫的正义举措等,这些均在伦理范围内。但是,在《兄弟》下册中,无论是表达出来的恶还是善都出现了极为明显的变化,在金钱最大的时代下,直接可以获得金钱的行为代表着“善”,在该情况下,“善”与“恶”的界限逐渐模糊,并在李光头成功后将其渲染成为“成功人士”,暗示在该社会语境下,这种“恶”是被允许的,是受推崇的,这与《兄弟》上册中善与恶的简单对峙形成了强烈反差,这使得《兄弟》叙事立场出现断裂。而恰是在该情况下,读者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叙事者的随波逐流,当读者習惯余华以生活经验创作作品、塑造人物行为逻辑时,却从《兄弟》感受到余华作为后时代人的优越感。如果说在《兄弟》上册中还能够感受到余华以小人物的悲惨遭遇对大时代背景进行反讽的意味的话,那么《兄弟》下册很明显与物质利益为上的价值观念进行呼应。但从该情况来看,《兄弟》分册出版并非如作者原先预想的“两个时代的连接”,若是站在精英文学的角度来看,《兄弟》的断裂仍是败笔,若是从文学市场的角度来看,将纯文学去掉,那么在对《兄弟》进行批判分析时则需要从另一种角度以及方面展开[5]。
若是联系当代文学生产机制,那么能够理解《兄弟》中叙事角度的转变,但是从读者与余华之间的交流中可以明确发现,大部分读者不在乎余华投放在《兄弟》中的个人想象,由此可见,对于大部分读者而言,其寻求的是一种自我认同,为此,更加关注那些事件是否符合自己“真实”的记忆,导致超脱于常规情感范围外的立场会被批判,这也是主流文学界与读者发生矛盾、对《兄弟》存在争议的原因之一。当余华的《兄弟》与当代文学生产机制进行联系,其分册出版的原因则显而易见,即《兄弟》立足于市场,余华以“庸人”的姿态对时代进行判断甚至是批判,但在社会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徘徊在善与恶的边缘,《兄弟》上、下册各反映了当前时代人的挣扎。从这个角度来看,《兄弟》的分册出版一方面可以视为两个时代的割裂与变化,另一方面则是余华通过这个方式直接告知自己的写作姿态,那就是自己并没有扮演文学创作作品中的救世主,而是将欲望化行为变为一种合理的方式,虽然与“庸人”立场相矛盾,但又可以共存,响应《兄弟》下册各隐约透露出来的“存在即合理”,那么,分册出版则是迎合了当前时代下大多数人生存观念的尝试。由此看来,这部长篇小说的成功是作者、出版社以及读者共同打造的一种文化商品,不仅立足于市场,还具有十分清晰的市场定位,通过辅以完善的市场营销和推广,迎合了读者的阅读兴趣,进而最终形成极大的市场影响,使《兄弟》成为百万畅销书。但是,这并不意味《兄弟》是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只是社会形势的变化使得分析《兄弟》的角度更加多样化,单一的指标不是评判一部作品是否成功的硬性标准。不可否认的是,以往纯文学的评判方式已经逐渐不适用于当前时代,需要立足于实际情况,构建符合当下文学生产现实的评判体系,既避免纯文学的虚空高蹈,也避免来自部分读者固执的立场批判,而这应该是文学生产中的《兄弟》给当下最大的启示。因此,即便主流文学对《兄弟》进行批判,发出捍卫纯文学的呼声,但这种呼声也会被这个时代转化为“流量”,作为这本畅销书营销策略的一种,形成单纯意义上的市场炒作。而在日后发展过程中,这种畅销书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因此,在面对这种情况时,期望能够构建一种以作品文本为基础的批判方式,使批判更加具有力量[6]。
三、结语
文学生产中的《兄弟》不仅具有传统意义上纯文学的特质,其分册出版还具有极强的商品性质。因此,当文学批判已成为市场营销、推广、炒作的一种被动手段,亟须立足于实际情况构建适合当前时代的批判方式,从而真正做到对文本的批判。
参考文献:
〔1〕刘中望,费振华.论余华小说《兄弟》的接受及其异质性[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4(5):78-85.
〔2〕郑贞,张韵菲.余华《兄弟》中暗喻的翻译研究[J].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18(2):28-32.
〔3〕邱岚.余华:历史与现实交织下的人性探寻[J].汉语言文学研究,2020,11(2):114-120.
〔4〕吴景明.从“形式先锋”“民间生存”到“社会现实”——余华小说创作转向论[J].当代文坛,2019(4):48-55.
〔5〕李冰洋. 余华《兄弟》主题意蕴研究[D].延吉:延边大学,2019.
〔6〕贡卫东,赵淼.余华长篇小说《兄弟》中重复格的翻译研究[J].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16(4):43-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