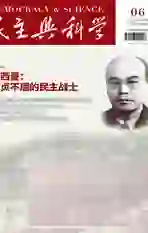桃蹊李径十年灯
2021-03-09李醒民
读者从本书中文版的序言不难看出,皮尔逊是英国著名的哲人科学家和自由思想家,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这样的学人在学科分化日益加剧、各个知识部门老死不相往来的当代实属凤毛麟角。他在科学与人文的交叉领域致力良多,研究深广,成果卓著,影响远播。他的《科学的规范》[1](The Grammar of Science,1892)和《自由思想的伦理》[2](The Ethic of Freethought and Other Addresses and Essays, 1888)的中译本已由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他的《死亡与进化》中译稿于近日完稿,不久即将付梓。
《死亡与进化》原名《死亡的或然性和进化的其他研究》(The Chances of Death and Other Studies in Evolution),该书分一、二两卷,于1897年出版。第一卷收录八篇文章。其中“死亡的或然性”是作者1895年作为讲演稿在利兹文哲会宣讀的,它探究了中世纪的死神之舞的来龙去脉及死亡与或然性(机遇、命运)的关系,对死亡做了概率的和统计的分析。“蒙特卡洛轮盘赌的科学方面”(1894)是对赌博中的概率研究;作者认为,或然性等价于知识,而不等价于无知,科学的或然性概念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度量概念,是用许多事件的平均结果的知识代替对任何个别事件的结果的无知,因此科学有权进入像蒙特卡洛这样的或然性的殿堂。“生殖选择”是新写的,作者不满意关于社会问题的作家,他们以不严格和非科学的方式把诸如自然选择、遗传和随机交配等从科学中来的术语用于社会进化阶段,而对影响人的社会进化的各种因素却缺乏适当的数量权衡。“社会主义和自然选择”(1894)是对基德在《社会进化》中所表达的观点的反驳,作者在论证后,“大胆地做出下述确定的陈述”:
在精确地断定作为进化论而含糊地聚集在一起的各种事实的定量意义和数值关系之前,关于文明人社会的成长,没有什么可靠的论点能够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上。进化论在它的新基础上再调整之前,我们对这些问题必定依然一无所知。[3]
《政治和科学》(1894)一文批评了索尔兹伯里勋爵1894年在牛津的科学促进协会的主席演说;作者注意到,科学人习惯于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做他们自己的工作,而不关注知识小角落之外的政治和社会思潮的运动;有人虽有精确概览科学全貌的能力,但他们人数甚少且常常缄默不语;作者倡导做像赫胥黎和克利福德那样的科学家,既有广阔的科学视野和发言能力,又能把握科学进步与他们时代的社会运动的关系。他的下述话语掷地有声,发人深省:
一句话,从社会的观点看,虽然科学在其最真实和最广泛的意义上的普及是对科学的十分充分的辩护,同时也是对科学完全必要的辩护。不幸的是,科学人受到他们自己在无知莽丛漆黑一团的幽深处特地猎取真理的激励而失去自制力,太易于把大众视为必然无知,把普及者视为必定浅薄——尽管实际上并没有视其为十足的江湖骗子。江湖骗子有时依然活跃,这主要是由于忽略真正的研究者和学者——他破门而出,展示他的货物比市场人(the man of market-place)的货物多么经久耐用。并非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在人民中间发出声音”,但是在年青一代中,迄今没有一个稳健站在自然哲学家前排的人被人民理解,则是科学软弱无力的表现。在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够作为科学的追随者和日益成长的民主之间的调停者发挥作用。请牢记,民主是欧洲在一个世纪目睹的巨大工业危机和广泛达到的社会激变的产物;它的成长正在包含并必定包含在每一等级的阶层与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关系中的几乎革命性的变革。[4]
在《反应》(1896)中,作者严肃地批评了鲍尔弗的《信仰的基础》:他简要地阐述了他关于科学的基础的观点,论证了科学与神学、知识与信仰的含义和关系。接着的《妇女和劳工》(1894)探讨了两个现代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妇女问题和劳工问题:它们以显著的、几乎还未被充分评价的方式交织在一起,构成现代思想的基石,并在形形色色的形式下隐蔽着现代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的因素。新写的《在男人和女人中的变异》中则寻求回答这样的问题:测量男人和女人相对变异的最合适的器官和特征是什么?如何科学地测量变异?第一卷的最后是《附录:宗派的批评》(1895),作者如下定义:
宗派批评家是被他自己的信仰,或者宁可说被他的宗派的信仰冲昏头脑的人,以致他面对他所批评的那些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拒绝他们独有的每一个特征。被批评者可能一次又一次地宣称,他们坚守如此这般的观点;没有关系,宗派批评家则坚持,他们一定持有某一见解,他作为批评家通过把这一见解批得体无完肤而宽慰他自己的良心。[5]
皮尔逊当然不会把自己计入“宗派批评家”之列的,他在上述三篇批判文章及附录中也许正是把矛头对准他们,“力图捍卫近代科学,以回应伪科学的、政治的和神学的批评家最近发起的攻击”[6]。皮尔逊的儿子、统计学家伊冈在其撰写的皮尔逊传记中这样描绘道:厉害的K. P.(卡尔·皮尔逊姓名简写) 其人再次操起他的长矛,在理性事业中反对用科学的外衣伪装起来的新顽固和新偏执。皮尔逊的斗争勇气像通常那样与下述信念结合在一起:他面对的观念是误入歧途的和倒退的;它们可能具有的有害影响更加危险,因为它们似乎是由权威支持的;因此,不遗余力地使这样的说教丧失信誉正是他的责任之所在。[7]
在第二卷中,共收集了四篇文章。在这里,皮尔逊重返关于德国早期史和民俗学的研究。他在兴味盎然地阅读了德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格林和其弟威廉·格林的著作后,告诉他的小女儿,他要科学为这样的智力漫游和消遣挤出时间。就这样,他以“作为女巫的女人”为题于1891年在萨默维尔俱乐部发表讲演,探讨了中世纪巫术习惯中的母亲权利的证据以及女巫角色的演变。它向我们表明:
道德和社会建制对每一个阶段和每一个文明都是独特的;它向我们表明,成长即使不是十分疾速的,它也一直是连续的。它教导我们,那些空谈绝对好的和绝对坏的以及不变的道德准则的人,可能有助于管理现有的社会,但是他们不能改革它。成功地发动改革需要历史精神,也就是这样的概念:社会建制无论多么历史悠久和神圣,无非只有相对的价值,永远需要调整它们本身,并且是可以自由调整的,以便适应社会成长的需要。[8]
新写的《阿西贝托:或汉斯寻找他的运气》是德国早期婚姻制度的研究和诠释。“亲族群婚”起初作为一篇论文在1885年宣读,在第二卷中首次发表。这是一篇关于原始婚姻和性关系的长篇研究,作者立足于一个基本的人类学原则和比较语言学诠释方法:对原始人而言,行为的主要动机是对食物和性本能的欲求;因此,早期的关系词汇的意义必须在它们的负荷者性功能——所有观念中最原始的——中去寻找,而不必在他们家庭的或部族的活动中去寻找。这篇论文分三部分展开:母亲时代的文明,关于性和亲属关系的一般词汇,关于性和亲属关系的特殊词汇。不难看出,这实际上也是远古语言的钩沉和勾稽。《德国的耶稣受难复活剧:西方基督教进化研究》是从1883年关于中世纪德国文学的系列讲演中抽取出来而首次公开发表的,它集中论述了这种剧目的统一性、精神、成长、舞台及其道具、人物塑造、表演者、内容。这篇论文以耶稣受难复活剧为主线和背景,全面勾勒了德国中世纪的社会生活和庶民情感,描绘出一幅栩栩如生的民间风俗画。皮尔逊在这项艺术史研究中像迪昂[9]在中世纪科学史研究中一样(比迪昂早二十余年),批驳了中世纪是“黑暗世纪”的神话:
那些称中世纪是“黑暗时代”的人只是表明,他们因自己的无知正在忽略像古希腊文化本身一样伟大的因素。他们因盲目的偏见正在把大部分生来就有的权利推到一边,这种权利是过去诸多世纪的人为未来许多世纪的人赢得的。文艺复兴应该教导人们理解希腊思想,这一点完全达到了,而它竟然促使他们鄙视中世纪,这一点则完全是损失。今日,我们确实足以相信我们从迷信中解放出来,从而力图正确评价二者。我们不可能比崇拜希腊诸神那样更多地再次崇拜中世纪的神祇。[10]
第二卷之后有四个学术性很强的附录,它们是:“五朔节采邑”与“少男和少女夜间幽会”,英国16世纪的教会剧,论“耕种”的性含义,论法庭和合作社。尽管《死亡的或然性和进化的其他研究》一书的材料内容五花八门,思想异彩纷呈,但它们却贯穿着一条主线,这就是皮尔逊在“序”中点明的:
肆力把所有现象——物理现象和社会现象——视为关联的生长,并用尽可能简洁的公式把它们摹写为这样的。在不断言进化能够说明任何事物,但是当我们拥有现象的经验时,却接受进化是摹写它们的序列的最宝贵公式的情况下,理性论者现在拥有相当坚不可摧的堡垒,以抵御每一类型的极端保守分子。他未被要求证明,进化说明宇宙;他可以使自己满足于仅仅质疑他的批评家,以便在摹写我们关于现象联结的经验时,提出如此有用的任何其他公式——如此显著地使思维经济的任何其他公式,或者换一种不同的说法,如此充分地实现科学要旨的任何其他公式。[11]
我是从1970年代末开始准备硕士论文《彭加勒与物理学危机》[12]时接触皮尔逊的论著的,在1980年代末做了初步研究,先后就皮尔逊的生平和工作、科学哲学、科学观发表了三篇论文[13]。1990年代中期,我应《世界哲学家丛书》主编傅伟勋、韦政通之约,拟为台北三民书局撰写《皮尔逊》。为此,我尽可能收集了皮尔逊的有关论著以及与之相关的研究资料,其中包括皮尔逊的三种名著《科学的规范》《自由思想的伦理》《死亡的或然性和进化的其他研究》。在研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深入思考,《皮尔逊》一书终于在1998年1月杀青,随即在同年10月顺利出版[14]——恕我孤陋寡闻,这本书在当时、也许乃至现在,依然是学术界全面研究皮尔逊思想的唯一专著。翌年,在研究期间顺便译就的《科学的规范》也得以面世。本来,在《皮尔逊》的手稿中,我还探讨了皮尔逊的社会哲学思想。无奈,因一向大度、宽容的主编傅伟勋不幸于1996年去世,三民書局编辑按照丛书体例,要求书稿不能超过20万字(其实,此前出版的《马赫》[15]、《迪昂》[16]、《爱因斯坦》[17]均超过此数目),作者只好删除原有的三章(社会学说和历史观念,社会主义和妇女解放,自由思想和研究的热情)。此后多年,这些内容以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18]
由于我专门研究过皮尔逊,对他的生平、工作和思想比较熟悉,遂有意把他的几本主要著作翻译出来,呈现给国内学术界。在《科学的规范》出版后,我于2013年7月翻译完《自由思想的伦理》。眼下的这本译著,从2017年春动笔移译,中间有所中断,直至数天前才译毕,延续了将近两年时间。本书内容之丰富、思想之新颖、研究方法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对此,读者只要稍加浏览,不难了然于心。与此同时,读者也很容易发现翻译本书的难度——尽管译者已尽力而为,唯恐仍有疑窦之憾,切盼译界解牛之庖丁、斫轮之轮扁指点迷津、匡谬纠误。
“超凡脱俗只有两条路:诗和哲学。”[19]这是德国古典哲学家谢林的至理名言。确实,哲学(包括曾经作为自然哲学的科学)是人类思想峰巅的灯塔,诗是人类精神皇冠的明珠。哲学是理性纵横驰骋的结晶,诗是情感恣意勃发的写照。人最伟大的东西,莫过于思想和情感。思想是人之为人的终极标志,是人高于一切物种的神圣性之所在,是人的尊严的全部体现,是人的不朽的唯一依托。当然,我们也不可低估情感的力量:它是意志的催化剂,是行动的原动力,也是认知的官能和思想的源泉。
先说哲学和思想。意大利哲学家、人文主义者皮科·米兰多拉在其作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宣言”的论著中大张旗鼓地为哲学辩护,发扬光大哲学的思想价值。他钩沉稽古,发微抉隐,而且妙语连珠:
事实上,现如今的哲学研究总体上是遭人嘲笑和蔑视(这是我们时代的不幸!),而不是受人尊敬与荣耀。所以,那种毁灭性的古怪论点几乎侵占了所有人的心灵,即要么没有人要么只有极少的人会研究哲学。就好像把事物之因、自然之道、宇宙之理、神的计划与天地之奥秘置于眼前、握于指尖都毫无价值,除非这使人受惠或有利可图。事实上,如今已经到了只有那些把对智慧的研究降格为营生的人才被视为智慧的地步(多么可悲!)。这就像眼看着那因为诸神的慷慨而居于众人之中的贞洁的帕拉斯被抛弃、哄走、还惹人嘘声,没有人爱她和保护她,除非她像个妓女一样靠着贞洁被玷污而得一些施舍,再把那些不洁之财存进她爱人的钱柜中。我说的所有这些(无不带着最深的悲痛和愤怒)并非针对我们时代的大人们,而是针对某些哲学家,他们仅仅因为哲学家没有市场,得不到酬劳,就相信并公开宜称任何人都不该追求哲学,好像这没有向世人表明他们并非真正的哲学家似的。因此,只要他们一生都致力于追名逐利,就不能拥抱对真理本身的知识。对此,我自诩(在这方面我决不会因自夸而脸红)除了想成为一个哲学家,我从不为任何其他原因追求哲学,也未曾从我的研究和探索中希冀或者求取过任何其他的报酬和成果,除了我一直强烈渴望的心智养料和真理之知。我是这样地渴望和迷恋哲学研究,以至抛开所有私人和公共的顾虑,全身心地投入到沉思的闲暇中;这样,任何嫉妒者的中伤或智慧之敌的毁谤不仅过去未曾,而且将来也不会使我分心。哲学本身教导我倚赖自己的良心而非他人的意见,它教导我们要始终保持谨慎,这与其说是为了避免别人的中伤,倒不如说为了防止我说或做任何本身为恶之事。[20]
17世纪法国卓著的哲人科学家帕斯卡更是把思想的重要性推到极致,他的一席话掷地作金石声,具有撼人至深的力量:
思想形成人的伟大。
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正是由于它,而不是由于我们所无法填充的空间和时间,我们才必须提高自己。因此,我们要努力好好地思想;这就是道德的原则。
······由于思想,我却囊括了宇宙。[21]
我是从科学步入哲学的,又一直爱好文学,尤其喜欢古典诗词——在正事之余,也从心灵深处不期然而然地冒出一二诗句。因此,我自信我自己多少还有点科学家的实证精神、哲学家的理性气质、诗人的浪漫情怀。我的人生支点是真、善、美。我的价值坐标是:精神生活远远高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X坐标是社会正义,Y坐标是人格尊严,Z坐标是文化创新。[22]而且,我向来认为,思想和道德具有永恒的价值,[23]思想和人格万古不没[24]。因此,对于社会上的积习流弊、歪风邪气,我总是本能地疾恶如仇,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对于人世间中的熙熙舐痔、攘攘乡愿,以及那些“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25]式的人物,我总是本能地看不起他们,甚至忍不住予以抨击。“读曹丕《典论·论文》”“人行”二诗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的这种情愫和心语:
而今士人熙熙攘,脱颖而出争食忙。
贵远贱近鼠目短,向声背实狐心长。
学无遗漏原根本,文有独创自昭彰。
良史飞驰辞势去,一家之言万古芳。
人生总该有人行,不枉世间走一程。
是非正误泰山重,祸福得失鸿毛轻。
国是学理心中事,鸡毛蒜皮耳边风。
可谴舐痔与乡愿,污染空气遗膻腥。
屈指算来,今年我退休已经十载。本来,我一向就是“体制内”的“体制外”人,也就是“思想和行动上的自由人”——这有言论和实践为证。[26]退休后,我就更加自由了,时间全属于我的,由我自由支配。在这不算短也不算长的十年间,我撰写了两部书稿,翻译了10部(11本)书籍,发表了60多篇论文和诸多短文,出版了4本著作[27]和6本译著[28]。我自以为日子没有白过,生命没有浪费,心里是充实的,精神是富有诗意的。而今,我已经七秩有四,距离大自然回收和废物再利用指日可待。翻译此书之后,我不打算再致力译事,而着力研究“中国现代科学思潮”和“科学与人生”两个课题,冀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再做出一两个像样的成果。熊十力在致徐复观的信中所说的一段话言微旨远:“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29]我愿把它铭记于心,作为警示。在这里,我还想选录我先前的“古稀自述”“退休十周年感赋”二诗附后,以明心志,并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獨寐寤言士林间,永矢弗告意拳拳。
心有幽趣慕严斶,身无蓄谋效冯谖。
磊落使才耸天地,慷慨任气睥权钱。
腾蛟起凤寻常事,古稀虽逾梦蹁跹。
裸退辞聘身心清,所在无时不春风。
虚衔红利若败絮,真才实学乃令名。
累累学苑结硕果,缕缕憩园萌诗情。
举杯邀月一樽酒,桃蹊李径十年灯。
注 释:
[1][英]K.皮尔逊:《科学的规范》,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版,xii+410页。K.皮尔逊:《科学的规范》(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哲学),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版,xxx+458页。K.皮尔逊:《科学的规范》(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版,xxx+458页。K.皮尔逊:《科学的规范》(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哲学·纪念版),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版,xxx+458页。K.皮尔逊:《科学的规范》(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纪念版),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月第1版,xxx+458页。
[2]K. 皮尔逊:《自由思想的伦理》,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版,xxii+528页。
[3]K. Pearson, The Chances of Death and Other Studies in Evolution, Vol. I,Edward Arnold, London and New York, 1897, p. 105.
[4]K. Pearson, The Chances of Death and Other Studies in Evolution, Vol. I,Edward Arnold, London and New York, 1897, pp. 141-142. 皮尔逊紧接着的上一段话也振聋发聩:“读者不必暂且假定我们认为,竭力鼓吹某种显著的物质利益最终将从每一种深奥的研究中产生,或者是正确的,或者是必要的。尤其是,科学人尤其必须做的事情是,在为思索真理而思索真理中广泛地蓄养其乐,表明科学过程只是通常的逻辑定律——精炼的常识——的应用,因此这些过程没有超越正常构造的人的心智的认识范围,不仅如此,它们实际上能够给予一般人以赏心悦目的乐趣。”(p.141)
[5]K. Pearson, The Chances of Death and Other Studies in Evolution, Vol. I,Edward Arnold, London and New York, 1897, p. 379.
[6]K. Pearson, The Chances of Death and Other Studies in Evolution, Vol. I,Edward Arnold, London and New York, 1897, p. vii.
[7]E. S. Pearson, Karl Pearson, An Appreciation of Some Aspects of His Life and Work,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38, p.33.
[8]K. Pearson, The Chances of Death and Other Studies in Evolution, Vol. II,Edward Arnold, London and New York, 1897, p.4.
[9]李醒民:《迪昂》,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第1版,xiii+510页。
[10]K. Pearson, The Chances of Death and Other Studies in Evolution, Vol. II,Edward Arnold, London and New York, 1897, p.400.
[11]K. Pearson, The Chances of Death and Other Studies in Evolution, Vol. I,Edward Arnold, London and New York, 1897, pp. vi-vii.
[12]李醒民:《彭加勒与物理学危机》,杨玉圣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哲学卷(中)),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247-1285页。
[13]李醒民:《卡尔·皮尔逊:著名科学家和自由思想家》,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12卷(1990),第2期,第65-78页。李醒民:《简论皮尔逊的科学哲学》,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第7卷(1991),第3期,第60-65,59页。李醒民:《论皮尔逊的科学观》,成都:《大自然探索》,第13卷,(1994),第1期,第93-98页。
[14]李醒民:《皮尔逊》,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10月第1版,vi+357页。该书目次为:自序、第一章 卡尔·皮尔逊: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和思想家,第二章 认识论:以怀疑和批判为特征的观念论的经验论,第三章 方法论:科学方法是通向知识和真理的唯一入口,第四章 旨永意新的科学观,第五章 妙趣横生的自然观,第六章 皮尔逊思想在西方,第七章 皮爾逊思想在中国,后记,年表,主要参考书目,索引。
[15]李醒民:《马赫》,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第1版,xvii+412页。
[16]李醒民:《迪昂》,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第一版,xiii+510页。
[17]李醒民:《爱因斯坦》,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第1版,xii+593页。
[18]李醒民:《自由思想和研究的热情——皮尔逊社会哲学一瞥》,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2卷(2000),第1期,第21-28页。李醒民:《皮尔逊的优生学理论和实践》,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3卷(2001),第3期,第58-64页。李醒民:《皮尔逊的教育思想:重视素质培养》,北京:《科技导报》,2001年第11期,第10-12页。李醒民:《皮尔逊的历史研究和编史学观念》,北京:《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1卷(2002),第4期,第354-369页。李醒民:《皮尔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北京:《哲学动态》,2003年第9期,第38-42页。李醒民:《皮尔逊论社会主义和妇女解放》,上海:《哲学分析》,第2卷(2011),第1 期,第117-140页。
[19]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梁存秀、薛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版,第17页。
[20]皮科·米兰多拉:《论人的尊严》,樊虹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版,第75-76页。
[21]帕斯卡:《思想录》,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版,第157-158页。
[22]李醒民:人生支点和价值坐标——《爱因斯坦论和平》译者后记,O.内森、H.诺登编:《爱因斯坦论和平》,李醒民译,2017年第1版,第955-963页。
[23]李醒民:《思想和道德是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北京:《中华读书报》,1999年3月3日,第15版。
[24]李醒民:《唯有思想和人格是万古不没的——<力学的进化>中译者后记》,《民主与科学》,2021年第5期。
[25]杜甫:绝句漫兴九首·其五。
肠断春江欲尽头,杖藜徐步立芳洲。(春江 一作:江春)
颠狂柳絮随风去,轻薄桃花逐水流。(去 一作:舞)
[26]李醒民:我的“六不主义”,《自由交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第107-112页;李醒民:《不把不合理的“规章”当回事》,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2卷(2000),第3期,第7-8页;李醒民:《我为什么从来不……?》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33卷(2011),第2期,第115-119页;李醒民:《自由思想者诗意的栖居和孤独的美》,北京:《光明日报》,2011年6月14日,第11版。李醒民:《泛舟学海任西东》,葛剑雄、丁东、向继东主编:《望尽天涯路——当代学人自述》,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143-155页。
[27]李醒民:《科学论:科学的三维世界》(上卷、下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版,xiii+1354页。李醒民:《什么是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版,iv+323页。李醒民:《科学的社会功能与价值》,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版,iv+345页。李醒民:《科学与人文》,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第1版,x+292页。
[28]P.迪昂:《德国的科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版,274页。P.迪昂:《德国的科学(修订译本)》(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哲学·纪念版),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版,275页。P.迪昂:《德国的科学(修订译本)》(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纪念版),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版,275页。E.马赫:《科学与哲学讲演录》,李醒民、庞晓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版,ii+433页。E.马赫:《力学及其发展的批判历史概论》,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版,xxix+624页。E.马赫:《能量守恒原理的历史和根源》,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版,xxii+117页。K. 皮尔逊:《自由思想的伦理》,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版,xxii+528页。O.内森、H.诺登编:《爱因斯坦论和平》,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版,x+963页。
[29]熊十力:《现代新儒学的根基》,郭齐勇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ix页。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教授)
责任编辑:尚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