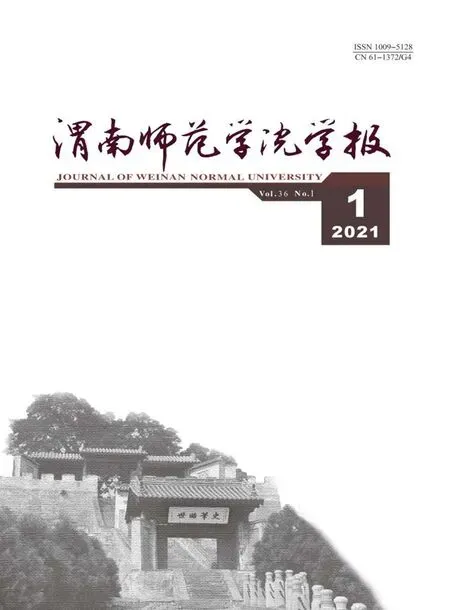王世懋研究述评
2021-03-08周慧敏
周 慧 敏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哈尔滨 150080)
王世懋(1536—1588),字敬美,号麟洲、墙东生、损斋居士,娄东太仓人。他是“后七子”领袖王世贞的弟弟,因王世贞的文坛威望,所以一般认为王世懋“名亚其兄”,但“世贞力推引之,以为胜己”[1]7382。文苑英才都对王世懋赞誉有加,“有所酬倡,出一语必翕然叹服”[2]503。王世懋一生著述颇丰,然学界却对他疏少瞩目,仅有的研究资料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明清传记、志铭及志书中对其生平的概述,二是结合《艺圃撷余》分析他的诗学观,三是对其评点、批释的《世说新语》的研究。而对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却未能予以准确定位,对其文学成就更是鲜少提及。现对王世懋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期对后之研究者提供借鉴。
一、生平行实的研究
有关王世懋的生平行实,最早见于明人所撰行状、碑铭及清人王瑞国所撰年谱中。王世贞于万历十七年(1589)始撰成《亡弟中顺大夫太常寺少卿敬美行状》[2]495-536一文,详细记述了王世懋的一生,是目前所见关于王世懋生平的最早资料。文中对王世懋的字号由来、家世背景、求学读书、仕宦经历、父难幽居、交游酬唱、诗文著述等进行了详细记述。全文“累万言,皆实录也”[3]91,不仅展现了手足深情,所记也最为真实可靠。明人王锡爵《南京太常寺少卿麟洲王公世懋墓志铭》[4]239-243、汪道昆《明故中顺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琅琊王次公墓碑》[3]91-93、赵用贤《太常王敬美传》[5]183-187、沈思孝《祭王敬美文》[6]、费元禄《国朝儒林赞》[7],都是记录王世懋生平的较早史料。而吴国伦、陈文烛在《王奉常集序》中对王世懋的生平、仕宦亦有简要介绍,但各有侧重。吴《序》中除阐明与王氏父子的师友关系及诗歌唱和外,对他的仕宦、退居、著述等都有提及,对其生平有所补充。陈《序》简述王世懋的仕宦经历,又谈及二人的相识、结社,以及共仕闽中时的唱和往来,这些都进一步丰富了王世懋的行实研究。
此外,另有一些生平资料散见于明人所撰各类官修、私修史书、传记和方志中,如王兆云《皇明词林人物考》[8]563-568、过庭训《明分省人物考》[9]201-204、尹守衡《明史窃列传》[10]398-399、《明史·王世贞传》(附)[1]7382、傅维鳞《明书列传》[11]441-442(1)按,该书载王世懋“登嘉靖十四年进士”,此处有误,实为嘉靖三十八年(1559)。、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王少卿世懋》[12]438、《明史稿列传》[13]441、《罪惟录》[14]489、《太仓州志》[15]1202-1204等,所述繁简不同,但详细程度均不及其兄所撰行状,然亦对王世懋交游、著述、思想有所补充。
清人王瑞国《琅琊凤麟两公年谱合编》[16]223-302以记录王世懋兄弟为主,兼记其父王忬。王瑞国是王世懋的后世孙,该谱以年为序,多记重大事件,虽条理清晰,但失之省简,未能详细全面呈现王世懋的一生。然对其诗文创作多有提及,对二人交游、诗文集编年有一定裨益。随着郑利华、徐朔方、周颖《王世贞年谱》的出版,及与王世懋过从甚密的同时期文人,李攀龙、吴国伦、徐中行等人年谱的问世,这些都对完善王世懋生平有重要补充作用。美国学者富路特《哥伦比亚大学明代名人传》亦对王世懋的生平、家世、仕宦、结社、著述、子女情况进行了梳理,行文简洁,便于通观王世懋的一生[17]1937-1939。
现当代以来,对王世懋生平行实的研究主要以各类论文为主。如李艳好《王世懋年谱》[18]通过对王世懋史料的收集,将谱主的重要作品、仕宦及广泛交游情况进行大致系年,视情况进行考证。尽管该文尚存在一些讹误,但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王世懋研究的空白,而作者也力求尽可能全面呈现王世懋的一生。这不仅有利于还原当时的文学生态,还有助于深入认识和评价王世懋的文学地位和影响。
有关王世懋的交游情况,李圣华在《晚明诗歌研究》[19]中一语带过提到其与屠隆的交往,在《略论后七子派后期诗歌运动》[20]一文中也简单提及其与新安诗人汪道贯是道义之交。李波在《明代陕西提学——王世懋》一文,介绍了王世懋在陕西提学任上的督学与游历,以及与陕西文人温纯、南轩的交往与创作。[21]而分析王世懋仕任陕西期间的诗歌创作,对于明确其生平仕履、诗歌编年有一定的提示作用,但该文所论失之简略。姬毓《王世懋诗学及心态研究》[22]第一章主要写王世懋的生平与交游,将其一生分为:负笈游学、中遭家难、宦海沉浮三个时期,对其交游对象,主要论析的是后七子及其他复古派成员,所论比较翔实,但对其与复古派之外的交游则未谈及。
二、诗文研究
当前学界对王世懋的研究多集中于他的诗歌理论,而对他的文学成就却疏少关注。事实上,最早对王世懋诗歌成就进行关注的是王世贞。他指出:“(王世懋)于诗虽自济南始,其所涵咏多汉、魏、晋、宋,以至盛唐诸大家。然不肯从门入,亦不规规名某氏业,而神诣之境为胜,七言律尤其踔绝者。文出入西京、韩、欧诸大家,间采刘义庆《世说》,自以为得其三昧。而《名山游记》尤详婉有力,善持论,往往以识胜。”[2]533此外,同时代的文人吴国伦、陈文烛、李维桢、高出都曾为王世懋《王奉常集》作序。其中前三位与王世懋交谊甚笃,因受王世贞之托为之作序,而高出是受王世懋之子的请托而作序,这四篇序文都是研究王世懋其人其诗文的重要资料。吴国伦对王世懋的才学评价甚高,“敬美其才兼人,而尤研精于风雅典谟”,“闻识广而神气益完,思虑深而天机益敏,意兴高而风韵益鬯之。其境之所会,而极其情之所通,无不应手立就”,甚至说“予才不逮敬美远耳”。进而评价王世懋诗文:“予窃拟其性情发于诗而风世之道寓焉,论议持于文而经世之道载焉。”陈文烛评其诗曰:“今观敬美古体,风骨本于建安,藻缋源于三谢。响逸而调远,兴高而采烈,可方驾古人也。至于律细天巧,秀色如春云秋水,难以名状,似王、孟者十之五,似钱、刘者十之二,意极变化,语鲜雷同,大自惊人。歌行丽而婉,排律整而健,未若近体之擅场也。”[23]卷首又指出王世懋为文服膺汪道昆,并评价其各类文章的特点。李维桢高度赞扬王世懋的学与识——“真命代之雄才矣”,认为与其兄齐名,然“好事者或谓公才名得司寇而亦彰,知者谓公才名因司寇而小掩”,至于孰是孰非,作者指出:“则有是编以俟夫百世之立言、知言者矣。”[23]卷首但从前文来看,李《序》是认同“公才名因司寇而小掩”的说法的。高出称王世懋“诗本陈思王、韦左司”,“文本太史公、苏老泉”,并将其至于明代文学的大背景下进而指出“七子于吾代文章,为盛之终而衰之始,而先生尚其后劲,故与七子游而为七子易也,与七子齐名而能不为七子,亦易也”[23]。高出意指王世懋游处于后七子之中,深受复古思想影响,其与后七子齐名,却不惟复古是从。四人不仅肯定了王世懋的才学与诗文成就,还指出其诗文渊源不局限于一家,而是博采众长。与前三篇序不同的是,高出能从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下指出王世懋“不苟同时风”[23]卷首,对后七子既有继承又有改变,颇具宏观视野。
此外,一些明清文人对王世懋其人其诗也有不同评价。汪道昆评其为:“诵诗自《周南》以下,迄于盛唐,不径不庭,务求神造。”[3]93赵用贤称“公握灵蛇,词坛俪美,百氏纷拏,莫窥涯涘”,指出王世懋在文坛诸子的论争中能“独探秘旨”,并广泛吸收,“沛乎徜徉”,所作有如“子云笔札,户宝家藏”[5]352,给予王世懋非常高的评价,所言不无溢美,但也充分肯定了王世懋的文学成就。而王世懋的好友沈思孝以骚体行文,作《祭王敬美文》,指出王世懋诗文英词洒洒,将之媲美《韶》《夏》,有大音希声之感,亦是对其给予了非常高的肯定。相较而言,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评价“敬美才虽不逮哲昆,习气犹未陷溺”[24]399,所言比较公允,不仅指出王世懋与王世贞诗风之不同,亦从侧面反映了后七子弊病的显而易见。
关于王世懋的诗学观,明人较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陈文烛在《艺圃撷余序》中指出:
王元美有《艺苑卮言》,博雅并称,中多诗话。今敬美有《艺圃撷余》,专为诗而发也。哲匠鸿才、巧心独运,皆古人所未道、今人所难言者。窃谓《厄言》所纪,如长江大河,无所不有。兹编所载,如中泠惠泉,尤足快心,高言绝识,真足羽翼。[25]415-416
将王世贞《艺苑卮言》与王世懋《艺圃撷余》对举,对后者评价甚高,肯定其复古立场,不仅羽翼其兄,还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意。指出二者所论不同,前者宏阔,后者精微,可互为补充。清人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称:
然其(王世懋)论诗,不规规名某氏,以不从门入者为佳。论本朝之诗,独推徐昌榖、高子业二家,以为更千百年,李、何尚有废兴,徐、高必无绝响。其微词讽寄,雅不欲奉历下坛坫,则于其大美,亦可知也。[12]438
钱谦益指出王世懋为诗不宗一家、不守一格、通融兼济的诗学观。而四库馆臣则认为“是编(《艺圃撷余》)杂论诗格,大旨宗其兄之说”[26]2757,又言:“世懋名亚于其兄世贞,而澹于声气,持论较世贞为谨严。厥后《艺苑卮言》为世口实,而《艺圃撷余》论者乃无异议,高明、沉潜之别也。但天姿学力皆不及世贞,故所作未能相抗耳。”[26]2468既指出王世懋的不足之处,肯定其诗学成就。虽才学不及其兄,但《艺圃撷余》是“专为诗而发”,并且“持论较世贞谨严”。而“大旨宗其兄之说”,亦指出王世懋的复古立场,这也是学界的共识。
20世纪40年代,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中国文学思想史》“拟古派的兴盛”一节中指出,后七子一派势力虽盛,“惟世贞之弟世懋则不苟同于乃兄,其《艺圃撷余》一卷,深叹时人但知崇奉李攀龙、王世贞之说,以不言初唐盛唐为耻,专以剽窃模仿为能事,而预言‘第恐数十年后,必有厌而扫除者’。可谓一语中的,果然数十年后而开始扫除运动也。”[27]115所论比较简略,但这是近现代以来最早关注王世懋诗学思想的外国学者。80年代以后,有部分学者围绕王世懋的诗学观进行了探讨。蔡钟翔、黄保真、成复旺对《艺圃撷余》予以分析,指出王世懋是从格调走向神韵,“是以性情和神韵救片面提倡格调之失”,“实际上把‘高韵’和‘深情’看得比格古调正更重要”[28]135,又认为“发展到‘本性求情,且莫理论格调’,就几乎成了对格调说的否定”[28]136。书中虽然指出王世懋相关言论是对王世贞“格调说”的发展,以及为救“片面强调格调之失”所做的努力,但对王世懋诗学主张到底有没有否定格调,则表述得不够明确。蔡楚镇同样指出:“世懋论诗仍从其兄世贞之见,主格调说,但比他的兄长转变得更为明朗、更为突出一些。”[29]162并比前后七子的格调都略高一筹,“因为它已使格调通于神韵”。这一解释比较客观合理地指出王世懋的格调论立场及对格调说的发展。但对于“今之作者只须真才实学,本性求情,且莫理论格调”,蔡先生认为,“‘本性求情’,就是根据诗人的性情去求其思想情感和艺术个性的表现”,这有其合理之处,但又指出:“王世懋认为作诗应当重视才学性情,不必过多地去理会格调。”[29]163重视才学性情与理会格调,二者并不冲突,蔡先生的解读是认为王世懋已将才学性情置于格调之上,这恐非王世懋本意。
此后,有个别学者对王世懋的诗学观又提出了不同看法。廖可斌指出,王世懋的诗论“对剽窃模拟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并对复古理论有所修正”,但随后又称:“这是作为后来者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困难的是真正有新的开拓,而在这方面王世懋似乎没有什么建树。”[30]359廖先生只是肯定王世懋对修正复古弊病所作的努力,但还算不上是真正的新的开拓。林庚认为,明人对于诗的意见,可从王世贞《艺苑卮言》、王世懋《艺圃撷余》、徐祯卿《谈艺录》等看出,并以王世贞、徐祯卿所说为例,指出他们作诗的法则“原是八股的精神格式,乃同时都成为诗文的不二法门”,虽然后七子派的模拟“不具八股的形式,却无往而不是八股的精神”[31]519,这一提法比较新颖,概括也比较精准,但这同时也将王世懋包括在内,同属明代文坛模拟论的阵营,也就忽视乃至否定了王世懋对修正后七子模拟之失所做的努力。
有部分学者对王世懋诗学观的理解有其合理性,但同时也有些绝对化。袁震宇、刘明今认为,王世懋是“后七子派中诗风转变的代表人物”,其《艺圃撷余》“有宗格调说者,有反格调说者,甚至有十分接近于性灵说者,似乎有些矛盾,其实正是体现了这一转变”[32]299。袁、刘二位先生在此对古今学者关于王世懋诗学主张的不同看法进行了客观概括,并进而指出其转变有二:一是变与逗,指出王世懋的观点“打破了体格声调的框框,已不再是格调说了”[32]302。二是性灵说的萌芽。又称:
王世懋的诗文批评实际上已具备性灵说的基本因素。当然,他对格调说的态度还是若离若即的,对拟古尚古的批判还是软弱的,均不能与后来的公安派相比,并且也没有把对格套的否定与性灵的宣泄密切联系,使之成为一完整的明确的创作方法,因此王世懋的诗文批评还不能称之为性灵说,只是萌芽而已。[32]305
这一分析有其合理性,比较严谨地界定为“性灵说的萌芽”,而袁、刘二位先生既说王世懋已打破体格声调的框框,又说其对格调说的态度若离若即,并最终认为这已不再是格调说,则未免有自相矛盾之嫌。事实上,其“变”与“逗”,正体现了其对格调说的审视、弥补和修正,而性灵说的萌芽,亦是对格调说的发展。
对王世懋诗学思想有准确把握的是郭绍虞先生,他认为王世懋论诗“也是站在格调派的立场”[33]188,但也指出其论调倾向神韵,是格调说的转变者,并不是反对格调,他只是矫正格调派末流之失。郭先生进而概括了王世懋为矫正格调派末流之失的两条途径:一是“宗其盛,更须溯其源”;二是“知其正,更须明其变”[33]190,并最终将其称为格调派的修正者。这一解读无疑是最为全面、也更符合当时诗歌创作的实际,亦被此后的研究者所接受,并沿其流而扬其波。如许总称,王世懋《艺圃撷余》中的某些主张也是格调派之论,与神韵派主张相通,是以“神韵”补充“格调”[34]368-369。周群指出王世懋“堪称是与后七子关系最切者,他主张师法古人,但是并不胶执一端”,认为其论诗“较为通脱而与革新派有所应合”[35]44,主要表现在:一是以“性灵”论诗,二是师古不可胶执一体,三是以“逗”“变”论诗。他认为王世懋所论“实为‘格调’向公安派‘直抒胸臆’、‘独抒性灵’的过渡,亦即由拟古而至革新之间之‘逗’”[35]47,指出他与公安派的相通之处。而朱易安结合王世懋所处的时代与环境,指出他的诗学传统受格调论深刻影响的必然性,但由于性灵说的兴起,他又能接受新的诗学思潮的启发,并用空灵的“神韵”来救摹拟之弊。所以,朱先生认为王世懋“不反对师古,但不主张摹拟,也不主张事事囿于格调”[36]145,但朱先生对“予谓今之作者,只须真才实学,本性求情,且莫理论格调”这一观点虽未具体阐释,但他认为王世懋很大胆、直接,与前述蔡楚镇先生有相同之处。这也是朱先生与郭先生观点的同中之异。对此,漆绪邦、梅运生、张连第在《中国诗论史》中进行了合理的阐释:
王世懋在同一书中,既讲“固当严于格调”,又说“且莫理论格调”,似乎自相矛盾。而实际上,“且莫理论格调”之说,并不是反对或否定“格调”论,此说是针对那些从古人“格调”入手的学诗者而言的。本来,七子教人学诗,是要求诗人以一己之才情寄于古人之高古“格调”,他们都是首重才情学识,然后再讲“格调”的,他们并不认为“格调”就是诗的一切。而七子的一些追随者,并无七子的才识,误以为诗的一切就是“格调”,以为“格调”似于古人就是好诗,学诗入手就求“格调”之与古人合,于是流于模拟剽窃。王世懋所谓“但须真才实学,本性求情,且莫理论格调”,正为此辈人说法,是要他们先具真才实学,先求性情之真,不要一上手就在“格调”上下功夫。[37]817
这一段分析不同于蔡钟翔、蔡楚镇等人的观点,清晰阐述了在“七子后学模古之病已经显露”的背景下,王世懋没有离开七子的基本立场,仍是一个“格调”论者。因此,“在《艺圃撷余》中,虽为了纠正七子之弊而颇多重情之论,而王世懋论诗的基本观念,与‘性灵’之说还是有原则的区别的”[37]817。这一解析更通脱,这也是对郭先生观点的进一步阐发。
而陈国球在《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中,就七律源流问题,认为王世懋《艺圃撷余》中的相关论说是对“乃兄之论的补充”[38]76,对其诗学思想比较赞赏,但也指出其有自相龃龉之处。陈文新论及王世懋作诗之法认为其重“自运”,即“诗必自运,而后可以辨体”,也就是“置‘自运’于‘辨体’之前,即置精神于体制、技法之前”[39]191,这一解释比较具体细微,区别于以往学者多聚焦于王世懋对格调说态度方面的研究。
综合来看,对于王世懋诗学观的讨论,以上各家之言或认为他是对格调说的否定,或认同他的格调论立场,指出他对后七子的发展与修正,只是发展方向有二:一说通于神韵,一说通于性灵。事实上,无论是通于神韵还是通于性灵,都是对王世懋对后七子之弊所做的努力,也是他不胶执一端、通融兼济的体现,是视情况的灵活处理与变通。
除上述著作外,另有一些论文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史小军《论“末五子”对“前后七子”格调理论的发展与突破》[40]一文指出,作为“末五子”成员的王世懋从“变”的立场出发,对七子派格调论进行了修正,直至放弃格调论而趋向神韵和性灵论。该文认为格调论与神韵论、性灵论有相通之处,而追求神韵和性灵则是放弃格调论,这种非此即彼的说法有些过于绝对化。
王英志《王世懋不属复古格调派——〈艺圃撷余〉论析》[41]一文,通过分析《艺圃撷余》所反映的主性情、求发展变化、倡独创、重神韵等诗学主旨,指出王世懋是格调派的蜕变者,其诗学观不属于复古格调派,而是与其后的公安派及清代性灵派的性灵说思想相通,亦是明代神韵思想向清代王士祯神韵说过渡的一个环节。邓新跃《王世懋对后七子格调论的修正》[42]一文,指出王世懋是明代诗学复古格调派流弊的反省者与革新者,他对后七子格调论的矫正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反对拘泥格调,二是肯定文学风格的渐变与过渡性,三是强调冲淡含蓄的神韵。认为王世懋虽然也有一些偏激的言论,但他矫正前后七子流弊的理论观点仍具有重要意义,对此应予以肯定。这两位研究者都肯定了王世懋诗学观的发展变化,但结论却迥然不同。
孙学堂《隆庆万历间文坛风气及文学思想的变化》[43]一文结合隆庆、万历间的文坛风气及王世懋文学思想的转变,认为他并未完全放弃讲求格调法度的宗旨。王逊《〈艺圃撷余〉新论——从当下研究中的问题说起》[44]指出,当下对《艺圃撷余》的研究,因对文献的误解或误用,使得一些理解并不符合王氏原意。详考其书,王世懋坚持七子派观点的立场并未改变,而是对其进行了有益的补充与修正。该文比较可贵之处在于,在认同王世懋以“七子派”中人自居的同时,不要忽视他作为文人群体的一员,他与朋友间的诗酒唱和,不单是为提倡某种文学信念,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情趣的共同偏向。
另有两篇硕士论文是对王世懋诗学观的专题研究。李波《王世懋的诗歌理论》[45]1从“诗抒性情”为主的诗歌本质论、“诗必自运”为主的诗歌创作论、“变”“逗”观点为主的诗歌发展论、对七子派批评为主的诗歌批评论四个方面,对王世懋的诗歌理论进行阐述。最后指出王世懋或持论公允而具客观性,或纠正流弊而具针对性,或观点新颖而具创新性。该文虽对王世懋诗论予以肯定,但还缺乏深度阐释与探索。姬毓《王世懋诗学及心态研究》除对王世懋的生平、交游进行叙述外,对他早期的诗学思想与心态、后期心态的蜕变及诗话、晚年的诗学体系、时代坐标中的诗学定位等四个方面进行论析,指出心态的变化在诗文创作及《艺圃撷余》中均有反映,促成了晚年诗学观的某种自省与重构。最后,在与性灵说、神韵说的对比中,指出王世懋的诗学与性灵说貌合神离、与神韵说审美同趣。姬毓对王世懋的诗学定位较之以往研究者,论断更清晰明确。作者引证翔实,见其用力之勤。
以上各类论文所述虽并未超出前述专著所论的范畴,但李波、姬毓针对王世懋诗学观的专题研究,亦是对此以往研究的拓展与补充。同时,对了解七子派的文学活动、发展轨迹及当时复古运动的真实情况,亦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三、其他作品研究
除对王世懋的诗文成就与诗学观进行研究外,有部分研究者对其所评点的《世说新语》和笔记作品也进行了关注。王旭川《明代〈世说新语〉的研究及影响》[46]一文指出,明代《世说新语》评点的代表是王世懋与何良俊。其中他对王世懋《世说新语》评点的研究,主要从《世说新语》的分类、文辞、人物等方面进行分析,并指出王世懋等人的评论与研究对该书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不仅促进了《世说新语》仿续之作的纂辑,还使得这些仿续之作对叙事语言的关注。甄静《略论王世懋〈世说新语〉的评点特色》[47]一文,是对其博士论文中相应内容的深化。文中指出,王世懋评点侧重文字词意的辨正疏解,且较早注意到刘孝标《注》中掺入他注的问题,对魏晋名士及魏晋风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或认同,或反驳,从中也可折射出评点者的审美趣味和价值标准,并认为王世懋的评点对于《世说新语》文本的阐释与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广作用。曹子轩《明代〈世说新语〉研究》[48]除对明代《世说新语》评点情况进行简要概述外,主要对评点内容、评点的功能与特色、价值及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而比较突出之处在于,能从评点学、文献学、文艺学、传播学等方面进行研究,指出评点内容在形式上与思想上的局限性,以及在美学、文献学、文学等方面的价值。刘强《王世懋的“〈世说〉学”》[49]一文指出,王世懋对《世说新语》的流传与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最早提出“世说学”这一概念的人,并促进了《世说》多种版本的刊刻与传播。该文认为王世懋的《世说新语》批释承前启后,富有特色,一是情感饱满,能移人情;二是触类旁通,明察秋毫。对王世懋及其《世说新语》评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对王世懋笔记作品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学圃杂疏》和《闽部疏》。李彬《王世懋澹圃造园思想初探》[50]一文,对王世懋“澹圃”的造园艺术从园艺学视角进行分析,并对他在澹圃养病期间写成的《学圃杂疏》一书进行分析,认为王世懋因笃信道家思想从而在澹圃中保留了更多的生产性园林基因,以此来抵制园林“世俗化”,而追求自然意境美是王世懋造园艺术渴望回归自然的物化过程,他的园林艺术思想核心就是“志澹”。这从根本上指出“澹圃”是王世懋思想与心态在文学之外的物化与投射。随后,李彬《浅析娄东私家园林的植物景观特点》[51]一文据《学圃杂疏》记载,分析娄东私家园林植物景观的造园艺术,体现王世懋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品质和不愿耽于功名利禄、喜爱隐居生活的惬意心情。同时,《学圃杂疏》的记载,对了解明代太仓园林植物的分布与栽培具有重要价值,对于今天的景观建设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此外,石润宏《王世懋〈闽部疏〉版本考》[52]一文指出,王世懋所撰《闽部疏》一书,多记闽地风物,对于研究福建的历史地理很有帮助。该文对《闽部疏》的版本详加考察,并对一些谬误进行了辨正,在版本学、文献辨伪及地域文化研究方面有重要价值。
总体来看,当前学界对王世懋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主要体现在:
一是总体研究失衡。当前还没有对王世懋进行全面论述分析的研究成果,已有的评价与分析散见于各类著述中,且主要集中在诗学观方面,对其生平行实的考论不够具体明晰。王世懋仕宦南北,交友广泛,已有的研究仅局限于其与复古派成员的交游,且缺少对其诗文的专门研究。王世懋的诗文总集为《王奉常集》,存诗15卷,文54卷,历来研究者都仅是摘其只言片语来论说他的诗学观,却对其诗文却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除明清文人予以简要评价外,近代以来的研究者鲜有提及。
二是研究领域有待发掘。王世懋早年以奉儒为主,仕宦偃蹇中又参以佛道,“三教通体”的思想与明代中晚期的政治生态及其仕隐抉择密不可分,然学界却未曾予以关注。除对《学圃杂疏》《闽部疏》及《世说新语》批点进行研究外,对其他笔记作品如《窥天外乘》《二酉委谈》的研究也同样迟滞。而其批点的戏曲作品《大雅堂杂剧四种》及《经子臆解》《易爻辞》《读史订疑》等则无人问津。
三是研究视角有待开拓。从横向上,需进一步考察王世懋与明代中晚期的文坛生态;在纵向上,探究其对复古的追随与修正及 “格调”与“性灵”“神韵”的关系。此外,还需做交叉领域的研究。王世懋不唯在诗文上有一己之见,其于书画亦独有见地,与当时文人多有品评题赠之作,目前已有的研究多是碎片化提及,应对其进行系统分析。
四是缺乏文学史上的明确定位。作为复古后劲,学界在论及复古派时,多将王世懋附在王世贞后对其诗学观进行分析,但所论都比较笼统宽泛,缺乏准确定位。事实上,王世懋是一个既秉承传统,又善于扬弃与纳新的富有使命感的文人,其典型性在于,他的文学观与文学创作既体现了在文学转变过程中的阵痛与勇气,又呈现出文学发展中的时代脉动。因此,要将王世懋从王世贞的光环下抽离出来,作为独立的个体进行追踪,进而来评价其文学成就与文学史地位。
综上所述,对王世懋全面系统地研究,要开拓视野,转化视角,尽力地搜集与王世懋有关的全部史实,“在阅读大量基本文献的基础上,搜寻考释,钩玄探逸,进而追踪觅影”[53],考察诸多与王世懋有关的人物和事件,去伪存真,以期还原当时的生态原貌,打开王世懋研究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