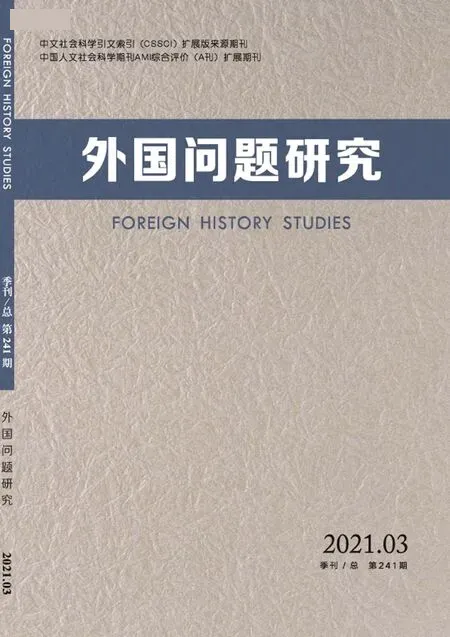冷战中的美苏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探析(1958—1972)
2021-03-08王子晖李楚楚
王子晖 李楚楚
(1.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2.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冷战爆发之初,尽管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展开了激烈的全面对抗,但另一方面,美苏两国基于各自的国内外政策目标,又都对文化领域的交流活动表现出一定的兴趣。经过一段时间的谈判磋商,双方于1958年正式签订了文化交流协定,由此两国在文艺、科教等领域持续展开了一系列交流活动,形成了冷战期间的一种独特现象。可以说,冷战中的美苏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充分反映了双方在进行意识形态竞争时,不仅充分利用政府的资源和力量,还尽量调动全社会的资源和潜能,动员包括学者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宣传各自文化特色和技术优势。近年来,国内关于“文化冷战”的研究方兴未艾,成果颇多,但大多侧重于“心理战”及“宣传战”,而有关美苏之间的文化交流却着墨不多。(1)有关“心理战”及“宣传战”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郭又新:《穿越“铁幕”:美国对“苏东国家”的冷战宣传(1945—1963)》,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2003年;张晓霞:《从进攻性的心理战到渐进的文化渗透——评冷战初期美国对苏东宣传政策的演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郭又新:《东西方交流与艾森豪威尔的冷战宣传攻势》,《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2期;赵玉明:《文化冷战与冷战初期的苏联反美宣传——以中央宣传鼓动部解密档案为切入点》,《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1期;赵继珂:《美国新闻署对苏文化冷战行为研究(1953—1961)》,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4年。有关美苏文化交流的代表性成果有:温显娟:《美苏体育外交初探》,《外国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贾付强:《冷战时期的美苏宗教外交》,《公共外交季刊》2015年第1期;高大为:《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苏文化交流政策》,《文化学刊》2018年第5期。国外学者中,美国苏联学家、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罗伯特·伯恩斯在1962年发表了《与苏联的学术交流》一文,后来又出版专著《苏美学术交流:1958—1975》。(2)Robert F. Byrnes, “Academic Exchanges with Soviet Union,” Russia Review, Vol.21, No.3 (Jul. 1962), pp.213-225; Robert F. Byrnes, Soviet-American Academic Exchanges, 1958—1975,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6.除此之外,美国资深外交人士、跨文化交际专家耶尔·里士满对这一问题也曾有过研究。(3)Yale Richmond, U. S.-Soviet Cultural Exchanges, 1958—1986: Who Win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7; Yale Richmond, Cultural Exchange, The Cold War: Raising the Iron Curtain,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3.但国外学者的成果,大多是基于自身经历,缺乏对于这一现象的宏观考察及客观评价。本文基于对美国外交关系文件、中央情报局解密文献及国外相关学者著作的解读,梳理了1958年文化交流协定签署到1972年尼克松访问苏联之间这段时期美苏学术交流的过程,探究了其缘起的背景、运作的机制和障碍及其对于冷战本身的影响等问题,旨在为我们考察冷战时期的美苏文化关系提供一个特殊的视角。
一、美苏学术交流的缘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冷战随即爆发,因而可以说在此期间美苏两国几乎不存在学术交流的可能性。当然,美国方面为了能以某种形式向苏联渗透其思想观念,曾尝试打开与之进行交流的大门,但苏联方面出于维护其社会制度和保持其政权稳定的谨慎考虑,强化了对文化领域的控制,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其公民同外界的接触。罗伯特·伯恩斯在《苏美学术交流:1958—1975》中提到,1945年11月13日,美国驻苏大使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曾代表美国国务院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交涉,希望从1946—1947年度开始与苏联交换学生,但并未得到苏方回应;1947年4月,美国驻苏大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向维辛斯基表示,美国将邀请50名左右苏联学者到美国“与美国学者就相同领域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进行讨论”,然而该建议亦被苏方拒绝。(4)Robert F. Byrnes, Soviet-American Academic Exchanges, 1958—1975, pp.31-33.
1948年1月,苏联颁布了关于控制公民同外国机构及其人员之间关系的法令,该法令与1926年8月颁布的同类旧法令相比,对限制范围予以扩大,将“文化”“科学和教育机构”“其他”从原先的豁免清单中删去,因而规定各类文化、科学、教育机构(如列宁图书馆和科学院)不能直接与外国人打交道,甚至不允许苏联的相关机构和个人回复外国人的信件。(5)“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 (Smit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29, 194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48, Vol.IV: Eastern Europe; The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USGPO, 1974, pp.798-799.如此一来,美苏之间几乎完全没有学者互访和其他形式学术交流的渠道。然而,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逐渐掌握苏联党政大权并开始调整对外战略,强调广泛意义上的东西方和平共处,以期缓和紧张的国际形势。于是,《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就此做出判断:气氛的明显变化标志着一个同苏联进行文化交流的有利机会。他相信东西方交流将有助于美国的利益,如果此时华盛顿提出一个正式的交流项目,莫斯科将很难拒绝。(6)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Report on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Exchange of Persons: February 23, 24, 25, 1955, New York: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955, pp.52-53.
与此同时,上台伊始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为了应对苏联的“和平攻势”,在其所提出的“新面貌”战略中,把“心理战”作为遏制苏联、不断扩大美国在世界的影响力、把西方的价值观和制度推广到全球更广阔地区的关键要素。1953年9月2日,艾森豪威尔签署10483号总统行政命令,宣布建立行动协调委员会(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 OCB)以取代杜鲁门政府的心理战略委员会(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PSB),(7)“Memorandum from President Eisenhower to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Lay), September 2, 1953,” FRUS, 1950—1955,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1950-1955, Washington: USGPO, 2007, pp.456-457.并将心理战的目标调整为对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和平演变”。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说,他长期以来一直主张“直接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走向世界和平的一个良好的、开明的步骤”,(8)Dwight D. Eisenhower, Waging Peace, 1956—1961, New York: Doubleday, 1956, p.410.因此他表现出对交流项目的浓厚兴趣,并经常就此类项目可能对苏联所造成的影响发表看法。艾森豪威尔曾于1955年5月24日对国务卿杜勒斯说:“交流项目和宣传应当被不断推进,我们必须加紧进行这项工作”。他宣称“我们多年来一直称之为心理战”的东西是“以人的思想为目标的攻击”,是促进“铁幕背后的不满”和赢得发展中国家支持西方目标的手段。杜勒斯也认为,宣传和交流项目能够增加“解放”东欧和苏联的机会。(9)Walter L. Hixson, Parting the Curtain: Propaganda, Culture, and the Cold War, 1945—1961,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p.104.鉴于冷战局势及彼此对外政策的变化,美苏两国高层针对包括学术交流在内的一系列文化交流事宜开始了正式沟通。
1955年7月18日,美、苏、英、法四国首脑会晤在日内瓦举行。美苏双方就开展文化交流达成原则性共识,但在讨论采取何种具体措施来加强东西方文化交流时,则存在着分歧和矛盾。美方强调的是人员和信息交流,特别是自由旅行和政治信息传播,而苏方则注重有助于加强其经济、军事能力的技术交流,要求大幅度放宽乃至取消西方对苏联的出口管制。由于双方互不让步,一时无法达成实质性协议,只好留待稍后的四国外长会议继续讨论。在同年10月27日召开的四国外长会议上,美、英、法三国向苏联提出了在新闻媒体、文化、教育、图书出版、科学、体育和旅游等方面进行正常交流的17点建议。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会上重申苏联立场,把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与经贸关系的正常化联系起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则拒绝放宽对苏联的贸易管制,特别是战略物资的管制,并反过来强调东西方信息自由流动的重要性,不断谴责苏联的审查制度和干扰西方广播节目的做法。因此,四国外长会议上美苏双方依然未能就文化交流问题达成协议。(10)Yale Richmond, U. S.-Soviet Cultural Exchanges, 1958—1986: Who Wins, p.4.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是苏联对外文化关系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标志。尤其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路线被确立为苏联外交政策的核心,进一步表明苏联方面希望以缓和代替对抗、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改善关系并展开交流与合作的意图。随后不久的同年6月2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607号文件(NSC 5607)——“关于东西方交流的政策声明”出台,确立了美国对苏文化交流的基本政策。其中明确表示,美国要在促进苏联内部演变的原则下与苏联展开交流。(11)“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June 29, 1956,” FRUS, 1955—1957, Vol.XXIV: Soviet Union; Eastern Mediterranean, Washington: USGPO, 1989, pp.243-244.然而,受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影响,美国国务院于当年11月13日正式宣布,东西方交流计划“被暂时搁置以等待情况明朗和对情况的重新评估”。(12)“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the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Soviet Union, November 13, 1956,” FRUS, 1955—1957, Vol.XXIV: Soviet Union; Eastern Mediterranean, pp.253-254.
尽管美国政府暂缓了东西方交流的推进工作,但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仍在不断寻求与苏联进行文化交流的尝试。另一方面,与美国寄希望于谈判相似,苏联同样不想就此止步。1957年1月24日,苏联曾向美国询问如何落实1956年美苏技术交流谈判达成的协定。(13)“Memorandum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President, March 27, 1957,” FRUS, 1955—1957, Vol.XXIV: Soviet Union; Eastern Mediterranean, p.258.随后不久,美国取消了1952年《移民与国籍法》中规定来自共产党执政国家的非官方访问者在入境美国时必须登记指纹的条款,在一定程度上为美苏双方恢复谈判扫除了障碍。1957年10月28日,美苏关于文化交流的谈判重新开始。苏联的提案主要涉及代表团和个人之间的交流,重点在于各种各样的工业和科学技术交流。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减少苏联对信息自由流通的障碍,并通过派代表团访问苏联科学院了解苏联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14)“Policy Information Statement Prepa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29, 1958,” FRUS, 1958—1960, Vol.X, Part 2: Eastern Europe; Finland; Greece; Turkey, Washington: USGPO, 1993, p.3.经过三个月的谈判,美苏双方消除较大的分歧并各自做出了妥协和让步,尽管双方都没有完全实现各自的主张,但还是于1958年1月27日正式签署了《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文化、技术和教育领域交流的协定》(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on Exchanges in the Cultural, Technical, and Educational Fields)。(15)由于双方谈判的首席代表分别是美国总统东西方交流特别助理莱西(William S. B. Lacy)和苏联驻美国大使格奥尔基·尼古拉耶维奇·扎鲁宾(Георг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Зарубин),因此这份协定也被称为“莱西-扎鲁宾协定”。根据该协定,美苏双方同意展开学术交流。
关于这一时期美国极力促成与苏联进行学术交流的原因,首先从冷战国际格局的角度来看,二战结束后美苏争霸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旋律,美国需要派遣人员进入苏联内部,拓展与苏联民众和机构的联系,加强对苏联社会真实状况的了解,从而为政府制定对苏政策提供依据,甚至不少专业人员受美国政府指派,还会展开间谍活动从事情报搜集工作。其次,与苏联进行学术交流有利于美国向苏联进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传播和文化渗透,达到促使苏联走向和平演变的目的。(16)“Paper Prepa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6, 1956,” FRUS, 1955—1957, Vol.XXIV: Soviet Union; Eastern Mediterranean, pp.220-221.对于来到美国的苏联人,美国可以向其充分展示美国发达的社会经济、开放的文化氛围,改变其对美国固有的认识,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苏联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观念。正如美国政府所估计的,“苏联的一些访问者必定会被美国的繁荣面貌和科技成就所折服,而且会在回国后把这种见闻告诉亲友。”(17)“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March 26, 1955,” FRUS, 1955—1957, Vol.XXIV, Soviet Union; Eastern Mediterranean, p.201.再次,从美国国内学术发展的需要来看,冷战爆发后,针对苏联问题的研究日益重要,而美国国内又缺乏相关领域的学者,因此为加紧培养苏联问题专家和俄语人才,美国也需要与苏联进行学术交流。最后,在冷战中试图与苏联开展学术交流的努力,也可以向外界展现出美国希望与苏联对话和谋求和平的姿态,从而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
对苏联而言,在斯大林时期之所以拒绝与美国进行学术交流,首先是苏联方面对美国提出的“学术交流”项目并不感兴趣,但最重要的还是斯大林认为美国表现出的学术交流意向,是企图对苏联进行政治宣传和文化渗透,担心美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扰乱苏联社会,进而颠覆苏维埃政权。然而赫鲁晓夫执政后苏联对外政策的改变,首先是赫鲁晓夫本人及苏联领导层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并且将和平共处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其次,尽管苏联在军事、工业等方面具备与美国抗衡的潜力,但实际上其总体科技水平处于劣势,因此越来越认识到有必要向美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提高自身的科技实力。另外与美国类似,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苏联与美国进行学术交流也怀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其派出人员都是由苏联政府精心选拔的意志坚定、学术造诣高的专家,难免要承担搜集情报的任务。同时,苏联也希望通过与美国的交流,能够向外界展示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为强大的工业国的伟大胜利,以及苏联在文化、艺术和科技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18)Yale Richmond, U. S.-Soviet Cultural Exchanges, 1958—1986: Who Wins, p.5.最后,苏联方面还认为,能够与美国签订文化交流协定,足以表明美苏两国的平等地位,和苏联乐于支持国际合作和坚定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19)Frederick C. Barghoorn, “Soviet Cultural Diplomacy since Stalin,” The Russian Review, Vol.17, No.1 (Jan. 1958), pp.41-55.
二、美苏学术交流的机制与障碍
1958年1月美苏文化交流协定签订后,美苏之间便展开了包括学术交流在内的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从1958年文化交流协定的签订到1972年尼克松访苏,是美苏学术交流的初步阶段。这一时期双方基本上每两年签订一次文化交流协定,即分别在1959年11月、1962年3月、1964年2月、1966年3月、1968年7月和1970年2月又先后签订了6个文化交流协定。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交流在1959年的协定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并且被提到了文化和教育的前面。新协定的全称是《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科学、技术、教育和文化领域交流的协定》。1962年签订的文化交流协定还加上了关于“其他领域”的交流,这种形式的交流一直持续到1973年。(20)Yale Richmond, U. S.-Soviet Cultural Exchanges, 1958—1986: Who Wins, p.2.
(一)美苏学术交流的机制
根据1958年签订的文化交流协定,美苏双方都建立了相应的机构来管理文化交流活动,美国方面最初是由国务院东西方交流处(East-West Contacts Staff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负责,到1960年被联邦欧洲事务局的苏联和东欧交流处(Soviet and Eastern European Exchanges Staff in State’s Bureau of European Affairs)取代;苏联方面最初的管理机构是国家对外文化关系委员会,到1967年被外交部文化司取代。
具体到学术交流方面,在1958年文化交流协定签订前,1955年时由来自7所美国高校的一些学者创立了旅行资助校际委员会(Inter University Committee on Travel Grants, IUCTG),当时这些学者相信,对美国学者来说能够短暂地访问苏联这一他们有着特殊兴趣的地方将很快成为可能。在卡内基公司和福特基金会的持续资助下,委员会于1955年到1958年末使来自75所高校15个不同学科的近200名学者以游客身份访问了苏联,时间一般为30天,这是苏联政府通常允许的最长时限。到1958年,交流协议明显使一小部分美国学者可以在苏联停留更长时间,同时也为相同数量的苏联学者提供了对等的在对方学术机构从事研究的机会。但此时旅行资助校际委员会则改变了它的项目,逐步结束了对教师的资助,而将其全部基金和精力投入到协助大量年轻美国学生在苏联度过一个学期或一个学年方面。从那时起,有来自27所大学的103位美国人在苏联高等教育机构用一个学期到两年的时间学习,一般情况下只能是在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这两所高校。在同一时期,来自7所苏联大学和32所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99位苏联研究生和青年学者在24所美国大学也度过了一个学期或一年。(21)Robert F. Byrnes, “Academic Exchanges with Soviet Union,” Russia Review, Vol.21, No.3 (Jul. 1962), pp.214-215.后来,旅行资助校际委员会的职能在1968年7月被国际研究与交流理事会(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Exchange Board, IREX)所接替。
根据文化交流协定,旅行资助校际委员会和国际研究与交流理事会与苏联高等教育部进行着三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第一种是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交换项目,美苏双方均派遣40—50人,进行为期一或两学期的交流。第二种是针对博士后阶段的高级研究者项目,双方都交换至少10人进行为期2—5个月的交流。第三种是暑期语言教师交换项目,双方交换30(后来增至35)名教师,每年暑期进行为期9周的交流。国际研究与交流理事会还代表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CLS)和社会科学研究协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与苏联科学院进行博士后阶段的学者交流,每年大约有15名美国学者和30名苏联学者以短期访学的形式参与。(22)Yale Richmond, Cultural Exchange, The Cold War: Raising the Iron Curtain, p.23.文化交流协定还为工业、农业和医药方面的代表提供了交流项目,通常为期两周。1959年,美国科学院与苏联科学院在交换科学家项目上签订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作为1962年文化交流协定的附件,为授课、开展研究、和相互了解提供短期交换项目,同样也为科学和高水平研究提供长期交换项目。(23)Yale Richmond, Cultural Exchange, The Cold War: Raising the Iron Curtain, p.68.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单方面”的交流项目,即美国方面自行承担经费向苏联派遣大学本科生去苏联学习俄语,但没有相应的苏联学生到美国学习。其中最大规模的交流是由国际教育交流委员会(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change, CIEE)组织的,它从1966年开始派学生去列宁格勒大学学习。CIEE项目每年派遣超过200名美国学生(主要是本科生)进行一个暑期或一至二个学期的俄语强化学习。CIEE项目由34所美国学校发起,但是来自其他机构的人员也可以被接收。(24)Yale Richmond, U. S.-Soviet Cultural Exchanges, 1958—1986: Who Wins, p.34.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美苏学术交流,实质上双方主要是派遣专业人员到对方国家参观,以观察对方在做什么,几乎没有涉及合作研究。
(二)美苏学术交流的障碍
这一时期美苏之间的学术交流规模非常有限,主要是由于冷战爆发以来美苏之间长期对立所造成的相互不信任,并且文化交流协定中规定的人员数量是最多而不是最少,限制了交流规模的扩大。除此之外,美苏之间关于学术交流的合作意向虽然达成,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仍存在着较大分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在交流人员的数量和身份上,美国想尽量多地派遣学者去往苏联,而苏联对于这一提议却十分谨慎;美国希望派出高级学者进行短期交流,而苏联一方面希望派出研究生在其最感兴趣的领域安排长期交流,以获得所需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决定仅给予所有在苏联的美国学者以“研究生培训生”(аспирант стажер)或者特别研究生的身份,从而限制他们接触各种资料。(25)Robert F. Byrnes, “Academic Exchanges with Soviet Union,” p.219.其次,在派出人员的选择上,美国方面是由旅行资助校际委员会和国际研究与交流理事会公开选拔的,但申请人实际上受到美国政府和中情局的审查。苏联方面则是由相关政府部门直接指派。美国学者主要致力于苏联文学、历史和社会等人文科学的研究,而苏联学者主要专攻科学、技术和工业领域的学问。双方关注点的不同也造成了一系列问题,例如双方的交流人员经常被拒绝入境,苏联学者被拒绝是因为他们可能会接触与国防军事工业相关的高科技,美国学者被拒绝是因为他们的课题太过敏感,涉及苏联当代(1917年以后)的历史、意识形态和政治状况。(26)Guy E. Coriden, “The Intelligence Hand in East-West Exchange Visits,” CIA Historical Review Program, July 2, 1996, pp.63-70.此外,由于双方达成的人员交流数量必须对等的原则,一方的人员被拒绝,另一方也会相应减少交流人员的数量。(27)Yale Richmond, Cultural Exchange, The Cold War: Raising the Iron Curtain, p.25.
在生活和工作条件方面,据参与学术交流的美国学者反映,他们在苏联还面临着住房简陋、查阅档案和外出旅行受限等问题。住房简陋的问题较为普遍,尤其是在列宁格勒,美国学者须入住苏联为他们提供的标准间,然而美国学者大多认为这些房屋不够舒适,且经常面临热水供应不足和电梯无法正常使用的麻烦。美国学者在苏联期间开展科研工作也往往不够顺利,一方面他们必须向其苏联方面的合作导师提交详细的研究计划,且必须得到导师的支持才能拥有出入图书馆和档案馆的许可。(28)Sheila Fitzpatrick, “A Spy in the Archives,”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32, No.23 (Dec. 2010), https://www.lrb.co.uk/the-paper/v32/n23/sheila-fitzpatrick/a-spy-in-the-archives,2019年3月2日。另一方面,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拒绝接触对研究来说非常必要的档案资料,限制规定甚至已经延伸到了禁止他们接触依法存放在莫斯科列宁图书馆的苏联博士学位论文。例如,为查阅档案需要向苏联相关部门提出申请,然而审批通常需要等待数月且经常因各种理由被拒绝。即使被批准进入档案馆,有时也会被告知没有与他们研究课题相关的文件。(29)Yale Richmond, Cultural Exchange, The Cold War: Raising the Iron Curtain, p.26.一位美国博士后学者在1961—1962学年春季学期被其苏联导师鼓励查阅存放在列宁图书馆的35篇博士学位论文;但他最后只被允许阅览其中的5篇,并以不做记录为条件。(30)Robert F. Byrnes, “Academic Exchanges with Soviet Union,” p.220.
学者的研究课题也经常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横加干预。历史学家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曾申请研究1905年革命期间的俄国军队,苏联方面最初拒绝了他的申请,断言当时“不存在真正的军事问题”。在美国组织者予以抗议后,苏联当局做了重新考虑,但再次拒绝了他的申请。理查德·斯泰特斯(Richard Stites)在研究19世纪俄罗斯的女权主义时,则被告知身为一名男性他并不适合从事这项研究。(31)David C. Engerman, Know Your Enemy: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s Soviet Exper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71.
在旅行活动方面,尽管协议规定与学业相关的旅行应被允许甚至被鼓励,但美国学生在旅行活动方面受到了苏联限制条件的严重阻碍。到有着重要资料收藏或影响很大的学者居住的特别城市和机构旅行,都会原则性地被拒绝,并且美国人也基本不被允许到苏联的历史文化名城参观游览。(32)Robert F. Byrnes, “Academic Exchanges with Soviet Union,” p.220.
当然,作为报复,美国方面也通常对来访的苏联学者实施类似的限制措施。更重要的是,冷战时期美苏之间长期的对立状态,导致在学术交流过程中,安全和情报是双方首要考虑的因素,因而进入两国交流的学者都或多或少会被当地政府监控,学术交流受到很大限制。苏联方面限制外国人进入苏联的一些领域并限制其与苏联公民和相关机构接触。美国方面则事先安排好所有苏联交流人员的行程,有些地区除非得到联邦政府的同意否则不允许任意出入。在这一时期美苏学术交流的过程中,双方都怀有各自目的,其中政治因素占很大分量,因此这一时期美苏学术交流本身的学术价值非常有限。
三、美苏学术交流与冷战的关系及其影响
这一时期美苏学术交流与冷战局势变化有着密切关联。1959年11月,在赫鲁晓夫访美后两国关系呈现缓和局面的情况下,美苏签订了第二份文化交流协定,大大扩展了相关计划,为哈佛大学与列宁格勒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与莫斯科大学之间的直接交流提供了条件,协定还包括两项科学交流协议的附录。1962年3月签订的第三份文化交流协定增加了近15%的项目,并且同意资深学者、讲师交流以及设立语言教师的暑期课程。这些协议反映了1963年夏季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后所迎来的美苏关系改善的一次高潮,因此1964—1965年度是美苏学术交流的高峰期。但随着美国逐步扩大在越南的军事干预以及苏联关注到交流中所暴露的意识形态问题,1964年2月签订的文化交流协定大幅削减了学术课程。1966年3月的文化交流协定又进一步削减了相关项目。1967年美苏之间开展的学术交流项目比前9年的平均水平低30%。1968年7月15日在莫斯科签署的协定中,学术交流规模进一步缩小。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决定从越南战争抽身、中苏关系紧张以及苏联国内粮食危机的进一步加深,都迫使美苏之间缓和关系。于是1970年2月10日签订的文化交流协定在项目和人数上都有所增加,不过并未超过60年代中期的水平。(33)Robert F. Byrnes, Soviet-American Academic Exchanges, 1958—1975, pp.41-49.由此可见,实际交流的波动往往落后于政治发展两年左右,这表明包括学术交流在内的美苏文化关系反映而不是直接影响了美苏关系的重大变化。
关于冷战中美苏学术交流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对苏联而言,在这一过程中学习到的美国科学与技术提高了科技水平,促进了本国工业的发展,缩小了与西方科技的差距。例如苏联列别杰夫物理研究所的半导体和量子无线电物理学专家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波波夫(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Попов),曾先后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加州理工大学和加州大学从事学术交流活动,在微波激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甚至领先美国学者。美国中央情报局经调查认为,其研究受到苏联政府的直接指示,并且在其回国后利用在美国获得的知识帮助苏联展开以激光为有效武器的军备竞赛。(34)Amos K. Wylie, “Unfair Exchange,” CIA Historical Review Program, September 18, 1995, pp.9-15.另一方面,通过和美国的交流,苏联政府向外界展现出这样一种形象,即苏联不是一个威胁,苏联谋求世界和平的姿态,也为苏联领导人赢得了尊重和声望。但是,伴随着苏联打开国门,以及和美国日益密切的文化交往,苏联国内受到的美国文化影响越来越多,使得苏联从知识分子到文化界对西方社会的看法逐渐发生转变,苏联政府对于国内思想的控制也逐步减弱。在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中出现了不同意见,越来越多的苏联人要求所谓的自由。绝大多数忠诚的苏联公民也可能会受到他们曾出国的同事或与外国人密切接触的影响。这种变化,尽管在短期内对苏联所产生的不利影响较为有限,但从长远来看,通过学术交流所获得的科学技术优势,逐渐被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异见所淹没,经过发酵也导致了思想界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混乱局面。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曾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苏共政治局委员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Яковлев)。雅科夫列夫曾于1958—1959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师从反共的政治学家大卫·杜鲁门(David Truman)并深受其政治多元化观念的影响。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雅科夫列夫作为意识形态的主管,是所谓“公开性”运动的实际推动者,也是苏共高层领导中西化的代表人物。(35)孙铭:《瓦解苏共的思想杀手——雅科夫列夫》,《红旗文稿》2014年第11期。苏联国防部长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亚佐夫(Дмитрий Тимофеевич Язов)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рючков)都曾提到,有确切情报表明雅科夫列夫在美国学习期间曾被美特工机关策反。(36)黄登学编译:《“变节”分子成了苏联解体的内部“推手”——俄罗斯〈独立报〉采访前苏联国防长Д.Т.亚佐夫》,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编:《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2011—201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39页;弗·亚·克留奇科夫:《雅科夫列夫有谍嫌》,王树本主编:《世事复多变 历史有新说——〈参考消息〉连载文章集粹之三》,北京: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1994年,第135—136页。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在其《软实力:世界政治的制胜之道》一书中也以雅科夫列夫为例指出“文化交流对精英们的影响,一两次关键的接触就能产生重要的政治效果”,此外他还引用与雅科夫列夫同期赴美学习、后来成为克格勃高级官员的奥列格·丹尼洛维奇·卡卢金(Олег Данилович Калугин)的话证明了文化联系所产生的软实力为美国实现其政策目标所发挥的作用——“交流对苏联而言就是特洛伊木马。他们对苏联制度的侵蚀起到了无与伦比的作用,……这种交流多年来持续影响了更多的人”。(37)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4, p.46.
对美国而言,和苏联学习到的先进科学技术相比,似乎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好处。因此,美国民众乃至美国政府中都有部分人认为,美苏学术交流是一种“不平衡的交流”,美国在科学技术知识方面存在着损失。但实际上,对于苏联试图和美国就某个领域展开交流的请求,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都会提前进行评估,以决定是否同意。同时,美国方面还想方设法使访问者与应用研究和开发环节隔离,将交流活动限制在基础科学领域。例如,美国政府拒绝了苏联教育交流代表团访问IBM罗彻斯特工厂的请求,并通知苏联大使馆此类请求未来需要向国务院提出,而不能直接向美国工业界或研究单位提出。(38)James McGrath, “The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Exchange,” CIA Historical Review Program, September 18, 1995, pp.25-30.与苏联不同,美国在学术交流中更关心的是思想文化方面的好处,美国希望通过让苏联获得先进技术,以得到媒体自由和文化渗透的权利。美国方面负责发起和实施学术交流计划的人实际上并未指望交流本身能够对苏联社会的自由化直接起到决定性作用,然而他们却意识到交流可以推动苏联精英阶层对美国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及价值观的态度从否定转向羡慕与崇拜。事实上也确有一些苏联大学生和年轻的知识分子,甚至包括国际政治和经济研究机构的年轻成员,逐渐对官方意识形态中的反美观点持有异议。一些曾参与对苏学术交流的美国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则认为,苏联对西方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方法产生兴趣、苏联生物学研究各方面的进步以及苏联对先进工业管理技术的热情与日俱增等一系列从所谓“开放社会”的角度来看的积极成果,事实上也都可以归因于学术交流。尽管这些趋势难免会加速苏联国力的提升,但在美国相关人士看来,对于渴望苏联社会朝着自由化方向演变的努力来说那也是值得的。
美国政府通过学术交流加强了对苏文化渗透并且获得了许多情报,为其更好地制定对苏政策服务。每年去苏联交流的美国学者都要接受中央情报局的询问,从而为其提供分析判断苏联国情所需的素材。中央情报局还在文化交流协定生效期间建立了一些临时的假冒基金会,如诺斯克拉夫特教育基金会(Northcraft Education Fund)和J.N.卡普兰基金会(J. N. Kaplan Fund),旨在将间谍以“学生”身份派往苏联搜集情报。1962年,一个旨在帮助青年学者同苏联学生进行交谈的“跨文化交流项目”被巧妙地设立,相关学术组织为其发布了广告,还有两位研究苏联政治问题的高级学者担任其理事。随后,在中央情报局的控制下该项目开始向苏联来访学者提供学术书籍,并在他们返回苏联后继续以该项目的名义邮寄更多资料。美国情报机构利用学术交流活动进行文化渗透的这些勾当非常普遍地存在着,因而也经常被苏联方面谴责为“情报阴谋”。(39)Robert F. Byrnes, Soviet-American Academic Exchanges, 1958—1975, pp.144-147.当然,一些赴美交流的苏联知识分子通过在美国的工作和生活对美国也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认识,客观上确实受到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对于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心被不同程度地瓦解,这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结 语
受冷战影响,1958—1972年间的美苏学术交流规模有限,并且面临很多困难,但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它反映了美苏两个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根本对立的国家尽管处于冷战当中,但仍存在着走向对话与合作的可能。通过这一时期的学术交流,美苏双方更加了解彼此,懂得适应对方国家的法律和传统,学会如何与对方正常交往,包括学术交流在内的文化交流得到两国政府的重视,文化关系成为双边关系中较为稳定的因素,由此为20世纪70年代美苏关系缓和期间双方开展更广泛、开放的学术交流打下良好的基础。
通过学术交流,到美国学习的苏联科学家和其他学者确定无疑地获得了相当有用的知识。交流对于苏联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则更为深远。同时,在交流中美国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渗透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后来苏联国内思想混乱的局面。因而美国达到了对苏开展文化冷战的目的,并且其影响不断增大。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冷战期间国际局势的影响,美苏通过1958年文化交流协定所建构的有关文化交流问题的协商机制基本被确定下来,这种形式的交流合作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为冷战时期两国关系的缓和提供了一些契机。冷战期间,当美苏两国在其他问题上面临尖锐冲突时,双方都转而在文化层面寻求共同利益,试图用文化交流来缓和在其他领域的对抗。因此,冷战时期美苏学术交流作为双方文化关系的重要环节,其意义不应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