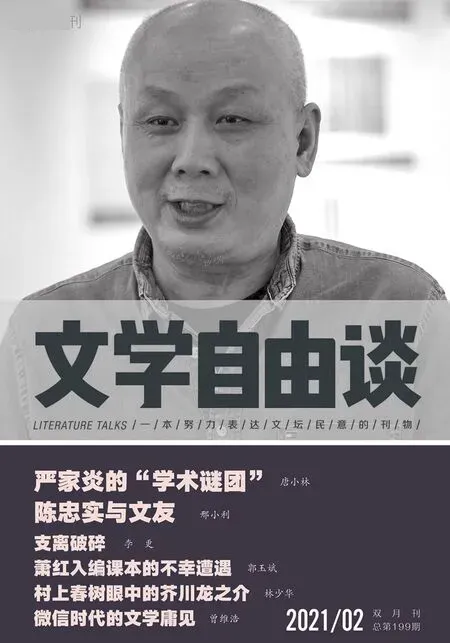自省录(二)
2021-03-08陈世旭
□陈世旭
幻觉
1980年夏,我在中国作协第五期文讲所学习结束,回到小镇。省里文学期刊《百花洲》的诗人编辑洪亮出差路过,顺便来寒舍小坐。问及我在京学习的感受,我说压力很大。他很同情地看着我,说:我理解。我们编辑部议过,新时期文学,省里并没有达到全国水平的作者。你觉得压力大,是因为你把自己放在了全国水平。
我心里“咯噔”一响。
然而,也就是“咯噔”一响而已,未必认可。那时候,江西那些后来被京城影响最大的著名作家流泪击节盛赞的名家名作,以及被全国评论界列入中国小说几十强的国家级作家,尚没有登场。我口中没说,心里颇有些“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自负。
去京之前就知道了,那期文讲所的许多人,都是我之前仰望的文学星空的明星,遥不可及。跟他们一块待了几个月,我居然有了一种幻觉,以为自己已是与他们平起平坐的角色了。
这种幻觉在很长一段时间如影随形。
1986年,随几位作家到湖南岳阳,当地文联热情安排登岳阳楼。岳阳楼一楼和二楼的中堂都挂着檀木镌刻的巨幅《岳阳楼记》,是清代书家、时任县令张照的法书。为安全起见,一楼挂的是后人的摹本,真迹在二楼。听介绍时,我煞有介事地颔首沉吟。登楼完毕,回到一楼大堂,我再次久久注视摹本,深沉感叹:这真品比楼上的摹本就是强多了!说完周围一片寂静,我以为众人大有同感,不料一位北京作家说:你瞎掰什么?这是摹本,楼上的是真品!
当时的感觉,真是恨不得有条地缝钻进去。岳阳的朋友赶紧打圆场,说摹本的确几可乱真,许多人都搞不清的。我立马轻松,心里跟着就自宽自解:谁敢说自己没有知识盲点?
又几年,出差深圳,在深圳大学任教的作家南翔出于同乡之情,邀我去给他的学生作讲座。当时,众多北大早年大师的风范正是高校的时髦。我于是端起架势大讲“正如王国维所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云云,底下的大学生听着,一个个瞠目结舌。讲座结束,南翔开他的私家车送我去机场。只有我们两个人了,他像是跟我探讨似的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应该是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上的题词吧?
我支支吾吾。因为我当时根本就没闹清陈寅恪、王国维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是不知在哪儿听过那句话。
王朔有句名言:无知者无畏。他是调侃,我是事实。
绝对自以为是的幻觉,让我一再出乖露丑,至今想起,仍不免恶心。无知并不是罪过。我恶心自己的是无知硬充有知,用我务农的乡下话说是“手捏那玩意儿——充六指头”,轻狂自大,不可一世。
小人得志,固然是一种幸运。但有时候,也未必不是一种灾难。
小聪明
因为《小镇上的将军》获奖,我被调到省里专业写作。好长一段时间,每天打开稿纸,脑子一片空白,一整天一整天地发呆。许多关心我的人急坏了。省报上有了公开的议论,关于我的“苦闷”,关于让我离开基层是否明智……私下的说法就更加尖锐,形容为“只生一个好”之类。我焦虑不堪,惶惶不可终日。
有一天,我在单位资料室看到一篇翻译的苏联作家短篇,讲一个集体农庄的青年进城卖农产品,他很诚实,却不被信任,很生气,几乎跟人打起来。我眼前一亮。在小镇做农民通讯员期间,我也听到过类似的故事:
一个山里青年把自家烧的木炭挑到集镇上卖,镇上人故意挑剔,一会儿说烧炭的树木不是硬木,一会儿说炭没有烧透。那青年火了,把两大篓子炭全倒出来,一根一根在地上踏碎,一边踏一边说:给你看,给你看,是不是硬木,烧没烧过心!
我照搬那个苏联小说的结构,把这个情节塞进了现成的框架,表现山里人的纯朴,题名《山里山外》,不久就在《十月》发出来了。
收到样刊的时候,我长长地舒了口气。忽然有一天,一个同事悄悄告诉我:领导收到了检举信,说你抄袭。检举信并说,已经要求《十月》编辑部刊登启事,声明《山里山外》是个抄袭作品,向读者检讨。
抄袭就是偷窃!
我当时站在阳光灿烂的大街上,一阵眩晕。用得上《静静的顿河》里的一句话:格里高利抬起头,看见太阳是黑的!
《十月》编辑部的启事一直没有登出。但我的心理危机并没有解除:《山里山外》故事的素材虽然来自我自己的生活积累,但我也不能否认,小说结构的确是从那个苏联小说的模子里脱胎出来的。我更不能左右《十月》编辑部对此的判断,单纯站在刊物角度,他们完全可以采取更严格的判断标准。无论如何,这种做法至少是投机取巧的一种。
《十月》可能刊登的“启事”或是“读者来信”,就像达摩克利斯剑高悬着。启事一旦刊登,对于我,无异于法院的死刑布告。
按说,经历了这样的危机,任何投机取巧的念头都不该再有了。但要根除一种品质缺陷,谈何容易?
1993年由中青社出版的长篇《裸体问题》,其实是众多中短篇小说的组合。出书前,我临时补充了一些章节。这些章节没有作为单篇发表过。2010年,深圳《特区文学》革新版面,大幅度提高稿酬。接到他们的稿约,我自是高兴,新的稿费标准是那么诱人,但苦的是手头一时没有存稿,新写一个不知要到猴年马月。这样的机会很难轻易放弃,投机取巧的念头又油然而生。
我把《裸体问题》里那些没有作为单篇发表过的章节摘出,戴帽穿靴,鼓捣出一个中篇,题名《特区三色旗》。我满心侥幸:那个长篇是在北京出的,而且已经好几年了,深圳未必有人读过。自我复制,江郎才尽而已,与抄袭别人毕竟不是一回事。
稿件采用,我引颈鹤望提高了标准的稿酬。
我等来的是责编一封措辞简洁明了的电邮:读者举报,该作摘自旧作。经查,属实。
我盯着电脑上的那行字发懵。良久,有气无力地回了个道歉的电邮,却又特别“大度”地加了一句:稿费你们就别给了。
已经让人家的声誉受损了,还好意思提稿费,真是混账到家了!
《山里山外》《特区三色旗》都是毫无影响的作品,但对我的写作却有着极重要的意义,让我铭心刻骨地记住:
永远不要指望投机取巧不会被读者发现。
小聪明终难修成正果,更不用说成就什么大器了。
一个作者如果不能得到光明正大的成功,至少不应该让所有善待自己的人们失望。
读者的视野
先天才华和后天修养的缺失,让我的写作始终步履维艰。《小镇上的将军》发表之前,我写过十几个短篇,除了一两篇在地方报刊发出,大多成了废纸。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写的《小镇上的将军》,发表前也先后被两个刊物退稿。获奖作者座谈会上,大家聚精会神聆听大评论家冯牧先生讲话。我头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诚惶诚恐。忽然听到他点我的名字,以为会有“新秀可喜”一类夸奖,听到的却是:据说,他写了《小镇上的将军》后,就再也写不出东西了。
我当时受到的冲击无法形容,说是痛不欲生亦毫不为过。
冯牧先生的“据说”,显然反映的是一种普遍的舆论。他在这样的公开场合说出此言,表现出对一个青年作者的殷切期望,恨铁不成钢。只是他没有想到,对一个来自遥远乡镇、从未见过大世面的极其脆弱的心灵,这是一种几近毁灭的打击。
“再也写不出东西了”像一句魔咒,一语成谶。
成名作即是代表作。我最终也没能爬出这个让人深怀恐惧始终不甘的陷阱。
想要爬出陷阱的愿望是如此丧心病狂。小说一旦刊发,就眼巴巴地注意有没有评论,会不会转载。热心的朋友推荐评奖,我口里忸怩作态,实际半推半就。写文章说只问耕耘不问收成,心里却饥渴着奇迹的发生。《裸体问题》出版后,出差北京的同事回来转告,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文学评论》让你请评论家写个评论在他们那里刊发。我大喜过望,立刻给只有一面之缘的李洁非先生打电话,劳他大驾。他很仗义,文章很快写出,但《文学评论》一头雾水:根本就没有人约过《裸体问题》的评论。同事的转告无疑出于好意,可笑的是我根本没有核实就信以为真。
很长一段时间,外界的所有响动,跟自己有关无关,都有可能让我心惊肉跳。
刚学会电脑,无聊上网,忽然发现一个文学网站对我的介绍,生辰八字之外,关于我的写作就一句话:
文字朴实没有趣味。
一个正常人,对这样的评论,正确的做法是努力让自己的文字有趣,但我的做法是设法让网站别说我“没趣”。
拐弯抹角打听到这个网站在辽宁,赶紧给辽宁的名家刘兆林去信,请他帮忙找找这家网站的负责人,看看能否删去这八个字,或者至少是后面四个字。
我的理由振振有词:网站应该秉持客观立场,引述各种见解,不宜直接评判。
这样的本末倒置,结果当然是让自己更加没趣。
我不得不接受难堪的事实,写了长文《平庸的生活和平庸的写作》,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的平庸。
这种平庸其实从一开始就已定型。一切在莫大程度上被基因所决定,难以改观。即使因为偶然因素凑巧获奖的作品,在专业范围的认可也是相当有限的。而今,我专业写作快一辈子了,或有进步,但退稿依旧是常事。编辑部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退他们自己约的稿。虽然可以拿取舍眼光不一来安慰自己,但也说明作品没有达到公认的水准。近年因为微信的方便,读到阿成、储福金、肖克凡的中短篇,他们选材不以时胜,叙述唯重生活本身的固有韵律,从容、流畅、圆熟,让我看出自己与真正的小说艺术还相距甚远。
有一次参加一家出版社的活动,同车的几位男女青年作家、编辑、记者对我一无所知,很奇怪出版社怎么邀请了这么个不相干的人来。我背过身去,默默听着他们的窃窃私议,很后悔接受了这次邀请。一个写作者连圈子里的人都不知道,也就是那首著名的诗说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但我的心没有死。
2014年,距冯牧先生那次讲话三十四年后,我刚杀青一个长篇。在一次通电话时,我顺便告诉一位正值创作盛期的新锐作家,暗自期待一声祝贺,没想到对方突兀地说:怎么写你也不在读者的视野了。
这位作家是个实在人,心直口快,以他的敏感,很容易就听出了我的嘚瑟。尽管话很直率,却是善意的提醒。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说得一点不错。那个小说出版后,一位在深圳某企业当头儿的朋友邮购了一百本,用于企业文化活动。一年后,那位朋友很尴尬地跟我说,那堆书一直原封未动,无人问津。我赶紧找了一位大学毕业分在当地工作的小老乡,开车拉走处理了事。
对于一个写作者,有什么比这更悲哀的呢?写作的终端不在完稿,不在刊发和出书,而在读者。希利斯·米勒说:“文学是通过读者发生作用的一种词语运用。”没有读者,前面做的一切都是瞎耽误工夫,不过是给朋友添麻烦、给社会添垃圾而已。
不时听到对过气写作者的奉劝:生命力、创造力枯竭了,就该“歇菜”了。更有一种激愤观点认为:作家不伟大,就一定无耻。
写,还是不写?成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
在微信中与文友谈起,《北京文学》的晓升兄颇不以为然:你写你的,管人家说什么!
仿佛是在疲惫不堪的沙漠跋涉中遇到的一泓甘泉,直沁心脾。
是啊,写作是个人权利的一种。一百多年前的外国文豪就说过,大狗叫,小狗也叫。小狗叫有什么可非难的呢?只有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争取非分的荣誉,非要钻进大狗之列不可,或者干脆自封甚至冒充大狗,才是无耻。
这样想着,我又坦然。只要还有一家刊物约稿,我就不必放弃写作。如果哪天没有稿约了,我依然可以把文字当作不离不弃百依百顺的情人,倾情相与,直到荷尔蒙耗尽。古往今来世上的所有写作,并不一定都为光宗耀祖,也不一定都为稻粱谋,更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奢望功勋牌或是垫棺材的砖头,登上金榜,载入史册,有故居有纪念馆,被今人和后人研究和瞻仰之类。有些仅仅是一种痴迷,一种消磨,一种性情,一种内心的抒发。一个写作者即便不在读者视野,终至被读者完全遗忘,也至少会有一个绝对忠实的读者,那就是他自己。
结语
从十余岁下乡谋生,每天田间地头、灯下床上折腾文字算起,投身文学,近一甲子了。虽然无可自矜,所幸终日矻矻,与文学相伴了一生。曾与朋友谈及一同起步的同行许多已巍然成为参天大树,朋友叹息我们才情有限,最多算棵草而已,很没劲。我同意他的比喻,却不同意他的自卑。没有长成参天大树,长成了草,也是文学原野上的生命。而且,一粒种子,能长成一棵草,生动地活着,其实也并不容易。参天大树不是一天长成的,草又何尝不是?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能少。不说社会历史那么高大上的原因了,仅仅是为了帮助一个写作者安于平凡,心无旁骛,坚持写下去,文坛多少良师益友就不知付出了多么良苦的用心,给予了多么宽广的包容。
看过《文学自由谈》2021年第1期刊发的我的《自省录》,反应不一。好心的朋友觉得人无完人,不必过于苛责,有些失误无足轻重,专文提及,反而过犹不及;也有人批评为故作姿态,玩深沉,刷存在感,状若乞丐,自我打脸引人注意。
我感谢朋友的温暖体贴。至于笑骂,姑且理解为人性的一种。我所指望的,只在日子能尽可能单纯,内心能尽可能清静,放下种种人生负累,自我解脱。
一个写作者最大的负累,莫过“功名”二字。放下对功名不现实的企求,是万缘放下之始。人生固应有高远的抱负,但在阅历相当后,也应有相应的清醒。检点自己,如同搓澡去垢,写作就或许有可能成为一种轻松愉悦的精神运动。
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