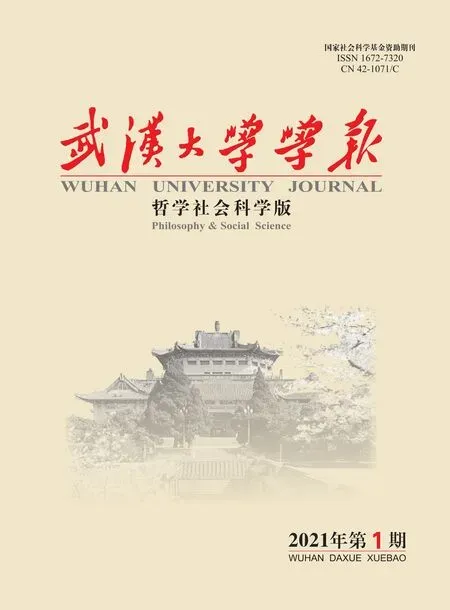方物:从永州摩崖石刻看文献生产的地方性
2021-03-06程章灿
程章灿
“方物”一词,本来是指某个地方的特产,其意略近于土产、特产之类。从物质生产的角度来说,无论是中心之地,还是偏远之区,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产。“方物”一词有着悠久的传统,不过,在古代东亚政治话语体系中,“方物”又是与“贡献”这一古代东亚政治制度密切相联的。《尚书·旅獒》:“无有远迩,毕献方物。”传曰:“天下万国,无有远近,尽贡其方土所生之物。”[1](P1846)一般情况下,都是遥远、偏僻之地向中心之区贡献方物,通过这样一种形式,确认中心对于地方的权力,以及地方趋向中心的认同。这些来自远方的方物,亦可称为贡物,地理位置越是偏僻,相隔越是遥远,道路越是艰险,进贡越不容易,那么,贡献到京城的方物的地方性往往越是突出,其政治文化意义也就越为强烈。当然,也有许多方物的获得,不是通过进贡,而是经由商品贸易等经济交流方式,虽然没有政治意义,但却同样具有地方性。这种地方性不仅表现在其原材料来源,也表现在其制作方式,还表现在其使用方式。正是这些内容与形式的配合,造就了方物的地理识别度及其文化政治的象征意义。
与普通的物质生产一样,古代文献生产中也存在着地方性。这种具有地方性的文献,就是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上的“方物”。从内容上说,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的各色地方志(简称“方志”),其中就包含对于本地各种方物(人、事、物)的记载。从形式上说,则有例如版本学上经常提到的、也已经得到学术界较多研究的“建本”“杭本”“蜀本”等。这些地方性文献的生产,一方面利用了本地特有的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另一方面也引入或融合外来的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在石刻文献生产中,也有一些具有强烈地方性的石刻生产与拓本制作方式,例如,昭陵碑刻、泰山石刻、北京房山云居寺刻经、永州及桂林等地摩崖石刻等,就是地方性十分突出的文献方物。本文以永州摩崖石刻为例,考察中国古代石刻文献生产的地方性问题。
一、摩崖刻石的文化传统与时空交叉点
永州的摩崖石刻文献资源十分丰富,其中,阳华岩、朝阳岩、浯溪、玉琯岩、月岩、澹岩、月陂岩七处都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永州摩崖石刻经历“唐代创始,宋代流衍,明代追摹,清代考据”的漫长过程,数量繁多,形式多样,“呈现着清晰的阶段性和连续性”[2](前言 P1),文化意义也特别丰富。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摩崖就是永州石刻的代表,当之无愧;另一方面,永州摩崖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摩崖石刻的内涵,将其称为中国摩崖石刻的典型代表也不过分。
中国古代石刻类型繁多,仅清人叶昌炽《语石》之中所列举的就多达 43种,其中第26种为摩厓(即摩崖)[3](P182-383)。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将石刻分为七种,而将摩崖附列于“杂刻”类中[4]。石刻文献分类,大多根据石刻的文献形式,有时候也兼顾其内容特点,难免有所交叉。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摩崖石刻都有明显的特征,不容易与他者相混。
首先,从物质媒介来看,摩崖石刻是一种“天然之石”,“其先盖就其地以刻石纪事,省伐山采石之劳”[5](P68)。虽然崖石在刊刻前也要进行整治,除去表面杂草土块,求其平整,但与碑志等需要经过开采、磨砻乃至运输等程序相比,摩崖节约了很多人力物力成本。就这一方面而言,摩崖显然具有明显的媒介资源优势。
其次,从视觉效果上说,摩崖依托山崖的高大雄伟之势,容易凸显宏大雄浑的效应,借助山崖水滨的自然地势,容易产生景观审美的效果。例如,永州浯溪摩崖《大唐中兴颂》,规格为310cm×320cm,字径四寸五分,非一般碑石可比。一般来说,摩崖是不可移动的①近代以来,在道路开凿和水利工程兴建过程中,曾对一些摩崖石刻进行切割、迁移,此乃出于保护摩崖石刻之目的,非摩崖石刻当时之本意。,与大自然浑然一体,借用陶渊明的诗句来说,就是“托体同山阿”[6](P293),寓有与天地共长久之意。值得一提的是,在永州摩崖以及其他各地摩崖中,也可以看到崖壁上的一些“嵌入式碑刻”。这些“嵌入式碑刻”的出现,是因为日积月累,前人题刻遍布山崖,后人很难找到适合刻石的摩崖空间,只好以一种小碑(竖式,或帖式横碑)嵌入作为替代品。这是摩崖刻石的变通方式,也可以视为摩崖石刻的衍生形态。摩崖刻石是天然山崖的一部分,是不可移动的文物,而这种“嵌入式碑刻”则是经由人工移植、装嵌,与不可移动的山崖融为一体,其性质介于移动与不可移动之间。如果需要命名,那么,前一种可以称为“原生型摩崖石刻”,后一种可以称为“再生型摩崖石刻”。“再生型摩崖石刻”既是永州摩崖石刻的特色,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从文化意义上说,摩崖刻石融山川自然与人工镌刻于一体,通过这样一种特殊的石刻形式,表达一种恢弘、庄严的政治或文化主题,不仅能够体现内容与形式的和谐,而且具有某种得天独厚、天人合一的象征意义。《大唐中兴颂》结尾诸句,“湘江东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齐。可磨可镌,刊此颂焉,何千万年”,即有这种“天人合一”的意涵。
从摩崖石刻产生的历史来看,它也具有独特的文化渊源。摩崖刻石起源甚早。据《韩非子》记载,秦昭王曾与天神赌博于华山之上,并刻石于华山崖壁之上②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文心雕龙·铭箴》所谓“秦昭刻博于华山,夸诞示后,吁可笑也”,即指此事。,此事虽然未必可信,却说明摩崖这种石刻形式很早就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很早就被用来处理人神交往、天人之际的事务。石刻包括摩崖石刻,可能是秦文化传统中的一部分。这一传统可以上溯到秦石鼓和秦昭王刻石,下接秦始皇东巡刻石。秦始皇东巡六刻中,五刻皆为石碣,可谓上承秦石鼓,唯有河北秦皇岛碣石山摩崖石刻,可谓上承秦昭王华山崖壁刻字③饶宗颐曾提出,“石刻的发展,与秦地文化似乎很有密切的关系。”“刻石的风气是秦人加以发展的。”“刻石文学,是秦文化中一种重要表现,有它的很长远之渊源的。”[7][8][9](P197-232)。所谓碣石山,顾名思义,就是以山为碣。与石碣相比,碣石山借助自然、托体自然,较少人工痕迹,在形制上也更加宏伟。从文体上看,碣石山摩崖刻石与秦始皇东巡五刻一样,都属于“三句为韵”的“颂”体[10](P318)。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刻石是在秦始皇三十二年(前 215),其背景是:“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山。”[10](P318)羡门、高誓,皆是古之仙人。可见此次刻石与秦始皇求仙有关,亦即与天人之际相关。换句话说,这次摩崖石刻的产生,正处在一个重要的时间和空间的交叉点上,与此同时,摩崖石刻制造了一个不可移易的历史现场。
汉代石刻中,也有几件摩崖,其所处的时间和空间的交叉点也有特殊的意味。例如《鄐君开褒斜道记》《石门颂》《西狭颂》《郙阁颂》等,其地多处于秦蜀交通的险要之地,因为有了摩崖刻石,有了记录历史性事件的文字,这些偏远之地从而有了文化标记,引人注目。南北朝特别是北朝,造像石窟甚多,叶昌炽所谓“晋豫齐鲁间,佛经造象,亦往往刻于摩崖”[3](P357),主要就是指这一时期。此类摩崖石刻比较著名的是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经文为隶书,刻在约3000平方米的大石坪上,原有2500多字,现尚存1067字。它反映了佛教信仰在北朝社会的流行。
初盛唐摩崖石刻,最重要的是开元十四年(726)九月所刻《纪泰山铭》,亦称《东岳封禅碑》或《泰山唐摩崖》,这是上一年十一月唐玄宗封禅泰山留下的历史记录[11](P131)。此篇铭文为唐玄宗亲撰并书,刻于岱顶大观峰石壁之上,高1320厘米,宽530厘米,正文隶书24行,满行51字,现存 1008字,字大16cm×25cm,形制雄伟,非寻常碑刻所能比拟。泰山地位崇高,从秦始皇刻立石碣到唐太宗刻摩崖铭文,后代继起刻石者不胜枚举。泰山石刻现存1800余处,摩崖石刻多达1000余处,超过碑碣。总体来看,泰山石刻大部分是自然石刻,也就是摩崖石刻。
二、从元柳对照看元结与永州水石的因缘
永州摩崖的出现背景,与上述各种摩崖皆有不同。永州摩崖石刻的大量出现,与元结个人的关系特别密切。在元结之前,永州水石籍籍无名,绝不能与华山、泰山相提并论。元结是永州水石的发现者、欣赏者和开发者。
元结(719—772)于广德元年(763)敕授道州刺史(道州,治今永州道县),至大历七年(772)朝京师而离开永州,前后留居此地十年。他对永州有深厚的感情,刻石特别是摩崖刻石是元结表达这种感情的最主要的方式。永州本地学者已经指出:“元结在永州,时间久,创作多。其诗文开拓景地及命名景地最多,其文体以铭最多,其书体以篆最多,其新造景地名义最多,其作品刻石最多。其影响于后世,形成摩崖石刻景区最多。至于近代,其惨遭毁坏亦最多。”[12](P240)这八个方面的“多”可以概括为“八多”。“八多”的核心就是元结在永州留下的石刻,亦即永州摩崖石刻。
元结在永州留下的石刻,最有政治意义、最名闻遐迩的是《大唐中兴颂》。其序云:“天宝十四载,安禄山陷洛阳,明年陷长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于灵武。明年,皇帝移军凤翔,其年复两京,上皇还京师。于戏!前代帝王有盛德大业者,必见于歌颂。若今歌颂大业,刻之金石,非老于文学,其谁宜?为颂曰。”[13]显然,这是一篇歌唱大唐中兴的颂歌,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全篇正文45句,句句用韵:
嘻嘻前朝,孽臣奸骄,为昏为妖。边将骋兵,毒乱国经,群生失宁。大驾南巡,百寮窜身,奉贼称臣。天将昌唐,繄晓我皇,匹马北方。独立一呼,千麾万,我卒前驱。我师其东,储皇抚戎,荡攘群凶。复服指期,曾不踰时,有国无之。事有至难,宗庙再安,二圣重欢。地辟天开,蠲除祅灾,瑞庆大来。凶徒逆俦,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劳位尊,忠烈名存,泽流子孙。盛德之兴,山高日升,万福是膺。能令大君,声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东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齐。可磨可镌,刊此颂焉,何千万年。
黄侃曾说:“秦刻石文多三句用韵,其后唐元结作《大唐中兴颂》,而三句辄易,清音渊渊,如出金石,说者以为创体,而不知远效秦文也。”[14](P73)他指出了《大唐中兴颂》与秦始皇东巡刻石文之间的渊源关系,这是一个相当敏锐的观察。但是,也必须指出,《大唐中兴颂》与诸篇秦始皇刻石文之间也有不同之处。首先,《大唐中兴颂》是元结自发的创作,是个人行为;而秦始皇刻石文则是李斯奉命而作,是李斯的职务身份所决定的,是官方行为。其次,从形式上讲,元结之颂虽然“远效秦文”,但与秦刻石文又有明显不同。秦刻石文大多是“三句用韵”①“三句用韵”,如泰山、之罘山、之罘东观、碣石山、会稽山刻石文。,亦即三句一韵,亦偶有“两句用韵”者,如琅琊台刻石文[10](P310-311)。所谓“三句用韵”和“两句用韵”,都是指每隔三句或两句用韵,构成一个单元的三句或两句之间,彼此并不谐韵。《大唐中兴颂》则是“三句辄易”,也就是每三句一换韵,构成一个单元的三句之间,句句谐韵。总之,《大唐中兴颂》与秦始皇刻石文在形式上的共同点可以这样总结:二者同为四言颂体,同样以三句为一单元,同格风格古雅。简言之,元结和李斯同样为一个王朝写作颂歌。
《大唐中兴颂》作于上元二年(761),其时元结在江陵,任荆南节度判官。两年后,他才出任道州刺史,此颂在浯溪刻石则迟至大历六年(771),撰刻二事相距十年。这一点摩崖石刻上写得清清楚楚。清代金石家王昶曾有一个疑惑:“其刻《峿台铭》在大历二年,《浯溪铭》《亭铭》俱在大历三年,不知何以刻此颂独迟至大历六年也?”②按:王说不确,据《永州摩崖石刻精选》第76-77页,《浯溪铭》刻于大历二年。[15]实际上,元结初作此颂之时,并无刻石动机,或者说,江陵没有适合摩崖刻石的地理条件。直到他来到浯溪,发现了这里的崖壁,才有《大唐中兴颂》的摩崖刻石。
元结对永州文化的最大贡献,就是以摩崖的方式命名了永州水石胜迹,留下了多处摩崖铭刻。他是永州摩崖石刻的创始者。现存最早的是永泰二年(766)所刻《阳华岩铭并序》,瞿令问所书,序文隶书,铭文则大篆、小篆、隶书三体并用,模仿曹魏正始石经,大有自我作古之意。元结自称“漫叟”“漫郎”“浪士”,足见他是一个浪漫之人。浪漫,从一个方面来说,意味着对传统和陈规的不以为然。元结热爱永州山川,对这里的山水极为认同。他所命名的“三吾”,亦即浯溪、峿台、庼,明确了他对山水亭台的享有③元结《浯溪铭》:“溪古地荒,芜没已久。命曰浯溪,旌吾独有。”,也表达了他与永州山水亭台融合无间的态度。另一方面,“峿字、字,不见《说文》,次山出新意为之”[3](P122),颇具创意。要之,在对待山川命名的时候,元结是敢于创新,敢于自我作古的。
元结对永州山水的认同,根底在于他对永州“水石文化”的认同。“水石文化”的概念,最早是李花蕾和张京华所撰《元结与永州水石文化》提出的[12](P240-269),很有启发。据笔者统计,在《次山集》中,“水石”一词一共出现了15次:
1.丛石横大江,人言是钓台。水石相冲激,此中为小回(《漫歌八曲·小回中》)。2.小溪在城下,形胜堪赏爱。尤宜春水满,水石更殊怪(《游右溪劝学者》)。3.广亭盖小湖,湖亭实清旷。轩窗幽水石,怪异尤难状(《宴湖上亭作》)。4.水石为娱安可羡,长歌一曲留相劝(《朝阳岩下歌》)。5.沟塍松竹,辉映水石。尤宜逸民,亦宜退士(《阳华岩铭》)。6.丹崖,湘中水石之异者,翁,湘中得道之逸者(《丹崖翁宅铭序》)。7.爱其水石,为之作铭(《丹崖翁宅铭序》)。8.至零陵,爱其郭中有水石之异,泊舟寻之,得岩与洞(《朝阳岩铭序》)。9.于是,朝阳水石,始有胜绝之名(《朝阳岩铭序》)。10.于戏朝阳,怪异难状。苍苍半山,如在水上。朝阳水石,可谓幽奇(《朝阳岩铭》)。11.刻石岩下,问我何为?欲零陵水石,世人有知(《朝阳岩铭》)。12.吾于九疑之下,赏爱泉石,今几三年……松竹满庭,水石满堂(《送谭山人归云阳序》)。13.县南水石相映,望之可爱(《寒亭记》)。14.闻元子亦浪然在山谷,病中能记水石草木虫豸之化(《浪翁观化序》)。15.林野之客,所耽水石(《亭铭》)。
值得注意的是,在通篇不足200字的《朝阳岩铭并序》中,“水石”一词出现了四次,频率之高,令人叹异。具体说来,“水石”中的“水”,包括江(如湘江、潇水)、溪、泉;而“石”则包括岩、洞以及更大的山体。实际上,“水石文化”与更有文学色彩、更有文化渊源的“泉石文化”或者“山水文化”一脉相承,貌异心同。元结《阳华岩铭》正文称此岩“辉映水石”,序中则以“泉石”相称:“吾游处山林,几三十年,所见泉石如阳华殊异而可家者,未也,故作名称之。”在元结眼中,这些山水泉石“堪赏”“可爱”“可赏”,而且“可耽”“可家”,他为它们不为人知赏而叹惜不置。
在元结之后30几年,柳宗元(773—819)被贬永州司马,也在永州生活了大约十年时间(805—815)。这两个中唐文学名家都是永州山水的知音,他们以永州山水摇荡性灵,写下了文学史上不朽的作品。伴随着他们的到来、逗留以及写作,永州山水的声名也远播海内外。遗憾的是,元、柳二人不曾交接。从现存作品来看,柳宗元在文章中很少提到元结,他与元结之间缺少直接的文字交流,只有少量间接的对话。柳宗元诗中仅一处提到浯溪,即《游黄溪记》:“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环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泷泉,东至于黄溪东屯,其间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数,黄溪最善。”[16]但没有直接提及元结。
作为后来者,柳宗元在游历永州山水、交接当地士人的过程中,一定有机会接触到元结的遗迹,听到一些有关元结的遗闻佚事。比如,柳宗元到过朝阳岩,并有《游朝阳岩遂宿西亭二十韵》之诗,朝阳岩在零陵,这是元结命名的名胜,元结在这里留下了《朝阳岩铭》《朝阳岩下歌》等文字①孙望《元次山年谱》:永泰二年,“至零陵,游郭中,得岩与洞,命曰朝阳岩,作《朝阳岩铭》。”[2](P23)[17]。实际上,柳宗元在永州的一些行为方式,也很可能受到了元结的影响。例如,他对永州山水的命名,就与元结殊途同归。愚溪就是柳宗元命名的,他为此作有《愚溪对》《愚溪诗序》等。又比如他的某些刻石文字。柳宗元的碑文,包括墓碑文和祠庙碑文,也有不少与湖南特别是永州相关者。他在《零陵三亭记》中说:“余爱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书于石。薛拜首曰:‘吾志也。’遂刻之。”他的《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也说:“或曰:‘然则宜书之。’乃书于石。”[16]这两篇记文都曾刻石,这种做法也可能受到元结的影响。不过,这两篇记文所写都是人间建筑,而非自然景点,与元结之铭刻有所不同。
元、柳二人对于永州山水自然的态度不同,相当明显地体现在各自的文学作品中。柳宗元《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诗有云:“谪弃殊隐沦,登陟非远郊。所怀缓伊郁,岂欲肩夷巢。髙岩瞰清江,幽窟潜神蛟。开旷延阳景,回薄攒林梢。西亭构其巅,反宇临呀哮。背瞻星辰兴,下见云雨交。惜非吾乡土,得以荫菁茆。羁贯去江介,世仕尚函崤。故墅即沣川,数亩均肥硗。台馆集荒土,池塘疏沉㘭。会有圭组恋,遂贻山林嘲。薄躯信无庸,琐屑剧斗筲。囚居固其宜,厚羞久忆包。”②宋韩醇音释引桓谭《新论》曰:“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一曰隐沦。”按:明正德十六年(1521),朱衮将柳宗元此诗书刻于朝阳岩崖壁之上。[2](P45-46)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柳宗元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及其面对永州山水的心情。简单地说,柳宗元自居“谪弃”之身,与元结自居的“隐沦”之身截然不同。元结外虽为永州地方官员,内则全然是一副“逸民”的“隐沦”心态。《阳华岩铭》云:“尤宜逸民,亦宜退士。吾欲投节,穷老于此。”就是最好的证明。元结多次强调永州水石的可爱、可赏与宜居,而柳宗元则强调自己的“囚居”“包羞”“贻嘲”,诗中充满了“惜非吾乡土”的疏离之感。二者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面对永州山水,柳宗元与元结有着共同的寻奇、访幽乃至探险方面的浓厚兴趣,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一系列山水游记,就是柳宗元在永州寻奇访幽的结晶。这些游记文字每篇都对应一个景点,篇幅不大,并不难刻石。但是,柳宗元的目光所关注的,更多的是流动的水,例如黄溪、钴鉧潭、小石潭、袁家渴、石渠、石涧等,而较少关注山③“永州八记”中,亦有写到西山、小丘、小石城山者。,尤其较少关注岩穴。《柳河东集》中与岩穴相关的,只有《永州万石亭记》《零陵郡复乳穴记》两篇[16]。因此,或许可以说,同样面对永州的“水石文化”,柳宗元更多关注的是“水”,元结更多关注的是“石”。所以,元结“与柳宗元著永州八记而无一石刻,各有异同。柳文以抄本传世,文献远播东亚,元结所为乃是‘不动产’,皆留本土。其贡献于后世有此不同”④按:原文“永州八记”后原衍“九记”二字,已删。此文后亦收入张京华、侯永慧、汤军著《湖南朝阳岩石刻考释》,改题《元结与湖南水石文化》,无“九记”二字。[12](P240)[2](P3)。
总之,面对永州的水石文化,元、柳二公采取了不同的观看方式、不同的记忆方式。柳宗元诉诸纸本的文字,元结采取摩崖的铭刻。由于摩崖文字“托体同山阿”,不仅文字铭刻得以留存,其历史现场亦得以保存。两种文献的生产方式与物质载体不同,传播方式和意义再生产也因之而不同。
三、永州摩崖石刻及其文化景观建构
永州摩崖的出现与永州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连。所谓自然地理环境指的是永州山水崖石。“唐代宗广德、永泰、大历间,元结两任道州刺史,辞官后寓居浯溪,在今永州境内活动前后十年,著述约70篇,其中最值得注意者有19铭一颂。元结在道永二州所游历,则有三溪、三岩、二崖、一谷。元结大规模开辟了今永州境内的景地,开创了摩崖石刻的先河。由其诗文意象所描述而言,永州本土文化可以称之为‘水石文化’。”[12](P240-269)元结所开创的永州摩崖石刻,丰富了中国摩崖石刻的内涵,另一方面,摩崖石刻又以特殊的方式,开辟永州山水文化和地方文化的新境界。
元结不仅命名了三吾胜迹,而且命名了阳华岩、朝阳岩等。他命名的目的,一是为了自我享有,二是为了使胜迹“世人有知”,三是为了使胜迹传之后人。《朝阳岩铭》云:“刻石岩下,问我何为?欲零陵水石,世人有知。”《阳华岩铭序》:“道州江华县东南六七里有回山,东面峻秀,下有大岩。岩当阳端,故以阳华命之。吾游处山林,几三十年,所见泉石如阳华殊异而可家者,未也,故作名称之。”“铭”就是他命名的独特方式。“铭”原本就有“名”之义,《释名》亦云“铭,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称名也”[18]。《文心雕龙·铭箴》:“故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徳。”[19](P193)元结为这些名胜命名的铭文,被铭刻于摩崖石壁之上,可以说是双重的“铭”,也可以说是双重的命名。在这一过程中,他的文字得到了铭文这一文体形式的赞助,得到了书法这一艺术形式的协助,得到了石刻这一文献形式的扶助,成就了所谓“三绝”。正如《大唐中兴颂》经由颜真卿的书写而名扬遐迩,《阳华岩铭》也因为有瞿令问的三体书写而引人注目。《阳华岩铭序》云:“县大夫瞿令问,艺兼篆籀,俾依石经,刻之岩下。”其时瞿令问恰好任职于永州,亦可谓永州本地资源,故得以发挥其书艺之长,使阳华岩有了新的、属于永州本土的“三体石经”。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因为瞿令问书长众体,“艺兼篆籀”,所以他才选择以大篆、小篆、隶书三体书写《阳华岩铭》。实质上,阳华岩特有的“九疑万峰,不如阳华”的胜景,不仅点燃了元结的复古观念和文学创作激情,也点燃了瞿令问的文字书写激情。应该说这是永州与石刻尤其是摩崖石刻的相互成就。
在永州摩崖石刻中,朝阳岩、澹岩二处早著令闻。明人黄焯曾说:“两岩之观,最著者如元子,如周子,如山谷黄子,道德、文章、政事皆可师法。”[12](P81)确实,唐代的元结、宋代的周敦颐和黄庭坚,是永州摩崖石刻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三个人物。这三位一为永州地方官,一为永州本土人氏,一为永州之过客,身份各异,各结缘分不同。他们正好从道德(思想)、文章(文艺)、政事(事功)三个不同的维度,开发永州石刻的文化意义,成为永州石刻的三个文化符号系列。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道德、文章和政事三个维度,分别对应周敦颐、黄庭坚和元结三位名贤,分别对应铭颂、榜题和诗文三种文体。当然,我们也可以不作这样呆板的对应,而是对三位名贤、三种文体和三个维度的关系作更加浑融、灵活的理解。
出于论述条理化的需要与方便,下面就以三种文体为中心,围绕三种文体与三位名贤及三个维度的关系,围绕其所构成的文化符号系列来展开,论述永州摩崖石刻对于永州文化景观的建构。
第一,铭颂系列,以元结《大唐中兴颂》和诸篇铭文为原创和代表。《大唐中兴颂》为永州摩崖石刻确立了一个宏大主题的基调。其后,永州摩崖石刻中相继产生了《大宋中兴颂》和《大明中兴颂》,可谓一脉相承,自成系列。《大明中兴颂》作于万历三年(1575),作者丁鸿儒时任湖广永州府知府。其序云:“曰若稽古,帝王之兴,皆不繇楚,我世宗肃皇帝,始以兴国。入继大统,盛德大业,超越前代。”又云:“儒不敢妄拟颂磨崖,彼唐宋所称,视此万万不及也。”[2](P152-153)可见《大明中兴颂》的产生,与湘楚文化与永州地缘皆有关系。铭亦是广义的颂的一种,铭体四言,即与颂体相同。元结之铭,专为永州山水而作,奠定了永州摩崖的主题基调。后来者围绕这一主题各有生发,文体不同,题旨多样,但都可以看作元结铭颂的文献衍生。
第二,榜题系列。榜题主要有三种内容:其一是题名,为前人交游和行踪留下印迹,如皇祐六年(1054)柳拱辰、周世南、齐术等人的浯溪题名[2](P92-93);其二是题写景名,如嘉祐五年(1060)张子谅书、卢臧题“朝阳岩”三大字[2](P38-39);其三是以道德箴言为内容的榜书,如明嘉靖二年(1523)黄焯榜书“雩风沂浴”[2](P146-147),又如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王伟士榜书文天祥“忠孝廉节”[2](P290-291)。“雩风沂浴”典出《论语·先进篇》:“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以摩崖石刻的形式,宣扬儒学,树立理学传统,这一传统是由朱熹在福建地区开创的。由于周敦颐是道州(今永州道县)人,这一传统又在明清时代的永州重新出现。
第三,诗文系列。永州摩崖石刻中的诗文作品,历唐宋元明清延及民国,诗体有律有古,有五言有七言,篇幅有长有短。值得注意的是,“湖广湘漓一线,自古为荆楚至岭南的水路通道,加以水石清秀,流寓者多”[2](前言 P1),往来永州的文人墨客大多题咏赋诗,作为自己置身永州摩崖石刻历史现场的见证。后人赋咏,是对前人的凭吊、唱和、印证或者异议。仕宦迁谪之人往返经过楚南之地,先后两次赋诗,既是抚今怀旧,也是与山川之灵的再次对话。越南使臣经过此地,为表示对上国文化的理解与认同,也赋诗言志,使永州摩崖成为中外文学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12](P408-418)[20],并进一步确认了永州所处南北交通与中外交往之交通要道的重要地位。宋代及宋后的摩崖诗文,还可以看出版刻对于石刻的影响。对于他们来说,摩崖只是纸本之外的另一种形式的版面。
日积月累,摩崖题刻越来越多,崖壁上越来越密集,后人题刻有时不免覆盖前人的题刻①清代金石学家瞿中溶在元结《右堂铭》旁边题刻,就不慎刻在前人题字之上。其《古泉山馆金石文编残稿》卷二(《四明丛书》本):“予细审并无文字,乃题名于上,募工刻之。及刻竣,搨视,微见楷书字迹,颇类《右堂铭》,字小不及半,而一字不可辨识为恨,且悔余之题刻卤莽也。”[2](P177)。为了避免地方文献佚失,避免历史记忆被覆盖,有好事者遂起而蒐集,并以纸本的方式保存文献。早在明代嘉靖初年,时任永州知府的福建南平人黄焯就编纂了《朝阳岩集》《澹岩集》[21](P663,1743)[2](P145),这是较早的两种地方石刻文献集。个体的永州石刻早在北宋时代就已进入《集古录》《金石录》等金石著作,而以拓本和纸本方式传播;而整体的永州石刻,至少从嘉靖时代开始,也转换为典籍的形式,成为富有永州特色的文献景观。
建构地方文化景观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地方文献整理,另一方面是地方自然景观命名。永州摩崖石刻本来就是从元结对永州山水的发现与命名开始的,可以说命名是永州摩崖石刻与生俱来的遗传基因。从“浯溪八景”“浯溪十景”“浯溪十二景”发展到“浯溪十六景”,摩崖石刻功不可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号称“摩崖三绝”的《大唐中兴颂》一直是浯溪景观的核心,令人赞叹。
石山保是永州摩崖石刻中特有的现象,集中出现在朝阳岩摩崖石刻中。当地人相信巨石有灵,故生下儿女之后,寄名作巨石之神(通称“石山保”)的子女,以保平安,以求富贵。例如,嘉祐四年(1059)张子谅、陈起、麻延年、魏景、卢臧、夏钧等人题名石壁上,字里行间就有多处刻有“寄名石山保,长命富贵”之类的字样,又如“朝阳岩”榜书石刻旁边,也刻有“寄名石山保,长命富贵易养成”的字样[2](P36,38)。据研究,石山保题刻最早在明末天启三年(1623)已经出现,这是摩崖石刻这种文人文化与永州当地民俗信仰相结合而产生的产物[22][23]。
“永”字之形,实与水相关。《说文解字》十一下:“永,长也,象水巠理之长。《诗》曰:‘江之永矣。’”永州多巨石大崖,刻石其上,希冀垂之永远。“水石文化”确实是永州文化的特质。永州摩崖处于水之滨、石之崖,正是“水石文化”的典型代表。作为中国古代文献十分重要的物质形式,永州摩崖石刻的地方性是十分突出的。中国古代文献的生产与衍生,往往都有其地方性,这种地方性参预构筑其地方文化传统,并且最终成为这种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永州摩崖石刻即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