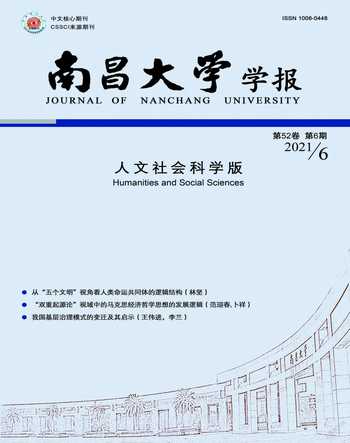“双重起源论”视域中的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发展逻辑
2021-03-05范迎春卜祥记
范迎春 卜祥记
摘 要:依据“双重断裂论”的解释方案,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不仅存在着早后期思想、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之间的断裂,而且“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这一基本概念甚至都是不能成立的,更遑论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发展逻辑”。即使我们依然固执地使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这一概念,那马克思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关联也只能停留于外部反思关系。因而只能在“推广应用与反证说”的传统框架内呈现“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发展逻辑”,并把这一发展逻辑描述为相互外在的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历程。只有立足于“双重起源论”的解释方案,才能彻底打通马克思早后期思想、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断裂,才能真实呈现马克思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体性及其整体性的历史性,也才能据此讨论“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发展逻辑”。
关键词:双重断裂论;双重起源论;经济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
中图分类号:F0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21)06-0025-10
如果把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看作是以共产主义为宗旨的哲学与经济学交叉融合的思想体系,那么对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发展逻辑的思考就不能不本质性地关涉到马克思早期与后期思想、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关系问题。面对国内外久已存在的“双重断裂论”思潮,我们不能不认真思考如下问题:其一,就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早后期关系而言,《资本论》究竟有没有其直接的理论前史。如果它不是马克思的即兴之作,那么这一理论前史可以追溯到何处。如果像阿尔都塞所理解的那样只能把《资本论》的直接理论前史上溯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那么《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何种理论总问题引导着马克思必然走向《资本论》研究。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引导着马克思走向《资本论》研究的总问题,又植根于何处,它难道仅仅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突然显现的,并与作为马克思早期著作之精粹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毫无内在性关联吗?其二,就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而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有没有其直接的理论前史,它与此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有何内在性关联;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的哲学批判与哲学革命,与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是何种关系。如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不是马克思的灵光闪现之作,那么它的思想源泉可以追溯到何处,它又是以何种逻辑必然性引导着马克思走向《德意志意识形态》,草创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并决定性地走向《资本论》研究?把这两个问题综合起来,我们从中看到的就是马克思思想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的理论进程,就是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发展逻辑。因此,对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发展逻辑的反思,就不能不直面“双重断裂论”的诠释方案,并在“双重起源论”的理论视域中重思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发展逻辑。
一、“双重断裂论”与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发展逻辑的断裂
所谓“双重断裂论”,是在反思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把马克思早期与后期思想、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对立起来的诠释方案。就早后期思想的断裂论而言,它主要关涉的是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至《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历程,并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断裂点,制造出《资本论》研究之前的马克思思想发展逻辑的断裂;就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断裂论而言,它主要关涉的是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的哲学批判与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理论关系,并以“推广应用与反证说”的解释方案,制造出自《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研究之间的马克思思想发展逻辑的断裂。
(一)马克思早后期思想的断裂
每当涉及马克思早后期思想的断裂,我们就会想到阿尔都塞。但是,实际上阿尔都塞的“断裂论”发源于亨·德曼。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全文发表的1932年,德曼就已经提出了马克思早期与后期思想的断裂论观点。在同年5-6月发表于社会民主党月刊《斗争》杂志(维也纳)第5-6期的《新发现的马克思》一文中,德曼就以非此即彼的方式尖锐地提出了如下问题:“应当把这个‘人道主义的’阶段看作马克思学说的后来被克服了的预备阶段,还是看作马克思学说的一个固定的组成部分,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本身现在已经不能再回避了。”[1](P348)德曼强调:“现在必须做出决断:要么就是这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属于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必须彻底修正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和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要么就是这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这样就会有一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人们可以用它来反对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1](P348-349)在这里,德曼的提问方式——要么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要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就已经把马克思前后期的思想对立起来了;换言之,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断裂论”就已经呈现出来。基于这种“断裂论”的呈现方式,德曼认为:“决不能把马克思的这部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引者注)只看作是‘不成熟的青年时期的作品’而予以摒弃。不错,马克思当时才26岁;但是,《共产党宣言》只比手稿晚3年,而《共产党宣言》证明,他当时作为思想家和作家却站在他后来再也没有超过的高峰上。”[1](P370)因此,在德曼看来,“这部著作对于正确评价马克思学说的发展过程和思想内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部著作比马克思的其他任何著作都更清楚得多地揭示了隐藏在他的社会主义信念背后,隐藏在他一生的全部科学创作的价值判断背后的伦理的、人道主义的动机”[1](P348)。
作为一名自誉为“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学说的异教徒”[1](P349),德曼的观点一经提出,就遭到了来自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的激烈批评。在所有批评意见中,阿尔都塞的观点是非常有特点的,因为他一方面接受了德曼的提问方式,采纳了德曼的断裂论思路,提出了著名的“断裂论”;另一方面又不同意德曼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高度评价,不同意德曼把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看作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高峰。在阿尔都塞看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确是人道主义性质的作品,但这一作品既不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高峰,也不代表真正的马克思,它是一部“可以比作黎明前黑暗的著作”,同时也“偏偏是离即将升起的太阳最远的著作”[2](P19);只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与费尔巴哈思想的断裂才开始发生。如果说德曼的观点显得过于离经叛道,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中根本无法取得任何可能的理解和同情的话,那么阿尔都塞的观点则深深影响了此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它的影响力是以非常奇怪的方式展现出来的。一方面,正如德曼的断裂论观点并不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接受一样,被阿尔都塞推向极致的“断裂论”当然也不会被接受;另一方面,由于阿尔都塞选取了“断裂期”之后的马克思思想,并把自“断裂期”开始、历经“成长期”并达到“成熟期”的马克思思想看作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解具有更多的相近之处。因此,从总体上看,阿尔都塞的观点为马克思主义阵营的理论家们保留了巨大的批评和修正空间。故而,相较于德曼、阿尔都塞的观点发生了更为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力。
如何既合理肯定“断裂期”之后的马克思思想的正统地位,又避免“断裂论”的突兀逻辑,从而把马克思早后期思想的发展诠释为一个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拉宾提出了一个有代表性的修正方案。在拉宾看来,马克思的早期思想是后期思想的“出发性论点”的阐述,“因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虽然打上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和马克思后来称之为‘对费尔巴哈的迷信’的东西的烙印,虽然有后来被克服了的旧观点的个别因素并且有同新内容不相适应的术语,实质上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以及与科学共产主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出发性论点的阐述。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唯物主义、无神论、对异化和否定的否定的新观点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是对完整的世界观的天才概述和以后的理论研究工作的一个纲领”[1](P56)。
正如德曼、阿尔都塞的观点一样,拉宾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理论性质和思想地位的解释也招致了许多人的批评,似乎他过高地肯定了该手稿的理论意义。但是,纵观国内外理论界的相关解释方案,它们都没有也不可能逃脱德曼、阿尔都塞和拉宾的理论场域,都不过是德曼、阿尔都塞或拉宾理论要素的整合。如果一个人赞同“断裂论”的解释方案,那么在如何看待《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理论性质和思想地位的原则性立场上,他就只能要么选择德曼,要么选择阿尔都塞。至于是否在德曼的解释方案中加入一点阿尔都塞的因素,或者是否在阿尔都塞的解释方案中加入一点德曼的因素,借以缓和“断裂论”的非此即彼性质,那都不过是一些非原则性的或者技术性的考量了;如果一个人不赞同“断裂论”的解释方案,那么他就只能或者选择拉宾的解释方案,或者把德曼和阿尔都塞的因素引入拉宾的解释方案中,借以把马克思前后思想的发展描述为一个非断裂性的历史过程。换言之,在这样的非断裂性的解释方案中,人们可以像拉宾一样赋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更少的费尔巴哈性质,并给予该手稿以高度肯定,也可以引入德曼和阿尔都塞的理论因素,赋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更多的费尔巴哈性质,以降低该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理论地位。
回顾国内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历程,国内的解释方案基本上是在德曼、阿尔都塞和拉宾开启的理论场域中展开的。当这一研究最初以“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迅速发酵时,德曼式的人道主义解释方案一度产生很大影响。但是,这种解释方案很快就被放弃,取而代之的则是阿尔都塞和拉宾方案的综合。作为一种主流性的解释方案,国内学者认为:一方面,马克思早后期思想的发展并不存在真正的断裂,而是一个完整一贯的历史过程,在这里出现的是拉宾解释方案的理论要素,是对断裂论解释方案的原则性否定;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发展历程,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马克思早期思想的理论地位,只有自《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或《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的马克思思想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这里出现的是阿尔都塞解释方案的理论要素。至于应该是阿尔都塞的因素还是拉宾的因素更多一些,这就产生了各有差异的不同解释方案。换言之,如果我们试图呈现国内解释方案的共同点,那么对德曼方案和阿尔都塞方案的批评与舍弃,即对马克思早后期思想发展的历史性和完整性的肯定是国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但是,在这一基本共识之下,究竟如何合乎逻辑地呈现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性和完整性,则存在着理解上的差异。直接地说来,差异主要集中体现在如何看待《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论性质和思想地位,即我们应该像拉宾一样把该手稿看作正在形成中的马克思新世界观的一个纲领性文件,还是在拉宾的解释方案中注入一点儿德曼或阿尔都塞的理论因素,把它主要地看作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立场的作品,但其中也已经蕴含著超越费尔巴哈的理论成分。伴随着思想的推进,马克思思想中的费尔巴哈人道主义逻辑逐渐退隐,而马克思自己的革命人道主义和新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逐渐成长,从而自《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始,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了对费尔巴哈的超越,马克思才成长为真正的马克思。显然,第二种解释方案基本上是拉宾方案和阿尔都塞方案的综合:它从拉宾方案中吸取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性和整体性因素,坚决拒斥德曼和阿尔都塞的断裂论诠释,但又吸取了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断裂期之后思想的高度评价,然而加入了对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之双重逻辑的解释,从而把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描述为一个非断裂性的逻辑演进历程。
由于种种因素的作用,这一解释方案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如果仔细审视这一解释方案,我们就会发现它依然带有“断裂论”的理论色彩,因为在这个解释方案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马克思的本质性立场还是被理解为费尔巴哈的抽象人道主义或人本学唯物主义,而马克思从抽象人道主义向革命人道主义、从人本学唯物主义向新唯物主义的转轨似乎是一个突然发生的思想事件——或者像阿尔都塞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令人“惊叹不已”的思想“闪电”[2](P19)。只要人们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论立场本质性地归于费尔巴哈的抽象人道主义或人本学唯物主义,它就无法彻底摆脱这一解释困境或难题,或者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出现就只能被解释为突然而至的思想闪电;这一点不会因为人们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发现了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的某些微不足道的思想火花而有任何本质性的改观,也不会因为加入《神圣家族》的某些新思想就构建起通向《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思想桥梁——因为在《神圣家族》中,不仅恩格斯依然给予费尔巴哈以极为高度的评价,而且马克思也依然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称为“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3](P327),并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作为霍布斯的“漠视人”的唯物主义的对立面给予高度肯定。
如果要真正破解第二种解释方案面临的困境或难题,就必须与“断裂论”彻底划清界限;而彻底划清界限的出路就在于重新思考并重新界定《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论性质。也就是说,只有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全部思想要素上溯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并把该手稿作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思想源头,作为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理论发源地,才能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间建立起思想的桥梁,才能正确界定《神圣家族》的理论地位,也才能真正呈现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逻辑,把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真正地诠释为一个历史性的过程。
(二)马克思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断裂
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看作《资本论》研究的思想发源地,还隐含着对那种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与经济学批判思想对立起来的解释方案的不满。这种类型的解释方案包括以下两种主要形式。首先,在阿尔都塞那里,它以显性形式而存在。当阿尔都塞不仅把马克思的“青年期”与“断裂期”思想对立起来,而且把“断裂期”甚至包括“成长期”之前的思想与“成熟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对立起来,而“青年期”“断裂期”和“成长期”的思想又主要地被归结为“哲学”
这里所谓的“哲学”,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不是阿尔都塞意义上的“哲学”;阿尔都塞把马克思的“哲学”狭义地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而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作为“历史科学”的“科学”,把马克思青年时期的人本主义哲学理解为“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
——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和作为“历史科学”的“科学”时,阿尔都塞实际上已经把马克思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对立起来了。其次,在国内流行的诠释马克思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关系的“推广应用与反证说”中,它以隐性形式而存在。直接地说来,“推广应用与反证说”是在批判阿尔都塞的“断裂论”观点中形成的,旨在把马克思的哲学批判及其理论成果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统一起来。在这一解释方案中,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以及由此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前提,它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被运用于《资本论》研究,而《资本论》的研究成果则反过来验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而言,这一解释方案好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仔细斟酌就會发现以“推广”为前提的“应用与反证说”实际上还是把马克思的哲学工作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分离开来了,似乎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中存在着两个相互外在的理论中心:一个是哲学批判,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哲学批判中所发生的哲学革命以及由此所规定的马克思哲学的现实性品格,一步步地引导着马克思走向政治经济学研究
这一解释路径与阿尔都塞的如下理解是极为类似的:马克思摆脱了“人本学”逻辑,也拒绝国民经济学把经济现象理解为一个“平面空间”中的线性因果关系;他从实践出发确立了“结构的因果性概念”,从而完成了巨大的理论革命,并导致了“巨大的科学发现:历史理论的发现,政治经济学的发现,《资本论》的发现”。参见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11页、第216页。
,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反过来验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里,哲学批判是“中心”中的“中心”,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使命只是为这一“中心”而服务的“次中心”。但是,问题在于:以《资本论》为主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究竟发端于何处,它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程中处于何种理论地位?如果真实地还原马克思思想的发展逻辑,我们就会看到:实际上,只有政治经济学批判才是贯穿马克思一生思想进展的核心主题,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服务于哲学批判和哲学革命,而是哲学批判和哲学革命服务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同时,如果可以把《资本论》研究课题的最初萌发追溯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该手稿中对国民经济学理论前提的批判又源自《莱茵报》时期对物质利益的困惑,我们就会看到: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逻辑学》和整个旧哲学的批判以及在这一批判工作中所发动的哲学革命,都只是为不同时期的经济学研究和批判工作奠定坚实的哲学基础。因此,并不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立场的哲学批判萌发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批判意识,而是对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批判生成出必须进而批判黑格尔逻辑学的诉求;并不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引导着马克思走向对国民经济学理论前提的批判,而是对国民经济学理论前提的批判引导着马克思走向对黑格尔哲学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并不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推动着马克思走向《资本论》研究,而是《资本论》研究的理论诉求推动着马克思走向《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正是萌发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资本论》研究的理论诉求以及由此而意识到的必须解决的“两个任务”,推动着马克思走向新世界观的伟大创制。因而新世界观的伟大创制只是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走向《资本论》研究的理论环节,是服务于《资本论》研究的理论准备。只有本质性地确立了如此这般的内在关联,我们才能据此谈论马克思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应用与反证”关系,而这种关系当然也就不再是从哲学“推广”到政治经济学批判意义上的“应用与反证”,而是哲学服务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意义上的“应用与反证”;只有在此基础上,“应用与反证”关系才不是“断裂论”式的关系,才能真正内在地把马克思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贯通起来,才能呈现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发展的严整逻辑。
总之,只有本质性地确立起“双重断裂论”的诠释方案,即不仅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理论发源地,而且作为《资本论》研究的理论发源地,才能彻底破除“双重断裂论”的诠释方案,本质性地打通青年马克思与后期马克思、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断裂,才能不仅呈现出马克思思想的经济哲学性质,而且把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发展描述为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历程。
二、马克思哲学新世界的理论发源地与马克思早后期经济哲学思想的内在贯通
作为主要地由“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和“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组成的文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其基本哲学立场上已经内在地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抽象人道主义或人本学唯物主义,已经公开超越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和思辨神学立场,并蕴含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几乎全部理论要素,也初步规制出走向《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取向。
就“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文本精义而言,它内在地包含着对费尔巴哈抽象人道主义逻辑的超越。从思想逻辑看,费尔巴哈是从对人的理想本质的抽象预设出发讨论人的本质的异化。而早在柏林大学就走出康德实然与应然对立逻辑的马克思,则是从与费尔巴哈抽象人道主义逻辑截然不同的科学逻辑出发讨论异化与异化劳动的。这一点集中体现在马克思对“工人”“商品”以及工人创造商品的“工业劳动”的现象学还原中,体现在基于这一还原对“劳动者”创造“劳动产品”的“劳动”本质的科学界定中——“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3](P156-157)也就是说,马克思不是像费尔巴哈一样从应然理想走向对异化现实的指认和批判,不是从劳动应该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出发指证当下劳动是异化劳动,并对异化劳动展开道德批判和理论控诉,而是从对现实个人劳动之作为对象性活动的普遍本质出发,从作为科学事实判断的劳动活动出发,借助国民经济学家私有财产观点,引导出异化劳动,并走向对异化劳动的现实批判。从马克思讨论异化、异化劳动的政治立场看,费尔巴哈是基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立场批判宗教异化,追求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马克思则是立足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立场批判经济异化,追求的是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它同时也是整个人类的解放。因此,尽管大量采用了费尔巴哈的术语,但是马克思使用的“人”“类”“类本质”“自由”等概念,无不都是在有产者与无产者、资本家与工人的阶级对立场域中使用的,因而已经具有了与费尔巴哈完全不同的思想内涵。
就“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的文本精义而言,它同样内在地包含着对费尔巴哈抽象人道主义逻辑的内在超越,同时也包含着对旧的“理论哲学”范式的质疑,并初步拟定了超越“理论哲学”、走向“实践哲学”范式的路向。从对以往“共产主义思潮”的批判和他自己所主张的“共产主义”本质内涵的诠释看,马克思是基于“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文本得出的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根据和原因的基本结论,是围绕如何积极扬弃私有财产的核心议题展开的,这一议题是费尔巴哈完全不关注的。当马克思把共产主义本质性地界定为“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3](P185)时,表面地看来这一表述充斥着费尔巴哈的用词和抽象人道主义色彩,但是实际上马克思这里所采用的“人”“人性”等概念指称的乃是现实的人,是被“资本家”奴役的“工人”。而他所说的“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工人”占有自己的“本质”,即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它现在以异化的私有财产的形式被资本家据为己有了。当马克思进而把共产主义本质性地界定为“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P192)时,表面地看來,“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同样是费尔巴哈式的表述,但是马克思赋予它们的本质性内涵却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就此本质性内涵而言,它显然与费尔巴哈也有本质性差异,因为它指向的不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抽象的爱,而是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场域内的现实矛盾和阶级对抗关系的根本性解决,是无产阶级的解放与自由。就此而言,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学理性分析与论证,已经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3](P502)作好的充分的理论准备。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哲学意蕴的分析看,当由对共产主义思想内涵的分析转而走向对共产主义哲学内涵、哲学基础和哲学高度的分析时,当依据作为“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的共产主义分析转而讨论“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在“共产主义”的“社会状态”中“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时,马克思已经原则性地流露出对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旧哲学的质疑。尤其需要看到的是,当马克思继而指出“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3](P192)时,他已经明确地把以往的旧哲学定性为“理论哲学”,并初步意识到或初步拟定了超越“理论哲学”的路向;这一路向就是“通过实践方式”“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越出“理论哲学”的范式;在这一“实践意识”的引导下,马克思对传统的“创造”概念作了批判性的澄清,把对于理性思维来说能够作为哲学概念使用的“创造”概念改造成“实践”,把“人民意识”赋予“创造”概念的“无中生有”内涵改造为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人类社会——“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3](P196)在这里出现的不仅是马克思走向《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逻辑必然性,而且已经明确提出了作为该提纲理论基石的“实践”概念;同时,对这一概念的进一步论证与展开引导着马克思走向“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就“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文本精义而言,它乃是基于对费尔巴哈“伟大功绩”及其理论局限和对黑格尔哲学理论缺陷及其“伟大之处”的综合性诊断与理论综合,初步创制了作为新哲学范式理论基石的“感性活动”“劳动”或“实践”概念。就其对费尔巴哈的基本评价而言,一方面,马克思虽然高度评价了他的“伟大功绩”,但也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费尔巴哈的理论局限,即他“仅仅”看到黑格尔哲学是哲学与神学的统一,因而只看到黑格尔哲学的“抽象形式”,但没有看到黑格尔哲学所具有的“批判形式” ;只看到黑格尔哲学的思辨哲学和思辨神学性质,但没看到黑格尔以思辨形式把握住了历史的运动,并把“精神劳动”作为历史运动的根据。另一方面,在对费尔巴哈“伟大功绩”的阐释中,马克思实际上也是立足超越费尔巴哈哲学高度的理论立场,即立足孕育中的“实践哲学”范式来具体言说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的。如果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部分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立场的超越还是潜在的,还是需要我们透过直接性表达去仔细分析的,那么在这里马克思则直接表达出了对费尔巴哈哲学的不满,直接指明了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立场的局限性。
马克思的原文是:“由此可见,费尔巴哈把否定的否定仅仅看做哲学同自身的矛盾,看做在否定神学(超验性等等)之后又肯定神学的哲学,即同自身相对立而肯定神学的哲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0页。在这里,“仅仅”两个字是值得仔细玩味的,它显然意味着马克思已经开始明确意识到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局限性。
马克思的原文是:“费尔巴哈还把否定的否定、具体概念看做在思维中超越自身的和作为思维而想直接成为直观、自然界、现实的思维。但是,因为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真正的和唯一的肯定的东西,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他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我们既要说明这一运动在黑格尔那里所采取的抽象形式,也要说明这一运动黑格尔那里同现代的批判即同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所描述的同一过程的区别;或者更正确些说,要说明这一在黑格尔那里还是非批判的运动所具有的批判的形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1页。
同时,对费尔巴哈哲学局限性的分析也引导着马克思走向对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伟大之处”及其局限性的分析。在超出费尔巴哈的维度上,马克思指出:“我们既要说明这一运动在黑格尔那里所采取的抽象形式,也要说明……这一在黑格尔那里还是非批判的运动所具有的批判的形式。”[3](P201)就前者而言,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的运动不过是逻辑思维的生产史,是披着批判外衣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但就后者而言,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在于“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3](P205)。然而,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虽然是劳动辩证法,但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没有看到消极方面;他唯一知道的是“精神劳动”,只是表达了知识论视域中的精神劳动的历史,因而本质上是“理论哲学”。基于从知识论向本体论境域的转换,马克思把精神劳动辩证法翻转为现实个人的劳动辩证法,即作为现实个人对象性活动的劳动辩证法。在这里发生的是马克思对“实践”概念的基本规制,是马克思劳动辩证法的初步创制。它为即将出场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奠定了坚实的“实践”理论基石,并预示着马克思将要越出以费尔巴哈和黑格尔为代表的“理论哲学”范式并决定性走向新哲学世界观伟大创制的理论路向,预示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理论出场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马克思指出:“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定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它所以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9页。
总之,就其基本哲学立场或理论性质而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已经可以被诠释为对费尔巴哈抽象人道主义或人本学唯物主义立场的内在超越——如果充分重视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部分直接表达出来的不满和对费尔巴哈理论局限性的清醒意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超越甚至不再是内在的,而是已经公开的了;同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已经是对黑格尔思辨哲学和思辨神学立场的公开超越。因此,总体性且原则性地看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显然已经制定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基本立场和全部理论要素,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理论发源地。
三、《资本论》研究的理论发源地与马克思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贯通
当我们倾向于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马克思新世界的理论发源地时,我们试图强调的不只是该手稿时期的哲學思想与断裂期、成长期和成熟期的哲学思想之间并不存在阿尔都塞意义上的断裂,还试图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即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至《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马克思思想进展,与此后开展的《资本论》研究之间,也并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思想断裂。只有不仅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哲学思想之间,而且在该手稿与《资本论》研究之间,建立起内在性的思想关联,才能从根本上破除“断裂论”的解释方案。就后者而言,我们认为:从《莱茵报》时期的物质利益困惑到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意识到必须研究国民经济学,从《德法年鉴》时期基于共产主义政治立场对研究国民经济学必要性的再度确认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研究国民经济学,并在对国民经济学理论前提的批判、颠覆和重构中给自己提出了重构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理论课题,这是一个清晰一贯的思想发展历程。当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重构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理论课题时,它实际上已经是马克思对他后来展开的《资本论》研究课题的最初意识和初始表达。换言之,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经给自己提出了《资本论》研究的重大课题[4]。马克思指出:“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重新发现,每一个范畴,例如买卖、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3](P167)当马克思基于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开始阅读研究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论著作时,马克思迅疾发现了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前提不过是无历史性的私有财产,他们无不把私有财产看作当然存在的经济事实并把私有财产看作异化劳动的根源和原因;既然私有财产是一个自有人类以来就已经存在的因而无须追问其历史来历的经济事实,而且正是这一当然合理的私有财产导致了劳动的异化性质,那么异化劳动也就具有当然合理性。因此,全部国民经济学的政治立场就是资产阶级的立场,国民经济学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这是已经完成了政治立场转变并致力于为无产阶级解放提供理论武器的马克思完全无法接受的。因此,马克思很快就结束了文献摘录,并放弃了分栏写作的形式,转而抒发自己的思想,把对国民经济学的研读变成了对国民经济学理论前提和政治立场的批判,从而给我们留下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部分的大段文稿。应当说,这是一个思想逻辑极为清晰的文稿;文稿的核心是对国民经济学理论前提的批判,这一批判是通过对异化劳动四重性的分析展开的,而基于对劳动产品、劳动活动、人的本质和人与人相异化的分析,马克思证伪并颠覆了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我们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诚然,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外化的生命)这一概念。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性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性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3](P166)既然国民经济学的私有财产的理论前提已经被历史性地归之于异化劳动,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异化劳动的结果,因而不再是一个无历史的永恒的经济事实,既然国民经济学赖以建构起全部理论体系的理论前提已经被证伪和颠覆,那么依据新的理论前提,即依据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而且是异化劳动导致私有财产,重构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也就成为一个必要而重大的理论课题。正是依据如此鲜明的思想逻辑,马克思写下了这样一段没有引起应有关注的文字——“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重新发现,每一个范畴,例如买卖、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3](P167)在我们看来,这段文字恰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正是在这段文字中,马克思倾注了后半生全部心血的《资本论》研究课题已经被最初提出来了。《资本论》研究难道不就是依据异化劳动导致私有财产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相互作用的关系”的全新理论前提,对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构吗?当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明确地把《资本论》的研究任务界定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以“揭示现代社会的积极运动规律”[5](P8)时,它难道不既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批判和重构,也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开创性建构吗?据此,我们认为,《资本论》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作为初始表达的依据新的理论前提重构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之理论诉求的全面展开与理论实现。
当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资本论》研究课题还只是依据思想逻辑而刚刚被意识到的理论诉求;但即便如此,马克思也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研究课题的艰巨性,并意識到这一研究课题的展开是需要预先奠定必要理论前提的。马克思把这个理论前提概要性地归结为如下两个任务:“但是,在考察这些范畴的形成以前,我们还打算解决两个任务:(1)从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规定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2)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劳动的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是怎样使自己的劳动外化、异化的?这种异化又是怎样由人的发展的本质引起的?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因为当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总以为是涉及人之外的东西。而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关系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3](167-168)直接地说来,这两个任务是对资本主义前史的追问,它意味着只有搞清楚资本主义的历史来历,才能去研究资本主义;间接地但却实质性地说来,这两个任务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宏大叙事,是对劳动何以成为异化劳动并导致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又历经哪些历史环节才成为当代形式的私有财产即工业资本的。如果把它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在这里出现的不就是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及其内在发展规律的追问吗?因此,正是在这两个马克思认为必须首先解决的任务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的未来思想进展走向《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逻辑必然性,同时也看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草创正就是为了破解《资本论》研究的两个前提性任务并紧密服务于《资本论》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因此,当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借助“自发分工”揭示了劳动之成为异化劳动的根据从而导致私有财产,进而借助“自发分工”的历史演进分析了私有财产历经土地不动产的私有财产、等级资本的私有制、在行会手工业的等级资本之外出现的商业资本的私有制以及由此而推动的由工场手工业的工业资本向资本主义工厂和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工业资本的历史进展,从而本质性地揭示了私有财产的历史、工业资本的生成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来历时,马克思不仅决定性地破解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了“两个任务”,而且草创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体系,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借助《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的必要理论环节,毅然转入漫长而艰苦的《资本论》研究。
如果这样的解释方案是符合马克思思想发展逻辑的,那它就意味着马克思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进展,与此后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并不存在本质性的断裂与突然而至的思想转轨。实际上,《资本论》研究或“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源头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此而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只是马克思“哲学新世界观”的理论发源地,它同时还是《资本论》研究的思想发源地。只有当我们实质性地把《资本论》研究的理论诉求上溯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才能从根本上彻底破除一切形式的“断裂论”理解,从而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与后期思想之间搭建起前后贯通的桥梁,才能从根本上破除阿尔都塞的“断裂论”及其各种理论变形,才能本质性地打通青年马克思与后期马克思、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断裂,也才能完整呈现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和思想逻辑。
我们认为,那种把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与后期思想割裂开来,制造两个马克思的“断裂论”主张,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就《资本论》研究的理论进程而言,它是贯穿马克思早期与后期思想的一根理论红线,因而表现为马克思唯物史观发展完整理论历程中的、一以贯之的理论要素或理论环节。在这个意义上,根本就不存在“青年马克思”与“后期马克思”或“老年马克思”的思想断裂;就唯物史观的理论进程而言,以《资本论》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批判,既根源于并从属于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等文献群为代表的唯物史观建构的早期理论行程,也是这一早期唯物史观理论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形态研究中的应用,并通过这一具体应用一方面推进、发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有力地检验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质,因而同样表现为唯物史观理论行程中的重要理论环节[6](P107-108)。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就是一部浓缩版的唯物史观,因而也不存在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与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的断裂。在这里出现的才是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发展的完成逻辑。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2]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卜祥记.《资本论》的理论空间与哲学性质[J].中国社会科学,2013(10).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陆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唯物史观[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2).
The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s Economic Philoso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ual Origin Theory”
FAN Ying-chun1,BU Xiang-ji2
(1.School of Marxism,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1701,China;
(2.School of Marxism,Institute of Economic Philosophy,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interpretation scheme of “double rupture theory”,there is not only a fracture between early and late thought,philosophical criticism and political economy criticism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rx’s thought,but also the basic concept of “Marx’s economic philosophy” can not even be established,let alone the “development logic” of Marx’s economic philosophy.Even if we still stubbornly use the concept of “Marx’s economic philosoph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s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economy can only stay in the external reflection relationship.Therefore,the “development logic” of “Marx’s economic philosophy” can only be presented within the traditional framework of “popularization,application and counter evidence”,and this development logic can be described as the relationship process of mutual external philosophical criticism an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riticism.Only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scheme of “dual origin theory”,can we completely break through the fracture between Marx’s early and late thought,philosophical criticism and political economy criticism,truly present the integrity and historicity of Marx’s philosophy,political economy and scientific socialism,and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logic of Marx’s economic philosophy”.
Key words:
double rupture theory;dual origin theory;economic philosophy;criticism of political economy
(責任编辑
徐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