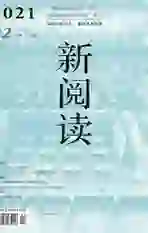阅读让博物馆教育更出彩
2021-03-02张鹏
张鹏

截至2019年底,中国共有在册博物馆5535家,年参观人次12.28亿,未成年人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不论是国务院《博物馆条例》中把博物馆教育的职能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还是近期教育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出台的相关文件中,都提出了利用好博物馆教育资源的新要求,使博物馆融入教育教学中来,更值得关注的是,社会公众也给予了博物馆教育更大的参与和学习热情。在上述背景推动下,博物馆教育也越来越多的跨界融合,面向少年儿童群体的童书出版和阅读推广也成为重要的载体,极大地拓展了博物馆教育的呈现方式,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童书出版的专业内容。
博物馆教育的特点
教育是博物馆的重要职能之一,在人的终身学习过程中,既有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塑造,同时更有公共教育的部分。
博物馆教育有着自身的独特性:一是终身性,服务的社会公众既有学龄前的儿童,也有退休的老人,涵盖了几乎全部的人生階段,为每个观众在不同的时期带来具有一定针对性的公共教育内容;二是开放性,即使是同一文物,也能够连接不同的专业,不同的观念,不同的时空,拥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和外延;三是拓展性,博物馆教育的最终方向,是可以服务于当下和未来,呈现在不同的应用场景当中,为社会发展注入力量。这些独特性既是博物馆教育的魅力,同时也是博物馆教育的难点。
当然,也为博物馆主题图书的出版以及阅读推广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让文物和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通过更加丰富的形式,与读者对话。
阅读是博物馆教育的重要形式
原有博物馆教育的呈现方式是比较传统和单一的,比如定时讲解、公益讲座、专题活动等形式,但随着博物馆教育和不同专业领域的深入融合,更多具有创新意识的博物馆教育形式开始多元化呈现出来。尤其是面对未成年人群体,随着一系列馆校结合政策文件的出台,让博物馆教育在实现课程化的方面有了更多的探索和实践。
这其中,童书出版以及阅读推广和博物馆教育的融合是非常值得博物馆关注的,是开展博物馆教育的重要形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博物馆开展现场实践的参观学习之前,阅读是非常好的铺垫,会很大程度提高公众在博物馆学习的获得感,也会让博物馆学习变得更加有效,不少游学机构和研学机构在组织相应的产品时,把图书阅读放在了行前学习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是在博物馆现场学习之后,阅读是非常好的延伸,能够让博物馆的教育内容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拓展到后续的个人学习和成长中来,很多博物馆主题的童书也都进入了中小学校在寒暑假的推荐阅读书目当中,不论是学校老师,还是博物馆教育从业者,也越来越多地使用到博物馆主题童书,作为教育活动及课程开展中的重要手段。另外,更多的父母也逐渐意识到了上面两个方面的情况。
现阶段,阅读与博物馆教育的融合更加深入
童书出版及阅读推广与博物馆教育的融合值得关注,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以博物馆为主题的童书日益丰富。既有出版机构着力打造的作品,如天津新蕾出版社推出的《博物馆里的中国》系列丛书等,也有博物馆社会教育部门联合出版机构推出的作品,如童趣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儿童历史百科绘本》。不少出版社把与博物馆的合作作为了重点项目,充分挖掘本地历史文化内涵,在青少年群体中进行深入推广,如浙江大学出版社联合杭州博物馆推出的《寻找回家的路》、联合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中国刀剪剑博物馆、中国扇博物馆和中国伞博物馆共同推出的《我的木偶师朋友》等。
背后的原因主要来自三方面助力,一是童书出版水平,尤其是原创水平的提升,让出版社有能力去触碰到历史、文化、艺术等类别的博物馆童书,二是博物馆社会教育水平的提升,更多优秀的博物馆教育课程涌现了出来,也带动了一批优秀的作者,三是社会公众的需求,伴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中,开始关注围绕着博物馆来培养未成年人的终身学习能力。
第二,博物馆童书的阅读推广也日益丰富。近年来,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深入推动,研学旅行市场的不断发展,以及素质教育领域的持续兴起,都让博物馆童书有了更多被使用的场景。一方面是不少学校和博物馆,都将阅读与博物馆课程进行了深度的结合,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联合嘉定区教育局共同推出的《博物学记》,就配合着多条研学的线路,值得关注的是,很多教学水平突出的学校也逐步将博物馆校本课程成果化,推出了更加聚焦的出版物。另一方面,博物馆童书阅读助力博物馆教育的效应更加明显,伴随着博物馆的热度,也出现了很多受家长孩子认可的精品,如步印童书馆的《中国历史长卷》,电子工业出版社的《打开故宫》,米莱童书创作的《穿越时空看文明——全景手绘中国史》等,在家长和孩子当中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首都博物馆联合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共同推出了首届博物馆童书阅读推广系列活动,组织了2019年度博物馆主题优选童书的评审和推荐,形成了30本博物馆主题优选童书的推荐书单,该项活动还将继续深化。
需要继续努力的方面
博物馆主题的童书有着较高的水准,一方面体现在童书的内容,涉及范围基本涵盖了博物馆的领域,同时在选题方面也更加精准,贴近孩子的视角;另一方面体现在童书的形式更加灵活,有的融入了新的技术,有的配合着孩子的互动和体验。但我们也发现,还有着可以继续提升发展的巨大空间,既表现在创作的空间方面,也体现在市场的空间方面。
一是博物馆的教育资源挖掘不够,与博物馆的结合度还可以继续深化。中国有1.08亿可移动文物,每年举办2.6万个展览,中国有5000多家博物馆,很多值得去用童书的方式呈现给孩子的博物馆教育资源还没有进入出版工作者的视野,如位于浙江的湖州博物馆,是丝绸、茶叶、瓷器、毛笔的重要故乡,馆藏文物非常精彩,但还没有能给到孩子们去阅读的博物馆童书。
二是博物馆童书的原创水平还不够,与博物馆的专业要求还有部分差距。博物馆所涵盖的范围是很广的,不仅包括了我们传统认识的历史类的场馆,也包括了美术馆、自然馆、科技馆等众多公共教育空间。相比之下,历史人文类的选题内容有着更高的专业要求,这对作者、绘者、编辑来说都是困难。比如有书中给孩子们讲到秦汉时代修筑长城的部分,描绘出来的场景是用青砖垒砌,而实际那时的长城多应是夯土筑就的。
三是博物馆童书的利用空间还不够,与博物馆教育的结合还有差距。博物馆的教育是实践性的,打开孩子们的感官和思考去带入的,与阅读的配合是有益处的,更是有必要的。没有走进博物馆前,阅读会帮助孩子们建立场馆学习的基础,而走出博物馆后,阅读会帮助孩子们把博物馆的学习向外扩展,在不同的领域、时空和观念中延伸。
从事青少年博物馆教育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探索着博物馆教育的创新形式,自2014年注意到博物馆教育与童书出版和阅读推广领域的融合依赖,也做了诸多的实践工作。先后完成《宫城:写给孩子们的紫禁城》《朋朋哥哥讲故宫》《博物馆里的中国:绝妙器皿》《倾听博物馆:朋朋的时光笔记》《和朋朋哥哥一起逛北京》等图书五部,同时还主编了面向少儿群体的系列丛书《奇趣博物馆》,两年多时间里已完成三十余本,另外还翻译了博物馆主题童书三部。希望能从自身做起,用阅读的方式助力博物馆教育行业的发展。
相信未来,博物馆教育和图书出版及阅读推广的结合会更加深入,博物馆教育资源会被更加充分地挖掘出来,博物馆教育的形式也会被更加立体地呈现出来。这些,都值得我们共同继续去努力。
作者系2015年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耳朵里的博物馆创始人、北京郭守敬纪念馆执行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