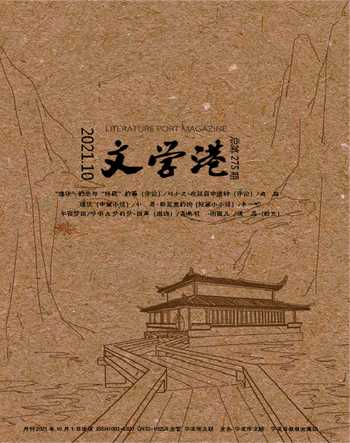卧室里的狗
2021-02-28丰一畛
丰一畛

小孙子跟着她一起睡在女儿的房间。从医院回来有一阵儿了,他一直处在半睡半醒的状态。出租车里,快到家时,他睁开眼,愣着神,有气无力地喊了声奶奶。那会儿抱着他的是儿媳。怕他哭闹,她犹豫着要不要换把手。像是觉察到了她的为难,他咕哝了句什么,闭上眼,没再说话了。这会儿,他的呼吸还有些浊重,她凑上去摸摸他的头,烧总算退了。小孩子生病不稀奇,不太清楚怎么得的病也不稀奇,但生病总归不是好事。孙子主要她在带,狗也是她在伺弄,那种无端的不适感觉倏忽而来,紧一下慢一下,顶得她喉咙里直泛酸水,好像做錯了什么,好像责任都是她的,真奇怪。
出了门,她朝卫生间走。晚饭还没着落。客厅里,儿子侧躺着,儿媳坐着,都在看手机。卫生间的门正对着小卧室的门。她驻足,手握住把手了,又收回来。里面一片阒寂。坐便器上有几滴可疑的尿渍,她攒攒力气,清理了。儿子叫了三份外卖,她已去厨房拾掇了一会儿他才踱近了说的。不用做饭了,突然不知道该干点什么,这时反而意识到了累。累这种东西就怕意识到。吃饭时,没人说话。累的意识也是传染的。小孩子生病,不是大人的原因,但谁还能高兴得起来?谁还有说话的兴致?那就让无关的人发出声音。儿子打开电视,随便停在一个播着电视剧的卫视上。有了声音的衬托,沉默更明显。她进了女儿的房间,查看小孙子的状况。儿子儿媳看了很长时间的电视,仿佛某种蓄谋的对峙。她按捺着冲动,心平气和地等着。小孙子醒了,她想喂他点吃的,他不乐意,纠缠了会,喝了几口牛奶,又昏沉沉睡去。等客厅没了动静,儿子儿媳回了他们的房间,她才出来。
小卧室的门反锁了。她拧了多次,打不开。这有点匪夷所思。出门时慌张,她是不放心稀饭,但没锁这个门的习惯。还好,电视柜下面的抽屉里有钥匙。她开了门,揿亮灯。稀饭趴在床和衣柜间狭窄的过道里,咬着磨牙棒,若有所思。她进来了,它扭扭头,没有表现出任何亲昵。她轰它,它站起来,跳上了床。狗窝垫子什么时候被叼到了床上。她扫视了一圈,没发现它的排泄物,揪揪它的耳朵,套上狗绳,感激似地对着它的黑眼球使劲瞅。养狗这一点麻烦,要遛。往常都是她带着稀饭出去,每天两次,主要为了解决稀饭的大小便问题。这次小孙子生病,她陪着在医院住了一夜,稀饭该憋久了。但她还是等到儿子儿媳回了房间才过来。她拉着稀饭往外走,出乎意料,稀饭一点也不情愿。难道是乱了规律没反应过来?她继续拉它,看见穿衣镜里稀饭往后扽着绳子。她把它拽出来,到了小卧室门口,稀饭干脆趴下了。她蹲下,摸它的脑袋、脊背和尾脊骨,一遍又一遍里,她的情绪有了沉陷,不知道是委屈还是生气。不能这样。她告诫自己,决绝地抱起稀饭,起身,抱到客厅门口,腾出一只手开门,再轻轻关上。
小卧室其实是她的房间。当时三个人的钱加一块也勉勉强强只够一个小户型的首付。他们权衡良久,还是决定借一些买个三室的。多少年了,为了谋生,她和儿子女儿天各一方。老家的房塌了,婆家没人娘家的关系也淡了,他们只能在城里挣个落脚之地。女儿长大,肯定不愿意再跟她一张床上睡。这个落脚之地,最好有三个卧室,小点没关系,三个卧室才能保证久不住一起的三人之间亲近又不至过于亲近。
夜色冥蒙,小区里的灯光饱含缠绵与秘密。几棵移植过来被支架固定的树,身影孤绝。感觉不到风,风只在斑驳的树影中穿梭。稀饭走得慢,有条后腿蹩拉着,这里闻闻,那里嗅嗅。她没带手电筒,借着路灯光查看,应该没什么大碍,估计是运动太少的缘故。顺着小区的绿化带走了半圈,稀饭去了一棵树下,左右逡巡。她站在草坪边缘,背对着。她家住在左前方那栋的18层。或许是眼花了,她从下往上数,还没到10层,指代与被指代的关系就开始凌乱。那些光是悬浮的、晃动的、支离破碎的。那些黑暗同样在游弋、流淌。她不死心,又从上往下数,这次光昏暗得更厉害。关键的是,她不记得整幢楼拢共有多少层了。稀饭突兀地叫了一声。叫声让她想起,它好像很久没叫了。她转过身去,稀饭回来了,站在她右后方,昂起头,仿佛学着她的样子,也在眺望着高大建筑物里吐纳出的沉默的光和黑暗。她俯身,挪步,寻找着它的排泄物。快到树底下时,一句“干吗呢”的问话吓了她一激灵。赶紧站起来。这个时候遛狗呀。是刘姐。她走到路边,屏了下心气才说,这个时候跑步呀。正想和你说说话。刘姐说。小区的儿童设施那儿有张休息长椅,她牵上稀饭,她们坐过去。
刘姐住20栋。是这个偌大的小区里为数不多、见了面会打声招呼或寒暄几句的人。印象里,也是在健身器材这儿,闲聊时,她们发现了个巧合。虽然刘姐看起来比她年轻很多,但她们同一天生日。陌生人,同一天生日,又日渐熟络,反而不知道怎么称呼好了,也不能总用“哎”代替。刘姐提议,彼此喊对方姐,谁也别占谁的便宜。她喊了声王姐,她回敬了声刘姐。刘姐开玩笑说,总感觉还是吃亏了。要不再往细了比比,你啥时辰生的?算了吧,刘姐。她记得她一笑,背上的小孙子哭起来。
她们说话的时候,稀饭钻进了滑梯与撑杆之间的缝隙。刘姐像是忽然想起来似地问她,稀饭是公的还是母的、有没有做绝育手术。她一一回答。刘姐说,怪不得。她之前养过狗,做了绝育后性情大变,跟稀饭相反,变得更暴躁。刘姐说她现在改养猫了。她其实知道。刘姐之前说过,知道她家的狗叫稀饭后,还说要把猫的名字改成咸菜。当然没改。那次一块去公园,刘姐抱着那只通体雪白的猫去的。她叫它小东西。
怎么这个时候遛狗?刘姐说,他们下班晚了?是啊,她说,你呢,怎么这个时候跑步,不应该呀。可别提了,刘姐说,那次咱们一块出门,惹下事了。有个男的,败顶,个挺高,穿身运动装,过来和我们搭讪,还有印象不?她脑子一片空白,完全想不起来了。只隐约记得,那天小孙子很调皮,非要一页一页撕扯她带去记录信息的一个小本子。她们是去相亲的。给女儿相亲。同一天生日是挺巧,她和刘姐各自有个女儿,这不能算多巧,但她们的女儿都不是省油的灯儿,三十多了不结婚,她们忧心。她们忧同样的心,这就挺巧。看来巧合的事不止一桩。那个有相亲角的公园离小区较远,她去过,但次数有限。她们约了几次才成行的。即使不被撕,那个小本子也几乎派不上用场。电视上放的在公园相亲的,定格的都是看“简历牌”的画面。树与树之间拴上绳子,把载有子女年龄、身高、工作单位、兴趣爱好等基本信息的文档打印出来,夹在绳子上供人观摩。现实情况完全不同,没人愿意将子女的信息直接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家都是面对面试探。更像电视剧中神神秘秘的接头。刘姐说的那个男人,应该就是主动过来接头的。但她确实想不起来了。
说喜欢小东西、说小东西像哲学家的那个?儿子清华毕业的那个?看她还是木木地没响应,刘姐语气里的光亮拱出了股烟尘般暗了片刻。算了算了,就是一个老男人,你见过的,我们去给女儿相亲碰上的,他要找我当老伴儿。你说这算啥呀。烟尘消失了,刘姐的语气里跳出新的光亮。不知道这算啥,算个西洋景儿吧,她心里这样想,嘴上肯定不能这么说。他没骚扰你吧,不行就报警。没有。刘姐说。现在骗子无孔不入,你可要小心。是啊。刘姐说。她不知再怎么安慰了,便岔开话头,问她为何离异。她说这说起来话就长了,她以为她要说下去,讲一个长长的故事,但她沒有。当她意识到刘姐不是在酝酿情绪,只是沉默不言,又问啥时候离的、后来又找没。刘姐说找了。这次换她沉默不语了。她不说话,也许刘姐就会酝酿情绪,讲讲她后来怎么找的,那将是另一个长长的故事。时间有了足够的间歇。刘姐也应该意识到了她是在等她说话。你从来没想过找老伴儿?刘姐说了,但她也岔了话头。一个小孩子一条狗就够我忙的了……她仓促回应的时候脑海里挤出了某种模糊的顿悟,一丝颓唐随之而来,刘姐似乎并不需要她的安慰。或者,她需要的不是安慰。她拍了拍手,说想起来了,那个老男人看上去知书达理,像个退休教师。是吗?刘姐说。败顶,个挺高,穿身运动装,是那个吧?是的。刘姐像是相信她真记起来了。
聊天的某个间隙,她提醒自己有件事没做。跟刘姐分别时这个提醒还是有轮廓的。她的意识停驻在上面,若有所动,只是若有所动。等回了家,轮廓里的内容才终于姗姗来迟般冒出来。光顾着说话,她忘了回去捡稀饭的排泄物了。也怪稀饭。它太唯命是从,没给她任何提示和指引,甚至都没叫一声。它的安静让她怀疑,它之前突兀地叫过的那一声是不是只是她的幻听。
开了门,摘了牵引绳,稀饭没先走,等她换了鞋,前头迈开步,它还没走。她抱起它,穿过客厅,开了小卧室的门,稀饭欻地从她怀里蹿出来。关门只不过一个回身而已,再转身,刚刚因为措手不及而加速的心跳还没来得及恢复平稳,稀饭不见了。她环顾整个卧室,揿灭灯,再揿亮,一股强烈的恍惚感袭来。有一段时间,稀饭喜欢后腿撑着床沿前腿扒着窗边往对面的窗看。那家也养了条狗。窗帘是拉着的,她过去掀掀,飘窗上空无一物。或许那段时间对面窗里的狗正在发情。它想看看。
她退到衣柜这一侧。穿衣镜里的自己很陌生。她看着镜子。镜子里的她看着她。她无法描述自己的容貌和穿着,也没想着描述。穿衣镜其实就是衣柜的一扇推拉门。卧室太小,衣柜门上镶镜子,节省空间,还能带来开阔感。坏处是,拉到左边,镜子对着床尾,拉到右边,镜子对着床头。有的人忌讳这个,说是不吉利。当然只是种说法。就像住18层如置身地狱一样,都只是种说法。人总是生活在将就里,尤其像她这样出身的。她猜到了,稀饭在镜子后头。衣柜左下角是块弹性空间,她推动镜子,稀饭正屁股蹭地缩在里面,耳朵耷拉着,眼皮也耷拉着。不像在跟她玩游戏。会不会是什么暗示,她脑子里掠过一丝警醒,把稀饭拖出,仔细检查衣柜的角落。她误会它了。稀饭不会把屎拉在卧室里,更不会拉在衣柜里的。那她要回去捡它的粪便吗?
抽水马桶轰隆了一阵。声音慢慢遁去,末梢处,新的声音传来。妈。儿子站在小卧室门外轻轻喊了声。她没应。敲门声响了。在的。她说。敲门声又响了两下。她知道儿子是想让她出去。她知道儿子不想进来。有事吗?她问。停了一会儿,他说,是的。他知道她问有事吗是在告诉他不想出去。她知道他隔了会儿回答是的还是想让她出去。可她不想出去。啥事?她说。他没应,隔了更久一会儿,还是没应。她看看稀饭,按捺住走出去的冲动,时间悠远而漫长,门吱扭一下,儿子进来了。儿子像另一个稀饭,不看她,也不乱瞟,断断续续又轻描淡写地说完了两件事。他说,您不是一直都说,一儿一女凑个“好”,儿女双全有福气吗?他语气有点轻巧,好像没经过深思熟虑,好像置身事外,只是个传话的。是她说的。她还说过,带一个是带,带两个也是带。她无可辩驳。希望的事要发生了,为什么要辩驳?可不知怎么,她感觉更不高兴了,负气般在心里嘀咕,盼女孩就会是女孩吗?
他说,要不,要不还是把稀饭送走吧。她没抬头观察他说这话时的表情。或许,他不会呈现什么表情。她说好的,说得很快,公事公办的样子。他说他要回去睡觉了,说着退出小卧室,轻轻带上了门。脚步利落。动作敏捷。她知道,他也知道,延长这时候的尴尬是危险的,也是会让人无所适从的。所以他们配合默契,别过脸去,给尴尬包裹上糖衣,迅速地吞咽下去。稀饭又藏进了衣柜,她拉动穿衣镜,看见了自己。
稀饭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起先,它哪里都可以去。这里也是它的家。后来,它不能去儿子儿媳的房间了,不能在客厅、厨房流窜了。它被关进女儿的房间。再后来,小孙子要跟她睡,她搬进女儿房间,那里大点,稀饭则被转移,关进小卧室了。起先,稀饭是儿子带到这个家的。那时候,他刚跟那个瘦瘦的手背上长了颗痣的女孩分手。稀饭不过是条流浪狗。他的同事捡的,送给他了。他跟稀饭很是亲昵过一段时间吧?后来,儿子又恋爱了。女儿换了工作,去了家日资企业,把同事介绍给了郁郁寡欢的弟弟。儿子有了新女朋友,女儿只好担负起照顾稀饭的重任。这些是女儿告诉她的。小孙子出生的前几天,她才辞职,第一次踏进这个建筑面积90多平方米的家。
女儿的前同事、儿子的新女朋友、现在她的儿媳,不喜欢稀饭。她不喜欢稀饭,但她没告诉女儿也没告诉后来的她。女儿是慢慢察觉的,察觉到了弟弟的变化,并把这些察觉交待给了她。她第一次来到这个家时,稀饭就只能在女儿的房间活动了。她们达成了某种默契,女儿儿子儿媳之间。儿媳刚怀孕时,儿子跟女儿提过送走稀饭的事。家里有孕妇还养狗,感染了弓形体病确实很麻烦。也许儿媳不是不喜欢狗,是不喜欢她怀孕了还养狗,不喜欢她怀孕了家里假装没看见一样继续养狗。但她们达成了某种默契,主要是女儿和儿媳之间。
儿子以前不是这样的。狗是他带进这个家的,可他悄悄溜了,消失了。这是他们的新家。儿子女儿连同她共同攒下的。可她也发现,新家的确是新的,新家里的每个人也都是新的。女儿跟她抱怨过,之前她和弟弟在客厅说话,时间长了些,笑声大了些,儿媳的房间里稍微有点响动,弟弟便很快结束了聊天。她一天到晚神经兮兮的,弄得弟弟跟着神经兮兮的。女儿说,她们只共事了几个月,谁会晓得是这样的。有时候她觉得女儿太敏感,说的话偏颇了。有时候她又觉得女儿的话并非空穴来风、耸人听闻。有一次,她临时出门去下面的小超市买佐料,回来正要开门,听见小孙子哇哇哭,儿媳不哄,反而幸灾乐祸地说,你奶奶不要你了,哈哈。她以为她不过开句玩笑,没想到,小孙子越哭她越是这么一次次重复,你奶奶不要你了。小孙子都岔气了,她还要这么说。
女儿去读研了。这是要趁着女儿不在把她们曾经的默契和平衡打破吗?儿子儿媳的借口是充分的。这不又怀孕了吗?儿媳从来没有撒泼打诨,胡搅蛮缠,她一开始也没那么强势,没那么理直气壮。她要循序渐进、步步为营地宣示她的主权。想到儿媳的这份长久的小心翼翼,她坐立不安起来。儿子至少有一两年没进小卧室了吧?他告诉她媳妇怀孕、送走稀饭的时机也是恰到好处的。她在带的小孙子生了病。她不该内疚吗?狗也是她在伺弄。她不该顺理成章地联想点什么吗?
女儿也是,师范毕业时,怎么劝也不读研不教书。兜兜转转,三十岁了,又要去读研又想教书了。她呼叫了女儿。接通视频后,家常没聊几句,女儿便嚷嚷着让稀饭出镜。她把狗垫挪到地板上,唤过稀饭,调转摄像头,对准了它。稀饭叼起磨牙棒原地转圈圈,间或张望着屏幕。女儿说,寒假回来找工作,定了地点会在附近租房,到时就把稀饭带走。女儿像是预料到了什么,她差点和盘托出,稀饭等不了那么久了。她忍住,只说了儿媳怀孕的事。女儿显得有些义愤填膺,她弟弟跟她提过要二胎,她建议缓缓,经济条件不允许,再说,当妈的太累了。儿子的意思是,到时候再说,实在不行就让儿媳辞职。女儿复述了她和弟弟的对话,说,妈,你说这叫什么话,啥叫实在不行,他俩想把你累死吗?不至于的,她说,你看你老是危言耸听。好吧,是我不对,女儿说,反正累的也不是我,懒得管闲事。每次视频,女儿说那个说这个,但从不说自己。她也不好意思直接问。母女俩好像只有这么一种谈话模式。这次她想突破一下,问问女儿寒假回来能不能去相相亲,她已做了准备。话到嘴边,正在最后斟酌,她听见了小孙子嘤嘤地哭泣。不说了,她说。她挂掉视频,跑出去。
她给小孙子换尿不湿,陪着他玩了会儿玩具。他好像饿了。她去厨房蒸了个鸡蛋,端进来,一勺一勺喂他。小孙子冷不丁咳嗽两声,她赶忙拿来水瓶,水是兑过的,不烫不冷,他吸了一气儿,忽然停下来笑眯眯地说,狗狗,狗狗。她一错愕,才听明白,小孙子在叫稀饭。每天上午那次遛狗,她总是背着他出去。他对它充满好奇。那种好奇仿佛与生俱来。但他们不能接触。在家里,更不可能。客厅里安装了监控。儿子能看到。儿媳也能看到。那种倏忽而来的不适的感觉也许并非毫无缘由。小孙子生病的前一天,他吃着颗棒棒糖走向小卧室,她没注意,估计是听到了响动,他砸了两下门。她把他抱走,棒棒糖掉在地上。她觉得可惜了,开条门缝扔给了稀饭。小孙子生病的那天,趁他洗完澡午睡时,她也给稀饭洗了澡。可这又能算什么缘由?稀饭不是脏东西,不是污染源,因为跟稀饭共吃过一块糖、在同一个地方洗过澡,小孙子便生病了?这又不是聊斋故事。
没必要这样的。想这些没用。她没做错什么。她挥舞一辆塑料坦克车,转移了小孙子的注意力。一瞬间,做了个决定。小孙子睡着了,她要出去打个电话。等了半晌,没发现他要睡觉的迹象,她的决定又开始动摇。她换了思路,想着要不要背着小孙子出去打个电话。可她做不了这个决定。他刚从医院回来,别再着了凉。迟疑像口井,她盯着井口层层叠叠千篇一律的天,蓦然惊觉,小孙子睡着了。
出了楼门,凉意灌入怀中。风似乎从婆娑的树影中掉落下来,一片片,一坨坨。是有些晚了。20栋只剩了3户人家还亮着灯。犹豫是深的、粘滞的。不一定非要这个时候打电话。但她已经下来了。决绝也是深的、粘滞的。她拨了刘姐的号。她要把稀饭寄养在她那里。每天还是她来遛,直到女儿回来,直到它被女儿带走。电话无人接听。的确有些晚了,还显得唐突。刘姐不过是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因为一些巧合,有了点交集而已。她没直接上楼,绕着小区毫无目的地走着,又像等待着冥冥中的神启。一股淡淡的尿骚味在风里游荡。她闻到了。仅仅是闻到了。仿佛丧失了知觉的那种沉浸。那个念头随后产生了。不知道跟尿骚味的刺激有无关系。她打开手机手电筒,去到印象里稀饭经常逗留的那几棵树下。她找到了动物的排泄物。不止一处。有的已经干了。她果断地放弃了清理这些粪便的想法。
手机这时叮了下,进来个短信。是刘姐。年轻时都没这么放纵过,我哭了,热泪盈眶。刘姐说。她不知怎么回,要不要说自己的事。她还是说了。发送的时候,异常沮丧。刘姐没回。她更沮丧了,努力回想着公园里那个过来搭讪的老男人的模样。她想不起来。她的世界被什么困住了。她从来没往另外的方向想过。她没法想起来。
回到家,她不自觉地进了小卧室,墙脚处的自助喂食器里,狗粮还是满的。稀饭这两天应该吃得很少。它又躲进穿衣镜后头了。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发愣。镜子忽然动了。稀饭走出来,绕过她,旁若无人地走到卧室门前。它后腿一蹬,跳起来,前腿一伸,搭住了门把手。吱嘎一声,门开了。它大摇大摆走出去。她目瞪口呆,跟着它走。它重复刚才的动作,卫生间的门开了。它进去,四条腿踩著坐便器,弓起身,屁股下蜷。它在像人一样上厕所。她鬼使神差般掏出手机,拍了张照。它轻轻上下颠动屁股,头抖擞两下,跳开,一跃而起,蹦上洗漱台,又一跃而起,蹦上抽水马桶。它用前爪按了按开关,水哗啦哗啦冲走了它的排泄物。它跳下来,大摇大摆走出卫生间,走进了小卧室。她亦步亦趋跟着。它后腿一蹬,跳起来,前腿一伸,搭住了门把手。吱嘎一声,门关了。它转过身,走进衣柜,又转身,拉动了穿衣镜。现在,镜子里的人正看着她发愣。
她彻底被惊着了。女儿之前教过稀饭一些简单的口令。但这么复杂的一连串的行为,没人能教会它。它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它主动让自己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它委曲求全、无师自通地掌握了新的技能,人的技能。它被逼成了一个人。一条狗被逼成了一个人。
她要告诉女儿吗?她要告诉儿子儿媳吗?她恨稀饭,无端地恨之入骨。就像恨自己。聊斋故事是真的。她感觉她是另一个稀饭,稀饭是另一个她。稀饭的技能吓到了她。她走出小卧室,走到客厅。她感觉到了恐怖,小卧室的恐怖,家的恐怖。
她推开家门,走出去。出小区,走到大马路上。她被稀饭弄哭了。被它的突变弄哭了。她这是要去哪里。离家出走吗?夜色苍茫,她在往前走,可她无路可去。儿媳又怀孕了。这是她期待的生活。她在她期待的生活里。她这样跟自己说。她给刘姐发了条短信。她说她也哭了。她说,祝福,也恭喜。
她的泪被风吹走了。她不知道要去哪里。她走了很久,天好像被走亮了,心好像被走空了。她想念起稀饭来。想念如决堤之水,汹涌而至。她往回走,走得飞快。她想见见稀饭。迫不及待。刻不容缓。她需要它。她强烈地意识到,起码在人生的这一时这一刻,她比任何人都更需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