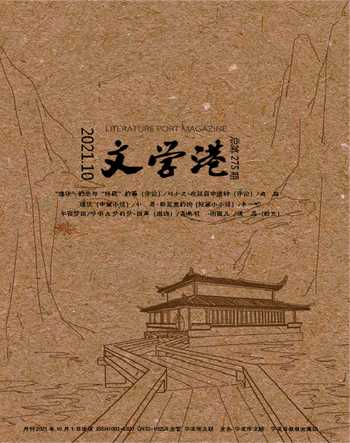谈喝酒(外一题)
2021-02-28曹永
曹永
包倬兄:
近日看到网店售卖一个酒瓶,造型稀奇,竟是鲁迅先生怀抱双臂,倚靠着一块石头。瓶嘴就在石头上,没有盖子。早想搜寻几尊自己喜欢的作家塑像,奈何所见极少。鲁迅先生雕像,好歹还有两尊。其中一尊是瓷的,当年在北京潘家园购得。后来晓得一个朋友非常喜欢鲁迅先生,便把那尊瓷像赠给他了。另一尊是铜的,得来很不便宜。那雕像虽无编号,但轮廓分明,尽显鲁迅神韵,估计是某位雕塑家的手笔。这尊雕像就摆在我的书桌上面,兄前次过来,还见过。我试图寻找沈从文先生像,竟然多年未能如愿。倒是有一次,见到有店家出售赵树理和丁玲雕像。店主显然不知底细,没有认出是谁的雕像,我却晓得那是雕塑家的作品小样。那两尊铜像,毕竟摆在现当代文学馆和鲁迅文学院共用的院落里。
贵州是出名酒的地方,我却从不沾酒,大家都觉得这是身体上的问题,其实尚不至于。少年时代,我在姑妈家寄读。有一天放学回来,连灌两碗苞谷甜酒,然后撵着猪到山上去放。没想到,竟醉倒在坡上。几头猪失去监管,全都跑到地里,拱坏十几棵白菜。自那件事后,凡是含酒精的东西,我一概不沾。虽然不喝酒,我却几番想买那个鲁迅先生的纪念酒瓶,想着装点好酒,文友来访的时候,拎出来喝也有意思。只是店家咬定,非要五百块钱。这个价格并不算高,但我终究没有舍得。兄知道我的喜好,这个钱我宁愿用来收藏陶俑。这几天逛网店,发现那个酒瓶还在。哪天突发兴致,将它买下也未可知。
我家有一个地窖,原本没有打算用来放酒,只是觉得有这样一个空间,应当把它利用起来。后来察觉地窖有些湿潮,面积也不算宽,除开放酒,似乎再无用处。得出这样的观点,便把两瓶酒放进去了。半年后打开,原先装酒的纸盒竟然腐烂,连贴在酒瓶上的纸,也生出霉衣。后来宴请朋友,我拿出一瓶来喝,竟都称赞不已。也许这样存放几年,酒更能增加味道。剩余那瓶,我捡出来放在厨房。几个月不在家,前几日回来,发现瓶盖被老鼠啃过。我没有细看,但估计那瓶酒已经走气了。那两瓶酒,还是我的忘年交张友文所赠。
张友文兄是杜康门生,称得上土豪,却不是劣绅。他热情豪爽,往后有机会,当引你认识。十年前我去鲁院,他设宴践行。宴后剩下一瓶好酒,他随手便塞到我的手里,说拎到北京给铁凝喝。到京城当晚,就拎出来给同学喝了。我们的铁凝主席,自然酒香都没能闻到。某次见面,张友文兄提出要送我一百瓶酒,并在包装上标注我的私藏酒。我着实吓了一跳,当即拒绝,上百瓶酒,实在没有地方堆放。张友文兄商量说那就五十瓶。我滴酒不沾,仍不敢领受。张友文性格慷慨,让我拎着送给作家朋友。就在我开始盘算,怎样处理五十瓶酒时,却出了意外。制造包装的厂家,要求五百瓶起印。那五十瓶私藏酒虽未收到,张友文兄却专门定制一坛刻着名字的好酒送来。那坛私藏酒,以前就摆在客厅那个鸡翅木桌下层。
兄上次来的时候,那个木桌上层摆放的是一尊唐代佛身。那尊唐佛缺失较多,只有半截躯体,却线条流畅,有着极高的艺术水准。我常在佛前,喝茶看书。我的朋友古宴臣是茶道行家,收藏着许多昂贵的茶叶与紫砂壶。宴臣经常给我送茶,他每次过来,总说那个佛像不能摆在家里。书房摆放历代陶俑百余,我尚无忌讳。宴臣几次提到那尊唐佛,我却渐渐感到别扭。终于寻个机会,将它恭送出去。就连那坛私藏酒,也被我搬到别处去了。我知道兄的喜好,那坛酒却舍不得给你喝的。我估计兄的酒量,无非就是几两,但那坛却有二十斤。若不一次喝完,封口恐怕并不容易。
说到喝酒,我无端想起一件事来。几年前《走火》聚会,大家喝酒读诗,畅快淋漓。我素来不喜欢喧嚣,却又无法抽身,只得在一角枯坐。灯光明暗不定,周围飘着酒香。我闻着酒香,莫名想尝味道。屋里陡然放亮,李晁见我端着酒杯往嘴边送,大吃一惊,脏话也便脱口而出:狗日的,怎么劝都不沾酒,原来是躲着喝!李晁能喝,但据我猜测,酒量必不如兄。兄有刘伶风范,那次若是在场,酒量当可称王。
记得前年兄来贵阳,晚饭过后,我们各端一杯清茶,畅快坐谈。周围只有一架杂书,三面白墙。聊天到深夜,兄几次提出要喝一盅,都被我阻止了。在我的老家,几个酒鬼喝坏了身体。我的一个堂兄,某晚醉后失去踪影。村里的粪坑都用竹杆挑过,仍然搜寻无果。数月过后,方在山上寻见尸体。原来堂兄醉后,在自家附近迷路,走到山上,被一根树藤所绊倒,因无法挣扎起来,最终憋死……在我的认知里,喝酒是比较糟糕的事情。
去年我到昆明,徐兴正兄也赶来了。晚上吃饭,两位兄长喝得似乎不少。饭后到兄临时居住的地方,喝茶闲聊。凌晨时分,兴正兄回家去了。兄好像也有急事,安排我到客房休息,然后匆匆出门。我失眠严重,服下安眠药,希望好歹能够睡上一阵。也不晓得过了多久,兄进屋开灯,坐在旁边接上之前的话题。我不知兄是长谈,还是短聊,昏昏沉沉地靠在床头。清谈期间,兄拿来一瓶啤酒独饮,这让我相当惊讶。据我猜想,那瓶啤酒喝完,总该收场。未曾想,兄竟然拎出第二瓶。我陡然感到自责,兄在贵阳几次想喝都被我制止,实在不通情理。
前些时间,兄提出以后不喝酒了,真是让我吃惊。我猜想肯定遇到问题了,但兄不愿细讲。嗜酒到这步田地,突然表示要戒,换成别人我当然不信。但兄的坚毅,我却非常清楚。既然说往后不喝,那必定是真的了。我只是有些遗憾,世间难得有几样自己喜欢的东西,就这样戒掉,真是有点可惜。倘再见面阔谈,我们便只能各端一杯茶了。
关于饮茶
宴臣几次约到他家喝茶,回来都没能睡着。别人失眠,似乎第二天就能好转。我却有些奇怪,失眠还有连锁反应,硬要折腾十天半月才能恢復,简直糟糕透了。说起茶叶,我并无什么研究,不能解其妙理,虽然平时也喝,也无非习惯而已。挚友曾送一盒梅家坞龙井茶,打开喝过几回,实在没有觉得特殊,随手就给父亲了。老人除掉吃饭睡觉,总是抱着一个大茶杯,但他听说那盒龙井价格昂贵,竟舍不得喝了。上次回到老家,发现茶叶已经放得发霉。
在宴臣家里,昂贵的紫砂壶起码有几十把。茶室四周,还置放着许多寿山、青田、昌化,还有巴林之类的名贵石头,看起来奢华雅致。宴臣煮茶用的水,专门装在一个紫砂大瓮,据说这样止水不腐。黔灵山上有一眼山泉,水质极佳。清晨五六点,总有人跑到山上背水回来泡茶。因工作关系,宴臣起居规律,否则以他对茶叶的痴迷,早起上山取水的闲人里面,恐怕有他一个。
在城里,喝茶是一种格调。二三好友,品茶尝水,过得相当惬意。但在农村,茶叶的功效,差不多只剩解渴了。至于茶具和用水,更谈不上讲究。记得早些年,经常看到有人背着粗陶烧制的土罐,摆在街上贩卖。那些土罐银光闪烁,异常显眼。大个的那种叫砂锅,大家往往买去煮红豆,或者炖鸡和猪脚之类的东西。中等的土罐,通常是生病时熬药用的。剩余那种只有拳头大,腰更鼓,颈更细,嘴也更尖,我们称之为“茶烧”。前面两种,都是一两个地买,茶烧却是成串拎回家里。
在黔西北农村,堂屋必有火塘。无论走到哪家,迈进门槛,主人就递来一个茶烧。自己抓茶进去,随后放在火上烘烤。烤茶考验技术,每隔片刻要抓起茶烧,根据火候强弱,以适当的手力均衡抖动。茶叶半焦,注入滚水,随着噗的一声,白色的水汽扑腾而起,茶香也随即飘满四周。放在火炉上,重新煮沸后,才倾倒在杯里。这样烤出来的茶水,颜色澄黄,劲道十足。老家的村民喝惯这种茶水,晌午从地里回来,进门就要烤上几杯灌到肚里。下午扛着锄头出门,也要事先把茶喝足。倘若哪天有事耽搁,未能喝上茶水,必定要喊没精神。
无事读《茶经》,里面说煮茶用的水,以山水最佳,江河里的水次之,而井水最差。早些年,老家饮水非常困难。还没有搬到镇上时,母亲每天早起,走上两三里路,到一个叫砂锅窖的地方挑水。那口水井在草地上,比脸盆大不了多少,四周满是牲口足迹。后来我家搬到镇上,吃水的难题仍然未能解决。我们往往坐到凌晨,然后拎着桶去打水。先到的总要跳进去,踩得里面尽是乱七八糟的足迹,见井里蓄到一点水了,赶紧拿瓢去舀。井底的石板,刮出响声来。拎着水桶出来时,井边早就围满一圈排队的。这样的水用来泡茶,连卫生都成问题,跟生活品质实在不沾边。
《茶经》讲得透彻详细,种茶的土壤,以岩石风化处最好,其次是砂砾地,最差的是那种黄色黏地。那些年,村民手里并不宽裕。家里所放的茶叶,多半自己到山上摘来的,颜色醒目,叶片肥硕。黔西北山风粗砺,土地贫瘠,似乎应合了茶叶的生长条件。大家用土罐把茶叶烤焦,离多远也能闻着香味。以滚水煮沸后,他们噘着嘴,吸出响声来,偶尔把茶叶吸到嘴里,顺势就嚼来吃了。见他们喝得酣畅,我忍不住尝试,竟比中药还苦,再也不敢沾染。
写作的头两年,崇拜县里一位作家。几乎每次进城,都要跑到他家。村民喝酽茶,无非是止乏解渴。城里人多半不从事体力劳动,有闲情逸致,细品清茶。那位作家的书房里,就摆着一套精致的茶具。我总跟他喝着茶水,彻夜长谈。那段时间,听他说过不少稀奇的事情。他從部队退伍回来,凭着精明,谋得一个体制内的工作。县城扩张,他曾率队拆迁过许多坟墓。据说扒开一座古墓,发现棺材竟钉入铁棍。由于年代久远,差不多锈得只剩棺木上的铁柄了。我非常震惊,不明白墓主生前有何种恶劣行径,以至死后仍不得安宁,招来这种极端的报复。天亮过后,我带着满脑袋故事,告辞离开。估计我的体质不适合饮用绿茶,回来后依然精神亢奋,难以入眠。我现在严重失眠,也许和以往的积习有点关系。
自认识以来,这个作家总是昼伏夜出。起初我以为这是生活习惯,后来才听他讲晚上不敢休息。以前还用呼机的时候,家里的座机居然自动拨打他的号码。关键在于,他家里无人。还有一次,他开门回家,看到地板上赫然有一个血手印。然而最残酷的是,这个作家朋友曾有个儿子,某次带着睡觉,醒来发现,自己的一只手捂住孩子嘴鼻,已将其捂死。他身家千万,希望有个儿子能够继承家业,但硬是求而不得。这些事情未向其求证,尚不知真假。但多年前我和他去省城,偶遇一个和尚。那个修行人说,他的身边跟着许多邪物。
这个作家打算临时抱佛脚,专门在家辟出佛堂,但似乎效果并不理想。据我揣测,让他陷入恐惧的远不止当年拆除坟墓。这作家极其精明,他如同一口铁锅,就连身边的朋友,也都想多少熬出油水来。大家逐渐熟悉秉性,纷纷敬而远之。尽管他著述零落,但在地方好歹算文化名流,却因恶行太多,不敢按时睡眠,只能煎熬地坐到天明。倘无意外,这个活在县城的作家,此时必端着一杯茶水,孤独地坐在书房。连续几十年,他每晚饮茶,几乎把自己变成茶罐了。
这片土地,历来有喝茶的传统。千百年来,涌现不少写茶的诗句。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这样两句:诗写梅花月,茶煎谷前春。明代许次纾在《茶疏》里说,清明谷雨,摘茶之候也。清明太早,立夏太迟,谷雨前后,其时适中。谷雨时节采摘的春茶,滋味最好。若在茶室置放两枝梅花,格调大雅。品茶是生活质量的体现,宴臣精通茶理,也不为衣食所累,故常邀三五好友,坐饮畅谈,韵致清远,颇有上古遗风。
那个作家虽也富裕,却没顾上享受生活,仍要一门心思钻营名利。由此可见,龌龊并不是哪个阶层的专利。喝浓茶的起码能够出售力气,而喝清茶的缺乏身力,也无法出卖自己的肉体,似乎便只能售卖灵魂了。我与那个作家曾是忘年之交,但多少不愿往来了。茶叶倒宽宏得多,无论善恶,谁都饮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