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集兴答
——第六届杭州·中国画双年展》前言
2021-02-21许江
文/许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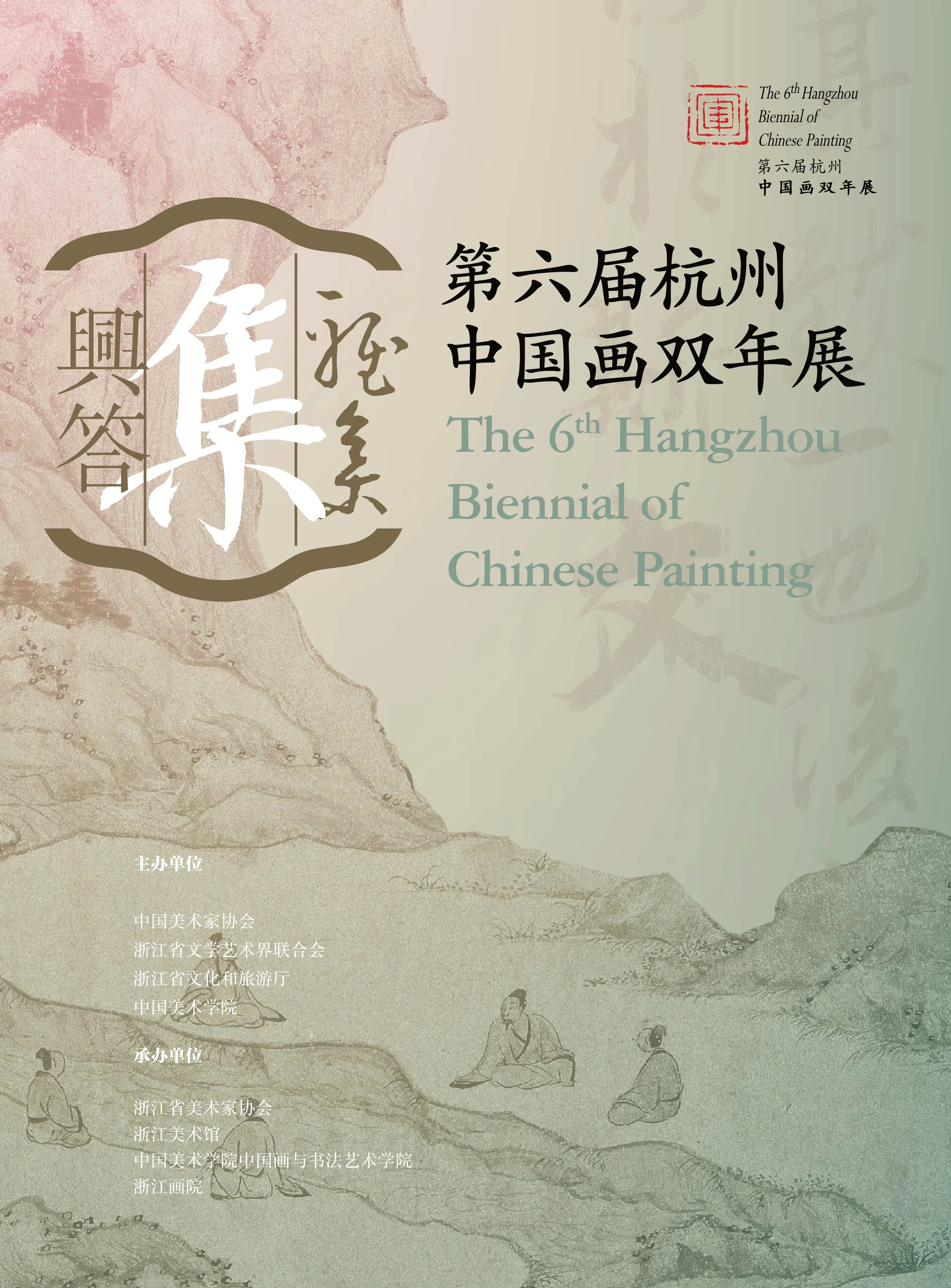
庚子年,新冠疫情无端延绵,杭州中国画双年展却不屈不挠,如期而至。隔离居家,最挂念的是聚会。雅集,沿着杭州中国画双年展深扎东方文化生态、对标中西根源差异的路径,栖栖然扑腾而来。好友数人,如约契会,真情畅叙,觥筹相对。《文心雕龙》有言:“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正是对雅集的兴意写照。起兴、情酬、共赴、畅答,诸般风来雅合之举,俱在其中。风月正好,时不再来,雅集之中的,正在兴与答。故本届主题脱颖而出——雅集兴答。
雅集之美,不唯佳肴,不唯美景,而在雅集者蹈约而来,豪情相赠,聚成一片,即情即兴,通达无涯的生命风华!某个节令和情景的当下,离别送行,寻游来访,山水登临,良辰新月,诸般聚集,将心灵置于杯盏之上,抒展即时的吟咏与挥洒,情感须臾,聚兴笔下,不期然涌起一份特殊的充溢。古之兰亭是一例,往昔千万诗人觥筹交错,醉歌乍起,成百千例。同志者齐蹈山河,共历美景,正自有心灵契合的风神,此所谓唱和。如是兴答与唱和,风雅款款前来,其相会便有诸般变化。在此,略以雅集的四种设想,来叩问古往今来的风雅聚会,探秘天南地北的幽院雅园,与天下雅集者共赴心灵邀约,引觞满酌,陶然就醉,共造物者一道振翮抚霄,做无尽之游。
第一种设想:雅集之登临胜迹之境。孟浩然诗云:“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孟公吟诗念羊公。当年羊祜常游诸山,登岘山,宴同游,慨然而言:“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圣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登高望远,如若古老的契约,让人心在山水中相逢,由此去揭示山河及其历史的真理。孔子设问诸生的理想,曾皙镪止而答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种节令中的雅集和履旅,最接近自然生命的本色,它让人的身体与节候时温相浸润,最具中国人自由畅神的诗性特点。此般山高俯仰,风船徘徊,胸襟激荡,目光流盼,令山川俱景,草木皆神,让生命的叹欢、流逝的行迹、山川的秀美、云色的苍凉,俱在此时此地相聚,山壑、晴岗、草木、高台、故物、新月凝在一起,供吾辈远眺瞻望,并立于一个高度之上。念天地之悠悠,聆往圣之余响,迎时风而高歌,乘神气而图景,正是雅集的登临胜迹之境。
第二种设想:雅集之逐迹怀远之境。李白有诗《谢公亭》。谢亭是当年谢朓与范云离别处,不知有否宴集,李白却每每不禁生愁。青天明月,碧水空流,池花映日,窗竹鸣秋,“今古一相接,长歌怀旧游”。我与古人息息相接,高歌一曲,怀念先贤的此地旧游。此诗写景,也表达诗人面对谢亭追思遐想、欲与古人神游的情状。诗者在缅怀遐想之中,依稀见到古人的风貌,沟通了古今的界限,乃至由怀远而达到共鸣。这里所谓的“一相接”,是由于心往神驰而与古人在精神上的契合,并由此来完成与远方故人的追踪逐迹。
有朋相会,抚今追远。当年王羲之率好友与众同族子弟,游会稽山水,聚曲水流觞,取诸怀抱,因寄所托,兴味老之将至,感怀今后之视,俯仰兴怀,挥就千古名篇《兰亭集序》,中国雅集之风由此兴盛。孔子曰:“告诸往而知来者。”逐迹长歌,追远溯源,恰是雅集的不尽兴味,以不同的进行时的方式追访往圣的、这些不凡的缺席者的现场,用自己的身体重蹈先行者的胸怀,寄寓日暮乡关的殷切。在那里放拓激昂,纵励生命,恰成雅集的逐迹怀远之境。
第三种设想:雅集之伤逝悲慨之境。自然本无情,宇宙了无时间伤害的痕迹。中国的雅集诗人们都有一种共通的时间感受的模式:天地不变与人世无常的对比和冲击。季节有时,世事无端,正是这种基于“时”的感念,带来不尽的伤逝与追怀。“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江山不管兴亡事,一任斜阳伴客愁。”俯景伤怀,冷酒愀心,诗尽处,最是沉甸甸的悲慨。雅集之景,或登高望远,或临风怀远,举觞之间的现场和风情不能不重视。此现场多为送别践行,风情便总含伤逝。怀春、悲秋、故地重游、人去楼空、风景不殊、江山易主,清茶熟酒里总怀一份忧伤;即目之所,处处泛起悲歌。
杜甫的名诗《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大概也是一次雅集上的相逢。诗人的追怀是对往昔盛世的怀念。“岐王宅里”“崔九堂前”是当日文艺名流雅集之所,是鼎盛时期精神文化聚集的地方。在这脱口而出的咏叹中,流盈着诗人对往昔的无限眷恋。接下来,江南好风景与落花时节、乱世动荡的强烈反衬,一位老诗人与一位老歌唱家在颠沛漂流中重逢。凄光流水的风色,点缀着两位形容憔悴的老人,成了时代沧桑的典型画面。像《长生殿·弹词》中李龟年所唱:“当时天上清歌,今日沿街鼓板。”“唱不尽兴亡梦幻,弹不尽悲伤感叹,凄凉满眼对江山。”如此短短的吟唱,让“世运之治乱,华年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俱在其中”。
中国诗人的写作,多免不了有某种自传的成分,因为其书写的是真实生命的周遭,是在山水中、生活中即刻的身体经验。雅集更是这种即刻的吟咏。无论“登临”“怀远”,还是“即目”“直寻”;无论是“情往似赠,兴来如答”,还是“情感须臾,不因追忆”,都将诗作视为诗人某种片段性的自传。画却不然,它自有一份虚拟的时空想象,含道映物,澄怀味象。此象非确定对象,亦非纯然虚构,而是妙在似与不似、情往兴答之间。热眼看花,醉笔潇洒,那手握之笔总是指向划土为疆的田地。雅集又将之导入随性率意的时空,形成某种非虚拟却又不受自传时空束缚的想象。画者当时此地的专注,那朦胧迭进的境界,那无端地感时伤世的怅惆,交相映射,催笔传情。诚如明清之际的弘仁所言:“倾来墨沈堪持赠,恍惚难名是某峰。”
第四种设想:雅集的御风陶醉之境。雅集必饮酒,酒酣耳热之时,容易放任纵浪,直入陶然醉酡之境。此时醉笔,提按风雨,使转烟云,可谓御风。《列子·黄帝》有言:“心凝形释,骨肉都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随风东西,犹木叶干壳,竟不知风乘我邪?我乘风乎?”
《诗经》中写得最多的是草木,以草木寄寓人心。这也照出中国人的心灵始终带着一种植物性的依恋:体认根源,念恋群体;从不轻移,含英咀华;四方生长,向心归簇;含中向道,挺质倚天。因此,中国诗人们对草木、山水的书写、诗写、画写从未停止过。梅兰竹菊,曾是古往今来多少雅集上众笔传递、群韵唱和的莘莘之物。那墨梅风竹更是兴来之时、纵笔直追的淋漓畅意。陶渊明的《饮酒》,写那高贵的翼翼归鸟,不愿轻易落下。“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它看到山崖上挺立的孤松,就收敛了翅膀,遥遥栖落。后来,它将此松视为栖居之所。“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陶渊明总以飞鸟托志,写青山不老,写隐逸之心。“此中有深意,欲辨已忘言”,正是精神御风的写照。
柳宗元在永州,委废于世,却与山水为伍。始登西山,觉“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此是御风之语,“引觞满酌,颓然就醉”,此语方能出。
苏轼《赤壁赋》名贯古今,皆酒酣心醉、陶然入化之作。苏子与客泛舟赤壁之下,客叹生之须臾,羡长江无穷,于慨然中托遗响于悲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苏子坦坦然言说:“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这是诗,也是宇宙宣言。水与月,消与长,变与常,一瞬与无尽,所有与莫取,耳声与目色,最后归于造物者之无尽藏。一番话,让人心醉,让历史俱醉,正“不知东方之既白”。
四种设想,指向四境。此四境,交揉叠错,彼此诱发。良辰当时,佳肴即鲜,起兴在盘餐之间,酬答犹举觞时刻。又依稀先人踪迹,我们逐迹而行,将自己一次次地泊锚于这一片已自文本阅读而“经历”过的场所,长相浸润,情似赠,兴如答。
所有的民族对山野林泉俱有神往。但民族不同,审美亦不同。各种语言体系中的美感经验,主要借文学、绘画、器物、园林得以积淀和传承。真正的艺者乃由这些语言洞烛幽微的理解而非对事物的了解来分辨。母语体系中的诗是不可以翻译的。据此,常被视为本然的草木山水的美感,其实是一种值得我们悉心研究的文化。通过雅集,我们可以看到民族心理、精神趋向、形式语言在生活之树上的成长,并沿着这份生命的长青,而抚今溯往,逐迹古今,把盏唱和,挥毫兴答,上下五千年矣!
谨以此文,寄语杭州中国画双年展,并热盼开幕之日的雅集,雅相集,兴如答! ■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