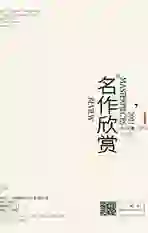论李娟“羊道”系列散文的人文精神
2021-02-08王辉
摘 要:李娟“羊道”系列散文,取材于她在新疆哈萨克族家庭体验游牧生活的真实记忆,围绕着扎克拜妈妈一家,记录和书写了当地游牧民族的生命形式,以“在场”的姿态和精神,细腻地描绘了游牧民族的人文风情和自然景观。对哈萨克游牧民族人事物的观照、民俗文化的全息式的呈现,以及人情人性的展示与高扬,无不凸显李娟散文的人文关怀品格,此外,作者在散文中表现出的自我审视和文化反思的精神,也同样传达了对人文价值的追求。
关键词:李娟 羊道 游牧民族 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诚如第二届“朱自清散文奖”给予散文集《羊道》的颁奖词:“李娟以一种个性鲜活的方式,看取边塞人民的生活状态,观察边塞人民的生命态度,探究边塞人民的价值观念,也惊异,也慨叹;也感动,也凝思。”李娟“羊道”系列散文表现出的对游牧民族生存状态的关切,对他们精神品格和民族文化的关注与探求,以及对自我生命的审视,不仅仅是她独特的审美情趣和创作理念的折射,更重要的是,展现了一个作家所应有的人文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一、 游牧民族生存状态的观照
李娟笔下的哈萨克游牧民族生活在祖国的边陲地带——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富蕴县,这里自然条件恶劣,冬长夏短,低温是常态,大风大雪更是不定期轮番登场。在日常生活中,游牧民族有许多困难和不方便之处。平常的饮用水,他们需要跋涉离驻扎地很远的一段距离,靠人工从有结冰的地方凿冰背回家,以便家用,“在吉尔阿特,能供我们食用的水,只有山体背阴面褶隙处堆积的厚厚冰层。我们得用斧头把冰一块一块砍下来,再背回家化开。取用最近的冰源得翻过一座山坡,再顺着山谷一直走到西南面的山梁下”a。 落后的交通也同样成了生活的阻碍。每次出门去县城办事或购买生活必需品,牧民们不得不几经辗转与波折。想进城的人得一大早出发,骑马穿过重重大山,去石头边等车。听闻有人在某处等车,司机赶往那边接人,等凑够了一车人,就跑一趟县城。
游牧民族是被现在文明遗忘的群落,他们的生存高度依赖自然环境,时节气候的变化决定了他们一年的生产秩序和节奏,比如转场的时日和去向,薅骆驼毛和羊毛的时机,驻扎地的选择也要充分考量地理生态的情况。他们对待自然的态度是敬畏和顺从,有与生俱来的生态保护意识和节制精神,因为在他们看来,自然提供了他们所必需的基本生活资料,是人类母亲般的存在。此外,为了延续本民族的长远发展,对自然的索取应该是节制的,要给予它恢复生态的足够时间和适当环境。关于游牧民族的自然保护意识,李娟在散文中有过这样的叙述:“妈妈向我解释了几句,大约是与草有关的原因。对了,这是保护环境的需要。如果嫌麻烦,长时间在一个地方驻扎、炊息、圈羊,对那个地方的破坏该多严重!”b
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是原始的,生活形式是传统的,注定了他们的生存脱离不了繁重劳动的艰难和积劳成疾造成的伤痛。但是,辛勤的劳动让他们生命的质具有强大的韧性和力量,传统的生活形式让他们对生命的认知充满着朴素的智慧,也使他们能够得到独一无二的快乐,这种快乐比现代都市靠泛滥的商品和物质堆叠出来的快乐更恒久和踏实。在《从城里回来的人》这篇散文中,李娟对扎克拜妈妈令人酸楚和感动的辛劳有过描述。妈妈要去城里吊唁,为了不耽误家务,挤压自己的休息时间通宵干活,“出发头一天,妈妈几乎忙碌了整个通宵,尽可能多干些第二天的活儿。还要煮牛奶,捶酸奶,洗黄油,再一一装罐”c。 由于没有现代工业和技术带来的高效率,几乎全靠体力劳动从事经济生产活动,游牧民族的辛苦和劳累超越了普通人的想象,他们的生命承载和背负了太多,扎克拜妈妈操劳的一生是整个民族的一个深度缩影。
游牧民族是一支永远走在路上的民族,也是一支融入自然,依靠自然生存的民族,他们以草原为家,以羊群为伴,以自然雨水为生命之甘霖,也源于此,他们对生命的认知也处处显现出顺其自然的态度与哲学。在《马陷落沼泽,心流浪天堂》这篇散文中,游牧民族那种“尽人事,听天命”的自然哲学和达观态度,从救马事件中可见一斑。该散文叙说了阿依横别克、斯马胡力和卡西成功拯救一匹陷落寒冷沼泽的马的故事。在整个救马的过程中,面对马儿命悬一线的危险处境,“我”只是一味泛滥悲情和表现出怜悯的样子,却没有能力做出实际的行动,而斯马胡力他们尽最大努力投入营救,并且從头到尾都无所谓地笑着。通过对比“我”与斯马胡力他们表现出的截然不同的处事态度与智慧,高度赞扬了他们从容与豁达的生命观,正如作者在散文最后发出的深刻议论:“节制情感并不是麻木冷漠的事情。我知道他们才不是残忍的人,他们的确没我那么着急、难过,但到头来却做得远远比我多。只有他们才真正地付出了努力和善意。” “他们一开始就知道悲伤徒劳无用,知道叹息无济于事,知道‘怜悯更是可笑的事情——‘怜悯是居高临下的懦弱行为。他们可能还知道,对于所有将死的事物不能过于惋惜和悲伤,否则这片大地将无法沉静、永不安宁。”
二、 人性美的展示与高扬
作家李娟的人生经历充满着曲折与磨难,她有过晦暗的成长时光。年幼父爱缺失,与七十多岁的外婆、九十多岁的祖祖生活在一间八平方米的房子里,房屋破败不堪,家产只有一个泡菜坛子,一个大木盆,一个陶炉,此外还有一把竹几,一个木柜,几个板凳。外婆以捡破烂为生,逼仄的房子里除了三个人,便是碎纸破布、瓶瓶罐罐这些垃圾。由于贫困和缺衣少食,李娟童年矮小瘦弱,形象邋遢,放学路上常常被男同学霸凌与殴打。频繁辗转于四川和阿勒泰两地,也使她的生活处于漂泊流浪的不稳定状态中。诸如种种,李娟过早地体验了人生的苦难与不堪,也渐渐养成了敏感细腻的性格和对人情冷暖卓越的洞察能力。李娟在散文中,极力描绘和全息式地呈现哈萨克游牧民族的民俗与文化传统,努力挖掘文化和民俗行为背后牧民们的优美人性与人情。
李娟在“羊道”系列散文中,描绘了大量哈萨克族家庭的生活片段,而这些零碎的生活细节,共同拼凑成了哈萨克游牧民族的壮丽生活图景,而最让人憧憬和迷恋的是他们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礼俗。哈萨克族有互助的传统礼俗,是不掺杂任何功利企图和交易意识的。他们心甘情愿地给邻居提供帮忙,是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也是一种特有的民族本能,而邻居在接受帮助后,会给予感恩和回馈,这种回馈并非是钱财来衡量的,而是一件充满人情味的礼品或生活用器。这种纯粹的礼俗往来,排斥了现代商业社会人与人之间冰冷的契约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利用,剥离了人的虚伪与欺骗,只剩下心与心的赤诚相对,情与情的碰撞与升华。
热情好客是哈萨克族的另一民族传统,与其说这是他们世代传承的生活礼仪,不如说是支撑起本民族蓬勃与繁荣的民族精神。游牧民族人口密度低,稀稀落落地分布着,转场驻扎在一个地方,映入眼帘的只有茫茫荒野,如果需要到邻居家串门得辛苦奔走一段距离。可以想象哈萨克族牧民生活在如此冷清与荒凉的环境,该是多么的寂聊,多么的孤独。大概也正是人烟稀少的地域特征和流浪般的转场生活,难以有足够的社交活动来填补情感的空虚,哈萨克民族会格外倚重人情交往。一旦有骆驼队从自家门前路过,牧民会给予他们热情的问候,提供他们吃食和奶茶,如果有邻居来串门,会像对待贵客一样款待他们。此外,如果有转场新搬来的邻居,牧民同样会携食物上门拜访。
哈萨克民族除了在人际社交方面注重礼俗,在屠宰方面会遵守宗教仪式,给家畜必要的礼遇和尊重。比如,李娟在《山羊会有的一生》 中写道:“我知小尖刀,鲜活畜。仅仅几分钟的时间,它就从睁着美丽眼睛站在那里的形象化为被拆卸的几大团肉块,冒着热气,堆积在自己翻转过来的黑色皮毛上……我知道斯马胡力在结束它的生命之前,曾真心为它祈祷。我知道,它已经与我们达成了和解。”d哈萨克族牧民是伊斯兰教的忠实信徒,在屠宰家畜过程中会严格依照宗教规定的程序和方法。比如,要使牲畜面向“格卜赖”,念“台克比尔”赞词;应该从动物的前面宰,不可以从其后面、脊背宰起,割断动物脊髓是不可以的。从这一系列宗教仪式中,我们感受到的是牧民心灵的圣洁,屠宰行为的文明,以及对家畜生命的无比敬重。
三、 自我审视与文化反思
李娟的“羊道”系列散文,不仅表达和记录了哈萨克游牧民族生命形式与文化传统,而且揭示了作家自我的情感与精神世界。透过散文质朴清新的文字,我们在为哈萨克族生命的坚韧与人性的高贵肃然起敬的同时,也会为作者自我审视的真诚人格和文化反思背后的人文关怀所感动。李娟散文的自我审视,来源于对“孤独”的深刻体验,她在散文中大胆袒露和抒写自己的孤独感,并追寻和探求造成这种孤独感的根源。有关孤独感的文字书写,如“每平方公里不到一个人,这不是孤独的原因。相反,人越多,越孤独。在人山人海的弹唱会上,我更是孤独得近乎尴尬”。“坐在大家中间,一边喝茶,一边听他们津津有味地谈这谈那……我无法进入。我捧着茶碗,面对着高山巨壑。不仅仅是语言上的障碍,更是血统的障碍,是整个世界的障碍”。从这两段文字中,作者给我们揭示了自身孤独感的根源,即文化的差异和隔阂使作者无法完全融入哈萨克族的民俗生活。拥有汉族血统身份的李娟,从小接受的是汉文化教育,价值观、文化心理和生活方式完全异于游牧民族,即使有与哈萨克族共同生活的经历,也难以跨越两种异质文化的鸿沟,消弭种族属性和生活习惯的差异。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其实孤独感是人类生命主题之一,孤独体验作为生命存在,是普遍的,无法避免的,正如作者说的“是整个世界的障碍”。
李娟是一个具有强烈忧患意识和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家,她秉着纪实的态度,以“非虚构”的创作形式,为我们高度还原和呈现了哈萨克族的真实生存景观,不仅揭示了游牧文明的优与劣,而且洞察出现代文明的渗入给当地促成的变化与影响,文化反思的意味十分浓厚。李娟对游牧民族的文化整体上抱以肯定和赞赏的眼光,在某些方面,她却持谨慎和保留的态度。游牧民族勤劳节俭,尊重自然,热情好客,讲究礼性,但是缺乏人本意识和科学观念,不重视生命健康。例如,有的哈萨克家庭把孩子的命看得比牛羊轻贱;卡西的耳朵流脓,她自己却不当回事;斯马胡力牙疼了,在家里翻到药就吃,也不看药是否适合病症;扎克拜妈妈犯胃病,家里胃药吃完了,就用土方子随便应付一下。游牧民族继承先辈一代代积累的生存经验和智慧,安守于草原谋取生计和繁衍子孙,因各种原因与外界的交流较少,新的文明和思想难以在当地落叶生根和普及,所以,依赖本土经验的牧民们的思想观念难免倾向传统和保守。
阿勒泰哈萨克族游牧区虽然远离都市的喧嚣与繁华,没有发达的工业、盛行的消费文化和拜金主义,牧民们基本上仍旧保持着本民族古老素朴的生活方式,节制物欲,也没有沾染城市人的坏习气。但是,强势的现代文明还是像风一样,悄无声息地吹到了这片土地。比如,新的奶油分离工具——分离机的使用,把许多主妇从沉重的劳动中解放了出来,但是,用这种省功的方法生产出的脱脂牛奶,做成胡尔图又酸又硬,也没有什么香味,口感差多了。還有家畜生长激素的应用,“实在难以想象,如果有朝一日,牛羊不再依靠青草维持缓慢踏实的生长,而借助黑暗粗暴的力量走捷径的话……那种东西才是最肮脏的东西”。生长激素虽然能够缩短牲畜的生长周期,使牲畜长得看起来膘肥体胖,提高了牧民的经济收入,但是,食品安全会因此成为问题,人心的异化也会随之产生。李娟在她的另外一部散文集《我的阿勒泰》的《木耳》一篇中,也提到过外界事物的渗透给游牧民族带来的改变。叙述的是受金钱的诱惑,牧民竞相疯狂的采摘山里的木耳,最终导致木耳濒临消亡的故事。综观李娟“羊道”系列散文,作者虽然没有给游牧文明做出确切的评价,更没有与现代文明进行比较,给出直接分明的立场与态度,但是,她对哈萨克民族的常与变的如实描述,对他们生存形式和民族文化的冷静观照,能够给读者提供许多文化反思的空间与方向。
总而言之,李娟散文对哈萨克民族生存的全景式书写,对他们人性和人情的展示,以及对他们民族文化的关切和自我生命的审视,饱含了深厚的人文精神和价值内涵,同时也彰显了作者真诚的人格和现实关怀精神。阅读李娟“羊道”系列散文,让我们得以走近哈萨克游牧民族的真实生活样态,窥见他们的精神世界,触摸到他们民族文化的肌理。
a李娟: 《春牧场》,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21页。
bd李娟: 《深山夏牧场》,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355页,第376页。
c李娟:《前山夏牧场》,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121页。
参考文献:
[1] 龚自清.回到世界与人的基本——李娟散文论[J].艺术评论,2016 (7).
[2] 刘志荣.大地与天空的辽阔与隐秘——李娟散文漫谈[J].文艺争鸣,2011 (9).
[3] 向迅.平凡的世界 温暖的人生——论李娟的散文创作[J].百家评论,2013 (10).
作 者: 王辉 ,中南民族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