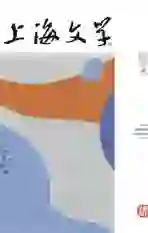关于《风声》的风声,或一个小说家的怕与爱
2021-02-05麦家何平
麦家 何平
何平:我们先從《风声》的外围开始聊吧?
麦家:好,《风声》确实也有些“花絮”可以聊。
何平:我记得,《风声》是2007年以《暗算》第二部之名,在《人民文学》第10期发表的,而《暗算》则发表于2003年的《钟山》,中间隔了四年多的时间。这仅仅是因为2006年电视剧《暗算》的“影响”,还是两者之间存在更隐秘的联系?
麦家:确实存在“隐秘”,但不是《暗算》影响了《风声》,恰好相反,是《风声》影响了《暗算》。《风声》的源头早在1998年,那时无人关注我,你也不可能关注到。
何平:1998年?那一年我好像才开始写文学批评。你把源头推到那么以前,一下空出差不多十年时间,让我十分好奇。
麦家:我是1997年从部队转业到成都电视台的,在电视剧部当编剧,不坐班,也没活干。我在电视台干了十一年,就干了三两件活,加起来花不了半年时间。这十一年我无聊到底,倒也逼我当了个小说家。小说家是被“废”的一种人,火热地生活,每天被人要、被人管是当不了小说家的。生活废了,空了,小说家才活了,蹒跚地上路了。所以,我经常说是成都电视台“培养”我当了小说家,领着不菲的薪资,每天在家写小说,写不出来说明你就不是这块料。
何平:你写出来了,确证你是这块料。
麦家:我以为我是有写东西的天赋的,这种天赋主要体现在摸得到方向、忍得住煎熬,可以用一个晚上想一句话。我1986年尝试写小说,写之前没看过几本小说,但读了大量的诗。有一天我决定写小说,没有故事,只有一些情绪就开始写了,像跟人吵架,毫无章法。弄了小半年,弄出一个两万字的东西,居然发表了。甚至,后来还以此敲开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门,说明它确实有些品质。然后,到1998年底,我在电视台已就职一年多,却只开过会,没开过工。一天我部门的头有点要考我的意思,安排我写一个迎接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的电视剧。我不知道怎么写,临时找了个《美国丽人》的电影剧本,先把样式搞懂了,然后想故事。当时我正在看王央乐先生翻译的博尔赫斯的一个短篇小说集,里面有一篇小说《交叉小径的花园》,现在都把它译成《小径分岔的花园》。这是一个间谍小说,讲的是欧战时期一个德国间谍,在被英国间谍追杀的情况下如何把一个情报传给上司。不论《美国丽人》还是《交叉小径的花园》,离我的剧本都差着千万里,但我就拄着这两根“拐杖”跌跌撞撞上路了,最后写出两集电视剧《地下的天空》。领导看了很喜欢,就组班子拍了。拍到一半,央视一个领导回成都探亲,住在宾馆里,闲着无事看了我的剧本,问谁写的,说这么好的剧本完全可以拍电影。电影他管不着,不了了之,电视剧他是老大,说了算,大笔一挥,拨给我们台五十万,买了这剧。这也替我在台里买了名声和地位,让我可以名正言顺窝在家里写小说了。由此才熬出了小说《解密》和《暗算》,包括《风声》,这都是我在电视台时写的。
何平:我看到作你小说研究的人常勾连起你和博尔赫斯的关系,没想到你的电视剧背后还荡着博尔赫斯的“幽灵”。这或许可以找到你的影视剧与众不同的密钥。下次有机会,我们可以就这个问题聊聊。
麦家:现在就可以聊。你知道,《暗算》是一部“抽屉小说”,由五个独立的故事串的:一个“听风者”,两个“看风者”,两个“捕风者”。2003年7月出版,当月一家影视公司捷足先登,把两个“捕风者”的故事买了。第二家公司想做一个“三部曲”的系列,问我手上还有没有“捕风者”的故事。我就想起《地下的天空》。对方看了很喜欢,但问题也出来了,这东西怪怪的,一半小说,一半剧本,不好找编剧,有署名麻烦。就这样,我索性揽下活,昏天黑地了大半年,弄了一个三十集的《暗算》电视剧本,其中“捕风者”的十集是从两集《地下的天空》长出来的。从两集到十集,不可能只是“注水”:一头猪是无论如何“注”不成一头象的。就是说,在扩写过程中,我加入了大量新东西。电视剧播出后,火了!不仅剧目火了,连带这个题材都火了,谍战剧的剧种应运而生。现在我经常被称为“谍战之父”,其实我是不要这玩意的,它遮蔽了我小说太多的光辉。但平心而论,当今迭代风起的谍战剧风潮正是《暗算》刮起的,严格说是其中的“捕风者”刮起的。“捕风者”是个十分正统的谍战故事,好学易仿,一下子像癌细胞一样地派生,灭都灭不掉。相比之下,“听风者”和“看风者”专业性强,一般人攀不上的。
话说回去,2005年,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收获》的王彪约我写一个正面抗战的东西,时间十分紧,我就投机取巧,把十集“捕风者”剧本改成一部中篇小说,发了。在改写过程中,这个故事被《圣经》的故事照亮,依稀照出《风声》的影子了。我家族里有信基督的遗风,我虽不是基督徒,但确实经常看《圣经》,对《圣经》的故事是了解的。《圣经》的四部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记述的是一个人,即耶稣的生平故事。四部福音书各自为营,有同有异,既冲突又补漏,给了我创作《风声》的灵感。《风声》是“一事三说”:共产党说,国民党说,作者说。所以,要论一事多说的源头,不在《罗生门》,在《圣经》。
啰嗦这么多,我大致把《风声》的写作经过交代出来了。
何平:这些盘根错节的写作秘道,你不说没人能看清楚。这也提醒包括我在内的所谓专业读者,对一个作家的个人写作史,或者说写作逻辑的复原和再现,不能单单依赖作品发表的时间和刊物等这些表面信息。作家的写作,从获得灵感到最后瓜熟蒂落是个相当漫长的生长过程。同时我发现,《风声》的写作过程其实很像《解密》,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述同一个故事。你好像很享受这种近乎游戏的快乐。
麦家:我喜欢对一个故事颠三倒四地写。我不知道有多少故事值得我们去写,但知道一个好故事值得我们反复写。好小说都是改出来的,我迷信这个。《风声》也是这样反复出来的,从最早的《地下的天空》出发,挨了一刀又一刀,除了心脏,其他都换完了。这个过程一点不游戏,而是充满挑战。
何平:再说《风声》的发表吧,好像争了一个第一。据我所知,《人民文学》以前不发长篇小说的,你当时怎么会把它投给一个不发表长篇的杂志?
麦家:当时《人民文学》主编是李敬泽,他一直很关心我的写作,一般我有新作都会请他把把关,提意见。没想到他很喜欢,直接发稿了,成了《人民文学》创刊后第一部完整刊发的长篇小说。责任编辑是徐则臣,现在是副主编了,他为此还写过一篇文章,谈《风声》“破纪录”的发稿过程。
何平:《风声》发表和出版后,你即获得当年华语文学传媒年度小说家。授奖词可以随手在网上查到:“麦家的小说是叙事的迷宫,也是人类意志的悲歌;他的写作既是在求证一种人性的可能性,也是在重温一种英雄哲学。他凭借丰盛的想像、坚固的逻辑,以及人物性格演进的严密线索,塑造、表现了一个人如何在信念的重压下,在内心的旷野里为自己的命运和职责有所行动、承担甚至牺牲。他出版于2007年度的长篇小说《风声》,以從容的写作耐心,强大的叙事说服力,为这个强悍有力、同时具有理想光芒的人格加冕,以书写雄浑的人生对抗精神的溃败,以关注他人的痛苦扩展经验的边界,以确信反对虚无,以智慧校正人心,并以提问和怀疑的方式,为小说繁复的谜底获得最终解答布下了绵密的注脚。麦家独树一帜的写作,为恢复小说的写作难度和专业精神、理解灵魂不可思议的力量敞开了广阔的空间。 ”
这个授奖词应该出自评论家谢有顺之手。对一个小说家而言,“为恢复小说的写作难度和专业精神、理解灵魂不可思议的力量敞开了广阔的空间 ”是很高的褒奖。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对《风声》的评价,也是对《风声》之前的《解密》和《暗算》的追认。后来《暗算》也获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从评奖制度上看,华语文学传媒奖和茅盾文学奖并不相同,前者一定意义上是独立的、民间的,后者则是“国家”意义上的。先后获得这两个奖,再加上读者的广泛认可,有这样成就的作家在当代文学史上并不多。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麦家:这应该问你啊,作家管写,你们评论家管评,奖也是你们管的。虽然有种说法,优秀的作家都善于阐释自己的作品,但我更亲近另一种说法:一个作家的优秀与否在于他写下了什么作品,而不在于他的阐释水平。打个蹩脚的比方,曹雪芹从没有阐释过自己的作品,福克纳也不大有。还是你来吧,这是你的特权和专长,我相信你在抛问的同时心里自有答案,把答案也抛出来吧。
何平:谈不上答案,只是一些个人的想法。我觉得,你的小说里蕴含着中国当代作家很少写却又无法忽视的典型中国革命经验和记忆。一直到现在,“地下工作”“谍战”仍然是中国人革命记忆和想像中最鲜活的部分,“特务”更是过去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当代作家对这么大的一块经验却很少关注,你应该是最先关注的。当你把经验的触角伸展到这样的隐秘世界,如果把你的小说也看作推理悬疑小说,你的写作其实提出了一些悬疑小说的核心问题:悬疑小说究竟是我们生活不可抵达的遥远的异邦,还是我们生活若即若离的周遭?悬疑小说的恐怖、不安、残酷、凶险究竟是生活的意外,还是我们生活的日常?悬疑小说究竟是智力游戏还是心灵探险?等等。
你擅长拿捏读者的心窍,设置小说世界的明与暗,然后摇身一变作为一个自由出没于明暗世界的亲历者出场,把在黑暗中跌跌撞撞的摸索说了出来,获得了对黑暗包裹的一切命名的权力,而且是世界之“暗”最可靠的“传”人。对于我们生活的世界,难道那些被照亮的部分,真的就那样可靠吗?
麦家: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我害怕黑暗、残暴的人性,又渴求去揭露。你说我是“黑暗的传人”,陈晓明也曾有相似的解读。英国一个专业书评人,包括我的翻译和编辑,都有这种指认。甚至,《暗算》的英文书名也被译为In The Dark,翻译回来应该是“在黑暗中”。我很怪的,一个乡村野孩子,却从小就怕黑,做的梦都是黑夜里的事。我没有梦见过白天,而且少年时代经常做同一个梦,一只黑色的大鸟,像老鹰又不像老鹰的一只大鸟,翅膀张开来有一座房子的屋顶那么大;无数次,它从浩瀚的天外飞来,羽毛都是黑色的,在黑暗中黑得发亮,像闪电一样刺眼。然后我一只眼睛,右眼,十一岁那年,一夜醒来瞎了,经过长达半年的中西医治疗,也只恢复到0.3的视力。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但确实在我身上发生了:梦中的一道黑光把我一只眼刺残了。我不知道我想说什么,也许是想说:我一直生活在恐惧中,对黑暗的恐惧,对怪物的恐惧。其实人是最可怕的怪物,我一直相信,那只大鸟是人变的。这种恐惧是我写作的神秘力量。
何平:有意思,你把“黑暗传”理解成写黑暗的“传人”。两个“传”,字同音不同。“传人”记录下来的文字成为“传”。“传人”,既要写出经验到的黑暗、恐惧、孤单、未知等极端个人化的感受和反思,又要让这些经验、感受和反思得以“流传”。从“流传”之“传”的意义上,当代作家很少像你这样做到极致。但是,我们往往很容易把“流传”之“传”看成很俗气,非文学的。这可能是很多作家的一个误区。
麦家:可能首先是你们评论家的误区,你们把作家往“象牙塔”里赶,把讲故事、重“流传”看作俗气,贬为“非文学”。看轻故事是中国当今小说的一种时髦,其实,故事绝对是小说的上层建筑,有故事才是“曲”,没有故事的“曲”,不过是小调而已。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小说一直受“文学”的奚落,连发表都难。
何平:你刚才说了,你是1986年开始写作的,按照世俗意义上一个作家的成功指标,你应该到2006年后才“达标”,历经二十年。你也说过,《解密》在《当代》发表之前经历过十七次退稿。这意味着你的写作生涯有一个漫长的黑暗期,这个黑暗期之长,在当代成名作家中也是罕见的。
麦家:这个黑暗同样让人恐惧,但不会把我变成一个“写黑暗”的“传人”。这个“黑暗”是一块磨刀石,只会把我磨锋利了。花开太早不见得是好事。我庆幸自己没有迅速成名,然后迅速消失。
何平:这次重读《风声》,它“回忆录叙事”的特征,让我想起一本小书《伪装的艺术:回忆录小史》。此书提醒我们,凭读者个人之力是无法辨别那些对着上帝发誓声称自己所言非虚的回忆录的,而专业读者则无意理会真实性这种东西,因为他们默认文学的真实本身就不是客体真实。然而问题在于,如果“真实”标准是多元的,那么真实本身就成了伪命题。
在《风声》里我看到一种非常稳定的结构:面对同一段往事,不同的当事人有不同的“回忆”,读者先要听潘老回忆的“东风”,再听顾小梦回忆的“西风”,最后还要跨越时间去感受“我”所叙述的“静风”。这是一种很后现代的多元主义风格,背后的逻辑是承认真相是无限的,而能够被记录下来的历史记忆只是一种“小真相”。换句话说,它把记忆认定为一种社会活动,通过每个个体的差异之中的记忆来修正那些记忆的“标准像”。你之前提到了“四福音书”对《风声》的“照亮”,事实上,我们如今很难说后现代主义和《圣经》式的叙事究竟是谁先发现了谁,它们好像是同时向我们扑过来的。在先鋒叙事逐渐退场的今日,我们似乎更倾向于把解构带来的那种后现代主义本身视为一种相对主义,认为后现代的背后还有一个真相。
说了这么多,我想知道的是,十多年过去了,也就是当你再次回溯当年架构的“东风”“西风”和“静风”三重叙述,你觉得这样一种对峙的叙事结构,究竟把历史的真实或文学的真实带到了怎样的境地?
麦家:我们知道,真实的生活里其实充塞着太多的不真实,儿子为了一双名牌皮鞋把母亲杀了,贪官把几亿现金窝藏家中,事发后夜以继日地焚烧,匪夷所思到了完全失真——失去 “标准像”!但我们不能指责生活,因为生活有不真实和荒唐的特权。小说有虚构的特权,却被剥夺了不真实的最小权力,《风声》中笨重的窃听设备绝不能被针孔探头替代,院子里的竹林不能换成椰子树林,否则就虚假了。小说中任何一个失真的物件、反常的细节都可能是致命的,因为赋予它虚构的特权就是要高保真,杜绝虚假。所以,海明威说,他不允许任何不真实进入到他的小说里。
也许你说得对,历史的真实是一个伪命题,但文学的真实是一道数学题,是由读者心中的“标准像”和作家对事物的认知换算嫁接出来的。正如数学是最根本的哲学,文学的真实是最高级的,它是从生活本源中提炼出来的一种高保真,犹如玫瑰精油之于玫瑰花。
何平:在《风声》中,历史的真相或曰真理,不是越辨越明,而是越辨越缠绕越浑浊。细读《风声》,你既是命题者又是解题人,那么在具体写作中,谜底在手的你是不是胜券在握地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呢?不是。你把自己设定在一个面对世界之“暗”同样无能为力的捕风者的位置上,一面引领读者去建构一种确信,一面又悄悄去瓦解这种确信。事实上,你的小说到处充满着自我否定和篡改,也就是我上面提及的那种三重叙述对峙的结构,它因为对峙而具有了小说力学上的稳定性。或许正因如此,在特情小说或者谍战小说这种类型小说的专业名词被广泛接受之前,你的小说曾被命名为“智性小说”,王安忆评价《风声》时说它“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将条件尽可能简化,压缩成抽象的逻辑”。
麦家:不是真相或真理越辨越浑,而是多了视角,多了切面。我们接受的教育过于正面、单一,这不符合认清历史真相的逻辑。在一个声音大行其道的高压秩序面前,我们需要其他声音,需要一个怀疑的声音,一种怀疑的精神:怀疑从来不会伤害真相,只会让真相变得更加清白,更加稳固。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跟历史书对着干,这是文学的任务之一。
我一直认为,《风声》里是有大绝望的。从大背景看,1941年的中国乃至世界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时间,二战局势未明,人类处于硝烟不绝的乱世。从小环境说,美丽的裘庄实是人间地狱,人人在找鬼,搞鬼,恶对恶,狗咬狗,栽赃,暗算,厮杀,人性泯灭,兽性大发。而真正的“老鬼”李宁玉,身负重任,却身陷囹圄,内无帮手,外无接应,似乎只能忍辱负重,坐以待毙。眼看大限将至,她以命相搏,绝地反击,总算不辱使命,令人起敬。殊不知,翻开下一页,却有人跳出来,把她舍生取义的故事推翻,形象打碎,一切归零。这是多大的绝望!空间的裘庄转眼变成时间的裘庄,我们都身处裘庄里、迷宫里,看人在时间的长河里不休止地冲突、倾轧、厮打,不知谁对谁错。“我”费尽心机,明访暗探,仍不知所终,甚至挖出来更多令人心寒的“史实”。
何平:我们已经几次谈到博尔赫斯,让人不免想到中国当代先锋文学鼎盛时代,你也是从那儿出发的。但我留意了下,很少有人将你作为形式和观念意义上的先锋作家来看。从今天的中国小说格局看,你是少有的能够将上世纪80年代先锋传统转移和安放在当下,并在当下激发出新的创作活力的作家。先锋小说家普遍征用的“元叙事”、“第一人称叙述策略”、“非道德化视角”、“解构历史”、“游戏化”以及“语言策略”等技艺,这些在你小说中被运用得娴熟老到。从整个写作观来看,你不再按照传统和先锋、雅和俗、宏大和个人等等来建立自己写作的精神谱系和边界,而是自由地调动诸种写作资源。而且,先锋注重的只是小说的结构变化和叙事策略,从小说的世界观看,隐隐约约感到你在向卡夫卡式体制对人压抑的现代命题靠近。
麦家: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今天大概是找不到了,连气味都闻不到。但对什么是先锋文学我有自己的理解,不是一味往前走就是先锋,有时大踏步回头也是先锋。今天我们普遍认同的先锋文学的一些要素,如你说的“元叙事”、“解构”、“游戏”、“反道德”等都失去了簇新的锋芒,老掉牙了。我甚至想,即便我们长出了“新牙”,发明了一些“新钞票”也难以发行。为什么?因为先锋文学的现场是建立在精英阅读的舞台上,而今天精英阅读的台面已经坍塌。互联网让众声喧哗,把精英赶下台,成散兵游勇,随时可能遭大众群殴。精英如虎落平川,失势了,失声了,无力发行“新钞票”,也不想发行了。所有歌声——文字也是歌声——都有表演的诉求,当精英的歌唱无人聆听,甚至只能被刻薄,闭上嘴也许是唯一选择。从701到裘庄,我小说里的人物都被困限在高墙里,人性被重压、异化。但人们津津乐道的是谍战,是故事:这不是精英的声音,是大众的喧哗。这是令人沮丧的事情,但这是现实,恐怕也是未来。
何平:言重了。说实话,我觉得研究你的人并不少,《人生海海》出版一年多来,我注意到至少有二十多篇评论,几乎各大文学评论刊物都作了专题研究。也许你会觉得这些声音微弱,传不远,但可以传下去。传下去才是真正的远,那些喧嚷不过是泡沫,经不起时间的风吹。
麦家:你这是典型的精英思想。
何平:是不是有点堂·吉诃德?
麦家:堂·吉诃德战的是风车,你今天战的是《风声》。
何平:我愿意把这个“你”置换成你小说的读者。我不知读者有没有发现,你的小说所塑造的人物,无论是瞎子阿炳,还是黄依依、陈二湖、容金珍、李宁玉、陈家鹄、林婴婴,或多或少都是带有魔性的人物。陈思和在近几年提出中国作家写作中的“恶魔性因素”。你小说中的魔性人物究竟属于一个怎样的人物谱系,值得我们思考。其实,中国古典传奇和志怪的叙事传统谱系中多的是魔性人物的述异志和畸人传。应该说,我们现在对这样一种带有召唤性的民族阅读传统的研究还不是很充分,包括《暗算》《解密》《风声》《刀尖》等,你一直以来都在强调凸现人物的异质性与偶然性,强调“特殊情境下的特殊天才”。他们在破译形形色色密码的同时,本身已然构成了一种难以言明人物或者英雄或者魔性的历史密码。这自然带来一个相关性的问题,当然也是刚刚说起的堂·吉诃德给我带来的兴趣,即你是如何理解“人”、“人性”和“英雄”这些不断被制造又不断被挪用、讹误的文学元素的?
麦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说,由于亨利·詹姆斯忽视了生活,他将会灭亡。小说不同于诗歌和戏剧,可以放弃对生活的忠诚;小说从生活中汲取养料,必须回到生活中去,对生活负责。说到底,是要对人负责,要提示人的生存状态、内心、人性。问题是我们要对什么人的生活负责,对一个政治家甚至科学家来说,无疑是广场上的人,平头百姓,生而平凡的人,因为他们是大多数;对一个文学家来说,什么人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认知人,什么人的生活更具备文学性,是必须要独立出来考量的。这一点,我有点“复古”,我偏爱深宅大院里的人,有传奇异质的人,有特殊使命和经历的人。他们的生活也许缺乏世俗现场感,缺乏生活质地,少了烟火气,但大开大合的经历,大悲大喜的感受,大荣大辱的考验,可以极限地展示人的内心,透露人性最幽暗的光。尤其在今天,互联网让每个人都成为书写者,人人都把自己当作英雄、传奇者,不厌其烦地推销他们猫猫狗狗的生活,烟雾缭绕,汹涌澎湃。你听到了人的脚步声,但听到心跳声了吗?你领看了生活的多样异彩,但感受到了美了吗?虽然小说家不能以追求美感为目标,但不能获得美感就意味着灭亡。虽然传奇异人的生活不乏偶然性,但什么是偶然?偶然就不是生活吗?用博尔赫斯的话说,所谓偶然,不过是我们对复杂的命运机器的无知罢了。世界不是偶然就是必然,我暗暗对自己说:留下偶然,把必然交给哲学家吧。
何平:研究者关注最多的是你小说里的英雄。你用了两个词:“英雄”和“传奇者”,“传奇者”要远大于“英雄”。从权力关系看,《风声》有很多我们习惯上认为的“反角”和“反派人物”。这些人对小说家和小说技术而言,有的可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传奇者”,比如我就注意到《风声》中肥原从热爱中国到仇视中国进而成为施暴者的人生反转。事实上,你小说中很多所谓的“反派人物”都有他们的传奇性。以前我读你小说,都被英雄人物迷惑了,现在这个问题我要花时间好好想想。
最后一个问题。我突然想起你在《风声》获华语文学奖的演说中说到作家有三种写作方法:“用头发写”、“用心写”和“用大脑写”。你说《风声》是用大脑写的,因为“这不是一个用心写作的年代。用心写作必须具备一颗非凡伟大的心,能够博大精深地去感受人类和大地的体温、伤痛、脉动,然后才可能留下名篇佳作”。去年《人生海海》出版,你觉得这是不是一部符合你想像的“用心”写作的小说? 如果是,你现在怎么看自己个人写作史的用心和用脑写作?
麦家:事实上,没有一个人会说他的东西是不用心写的。不用心就不会提笔,笔不是手提起来的,是心。所以有种说法,人提笔就老,因为要用心,眉头皱起来了。但是心本身是不会写作的,写作是一门手艺。博尔赫斯有一个短篇小说集,起的书名就叫《手工艺品》,旨在强调写作是门手艺活,农民种地一样的,没有脑子,不懂农业,种不好地的。《风声》这个小说,像黑塞的《玻璃球游戏》一样,是一种观念性小说,是作家跟历史下的一盘复杂神秘的棋局,经验、技巧的占比要大一些。这里的经验更多的是集体经验,个人要化到集体中去。但我能把自己化入大和人、斯拉夫人的集体中去吗?化不进去的。我的心只对中国经验敏感、多情。就是说,虽然过程中有诸多技術、设计,但起头的还是心,是一颗中国心,是民族情感。这类小说是不大有作家个体的心跳和体温的,它有脑电波,有算计,有智力铰杀的齿痕。
《人生海海》是反智力的,采用孩子视角就是不要智力,要感受,要心气。孩子有灵敏真切的感受力,我在创作中要不停地回顾、回顾,去找到失散久远的我,那个懵懵懂懂、一惊一乍的孩子。如果说《风声》种的是公共用地,《人生海海》是自家一亩三分地,给人感觉它更加用心、倾情——恐怕你也有这种感觉。但我不认为这是一把衡量作品好坏的尺子。这是两类作品,像锄头和匕首,不可比。也许《人生海海》像锄头,有泥土味,接地气,我们偏实用的价值观会更偏爱它。但这不是匕首的问题,是我们趣味的问题。说实话,十多年过去了,这次重读《风声》,我依然觉得这是一部好小说,真的像匕首一样精致机巧,衔着刀刃的光芒。
何平:对的,像匕首,它的精致机巧,既是小说家天赋的,也是一代又一代读者磨砺的。所以我一直认为,所谓文学经典,是作者和读者在时间长河里的无限延宕下去的密约,是彼此联手打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