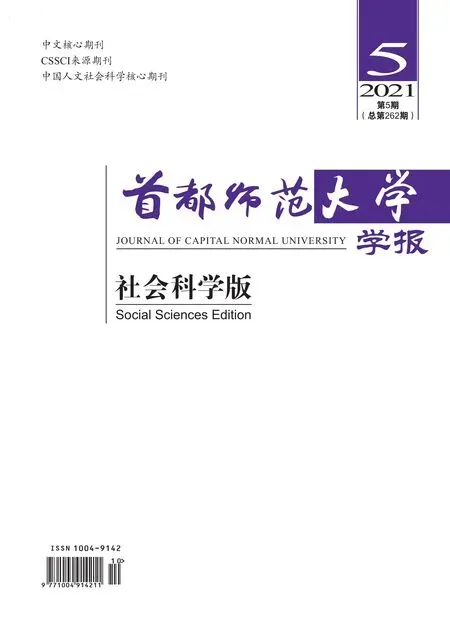日本观念对初期中国“纯诗”的塑造
2021-02-01罗振亚
罗振亚
“纯诗”的有关问题已是全球文学圈内的常识。它先是由美国诗人爱伦·坡论及,说理想之诗应该“完全是为诗而写的”,是“美的有韵律的创造”①爱伦·坡:《诗的原理》,潞潞主编:《准则与尺度——外国著名诗人文论》,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而后在象征主义诗歌鼻祖波特莱尔那里发端,中经马拉美的奠基,到1920年瓦雷里在为法国作家法布尔的《认识女神》所写的前言里第一次提出,最终逐渐蔓延为一股世界性的艺术潮流。中国“纯诗”概念的正式出现,是在创造社后期三诗人之一的穆木天1926年发表的文章《谭诗》中,他和王独清、冯乃超联袂互动,在《创造月刊》创刊号上共时性推出诗论和创作文本,吹送出“纯诗”的最初信风。后来通过梁宗岱、李健吾、戴望舒、何其芳等人的不断阐发和实践,形成了不绝如缕的创作与理论现象,虽然它在抗战期间一度消隐,但又多次被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现代诗运动和20世纪80年代的新潮诗人重提,影响持续而坚挺。对20世纪20年代中期穆木天、王独清等倡导的“纯诗”及实践,以往国内学术界基本认定是引入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欧化”结果,殊不知它远非那么简单。事实上,它是西方象征诗学、日本辰野隆的心灵愉悦理论和诗人主体日本际遇的多元“合力”促成的。穆木天、王独清在文章中强调诗要将自己与散文的世界分开,要有大的暗示能,即来自于穆木天的指导教师辰野隆的“激发”,中国初期“纯诗”中的物哀情调和色音追求,也同日本文化观念的制约有很大关系。
一、“合力”激发的纯诗场域
1925年,李金发的诗集《微雨》出版,宣告现代主义诗歌开始在中国的自觉生长,并且他和蓬子、胡也频、石民、侯汝华等诸多诗人一道,把诗坛渲染得十分热闹,酿成了中国新诗史上第一个先锋诗歌群落——象征诗派。但时过境迁之后,人们发现李金发因根基浅薄,只能让“将东西两家,试为沟通”的愿望停浮于口号层面,真正把象征诗派支撑起来产生影响的,是直接领受“异国熏香”的王独清(诗集有《威尼市》《圣母像前》)、冯乃超(诗集有《红纱灯》)和穆木天(诗集有《旅心》)等创造社后期三诗人。特别是1926年3月,《创造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留学日本的穆木天被誉为中国象征主义宣言书的文章《谭诗》,和王独清的响应之作《再谭诗》,提出“纯粹诗歌”概念,将中国新诗引向了“纯诗”道路。
问题是中国“纯诗”的提出为何是在1926年,为何是在日本,这个时空的场域又是如何形成的,上述一系列的现象背后究竟隐含着什么样的动因抑或背景?在笔者看来,它是多方因素“合力”激发、促成的结果。
一是缘于诗人情思与时代氛围的心理遇合。五四绝非只是历史记录的冷态符号,它对社会、时代和人的心灵冲击影响的内涵,比人们想象的远为阔大、复杂得多,其最明显的表征即是投诸文坛的那种动荡与茫然。随着五四运动落潮,时代的情绪渐从高扬个性与反抗向自我失落的感伤转移,很多知识分子的心里滋生出一种浓厚的苦闷、忧郁与悲戚,这便给象征主义在中国萌芽提供了最为适宜的土壤与气候。而穆木天、王独清和冯乃超三位诗人又偏于内向、敏感、孱弱,或如王独清似的生活潦倒、友情崩坍、孑然一身,或像穆木天似的婚姻不幸、家境凋零,多孤寂冷漠,颓废得无力自救,日积月累便形成了远人厌世的心理结构。同时,他们又是海外寄居的“游子”,为舒缓时代与个人的双重郁积,这几位对现实不满又无可奈何、找不到出路的诗人,只好以歌当哭。可他们的情思难与浪漫主义的澎湃激越协调,也和现实主义的理性客观相去甚远,却贴近着象征主义的颓废唯美;所以,他们自然钻进波特莱尔、魏尔仑、马拉美、耶麦、果尔蒙等营造的艺术天地,沉迷于象征主义诗歌迷离的意象、缥缈的字句与幽抑的节奏等因素组构的神秘氛围,回味起心灵的阴晴圆缺、风雨雷电来。难怪马拉美、拉法格的诗让穆木天“如获至宝”,他说:“我记得那时候,我耽读古尔孟、莎曼、鲁丹巴哈、万·列尔贝尔克、魏尔林、莫里亚斯、梅特林、魏尔哈林、路易、波多莱尔诸家的诗作。我热烈地爱好着那些象征派、颓废派的诗人。”①穆木天:《我的诗歌创作之回顾》,《现代》第4卷第4期,1934年2月。三诗人当时的情形从其耐人寻味的陈述中可窥见一斑。
二是由特殊的生命氛围所铸成。仅仅从时代情绪视点并不能完全说明“纯诗”理论与创造出现的原因,还揭示不出它为什么没在其他诗人那里发生,而偏偏发生在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身上的独特点。这就涉及“纯诗”发生的直接原因,即三诗人面临的艺术与生命氛围问题。作为大学生,他们都在日本留学或生活数年,这种知识结构特质与远离家国的“流浪”遭遇聚合,使他们既敏感于个人的愁苦,同时“近水楼台”,也容易直接深切地领悟象征主义的妙处,从审美趣味和思想感情层面与之共鸣。因为当时的日本诗歌界象征主义气氛浓郁,创造社后期三诗人当时就身处“腐水朽城”的异国情调之中,便于和那种氛围亲近。穆木天是没落地主的儿子,1920年又遭逢父亲去世,家境愈加凌乱,而久居异国他乡的弱国子民心理上自然“阳气变成忧郁”,以至于1923年东京大地震时面对“只剩下一片灰尘了。残垣破瓦,触目凄凄”的景象,却“反觉得那是千载不遇的美景”②穆木天:《我的诗歌创作之回顾》,《现代》第4卷第4期,1934年2月。,从中不难窥见诗人心理颓废的深度。冯乃超在日本生活了24年之久,“因1923年9月东京附近发生的关东大地震,冯家破产,由于这个原因,冯乃超对理工科失去了兴趣,开始热爱文学”,“喜欢读象征派、高蹈派的诗”③岩佐昌暲:《浅说“苍白”——冯乃超诗中日本象征诗歌的影响》,《文学前沿》2002年第1期。,他和知音穆木天谈到:“很想作表现败墟的诗歌——那是异同的熏香,同时又是自我的反映——要给中国人启示无限的世界。腐水、废船,我们爱它,看不见的死了的先年,我们要化成了活的过去。”①穆木天:《谭诗》,《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1926年3月。王独清的没落官僚家庭出身,加上李义山、温庭筠等人的香艳诗偏好,使之虽然后来从日本转去法国留学,但在日本的经历和体验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心理与审美结构,落寞孤独,诗中充满幻灭颓废情调,他说“我过去的倾向是经过浪漫谛克而转向狄卡丹(Decadent——颓废的中文音译)的,不消说我过去的生活多是浸在了浪漫与颓废的氛围里面”②王独清:《创造社,我和它的始终与它底总帐》,《展开》第1卷第3期,1930年12月。。而“处于动荡生活之中的留日留法学生,由于对中国的封建传统与西方的资本主义抱有‘双重的失望’,他们对现代主义一般都比较容易接受”③陈思和:《中国文学发展中的现代主义》,《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172页。。这些因素就决定了他们能够直接地通过日本或者通过日本的中介,吸收象征主义艺术的营养,创造最富象征主义乃至“纯诗”神韵的作品。这种象征主义的艺术氛围,是推动他们进行“纯诗”提倡和创作的直接动力。
三是文学内在嬗变规律制约的结果。这种制约是从正向承继和反向超越两个维度上展开的。“纯诗”在中国出现可以说是新文学传统的推动所玉成,讨论这个话题必须正视象征主义运动和象征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概括地说,象征主义是承接了浪漫主义的余绪,又开启了现代主义的先河,它最初萌动于法国19世纪中期,鼻祖为波特莱尔,在他身边聚集了兰波、魏尔仑、马拉美等几员主将。时至20世纪初,象征主义逐渐扩展为全球性的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其重要的特征是往往以隐秘暗示等表现技巧,传达内心郁闷的愁思。在开放、“拿来”的五四时期,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然主义等哲学与文学思潮一起被援引到国内;并在和东方文化碰撞、融汇之后,在中国逐渐生根发芽。一些新诗创作的先觉者都曾译介过它,早在1918年5月,刘半农就在《新青年》上翻译德维的《我行雪中》等象征诗;1919年茅盾不仅介绍斯特林堡、沁孤、梅特林克等表象主义剧作家,还在1920年的《小说月报》11卷12期上发表《我们现在可以提倡表象主义吗》,主张“不得不先提倡”表象主义;而《少年中国》有更集中的介绍,田汉发表于《少年中国》三卷四、五期的《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百年祭》,直接称誉“波陀雷尔”为“法国十九世纪罗曼主义的殿将、象征主义的先锋”。刘延陵、闻天二人又于1922年、1924年分别出版《法国象征主义与自由诗》《波特莱尔》,更系统深入地评价象征主义,除波氏之外,梅特林克、马拉美、耶麦、魏尔仑、凡尔哈尔等皆被纳入译介视野。在对象征主义的整体认同中,一些诗人开始实验移植象征诗。如胡适的《鸽子》就借“夷犹如意”飞翔的鸽子,暗喻对无拘无束那种自由个性的渴盼,虽笨拙粗糙但已初具象征诗雏形。至鲁迅的六首白话诗,已有道地的象征意识,朦胧老练,《桃花》像是写“杨妃红”的生气桃花,实则曲比听不得批评的自视清高的知识分子,深沉婉转。周作人的《小河》乃“新诗中的一首杰作”,被石堰堵截挣扎乱转的小河描述,隐含着自由遭到扼杀的痛苦和对人性伸展的呼唤,情思与表现均多得波特莱尔韵味。发难期的创作实践、理论输入,表明象征主义诗歌始在中国起步,现代化、多元化情绪与表达已成为诗歌的趋向和潮流,象征诗派在中国的出现是水到渠成的。
“纯诗”的三位代表诗人在传统与现代传统的荫庇下生长,自然受惠于前人的开拓,但因留学之故更多得益于日本象征主义文学氛围的熏染,他们提倡“纯诗”也可谓源自辰野隆教授的“激发”。据考证,“20世纪前10年,象征诗成为日本诗坛的主流”④吕元明:《日本文学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在鼻祖蒲原有明的统领下,大手拓次、荻原朔太郎、三木露风、北原白秋、川路柳虹等名家云集,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三诗人在日本求学期间创作界象征主义氛围浓郁,如冯乃超1924年进入京都帝大写诗,就“喜欢读象征派、高蹈派的诗”⑤岩佐昌暲:《浅说“苍白”——冯乃超诗中日本象征诗歌的影响》,《文学前沿》2002年第1期。。在理论上著名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执教于京都帝国大学和京都三高,其广义的象征主义学说对喜欢文学的学生诱惑力很大;尤其是穆木天在京都帝国大学读书时,文学部法语法国文学科的三位教授辰野隆、铃木信太郎、山田珠树,分别讲授“19世纪法兰西文学思潮”“象征诗派研究”“现代小说与心理解剖”等均倾向于现代主义文学的课程,所以1923年“穆木天从京都来到这里之后,会感到完全进入了‘象征主义的世界’”①参见王中忱:《日本中介与穆木天的早期文学观杂考》,《励耘学刊》2006年第1期。,恰逢其时。其中辰野隆教授当时是穆木天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事过多年之后穆木天提到“在学校读书时,辰野隆先生以法文学之本质为拉丁精神与高尔精神之不调和见教。当时认为是无上的新的启发……文学研究的方法起了革命,而势所必然地要影响到我这个学徒身上来了”②穆木天:《法国文学史》“卷头语”,世界书局1933年版。。这种“启发”“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大的引导还在于‘纯粹诗歌’理论的建构”③刘静:《穆木天“纯粹诗歌”辨析》,《中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3期。,探讨纯诗的《谭诗》的写作。写作该文稍早一些时候,无法确认穆木天是否接触过伯雷蒙有关“纯诗”理论的资料,但其间正值撰写毕业论文《阿尔贝·萨曼的诗歌》,“法国文坛的最新消息,肯定也会成为他们师生间的话题”;1926年秋天辰野隆写了介绍法国“纯诗”讨论的文章《关于“纯粹诗歌”的论争》,师生二人之间关于“纯粹诗歌”问题肯定有很多交流和沟通。“了解了这些情况,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穆木天在写《谭诗》的时候,会把注有法文Lapoesiepure的‘纯粹诗歌’概念,那么自然地拿来作为评判诗歌的标准和讨论新诗发展的前提”④参见王中忱:《日本中介与穆木天的早期文学观杂考》,《励耘学刊》2006年第1期。,不然无法想象穆木天认同的纯诗的本质在于“交响”和辰野隆“纯诗”同内心的愉悦观点的基本一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辰野隆激发了穆木天对纯诗问题的探讨,并由此推出了一片“纯诗”理论的场域。
“纯诗”理论和创作的出现也是对诗坛弊端的一种定向反动。20世纪20年代中期,新诗陷入了停滞困窘的危机境地之中。现实主义诗歌大多粗糙浅白,浪漫主义诗歌则平淡显露,疲软得很,对于那种在革命低潮期滋生出的忧郁苦闷情愫,自由诗开始泛出传达的无力性;而且其形式自身也很快就出现了背离诗歌本质的散文化痼疾,结构松弛。对当时诗坛的态势,可用“单调二字涵括,一切作品都像个玻璃球,晶莹透明得太厉害了,没有一点朦胧。因此也似乎缺少了一种余香和回味”⑤周作人:《〈扬鞭集〉序》,《语丝》第82期,1926年5月。,文学的维度被严重削弱。事实上,危机肇源与新诗的拓荒者胡适有关,他在把诗神从一个死胡同领出来的同时,又领进了另外一个死胡同。他的“要须做诗如做文”的理论主张,只注重语言的精确,而不注意隐秘的模糊性,能够打破旧诗格律的镣铐;但更容易把诗引向“非诗”的歧途,因此说新诗陷入困境实乃必然。面对诗坛的“无治状态”,倡导“纯诗”者十分不满而且试图矫正,在《再谭诗》中,王独清表示要“治理文坛审美薄弱和创作粗糙的弊病”⑥王独清:《再谭诗》,《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1926年3月。;在《谭诗》中穆木天更直截了当地申明,“中国的新诗的运动,我以为胡适是最大的罪人。胡适说:作诗须得如作文。那是他的大错……几乎使新诗陷入无法自容的尴尬境地”,进而批评“现在作诗,非常粗糙,这也正是我痛恨的一点”⑦穆木天:《谭诗》,《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1926年3月。。正是出于拯救诗坛于危机的意愿,敦促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三位诗人,和徐志摩、闻一多等人以新格律诗营构诗坛秩序同步,从另一个向度上开始实施以暗示能的强调、扩大诗歌思考的空间,大胆提倡“纯诗”,使新诗步入了现代化的进程。
二、现代诗意中的“物哀”倾向
现代自然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19世纪以前的传统文学,大体以再现客观世界为主,轻心态,重世态,群体文明那种诗意结构曾经显赫一时;但是,当个体之人渐次脱离群体,一点一点地走下历史“祭台”的瞬间,它便开始面临新的抉择。象征主义的一大功绩,就是完成了诗意从“古典”向“现代”的艰难转换。它把诗歌的观照点由外部现实与客体拉回到主体心灵,把普通人的境遇纳为现代价值的发祥地,捕捉人类个体转瞬即逝的心灵意向与感应。它的直接后果是恶丑原则替代美善原则,“苦味儿”上升为艺术最基本的感觉。诗人波特莱尔及其代表作《恶之花》可视为它的典范。象征主义这种观念传到日本,引发出许多类似的表述。诗人北原白秋在1909年出版的诗集《邪教》小序中讲到,所谓象征,即在一种不可名状的情绪震颤中,去寻觅心灵的欷歔,去憧憬缥缈的音乐的欢愉,去表现自我思想的悲哀。穆木天的指导教师辰野隆这样谈论“纯诗”:“凡是诗歌里都存在着某种超越理性的,不能用言语来说明的东西。把这个称为神秘也好,称为秘密的魅力也好,总之,它是诉之于人的内心的潜藏着的愉悦。”①辰野隆:《关于纯粹诗歌的论争》,《法兰西文学》(下),东京白水社1946年版,第323—324页。译文参见刘静:《20世纪初期中国诗坛的日本因素》,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不论是心灵的欷歔、缥缈的音乐的欢愉,还是内心潜藏的愉悦,都顺应了现代诗意那种“向内转”的主体美学原则。
受西方“纯诗”主张、辰野隆等具东方色彩理论阐释的启悟,穆木天、王独清和冯乃超这三位诗人也确立了比较自足的诗歌观念。他们认为,写诗越能向人的灵魂深处掘进,就越能带来思想智慧的提高与丰富。为对抗诗坛当时的“散文化”流弊,他们“要求是‘纯粹诗歌’”“是诗与散文的纯粹的分界”②穆木天:《谭诗》,《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1926年3月。,从生命哲学和精神现象学出发,提倡发掘“潜在的能”“人的内生命的深秘”,以规避散文的“外生命”表现,甚至不无偏激地说“诗的世界是潜在意识的世界”③穆木天:《谭诗》,《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1926年3月。,已浸染着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的排斥理性色彩。在给“纯诗”开列的公式“(情+力)+(音+色)=诗”④王独清:《再谭诗》,《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1926年3月。里,也仍“情”字当先。他们在创作中虽也观照客观景致与直觉现象,但只是以之作为艺术的起点,目的在于表现超越外在现实的内在体验,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唯心的痕迹,却也契合着诗为主观艺术的本质特质。这种贵族性的诗歌观念,抒情主体对客体的处理路径,形成了“纯诗”内向聚敛式的感知世界的方式,使它不再在现实与时代区域寻觅诗意,而聚焦于心理体验的内宇宙真实,承担记录个人情绪与灵感的功能,成为人在精神领域的独白与自传。这种对个体生存之不完善与真实性的确认建构的诗境,由于已涉入下意识与潜意识领域,自然给诗带来许多模糊朦胧以至神秘的因素。
也就是说,“纯诗”大体属于一种情态文本写作,属于经验性的客观具象的符号组织,它不满足于对象的表象世界展现,而总是力求在双向同化、主客融汇中超越之,以传递私有化的个人情绪,进而实现诗意的现代性转换,与以前诗歌历史上的“精神化石”划开审美界限。因为后者基本上隶属于古典的群体诗意,龚自珍的那种“一箫一剑平生意”中箫声、剑气的心态,和周作人的《小河》那种意蕴所指,终究还都停留于类文明的诗意闪烁层面,不论是崇高还是肃穆的诗意形态,其中均沉淀着众多深层的群体意向;而“纯诗”传达的却都是不可重复、极其个性化的现代诗意,表现的多是跃动在时代大潮之外的诗人心灵潮汐的回味与咀嚼;充斥视野的是现实与理想错位、脱节后的悲剧性感觉:叹前程之渺茫、哀人生之多艰,厌世绝望,孤寂疲惫,伤感抑郁的情调扩张为占绝对优势的主旋律,并且因为异域体验和艺术观念的耳濡目染,“纯诗”的现代诗意中充满许多“物哀”的因子。
何为“物哀”?我们无力也无意在此概念及历史上纠缠,搞清其目的只是为说明问题起见。“‘物哀’是将现实中最受感动、最让人动心的东西(物)记录下来”,“写触‘物’的感动之心、感动之情,写感情世界”。⑤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页。按照日本人的理解,从物哀的性质可将之分为感动、调和、优美、情趣和哀感五类,其中最突出的是哀感。⑥久松潜一:《日本文学评论史》,至文堂1968年版,第87页。“日本人的敏感纤细,使其在审美意识中觉得越是细小、短暂的事物越具有纯粹的美感”⑦罗振亚:《日本俳句与中国“小诗”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这种“物哀”传统与支配几千年中国古典诗歌的悲凉基调不无相通之处,它决定了日本诗歌好以空灵淡雅、清幽闲寂之物象,咏叹生命无常和时光易逝,所以折射到日本人的心里,具有“物哀”之心,能够分寸感很强地以质感的意象传达情感,才是好诗人。所以“象征主义登陆日本后即与‘物哀’传统相融合,带上了浓厚的唯美和颓废的色彩”⑧刘静:《中国现代诗坛的日本因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2页。,遍查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三诗人诗歌文本中的灵魂情思“黑洞”,悲观灰颓,和西方、日本象征主义诗歌的世纪末姿态具有惊人的异质同构性。
作为都市浪子,置身异化情境中设身处地的感受与体验,使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三诗人不自觉间纷纷感染上了都市忧郁症,将梦、丑、恶等颓废事物视为生命、生活与本色和原态。于是,命运无常、人生如梦、生活幽暗等情调便大面积地集聚诗人笔端,诗美也因之发生了变异。据日本学者岩佐昌暲考证,冯乃超“是一位频繁使用‘苍白’一词的诗人”,其诗集“《红纱灯》由43首组成,其中14首使用了‘苍白’一词”①岩佐昌暲:《浅说“苍白”——冯乃超诗中日本象征诗歌的影响》,《文学前沿》2002年第1期。。如果认同新批评理论家弗莱的观点,即一个语象在同一作品中再三重复,或在一个诗人前后的作品再三重复,就渐渐积累其象征意义的分量,成为积淀着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原型象征;抛却反复出现的落叶、坟墓、夕阳、寒风、残梦、乱影、悲哀等残缺丑痛、阴滞冷森的意象不谈,仅仅频繁复现“苍白”恐怕绝非仅仅是一种嗜好,其“用意”虽然研究者语焉不详,却至少指涉着冯乃超诗歌充满病态因子、缺乏生机、黯淡灰颓的基调判断。其实,整本《红纱灯》吟咏的就是“颓废、阴影、梦幻、仙乡”,神秘而缥缈、痛楚又感伤。“苍黄的古月地平线上泣/氤氲的夜色露湿/夕阳的面色苍白了/沉重的野烟/沉重的忧郁”(《苍黄的古月》),负荷着黯淡凄冷的情感的词语排列,已氤氲着低抑的情调。夕阳逐渐西沉,面容憔悴、苍黄瘦弱的月亮哭泣于地平线上,满含如泪的露色,夜色湿闷沉重,好像田野的暮烟也升不起来。面对“古月”,谁又能不万点忧思,一腔愁绪,谁又感受不到严冬的到来,黑暗的逼压?可见阴冷萧索的景物观照中,都蛰伏着消沉忧郁的“灵魂的日暮”情怀!“一朵枯凋无力的蔷薇/深深地吻着过去的残梦”(冯乃超《现在》)。沉入残梦之中无力自救而只能沉思怀想之花朵,完全可视为一个弱者在美好的理想幻灭之后悲痛绝望情绪的物象外化,美的凋零正如理想与爱的凋零,始终与甜美、温馨相连的爱情书写激起的再也不是愉悦与美感,仔细读后却陡增惆怅与失落的心绪。穆木天的诗集名字《旅心》就极其耐人寻味,他那身受式的民族忧患本身即使其“隐伏着无限的血泪”。他更善于从细雨、微光、泪滴、草舍等浪漫意象中捕捉感伤与孤独的影子。《旅心·献诗》里浅淡的语流里包裹的轻愁,如烟似梦,说也说不清楚;《弦上》灰暗的冷色调凝结着惆怅孤寂的情绪,“忘尽了罢青春的徘徊/忘尽了罢猩红的悲哀/啊无限的追忆啊/那都是梦里的尘埃”,已有人生似梦的绝望韵味;即便是被视为爱国绝唱的《心响》,在“几时能看见九曲黄河/盘旋无际滚滚白浪”,“几时能含住你的乳房/几时我能拥在你的怀中/啊、禹城,我的母亲/啊、神州,我的故乡”的呼唤声里,仍然渗透着乡思之愁。待到被生存折磨、心理失衡的落魄情调型诗人王独清,文本中更充斥着悲哀的浪人愁思和对都市的陶醉享乐。他经常在记忆中美化已经逝去的一切,挽歌《吊罗马》看似在凭吊意大利的荒凉古城,实则在怀恋衰微颓败的故乡,罗马再兴的最后招魂,更像为他失去了“功勋”“荣光”和“兴盛”的长安招魂;现代沉落与逝去荣光的比对中,不乏呼唤新生的痛切爱国情愫,尤见涕泪交迸的悲痛与忧患;《死前的希望》竟把“荒凉的坟场”当成“休息的卧房”,愈见生之艰难和痛苦。
判定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的创作有“物哀”之气,也意味着它从取境到内蕴均偏于“纤细”,看不到多少传统的审美“风骨”。其实,日本文化的熏染,使这三位诗人的“哀感”都很十足,但在以“物”传达“哀”之情感的日本趣味方面却有所偏离,没学到位。对其评价时必须结合具体的时代与文化语境。正如当年的波特莱尔身心深陷于丑恶的境地,却始终苦恋着美与善、外表的冷漠下隐伏着滚烫的热情一样;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三诗人个人的不幸际遇,因为和羁旅他乡的民族苦难的际遇同构共振,所以其低抑的感喟里经常会闪烁着民族与时代的一丝苦闷的光影,颓废晦暗的诗思“黑洞”中,不时燃起几缕情爱美、家园感、异国情调辐射的“微光”。从这个向度上说,把他们称为“颓废诗人”,不如把他们称为“颓废时代的诗人”更为恰当。而且,若把现实与诗的关系转向心灵与诗的关系,从诗歌本体论的视角看,更该承认三诗人那种“人类灵魂真实探险者”的身份,他们的诗弥补、恢复了常被人忽视而现代人心灵中却一直存在的消极面,可以说远离了现实世界,也可以说是更深远的心灵拓展。
三、自足的艺术本体归趋
穆木天、冯乃超和王独清似乎更多诗人的直觉、敏感与细腻,他们“纯诗”探索的实绩主要是在一片迷蒙幽微艺术世界的营构上。说到艺术,东西方的“纯诗”理论具有高度的相似性,瓦雷里最初强调诗的自主性,倡导没有任何非诗歌杂质的纯粹写作。与之相应,辰野隆以为“所谓‘纯粹诗歌’,一言以蔽之,就是主张‘诗是为诗而存在的,理性非诗’”,“‘纯粹’不是‘自然’”,“纯粹诗应该是极度地精雕细琢的东西,因此它意味着是跟自然相对立的艺术领域里彻底地施加人工修饰的诗歌。我认为,大凡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东西无论如何不能说是纯粹的”。①辰野隆:《关于纯粹诗歌的论争》,《法兰西文学》(下),东京白水社1946年版,第323—324页。译文参见刘静:《20世纪初期中国诗坛的日本因素》,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东西方的影响和参悟在穆木天从形式“律动”、音乐性、暗示性、思维术等角度论述“纯粹诗歌”的《谭诗》中均有回响,他和同样重视诗歌本体的王独清、冯乃超一道,不让诗歌成为情感自然流淌的“跑马场”,而是突出“做”的环节,以艺术形式自足性的高扬,和充满暗示力的朦胧美感,雕琢文本,打磨技术,独辟路径,并因此奠定了在诗坛的地位。
一是寻求暗示效应,创造以象征为核心的朦胧艺术美。当我们面对“纯诗”的情思建筑物时,实则是面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心灵与文化,或者说它们都充满着暗示氛围与象征意蕴。即便是其中一些个人化的意象,也累积着深厚的集体无意识源。当年波特莱尔认为诗是带启发性的巫术,魏尔仑说好的诗应如面纱之后的美丽眼睛,马拉美在批评巴那斯派时更干脆地讲不能直接称呼事物名称,否则就丧失了诗歌四分之三的快感。即象征主义在艺术上注重隐喻暗示,以造成诗歌的玄妙神秘。受其影响和启迪,“纯诗”者们直接挑明“诗是要暗示的,诗是最忌说明的。说明是散文的世界里的东西”,“诗不是像化学的H2+O=H2O那样的明白的,诗越不明白越好”,“诗是要有大的暗示能”②穆木天:《谭诗》,《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1926年3月。;“诗,要作者不要为作而作,需要为感觉而作”③王独清:《再谭诗》,《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1926年3月。。种种非理性的直觉陈述,实际上都是要维护诗歌的含蓄蕴藉,发挥诗歌飘忽性、多义性、暗示性的隐喻功能。这种诗歌观念的统摄,决定“纯诗”探索者从两方面创造具备暗示效应的结构。
一方面“纯诗”的暗示效应,来源于诗人深刻敏锐的直觉力。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受暗示理论的启悟,将波特莱尔由神秘主义哲学家史威登堡的“对应论”精髓翻版过来的“契合观”为圭臬,以一个个的意象符号,象征、暗示和外物相应的感觉情绪和思想认识,它在一瞬间就快速把握住万物与性灵间不无神秘的固有联系点,从而抓住、表现物的本质属性过程,就成了给予诗歌暗示力之过程。因为直觉中的诗人可以“置身于对象的内部,以便与对象中那个独一无二、不可言传的东西契合”④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论》,《西方现代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实现自然与心灵的全息。所以一首诗在“纯诗”里都是情思的暗示场,穿过意象便会通往诗人的心灵。如在穆木天的《雨后的井之头》黯淡的雨后水乡图里,“浮云”澹淡,“薄雾”轻覆,水鸟“哀鸣”,寒鸦“欢唱”,小花“梦想着远国”,芦苇以哀琴在弹奏“虚伪的歌”,还有枯舟和腐草。诗虽客观得无情思的踪迹,可是随着转换的视境,你会发现荒凉苦恼的思索随着淡淡的愁绪,已慢慢攀上心头,欢乐与歌声“虚伪”,苦闷哀啼才属真实。自然之灰暗和“我”之怅惘泾渭难辨。再如冯乃超的《默》这样写道:
轻烟笼罩着池塘底安眠
冬天来到疲乏的草根头
沉默枯朽着梦里的睡莲
静悄悄地杀着苍白的微笑.
阳光隐在轻盈的树梢
不照树阴影里的哀愁
全诗观照冬天里枯枝、轻烟、乌鸦等颓败萧索的景观,但它诸多的意象敛聚背后,实则凸显着色彩感所酿成的“灵魂的日暮”的精神旨向。走笔虽然轻盈,沉重悲观的情绪却力透纸背。这类诗里,山川草物、花鸟虫鱼再不是异己之死物,而成了人们精神信息的相应载体;它们组构的诗自然极具暗示能,充满言外之旨,又难以破译和捕捉,如水中赏月,似雾里观花,若即若离,似又非似,深得朦胧之美妙。
另一方面,“纯诗”的暗示有赖于象征意识的渗入。在西方的象征主义者看来,在现代与传统的冲突、个体文明逐渐取代群体文明的过程中,原有的价值体系崩溃,而新的意义还没有确立,意义的空场敦促万物又成了需要诠释的象征符号,或者说外在的世界就是一片“象征的森林”。步其后尘,中国的“纯诗”人也把创作当作象征行为,甚至断言世界上若没有象征也就没有艺术;并且在结合传统的“兴”之理论基础上,以自然对应物象征传达幽远的心灵,用“此岸”象征“彼岸”世界,实现了情思与万物的对流,赋予物象以象征意味的同时,暗示性被推向了极致。如穆木天那首《薄光》就借原野里夕暮荒凉淡黄的薄光,玄想自然、人生与宇宙,薄光已从纯粹的自然之光上升为彼岸世界之象征,薄光究竟象征着什么?是传统思想?是黑暗的势力?是忧伤彷徨的情绪?都像又都不像,对之好像能够说清又好像永远说不清。它仿佛消解了时空、自然与社会的界限,成了带有批判色彩的精神所在,也寄居着诗人的忧伤凄清情怀。再看王独清的《玫瑰花》:“在这水绿色的灯下,我痴看着她,/我痴看着她淡黄的头发,/她深蓝的眼睛,她苍白的面颊,/啊,这迷人的水绿色的灯下!//她两手掬了些谢了的玫瑰花瓣,/俯下头儿去深深地亲了几遍……啊,玫瑰花!我暗暗地表示谢忱:/你把她的粉泽送近了我的颤唇,/你使我们俩底呼吸合葬在你芳魂之中,/你使我们俩在你底香骸内接吻!”诗借花象征性地表达对异国女郎的痴爱深情。深蓝的眼睛、淡黄的头发、苍白的面颊组构的斑斓的“油画”,活化出女郎的美丽后,诗人“愿永远这样坐在她底身旁”,花香不散爱永不老。在这些诗里,象征已从作为局部琐屑的手段,晋升为本体性的内容,使意象既是自身,又有自身外的许多含义,功能的多义性与多层性,规定意象及结构的二重性,在有限的空间里充满无穷的指归。它既诉诸读者的感受力;也能给人抽象感悟的鉴赏愉悦。“纯诗”就幽微去明显、重暗示轻说明的“象征的森林”构筑,驱散了草创期新诗经常把话说尽的通病。
二是强调音乐性与画意美整合,显示出一种形式自觉。现代主义诗歌的重要趋向之一是文本形式有了明显的自足性,象征主义诗人大都发过这方面的感慨,魏尔仑说音乐是万般事物中最首要的,马拉美要创造音乐般的“纯诗”,兰波认为诗人应是“通灵者”。日本诗人北原白秋也昌明“我的象征诗旨在追求情绪上的和谐和捕捉感觉印象,尤其追求富有音乐感的象征”①陈岩:《日本历代著名诗人评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66页。。显然,他们已把形式因素之一音乐提高到空前的位置认识,希望音乐能够脱离现实靠自身组构作品。“纯诗”探索者虽未达到形式至上的程度,但也声称“思想与表达思想的音声不一致是绝对的失败”②穆木天:《谭诗》,《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1926年3月。,努力创作“纯粹诗歌”。他们一定程度上排斥语言和文字,企图完全凭借艺术品类之间的交互融汇,和色、音、形的系统调动,使诗最终向绘画与音乐靠拢,在画意美、音乐性中收回自身的价值。
在这个问题上穆木天、王独清和冯乃超都比较规范自觉。针对诗坛形式粗糙的散漫无序状态,穆木天的创作总能如朱自清所说的“托情于幽微远渺之中”。他主张诗是“一个先验状态的持续的律动”,统一性与持续性统一;“诗要兼造形与音乐之美。在人们神经上振动的可见而不可见可感而不可感的旋律的波,浓雾中若听见若听不见的远远的声音,夕暮里若飘动若飘不动的淡淡光线,若讲出若讲不出的情肠才是诗的世界”;用物的波动状态表现心的波动状态。③穆木天:《谭诗》,《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1926年3月。他的不少诗实现了这种主张,以暮霭轻烟、微风雨丝、远山幽径等迷蒙渺远的意象律动,与惆怅轻思、朦胧哀怨的心之律动扣合。别说其《雨丝》中,绵绵不断、如雾如烟的雨丝飘落,形象而到位地外化着诗人剪不断的凄清迷惘的思绪,《苍白的钟声》就更为别致,不妨引述一段:
苍白的 钟声 衰腐的 朦胧
疏散 玲珑 荒凉的
谷中
——衰草 千重 万重——
听 永远的 荒唐的 古钟
听 千声 万声
……
听 残朽的 古钟 在灰黄的 谷中
入 无限之 茫茫 散淡 玲珑
枯叶 衰草 随 呆呆之 北风
听 千声 万声——朦胧——
音乐旋律构成了诗之自足,仿佛词语的意义在这里已不重要,钟声的形态、音响更加引人注目。深秋日暮时旷野的钟声印象,因为语言的拟神态表演,点化出一种缥缈孤寂的风韵。在感觉的交错挪移中,听觉已转化为视觉,阵阵连续而间隔的排列的句式,就像随着时空律动的波所形成的那种似断似续的钟声音波外化,空白则暗示着钟声节奏,固执悠长、沉稳疲惫的钟声乃单调倦怠情思的流动。
和长于音乐氛围营造的穆木天相比,王独清更善设色。他倾心魏尔仑说的音乐美,更神往于兰波的“色的听觉”。他说“这种‘色’、‘音’交错的感觉,在心理学上就叫作‘色的听觉’,在艺术方面即所谓‘音画’”,“那种在沉默中秋动律的手腕也可以使他底作品成为‘纯粹诗歌’”①王独清:《再谭诗》,《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1926年3月。,成为走向“音画”效果的重要途径。这种“音画”艺术乃王独清形式美观念的核心,它指的即是感觉交错的通感效应,《我从Cafe中出来》则是典范的文本:
我从Cafe中出来
身上添了
中酒的
疲乏
我不知道
向那一处走去,才是我底
暂时的住家……
啊,冷静的街衢
黄昏,细雨!
诗歌实现了律动、音色和情调的本质的统一。从文本的外观看,就是醉汉那种摇晃身心和行程轨迹的复现,语言的无伦次与断续,好似现代人醉后流浪感思绪碎片的载体。“冷静的街衢,黄昏,细雨!”黯淡背景已使色彩失去表面与皮相,贴近内在化的心灵,浸渍着一定的抑郁迷茫情调。上下两段有规律、有意识的复沓回环,强化音乐美的同时又拓长了情思氛围,它和《能唱》等诗运用的叠字叠句一样,均符合其叠字叠句是“表达感情激动时心脏振动的艺术”②王独清:《再谭诗》,《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1926年3月。逻辑。
和穆木天、王独清不同,冯乃超兼得绘画与音乐之美,集丰富的色彩和铿锵的音节于一身。这位“轻纱诗人”,张扬绘画经历之所长,总能让多种感觉联通,焕发出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如《红纱灯》就朗朗上口,韵律谐和,达到了色彩也是思想的境地。“森严的黑暗的深奥的深奥的殿堂之中央/红纱的古灯微明地玲珑地点在午夜之心//苦恼的沉默呻吟在夜影的睡眠之中/我听得鬼魅魑魉的跫声舞蹈在半空……我看见在森严的黑暗的殿堂的神龛/明灭地惝恍地一盏红纱的灯光颤动”。蛋白色的月亮、漆黑的殿堂、黑衣的尼姑、如尸僵的河流等斑驳色彩意象织就的凄凉阴森画面中,一线红而黄的灯火正在微弱燃烧着,冲动、响亮的金属一般的质感光调,似乎能够令人忘却身后死寂的黑暗,“红纱灯”不正是诗人苦闷而自赏心绪的象征吗?它无助而坚强,孤闷又彷徨,明晰却模糊。
总之,日本观念对初期中国“纯诗”的塑造利弊互见。它对形式自觉和暗示效应的高扬,是诗歌本体意识的自觉强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诗坛当时无治困窘的状态,带来了“新的颤栗”。但贵族诗歌观念的牵拉,使“纯诗”有时把晦涩当作美学原则,决定了受众必定有限。原来,“纯诗”留给未来诗坛的不止于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