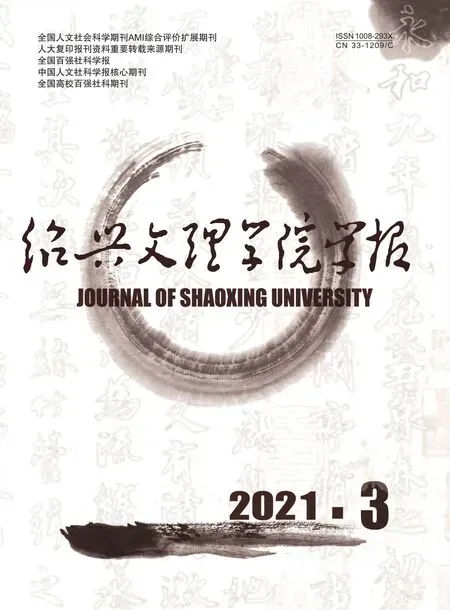论陆游宦游巴蜀间悲抑情怀之异变
2021-02-01付兴林
付兴林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陆游曾于乾道六年(1070)至淳熙四年(1077)间西行宦游巴蜀,先后在夔州、南郑、成都等地供职,度过了对他一生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八年生活。无论是出判夔州,还是从戎南郑,抑或是趋走成都,陆游均留下许多飞动豪迈、慷慨俊爽的诗歌,表达了他对当地、此期生活的感受、赞赏。如作于夔州的《初夏新晴》:“曲径泥新晚照明,小轩才受一床横。翩翩乳燕穿帘影,蔌蔌新篁解箨声。药物屏除知病减,梦魂安稳觉心平。深居不恨无来客,时有山禽自赞名。”[1]191作于南郑的《南郑马上作》:“南郑春残信马行,通都气象尚峥嵘。迷空游絮凭陵去,曳线飞鸢跋扈鸣。落日断云唐阙废,淡烟芳草汉坛平。犹嫌未豁胸中气,目断南山天际横。”[1]234作于成都的《海棠》:“谁道名花独故宫,东城盛丽足争雄。横陈锦障栏杆外,尽吸红云酒盏中。贪看不辞持夜烛,倚狂直欲擅春风。拾遗旧咏悲零落,瘦损腰围拟未工。”[1]295是故多年后,陆游在回忆这段入川驻陕生活时,还满怀激情地写道:“忆从南郑入成都,气俗豪华海内无。故苑燕开车载酒,名姬舞罢斗量珠。浣花江路青螭舫,槎柳毬场白雪驹。”[1]1864-1865梁启超先生在《读陆放翁集》中对陆游当年从戎南郑的壮举和境界更是高度称赞:“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2]4然则,当对陆游这几年留存和后来回忆这几年生活的诗歌进行全面梳理、咀味时,我们发现,陆游当年的处境、心境并不像他后来深情回忆巴蜀生活的诗歌所呈现的那般豪情万丈、激越澎湃,或可说我们简单、狭隘地相信了他所发抒的“投笔书生古来有,从军乐事世间无”[1]1318的豪言快语、片段体验。事实上,陆游这几年的宦游生活不乏忧怨色彩,且其悲抑情怀在不同时地呈现出转化异变的阶段性、差异性特点。
一、“淹泊蛮荒感慨多”——出判夔州的悲凉情怀
陆游生活在一个具有民族大义、爱国传统的家庭中,祖父辈们慷慨救国的意识和行为让他自小受到熏染,养就了一辈子抗金北伐、收复中原的血气与志向。《跋傅给事书》云:“绍兴初,某甫成童,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苦,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也。”[3]21从此,陆游的一生与爱国、抗金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其生命中最重要的职责、事业。也正因此,其所倡议、热衷、坚持的抗金北伐给其一生的科场仕宦、穷通进退带来了重大影响。《陆游年表》载:“赴礼部试,主考官置游前列,以论恢复语触秦桧,为秦桧所黜落。”[1]4617宋孝宗隆兴初年,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积极筹划北伐大业。陆游虽然于隆兴元年(1163)被任命为镇江府通判,但在整个开战过程中,他返居山阴。到第二年战争失利,张浚巡视江淮路时,陆游以通家子往谒,热情接待张浚父子及其随行人员。开禧三年(1207)陆游83岁时,曾于《跋张敬夫书后》,回忆了隆兴二年(1164)三、四月间,张浚视察江淮路过镇江时他的态度与作为:“隆兴甲申,某佐郡京口,张忠献公以右丞相督军过焉。先君会稽公,尝识忠献于掾南郑时,事载高皇帝实录,以故某辱忠献顾遇甚厚。是时敬父从行,而陈应求参赞军事,冯圜仲、查元章馆于予廨中,盖无日不相从。迨今读敬父遗墨,追记在京口相与论议时,真隔世事也。”[3]9其后,张浚被黜罢都督、右相,并于当年八月病逝。乾道元年(1165)冬,陆游以《去年余佐京口遇王嘉叟从张魏公督师过焉魏公道罢相嘉叟亦出守莆阳近辱书报魏公已葬衡山感叹不已因用所遗拄颊亭诗韵奉寄》对张浚谢世深表哀悼:“河亭挈手共徘徊,万事宁非有数哉!黄阁相君三黜去,青云学士一麾来。中原故老知谁在,南岳新丘共此哀。火冷夜窗听急雪,相思时取近书开。”[1]90时过境迁,淳熙十三年(1186),陆游在《书愤》中还深情地回顾了当时豪迈激荡的场面——“楼船夜雪瓜洲渡”[1]1346。正因家谊渊深、志气相投、过从密亲,不可避免地给陆游的仕途带来了灾祸。《宋史·陆游传》载:“言者论游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免归。”[4]12058乾道二年(1166)春,已被调任隆兴府通判的陆游被弹劾落职。
退居赋闲的陆游在山阴一呆就是数年。乾道五年(1169),宋孝宗接连颁行诏令,一批主张抗金的志士陆续担任要职,南宋朝廷呈现出积极的抗战态势。这一变化给陆游带来了希望和遐想。然而,陆游的命运却并未随着抗战氛围的浓厚、备战节奏的加快而发生较大改变。史载:“出通判建康府,寻易隆兴府。……久之,通判夔州。”[4]12058令人不解的是,陆游数年的累官集资竟被无视,居然一连三任均摆脱不了通判的命运;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由抗金的第一线到后方再到僻远的大后方。对于这样逆时代、忤人心而动的安排,陆游岂能甘心、岂能不生出悲凉的感受?朱东润先生在《陆游传》中对此评论道:“还是一位通判,可是由镇江而南昌,由南昌而夔州,官职依然,路确实愈走愈远了。……从乾道二年南昌罢官到现在,前后五年了,所得的是一官万里,怎能不使他伤感?镇江是军事重镇,南昌总还是一个大地方,可是夔府呢?”[5]84
早在隆兴二年(1164),陆游在镇江通判任上,曾写过一首送朋友赴任夔路运判的《送查元章赴夔漕》:“柳色西门路,看公上马时。亦知非久别,不奈自成悲。白发刘宾客,青衫杜拾遗。分留端有待,剩赋竹枝词。”[1]73应该说,这是一首一般意义上的送别诗,其艺术性大于思想性,或者说有事不关己而不痛不痒的泛泛之感。然当数年后,自己作为当事人要赴任夔州时,一下子触动了陆游离家去国、远走僻壤、失意落难的悲凉心绪,人未启程,酸楚的诗句已倾泻于笔端。《将赴官夔府书怀》写道:
病夫喜山泽,抗志自年少。有时缘龟饥,妄出丐鹤料。亦尝侧朝绅,退懦每自笑。正如怯酒人,虽爱不敢釂。一从南昌免,五岁嗟不调。朝廷每哀矜,幕府误辟召。终然敛孤迹,万里游绝徼。民风杂莫徭,封域近无诏。凄凉黄魔宫,峭绝白帝庙。又尝闻此邦,野陋可嘲诮。通衢舞竹枝,谯门对山烧。浮生一梦耳,何者可庆吊?但愁瘿累累,把镜羞自照。[1]131
诗一开头从自己的志趣、生计、仕宦、地位、品格、失意、人缘说起,中间着重对夔州的山峭地远、政荒令废、鄙陋民风、落后方式、怪病蛮舞等作了全面概述和整体否定,从中不难体会陆游对夔州的轻蔑、鄙弃。尤其是对于心怀“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1]357“我亦思报国,梦绕古战场”[1]917志向的陆游来说,这一远离东部淮河沿线、远走穷乡僻壤之地的任命,的确有些令其难堪、无语、难以认同接受。
在逆水而上赴往夔州的路上,陆游内心的委屈、悲凉时时倾注笔端。如《黄州》:“局促常悲类楚囚,迁流还叹学齐优。江声不尽英雄恨,天意无私草木秋。万里羁愁添白发,一帆寒日过黄州。君看赤壁终陈迹,生子何须似仲谋!”[1]141忧伤中裹挟着对历史、人生的怀疑和无谓感。又如《武昌感事》:“百万呼卢事已空,新寒拥褐一衰翁。但悲鬓色成枯草,不恨生涯似断鸿。烟雨凄迷云梦泽,山川萧瑟武昌宫。西游处处堪流涕,抚枕悲歌兴未穷。”[1]142自然景色与历史遗迹相组接、正面描写与冷言反语相交替、直抒胸臆与使事用典相嵌套,把置身流离荒途中的悲抑情怀写得凄婉动宕。再如《闻猿》:“瘦尽腰围不为诗,良辰流落自成衰。也知客里偏多感,谁料天涯有许悲。汉塞角残人不寐,渭城歌罢客将离。故应未抵闻猿恨,况是巫山庙里时。”[1]176诗章一张一弛、大开大合,采用加一倍、翻转递进的手法,写出了客中更别、意外之诧、哀中添恨的强烈感受。
“道路半年行不到,江山万里看无穷。故人草诏九天上,老子题诗三峡中。笑谓毛锥可无恨,书生处处与卿同。”[1]154经过近半年的逆水行船、一步一叹,终于于乾道六年(1170)十月二十七日到达夔州,开始在陌生、荒蛮的异地他乡从事微贱、无聊的通判生涯。陆游今存夔州诗不满60首,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而诗作不多,不能不说其创作兴致委顿不高。或许正是萧索低迷的精神状态消解、抑制了其创作的动力和活力。现有的五十几首诗歌,除个别流露出一些较为平和的心态外,可以说绝大部分浸染着作者忧怨不满的情绪。有对老大职轻的感叹,如《自咏》:“朝衣无色如霜叶,将奈云安别驾何?钟鼎山林俱不遂,声名官职两无多。低昂未免闻鸡舞,慷慨犹能击筑歌。头白伴人书纸尾,只思归去弄烟波。”[1]188有对家乡故土的思念,如《初夏怀故山》:“镜湖四月正清明,白塔红桥小艇过。梅雨晴时插秧鼓,蘋风生处采菱歌。沉迷簿领吟哦少,淹泊蛮荒感慨多。谁谓吾庐六千里,眼中历历见渔蓑。”[1]190有对闷热气候的不适,如《苦热》:“万瓦鳞鳞若火龙,日车不动汗珠融。无因羽翮氛埃外,坐觉蒸炊釜甑中。石涧寒泉空有梦,冰壶团扇欲无功。余威向晚犹堪畏,浴罢斜阳满野红。”[1]192有对宦情渐冷的倾吐,如《久病灼艾后独卧有感》:“白帝城高暮柝传,幽窗搔首意萧然。江边云湿初横雁,墙下桐疏不庇蝉。计出火攻伤老病,卧闻鸢堕叹蛮烟。诸贤好试平戎策,敛退无心竞著鞭。”[1]198有对处世个性的自诉,如《假日书事》:“万里西来为一饥,坐曹日日汗沾衣。但嫌忧畏妨人乐,不恨疏慵与世违。雕槛迎阳花并发,画梁避雨燕双归。放怀始得闲中趣,下马何人又扣扉。”[1]196类似的诗歌、诗情处处可见,可以说,陆游的生活远离了兴奋、惬意、亮色。毫无疑义,他在夔州通判任上过着低沉、郁闷、苦寂的生活。
陆游于乾道五年(1169)十二月被任命为夔州通判,因身体染恙,他实际动身赴任的时间在乾道六年(1170)闰五月十八日,抵达夔州时间为十月二十七日。宋代官员三年一考。陆游的任期在经历1169年、1170年、1171年后很快便面临终结,而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即何去何从、宦路何方?这时,他首先想到了在他通判夔州前曾向他发出邀请的时任四川宣抚使的王炎。于是,他于乾道七年(1171)主动给王炎写信申请,渴望能续接前缘、效力麾下。《上王宣抚启》曰:“薄命邅回,阻并游于簪履;丹诚精确,犹结恋于门墙。敢辞蹈万死于不测之途,所冀明寸心于受知之地。伏念某禀资凡陋,承学空疏。虽肝胆轮囷,常慕昔贤之大节;乃齿牙零落,犹为天下之穷人。抚剑悲歌,临书浩叹,每感岁时之易失,不知涕泗之横流。昨属元臣,暂临西鄙,获厕油幕众贤之后,实轻玉关万里之行。奋厉欲前,驽马方思于十驾;羁穷未慭,沉舟又阅于千帆。伤弱植之易摇,悼鸿钧之难报,心危欲折,发白无余。如输劳效命之有期,愿陨首穴胸而何憾。兹从剡曲,来次夔关,虽未觇于光躔,已少纾于志愿。此盖伏遇某官,应期降命,生德自天。……念兹虚薄,奚足矜怜?然遭遇异知,业已被扆前之荐;使走趋远郡,岂不为门下之羞?倘回曩昔之恩, 俾叨分寸之进。穷子见父, 可量悲喜之怀;白骨成人,尽出生全之赐。”[6]242-243言辞恳切,感情浓醇,意欲入幕效命的态度十分坚决、强烈。也许担心“受代”在即,生计尚无着落,情急忧患之下,陆游还于乾道八年(1172)二月给时任宰相虞允文写信请求施以援手,帮助其解决为官、生计问题。《上虞丞相书》云:“若某之愚,不才无功,留落十年,乖隔万里,而终未敢自默,特曰身之穷,大丞相所宜哀耳。某行年四十有八,家世山阴,以贫悴逐禄于夔。其行也,故时交友醵缗钱以遣之,硖中俸薄,某食指以百数,距受代不数月,行李萧然,固不能归。归又无所得食。一日禄不继,则无策矣。儿年三十,女二十,婚嫁尚未敢言也。某而不为穷,则是天下无穷人。伏惟少赐动心,捐一官以禄之,使粗可活;甚则使可具装以归,又望外则使可毕一二婚嫁。不赖其才,不借其功,直以其穷可哀而已。”[7]85此信道出了陆游无颜东归、口多家贫、仕禄无望的苦衷、隐忧、焦虑,读之令人对其夔州之任愈发哀矜同情。从种种情理、迹象考证推断,陆游“后得王炎之应允召辟,于乾道八年(1172)三月赴南郑就职,从此开始了一段为期八个月的从戎岁月”[8]。由此看来,陆游走上抗金第一线、开始其引以自豪的从戎壮举,原来也还夹杂着逼不得已的生计、家累、尊严等问题,也还有这么多苦衷、辛酸混杂其间。
二、“画策虽工不见用”——从戎南郑的压抑感受
陆游于乾道八年(1172)三月中旬抵达四川宣抚使幕府所在地南郑,其官衔是左承议郎、四川宣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检法官。陆游供职王炎幕府,也算是与王炎有缘和投缘。早在乾道五年(1169),王炎出任四川宣抚使时,即物色、延揽志同道合者,因“力说张浚用兵”而罢职在家的陆游遂入其法眼。在王炎发出邀请后,陆游致《谢王宣抚启》以示谢诚:“杜门自屏,误膺物色之求;开府有严,更辱招延之指。衔恩刻骨,流涕交颐。……曾未干于诏墨,已亟远于周行。病骨支离,邅途颠沛,驽马空思于十驾,沉舟坐阅于千帆。方所向而辄穷,已甘分于永弃。侵寻末路,邂逅赏音。招之于众人鄙远之余,挈之于半世奇穷之后。……曾是疏远至孤之迹,又无瑰奇可喜之能,不知何由,坐窃殊遇。称于天下曰知己,谁或间然;虽使古人而复生,未易当此。……某敢不急装俟命,碎首为期。运笔飒飒而草军书,才虽尽矣;持被刺刺而语婢子,心亦鄙之。尚力著于微劳,庶少伸于壮志。”[6]235-236从“赏音”“殊遇”“知己”“复生”“草军书”的遣词中,不难体察陆游对王炎提携之恩的感戴,也不难了解陆游所言及的“壮志”之所指。可惜的是,因为通判夔州职任的随即发布,陆游只得顺从王命而放弃了征召。此度入幕就职,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作合的结果,是陆游与王炎早期缘分续延的结果,是时代大业、抗金雪耻号召、吸引的结果。
尽管翻山越岭、鞍马劳顿,陆游从踏上南郑地界起,即一改夔州时期游离生活之外、满纸怨叹悲凉的状态,呈现出激动、乐观、无畏、勤勉的精神世界。他对南郑的民风民俗、物产地貌充满好奇并极尽讴歌,如《金牛道中遇寒食》:“乍换春衫一倍轻,况逢寒食十分晴。莺穿驿树惺惚语,马过溪桥蹀躞行。画柱彩绳喧笑乐,艳妆丽服角鲜明。”[1]230《山南行》:“我行山南已三日,如绳大道东西出。平川沃野望不尽,麦陇青青桑郁郁。地近函秦气俗豪,秋千蹴鞠分朋曹。苜蓿连云马蹄健,杨柳夹道车声高。”[1]232他与同僚远朋广泛接触、慰问牵挂,如《简章德茂》:“殊方邂逅岂无缘,世事多乖复怅然。造物无情吾辈老,古人不死此心传。冷云黯黯朝横栈,红叶萧萧夜满船。个里约君同著句,不应输与灞桥边。”[1]244《送范西叔赴召》(其二):“欲驾征车劝小留,南山南畔更逢秋。数声过雁催行色,一盏香灯话别愁。自昔文章关治道,即今台阁要名流。百头尚作书痴在,剩乞朱黄与校雠。”[1]143他对抗金北伐、驰骋沙场充满期待,如《和高子长参议道中二首》(其一):“梁州四月晚莺啼,共忆扁舟罨画溪。莫作世间儿女态,明年万里驻安西。”[1]235《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此兴悠哉。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灞桥烟柳, 曲江池馆, 应待人来。”[9]44-45关于陆游从戎南郑时期所写的诗歌,据其庆元四年(1198)74岁所写《感旧》诗夹注所云“予山南杂诗百余篇,舟行过望云滩,坠水中,至今为恨”[1]2380可知,原本应有一百余首,只是不慎过河流失,甚为可惜。所以我们可以猜想,陆游关于蹴冰衔枚、马探敌哨的抗金杀敌的诗歌还会有不少。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陆游后来离开南郑追忆这段生活的诗歌得到印证和补充,如《夏夜大醉醒后有感》:“客游山南夜望气,颇谓王师当入秦。欲倾天上河汉水,净洗关中胡虏尘。”[1]582又如《冬夜闻雁有感》:“从军昔戍南山边,传烽直照东骆谷。军中罢战壮士闲,细草平郊恣驰逐。洮州骏马金络头,梁州毬场日打毬。玉杯传酒和鹿血,女真降虏弹箜篌。大呼拔帜思野战,杀气当年赤浮面。”[1]827-828再如《忆昔》:“忆昔西征日,飞腾尚少年。军书插鸟羽,戍垒候狼烟。渭水秋风夜,岐山晓雪天。金鞿驰叱拨,绣袂舞婵娟。”[1]1894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对陆游的这类诗特别指出:“陈与义、吕本中、汪藻、杨万里等人在这方面跟陆游显然不同。他们只表达了对国事的忧愤或希望,并没有投身在灾难里、把生命和力量都交给国家去支配的壮志和弘愿;只束手无策地叹息或者伸手求助地呼吁,并没有说自己也要来动手,要‘从戎’,要‘上马击贼’,能够‘慷慨欲忘身’或者‘敢爱不赀身’,愿意‘拥马横戈’、‘手枭逆贼清旧京’。这就是陆游的特点,他不但写爱国、忧国的情绪,并且声明救国、卫国的胆量和决心。”[10]191
与为官夔州一年多只有不到六十首诗歌相较,陆游在南郑虽只有短短八个月却写下一百多首诗,不能不说其创造活力的回升、高涨。与夔州诗歌相比较,陆游南郑诗歌呈现出明显积极健朗的格调,但这不等于说,陆游从戎南郑就只有这种饱满热烈、情惬意畅的诗歌。事实是,陆游南郑诗歌仍然是多元化的主题、多样化的色彩,这其中就不乏忧怨低沉的诗歌。大体说来,有对家乡的时时思念,如《送范西叔赴召》(其一):“天涯流落过重阳,枫叶摇丹已著霜。衰病强陪莲幕客,凄凉又送石渠郎。杜陵雁下悲徂岁,笠泽鱼肥梦故乡。”[1]242又如《自阆复还汉中次益昌》:“北首褒斜又几程,骄云未放十分晴。马经断栈危无路,风掠枯茆飒有声。季子貂裘端已弊,吴中菰菜正堪烹。朱颜渐改功名晚,击筑悲歌一再行。”[1]251有对艰难危困生活的描写,如《三泉驿舍》:“残钟断角度黄昏,小驿孤灯早闭门。霜气峭深摧草木,风声浩荡卷郊原。故山有约频回首,末路无归易断魂。短鬓萧萧不禁白,强排幽恨近清樽。”[1]254又如《江北庄取米到作饭香甚有感》:“我昔从戎清渭侧,散关嵯峨下临贼,铁衣上马蹴坚冰,有时三日不火食,山荞畬粟杂沙碜,黑黍黄穈如土色,飞霜掠面寒压指,一寸赤心惟报国。”[1]1340再如《十月暄甚人多疾十六日风雨作寒气候方少正作短歌以记之》:“昔我从行台,宿师南山旁。仲秋已戒寒,九月常陨霜。入冬即大雪,人马有仆疆。土床炽薪炭,旃毳如胡羌。果蔬悉已冰,熟视不得尝。”[1]3438还有对饿狼猛虎威胁生命及打虎猎兽的描写,如《十月二十六日夜梦行南郑道中既觉恍然揽笔作此诗时且五鼓矣》:“我时在幕府,来往无晨暮。夜宿沔阳驿,朝饭长木铺。雪中痛饮百榼空,蹴踏山林伐狐兔。躭躭北山虎,食人不知数。孤儿寡妇仇不报,日落风生行旅惧。我闻投袂起,大呼闻百步。奋戈直前虎人立,吼裂苍崖血如注。从骑三十皆秦人,面青气夺空相顾。”[1]1092又如《怀昔》:“昔者戍梁益,寝饭鞍马间。一日岁欲暮,扬鞭临散关。增冰塞渭水,飞雪暗岐山。怅望钓璜宫,英概如可还。挺剑刺乳虎,血溅貂裘殷;至今传军中,尚愧壮士颜。”[1]1957
然则,这些都还是可以克服的,是困不住、吓不倒陆游的。某种程度上说,他在这样的环境中磨练砥砺,反倒激发了其悲壮主义情怀、英雄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色彩。但是,有两个前后关联的问题却成为笼罩在陆游心头的阴翳,使其憋闷、焦虑、压抑。
陆游早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即他三十八岁时,代时任枢密院使陈康伯、知枢密院事叶义问向宋高宗上过《代乞分兵取山东札子》,提出了重视江淮、师出东部的北伐战略。其文曰:“为今之计,莫若戒敕宣抚司,以大兵及舟师十分之九固守江淮,控扼要害,为不可动之计;以十分之一,遴选骁勇有纪律之将,使之更出迭入,以奇制胜;俟徐、郓、宋、亳等处抚定之后,两淮受敌处少,然后渐次那大兵前进。如此,则进有辟国拓土之功,退无劳师失备之患,实天下至计也。”[6]96虽是代人捉笔,但实亦代表了陆游的军事主张。然则,十年之后,等到他亲临川陕前线,却陡然改变了初衷。《宋史·陆游传》载:“游为炎陈进取之策,以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当积粟练兵,有衅则攻,无则守。”[4]12058这一主张在陆游不同时期的诗文中多次被提及,如刚到南郑写下的《山南行》云:“国家四纪失中原,师出江淮未易吞;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1]232淳熙六年(1179),在《送范舍人还朝》中云:“旄头下扫在旦暮,嗟此大议知谁当?公归上前勉画策,先取关中后河北。”[1]651绍熙年间,在《书渭桥事》中,陆游郑重其事重提这一战略思想:“河渭之间,奥区沃野。……夷暴中原,积六七十年,腥闻于天,王师一出,中原豪杰必将响应,决策入关,定万事之业,兹其时矣!”[11]118对于关中的涵盖地域,虽在中国历史地理演变中有广狭概念的不同,但其“范围或泛指战国末年函谷关以西秦国故土,包括秦岭以南的汉中和巴蜀”[12]10。邱鸣皋先生也明确指出:“至于《史记·项羽本纪》所谓‘巴蜀亦关中地也’,所指范围更广,自然汉中地区也在其中了。在陆游心目中的‘关中’,至少是把汉中包括在内的。”[13]120由此可见,南郑在陆游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重要;也由此可见,陆游这一战略思想经过实践检验、考验后多么固执绵长地深植其心。尽管有学者指出“他这一套计划并不是他的独家发明。南渡以后诸多抗战派人物都看重关陕”,如唐伯可、李纲、赵鼎、张浚、虞允文、陈亮等都有过兵出关陕的此类主张[14],但“却用关中作本根”的战略思想对陆游有着否定自己曾经的主张的翻转性,“是他亲临汉中后,有见于汉中的特殊地理位置和世风民性得出的理性结论”[15]167。故其意义对于更像是文人书生的陆游来说,自有其突破、超越自我的慎重性、标志性。
南郑在南宋的国防战略上具有突出的地位。南宋抗金名将张浚曾感慨道:“汉沔形势之地,前控六路之师,后据西蜀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16]南宋真德秀在《直前奏札二》更就江淮一线的总体格局明确指出:“今之边面控连要害者,近则两淮荆襄,远则蜀之关外。然以地形考之,蜀居上流,实东南之首,荆襄其吭而两淮其左臂也。”[17]197能在如此重要的地方戍边备战,陆游自然是苦中有乐、乐在其中。如果能推动北伐大业顺利挺进,那将是陆游最大的渴望和莫大的荣光。然而北伐之事却迟迟未有大的动静,这令求战心切、建功迫切的陆游感到焦虑不安。如《太息》云:“太息重太息,吾行无终极。冰霜迫残岁,鸟兽号落日。秋砧满孤村,枯叶拥破驿。白头乡万里,堕此虎豹宅。道边新食人,膏血染草棘。平生铁石心,忘家思报国。即今冒九死,家国两无益。中原久丧乱,志士泪横臆。切勿轻书生,上马能击贼。”[1]247又如《嘉川铺得檄遂行中夜次小柏》云:“黄旗传檄趣归程,急服单装破夜行。萧萧霜飞当十月,离离斗转欲三更。酒消顿觉衣裘薄,驿近先看炬火迎。渭水函关元不远,著鞭无日涕空横。”[1]254再如《归次汉中境上》:“云栈屏山阅月游,马蹄初喜踏梁州。地连秦雍川原壮,水下荆扬日夜流。遗虏孱孱宁远略,孤臣耿耿独私忧。良时恐作他年恨,大散关头又一秋。”[1]255陆游的忧虑、焦心是不无道理的。《宋史·孝宗本纪》载:(乾道八年九月)“乙亥,诏王炎赴都堂治事。戊寅,以虞允文为少保、武安军节度使、四川宣抚使,封雍国公。己丑,赐允文家庙祭器。壬辰,允文入辞,帝谕以决策亲征,令允文治兵俟报。”[4]654王炎被撤调遣京,抗战派遭受重大打击,南郑的宣抚使司随即解散,陆游所主张的战伐谋略和他心心念念的北伐大业也随即泡汤。
南郑任上,陆游与王炎相处总体是融洽的,正如他在《怀南郑旧游》中所咏:“南山南畔昔从戎,宾主相期意气中。渴骥奔时书满壁,饿鸱鸣处箭凌风。千艘粟漕鱼关北,一点烽传骆谷东。”[1]1716王炎在任期间,曾筹措资费修葺群吏谒见、筹边治军、燕劳将士的“西偏”之“便坐”。修缮启用,“名新堂曰‘静镇’,而命其属陆某记之。某辞谢不获命,则再拜启曰”[7]221。由命笔传记可见,王炎是知人善用、能尽人才的,陆游也是恰逢机遇、尤获重用的。然则,在事关人员的任用和北伐的节奏上,陆游与王炎显然存在着一些不合拍的地方。《宋史·陆游传》载:“吴璘子挺代掌兵,颇骄恣,倾财结士,屡以过误杀人,炎莫谁何。游请以玠子拱代挺。炎曰:‘拱怯而寡谋,遇敌必败。’游曰:‘使挺遇敌,安保其不败。就令有功,愈不可驾驭。’”[4]12058在节制将帅上,也许王炎的看法、做法更可取、更稳妥,但陆游出于公心、军纪的建言未被王炎采纳,显然对陆游属不小的挫伤。所以多年后,陆游在回忆南郑生活的《三山杜门作歌》中还耿耿于怀地感叹道:“中岁远游逾剑阁,青衫误入征西幕。南沮水边秋射虎,大散关头夜闻角。画策虽工不见用,悲吒哪复从军乐。”[1]2456钱仲联先生在对该诗的“注释”中着重指出:“不见用者,恢复中原之策不为朝廷所用,王炎内调旋罢黜;非谓画策不为王炎所用也。”[1]2457朱东润先生在《陆游传》中更早地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近人以为王炎、陆游之间,意见不完全一致,王炎没有采取陆游的主张。这可能是根据《三山杜门作歌》中间两句‘画策虽工不见用,悲咤那复从军乐’。但是问题还是有的。陆游画策不为王炎所用,固然是‘不见用’,可是陆游、王炎共同的画策,不为南宋最高统治者所用,也同样是‘不见用’。从‘宾主相期意气中’这一句,我们看不出王炎和陆游中间的矛盾,而从陆游诗词中的表现,到现在这一段时期,他的军中的生活,应当说是欢乐的。”[5]118两位前辈的体认确实新颖中的、启人心智,但笔者觉得还有再行参悟的余地、必要。
从前面论述可知,起码在用人问题上,陆游带有书生气的换将易帅建议未被王炎听取采纳,按常理会在其心中留下不快、生出怨叹。此其为一。陆游在抗金北伐的节奏、愿望上,明显急切、迫切,从“汉水东流哪有极,秦关北望不胜悲。邮亭下马开孤剑,老大功名颇自期”[1]252“忆昔从戎出渭滨,壶浆马首泣遗民”[1]2352“大散关头北望秦,自期谈笑扫胡尘”[1]2926“不如意事常千万,空想先锋宿渭桥”2927等诗句所传递的信息、信念看,陆游是颇为急迫地要纾民困厄、靖扫逆胡、建立功业的。他是王炎的幕僚,他有建议权、参谋权,却没有决策权、发令权。所以,出兵的心情再急切,也只能等待王炎的决断,而王炎的决断却又受制于朝廷,他也没有最终的定夺权。所以,陆游极有可能对直接的顶头上司王炎不能想他之所想、急他之所急而遗憾、不满,同时也对朝廷的主和派、妥协派贻误战机而怨叹、痛愤。所以,笔者判断,“画策虽工不见用”不仅有对王炎不能下令北伐的埋怨,也包含着对高乎乎在上的南宋朝廷贻误时机,不思光复失地、浪费人力财力智力、使殚精熟虑的画策弃置作废的怨愤。此其为二。综上,尽管王炎征辟陆游入幕,赋予他职权和抗金北伐的机会,他们总的关系协谐、融洽,但也在用人和出征上存在不尽如人意的错位,致使陆游心存遗憾、言有怨叹。是故,所谓“青衫误入征西幕”者,想必是既针对个人又针对朝廷的双关愤激之言。
三、“世间何地不羊肠”——趋走成都的失落意绪
乾道八年(1172)十一月,从戎南郑八个月后,随着王炎被调离川陕,陆游也结束了其在南郑的幕府生活。《陆游年谱》载:“十月,回南郑。王炎幕府已散。游被调为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十一月,自南郑启程,取道剑门关、武连、绵州、罗江、汉州,岁末,抵成都。”[1]4623离开抗金前线,到相对平静、安全、繁华、富庶、开放、热闹的地方为官,照理应是值得称道庆幸的好事、喜事,但对于一心想要扫胡尘靖国难、报君父不共戴天之仇的陆游来说,无异于斩断了他生命的脐带,使其精神失去了寄托、征程迷失了方向。陆游一下子从过去志在恢复、喜言恢复的亢奋状态,跌落到了冰冷的现实。在还没有展开真正意义上的抗金北伐的时候,南宋王朝其实已经自我松懈、自我放弃、自我毁灭。这既辜负了陆游誓志报国的壮怀,也辜负了敌占区众多暂寄敌营冒着生命危险暗中传信、远道寄物志士的良苦用心,更断送了金人统治下的遗民“忍死望恢复”的期盼。陆游想不通、搁不下,他把失落悲痛的情怀洒在了离开南郑、趋往成都的路上。这其中既有失意怨艾,又有感愤痛惜,还有遣玩放弃。如《初离兴元》写道:“梦里何曾有去来,高城无奈角声哀。连林秋叶吹初尽,满路寒泥踏欲开。笠泽决归犹小憩,锦城未到莫轻回。炊菰斫脍明年事,却忆斯游亦壮哉!”[1]257前四句明显流露出无常之悲,以旅途之凄凉、坎坷渲染、隐喻人生之悲凉、艰难。后四句似乎要另辟路径,变换态度与活法,但字里行间渗透着试图自我宽慰的自欺欺人、冷言反语。又如《自兴元赴官成都》写道:“平生无远谋,一饱百念已。造物戏饥之,聊遣行万里。梁州在何处,飞蓬起孤垒。凭高望杜陵,树烟略可指。今朝忽梦破,跋马临漾水。此生均是客,处处皆可死。剑南亦何好,小憩聊尔尔。舟车有通途,吾行良未止。”[1]258诗章感情复杂,跳跃性大。前四句自我调侃、酸楚嘲讽,第二个四句忆念南郑、向往京华,第三个四句感慨挫折、参悟人生,最后四句努力自慰、尝试解脱。诗意虽层次清晰,但忽此忽彼,夹杂着受挫后的遣玩不恭色调。从中正可感知陆游遭受打击之大,其精神、态度之恍惚、之杂芜、之迷惘。又如《遣兴》写道:“貂裘破弊色凄凉,塞上归来路更长。老骥嘶鸣常伏枥,寒龟藏缩正支床。凋零客路新霜鬓,扫洒先师旧草堂。九折阪头休绝叹,世间何地不羊肠!”[1]261此诗满纸呜咽,悲痛压抑的情怀分外强烈。有志而不得伸,被钳制而只能忍气吞声,世间布满陷阱而绝无坦途。最后一句像是自言自语的参悟,又像是在告慰、劝勉自己,真是含泪带血、闷愁至极。再如《剑门城北回望剑关诸峰青入云汉感蜀亡事慨然有赋》写道:“自昔英雄有屈信,危机变化亦逡巡。阴平穷寇非难御,如此江山坐付人。”[1]270诗虽短却颇有意味、力道。开头先谈世间变易、反转的大道理,意在指出屈伸有时、危机转化乃正常的普泛规律,后面结合刘禅自奉印玺、不战而降的历史,讽刺当朝懦弱不为的投降主义、卖国行径,最后一句何止是叹息、怨愤,简直是指斥、怒吼。
陆游行进在南下成都的路上,内心蓄满委屈、悲苦,禁不住油然生出强烈的思归之心。如《南沮水道中》:“磑舍临湍濑,罾船聚小滩。山形寒渐瘦,雪意暮方酣。久客情怀恶,频来道路谙。家乡空怅惘,无梦到江南。”[1]260又如《长木晚兴》:“沮水嶓山名古今,聊将行役当登临。断桥烟雨梅花瘦,绝涧风霜槲叶深。末路清愁常衮衮,残冬急景易骎骎。故巢东望知何处,空羡归鸦解满林。”[1]261这对多次幻想收复关中、长安,卜居鄠杜、终老其间的诗人该有多大的反讽意义啊!陆游不仅密集地表达了乡关之思,而且生出对人生、仕途、功名的质疑、否定,产生了隐退山林、求稳全性的念头,如《思归引》写道:“善泅不如稳乘舟,善骑不如谨持辔。妙于服食不如寡欲,工于揣摩不如省事。在天有命谁得逃,在我无求直差易。散人家风脱纠缠,烟蓑雨笠全其天。莼丝老尽归不得,但坐长饥须俸钱。此身不堪阿堵役,宁待秋风始投檄。山林聊复取熊掌,仕宦真当弃鸡肋。锦城小憩不淹迟,即是轻舠下峡时。那用更为麟阁梦,从今正有鹿门期。”[1]266
从今天留存的成都诗词来看,也有呈现出壮美快意、万丈豪情的,如《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前年脍鲸东海上,白浪如山寄豪壮。去年射虎南山秋,夜归急雪满貂裘。今年摧颓最堪笑,华发苍颜羞自照。谁知得酒尚能狂,脱帽向人时大叫。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破驿梦回灯欲死,打窗风雨正三更。”[1]299-300诗章在过往与当下间游移,在豪迈与颓废间挣扎,在自嘲与自雄间跳跃,显现出陆游的不甘、不弱、不放弃。但是总的来看,陆游成都诗歌的基调是灰暗悲苦的,即便是有亮色、有快意,也是快意与失意混杂、明丽与灰暗交织,他似乎跳脱不了忧怨的圈子、适应不了当下的生活。如《梅花》:“家是江南友是兰,水边月底怯新寒。图画省识惊春早,玉笛孤吹怨夜残。冷淡合教闲处著,清癯难遣俗人看。相逢剩作樽前恨,索笑情怀老渐阑。”[1]284梅花高标独立的品格正是诗人坚守不易的人格的象征,而梅花冷淡处寒的境况不正是诗人索寞失意的处境的隐喻吗?然则这样的苦情孤诣正是与环境不容、与时代不合、与过往不舍、与志气不离的结果,只有陆游才会有这样的状态,也只有有过壮举又有过失落的陆游才配有这样的混合样态。又如《登塔》:“冷官无一事,日日得闲游。壮哉千尺塔,摄衣上上头,眼力老未减,足疾有新瘳,幸兹济胜具,俯仰隘九州。雪山西北横,大江东南流。画栋云气涌,铁铎风声遒。旅怀忽恻怆,涕下不能收。十年辞象魏,万里怀松楸。仰视去天咫,绝叫当闻否?帝阍守虎豹,此计终悠悠。”[1]289诗章沉郁苍凉、哀痛透心,本来登高瞩望、饱赏风光,却不曾想事与愿违、触发隐痛。从这些诗句中,正见出陆游内心深处喜忧交错的无常状态和潜压已久的深悲巨痛。陆游成都时期的诗歌,总是在平常之中灌注着异常,在平静背后潜藏着跳动,在眼前境况中牵拽出昔日生活,在失意颓丧中翻腾出雄放澎湃。再如《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
“羽箭雕弓,忆呼鹰古垒,截虎平川。吹笳暮归,野帐雪压青毡。淋漓醉墨,看龙蛇、飞落蛮笺。人误许、诗情将略,一时才气超然。何事又作南来,看重阳药市,元夕灯山?花时万人乐处,欹帽垂鞭。闻歌感旧,尚时时、流涕尊前。君记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18]58
从章法结构上来讲,词作形成了过往与今日鲜明的对比,把快乐与失落团和在一起,给人以强烈的心理变异、落差。上片词人激情四射地追忆了从戎南郑激越昂扬、多彩绚烂的生活和他文兼武备、意气风发的才情和精神。下片则笔锋陡转,发抒命不由人、沉沦失意、无聊颓丧、酒泪合流的悲痛处境。结句忽作振起,以呵天吼地之力,表达壮心不改、追求功业的豪情。不难看出,陆游真正的快乐只存在于对过往的回忆中,是以当下的抑郁状态为参照体、衬垫物的,是其暂时摆脱、消解痛苦刻意酿制的麻醉剂。
《夜游宫·宫词》“当亦乾道九年间作”[9]52。此词与上一首词在抒情表意上的最大区别,一是满篇怨天尤人,二是显然别有寄托。词云:
“独夜寒侵翠被,奈幽梦、不成还起。欲写新愁泪溅纸,忆承恩,叹余生,今至此!簌簌灯花坠,问此际,报人何事?咫尺长门过万里。恨君心,似危栏,难久倚。”[18]62
从浅表层面看,该词描写的是一位失宠宫女愁苦、怨叹的生活和状态,但从深层次揣摩,词意实际上隐喻的是君臣离合的大节大义。陆游从戎南郑,实与王炎的赏识、眷顾、提携有很大关系。可以说,陆游在一定程度上是冲着具有抗金情结的王炎和清扫胡虏妖氛、完成统一大业的壮伟事业而来到南郑的。然(乾道八年)“九月……乙亥,诏王炎赴都堂治事。……九年春正月辛未,王之奇罢为淮南安抚使,王炎罢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4]654。王炎的调离继而被贬斥,宣告了政治风云的变换,抗金大业的流产,陆游宏愿的沉坠。于此背景下,陆游不仅自己难过,更替王炎悲哀。肝胆与共的知己遂不愿默默,而以比兴寄托的手法,假借君王、宫女之事发抒孝宗与王炎有始无终、半道离析的悲剧。是故,“从深层次看,此词深得骚人之旨趣,既为王炎蒙受屈辱而鸣不平,也为自己失怙无依而叹息,更为君心莫测、不可凭恃而发泄。是可谓色貌如花、荆刺锥心,言在此而意在彼也”[19]。
综上所论,陆游去东西进、宦游巴蜀期间,实有着难以挥去的低沉、伤感、抑郁的情怀。出判夔州,远离家乡与前线,悲凉的情怀始终渗肺透心,成为其为官一任的主色调;从戎南郑,激昂的情怀翻为主体,而画策不为见用的压抑感受潜滋隐伏,无从消除摆脱;南下成都,离开战地疆场,精气神陡然逆转,失望、失意的情绪蓄满心头,摴蒱醉饮、拥妓买笑成为其化解心病、暂忘苦痛的另一种扭曲方式,美梦存放在回忆中,安慰夹裹在自弃自废里,眼泪混合着烈酒长流在梗阻的心窝。夔州、南郑、成都,这段移步换形、无法挣脱的悲抑情怀,让我们窥见了陆游精神生活真实而立体的样态,也明白了陆游被迫无所作为、南宋不免走向覆亡的个中道理,更理解了陆游“早岁那知世事艰”[1]1346“悲吒哪复从军乐”[1]2456“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18]148怒吼与怨叹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