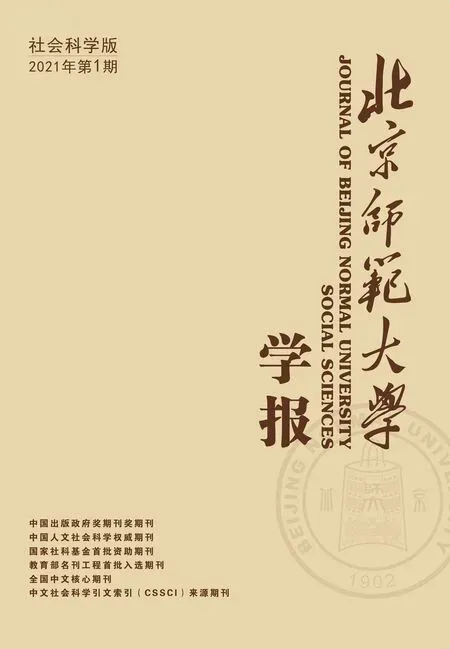究竟是yārghū还是“钩考”?
——阿蓝答儿钩考的制度渊源探微
2021-02-01周思成
周思成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 100017)
引言:重新审视阿蓝答儿钩考的制度史意义
“阿蓝答儿钩考”是大蒙古国蒙哥汗(元宪宗)统治时期发生的一起轰动一时、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1257年春,蒙哥汗突然解除了当时还是藩王的忽必烈的兵权,又派遣心腹阿蓝答儿和刘太平等前往忽必烈封地陕西、河南,设立“钩考局”,“钩校钱谷”,一时“虐焰熏天,多迫人于死”。陷入窘境的忽必烈不得不亲自觐见蒙哥,委曲求全。二人矛盾虽由此得到缓和,但忽必烈在陕西、河南等地设置的安抚司、宣抚司、经略司一类行政机构仍被裁撤。直到蒙哥南下征宋的东路军(塔察儿部)作战失利,忽必烈才重获机会回到蒙古帝国权力舞台的中心。
元史学界对“阿蓝答儿钩考”事件的关注虽不多,却均系前辈学者极有份量的研究成果。陈得芝、邱树森、王颋、萧启庆和杉山正明等多数研究者都倾向于从政治斗争角度解读这一事件,认为“钩考”其实是蒙哥和忽必烈政治矛盾激化的表现,进而也是大蒙古国内部奉行蒙古本位主义的“保守派”同倾向汉化的忽必烈派系之间的斗争(1)陈得芝、王颋:《忽必烈与蒙哥的一场斗争:阿蓝答儿钩考的前因后果》,元史研究会:《元史论丛》,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7-56页;邱树森:《浑都海、阿蓝答儿之乱的前因后果》,《宁夏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王颋:《钩考返权——阿蓝答儿钩考事件的前因后果》,王颋:《龙庭崇汗:元代政治史研究》,广州:南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196页;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萧启庆:《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293-294页;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と大元ウルス》,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4年版,第85-90页。。事件的起因是忽必烈在漠南汉地的势力发展,特别是他倾向汉法的统治立场,“不免侵犯了习惯于随意勒索的蒙古、色目贵族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嫉恨”(2)陈得芝、王颋:《忽必烈与蒙哥的一场斗争:阿蓝答儿钩考的前因后果》,第54页。;而钩考事件“表面上是检查京兆与河南的财赋,实际上是要否定忽必烈用汉人治汉地的成绩,并彻底瓦解他的势力。”(3)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第293页。
这一侧重政治斗争的解读方式,其合理性毋庸过多质疑。不过,这毕竟是一种回溯的事后视角,换言之,以“阿蓝答儿钩考”为标志的忽必烈同蒙哥间的权力斗争之所以凸显政治史意义,是因为研究者都预设了一个事实前提:忽必烈最终在这场斗争中胜出,他依托漠南的物质和文化资源,在汗位争夺战中成了蒙古帝国名义上的共主和元朝的创立者。然而,从钩考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回望,上述那样一个由无数偶然和必然因素际会而成的图景尚遥遥无期。雄踞当时政治图景中央位置的,是蒙哥汗厘革前朝的弊政积习,锐意在蒙古帝国全境推行收缴圣旨牌符,整顿驿站、斡脱和赋税等一系列“集权化”改革,其中的重要事项就包括将诸王在封地的部分行政权力收归中央(4)Thomas T.Allsen,Mongol Imperialism:The Policies of the Grand Qan Möngke in China,Russia,and the Islamic Lands,1251-1259,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p.78-115;78-79,50-51.。爱尔森(Thomas T.Allsen)提出,蒙哥的行政和财税改革旨在确保对外战争必需的资源以及中央-地方机构的效率和忠诚。对忽必烈漠南势力的清算,也可以算作其中的一环,意在打压后者愈来愈强烈的“自治”倾向(ongoing quest for autonomy)(5)Thomas T.Allsen,Mongol Imperialism:The Policies of the Grand Qan Möngke in China,Russia,and the Islamic Lands,1251-1259,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p.78-115;78-79,50-51.。在此语境下,与“汉法派”同“保守派”之间的政治斗争相比,“阿蓝答儿钩考”的制度史意义则显得更加重要。
从制度史角度审视“阿蓝答儿钩考”,迄今唯一的讨论来自李治安先生《元世祖朝钩考钱谷述论》一文的开篇部分。李先生在文中敏锐地指出:(1)“阿蓝答儿钩考”是大蒙古国时期理算钱谷的典型事件,在实施方法上对元世祖朝的钩考钱谷影响甚大。(2)元世祖朝的钩考钱谷有两大制度来源,一是以“阿蓝答儿钩考”为代表的“蒙古旧例”,二是唐宋“勾覆”和“磨勘”遗制,“二者分属蒙古法与汉法,但在检复考核财赋方面,又具有很多相通之处”(6)李治安:《元世祖朝钩考钱谷述论》,《历史教学》,2001年第2期;又参见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77-578页。。对上述结论,我深表赞同。不过,这一分析仍然留下了一个关键问题有待廓清,即:“阿蓝答儿钩考”所参照之“蒙古旧例”究系一种什么制度?漠北统一之前的蒙古氏族和部落组织并不产生“钩考钱谷”的问题,故虽言“旧例”,显然不至肇始于成吉思汗或窝阔台时代之前。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初步探讨,敬祈方家指正。
一、“阿蓝答儿钩考”类似唐宋时期的“勾覆”么?
“阿蓝答儿钩考”似仅见于汉文史料记载。在明修元史的《本纪》中,在与该事件有牵连的赵璧、廉希宪、商挺、姚枢等人的碑传史料中,除“钩考”外,亦多以“钩校”、“理算”、“会计”、“核藩府钱谷”来概括之,故研究者很容易略过基本的历史-文化语境转换过程,不言自明地将之与中原王朝传统的财政监察和审计制度联系起来。杉山正明所说的“会计监查”(7)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と大元ウルス》,第86页。,或李治安先生以“财务审计”来求二者之共同点,就是如此。“阿蓝答儿钩考”及其代表的“蒙古旧例”,究竟多大程度上类似于“理算财赋”?我们不妨先将之与唐宋时期的中央财政监察和审计的运行方式作简单比较。
唐代中央政务机构中的“勾覆”,由刑部下设比部专司其职。据《旧唐书》,比部郎中及僚属“掌勾诸司百僚俸料、公廨、赃赎、调敛、徒役、课程、逋悬数物,周知内外之经费,而总勾之”(8)刘昫等:《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39页。。宋代虽未明确区分会计和财政监察,立法较唐代则愈详密。《宋史》言:
旧帐案隶三司,自治平中至熙宁初,凡四年帐未钩考者已逾十有二万,钱帛、刍粟积亏不可胜计。五年十一月,曾布奏,以四方财赋当有簿书文籍,以钩考其给纳登耗多寡。遂置提举帐司,选人吏二百人,驱磨天下帐籍,并选官吏审覆。七年二月,诏帐司每岁具天下财用日出入数以闻。元丰初年,诏:“诸路财赋出入,自今三年一供,著为令。”官制行,厘其事归比部。(9)脱脱等:《宋史》,卷一六三,《职官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861页。
由此可知,北宋中央机构的会计和财政监察权最初归盐铁、户部、度支三司,三司下设三部勾院、都磨勘司、勾凿司、会计司等机构,又有提举帐司(10)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下,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49-654页;又参见方宝璋:《两宋经济管理思想研究》,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60页。。元丰官制行,权归比部,《文献通考》言:“比部掌勾稽文帐,周知百司给费之多寡,凡诸仓场库务收支,各随所隶,以时具帐籍申上,比部驱磨审覆而会计其数。诸受文历,每季终取索审核,事故住支及赃罚欠债负则追索填纳,无隐昧则勾销除破。”(11)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五十二,《职官六·刑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81页。由上述内容不难看出唐宋的“勾覆”和“磨勘”制度有如下特征:(1)由中央官僚体系中品阶较低的专门机构和官员负责。(2)通常有规定的程限(“月计、季考、岁会”)。(3)主要依据层层上报的帐籍文簿(所谓“所凭惟帐状”)(12)脱脱等:《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第4528页。,不直接勾摄和纠问干连吏人,较少主动调查取证。(4)向上级汇报帐籍文簿的出入问题,没有或者仅有微弱的司法裁量权(13)值得注意的是,唐宋之制将职司财政监督审计的比部从户部分离出来并置于刑部下,主要是出于审计独立的考虑,并不意味着比部因而拥有刑部的司法权。。唐宋中央“勾覆”之制的一个典型案例可见《宋史》。《梅执礼传》载:梅执礼出任比部员外郎,“比部职勾稽财货,文牍山委,率不暇经目”。一日,苑吏“持茶券至为钱三百万者,以杨戬旨意迫取甚急”,梅执礼审核单据后发现问题,“知其妄,欲白之”,比部长官和同僚畏惧权势,“疑不敢”,梅执礼只好单独具名上奏,调查结果是“果诈也”(14)脱脱等:《宋史》,卷三五七,《梅执礼传》,第11232页。。
“阿蓝答儿钩考”的汉文记载不多而且零散,前辈学者已作了近乎穷尽的考索,然而,若从制度层面加以梳理,不难看出阿蓝答儿所设“钩考局”及其办事程序和作风,反映出十分异样的制度特征:(1)“钩考”是经由某种告劾程序启动的。陈得芝、王颋二先生已经指出,告发者一则“宗亲间之”,二则“总天下财赋”的奸臣“扇结朋党,离间骨肉”,而告发之罪名为“王府得中土心”,以及“王府诸臣多擅权为奸利事”(即怀疑藩府及下属诸司截留侵吞了应上缴中央的赋税等等)(15)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姚景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52-153、160页;姚燧:《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查洪德编校:《姚燧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9页;姚燧:《谭公神道碑》,查洪德编校:《姚燧集》,第370页。。“钩考”开始前,忽必烈已经被解除了兵柄,听候进一步处分。(2)“钩考”由蒙古大汗直接授权之高级官员主持。阿蓝答儿“以丞相行省事,刘太平以参知政事佐之”,两人均是蒙哥的亲信侍从,是大汗权力在当地的最高代表。前者在汉文史料中又被称为“贵强相”、“左丞相”(16)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姚景安点校,第119页;王恽:《王恽全集汇校》,杨亮、钟彦飞点校,第6册,《史公家传》,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277页。。(3)直接逮系、拷讯当事官员,甚至接受告发,通过纠问获取口供定罪。阿蓝答儿一到京兆,就“大集汴蜀兵民之官,下及管库征商之吏,皆入计局”(17)姚燧:《谭公神道碑》,查洪德编校:《姚燧集》,第370页,颇类中古法庭审理案件时要求干连人证“随衙待对”。属官马亨执意将“岁办课银五百铤”输往王府,阿蓝答儿甚至有权“遣使逮之王府”,“既至,拘系之,穷治百端”(18)宋濂:《元史》,卷一六三,《马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827页。。除主动取证外,阿蓝答儿“复大开告讦,虐焰忷忷”(19)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姚景安点校,第126页。。《赵璧神道碑》记载,钩考局“屡鞫人于前,欲令侵公(赵璧)……(公)每诣渠,辨析案凭,致渠怒,端立拱俟,怒已,复辨如初。”(20)张之翰:《赵公神道碑铭》,李修生:《全元文》,第1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4)实行“有罪推定”,兼具完全的司法裁量和执行权。不少史料记载,阿蓝答儿的钩考局事先“罗织”了142项罪名(21)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姚景安点校,第370页;又见张之翰:《赵公神道碑铭》,第350页。,“文致多方”,公然宣言“惟刘万户、史万户两人罪请于朝,自余我到专杀”。对于那些级别较低的人员,“锻炼罗织,转功为罪,例遭凌辱”,“官吏望风畏遁,死于威恐者二十余人”(22)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姚景安点校,第119、228,126页。。
由以上四点不难看出,“阿蓝答儿钩考”的实况,与唐宋以来的“勾覆”和“磨勘”遗制实毫无共同之处,反而更接近中央机构在处理经济贪腐大案时特派的专门法庭或“专案组”。
二、“阿蓝答儿钩考”事件中的断事官身影
由上述比较可知,“阿蓝答儿钩考”事件的财政监察和审计色彩相当微弱,在河南、陕西等地新设的“行尚书省”及下属“钩考局”,更像是一个侦办经济案件的特别法庭。这样一种特殊的制度从何而来?

其次,史料记载,阿蓝答儿、刘太平两人“钩校括索,不遗余力,又取诸路酷吏分领其事,大开告讦”(27)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姚景安点校,第119、228,126页。,可见“钩考”首先是一件费时费力的“技术工作”,断非阿蓝答儿与刘太平二人袖手可办。那么,大断事官行署(行尚书省)和钩考局的人员班子,也就是汉文史料中所谓“诸路酷吏”或“群不逞辈”(《赵璧墓碑》)、“深刻吏”(《赵公神道碑铭》)从何召集而来?不可能来自钩考的对象,即忽必烈藩府下属的宣抚经略诸司系统。事实上,大断事官行署和钩考局(或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核心成员至少需要满足以下条件:须通晓相关语言,多少熟悉地方情况和财税技术知识,更重要的是忠诚可靠,不致与忽必烈王府暗通消息,给调查工作釜底抽薪(28)为了缓和“钩考”,忽必烈已派遣数名亲信“弥缝其间,时通动息藩府”,也就是采取了某些“反侦察手段”,见姚燧:《谭公神道碑》,查洪德编校:《姚燧集》,第370页。。
笔者推断,这些“酷吏”多半来自邻近的另一大断事官行署——燕京等处行尚书省的断事官集团。除了只有这一群体完全满足上述要求外,这一推断尚基于以下三点佐证:一,《元史·齐荣显传》提到,传主在任职山东西路时,“值断事官钩校诸路积逋,官吏往往遭诟辱”(29)宋濂:《元史》,卷一五二,《齐荣显传》,第3601页。,可见在大蒙古国时期,以断事官钩考逋负,应属于一种常规制度。二,王颋先生指出,自窝阔台汗到贵由汗统治时期,燕京等处行尚书省的断事官“员额数量非常之多”,在《庙学典礼》、《经世大典》等政书保存下来的官文书中,可考证出不少任职于该地又不见于正史记载的蒙古、色目断事官姓名(30)王颋:《断事尚质——大蒙古国的行尚书省和札鲁花赤》,王颋:《龙庭崇汗:元代政治史研究》,第138页。,此外,断事官还配备有郎中、都事、从事等僚属。这些断事官及吏员中许多人原先就在河南、陕西等地公干,因为这两个地区是后来才由忽必烈藉口“汉地不治”,从燕京行省大断事官的辖区中割裂出去的(31)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第288页。。蒙哥此次向河南陕西派出以阿蓝答儿为首的大断事官行署,意在“钩考”结束后,名正言顺地接管当地的全部财权和司法权。为此,将因王府分治而失去任职地面和利益来源、很可能对忽必烈藩府抱有敌意的断事官们抽调过来进行钩考工作,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三,《史楫神道碑》提到蒙哥汗即位之初(1251年)的另一次断事官办案:“辛亥,断事官也里干脱火思来按本部,性苛察喜事,凡被劾者,凌轹罗织,莫有脱其彀者。”(32)王恽:《王恽全集汇校》,杨亮、钟彦飞点校,第6册,《史公神道碑铭》,第2470页。这里描述的断事官苛察、好罗织锻炼的形象,与前述“阿蓝答儿钩考”汉文史料叙事中“诸路酷吏”的形象极为契合,阿蓝答儿本人就被汉人斥为“性苛刻,锻炼罗织,转功为罪”(33)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姚景安点校,第119页。,这绝非偶然。
“阿蓝答儿钩考”中主要办案人员的身份既是大断事官与断事官群体,那么,行省与“钩考局”的法庭或专案组色彩也就可以获得一个初步解释。蒙古官制中的也可札鲁忽赤及其行署,兼治政刑,然其核心职能在于理刑(司法)。到了元代,札鲁忽赤的诸项职能被逐渐抽离之后,给大宗正府剩下的就是处理蒙古词讼的司法职能(34)关于断事官在元代的发展,参见刘晓:《元代大宗正府考述》,《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刘晓:《元朝断事官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4期;赵文坦:《元代的刑部和大宗正府》,《历史教学》,1995年第8期。。大蒙古国时期的断事官人员拥有几乎不受约束的司法权,“时断事官得专生杀,多倚势作威”。正是在蒙哥汗统治初年,燕京行尚书省的断事官牙老瓦赤和不只儿二人,“视事一日,杀二十八人。其一人盗马者,杖而释之矣,偶有献环刀者,遂追还所杖者,手试刀斩之。”(35)宋濂:《元史》,卷一二五,《布鲁海牙传》,第3070页;卷四《世祖本纪》,第58页。作为河南、陕西等地行省的大断事官阿蓝答儿及其断事官僚属,自然也拥有广泛的司法和执法权力。因此,阿蓝答儿主持的“钩考”,他和他属下的职权范围,尤其是他们获取证据、裁定罪名和实施惩罚的种种手段,绝非区区“勾覆”或“理算”二字可以曲尽其情。
三、断事官的yārghū与“钩考”

Yārghū,若从明代《蒙古秘史》的音译,可作“札儿忽”,对应蒙古语中的jarghu(听讼、断事,如再加上表职业的接尾语chi,就是上文提到的“札鲁忽赤”)(37)札奇斯钦:《说元史中的“札鲁忽赤”并兼论元初的尚书省》,《蒙古史论丛》,(上),第147页。。德福(G.Doerfer)在名著《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和蒙古语成分》一书中就直接将yārghū译为Gerichtshof(德文:法庭)、gerichtliche Untersuchung(德文:司法调查),并依据波斯文和阿拉伯文史料指出这样一种法庭一般由8名札鲁忽赤组成,长官为札鲁忽异密(38)G.Doerfer,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Band IV,Wiesbaden:Franz Steiner Verlag,1963,pp.58,61.。大卫·摩根(D.O.Morgen)在《成吉思汗的“大札撒”与伊利汗国的蒙古法》一文中考证出yārghū在拉施特《史集》的蒙古史部分中共出现40余处,主要指一种特殊的蒙古司法实践——是历代伊利汗为调查失势的大臣和其他威胁统治的敌人(如被告发谋逆者)而启动的一种司法手段,通常伴随着使用刑讯逼供;在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中也有几处提到yārghū,主要指一种针对政治阴谋和受指控的官员的调查程序。摩根认为:“在这些史家看来,这种yārghū似乎是一种特别(ad hoc)法庭,旨在处置特殊案件。拉施特经常使用这样一个表达:‘他们对他进行了yārghū’(ū-rā yārghū dāshtand)。而这些案件通常都涉及蒙古人或者与蒙古的国家要务有关。”(39)D.O.Morgan,“The’ Great ‘yāsā’ of Chingiz Khān’ and Mongol Law in the lkhānate”,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986,49(1),pp.173-176.
伊朗中世纪史研究者兰普顿(Ann K.S.Lambton)对yārghū制度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从兰普顿的研究中归纳可知:首先,yārghū是一种纠问法庭,在蒙古帝国的各部分都存在过,法庭长官被称为umarā-yi yārghū,在伊利汗国称yārghūchi(札鲁忽赤),后期又称amīr-i yārghū(札鲁忽异密)。其次,在程序上,关于yārghū留下的细节虽然很少,但他们的司法准据应为札撒,“主要处理蒙古人内部的纠纷、蒙古国家事务和针对官员的控告案件,特别是关于侵吞公款和政治阴谋(着重号系笔者所加)的指控”。最后,在伊利汗国前中期,yārghū针对的首要目标,就是国家财政收入上的贪腐案件。例如,《瓦萨甫史》记载,阿八哈汗统治时期的札鲁忽赤Taghachar受命前往报达,审查阿塔—蔑力—志费尼在该地聚敛的库藏;又如阿八哈时期的一起针对法尔斯总督Angyanu的指控,据说他的施政和赋税征集遭到了当地蒙古异密们反对和嫉恨,于是他们奔走宫廷,控告总督意图谋叛和贪污公款(40)Ann K.S.Lambton,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edieval Persia:Aspects of Administrative,Economic,and Social History,11th—14th Century,Albany,N.Y.:Bibliotheca Persica,1988,pp.82-96.亦可参见:Bertold Spuler,Die Mongolen in Iran:Politik,Verwaltung und Kultur der Ilchanzeit 1220-1350,4.verb.und erw.Aufl.,Berlin:Akademie-Verlag,1985,pp.310-322。。由此可见,“阿蓝答儿钩考”事件中忽必烈藩府受到的主要指控——“得中土心”(或涉及政治阴谋)和“王府诸臣多擅权为奸利事”(贪渎问题),恰恰是断事官的yārghū法庭的主要职权范围。
关于蒙古断事官的yārghū法庭的程序特征,丹尼斯·艾格里(Denise Aigle)主要依据较晚期(帖木儿帝国时代)的史料提出,与传统的沙里亚法庭相比,yārghū法庭在采信证据方面极为宽松,在某类案件上沙里亚法庭要求四位证人到场,而yārghū法庭仅凭一位证人即可定罪,并且还接受青年、妇女和奴婢的告讦。他还引用苏布特尔尼(Maria Subtelny)的研究说:“yārghū违反了伊斯兰司法程序的基本规则,对被告实施有罪推定,并且多采信态度偏颇、资质可疑的证人的作证。”(41)Denise Aigle,The Mongol Em p ire between Myth and Reality,Leiden:Brill,2015,pp.150-152.为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不妨再来看两件伊利汗国时期的yārghū案件,两起案件在兰普顿的研究中都有简要概括,波斯文系笔者核对他引用的波斯文史料来源后补充的重点细节。
其中一个案件发生在阿儿浑阿合(Arghun Agha)任呼罗珊总督时期,记载在13世纪佚名波斯史家的《哈剌契丹王国史》(Tarīkh-iShāhī-yiQarākhatāyīyān)中。一些人前往阿儿浑处,起诉起儿漫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忽都鲁汗忽忒巴丁(Qutb al-Dīn)的遗孀秃儿坚哈敦(Turkan Khātūn)。阿儿浑无意与忽都鲁汗家族发生冲突,于是给秃儿坚哈敦写了一封信,随信附上了起诉书,授意秃儿坚哈敦的代表(nāyib)和当地的八思哈(basqaq,监临官)会同审理这些起诉者(波斯文原文为:召开一个yārghū)。秃儿坚哈敦将此事转交给了八思哈和札鲁忽赤。官员们将控告人带到一片荒地上:
对他们进行了严酷的yārghū,令他们赤裸身体,带上镣铐监禁数日,然后按照蒙古人的方式(chinānki rasm-i mughūl ast)对他们进行拷讯,直到他们招供并在招伏(khatt ba gunāhkārī)上画押。(42)Anon,Tarīkh-i Shāhī-yi Qarākhatāyīyān,ed.by M.I.Bāstānī Pārīzī,Tehran:Intishārāt-i Buniyād-i Farhang-i rān,1974,p.156.
犯人中的一些人被当即处死,另外一些人被赦免。另一起案件发生在回历705年(公元1305—1306年)的完者都统治时期,记载在《瓦萨甫史》中。某个名叫塔只丁(Tāj al-Dīn Gūr Surkhī)的人纠结朋党,指控完者都的两位大臣拉施特(Rashīd al-Dīn)和撒都丁(Sa‘d al-Dīn Sāvajī)犯有贪渎之罪。完者都知二人之冤情,命召开大断事官法庭(波斯文为yārghū buzurg,德文译文为der grosse Gerichtshof,即大法庭)进行审理。真相大白之后,塔只丁及其部分党羽被处死,另外一些犯人(很可能受到赦免)受到“杖责”(43)Abd Allāh b.Fadl Allāh Shīrāzī Wassāf,Tārīkh-i Wassāf (Tajziyat al-Amsār wa Tazjiyat al A’sar),Bombay:1269/1853,p.478;德文译文见Hammer-Purgstall,Geschichte Wassaf’s,Bd.4,Wien: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2016,pp.216-217。。
以上对yārghū法庭的诉讼程序和实际办案情形的描述,虽然比较质朴,却非常接近“阿蓝答儿钩考”中断事官的行为模式,特别是在有罪推定、酷刑拷问或无论嫌犯是否有罪均广泛采用杖刑等特征上,二者简直如出一辙(44)在札鲁忽法庭上经常使用暴力和刑讯,亦得到德福研究之证实,他列举的多起札鲁忽法庭案件中,多强调使用了Stockschlag(德文:杖打)或Folterung(刑讯、拷打),见G.Doerfer,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Band IV,pp.59-61。。除前面提到王府僚属马亨遭到拘系,“穷治百端”外,《元朝名臣事略》所引《赵良弼墓碑》还形容阿蓝答儿等人“盛暑械人炽日中,顷刻即死”,甚至在蒙哥下旨停止钩考后,“犹杖兵民诸官,凡昔所置司皆废”(45)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姚景安点校,第228页;姚燧:《谭公神道碑》,查洪德编校:《姚燧集》,第370页。。在对断事官主持的yārghū法庭的描述上,汉文史料与波斯文史料遥相呼应,互相补充,构成了一幅颇为奇妙的景象。
四、余论
前文对钩考局班子的断事官身份、职权和办案程序作了初步分析。由此可知,“阿蓝答儿钩考”本质上绝非普通的“财政审计”,如果说这次“钩考”依据了某种“蒙古旧例”,那么这一旧例不是别的,正是大蒙古国断事官的yārghū司法程序,汉文史料中所谓“钩考局”,其实不过是yārghū法庭的别称。
“阿蓝答儿钩考”(或可称之为“断事官型钩考”)对后来元世祖时期特别是阿合马、桑哥等人主持的“钩校钱谷”(“尚书省型钩考”)显然有着确凿无疑的影响,前辈学者已经看到了这种制度上的沿袭(46)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第578页。。不过,这种影响是否仅仅限于李治安先生提到的“遣使、置局、追赔”这类一般外部形式上?我们认为,“阿蓝答儿钩考”和yārghū制度对“尚书省型钩考”的本质性影响,在于堂而皇之使大量严峻的司法因素混入了本属于财政范畴的制度安排,用侦办重大刑案的思维、尺度和手段来进行“财政审计”。因此,元朝的“钩考”具有特别令汉族士人反感的“粗暴”和“凶狠”的面目:钩考一起,不仅大肆逮问干连人员,广开告讦之门,每兴罗织之狱,“敲榜偏于郡县”(47)刘敏中:《刘敏中集》,邓瑞全、谢辉点校,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97页。,官员、百姓破家丧身者相望于道,时人多以“难”、“害”、“祸”这类词语加以形容,甚至“尚书省型钩考”也同“阿蓝答儿钩考”一样,屡屡沦为当权者整肃政敌、翦除异己的政治斗争手段。从这些方面来看,“阿蓝答儿钩考”可谓开了一个“恶法”先例。
还需强调的是,“阿蓝答儿钩考”作为一种yārghū,应该是在汉文史料的叙事中被遮蔽和掩盖起来、在波斯文史料中被有意回避的事实。原因或许是这些记载都产生于较晚时代忽必烈的支持者之手。这些汉文史料的作者,一方面不一定熟稔大蒙古国的制度,或无法在本土语料库中找到yārghū的对应表述,即如元初官员胡祗遹所言:“蒙古祖宗家法,汉人不能尽知”(48)胡祗遹:《胡祗遹集》,魏崇武、周思成点校,“论定法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69页。;又或者是下意识地将之比附为“钩校”或“理算”,以便在浸染儒家传统的读者心中激起对王安石、曾布或者元初阿合马、桑哥一类理财之臣的厌恶情绪,最终企图否认这次钩考(至少在当时位于哈剌和林的帝国中枢看来)具有权力和事实上的某种合法性。
我们将“阿蓝答儿钩考”最终确认为蒙古断事官的yārghū司法,将京兆地区设立的“钩考局”——一个此前从未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机构——认定为yārghū法庭的一种形式,目的在于纠正将“阿蓝答儿钩考”单纯看作一种“财政审计”的偏颇印象,从而明确提出:“阿蓝答儿钩考”是大蒙古国权力中枢通过断事官对忽必烈藩府在河南、陕西等地任命的诸司官员发动的贪污税赋和渎职的司法调查程序。这一看法并不否认“钩考”事件背后的权力斗争潜流,或这一过程中的确采用了某些财税清查措施。相反,这一制度史的考察却能为政治史研究做出某种贡献,那就是指出:汉文记载不仅遮蔽了这次“阿蓝答儿钩考”制度本像,还可能遮蔽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这次政治斗争并不仅仅是在“保守”的蒙哥派系和“先进”的忽必烈派系之间展开的,它至少还有一个第三方,那就是大蒙古国的断事官群体。在被斥为“扇结朋党,离间骨肉”的宗亲和奸臣挑唆蒙哥发动对忽必烈封地的司法调查的幕后,必然有着因为藩府的存在而利益受损的、庞大的中央—地方断事官集团在不断推波助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