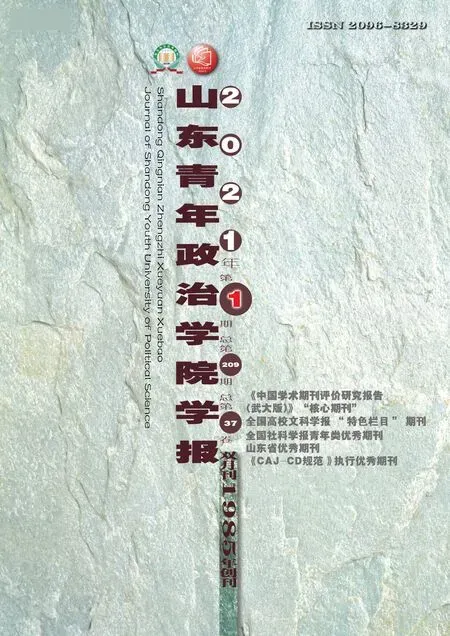缺失性创伤体验与“五四”现代话语的多元歧义
——以许地山“五四”文学实践为例
2021-01-29王威龙
王威龙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济南 250014)
一直以来,中国的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西化”,象征着自由、民主、科学等进步话语。如顾彬认为中国“现代”的过程就是“从中国传统向西方现代性过渡”[1],钱玄同则直言“一般人所谓,‘西方文化’,实在是现代全世界的文化”[2]。但实际上,中国“现代性”既不是西方的现代模式在中国的“移植”,更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意义系统,而是一个多元歧义交织出的格局。因此,进一步充实“五四”现代话语内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完善“多元歧义”这个空洞的能指并探究其成因,则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在此,“体验”是介入此问题的一个极富价值的视角。
王一川在其著作中认为清末的四种“现代性体验”:惊羡体验、感愤体验、回瞥体验、断零体验。[3]而“五四”的“现代体验”则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可以说,缺失性创伤体验贯穿了“五四”作家对现代话语的理解、改造与言说。从缺失性创伤体验切入作家和作品,不仅可以更清晰地把握作家主体创作心理、精神需求与文学行为之间深刻的互文性,更让我们完整地看到了文本背后独特的、个体的现代话语和现代立场生成的过程,并直接导致了“五四”现代话语多元歧义格局的形成。在此,许地山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极为典型的标本。
一、缺失性创伤体验与“五四”作家现代追求的发生
一直以来,文学史叙述大多认为《命命鸟》讲述了一个为反对封建婚姻制度,追求自由恋爱而殉情的故事。如杨义认为敏明与加陵的爱情不仅“冲破封建主义的门第等级界限”,“传达了‘五四’儿女对恋爱自由的热忱追求”。[4]朱栋霖、吴义勤、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5-2016》认为《命命鸟》“双双携手投湖殉情的故事,控诉了封建制度对青年的戕害”[5]。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认为《命命鸟》“清晰体现了主人公以殉情反抗封建家长的实际意向”[6],等等。
然而,《命命鸟》讲述的真的是一个“五四”反封建和追求自由恋爱的启蒙主义故事吗?启蒙话语和宗教信仰究竟是《命命鸟》创作的内在驱动力还是副产品呢?跳出“五四”的逻辑框架和宗教的拘囿,是否可以透过文本发现许地山更为隐秘而丰富的心理世界?将二人的殉情看作对自由恋爱的献祭,从而表现了反封建的主题,恰恰是“五四”启蒙主义话语对《命命鸟》的误读。当敏明在幻境到达情尘,却看到彼此表白的男女转眼间就相互啮食,不禁喊出“你们底感情真实反复无常”[7]。敏明从此“誓不再恋天人,致受无量苦楚。愿我今夜得除一切障碍,转生极乐国土”[8]。“无常”是敏明了悟的结果,也是《命命鸟》真正的主题。“无常”恰恰是对爱情的否定,并延伸到了人性和人生的无常,以至于厌世。因此,敏明从怀揣爱情的火炬到否定爱情,并最终皈依信仰,是参透世界无常苦空的本质,超越情感的业障和烦恼,最终开悟的过程。这决定了敏明的死并不是为了表现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由恋爱的主题,恰恰是在启悟和皈依中对爱情的质疑和否定。
那么,在“五四”语境中,人性、欲望、爱情作为启蒙的象征时,许地山为何否定爱情呢?当在“为人生”的口号下表现人生、书写人生时,许地山为何会向彼岸世界、宗教信仰寻求超脱呢?茅盾认为这是“‘五四’落潮期一班青年苦苦地寻求人生意义到了疲倦了时,于是从易卜生主义的‘不全则宁无’回到了折衷主义的思想的反映”[9]。还有研究者认为“怀疑论”源自“对‘五四’时期纷至沓来的‘主义’、思潮的怀疑”[10]。也不乏从阶级论和宗教角度认为“这种带着命定论的浪漫主义,一方面是他的小资产阶级身份所决定,另一方面是受佛教哲学的影响”[11]。其实,只有摆脱时代和历史的宏大话语,回到作家个体的生命体验,才能发现作家与作品之间的有机联系。与其说许地山笔下的悲观厌世的虚无主义和怀疑论是“五四”落潮时知识分子苦闷心态的反应,不如说来自许地山切身的缺失性创伤体验。缺失性创伤体验是主体因物质的、精神的、生理的等缺失而形成的一种强烈的、持久的、难以摆脱的心理创伤。从广义上说,它既包括原本不曾拥有而造成的生命缺憾,也包括得而复失造成的心理创伤。“五四”时期,由缺失性创伤体验而来的精神危机,对作家许地山的诞生来说,既是诱因,也是起点。
构成许地山缺失性创伤体验核心的是妻子林月森的去世。1920年秋天,许地山回福建接妻女进京,中途妻子林月清忽得急病,猝然离世。对许地山来说,“丧妻的悲哀是极神圣的悲哀”[12]。丧妻的缺失性创伤体验成为推动其文学创作的内驱力,并成为许地山创作中挥之不去的情感基调。许地山在《落华生舌·弁言》中写到:“方才梦见爱妻来,醒后急翻书箧,得前年所造诗,翻诵许久,不觉泪下,于是把它录下,作为第一首。更选记忆中的旧作为自己所爱的抄下,没事时可以自己念念。”[13]这首诗就是《七宝池上底相思》,诗作通过幻想亡妻在极乐世界与佛陀使者的对话,来叙说渴望回到丈夫身边的悲痛。同样,在妻子去世一周年之际,许地山梦见与爱妻促膝谈话,醒后写作《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三夜》。而直接叙写怀念亡妻的创作则更多。在《空山灵雨》中,《别话》还原了妻子弥留之际分别的场景,情真意切,令人动容;《爱流汐涨》写了在妻子去世百日之际,丈夫一夜的抽泣;《我想》表达了生活因丧妻而索然无味。此外还有诗歌《女人我很爱你》《看我》《情书》《月泪》等等。也正是基于这种“缺失性”情感的创作,陈平原认为许地山小说中诸多男女之情中“写的最好的是一种深沉的、痛苦的、永远失去的爱”[14]。因此,“五四”时期许地山的小说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视作一个“困爱者”的自白。
如果苦难是一个巨大的火药桶,那么“失妻”只不过是这个火药桶的一个引线。“失妻”的悲痛空前加深了许地山对苦难的感知能力,体味到“无情的东西变得慢,有情的东西变得快”[15],并引发了巨大的精神危机。《命命鸟》中敏明从有情走向无情,否定现实人生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许地山对“有情”产生巨大怀疑的过程。一方面,爱情的幻灭带来了对爱情的否定。无论是散文《爱底痛苦》《你为什么不来》《难解决的问题》《爱就是刑罚》《荼蘼》,诗歌《女人我很爱你》《看我》《情书》,还是小说《命命鸟》《换巢鸾凤》《商人妇》《黄昏后》《缀网劳蛛》《无法投递之邮件》,“爱情”都被视作人生痛苦的根源。另一方面,由爱情的无常和虚妄勾连起许地山对人生无常的深刻认知,以至于“我所看见底处处都是悲剧;我所感底事事都是痛苦”[16],并导致了虚无主义和“生本不乐”的人生立场①。可以说,许地山之所以执着地书写女性和爱情,其根本原因在于由失妻而来的独特体验,并非时代因素的激荡。而由缺失性创伤体验所引发的对现实人生的思考,更让许地山找到了文学创作的价值起点:“我自信我是有情人,虽不能知道爱情底神秘,却愿多多地描写爱情生活。我立愿尽此生;能写一篇爱情生活,便写一篇,能写十篇,便写十篇;能写百、千、亿、万篇,便写百、千、亿、万篇。立这志愿,为的是安慰一般互相误解,不明白的人。”[17]
而对“五四”新文学作家而言,缺失性创伤体验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既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也是一个多样性的问题。在“五四”现代话语内部,“体验”的差异导致了作家现代意识的发生、理解的差异。由失妻而来的缺失性创伤体验让许地山以不同于主流启蒙话语的方式理解“现代”,而“五四”其他作家“现代”立场的发生也可以从缺失性创伤体验身上寻找到脉络。首先,由男女、婚姻、夫妻、家庭的变动而来的缺失性创伤体验是影响“五四”作家创作的重要因素。郭沫若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写到:“因为在民国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的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18]同样,胡适的《尝试集》中也有相当的篇幅来源于在美国留学时的恋情。郁达夫的《茑萝行》几乎不加任何虚构地写出了与妻子孙荃之间的故事。徐志摩的诗歌更是情爱的直接表达。这都可以说明男女的情爱体验深刻地影响了“五四”文学创作的内容和形态。尤为重要的是,在“现代”的语境中,这种“情爱体验”已经带有鲜明的启蒙现代性的色彩。他们摆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或如鲁迅批判封建礼教,或如郁达夫大胆肯定和赞美人的合理欲望,或如许地山探求传统女性解放的可能性,或如冯沅君《卷葹》书写现代情爱的创伤等等。其次,对“五四”诸多作家而言,缺失性创伤体验是一种普遍性的创伤体验。对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而言,缺失性的创伤来自于爱情与现实的错位,也自然将这种无法弥补的生命创伤归咎于封建婚姻制度和封建礼教思想。郭沫若的性爱意识萌发极早,而且对自己的婚姻有着强烈的期待:“在未订婚之前他有他的梦想。梦想几时当如米兰的王子在飓风中的荒岛上遇着意味绝世的王姬;又当如撒喀逊劫后的英雄在决斗场中得着花王的眷爱。这样高级的称心的姻缘就算得不到,或当出以偶然,如在山谷中遇着一株幽兰,原野中遇着一株百合,那也可以娱心适意。”[19]而在与素未谋面的张琼华完婚之前,郭沫若从母亲和叔母的口中想象她是一个像三嫂一样在美貌、人品、修养、天足等方面完美的女性,可是掀开盖头,郭沫若看到的却是“一对露天的猩猩鼻孔”[20],理想婚姻被封建包办制度彻底毁了。这种缺失性创伤体验给郭沫若的心灵造成了“一种无限大的缺陷”[21],以至于“一生如果有应该要忏悔的事,这要算是最重大的一件”[22],甚至影响到其与安娜恋爱的心态②,也加重了其对封建婚姻制度和礼教的仇恨。鲁迅与朱安的婚姻使得鲁迅不仅在心理上陷入了深深的苦闷、压抑和悲痛,在身体上也通过冬天单薄的着衣来压制自己的欲望。同样,郁达夫则从情爱欲望无法满足的层面形成了缺失性心理创伤。正是在性的苦闷和躁动中,才发生了“窥浴”和嫖妓事件。这不可避免地给生性内向、胆小、脆弱、敏感的郁达夫留下了心灵的创伤,也直接导致了《沉沦》主人公的蹈海自杀。面对情感与理智、青春的激情与肉欲的苦闷的冲突,郁达夫对中国式的男女观念更加痛恨,并上升到东西方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国家的冲突。
由此,我们也就不奇怪为何“五四”众多的知识分子正是从反抗封建婚姻制度切入来反抗整个中国的文化传统,也不奇怪为何“爱情”及其“不满”成为了“五四”新文学初生之际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母题。由封建婚姻制度造成的缺失性创伤体验,让作家直接站在了以封建婚姻制度和封建礼教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面,并在异国现代社会中的现代体验中更加认识到了传统中国的落后和愚昧,也就自然而然以“全盘西化”的方式来对中国的思想、文化、社会、制度进行全面的革新。因此,缺失性创伤体验不仅是作家创作的力比多源泉,更是反传统的现代立场的起点。而爱情的创伤绝非缺失性创伤体验唯一的形式,再如生活的不幸、事业的失败、身体的残疾等等均有着缺失性创伤体验的身影。
二、缺失性创伤体验与许地山“现代”话语变形与想象
在缺失性创伤体验的驱动下,许地山“五四”时期的小说创作几乎都是“体验式创作”。如果“体验”是个体对外部社会情境的经验和感受,那么基于“体验”的写作则是对有关世界图景的一种积极的理解和创造,并因“体验”的差异导致了“五四”现代话语的多元歧义。透过许地山“五四”文学实践,可以看到缺失性创伤体验如何从情感层面上影响了作家主体对“现代”的理解、改造与接纳,进而如何影响到作家的文学创作实践。
第一,缺失性创伤体验的不同,以及创伤体验的感受方式不同,直接影响了“五四”作家个体独特的“现代性追求”。“精神产品的创造归根到底并不是观念的‘移植’而是创造主体自我生命的感受、体验与表达。”[23]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绝不等同于“西化”,中国的现代性也绝不是西方现代性的移植,而是作家基于不同的缺失性创伤体验对“现代”话语进行有选择的接纳和改造,也必然导致了不同的“现代”立场。以许地山为例,缺失性创伤体验对其现代立场的形成是通过对表象的“变形”实现的。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这就是在特定的心境中,为情感所歪曲、夸大和想象的产物。这说明当客观存在的表象被纳入情感经验的范畴,就要遵循情感的超时空、超逻辑的属性。因此,许地山的现代立场必然会因情感的策动而有所“变形”,并直接导致了与主流启蒙现代性的裂痕。反对“节烈”是“五四”启蒙话语的重要内容,而许地山的《黄昏后》则呈现出完全相悖的立场。当女儿希望关怀续弦时,关怀却反问“一个人能像禽兽一样,只有生前的恩爱,没有死后的情愫么”[24],“一个女人再醮人家要轻看她,一个男子续娶,难道不应当受轻视么”[25]?这恰恰证明了缺失性创伤体验让许地山的情感结构压制了认知结构而独立活动。这让他的心理情感得以释放的同时,也使得情感的洪流对主体的现代立场进行了扭曲和变形。因此,许地山早期的小说既是情感遇挫、创伤体验的产物,也是他人生哲学和生命意志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偶合、转移和再生。无独有偶,这种变形也同样展现在欧阳予倩的创作中。欧阳予倩起初的《泼妇》等剧作是支持恋爱自由和新式婚姻的。然而其后不久的《回家之后》则展现出了对知识分子陆治平与新式女性刘玛丽自由恋爱的批判,让新式女性的泼辣无礼、自私浅薄与传统女性的温柔敦厚、孝慈礼让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截然对立的转变恰恰是由于作者丧妹的缺失性创伤体验。其妹欧阳立颖被在被追求自由恋爱的丈夫遗弃后,忧郁至死,促使欧阳予倩更加深入地思考恋爱自由、离婚自由带来的深层次的社会问题。[26]这种浓郁的复古情怀的由来与许地山丧妻对现代立场的“变形”如出一辙。
第二,缺失性创伤体验在情感的驱动下,在文学创作中借助想象完成了另一种“现代”言说。在文学创作中,情感和想象往往是联袂而至的。正如休谟所言:“生动的情感通常伴随着生动的想象”[27]。许地山绝大多数的小说并不是基于现实“本事”的再创作,而是在异国风情的背景中虚构人物,在极具作家个人情感的想象中表达某种人生立场。《黄昏后》的故事被置于妻子去世十几年后,思念妻子的丈夫关怀通过给子女讲述两人的爱情故事的叙事中呈现的,甚至将其看作许地山在推演自己未来无妻生活,并展现自己的价值思考和现代立场也未尝不可。因此,对许地山来说,想象绝不是单纯作为一种创作手法而存在的,而是一种完成“现代”的想象和言说的方式。它不仅高度融合了许地山自身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世界,也让作者更自由地选择材料,更真实地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更充分地表达自己对复杂社会人生的深刻思考。而在具体的创作中,“情感规定着想象只应朝着一定的方向展开”[28]。许地山主要是通过“分想作用”来实现这种“定向”的。
朱光潜将“创造的想象”分为分想作用和联想作用。所谓分想作用就是“把某意象和它相关的意象分裂开,把它单独提出”[29]。即将某一个混整的情境中把与情感相协调的成分单独提取出来。如果没有“分想作用”,以往的经验就会全部复现在记忆之中。首先,“丧妻”的悲痛从另一个方面转化为许地山对往日幸福生活的回忆,并投射到对理想的婚姻生活和理想女性的塑造上,从而完成了传统女性的现代想象。“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意识的适应已不复存在(可能因为外界环境变得太困难了),那么,向前的自然运动就不再可能,这时力比多就退回到无意识当中,并最终成为寻求某种出路的超负荷的能量。这时候,无意识可能会在幻想的形式或者梦的征兆的形式下面注入到意识当中。”[30]丰富性体验与缺失性创伤体验之间产生的巨大落差,让许地山只能通过幻想实现自我抚慰,甚至还原现实世界中缺失的东西。体现在创作中,就是理想女性和美满婚姻的书写。对妻子之爱、女性之爱的渴望强化了他对“女性”崇高化的塑造,甚至达到一种夸张、极端的程度。有的学者将这种女性崇高化的塑造阐释为“女人在道德上高于男人,是对男尊女卑古训的大胆反叛”[31]。实际上,许地山对女性崇高化的书写与其被理解为反叛的象征,不如说是自己期望的爱、美、智的诠释,并借助“完美”女性,理想婚姻的想象来“教自己得着一点慰藉,同时也希望获得别人的同情”[32]。这也就决定了许地山笔下的女性绝不是叛逆的“娜拉”,而通过突出德性、善性、妻性、母性以及爱的追求,从而更加接近于中国传统女性的人格要求。这就呈现出与“五四”启蒙主义和女性解放话语相悖的现代立场。
其次,许地山笔下的理想爱情是“灵肉一元”的完满纯美的形态,而不是纵欲享乐的工具,而由爱情产生的痛苦是人生的常态,而不是反传统的理由。在许地山小说角色的设定和人物关系中,不仅“爱情”大多是呈现一种不完美的形态,而且女性角色也呈现出一种“在场”的“缺失”,同时男性成为了“怨夫”。表面上,无论是作为妻子还是作为母亲,女性都是“在场”的状态,然而这些女性角色大量的是以亡妻(《黄昏后》《海角底孤星》)、失联(《给贞蕤》《给憬然三姑》《复真龄》)、被驱逐(《缀网劳蛛》)、断交(《给琰光》)、神化(《海世间》)、出家(《答劳云》)的状态来呈现。即使女性出现在文本中,男性与女性的性格特征也呈现着明显的错位。女性如尚洁、惜官、春桃都是智性、刚毅、沉着的代表,而男性则以“困爱者”的姿态显得柔弱、幽怨、凄惶,如《无法投递之邮件》中的男性群像。而在这背后,是许地山坚持不懈地追求爱情形态的永恒、完满、灵肉统一。因此,对许地山来说,“爱情”自有其真义和价值,给人带来痛苦的同时也代表着一种幸福的人生追求,而不仅是反传统、反礼教的工具。因此,缺失性创伤体验使许地山沉浸在对美满爱情的渴望和书写中,而削弱了“爱情”的启蒙意义,从而与“五四”的时代主旋律分裂开来。
再次,这种“分想作用”深刻地影响到了许地山对文学内容的选择,使得许地山的创作以苦难书写汇入“人生派”的同时,更表现出探索人生终极价值和意义的神性追求。“失妻”的症候使得爱情和苦难成为许地山矢志不渝的创作主题,也由此走向了对人生意义的追问,以及如何处理自我与现实生活、苦难关系的探讨。而对苦难的书写,实际上已经让许地山的缺失性创伤体验超越了自身的个体性情感缺失,进而感悟到时代的、人类的情感缺失。因此,他的小说创作,以及对人生意义和终极价值的苦苦追索,才显现出超越时代的内容。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虽然许地山主情主义的文学带有极大的主观性、情绪性、宗教性,但也与“为人生”的时代旋律产生了同主题变奏。这也是许地山的文学立场和现代立场与“五四”有所差异,但又并未完全脱离“五四”时代主题的原因。
由此可见,缺失性创伤体验对作家现代价值立场的重新整合,以及对文学文本形塑有着重要影响。它不仅打破了作家的精神平衡,从而在文本中表达出一种痛苦、紧张、焦虑、抑郁、狂躁、渴求等反常的情绪,甚至达到一种病态、变态的程度,还在相当的程度上引起主题人生观、价值立场、性格发展和人生走向,从而极大地影响了作家的文学行为和文本形态。这也使得从缺失性创伤体验这个层面上来重新理解“五四”作家、“五四”文学显得尤为重要。同时,通过这种个体微观史的研究,“现代”话语也因缺失性创伤体验的差异和强度展现出巨大的分野,而多元的、个人化的现代立场又共同建构了“五四”现代话语多元歧义的总体格局。
三、“创伤—治疗”与许地山现代立场及创作的转向
从二十年代初期的小说集《缀网劳蛛》到末期的小说集《危巢坠简》,以及30年代在香港主持探讨国粹与国学,提倡拉丁文字等文化革新,许地山在文学上由宗教色彩转向批判现实主义,在现代立场上也重回了“五四”文化启蒙主义。以往常常将这种转变视为大革命的外部环境对作家主体思想的深刻影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作为创伤应激的另一面,一种“治疗”机制借助文学使许地山重获精神平衡。文学的治疗功能并不鲜见,但却常常为研究者所忽视。文学作为一种慰情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是作家不满于现实世界,并通过想象来超越现实,创造审美乌托邦的过程。正如许地山所言:“自愁苦的胸襟蕴怀着无尽情与无尽意,不得不写出来,教自己得着一点慰藉,同时也希望获得别人的同情。”[33]就此而言,许地山“五四”时期的文学实践带有典型的自我疗救的性质。而这也是“五四”时期相当一部分文学作品表现出来的特质。
第一,文学的“二重性”及其成因。茅盾指出许地山的小说具有人生观和形式“二重性”的特征。在人生观上,“一方面是积极的昂扬意识的表征(这是‘五四’初期的),另一方面却又是消极的退婴意识(这是他创作当时普遍于知识界的)”[34]。许地山文学作品的“二重性”甚至是悖论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其成因并不是“五四”时代情绪的映射,而是许地山在通过文学寻求精神自赎的产物。
创作主体的自我治疗大都肇始于由挫折感带来的创伤体验。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中认为:“当个人面对一个他无法适当应付的问题时,他表示他绝对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此时出现的便是自卑情结。”[35]当许地山遭到丧妻的打击,一旦意识到命运和苦难的不可抗性,则深感个人的弱小,以及抗争的无力,从而出现了自卑情结。这种对命运的强力和个人的无力的深刻体味和认知,让他不会与客观世界为敌。因此尚洁面对命运的苦难表现出的更多的是一种豁达和接受。一方面,她承认生命的残缺和苦难的无可逃避,因此“危险不是顾虑所能闪避的”[36],另一方面,她所能做的只是接受苦难的现实,“所有的网都是自己组织得来的,或完或缺,只能听其自然罢了”[37]。从深层的心理动因来看,正是面对现实人生的自卑感与佛教的“虚空观”遇合,才让许地山的小说呈现出浓重的宿命论、怀疑论和虚无主义色彩。这种由创伤带来的自卑在中国现代作家的精神状态中也普遍存在。如旧式婚姻给鲁迅带来的创伤使其此后面对爱情极为矛盾、犹豫、踟蹰:“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人”[38]。因此胡尹强认为《野草》中《影的告别》和《求乞者》便表现了这种在爱情中的自卑感[39]。
而另一方面,过度强调许地山的虚无主义色彩,认为“这种悲观消极的思想,使他看不到摆脱苦难的希望,更看不到人生还有积极光明的一面”[40]是偏颇的。正是在“治疗”机制的驱动下,许地山努力在避免与命运正面冲突的情况下,提出一套新的人生观体系,来重新处理个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个人面对命运苦难的姿态。因此,“蛛网哲学”的核心不仅是坦然地接受人生的苦难,更是在一次次的跌倒中,一次次的爬起。就像蜘蛛结网,“它不晓得什么时候会破。和怎样破法。一旦破了,它还暂时安安然然地藏起来;等有机会再结一个好的”[41]。这让其小说在豁达与悲观中蕴含了奋起的力量。正如惜官所言:“不但不愿死,而且要留着这条命往前瞧瞧我底命到底是怎样的。”[42]这种直面苦难、玩味苦难、欣赏苦难,甚至在与苦难的搏斗中获得快感的姿态,实际上也是许地山在为自己的人生树立信念。
这种避免与命运对抗,但又在苦难中毅然前行的二重性使得许地山并不像鲁迅、庐隐等知识分子拷问苦难背后的社会历史原因。比如在“五四”中同样是对苦难的表现,庐隐用“究竟知识误我?我误知识”[43]来追问觉醒中的女性深陷痛苦泥潭的原因。鲁迅会追问国家落后、人民愚昧、社会黑暗背后的深层动因。但是,许地山只思考作为人在无可避免的苦难面前如何自处,如何处理自我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当这种超越性的思考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呈现出来,文学的治疗功效也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因此,许地山人生观的二重性并不是偶然,而是深陷在精神困境与自卑情结中寻求自我救赎的必然。而文学写作的过程,也就成了许地山逐渐确立自己的生命哲学,实现创伤抚慰和精神治疗的过程。
第二,走向宗教的根本动因。一直以来,宗教信仰对许地山而言似乎是一个毋庸多言和不言自明的精神追求。但是,宗教对许地山来说究竟是一种理性的追求,还是面对人生苦难和精神危机时的情感激动?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仅仅看到文学表现出来的宗教表象,而应当尽可能地深入到文本背后许地山复杂的精神世界中去。总体来说,抚慰人精神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在虚拟的世界中消解它,二是在精神的世界中超越它。许地山通过小说对苦难的书写及其反抗姿态的形成可以视为第一种。但是如果这个崭新的人生哲学体系内部没有一个强大的终极价值作为内核,这种救赎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实际上,《命命鸟》中敏明的心路历程正映照着许地山的思想变化。敏明看透人生无常,转而向宗教寻求终极价值意义的过程,正是许地山投向宗教怀抱的过程。这是一种典型的“归依体验”。所谓“归依”就是作家精神探索、痛苦抗争之后为自己找到的精神家园。而宗教皈依是“归依”的一种重要方式。“文艺家的宗教皈依体验常常是以文艺家的人生坎坷和对现实人生的失望为心理基础的。”[44]而失妻的创伤为他走向宗教寻求自我精神的救赎提供了直接的动机。早年的许地山却并不认同母亲所笃信的佛教。据其弟许赞乔回忆,许地山“少年时代的思想,嘲弄攻击佛教迷信的态度”[45],甚至被其母亲斥责为“吃教仔”“异教徒”。成年后,许地山受到各种宗教的熏染,但是多元的宗教影响让他更多的是抱着一种研究的态度来致力于宗教比较学。③而在“五四”前后,无论是作为燕京大学的学生代表参加“五四”运动的游行,还是在《新社会》旬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启蒙主义仍旧是其基本立场。失妻之后,许地山的思想发生了彻底变化。此时,宗教对许地山来说已经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对象,更多的是从宗教中汲取对抗苦难以实现精神超越和自我超脱的力量。呈现创作中即人物借助宗教,或者以一种宗教的态度实现了人生的开悟,并摆脱了现实的痛苦。因此,在1923年发表的《我们要什么样的宗教》也是从人生角度上接受宗教的:“人生免不了有理想,欲望,病害,故此要向上寻求安康,宗教的感情,于是乎起。可以见宗教的本体,是人生普遍地需要。”[46]从此,许地山不仅转向宗教寻求精神的超越和解脱,更直接影响到宗教的情感、态度、信仰与其新文学事件的碰撞,为“五四”新文学提供了一抹与众不同的色彩。
宗教作为许地山文学创作的一个巨大的存在,固然构成其小说的独特之处,但是也作为一个巨大的阴影遮蔽了问题的本质。众多学者致力于儒、释、道、耶的宗教思想在文学中的呈现,这就实际上将作家、文学与宗教的因果关系本末倒置了。许地山绝不是为了表现宗教情感、宗教意识而创作文学作品,而是通过文学这个“有意味的形式”,借助宗教来为自己心理情感的洪流寻找一个释放的突破口。宗教只是许地山重新审视人生问题,并为自己精神危机寻找出路的手段和工具。因此,无论是基督教、佛教、道教,以及中国儒家传统思想,任何能够有助于解决精神危机的教义、思想,对许地山来说都是可取的,这也是许地山笔下宗教冗杂、思想冗杂但却又能够“毫不牵强地融成一片”[47]的重要原因。
第三,精神自救与许地山的创作转向。从1921年开始创作并发表《命命鸟》《商人妇》《换巢鸾凤》《黄昏后》,一直到1922年发表《缀网劳蛛》,许地山对爱情的态度和书写方式是动态变化的。《命命鸟》中敏明的自尽连同爱情、人生一起埋葬,可以说是失妻症候和情绪最为突出和极端的表现。一直到《黄昏后》这种对爱情的质疑始终存在。《商人妇》情感的热度已经稍有冷却,开始探讨人应当如何审视苦难。直到《缀网劳蛛》中提出的“蛛网哲学”才标志着许地山真正确立起了直面苦难、对抗命运的基本姿态。许地山由此借助文学创作重新确立了自己的生命哲学、精神坐标和价值坐标,也实现了自我精神救赎的成功。渐渐的,“失妻”的痛感力度也在渐渐趋于冷静。在1927年发表的诗歌《我底病人》中,同样是表达爱情的虚妄,但许地山却以一种极其冷静、甚至残酷的语气说到:“等你发见你底‘蜜’,/已是迟而又迟了!/爱者容易变成香渍尸,/不介意,便要向古沙里找。”[48]当许地山以如此冷静、坦然的态度说出对“爱”的认知之时,已经多么地从容。与此同时,人物的性格也趋向于独立坚强。茅盾认为从惜官、尚洁在“随着‘命运’拨弄”中“发明她们自慰的哲学”,却“没有一定的目标”,到“趾麟是有一个目标的,到了《春桃》,那简直是要用自己的意志去支配‘命运’了”[49]。小说中人物性格的转变,间接地反映着作家主体精神和现代立场的变化。
许地山曾立愿“尽此生;能写一篇爱情生活,便写一篇,能写十篇,便写十篇;能写百、千、亿、万篇,便写百、千、亿、万篇”[50]的志向。然而,从二十年代末开始,许地山的创作却从爱情题材转向了批判现实的方向。以往的研究将这种变化归因于时代风潮和社会矛盾对许地山影响。如宋益乔认为这是“在阶级矛盾空前尖锐激烈的年代”中,“随着时代的发展,他的思想也日渐进步,佛教思想的影响日渐消弱。进步的政治立场使他不可能再超然于大是大非之外”[51]。王文英、朱立元认为“他前期的人道主义、平民主义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向积极方面发展了”[52]。个人的转变不可排除时代的影响。但许地山的独特性在于,自我心理的净化和治愈带来的情感流变远胜于时代的影响。一方面,许地山避开了整个二十年代中国政坛和文坛最具风云激荡的年代。当国内大革命的风潮以及与之相伴而来的“无产阶级文学”“革命文学”兴起之时,许地山正在美国、英国留学,潜心于宗教研究。另一方面,当无产阶级文学、革命文学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许地山既无落潮时知识分子的彷徨,也没有革命文学的阶级立场和革命激情,甚至反对激进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而更贴近“五四”批判现实和文化改造的立场和态度。因此,与其说这是外在社会环境对许地山的改变,不如说是许地山精神的自我救赎获得了成功的结果。
缺失性创伤体验实际上是打开许地山的心灵世界和文学创作的一把钥匙。从“创伤”和“体验”的角度,清晰地看到了他理解、改造、接纳“现代”话语,以及现代立场转变的过程。而对更多的“五四”作家知识分子来说,由不同的人生体验和心理需求形成的经验系统也成为他们理解、改造、接受“现代”的出发点。而缺失性创伤体验的差异和强度的不同,也必然会导致对“现代”的理解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甚至相互拮抗。由此,我们不仅可以理解为何缺失性创伤体验构成了“五四”作家现代追求发生的重要内驱力,更可以发现缺失性创伤体验如何通过变形和想象的方式影响了“五四”作家知识分子不同的现代价值立场的生成和独特的文本形态的形塑,并最终共同建构了“五四”现代话语多元歧义的总体格局。
注释:
①许地山在《空山灵雨·弁言》中写到:“生本不乐,能够使人觉得稍微安适的,只有躺在床上那几小时,但要在那短促的时间中希冀极乐,也是不可能的事。”(许地山.《空山灵雨》弁言[J].小说月报,1922,13(4).)
②郭沫若在写给田汉的信中因“破坏了恋爱的神圣”而自责,但并未明言何为破坏。通过田汉的复信可知郭沫若是因封建包办婚姻与自由恋爱与安娜同居的“重婚”而心理自责,也即宗白华所言“乘一时感情,尤易做出越轨的事。”(宗白华.三叶集[A].见:郭沫若全集(第1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32.)田汉在复信中如此开导郭沫若:“我并非要引Goethe事来曲谅你的罪,总之觉得这是人生一件很难解决的问题罢!若照我彻底的主张,这件事是很自然的,即算从前结了婚,——照你说是你父母给你结的婚——到了你Fall in love with another woman的时候,对于前此结婚的女人,总算没有恋爱,至少也得说是恋爱稀薄了,于是结婚的意义便不完全,否!便不算是结婚了,于是乎尽可以‘You go your way we go ours’。”(田汉.三叶集[A].见:郭沫若全集(第1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59.)
③许地山第二任妻子周俟松在给许地山编著的年谱写到:1916年 丁巳 民国六年 25岁 在福建漳州华英中学校任教,月薪60元。曾加入闽南伦敦会(基督教会),渐不满其教义,开始有志于宗教比教学。(周俟松编:《许地山年谱》,见:周俟松,杜汝淼编.许地山研究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4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