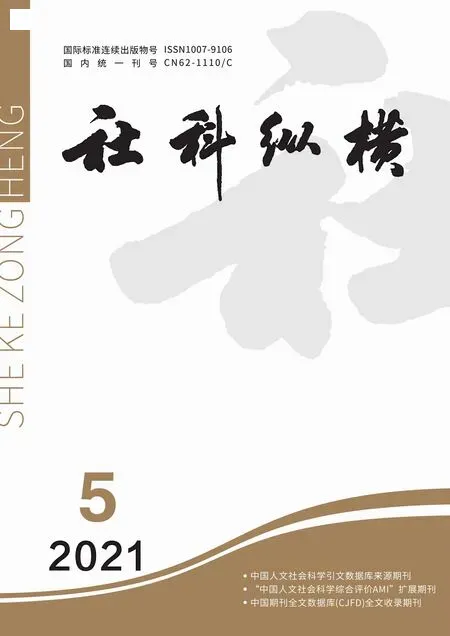牵引与整合:论乡村人际关系网络与西北传统乡村社会外出流动人口之间的逻辑关系
2021-01-29马小华
马小华
(甘肃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甘肃 兰州730070)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表现出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社会结构的调整以及社会总体结构的变动。具体到中国社会人口层面,表现出来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大量流动人口的出现。流动人口一方面源自不同区域之间在经济和其他层面的交流互动,另一方面主要源自大量乡村外出流动人口。由于城乡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大量的乡村人口流入城市寻找发展的机会,也就是所谓“打工一族”的出现,其中较为典型的群体就是农民工。大量乡村人口流入城市,无论对于流入地的城市来说,还是对于流出地的乡村来说,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乡村社会由于大量劳动力的外流导致了诸如劳动力不足、乡村社会秩序整合度下降、乡村社会整体结构发生变动等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外来流动人口的到来,使得城市管理、城市资源、城市社会结构等方面也受到巨大的影响和挑战。
西北传统乡村社会作为中国整个乡村社会体系的一员,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中同样也出现了大量乡村人口外出、乡村社会结构体系面临种种挑战的问题。来到城市社会的西北传统乡村社会这个个体,在城市生活中也面临着种种挑战和问题,城市流动人口聚居地同样也面临着种种挑战和问题。那么,在这种挑战和问题之下,作为西北社会中强有力的社会整合力量的乡村人际关系网络,对于西北传统乡村社会流动人口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力?而这种作用力又是如何影响整个西北传统乡村社会和城市流动人口聚居区的?这两个问题成为本文所讨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乡村社会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乡村社会在很多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具体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分化严重
随着社会转型效应的出现,中国乡村社会中社会分化趋强无疑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事情,学者文军等指出:“与社会结构的构成相适应,社会分化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是社会异质性增加,即群体的类别增多;二是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即社会群体间的差距拉大。”[1]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分化恰恰体现出了这种情况。一方面,原有的乡村社会中社会个体大都是从事种植业,群体异质性程度较低,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乡村社会中大量外出流动人口的出现,使得乡村社会中社会个体开始从事不同的职业,从而使得乡村社会中社会个体的异质性不断增强。另一方面,随着原有同质性的职业构成模式的打破,乡村社会中不同个体之间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的差距在逐渐拉大,从而使得乡村社会个体在各种资源的占有方面表现出了不同的程度,这也体现出了社会转型期乡村社会个体之间差距在不断地拉大之中,乡村社会中两极分化现象也逐渐开始呈现出来。
乡村社会的分化打破乡村社会原有的较为同质性的社会结构体系,使得乡村社会个体在不同的轨道上发展与突破,这也使得乡村社会出现不同利益表达群体,在这样不同利益诉求的现实背景下,传统乡村社会中对乡村社会的整体调整和整合体系开始面临挑战,而乡村社会似乎并没有相应的应对机制。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面对今天的快速变革,我最为恐惧的是,在乡村,人们还没有足够的准备去创造出新的、可替代的东西来顺利地取代正在消失的传统。”[2]5因此,从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分化的角度来说,乡村社会急需在社会转型期内生出相对社会分化的应对机制来,否则处在不断分化的乡村社会将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
(二)社会记忆弱化
学者贺雪峰指出:“社区记忆是一个重要的概念。社区记忆的对立面是社区不记忆,也即社区本身有无历史的问题。构成对村庄性质影响的是村庄活的历史而非死历史,是村庄过去的生活为村庄今天的生活留下的影响力。”[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社会转型期我们考察乡村社会记忆的时候,重点要去考察传统的乡村社会文化对于当前社会中的影响力,以及传统乡村社会中的民间自我治理体系是否在当前的乡村社会中得以延续等问题。
具体到社会转型期的乡村社会来看,由于社会转型期乡村社会分化趋势不断加大,乡村社会记忆不断趋弱。这种减弱一方面由于乡村社会中出现的大量外出流动人口,使得乡村社会个体开始逐渐脱离一些乡村公共活动,从而使乡村社会记忆开始逐渐减弱。另一方面,随着大量外出流动人口的出现,留守在乡村社会中的个体难以有效担负起延续乡村社会原有传统文化的重担,当然这里面的问题是随着市场经济对乡村社会个体价值观念的不断冲击,使得当前的乡村社会难以找到延续传统乡村文化的新生力量来,因为社会文化和大量流动人口的出现往往造成了传统乡村社会文化继承出现断代的问题。
(三)社会关联度降低
学者金太军指出:“所谓村庄社会关联,是指村庄内村民与村民之间各种具体关系的总和,它描述的是处于事件中的任何一个具体的村民在应对事件可以调用关系的能力。”[4]24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关联度主要考察的是乡村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关系强度,在社会关联度高的乡村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处于较强的状态,反之,社会关联度较低的乡村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处于较弱的状态。社会关联度主要用来分析社会转型期乡村社会内部个体之间各种关系的结构网络。
具体到当前的乡村社会来看,由于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使得乡村社会中大量劳动力外出,乡村社会原有的结构体系处于不断分化之中,使得原本处于强社会关联度的乡村社会开始面临社会关联度不断降低的挑战。此外,随着乡村社会记忆的趋弱,乡村社会中公共活动难以有效地维系起整个乡村社会的关系网络,加之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不断遭受外界价值理念,尤其是城市原子化、个体化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从而使乡村社会中个体的各种关系网络处于不断趋弱的状态,同时由于乡村社会个体越来越难以从原有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取相应的利益,他们对于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的依赖性越来越弱,这使得当前乡村社会关联度越来越低。
二、处于社会转型期的西北传统乡村社会
(一)从社会分化的角度来看
从实地调查情况来看,西北传统乡村社会的社会分化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以及性别上的差异性和行业上的集中性等特征。随着当前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乡村人口涌入城市寻求发展,西北传统乡村社会也不例外,但从时间上来看具有滞后性,尤其是西北偏远的乡村社会中这种情况尤为明显。从性别的角度来看,女性外出流动人口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时间方面,都弱于男性,这与西北传统乡村社会中长期以来形成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观念有着较大的关系。受到传统文化影响,西北传统乡村社会的外出流动人口的职业选择相对集中。
(二)从社会记忆的角度来看
西北传统乡村社会记忆从总体上来看,也处在不断趋弱的状态之中,但与整个中国乡村社会的情况相比,却有着其自身的特征,即西北传统乡村社会记忆并没有因为现代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而快速趋弱,反而表现出了一定的顽强性。西北传统乡村社会在社会记忆上面所表现出来的这种顽强性,主要体现在虽然在西北传统乡村社会中,年轻一代的西北传统乡村社会个体对于传统风俗习惯的坚持并不像老一辈那样坚定,但是由于西北传统乡村社会强大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使得年轻一代的西北乡村社会个体,仍然对自身继承传统文化方面表现出与整个中国乡村社会不一样的一面。当然,在分析西北传统乡村社会记忆的时候,绝对不能忽视现代化的进程带给西北传统乡村社会的影响,以及在整个城市化过程中西北传统乡村社会个体面对城市化和现代化所带来的挑战时,体现出的种种煎熬与徘徊。
(三)从社会关联度的角度来看
学者赵旭东指出:“结构可以带来一种秩序,这种秩序依靠一种意识形态而得到稳固,并经过长久时间的运作实施而使其极为稳固。这种稳固的也容易因为抽掉一些核心的要素而变得异常的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是秩序的不稳定,也必然是社会的不稳定。”[2]104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理论上,西北传统乡村社会在社会转型期由于大量外出流动人口的出现,社会分化的加剧,社会记忆的减弱而处于一种社会关联度较低的状态。然而,在实地调查中我们发现,在社会转型西北传统乡村社会的社会关联度虽有下降,但并没有我们所推理的那样低。
学者金太军将村庄关联划分为两种,即:“一是经济关联、文化关联和组织关联,一是传统关联和现代关联。”[4]249从经济关联度来看,西北传统乡村社会外出流动人口的职业选择存在集中性的特征,而这一特性使得西北传统乡村社会个体之间势必要保持较高的关联度。从文化关联度来看,由于传统文化的作用力,使得西北传统乡村社会个体在文化关联度方面体现出难以割舍的关联性。从组织关联度来看,西北传统乡村社会个体在现代化进程中,仍旧坚守着乡村人际关系网络的群体组织体系,并没有呈现出颗粒状的个体状态。
三、乡村人际关系网络对西北传统乡村社会外出流动人口的吸引力与牵引力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中国乡村社会原有的社会结构体系受到瓦解而呈现出社会分化的态势,在这过程中中国乡村社会的社区记忆逐渐减弱,同时乡村社会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关联度也不断趋弱。而西北传统乡村社会却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的表现主要源自西北传统乡村社会中以传统文化为核心而形成的乡村人际关系网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城市中乡村人际关系网络对于西北传统乡村社会外出流动人口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对于从西北传统乡村社会涌入城市的社会个体来说,由于受到自身传统文化的影响,在选择外出流动地时一般倾向于西北乡村社会个体聚居的城市,在城市生活的过程中也倾向于选择城市中的西北传统乡村社会个体聚居区作为他们生活的场所,在职业选择方面,倾向于选择人员较为集中的餐饮业及个体服务业等。聚居对于每一个外出流动的社会个体而言,无论是外界还是内心都是一种寻求安全感与归属感的表现。在城市聚居的环境中,外出流动的社会个体,才能更好地寻找到从乡村到城市这种跳跃式生活的过渡地带。
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分析,西北传统乡村社会外出流动人口在外出流动中的这种选择体现他们对于生理和安全需要的满足。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可以发现乡村人际关系网络对于乡村社会外出流动个体的强大的吸引力,主要来自社会个体对自身文化上的满足,因为只有在城市的生活中融入原有的乡村人际关系网络,才能保持他们自身所负载的文化得以维持并受到相应的保护。西北乡村外出流动人口在城市中这种聚居行为主要表现出对于自身“文化安全”的考虑,因为来到城市生活的他们,一方面为了生活,要不断接受城市各种现代生活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为了自身文化安全,他们也要不断通过一种群体组织来维系和保护自身所负载的传统文化不受到现代化的侵蚀。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加入原有的乡村人际关系网络的做法,无疑成了西北传统乡村社会外出流动人口的寻找“文化避难所”的最佳选择。
(二)乡村中乡村人际关系网络对于西北传统乡村社会外出流动人口有着强大牵引力
一般来说乡村社会外出流动人口与乡村社会之间联系纽带主要依靠家庭维系,而乡村社会本身或者乡村社会内部的组织机构对乡村社会外出流动人口的牵引力并不强,但对于西北传统乡村社会的外出流动社会个体来说,流出地对他们的牵引除了家庭这个纽带之外,还有乡村人际关系网络对他们强有力的牵引力。这种牵引力主要表现在作为乡村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一员,西北传统乡村社会外出流动人口需要不断通过各种“投入”,来维持其作为人际关系网络成员的资格,并在这个人际关系网络中享受“回馈”,无论是“投入”还是“回馈”都会使得外出流动的西北传统乡村社会个体需要不断与原有乡村人际关系网络保持密切的联系,才能维持其作为这个网络成员的资格。
从西北传统乡村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来分析乡村人际关系网络对于外出流动人口的这种牵引力,体现出乡村人际关系网络内部人际关系的运行机制,即加入某个乡村人际关系网络之中,能够获得相应的权利,但必须付出相应的义务,而且只有完成这些相应的义务,才能在乡村人际关系网络内部获得相应的人际关系网络的支持,否则就要被整个乡村人际关系网络内部的人际关系网络排斥。从乡村社会秩序的角度来看,“村庄秩序就是指村庄得以聚集在一起的方式,而且是生成性和建构性相结合的一种社会秩序,也即是个人之间自发生成的结果,也是人理性选择的结果,是两种行动相互交织而形成的”[5]。也就是说乡村人际关系网络对于外出流动社会个体的牵引力,主要表现了西北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生成的内在机制,即西北传统乡村社会个体需要乡村人际关系网络来维系自身的关系网络,同时通过完成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来达到维系这种关系网络的目的。
四、乡村人际关系网络对西北传统乡村社会外出流动人口的整合力
(一)城市中人际关系网络对于外出流动人口的强大整合力
城市中乡村人际关系网络对于外出流动人口的整合力主要体现在,乡村人际关系网络将外出流动人口很好地纳入整个乡村人际关系网络的体系之中,从而将西北传统乡村社会外出流动社会个体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社会整合是针对社会分化产生的异质性超越原有的规范而提出来的,是指通过各种方式,将社会结构不同的构成要素、互动关系及其功能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从而提高整个人类社会一体化程度的过程。”[1]具体来看,乡村人际关系网络对于外出流动人口的整合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主要是通过各种传统文化活动等形式,例如通过花儿、秦腔、剪纸、皮影等传统文化将外出流动人口纳入人际关系网络体系之中。另一方面主要是通过各种世俗活动,例如针对外出流动人口的各种技能培训、婚姻介绍、信息传递等方式,使得外出流动人口能够在人际关系网络内部获得生活资源,从而能够在城市的生活中更为有利地获得相应的生活资本。
(二)乡村中人际关系网络对于外出流动人口的强大整合力
如果说城市是西北传统乡村社会外出流动人口的“前沿阵地”,那么乡村就是西北传统乡村社会外出流动人口的“后防总站”,外出流动人口能够在城市中较为稳定的工作与生活,离不开乡村这个“后防总站”稳定的支持。只有流出地的稳定,以及西北传统乡村社会中留守群体的稳定,才能为西北传统乡村社会外出流动人口提供强大的支持,而乡村人际关系网络恰恰在这一方面发挥了强有力的整合力。具体来看乡村人际关系网络对西北传统乡村社会留守群体的整合力是通过传统与世俗两个方面来实现的。传统方面的整合主要体现在通过传统文化,例如乡村庙会、乡村社火、乡村其他的文化形式等方面,使得西北传统乡村社会能够在传统文化的引领下有序运行。世俗方面的整合主要体现在人际关系网络对乡村各种公共服务所发挥的功能来达到整合留守群体的目的,例如留守孤寡老年人以及残疾人通过乡村人际关系网络获得相应的帮扶、留守儿童获得相应的看护、乡村公共设施获得维护等等,此外,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乡村中,国家制定的法还不能完全替代乡规民约来发挥作用,尤其是在民族地区。在这种氛围下,协调和规范人际关系的规则更多地依靠非正式制度也就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6]316。西北传统乡村社会中,社会个体协调和解决乡村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冲突与纠纷也大都是利用乡村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传统权威力量来实现的,这也是乡村人际关系网络对于西北传统乡村社会强大整合力的体现。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城市化带给乡村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体系开始分化甚至瓦解,乡村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在逐渐演变成一盘散沙的状态。而随着乡村社会结构体系的分化,乡村社会记忆和社会关联度也开始趋弱,乡村社会运行秩序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而变得困境重重。相比较而言,西北传统乡村社会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其社会结构体系同样也受到了城市化的影响,但由于乡村人际关系网络通过对于外出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和牵引力,从而催生了外出流动人口与乡村社会“形离而神不离”的关系模式。此外,乡村人际关系网络通过传说和世俗两个方面,将乡村外出流动人口强有力的整合起来,从而保障西北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有序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