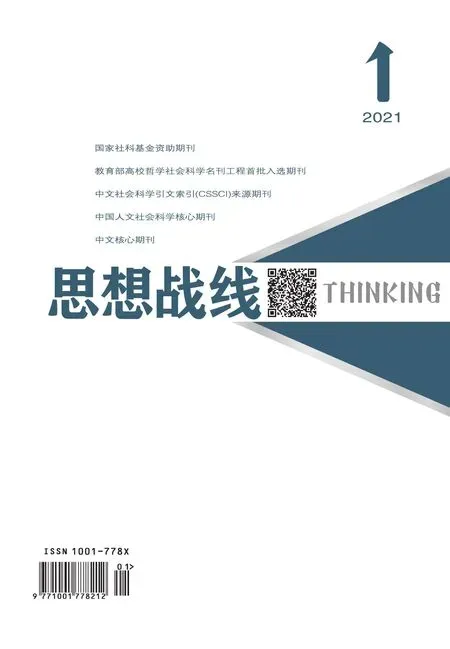生育利益私法保护的权利基础与规制范式
2021-01-28王歌雅张小余
王歌雅,张小余
生育,从微观层面讲,是实现个体自我繁殖及家族长久延续的前提;从宏观层面讲,是整个人类社会人口再生产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1)张作华,徐小娟:《生育权的性别冲突与男性生育权的实现》,《法律科学》2007年第2期。由此,对生育关系所体现的生育利益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生育利益代表着人们对生育的客观需求,而生育权是将生育利益上升为法律层面的权利表现。(2)王 卫:《论我国生育权公法调节的范围和边界》,《人民论坛》2020年第10期。现今有关生育利益与生育权的研究多侧重于理论层面的静态分析,较少涉及实证案件的类型化研究。当前,私法领域的生育利益纠纷逐渐增多,但立法规制的规范疏漏及司法裁判的差异保护,使得生育主体的生育利益无法得到全面维护。要解决好私法层面的生育利益纠纷与冲突,需立足于我国的司法实践,划分案件类型、提炼审判焦点、明晰裁判问题,明确以权利的形式加大对生育利益的保护,从而实现权利保护有据、利益救济全面的规制目标。
一、生育利益私法保护的实践样态:司法裁判类型化的视角
任何理论研究均无法脱离实践而独存,因此,在进行理论分析的同时,也要立足于司法实践,探究生育利益私法保护的现存问题及改进方向。人民法院在处理生育利益纠纷时,往往会根据当事人的不同诉请,基于不同的案由立案处理,而在不同案由的诉讼中,法院对生育利益保护的方式既有共性,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由此需要进行类型化的分析。以下将结合我国司法实践,按照生育利益纠纷争议主体的不同,从微观层面分别展现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组织之间生育利益私法保护的实践样态。
(一)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纠纷诉请
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生育利益纠纷,按照纠纷发生领域又可细分为三大类型,即婚姻家庭纠纷、同居纠纷以及事故流产纠纷,这三类纠纷中均存在对生育利益诉请保护的情形。
1.婚姻家庭纠纷影响生育利益案件
实践中,多数生育利益纠纷均发生于婚姻家庭领域,这是因为生育主要存在于婚姻关系下的夫妻间。这类案件主要表现为:案情1,因一方在主观意志上不想生育,影响到对方生育利益的实现;(3)如“李某诉王某离婚纠纷案”,高唐县人民法院(2014)高民一初字第1145号,北大法宝,https://www.pkulaw.com/pfnl/a25051f3312b07f348bbc7fe6fc29a5fc69159582e6ffb90bdfb.html?keyword=%E9%AB%98%E6%B0%91%E4%B8%80%E5%88%9D%E5%AD%97%E7%AC%AC1145%E5%8F%B7。下文中所用案例除有专门标注的外,均来自于北大法宝。案情2,因一方有疾病不能生育,影响到对方生育利益的实现;(4)如“佘某某诉苏某某离婚纠纷案”,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2014)潮湘法民一初字第502号。案情3,因妻子擅自堕胎或生育,影响到丈夫生育利益的实现;(5)如“王某甲诉王某乙离婚纠纷案”,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2014)丰民初字第2092号。案情4,因丈夫强迫妻子堕胎或生育,影响到妻子生育利益的实现;(6)如“徐某诉杨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石民二终字第00919号。案情5,因生育名额被占用,影响到生育利益的实现;(7)如“赵某诉曹某离婚纠纷案”,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2015)溧民初字第775号。案情6,生育非亲生子,影响到对方生育利益的实现;(8)如“赵某诉张某离婚后损害责任纠纷案”,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青民五终字第1962号。案情7,生育协议的签订,影响到一方生育利益的实现。(9)如“曾丽丽诉郭燕华离婚纠纷案”,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佛中法民一终字第490号。
针对案情1~5,从判决来看,对于离婚纠纷案,法院主要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9条,或者认为没有法律依据而认定未侵犯生育权,也未支持当事人的赔偿诉请,再结合案情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以判决是否准许离婚;对于离婚后的财产纠纷案,其实是将生育权受损的赔偿诉请在离婚后提出,法院亦未支持赔偿诉请;对于当事人提起的人格权纠纷案,法院一般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下称《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认为侵犯生育权的诉请并不成立;对于婚姻无效案,无法生育尚不属于婚姻无效情形,法院并未支持婚姻无效主张;对于抚养纠纷案,即便子女的出生不符合对方的生育意愿,但基于亲子关系的存续,仍需承担抚养义务。
对于案情6,司法实践中丈夫针对非亲生子的出生,均认为自己的生育权受到损害,经依法举证,如确认婚生子的确非男方亲生子,有的法院会直接认定丈夫的一般人格权(10)如“王某甲诉俞某、朱某离婚后损害责任纠纷案”,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0)杭萧义民初字第2号。受到侵犯,也有法院认定的是生育权、(11)如“陈某诉林某甲离婚纠纷案”,株洲县人民法院(2015)株县法民一初字第228号。知情权、(12)如“吴洪高诉刘华荣一般人格权纠纷案”,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5民终字第309号。名誉权(13)如“石某某诉刘某某离婚纠纷案”,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常民一终字第479号。等具体人格权受到侵犯,还有法院认定为配偶身份利益(14)如“田湘海诉彭强保一般人格权纠纷案”,隆回县人民法院(2017)湘0524民初字第2158号。受到损害,从而支持男方在诉讼中提出的返还抚养费、赔偿损失等主张;如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或虽已确定为非亲生子,但女方曾赔偿,男方便要承担败诉风险。
对于案情7,生育协议的签订既可能发生于同居期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还可能发生在婚姻关系终止之后。而当事人在诉讼中均认为生育协议的签订侵害其生育权,诉请协议的不履行、无效或撤销。因生育协议中约定的内容是有关身份关系的合同,虽无法适用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但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称《民法典》)第153条(原为《民法通则》第58条)认定。假若合同中约定限制合同一方主体的生育行为,如约定生育、引产或不生的补偿违背需承担的违约责任,则这类约定因违背公序良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均应为无效合同。当然,此类条款的无效,并不影响协议中其他合法条款的效力,如夫妻财产还应正常分割,抚养义务还需履行。
2.同居纠纷影响生育利益案件
同居纠纷与婚姻家庭纠纷影响生育利益案件具有相似性,案件前提为男女双方未缔结婚姻。针对两类案件的共性部分不再赘述,以下将结合同居纠纷的特殊裁判及问题予以归纳。
案情1:女方擅自生育,影响男方生育利益的实现。(15)如“安某某诉刘某某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案”,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7)鲁0103民初字第6942号。主要表现为抚养纠纷案,女方未经男方同意生育后,单独或与孩子共同诉请男方支付抚养费,而男方认为女方擅自生育,侵犯其生育权,主张不承担或少承担抚养费。法院在审理中均明确婚生子与非婚生子享有同等权利,女方并未侵犯男方权利,即便男方反对子女出生也应承担抚养责任。
案情2:女方受骗怀孕,影响自身生育利益。(16)如谢建瑗诉唐云健康权纠纷案,玉林市福绵区人民法院(2018)桂0903民初字第596号,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2e289327a73549f188cba9 bb01479bc2。这类案件中男方往往存在过错,欺骗女方感情,女方基于错误认识导致怀孕、流产等事实的发生,造成身体及精神的严重伤害。法院在认定男方侵权中,有的概括认定为人格权(17)如“蒋蔚诉李晨一般人格权纠纷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2民终字第11106号。受到侵犯,有的认定为一般人格权(18)如“廖冠玲诉廖皓炜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3)佛顺法勒民初字第703号。受到侵犯,基于权益受损的事实,进而裁决侵权人予以一定的赔偿。
3.事故流产纠纷影响生育利益案件
事故流产纠纷影响生育利益案件中的事故主要表现为,发生肢体冲突(19)如“刘艳平诉范爱君身体权纠纷案”,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穗中法民一终字第784号。或交通事故(20)如“刘芳诉范建芳、金坛市天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坛支公司、李正荣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2013)坛民初字第2352号。以致孕母流产,女方单独或与其生育伙伴共同诉请赔偿。针对起诉主体,法院认为生育伙伴虽未直接孕育胎儿,但如无事故,其生育权便不会因此受损。法院承认此种情形下生育伙伴作为起诉的主体,也从司法层面明确了生育权的享有主体包括男女两性,他们可单独或共同在诉请中主张被告的行为侵害了他们的生育权、健康权或身体权(21)如“刘石花、曹梦杰诉马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县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徽县人民法院(2016)甘1227民初字106号。,再由法院依法认定侵权、确认担责比例。
(二)个人与组织之间的案件
个人与组织之间的生育利益纠纷主要表现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个人与医疗机构之间的生育利益案件,不同的案件类型又呈现不同的特点。
1.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生育利益案件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为雇佣关系,用人单位侵害劳动者生育利益的案件主要表现为:其一,劳动者因劳动患病影响生育能力。(22)如“刘敏诉眉山市东坡区白马镇卫生院劳动争议案”,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2016)川1402民初字第2341号。在此类诉讼中,劳动者一般以人格权之诉(23)如“苏某某诉中国石油化工集团茂名石油化工公司及其分公司、吕某某人格权纠纷案”,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15)茂南法民一初字第167号。或劳动人事争议之诉(24)如“刘敏诉眉山市东坡区白马镇卫生院劳动争议案”,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2016)川1402民初字第2341号。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法院在审理中需明确劳动者是否因劳动患病及患病程度,进而判决是否赔偿及赔偿范围。其二,劳动者因生育被用人单位辞退。(25)如“马立仪诉珠海市众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2016)粤0403民初字第830号。这一纠纷因生理特殊性,主要是女性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争议,在双方举证的基础上,法院会最终认定是合理辞退还是歧视辞退。若是歧视行为,再依法裁判予以赔偿救济。
2.个人与医疗机构之间的生育利益案件
公民在医疗机构就医期间,因医疗机构的违法行为或其他状况的出现,导致个人与医疗机构之间发生诸多典型的生育利益案件,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的表现:其一,医疗机构的治疗违法行为,导致患者生育能力受损。因医疗机构违法实施手术、开药等治疗行为,直接影响了患者的正常生育机能,致其生育利益受损,在已有案例中,这类违法行为所引起的纠纷,当事人往往以生育权、生殖健康权、身体权、健康权、性权利等受到侵犯提起诉讼。法院的认定中,有的并未明确侵犯了何种权利,直接判决侵权成立;有的直接认定侵犯了生育权;还有的认为生育机能受损侵犯的是健康权,或因生育器官如子宫被切除而侵犯了身体权,进而裁决赔偿数额。其二,医疗机构的孕检违法行为,导致畸形儿出生的纠纷。这类案件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26)如“李红、李延召诉洛阳市中心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2009)西民初字第1587号。及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27)如“黄日娇诉佛山市南海区第六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5)佛南法民一初字第1169号。。在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中,因医疗服务合同的存在,在医疗机构未能依约提供孕检服务导致畸形儿出生的情形下,当事人一般会诉请医疗机构承担违约责任;而在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中,权益受损者往往以“生育知情权”“生育选择权”受到侵犯诉请医疗机构承担侵权责任,由人民法院在认定侵权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主观过错的基础上判定赔偿范围。其三,胚胎移植、胚胎继承等有关胚胎纠纷。由于这类案件是伴随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而出现的,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涉及复杂的伦理及法律问题,鉴于目前可适用的法律依据极其有限,法院审理中针对法理与情理的冲突往往存在更大的自由裁量权。
二、生育利益私法保护的权利基础:权益之分与公私之辨
在司法实践领域中,生育利益纠纷的类型化归结表明了现有生育利益纠纷的多样态,以及发生的多领域性。虽然法院均已进行裁决,然而,司法审理过程中仍存在共性问题,对此需予以明确,从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规制建议。
(一)权益之分:生育权与生育利益之差异
民法以权利为核心,民法上的权利不同于道德权利、自然权利,应为法律权利。(28)眭鸿明:《权利确认与民法机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页。法律权利的确认既保障了自由的实现,又防止了自由的滥用,在现实中具有更为重要的应用价值。人们对权利本质的探讨有利益说、资格说、法力说等,从立法技术来看,法律权利为“利益说”(法律所保护的利益)与“法力说”(法律赋予利益法律上的力)的结合。利益是人们为了满足个人生存和发展而产生的客观需求,(29)付子堂:《对利益问题的法律解释》,《法学家》2001年第2期。将利益以制定法的形式认可即转化为法律明文保障的法律权利,故“法律权利=利益+形式意义上的法”。(30)贺栩栩:《侵权救济四要件理论的力量——权益层级保护方法论之检讨》,《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只有那些被法律明确了内容、范围、救济方式等的利益,才能称之为法律权利。
法律对权利及利益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承认与保障。从《民法典·总则编》第五章规定的民事权利体系可见,第109条至第119条是对诸多具体人身权及财产权的保护,而通过第120条则将这些民事权益的救济路径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相衔接。《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1164条确定了该法的保护范围为民事权益,也即平等主体在民事活动中享有的权利和利益。若采用严格解释,便意味着权利和利益均受法律保护。当然,立法虽规定了对权利和利益均予以保障,但这种保障并非绝对相等,否则,权利和利益的区分便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意义。而且,并非所有的利益都会得到法律的保障,根据利益的重要性程度不同,相应的保障力度也存在差异。这是因为权利具有确定性,在法律上表现为清晰的内涵边界和明确的保护模式,可直接通过国家强制力予以维护;(31)王 涌:《私权的分析与建构——民法的分析法学基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79页。而利益具有模糊性,虽然涵盖范围广泛,但界线不清。利益被法律保护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利益自身的重要性,以及立法者对利益重要性的认识程度。由此,价值越大的利益,越易得到立法者的重视,保护范围也越明确。这也就意味着,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对权利的保障仍居于首要地位,而对其他利益的保障则需综合进行价值衡量,结合相关因素予以判断。因此,“理性人”更倾向于以权利作为维护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方式。当然,权利与利益可相互转化,但社会生活中纷繁多样的利益不可能在法律层面被全部转化为权利,立法者仅能在众多利益中过滤、筛选,撷取若干重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利益予以权利确认,比如,隐私利益向隐私权的过渡就是这一转化关系的生动体现。
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往往会在诉请中主张对自身“生育权”的保护,而有的法院也在裁判中认可“生育权”的存在,但纵览我国的私法体系,并未有对生育权的概念、内容、救济方式等内涵做出明确规定。由此可见,我国对生育利益的私法保护还未上升到权利层面。在很大程度上而言,这一局面的产生是因为:虽然生育利益对个人、家庭、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由于立法活动与司法实践的分离,导致立法未能及时、系统地体现出生育利益的重要性,立法的保守性、滞后性有时无法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贴近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使得法律对生育利益的保护并不全面。而在立法并未确认生育利益的情况下,司法实践中对“生育权”这一私权利的认可,大大超越了法律的适用范围,容易引起司法权威的降低,削弱司法公信力。(32)王 浩:《民法视野下生育权的保护》,《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私法规范对生育利益的权利定位阙如,使得当事人无法适用法律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审理法官无法准确认定以保证案件合法裁判,有的法院在处理生育利益案件时,还在以健康权、身体权、配偶权、一般人格权等权利形式间接对生育利益进行保障救济。以间接保护的方式维护生育利益的主要原因在于,生育利益体现的是综合性人格利益,在侵犯生育利益的同时,也有可能侵害当事人的生理机能,从而影响健康权的实现;也可能侵害当事人的身体完整,从而影响身体权的实现;还有可能侵害当事人基于配偶身份而享有的配偶权,进而从宏观上侵害一般人格权等。虽然间接保护也能解决大部分生育纠纷,但由于法官审判水平的不同,会因此产生同案异判的弊端,而且,间接保护的起诉主体仅为这一权利的真正受损主体,并不涉及对生育伙伴的权益保护,存在诉请主体的局限。另外,间接保护所获的赔偿额度也未体现出生育利益的特殊性,无法满足当事人内心的权利保护期盼。这也就从侧面反映了现有法律规定的不周延。
(二)公私之辨:公法保护与私法保护之区别
一般认为,公法调整的是国家利益,以权力为轴心,多为强制性法律规范,在其法律关系主体中,一方为国家,对应方为具有服从关系的其他主体;私法调整的是私人利益,以权利为核心,多为任意性法律规范,其法律关系主体为具有平等关系的普通公民或组织。(33)柴丽杰,贺小苗:《论生育权:以公私法分野为视角》,《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权利主体的意思自治是私法自治的核心要求,但过于尊崇私法自治,有可能导致环境恶化、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的出现,激化社会矛盾。面对这些问题,传统的私权自治中也会有国家干预的行为,但这种干预必须是适度的,其目的是为了使私权的发展合乎社会整体的演变要求,为防止过度干预,需以公法规范实现国家对私人利益的保障,从而促进实质正义的实现。
生育利益的本质要求是生育主体能基于个人意志决定生育或不生育,以及如何生育等与生育有关的事项,体现的是私法上的意思自治。但近代社会以来,随着人口数量的上升,人口总量、资源与环境之间严重失衡,为解决人口问题带来的各种挑战,人口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成为了公权力对生育的干预。在这一干预中,为了防止国家恣意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便以公法规范的方式体现对生育利益的保护。相较于生育利益的公法保护,私法保护主要是为了解决私主体之间发生的生育纠纷。他人行为、单位行为、医疗行为等都可能对生育利益产生影响,生育利益诉求的多元化不可避免地在私主体之间滋生矛盾,侵犯生育利益的现象亦频频发生。
由此可见,生育利益公法保护与私法保护的区别明显。公法保护抵御的是公权力的侵害,私法保护解决的是私主体之间的利益纠纷。从我国的立法现状来看,对生育利益的私法保护明显弱于公法保护,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规范均是从公法层面宏观调控人口总量,并防止调控中国家的不当干预;而在私法保护领域,仅有《民法典》对“民事权益”的兜底性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9条的个别调整。对于私法上生育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形,有些起诉主体明显将公法上生育利益保护的相关规定作为了依据,而对于当事人提出的公法依据,多数法院竟均采用。法院的这一做法实则忽视了公法与私法的区分,适用公法解决私法问题的出发点出现了错误,引起了法律规范适用的混乱。如在生育利益私法纠纷的处理中,法院多适用《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第1款的规定确认妇女有决定生或不生的自由,然而,这一款并不能直接引用,必须结合第51条第2款和第3款的立法目的系统适用。从体系解释的层面分析,《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整体是为了防止国家对公民生育行为的不当干预。所以,对生育利益的保障,不能贸然使用公法予以调整,必须明确发生纠纷的法律关系性质,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规定,从而决定采取的救济方式。
三、生育利益私法保护的规制范式:权利建构与补强规制
在司法实践中,随着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私主体之间的生育利益纠纷日益增多和棘手,从私法层面加强对生育利益的规范和调整已成为必要。针对目前生育利益私法保护所存在的问题,应及时、准确进行权利定位,选择恰当的保护方式,协调立法规范的统一。
(一)权利建构:完善生育权私法地位的建构
时代的发展促使新生利益的产生,而这些新生利益未必都是能被法律所承认的新兴民事权利。面对形形色色的权利诉求,应明确权利确认的必要性及具体的权利内涵,如此,权利概念的核心才不至于因权利的通货膨胀而贬值。(34)方新军:《一项权利如何成为可能?——以隐私权的演进为中心》,《法学评论》2017年第6期。
1.生育利益私权确认的必要性
对“生育权”的主张体现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而权利的产生绝非偶然。就生育权而言,需综合考量生育利益的重要性、生育利益的保护是否能以现有的权利体系涵盖,以及立法者对生育利益权利保护的主观重视。生育不仅是个人生命的延续、夫妻感情的联结、家庭兴旺的关键,同时也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司法实践中,从理论上讲,如果现有的法律框架能对新类型的案件予以合法、有效地审结,那么,就不能创设新的权利。(35)陈琳琳:《反思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权利泛化》,《法学研究》2014年第1期。然而,现有的民事权利体系并不能周延地保护公民的生育利益,将公法上对生育利益的维护引入私法纠纷的处理中未免有张冠李戴之嫌,无法从私法根源上予以维护。(36)姚 宇:《新型民事权利的界限及其证成》,《学术交流》2016年第11期。而在我国现有的私法规范框架下,生育利益又往往按一般人格权及其他具体人格权、配偶权等权利形式进行间接保护,此种保护方式不仅存在起诉主体的局限性,也无法实现对个人生育权益的特殊维护和全面保障。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对“生育权”的主张,以及法院对“生育权”的确认都表明了人们及法律适用过程对于生育权的重视。(37)朱晓喆:《私法的历史与理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87页。因此,立法者需立足现实需求,把这一利益的权利保护提上日程,将生育权法律化、确定化、客观化,从而为权益的保障提供有效的救济路径,实现案件的公平、公正、严谨裁判。
2.生育权私法规制的立法视角
生育权的私法确认应健全其权利内涵及外延规制。在生育权性质的界定中,因生育是与人身密切相关且不具有直接财产内容的权利,所以,应将其纳入人身权利的范畴中。受我国传统伦理观念的制约,基于对夫妻自然生育的尊崇,生育权曾被视为一种身份权,认为生育权只能基于合法的婚姻关系而产生,由夫妻双方共有。但是,这一观点忽略了非婚关系下生育主体延续后代的情形。现实中,缔结婚姻并非每个自然人必须经历的过程,单身生育、同居生育等情况客观存在。生育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为维护其独立人格所普遍固有的人格权,它的人格属性与配偶身份没有必然联系,只不过,夫妻生育仍是生育实现的主要形式。
在生育权主体的确定中,学界多有对生育权主体的探讨,如死刑犯、监狱服刑人员、同性恋者、非婚者等是否享有生育权。对上述探讨的分析首先应明确的前提是,生育权性质由身份权到人格权的转变是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在人格权的定性下,生育权的享有主体具有广泛性,人人生而享有。(38)[德]汉斯·布洛克斯,沃尔夫·迪特里希·瓦尔克:《德国民法总论》,张 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77页。但权利的享有不同于权利的实现,权利的实现受制于多种因素,如一个先天丧失生育能力的人同样享有生育权,但其权利实现方式存在重大阻碍。
在生育权内容上,学者们也未形成统一意见,如有学者认为生育权的内容包括生育决定权、生育知情权和生育健康权,(39)王 浩:《民法视野下生育权的保护》,《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有学者认为包括生育请求权、生育决定权、生育方式选择权和生育保障权等。(40)马 强:《论生育权——以侵害生育权的民法保护为中心》,《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6期。就此,首先,生育方式选择权从实质上看是生育决定权中的一部分,可由生育决定权予以包容;其次,生育请求权的说法不应确立,因为生育权是人格权,故其为绝对权,并非请求权,生育权的权利主体特定、义务主体不特定;再者,生育健康权本应是健康权或身体权的调整领域,无独立分离的必要。从社会发展现状、权利自身特点及生育纠纷的司法裁判来看,生育权的内容并非是与生育有关的所有权利,主要包括:其一,生育决定权。这一权利内容最大程度地体现了权利主体的生育自由意志,生育主体有权依法决定是否生育、何时生育、生育质量、生育伙伴、生育方式等。其二,生育知情权。这一权利内容是对权利主体生育自由意志的尊重,其中,生育知情权中信息来源的对象既包括自己的生育伙伴,也包括协助生育的医疗机构等。其三,生育保障权。这一权利内容主要体现为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生育权益的维护。这些内容的确立既兼顾了生育权的内外保障,也体现了与现有权利体系的衔接协调,突出了生育权的既有特点。
在生育权的保障方面,对生育权的侵犯,不仅会削弱甚至剥夺生育主体的生育机能,更重要的是会打击生育权所蕴含的精神利益。由此可见,针对侵犯生育权的违法行为,应在认定财产损害的基础上,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予以酌量增加。精神损害虽非有形、可量化的损害,即便进行财产补偿也无法真正填平,但财产补偿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权益受损者予以精神慰藉,从而平衡生育主体的心灵损伤,体现救济设计的人文情理关怀。
(二)补强规制:补强重点生育纠纷领域的规制
在生育权的私权确认基础上,对司法实践中的生育纠纷重点发生领域,应在立法上侧重完善。这一举措不仅有益于推进生育法律体系的周密性、协调性,而且有益于对典型案件、类似案件的有效、统一、公平裁判,提高司法公信力。
1.婚姻家庭领域的生育立法补强
传统伦理观念普遍认为,婚姻、性行为与生育之间的联系是必然的,生育只能由夫妻双方共同实现。(41)吴 俐:《生育权的尴尬与选择》,《人口与经济》2003年第4期。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育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婚姻不仅仅以生育为目的,生育也不再局限于婚姻关系中,虽然每个生育主体均享有生育自由,但国家在行政法律规范上对非婚生育的限制仍普遍存在,夫妻生育仍为国家首倡。综观《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规范条文,仅有对夫妻课以计划生育的义务,而未提生育权这一事关家族延续的权利保障,不失为立法的盲点与疏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9条仅对妻子擅自堕胎,丈夫诉请生育权侵权赔偿和夫妻因生育意愿差异诉请离婚这几种情形的司法裁判统一认定,而未明确涉及其他婚姻家庭领域的生育纠纷。由此可见,婚姻家庭领域的生育立法需要系统的补充,从而实现生育法律体系的完善,进而维系婚姻家庭秩序的和谐稳定。
在婚姻家庭领域,《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二章“结婚”所规范的是结婚的形式与实质要件,第三章“家庭关系”所规范的是夫妻、父母子女和其他近亲属关系,而家庭关系主要是通过缔结婚姻、生育子女所产生,不难发现,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之间缺少了过渡性的“生育”部分。生育作为亲属关系延续的必要一环,家族传承的客观规律要求婚姻家庭领域的立法要对生育权予以足够的重视。为保证法律规范的内在逻辑联系,可以考虑在第三章“家庭关系”中补充“生育”一节,以实现法律体系内部的衔接。在“生育”一节中,需通过生育明确亲属关系的产生、发展、延续、消失,明确婚姻家庭领域生育侵权的救济途径,将成熟的司法解释上升到法律层面,并予以修订和补充。另外,人工生育对婚姻家庭关系的影响也应予以强调,从而妥善应对这一领域中的生育纠纷。
2.劳动用工领域的生育立法补强
劳动者如因劳动患病,影响生育能力,可以直接诉请权益侵害赔偿,通过工伤求偿或用人单位担责予以救济,但如果因怀孕生育被违法辞退,这便涉及对女性劳动者的性别歧视。通常,鉴于怀孕对工作效率的影响,以及国家允许怀孕劳动者在法律范围内调岗和休产假,用人单位为追求工作效率和利益最大化,会不倾向于招收女性劳动者。再加上“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使得用人单位对女性的性别歧视进一步加剧,导致女性在劳动领域、劳动岗位、劳动层次、劳动价值、劳动智慧的边缘和低质化。(42)王歌雅:《性别排挤与平等追求的博弈——以女性劳动权益保障与男性家庭责任意识为视角》,《北方法学》2011年第6期。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法律规范中均有对女性劳动者的特别保护,如《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15条规定了用人单位违法辞退怀孕、生育或哺乳的女性劳动者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但如若仅以普通的劳动赔偿保障女性劳动者的权益,未免降低了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以法律手段助长用人单位的性别歧视意向。所以,针对用人单位因性别歧视对女性劳动者生育利益的侵犯,还应在法律保障部分加大对用人单位担责范围的补充设计。(43)黄桂霞:《女性生育权与劳动就业权的保障:一致与分歧》,《妇女研究论丛》2019年第5期。从长远角度看,应明确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从而威慑用人单位的此类歧视行为。同时,为了协调我国的赔偿制度立法,具体的惩罚性赔偿数额应为原有劳动赔偿数额的1~3倍,以加大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使女性劳动者的生育利益更有保障,在权益受到侵害时得到全面救济。
3.医疗卫生领域的生育立法补强
医疗机构的治疗违法行为影响了生育主体的生育能力,使其生育利益受有损害,这类纠纷的处理可直接在上述生育权私法界定的基础上,适用侵权规范予以救济。但对于因医方存在孕检违法行为导致畸形儿出生的纠纷,在当事人以侵权之诉诉请保护的情形中,法院审理这类案件时普遍存在诉讼主体认定不清、侵害客体认定不明、因果关系认定疏忽、损害后果认定混乱,以及赔偿范围认定不一等问题。因畸形儿的畸形并非医方导致,所以医方并未侵犯其权利,故畸形儿本不具有提起诉请的资格,但法院在进行司法认定时往往忽视这一问题。畸形儿父母因畸形儿的出生而权益受损,应为侵权之诉的诉讼主体,但具体影响了其何种权益的实现,法院在认定中还未统一,大部分案件认定畸形儿父母的“生育知情权”“生育选择权”受到侵犯,然而,这两项权利的权利基础在法律上又如何呈现,他们的上位权利是否为生育权,对此立法均未明示。畸形儿的畸形先天存在,与医方的过错行为并无因果关系,由此,便有法院基于此因果关系的不存在而判决驳回权益受损者的赔偿诉请。然而这种判决并未意识到畸形儿的出生与医方的过错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因果关系的认定疏漏也需明确。畸形儿即便天生存在缺陷,但生命是无价的,基于对生命的尊重,畸形儿的出生不能被认定是一种损失,因畸形儿出生使其父母遭受的财产及非财产利益损失才是这类案件的损害后果。有损失必有救济,但损失的确定在司法认定中又存在争议,特别是对孕母医疗费、畸形儿抚养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存在裁判分歧,这些问题都亟待通过法律规范的完善予以明确。
针对此类案件,鉴于立法稳定性与权威性的要求,对特殊案件的裁判若直接纳入立法体系,不免会产生随意立法的问题导向。所以,在综合法律制定成本、社会现实需求和司法实践样态等因素的基础上,可先以司法解释的方式针对案件的特殊性予以专门规范,填补立法空白,待立法时机成熟后再上升到制定法层面。在进行专门司法解释的过程中,一应明察违法行为类型,通过梳理司法实践违法行为样态来总结违法行为类型;二应明朗救济方式,违约之诉与侵权之诉均可适用,但需明确二者在起诉主体、举证责任及赔偿范围等方面的区别;三应明辨牵涉主体,侵权之诉中权益受损者为畸形儿父母,故他们为适格原告,医疗机构应承担相应的职务责任;四应明定侵犯权利,此类案件影响了畸形儿父母的生育决定权和生育知情权,他们均为生育权的内容呈现;五应明彻因果关系链条,孕检违法行为虽与畸形儿的畸形无关,但却与畸形儿出生有关;六应明晰损害赔偿范围,基于赔偿基础的差异,在此类案件中,对畸形儿父母因畸形儿出生所增加负担的医疗费、特殊抚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费用应予支持。
另外,针对胚胎继承、胚胎移植等掺杂复杂伦理的生育纠纷,目前可适用的法律仅有卫生部2001年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14号)等部门规章,高级别法律规范的制定,以及适应时代发展对现有规范的更新都应提上立法日程,以避免立法对新兴技术规制的迟延与滞后。(44)孙东旭,王 岳:《从冻卵看单身女性生育权的保护问题》,《中国卫生法制》2020年第6期。在立法内容的完善中,需界定胚胎的法律性质为特殊伦理物;在确定胚胎所有权、处分权、监管权、继承权时,应注意静态逻辑推理与多元化价值考量间的平衡,兼顾伦理与情感的需求,明确法律背后的温暖和智慧,从而实现裁决利益的最大化。
社会生活中的利益样态纷繁多样,诸多利益依据其重要性及价值表现得到法律不同程度的保护,虽然生育利益还未得到私权承认,但其重要性无庸赘述,上升到法律层面的权利均是在立法过程中“博弈”的结果。在私法领域将生育利益上升为法律权利是时代进步的体现,生育权的私法确立,还需洽和生活领域与社会领域,做到生育利益在《民法典》各编中私法保障的统一协调,从而使司法实践有法可依,更好地保障每个公民切身权利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