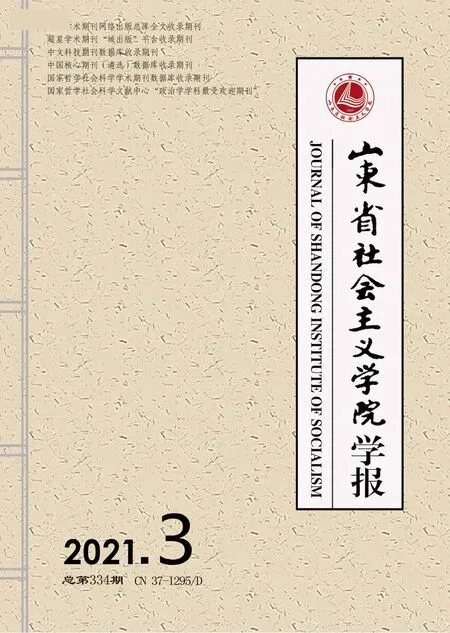“大一统”思想与中国国家建构
2021-01-28陈立明
陈立明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人文为本,其中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流派包括道家、儒家、墨家、法家等。众多的思想流派互竞交融,多元淬炼,终成大中华的伦理体系,其核心载体便是“大一统”。可谓诸子百家争鸣,“大一统”思想元素却能共享;中原政权更替,大一统制度却不断成型。经过几千年多元交融、伦理教化、制度实践的“大一统”思想文化体系,决定性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民族性格特征。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就是“大一统”,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密码就是“大一统”。
一、“大一统”的历史沿革
中国人具有追求思想和法度统一的悠久传统。“大一统”一词源于《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孟子明确主张天下“定于一”。荀子反复强调”一天下”。韩非子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
周朝奠定了“大一统”的伦理基础,解决了革命与执政的矛盾。周人通过“以德配天”的革命理论、“亲亲尊尊”的宗法制度和“有教无类”的执政者培养体系,为“大一统”奠定了坚固的伦理基础,确保“革命有道”“执政有序”“后继有人”。
秦汉架构了“大一统”的政治体制,解决了封建与郡县的矛盾。“百代皆行秦制”,秦为大一统贡献了郡县制、皇帝制等中央集权制度,但因其仅采“霸道”而短命。汉武帝将集权推至顶峰,“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开明专制。汉朝在政治上基本解决了封建与郡县之间的矛盾;在经济上以盐铁政策保证中央财政集权;在意识形态上以董仲舒“天人三策”为基本原则。董仲舒主张:“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
隋唐宋完善了“大一统”的官僚体制,解决了精英与平民的矛盾。隋唐为大一统贡献了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和成熟的文官制,打破了门阀大族的政治和文化垄断,开启了平民上升到中央的流动渠道。宋代全面开展平民化儒学教育,彻底开放科举制,再加上“不杀士人”的祖宗家法,使得士大夫阶层成为忠诚的政治精英。
明清实现了“大一统”的民族整合,解决了中原和异族的矛盾。雍正皇帝说:“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清朝统治者通过变更王朝名称、祭祀元明两朝的法宝、供养两朝皇帝后裔、恢复汉文科举、尊奉程朱理学、继承明朝法律等,确立执政地位;保持对蒙古、回部、西藏和西南地区的有效统治;皇帝兼任满族族长,保持满人的认同;在宗教政策方面,以“崇儒重道、黜邪崇正”为纲,对藏传佛教颁布金瓶掣签制度,把达赖、班禅继任人选的决定大权由西藏地方集中到朝廷中央。
二、“大一统”的内涵与基本制度
(一)“大一统”的内涵
“大一统”的法权内涵既指疆域又指人文,虽经范围不断扩展却始终保持统一。疆域范围指历代大一统王朝的本土疆界,在今天指中国所辖的主权领土;人文范围指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体,在今天统称为“中华民族”。
“大一统”的政体内涵是中央集权。像古代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自然农业国家,如果不建立一套近乎完美的中央集权管理体系是不可想象的。集权不是中国人的偏好,而是国情的实际需要。
“大一统”的治理内涵是礼法合治。古代中国面积大,人口多,没有现代化的行政治理手段,不可能事事介入,只能选择成本较低的社会治理模式,即所谓“儒表法里、外儒内法”,礼治是原则,法治是工具,礼法合一,德主刑辅。德治与法治并不对立,完全可以互相融合。
“大一统”的道义内涵是文化本位。为什么中国的“大一统”不叫“大统一”呢?“大统一”所强调的无非是领土与权力的集中,但是这种集权不可持久。“大一统”比“大统一”更高级,不仅强调权力的“一”,更强调思想的“统”。中国古代确立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至孔子、孟子、荀子的儒家道统,历代王朝兴替,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都要尊儒家为思想正统,奉正朔、易服色,体现了基于思想文化一统基础上的政治一统。
(二)“大一统”的基本制度
皇帝制度。从秦王嬴政首创皇帝制度,到1911年清朝被推翻,这一制度延续2100 多年。皇帝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由此衍生出君相体制以及官僚体制,进而演绎出选贤体制和乡绅传统。
郡县制。西周时期,建立了以封建制为特色的官僚政治体系。周王将宗亲和功臣分封到各地,广建封国,即所谓“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封建制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之上,实行公卿世袭、嫡长子继承制度,即所谓“世卿世禄”。秦统一六国,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增至40余郡。郡县制是一种地方直接受控于中央政府的官僚政治体制,各侯国不实行世袭,而按军功授爵。此后,地方行政体制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州郡县三级制、隋唐时期道州县三级制等发展。元朝时期,开始设置行省,全国分设10 个行中书省,行省管辖路、府、州、县。行省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和近代,成为中国特色的地方行政体制。
三省六部制。这是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基本运行架构。夏代已有辅佐夏王的六卿,西周时期辅佐周王的为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尚书·周官》云:“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秦汉时期,建立了以皇帝为中心的三公九卿制。三公为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分掌行政、监察和军事。隋唐时期,建立起以皇帝为中心的三省六部制。“唐初,始合三省,中书主出命,门下主封驳,尚书主奉行。”(《困学纪闻注》卷一三《考史》)尚书省是中央行政管理的中枢,下掌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宋代以后,三省制向一省制演化,元朝以中书省统领六部,为最高政务机关。明清时期,实行内阁六部体制,罢中书省,废宰相之职,设内阁大学士,为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机构。
科举制度。科举是分科选举的意思,其特点是通过逐级考试的办法选拔人才。中国的选官制度经历了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到隋代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开始设置进士科。经过唐代的发展,科举制到宋、明定型,前后延续一千三百多年,是一种中国特色的“选举”政治。
监察制度。监察制度是为了监督政府官员而设立:一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监察机构单线垂直,与上级单线联系;二是对监察官员的派遣贯彻“以小取大”的原则。
“大一统”的其他制度还包括史官制度、天下同序、乡绅制度、教化制度等。
三、“大一统”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发展,深受“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儒家很早意识到中原主体民族同周边少数民族的区别,提出“严华夷之辨”。但《春秋公羊传》又提出:“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别不以种族论,而以政治文化所达到的境界论,因此夷夏之间可以互相转化,夷可以进为夏,夏可以退为夷,这是中国古代处理民族关系的最好方针,无此方针不可能“大一统”。
(一)“黑河-腾冲线”与早期华夏文明
在中国版图东北和西南的两个边城,即黑河和腾冲之间画一条直线,会把中国疆域划分为面积差不多相等的东、西两部分。这条线就是“黑河-腾冲线”。在这条线的西半部分,占据着54%的国土面积,大部分的中国人口集中分布在占国土面积45%的东半部。“黑河-腾冲线”又与中国境内300-400 毫米年降雨量带的走向基本一致。而300-400 毫米年降雨量带,大部分与前工业化条件下雨养农业与牧业经济的分界地带相重叠。“黑河-腾冲线”实际上已经把近代之前中国大面积宜农区域的西部界线粗略勾勒出来了。把这根线叠加到中国各民族分布图上,就不难看出,在它以东,只有朝鲜、壮族、侗族、傣族等几个农耕少数民族,绝大部分人口是汉族。在它以西,则是广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所以它也可以被看作是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分布区之间的划分线。
在中国历史上,由汉文明所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中央王朝,曾多次将许多非汉语人群所在区域置于其统治范围之内。从唐、宋和明代历史来看,中央王朝把非汉语人群分布区纳入国家版图,主要通过三种依次演进的行政措施来逐步实现,即从建立“羁縻府州”到设置“土官”“土司”,再到“改土归流”。改土归流的必要前提,是保证汉语人口在当地户口中取得起码程度的比重优势,使国家对编户的赋税征收足以支持对所在地的行政建制。把幅员辽阔的西部非汉族区域纳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版图,是通过元、清这样的非汉语人群所创建的中原王朝来实现的。
我们可以按照每一千年为一个分期,从最近四千年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迁过程中抽出一条简明的线索。
1、从公元前两千年到公元前一千年,华北各地的史前文化在强烈的交互作用与整合过程中,终于跨过文明的门槛,发育成以“三代”(夏、商、西周)著称的早期华夏文明。
2、在公元前最后一千年,华夏文明逐渐扩大势力范围,将未能被同化在自身文化圈内的其他人群排斥到边缘。华北开始呈现“内夏外夷”的空间分布特征,并确立了中国经济文化核心地区的地位。在那里形成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官僚制政权,开始把远超出华夏文明地域范围的疆土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3、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汉文明一波接一波地从华北向南方社会全面渗透,以越来越快的节奏推动东部中国经济文化均质化的进程。中央王朝将西北部中国纳入自己版图的努力则时断时续、事倍功半。
4、公元后第二个千年,南方超越北方,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完成。西部及西北部各地区先后被元、清等政权稳固地整合到中央王朝的疆域结构之中,但西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仍严重滞后。
(二)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经历了四个时期,中国文明也实现了由北强南弱到南强北弱的转变。
1、华夏-汉民族的形成与先秦时期的民族融合。史前人类自南方进入今中国境内,在讨寻生活资源的艰苦迁徙中不断分化、融合,留下了许多史前文化遗迹,创造出一幅中国史前文化多头起源、多元发展的灿烂画面。灿烂壮美的晚期新石器文化和铜石并用文化随着“三代”在华北的兴起而结束。此后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华北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不断向前推进的动力所在。历史变迁的空间节奏“从南向北”转变为“从北向南”,华北的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遥遥领先于中国其他地区,并把自己的强大影响一波接一波地向它的外围,尤其是南部中国扩散开去。
当时中原地区生活着华夏族,他们是汉民族的前身。“华族”涵盖了共同尊奉黄帝为始祖的夏、商、周三族的“华人”,“夏族”通常指华夏化了的戎人、氏人和夷人。“华夏”一词常被用以区别中原地区的民族与其周边的民族(即蛮夷戎狄),然而华夏族实际上也并非全为中原之族,它融夏、商、周三族初具雏形之后,就像滔滔东注的长江,汇合百川,最后形成一个庞大的民族集团。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当时,中原地区“华夷”逐渐走向一体,内迁异族已被华夏吸收、融合。中原四周,齐、鲁吞并诸夷,秦霸西戎,楚征服统一诸蛮,边疆地区民族融合兼并的速度也在加快。而华夏诸侯国经过激烈的兼并、分化、吸收,到战国时期只剩下齐、燕、韩、赵、魏等几个大国和在它们夹缝中的几个小国。原来被称为“蛮夷”的秦、楚也已同称“诸夏”或“中国”,与周边各族出现了进一步融合的趋势。地区性的局部统一,为华夏一统奠定了基础,也为以华夏族为核心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提供了舞台。
2、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南北之间的差距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里逐渐缩小,最重要的原因是北方汉语人群的大规模南迁,以及随之发生的汉文明由北向南的拓展。这个时期最令人瞩目的汉语人群大规模南迁运动,是“五胡乱华”引起的“永嘉南渡”和标志着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南迁的北方人口放弃了原先种植谷子、小麦、高粱等旱地作物的农耕方式,像南方当地人口一样从事产出更高的稻作农业。他们对地广人稀的南方来说,不仅是珍贵的劳动力,而且成为全方位带动南方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
3、辽宋夏金元时期。自五代十国以后,中国历史又进入一个大分裂、大混乱之后的大统一时期。由金朝入主中原造成的“靖康之难”,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北方人口的大规模南迁。随着南部中国的人口增加和生产开发,北方汉人开始改变对南方的印象。这种改变在“安史之乱”阻断了华北对唐朝中央政府的税负供给之后就已发生。人们发现,“中原释耒”后,中央政府从南方获取经济支持,就是所谓“漕吴而食、辇越而衣”,居然也足以支撑下去。所以杜牧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樊文川集》),韩愈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送陆歙州诗序》)。到两宋之际的又一次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之后,南方进入超越北方的阶段。南宋时期,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完成了从华北向南部中国的转移。“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表明了长江三角洲已经成为天下粮仓。南方人对自己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优越地位有着明确的意识:“儒学之盛,古称邹鲁,今在闽越。机巧之利,古称青齐,今称巴蜀。枣粟之利古盛于北,而南夏古今无有。香茶之利今盛于南。……然专于北者其利鲜,专于南者其利丰。……漕运之利今称江淮,关河无闻。盐池之利,今称海盐,天下仰给,而解盐荒凉。陆海之利今称江浙甲天下,关陇无闻。灌溉之利今称浙江太湖甲于天下,河渭无闻。”从宋代开始,南方士人进入最高权力中枢成为不可抑制的趋势,南方文化在大踏步地赶超北方。宋元之际的动荡与破坏,也未曾终止这种趋势。
4、清代民族融合。清朝继承了由前代传承下来的朝贡观念和朝贡体制,并创造性地把传统的朝贡地区、人群和国家分置于两个不同的治理空间。一称“外藩各部”,包括内札萨克(内蒙古各盟旗)、察哈尔(内属蒙古各旗)、喀尔喀(外札萨克蒙古)、青海、西藏诸地域,以及金川土司、南疆回部各伯克头人属下等部。凡是对这些地方进行具体治理的政令、刑事、军旅、屯田、邮传、互市等方面的最高管辖权,均属理藩院。另外一类,则称“域外朝贡诸国”,清朝对它们完全不负国家治理的责任,处理与这些国家关系的职责,由类似外交部功能的礼部鸿胪寺来承担。中国的地理版图,也在这一时期基本稳定下来。所以,不同于其他现代国家诞生于旧式帝国的瓦解和分裂,中国基本上完整地将帝国时代的国家版图转换为现代中国的疆域。
(三)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模式
历史上的中国,先后有过五种互有区别的含义:
1、第一种含义指河南核心地区。现存文字材料里的“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铸成于西周时期的著名青铜器“何尊”的铭文内。铭文中,周成王追溯他的父亲武王的话说:“余其宅兹中国。”成王口中的“中国”,原指洛阳及其邻近地区。它与古时候的华夏人群把今登封、洛阳一带视为“土中”(即天下中心)的观念有关。这说明至少在西周初,“中国”已经成为对河南核心地区的一个流行称呼了。
2、第二种含义指关东,即函谷关或者后来潼关以东的黄河中下游平原。《荀子》中说,战国之秦,“威动海内,强殆中国”(秦之强能危殆中国)。《韩非子》中说:“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照这种说法,秦、越、吴、楚都不在中国的范围内。
3、第三种含义把关中地区也包括进来。《史记》记载:“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华山在今关中地区,是知西汉时期已经把北部中国的核心地区全都包含在其中。
4、第四种含义指以华北核心地区作为其统治基础(后也指自北方南迁、立国于南部中国)的诸多中央王朝所控制的全部国家版图。
5、第五种含义是随着汉语人群向华北以外地区的大规模迁徙流动而产生的,指在国家版图内不断向外扩展其生存空间的主体人群及其文化,也就是汉语人群和汉文化。
中国古代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可以概括为“自北向南”“从东到西”的两个过程。“自北向南”,指汉语人群在华北形成和发展起来,再从华北向南部中国迁徙,以及整个东部中国被汉文化所整合的过程。“从东到西”,则指汉地和中国西部被整合到同一个国家版图之内的过程。后一过程在最近一千年里所取得的显著成果,为今日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基础。
上述脉络告诉我们,把过去几千年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仅仅理解为由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之起源、发展和演变所支配的看法,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它实际上是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和以辽、金、元、清等政权为代表的内亚“边疆”帝国体制这两种国家建构模式,反复相互撞击与整合的过程。如果没有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民族对创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贡献,就不会有今天版图规模的现代中国。
四、“大一统”国家观的特点及影响
(一)中国政治的变与常
中国现代政治建构,具有两个要素,一是人民民主的价值取向,一是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保持国家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人们往往基于对民主化与现代化价值的追求以及对未来的期许,来设计、规划和建构中国现代政治,为此不惜用十分激进的观念和极端的方式否定历史与传统,甚至彻底割裂和全面否定传统,这包括对大一统的全面否定。其实,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既是西方现代民主政治发展和影响的结果,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特别是以“大一统”为代表的政治文明影响的结果。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需要维系国家统一或政治的“大一统”,也需要维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一统”。在现代中国,国家的统一与中华民族的“大一统”结构是相互塑造、相互决定的,这就使得中华民族“大一统”结构成为传统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所必须面对的现实基础和内在要求。对于传统中国社会来说,“大一统”既是一种政治形态,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得以生存与发展的组织形态。这一点,英国思想家罗素看得十分明白。他说:“中国的统一性不在于政治而在文明。中国文明是古代唯一幸存至今的文明。自从孔子时代以来,古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和罗马帝国都衰亡了;但中国文明绵亘不绝,生存至今。”[2]正是这种“大一统”,使得中华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并使得中华文明能够延续至今。中国要迈向现代化和民主化,不能摧毁作为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形态的“大一统”,相反应该以维系这种“大一统”作为其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逻辑。以“大一统”为核心的文化传统,是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发展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之根,是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社会基础。
(二)“大一统”政治的特点
1、制度性。传统中国之所以能够“百代都行秦政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秦制不仅是皇权统治的制度形式,也是传统国家组织和治理的制度形式。所以,皇权可以在各家、各族之间流转,但无论何人为皇帝,都必须以秦制为治国之正统,都必须运行这套制度体系。
2、厚植性。秦制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与宗法社会具有内在的契合性,最基本的体现就是家国同构、家国一体。正因如此,秦制也逐渐渗透到每个人的生活与内心深处,造就一种家国天下情怀,其表达模式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3、开放性。中国传统国家皇权统治是“家天下”的统治模式,在这套制度与治理体系下,皇权不可能为一家万世垄断,必然是在百家百姓之间流转,从而形成王朝更替。皇权赢得正统性与合法性的关键有两点:一是能够居天下之正;二是能够合天下于一。要做到这两点,就要弘扬维系“大一统”格局的制度与治理体系,并藉此创造天下一统与太平。在这种体制和治理体系下,所有权力都具有全面的开放性,皇权不属于哪个家族,为官者也不专属于哪个阶层。这种开放性是社会形态的内在要求,不是权力的制度化安排形成的。
4、精密性。人类创设的各种政体以及相应的制度形式,能够得以巩固和完善的关键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制度能够与外部保持持久的互动关系;二是制度内部具有很强的自我修复与完善功能。秦制具备这两个关键因素。首先,通过选官制度,秦制既能将其意识形态有效地贯穿到人们的知识体系与日常生活之中,又能源源不断地从社会中选拔到既认同意识形态又具有治国理政能力的人才。其次,通过选官制度,将支撑国家体系的三大系统整合为能够相互支撑、相互塑造的闭合的循环系统。这三大系统就是官僚系统、意识形态系统以及宗法社会系统。这样,相对于不同时期、不同朝代的个性化皇权来说,不论从内部还是外部,以秦制为代表的国家制度体系都具有精密性和完整性,拥有一种相对自主性。
5、自给性。不论是周制还是秦制,都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官制系统。《周礼》就是一部通过阐述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并由此确立了以官制来表达制度体系、国家组织以及治理形态的中国政治传统。隋唐科举制的确立,标志着选官制度经历了汉代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之后,终于定型于规范而系统的科举制,也标志着传统的“大一统”政治所运行的秦制达到了成熟和完美的形态。可以说,不论秦制的运行,还是皇权的巩固与实施,都离不开选官制度。整个选官制度是传统“大一统”政治体系的中轴,并赋予其独特的自给性。这种自给性体现为:选官制度生成的官僚队伍是秦制得以运行的关键所在;而官僚队伍得以生成的关键是秦制内生的选官制度。由此,官僚队伍、选官制度以及整个秦制之间形成了相生相成的自给性。这种自给性为秦制的千年存在与发展提供动力与资源。
(三)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基础
近代以来,西方史学界奠定了民族国家的叙事传统。然而,民族国家的叙事并不适合中国历史发展。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基于“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传统实际奠定了政治和文化共同体,这是中国文明具有持久性和绵延性的内在原因。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认为,中国能够持久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贡献人类文明辉煌发展的根本所在,不是基于“大一统”政治而形成的传统国家,而是中国历史与文化铸造出的“大一统”的中华民族。他指出:“在世界历史上,可以和我们比较的国,只有一个罗马。然而罗马早就灭亡了。这是为什么?因其只造成国家,而未造成民族。”[3]不同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是建立在欧洲“各民族各自发展”和分裂的国家基础之上,中国始终维系着民族的统一,具有持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这种建立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一统”基础之上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事实依据。
中华民族是在多元一体的结构基础上建构民族“大一统”的。这种民族的“大一统”,不是以消除民族差异为前提的,相反,是以承认并尊重民族差异为前提的。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促进民族凝聚与团结的力量,主要是内在的力量,而不是外在的。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中华文明与历史的发展始终是在汉族与其他民族的不断交融中展开。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格局形成的六大特点》一文中说:“汉族主要聚居在农业地区,除了西北和西南外,可以说凡是宜耕的平原几乎全是汉族的聚居区。同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要道和商业据点一般都有汉人长期定居。这样汉人就大量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正是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中国历史上,不仅出现过由非汉族人统治的王朝,如元朝、清朝,而且在国家分裂的时候,还出现过各种非汉族人统治的政权,如北魏的鲜卑族政权等。这些非汉族的王朝和政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接受汉文化,进而接受其民族与汉族相互融合的事实。二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始终存在着一个凝聚核心,这就是汉族。汉族成为凝聚的核心,主要不是其体量优势,而是其所基于的经济生产方式。“如果要寻找一个汉族凝聚力的来源,我认为汉族的农业经济是一个重要因素。看来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早就会服服帖帖地主动地融入汉族之中。”[4]三是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及其所带来的统一王朝,在为多民族的“大一统”提供政治支撑的同时,也提供了很强的文化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