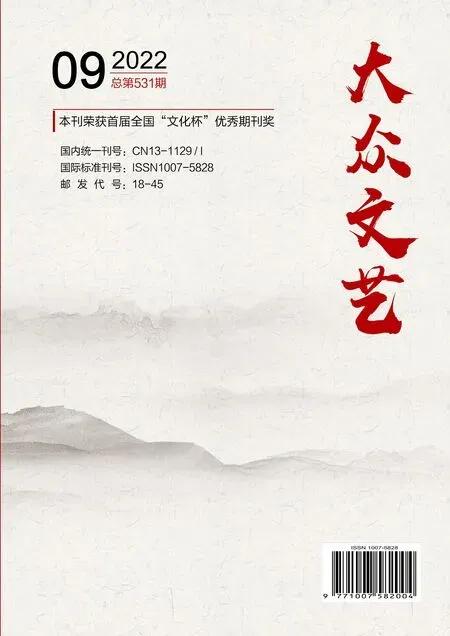浅析汉代砖文书法
——以刑徒砖为例
2021-01-27张铜伟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书法系100875
张铜伟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书法系 100875)
一、汉代砖文概述
汉代是中国书学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不但上承秦篆、下开隶变,且后世盛行的章草、今草与真书,也先后于此时期完成蜕变并渐趋成熟,至今两千余载“仍未脱其遗轨”。遗憾的是,西汉的书迹十分匮乏,宋人曾断言,‘前汉无碑’,欧阳修也曾道“欲求前汉碑碣,卒不可得”,继而曹魏禁碑,“晋武帝咸宁四年也下诏禁碑”。因此,汉代时期的砖刻频频映现,甚至出现了长逾数百字的砖铭。
时至清代,金石考掘之学大兴。由于出土砖文的数量不断增加,引起了学术界的注目。相对于较早的书籍有褚千峰的《古砖录》,其后则有数种关于古砖文的辑录,其中光绪年间石印刊行的《千甓亭古砖图释》,逾千种砖文拓片,甚是壮观。
汉代砖文的书法艺术不屑于讨好献媚,反映了最真实的汉代下层社会的信息和民间书法状态,内容多为纪年、记事、吉祥语、图绘等,生动展现了汉代的民间风貌,所包括的书体也是十分全面,有大篆、小篆、虫书、八分、隶书、章草、今草、行书、楷书等。汉代砖文有姓名砖、纪年砖、纪事砖、墓志砖、刑徒砖、吉语時,从一字到百字不等。其制作以范制的阳文居多,也有少量阴文是先锥划后烧固的。更有一些是直接书写“未经范制刻划的”。根据刻划方式的不同分为干刻和湿刻,干刻是在烧制好的砖面上直接刻画,由于烧后的砖块坚硬细腻,使用坚硬的刻刀刻后往往留下瘦硬挺劲的线条,时常含有刻工即兴发挥的成分。而在未干的泥胚上直接刻划的方式则是湿刻,这种方式留下的线条富于弹性,流畅自然,笔顺明确,显示出书刻者熟练的技能。启功先生曾说过“透过刀锋看笔锋”,正式的碑文刻字者大多精雕细琢,自然书写的痕迹必然有所破坏,而汉代砖文因为缺少官方正体的极致规范,反而展现出原生态的面貌,多了一份天然稚趣。
不同于碑版、摩崖等铭石书,汉砖的制作材料主要是土,通过不同的塑形烧制产生不同的物形,但各地土质不同,烧制出来的砖瓦自然存在差异,以浙江和四川为例,浙江砖材质与澄泥相近细腻温润所刻画的字口精美雅致,文人气息浓重,而四川砖因砂岩页岩地质烧至出的汉砖大多颗粒粗大,与宽博粗放的四川书风相符别具苍茫之气,不论是浙江、四川或是山东、河南,这些砖文书法都具有共同的汉代特征但也兼具地方特点,或精美、或粗放、或开张、或内敛。
汉代的造型艺术反映出宽博的审美境界,体现出汉朝开拓的气势。长期以来,书法或明或暗地从民间书法中汲取营养。这些“形制虽小”的砖文作品虽出自民间书手,但同样流露出古朴大度、纯真隽永而又充满活力的时代精神。艺术与创新相辅相成、不可或分,出自平民书家手下的砖文书法不拘一格且各具特色,体现出艺术是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对于自然美的特有发现,是民族审美心理的沉淀。砖文的制作与书刻者大多为下层工匠,普遍文化水平不高,也正因为如此没有受到太多的规制拘束,书刻更加自由,同一种书体时常在砖文中呈现规范化和草率化两种倾向,汉代砖文由于汉代文字的不成熟作为民间书法的一种,展现出丰富的面貌,传统名家书法的表现形式虽然极致完美,但过于单调的面貌与现代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产生了不小的矛盾,清代人面对帖学书法趋于流媚的局面通过新出土的一系列金石材料得以改变走向雄强,但由此带来的碑帖之争也影响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书法发展。日前,得益于更多考古材料的发现,碑帖之争基本结束,碑帖融合已经出现了不小的成果,古今社会书写条件的变化也使得书法的实用价值基本消减,更多的价值体现在艺术性上,而书法的展示空间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型的展厅、多样的尺幅都使得书法面临极强的艺术取向,章法在此时便显得尤为重要,汉代人写字大多是“无意识”的自然书写而已,即便有章法也是长期积累的经验所致,而今人的创作则需要“有意识”的控制整篇作品的章法,正文、落款、印章都在需要考虑的范围,刻意的安排往往不能达到“和谐”的目的,此时面貌丰富却又自然天成的汉代砖文就成为书家取法的重要材料,以期能够在书法艺术发展的新阶段取得成就。汉代砖文为今人的创作提供了营养,反之今人的学习也使得它的地位得到肯定,汉代砖文因此都具有了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为后世书家提供创作创新的范本。
除了书法本身,砖文书法对于篆刻的影响也逐渐显现。赵孟頫编成《印史》,自写印稿,开创“元(圆)朱文”流派,印章逐渐成为一种文人艺术,而清代更是篆刻发展的重要时期,赵之谦提出的“印外求印”更使得篆刻的取法进入新的世界,汉代砖中通过字形夸张产生的不规律章法变化成为多字篆刻内容的极好的样式,而改变规范字形所产生的艺术趣味也成为篆刻当中时常运用的手段,与篆刻同样用刀的特点使得汉代砖书法在群众中极易被接纳,干刻与湿刻产生的艺术效果都称为篆刻当中可以取法的面貌。
二、刑徒砖砖文书法
东汉时期,砖文书法发展兴盛,弥补了“前汉无碑”的缺憾。由于短暂暴虐的秦朝覆灭在前,汉朝开国后引以为鉴,采取休养生息、无为而治,节俭的政策,因此几乎没有较大的汉代早期的碑刻留存至今。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力与经济都较之前强盛繁荣,所以一时之间“非壮丽无以重威”,大造宫殿,建筑用砖数量庞大。再加上中国“重死甚于生”的文化传统与当时大一统的儒家文化影响下催生的“举孝廉”选官制度,使厚葬成为了东汉社会习俗。因此,刑徒砖也是自东汉时始。由于汉代的厚葬风俗,刑徒这一身份卑微的群体,被关押劳作的犯人,致死后才能够获得下葬时的一块简单标明身份信息的随葬墓砖,记述其姓名籍贯与生卒年月等内容。最早,刑徒砖拓本出现于1909年《神州国光集》,随后又出现于端方的《陶斋藏砖记》,罗振玉的《恒农砖录》。
刑徒砖是废弃的建筑用砖,由下层民众草草刻划而成,文字在砖的正面或背面,也有少数于侧面。上面的文字从右至左,篆隶笔法,随势附形。刑徒即是在封建社会生前低贱,死后亦被随意对待的底层,因此墓砖便是工匠或官吏随手找来使用木棍等工具信手刻划的,全部为干刻、阴刻,当然也不会有字格,随意挥就散乱的文字于废弃的残砖之上。
刑徒砖文多为隶书,结体宽阔开张,笔画伸长舒展。由于材料与工具的限制,笔画显得凌厉枯涩,如木棍一般搭架,连接在一起。每个刑徒只有一到两块砖可用,残砖面积有限,因此字与字之间压缩得非常紧密,然而单字的空间却占领得宽阔。如上图所示,“寇”字的捺画,“在”字的撇画,都极尽夸张。笔画形成的无形张力,在狭窄的砖面空间内构成一种力量,即使是略显单薄干燥质感的笔画也如同钢筋铁骨撑住了泥土混合的建筑。每个字外廓为方形,连缀异常紧密,如同一块块墙砖垒砌在一起。这种让人略感单调乏味的章法,彷佛将时间凝滞了一般,在墓中长眠。在无法产生节奏段落与强时间流动性的状态下,刑徒砖文依旧表现出奔放的抒情性,这一点是依靠其对空间的分布而产生的。这是特殊状态下所生发的特殊形式。有些横画甚至伸入了左右行内字的结构之中,浑茫一体,在拘谨的范围内努力寻求丰富的自由。书写者为民间工匠,书写对象又是犯人,因此产生的效果绝非是缜密的思考结果,而是下意识的想象力的表露。
“稚拙天真”是刑徒砖文书法的一个特点,这是许多文人书法家求之难得的审美境界。因为下层工匠与官吏在日常繁重的劳动中,更多地凭直觉和淳朴的情感来表现,毫无矫饰造作之风,意外获得充满形式美感的夸张造型,打开了古人与现代人在心理结构上沟通的桥梁,隔着千年都能使观者感受到那砖石之上承载的悲凉与哀伤。毫无拘束,没有虚假与伪装,更无固化的思想,技巧在这里少之又少。“稚拙天真”的背后是历史的苦痛与凄怆,书法艺术将这两种相异的思想情感统一于线条构成的汉字之中。
“怪异丑拙”,是刑徒砖文书法的另一特点。“怪异”其实是不同寻常,独具画目。刘熙载早在《艺概》中谈到“怪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不难看出,所谓“丑”只是表象,貌似丑的怪石一定蕴含着变化统一的形式美感,怪石不怪则不美。在这里,一般的美丑观念在形式美的原则下已经没有了界限。“丑拙”则如黄庭坚所说“虽其病处,乃自成妍”,其实是外丑内妍。在这里,强烈的个性取代了美的一般准则,不同的个性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了生命的本质美。刑徒砖文寥寥数字,写尽了人世的短暂与残破,是墓志,是死的明证,也是朝露蝼蚁般生命的划痕,生死的两极就在这陋砖之上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