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作家的中国认识
2021-01-24金鹤哲杨丽晶
金鹤哲 杨丽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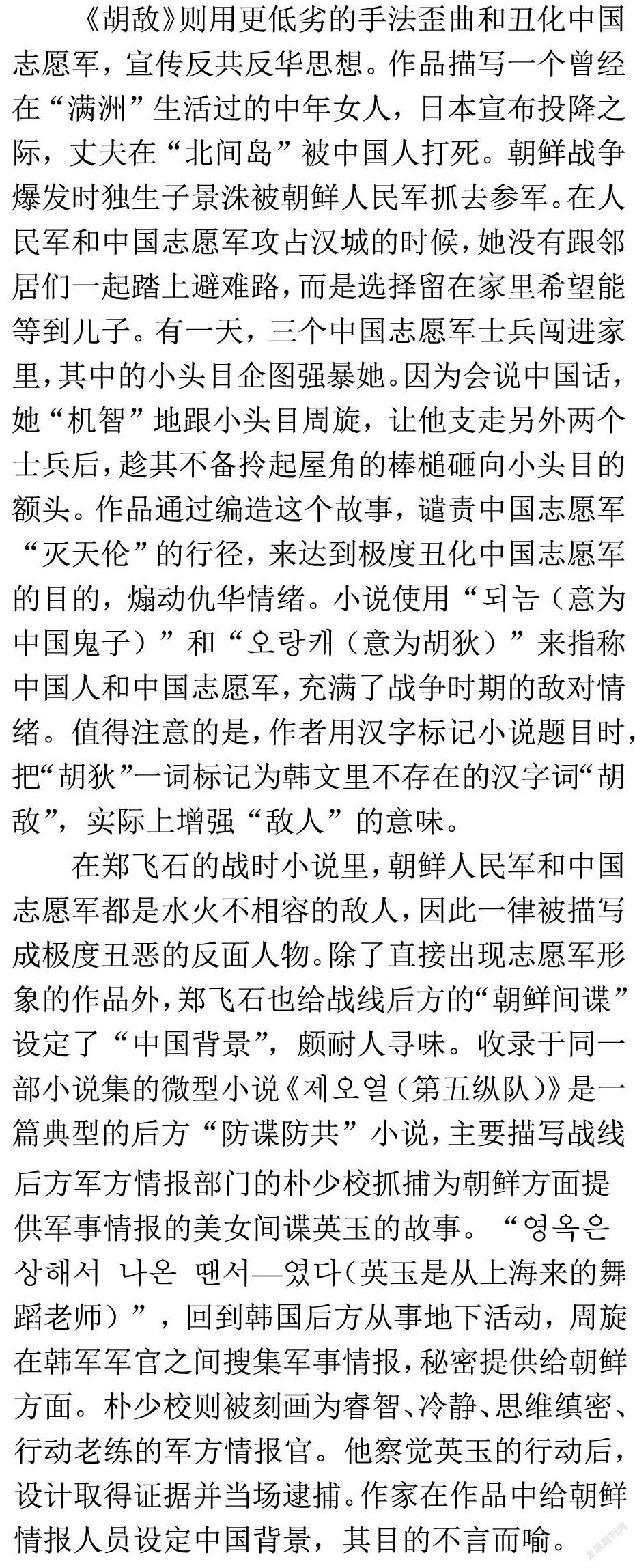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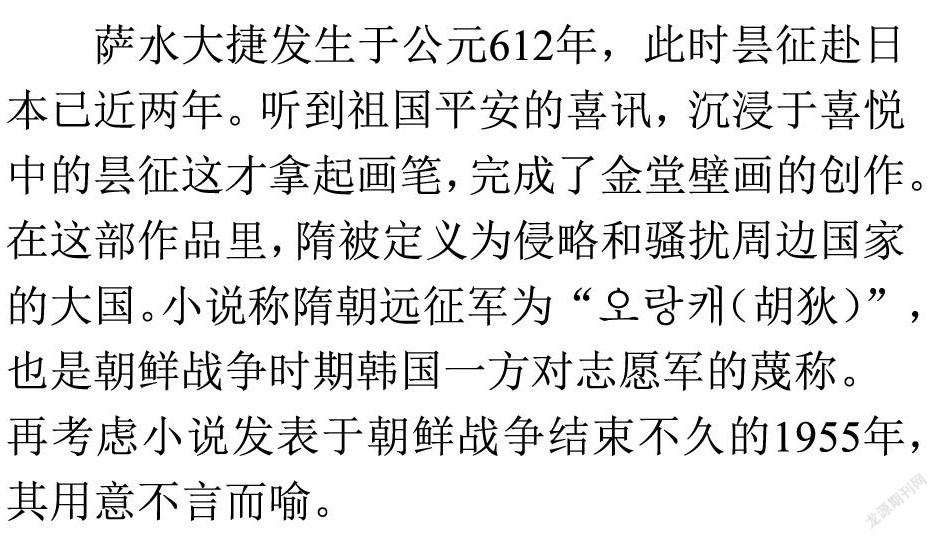
[关键词]韩国战后文学;中国认识;中国记忆;冷战文学;韩国作家
[中图分类号] 1312: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21)01-088-08
1948年,朝鲜半岛南北部各自建国,成为冷战最前沿的两个互相敌视的国家。1949年,新中国成立,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一时期开始,韩国作家笔下很少出现中国元素,以中国为作品背景或叙述空间的作品大多从文献资料和道听途说中取材,因为当时的中国已经成为陌生的、敌对的国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文学中几乎找不到以中国人为主人公或以中国为背景的作品,但是仍然可以从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找到一些中国元素,尤其是能够一窥当时韩国作家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这类作品主要有:(1)出现志愿军形象,或者韩国军人被俘后与中国人接触场面的作品;(2)中国作为敌对势力出现,或者作为反面人物的背景出现的作品,尤其是朝鲜战争时期发表的战时小说;(3)出现议论中国或中国人作为次要人物偶尔出场的作品,如崔仁勋的长篇《广场》。
除此以外,有关中国记忆的小说亦值得关注,一方面是有关古代中国的故事,如短篇小说《金堂壁画》《等身佛》《崔致远》等。在这类作品中,古代中国作为象征性的符号出现,在朝鲜战争这一不可忽略的时代背景下,颇有借古喻今的意味。另一方面是20世纪初抗日题材长篇小说里出现的苦难时期中国,如《北间岛》《关釜渡轮》等。在这类作品中,中国主要作为背景或人物活动的空间出现。
本文拟梳理韩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作品,考察包含中国元素或者反映韩国作家的“中国认识”的文学作品,借投射于作品中的现象及内涵来归纳战时、战后时期韩国作家具有普遍性的“中国认识”和“中国记忆”。
一、战时文学和战后文学描述的中国
经历了朝鲜战争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韩国,社会混乱,经济萧条,民众的精神世界如同战后的焦土一样荒芜,文学也迅速地从反共爱国的战争文学进入了混沌状态,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且短篇小说盛行,长篇小说的创作十分匮乏。因此,韩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者一般喜欢给这一时期的文学贴上“过渡期”的标签,即判定战后文学是混沌、摸索、转型的时期。批评家洪思重敏锐地察觉到这一时期短篇盛行的现象,批判韩国小说的短篇化现象是文学畸形发展的结果,导致作家们在创作中容易偏重情感而忽略理性和逻辑,偏重主观和诗化的映像而忽略客观性和准确性。其结果是把小说置入抒情的世界时,个人和社会的关系被忽视。由于战争给韩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精神创伤,文学因此呈现出的“短小化”“抒情化”,后来的学者将此评价为“情感泛滥”的时期。即使如此,近几年重新评价韩国战后文学的呼声渐高,尤其希望能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战后文学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意义进行重新评价。一些学者认为,战后文学很快摆脱了战时文学形成的反共、爱国、战争浪漫主义风格,开始反思不得不面对的战争创伤和精神废墟,开始直面战后出现的各种社会现象,揭露战争的悲剧和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思索人类的存在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并就韩国文学以后的走向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激烈争论。在当时主张反共意识形态的独裁政权之下,作家们能在相对自由的氛围里各抒己见是非常难得的现象。在这一过程中,法国的萨特和加繆倡导的存在主义、英国“愤怒的年轻人”、美国“机械中的个性(Beat Generation)”、日本的“斜阳族”等文学思潮,都对五六十年代韩国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文学的时代特征,可以用“创伤”“恢复”“转向”来概括,即从战时短暂出现的“反共护国文学”,迅速转向战后文学的“反省”主题,作家笔下的韩国民众陷入挫折与失落、幻灭与怀疑、彷徨与绝望、憎恨与虚无,表现出严重的不安与迷惘。孙昌涉、张龙鹤、康信哉、韩末淑、徐基源、河谨灿等人的创作,主要揭露了战争带来的创伤,表达了克服战争阴影的意志。年轻一代作家李范瑄的《误发弹》和《鹤乡的人们》、李文熙的《口琴季节》、李浩哲的《白纸的空白》等作品,揭露了战争的惨相,反思引发这场同族相残悲剧的原因。黄顺元的《鹤》和《人间接木》等作品,则体现出对人道主义的呼唤。孙昌涉的《人间动物园抄》《剩余人》《神的戏作》等作品反讽式地思索了人类存在的多样性和悖论。这些作家共同的特点是把人道主义和虚无主义混杂在一起。从战后文学的时代主题与文学思潮来看,废墟与重建、传统与现代、艺术与现实均构成了二元对立的格局,韩国战后文学就是在多重对立与和解中寻找自己的方向。韩国学者韩亨九在《50年代的韩国诗》一文中认为,20世纪50年代韩国诗歌的发展轨迹是传统诗歌和现代主义诗歌朝着“参与现实诗歌”过渡的阶段,同时指出:“韩国诗歌的展开情况,不论从传统主义或者现代主义哪一方面来说,其本质都是逃避现实的文学。”进入60年代后仍然出现了许多表现战争创伤的作品,如金承钰的《首尔1964年冬>等作品。但是“六一四”事件和一系列政治事件,促使作家们逐渐从表现战后精神创伤带来的彻底的迷惘和彷徨,转向关注各种社会现实问题,“参与文学”在激烈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韩国文学的主流。这种转变的结果使原本稀缺的中国元素在60年代文学中逐渐销声匿迹。
战时文学的中国形象不可避免地披上了“敌对”色彩。韩国战时的反共护国文学主要由《国防》《战线文学》《军乡》《海军》《战友》《海鸥》等杂志发表的所谓带有“政训”色彩的“战争小说”“前方文学”“军营文学”“后方小说”构成。这些杂志刊发的战时文学作品的内容主要有:(1)鼓吹反共爱国,批判共产主义;(2)关注国际新闻和思潮的变化;(3)描写战争残酷,塑造韩国军人英雄主义形象,鼓舞士气;(4)描写战线后方的社会现实和反间谍内容;(5)描写战俘内容。
在战时文学里,朝鲜人民军常被称为“傀儡军”,甚至被视为“克里姆林宫的婢仆”,如李东柱的诗歌《哦,自由》(发表于1951年《战友》杂志第13期)的一句:“看吧,残恶的‘克里姆林’的仆婢们,如今打上了侵略者的烙印,像可怜的落叶般被冲天的愤恨和诅咒的旋风席卷而去。”在战时韩国文人的作品中,形容中国志愿军形象时常常使用“侵略者”“帮凶”“赤色势力”“胡狄”一类标签。而对于美国或美军则常常形容为“救援军”“伙伴”“战友”。在韩国作家的笔下,朝鲜带上了“傀儡”的标签,苏联被指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主帅和指使者,而中国则被扣上了直接帮助朝鲜作战的“入侵者”的帽子。
例如,杨明文的合唱诗剧《总进军》有一段涉及中国志愿军的诗句:
把胡狄赶回鸭绿江图们江的对面
粉碎砸烂
充满仇恨的复仇之春终于到来了
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帮助朝鲜人民军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土地,向南最远只进入到汉城地区,僵持在三八线附近,绝大多数韩国人并没有亲眼见过志愿军,所以志愿军在文学作品里也只是偶然出现的人物形象,或者由道听途说而拼凑的形象。虽然有史料记载,朝鲜战争中有两万多名中国军人被俘虏,但是韩国的战俘文学中也很少出现中国战俘,韩国的战俘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韩国军人和朝鲜军人。究其原因,应该源自韩国人的民族意识。韩国作家们关心的是兄弟反目、同族相残的悲剧,而中国军人根据作品情节需要常常作为背景出现。如在朴英俊描写战俘的中篇小说《龙草岛近海》里,韩军士兵成柱被“中共军”俘虏后,被编入“傀儡军”投入到一线战场作战,后来因为战俘交换问题重新送回战俘收容所,通过战俘交换回到韩方。在这篇作品里,中国作为参战的敌对方出现在人物讲述的故事里,并没有作为作品中的具体形象出现。
作家郑飞石的微型小说《俘虏》《胡敌》里,则直接出现了中国人形象。《色纸风景——郑飞石微型小说集》是出版于1952年的微型小说集,第一部《女人抄》收录36篇爱情小说,第二部《战场点描》收录20篇战争小说。战争小说都是典型的战时“反共护国小说”和“政训小说”,主要宣扬反共爱国,塑造“国军”英雄形象,丑化朝鲜人民军为“傀儡军”,仇视中国志愿军为入侵的“胡狄”。其中《俘虏》是直接描写中国战俘的小说,通过歪曲事实把中国志愿军丑化为“鸦片鬼”“乌合之众”,以达到鼓舞己方士气的目的。作品虚构了韩方国军“部队长”审讯三名被俘的中国志愿军战士的事件,开篇就把被俘的志愿军士兵形象描写成“脸色暗黄”的鸦片鬼模样。
俘虏们瑟瑟发抖着被押到部队长面前。三个家伙全都是鸦片鬼一般暗黄的脸色。
“部队长”讯问战俘的参军目的时,三个人均表示他们参军并不是因为信仰共产主义或者对这场战争抱有某种信念,而是聽说参军就可以随意吸食鸦片。战时小说歪曲事实,丑化中国志愿军战士为“鸦片鬼”的手法令人大跌眼镜。作者的动机很明显,就是通过把中国志愿军描写为“鸦片鬼”,宣扬中国军队是一群毫无战斗力的乌合之众,借此鼓舞己方军人的士气。
崔仁勋的《广场>是20世纪60年代“分断文学”的代表作,也是一部苦苦思索朝鲜半岛分裂的现实,以及个人的信仰、人生、爱情、理想的观念性小说。生活在首尔的主人公李明俊不断思索个人与集体、人生、生活的意义等等问题,认为“人不能只生活在自己的密室。因为他与广场是相连的”。他渴望一种公众的广场和个人的密室能够和谐共存的社会和生活。但是目睹韩国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后,他对韩国的政治充满了失望,尤其因为父亲生活在北方而受到警察拷打审讯,便选择逃离韩国来到朝鲜,成为《劳动新闻>编辑部的记者,并开始新的恋爱。但是在朝鲜的生活,却让他发现了一个“灰色的共和国”。“明俊在北边遇到了灰色共和国。不像满洲的晚霞那样赤红,也不存在改革热情的共和国。”更让他吃惊的是,共产主义者并不希望变得有激情。他在党的安排下巡回朝鲜各大城市进行演讲时,清楚地认清了朝鲜的真实面目,那是把个人欲望视为禁忌的地方。人们无精打采地坐着,脸上看不到任何共鸣。他们根本不像住在革命共和国的热情市民。处于极度失望中的李明俊被派到战场上,偶然与北边的恋人恩惠重逢,产生了新的期待。但是恩惠牺牲的消息令他又一次幻灭,最后沦为俘虏。战争结束后,俘虏们在板门店选择去南边还是北边,无论面对朝鲜一方的劝说,还是韩国一方的劝说,他只是反复地回答:“中立国!”在前往中立国的轮船上,预感到自己在中立国仍然要重复毫无意义的生活,李明俊选择了投海自尽。
这部作品对资本主义韩国和共产主义朝鲜都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这部作品里,对任何一方的描述都没有战时文学中二元对立的冷战意识和敌对意识,包括仅出现两次涉及中国的描写,也以一种中立的视角进行观察。一次是身为记者的李明俊报道中国东北的朝鲜人农场的种种问题后,编辑部举办自我批判会批评明俊的思想问题,编辑部主任说:“同志!去年伟大的中国人民完成的人民经济计划,衣服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量超过了全国人民的使用量。可能有一两个人在干活儿时穿了日帝遗留下来的衣服,你就咬住这件事,在报道中怀疑人民充足的物质生活水平,这全都是因为同志你这个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造成的。”这一事件暗示了当时中国和朝鲜的同盟关系。
第二次涉及中国的描写,则是板门店交换俘虏时,直接出现一个没有任何外貌刻画的“中共代表”。在板门店劝说俘虏的时候,李明俊第五次用“中立国”三个字回答朝鲜方面的劝诱时,“不知道坐在旁边的中共代表嚷嚷了什么,朝鲜方面的军官凶巴巴地瞪着李明俊说:‘好!’”李明俊接下来走到韩方代表和美方人员面前,同样冰冷地回答:“中立国。”这段描写同样从侧面暗示了当时中国与朝鲜的关系。
二、韩国战后文学的中国记忆书写
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冷战体制影响下敌对意识仍然弥漫在韩国社会,中国元素很少出现在文学作品里也就不足为怪了。在这种状况之下,与中国有关的历史题材小说颇为引人注目。包括纯文学的主将金东里宣扬人文主义的两部短篇小说,郑汉淑演绎古代高句丽僧人昙征的爱国情怀的历史小说,还有以近现代中国历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北间岛》和《关釜渡轮》。
郑汉淑(1922—1997)的历史短篇小说《金堂壁画》发表于1955年,演绎了古代高句丽僧人昙征东渡日本创作壁画的故事。昙征(579—631)于公元610年东渡日本,在奈良县法隆寺为金堂绘制壁画,并在日本传授着色、纸墨、水碓制造等技术,对日本佛教绘画产生了深远影响。法隆寺的金堂壁画与中国的云岗石窟、韩国庆州的石窟庵并称“东方艺术三大瑰宝”。郑汉淑的历史小说演绎了这一历史事件,把隋炀帝远征高句丽的事件作为小说的主要背景,以此影射朝鲜战争。
小说开篇是高句丽僧人昙征坐在山坡上叹息。他应日本奈良县法隆寺住持的邀请东渡日本为法隆寺的金堂绘制壁画,但是时值隋朝大军攻打高句丽,祖国处在风雨飘摇的危难之中,令他忧心忡忡。另一方面,在祖国危难之时,他却东渡日本作画,内心无比自责,所以不能执笔做画,每天沉浸在忧愁叹息中。
现在祖国的北方,正卷入胡狄的铁蹄之下,自己不能回到祖国,反而远离祖国,昙征不能不陷入难以承受的苦闷。
由于昙征忧虑国家安危,无法安心作画,法隆寺的“倭僧”们误会他是骗子,甚至持棍追打,要将他赶出法隆寺。只有住持看出了昙征的心思,极力加以保护。但是忧心忡忡的昙征一直无法执画笔创作,每日遥望北方,祈祷祖国免于灾祸。
有一天,法隆寺住持跑来告诉他一个好消息,高句丽的乙支文德将军在萨水大败隋军。
有好消息啊……炀帝的两百万大军,在乙支文德将军的一把利刃之下,如枯叶般粉碎了。看样子大师绘制金堂壁画的时机到了。
相比之下,金东里则以存在主义观照人类的命运,以超越时代和民族的目光审视人类历史文化,他在作品中描绘了一个理想化的中国,但是这个中国却在遥远的古代。
金东里的短篇《崔致远》发表于1957年,以古代的中国唐朝为背景。小说结构采用了金东里拿手的“框形结构(story within a story)”形式,即外线故事是叙述者“我”——日本殖民统治后期的朝鲜人,在海印寺寄居期间,前往白莲庵拜访清籁禅师时,偶然得到一本新罗时期大诗人崔致远(669—935)所撰的《双女坟后志》。据传这本书是崔致远晚年生活于海印寺红流洞时撰写的,由寺里的僧人代代相传秘而不宣。“我”读了这本珍贵的汉文书籍并翻译成韩文,在与《文章》杂志协商发表事宜过程中,不幸被日本殖民警察逮捕,包括这本奇书在内的所有书籍都被没收,后来竟然遗失了。内线故事则是根据“我”读过这本书的记忆,以第一人称叙述视角重新复原了《双女坟后志》的故事。《双女坟后志》以公元875年的唐朝为作品空间,讲述“我(新罗人崔致远)”12岁入唐,18岁进士及第,出任溧水县尉的第二年,探访县内一处驿站时,听说此地有一处“双女坟”很有名,便前往游览,并有感而发,做诗《双女坟记》祭奠。
谁家二女此遗坟,寂寂泉扁几恐春。
形影空留溪畔月,姓名难问冢头尘。
芳情倘许通幽梦,永夜何妨慰旅人。
孤馆若逢云雨会,与君继赋洛川神。
“我”以此诗示次日来访的诗友“长秀”时,长秀却担心“我”会“人鬼恋”。一日诗友“陈德”读过这首诗后来访,邀请“我”前往他家做客。在陈德家的“别堂”,陈德的外甥女——鮂娘为我们唱歌,鲔娘则在隔壁弹琴伴奏。一来二往,“我”与鮂娘互生爱慕之情,但是她始终不肯以身相许,原来她放心不下双目失明的双胞胎妹妹鲔娘。小时候的鲔娘十分美丽,人见人爱。大家都赞美鲔娘,姐姐鮂娘心生妒忌,用热水烫瞎了妹妹的双眼。长大后父母双亡,两姐妹住在舅舅家里相依为命。虽然鮂娘与我互生爱慕,但不能丢下妹妹嫁人,所以拒绝了我的好意。妹妹了解姐姐的心思,为了不拖累姐姐,耽误姐姐的幸福,选择了悬梁自尽,希望姐姐可以与意中人喜结连理。听到妹妹自杀的消息,鮂娘也选择自缢,坚守与妹妹同日生同日死的誓言,留下一段令人唏噓不己的悲情故事。
崔致远在韩国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也是神话和传说中的人物。而在这部小说里,崔致远活动过的中国唐朝不仅是一个历史的空间,更被描绘为令人神往的国度。作品中的唐朝,像理想国一样可以给所有的人生存发展的机会,比如外国人也可以得到学习和科考的机会,有能力的外国人还可以得到官职走上仕途。而且小说刻画的几个中国人形象,包括诗友长秀和陈德,红颜薄命的鮂娘和鲔娘,都是饱读诗书、举止优雅、有情有义的人。从中可以窥见中国唐朝在作家金东里心目中的地位。
无独有偶,金东里发表于1961年的短篇小说《等身佛》同样出现了中国唐朝,同样采用了“框形结构”。外部故事的主人公“我”被日本殖民者强征入伍,作为韩国学生兵随日本军队参加太平洋战争,驻扎在中国金陵(南京)附近。为了逃避战争的杀戮,“我”找到了曾经留学日本的中国人陈奇修并请求帮助。为了取得陈奇修的信任,“我”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愿免杀生,皈依佛恩”。在陈奇修的帮助下,“我”历经千辛万苦逃离日本军营躲入偏僻深山的净愿寺。“我”在寺院里发现了供奉于金佛阁的一尊金铸等身佛像,感受到强烈的震撼。圆慧大师给“我”讲了唐朝有一位叫万寂的高僧烧身供养后成佛的故事,金佛就是在万寂的遗体上铸金塑成的。小说的内部故事则发生在1200年前的中国唐朝,即万寂禅师燃身供养而成佛的故事。万寂是中国唐代的高僧,小时候母亲改嫁谢家,为了儿子能继承谢家的家产而要毒杀同父异母的哥哥信。目睹母亲下毒的万寂悲从心生,欲抢食有毒的食物却被母亲制止。哥哥信明白了后母的用意,一日离家出走后便踪迹全无。万寂为了寻找离家出走的信,四处流浪,迷惘彷徨之后,皈依佛门。十年后的一天,他得知哥哥因为麻疯病而痛苦不堪时,终于下决心燃身供养让人类摆脱烦恼。在焚身那天,出现了许多奇异的现象。后来僧人们在万寂身上铸了金,并建造了金佛阁。小说《等身佛>直接“引用”了净愿寺住持圆慧大师拿给“我”看的《万寂禅师烧身成佛记》的汉文,并附了译文:
万寂法名俗名曰耆姓曹氏也金陵出生父未祥母张氏改嫁谢公仇之家仇有一子名曰信年似与耆各十有余岁一日母给食于二儿秘置以毒信之食耆偶窥之而按是母贪谢家之财为我故谋害前室之子以如此耆不堪悲怀乃自欲将取信之食母制之惊而失色夺之曰是非汝之食也何取信之食耶信与耆默而不答数日后信去自家行迹渺然耆曰信己去家我必携信然后归家即以隐身而为僧改称万寂以此为法名住于金陵法林院后移净愿寺无风庵修法于海觉禅师寂二十四岁之春曰我生非大觉之材不如供养吾身以报佛恩乃烧身而供养佛前时忽降雨沛然不犯寂之烧身寂光渐明忽悬圆光以如月轮会众见之而振感佛恩愈身病众曰是焚之法力所致竞掷私财赛钱多积以赛镀金寂之烧身拜之为佛然后奉置于金佛阁时唐中宗十六年圣历二年三月朔日
“等身佛”象征了人性和佛性的结合,既包含了自我救赎的意义,也包含了解救他人的意义。因此,作品的主题可以理解为用宗教式的拯救使人类摆脱苦恼的一种探求。在内部故事里,当时的唐朝如同一处信仰的圣地,人不仅可以通过苦修成佛,还出现了许多灵异的事,因灵验异常而受到僧侣和信徒的尊崇和膜拜。主人公“我”为了逃离战争的杀戮,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愿免杀生”,这一行为可以看作是为了摆脱罪恶的现实而做出的自我牺牲,跟唐朝万寂和尚的“燃身供养”有着相同的意义。在外部故事里,战火纷飞的“中国”成了一个来自日本殖民地朝鲜半岛的学生兵的避难所,也是让他得以认识等身佛的故事,并领悟佛法无边的修道之所。无论内部故事还是外部故事,金东里刻画的中国人形象,除了为作品情节发展提供矛盾冲突的“万寂的生母”外,都是充满正义、乐于助人、乐善好施的人。无论是唐朝的信、万寂和尚.还是太平洋战争时期山寺里慈悲为怀的僧侣,都是正义、仁义的形象,与战时文学和战后文学中出现的当代中国人形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与郑汉淑和金东里的借古喻今式的中国古代记忆不同,安寿吉和李炳注的中国记忆来自亲身的中国生活体验,在描写朝鲜人主人公的移动轨迹的同时,或直接或间接地描绘了20世纪上半期动荡不安的中国社会,刻画了身份各异的中国人形象。
安寿吉的长篇历史小说《北间岛》以日帝压迫下的朝鲜人移民中国东北的历史为题材,描写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延边地区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源自作家的中国东北生活体验。1924年14岁的安寿吉跟随家人来到中国龙井生活和读书,后来担任过龙井《间岛日报》和新京(长春)《满蒙日报》记者,其间创作并发表了许多以朝鲜人移民社会为题材的小说。除去1926年至1932年辗转于咸兴、首尔、日本求学的时间外,安寿吉在中国生活的时间长达15年之久。1945年6月回到故乡咸镜南道咸兴疗养,1948年南下韩国定居,并开始了旺盛的创作活动,1977年病逝于首尔。1959年4月通过《思想界》杂志发表长篇小说《北间岛》,1967年全部结集出版,是朝鲜半岛南北分裂后第一部反映朝鲜人移民“满洲”历史的长篇小说。小说描述主人公李昌允(第三代)一家四代在中国“满洲”的移民苦难史,历史跨度为1865至1945年光复。第一部讲述朝鲜人李翰福一家和妻弟一家由咸镜道钟城郡移居中国龙井。有一日,孙子昌允在清人地主董凤山家的地里偷吃土豆时,被长工们抓去剪了辫子头送回家。李翰福见到辫子头一气之下晕倒在地死去。昌允长大后在董风山的功德碑上放火后逃离村子,其父被清朝巡捕抓去拷打至死。第二部是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由于日本人的奸计,清人和朝鲜人之间开始出现不和的兆头。清末延边地区马贼横行,清政府为阻止日本伸出的黑手,对朝鲜人实行了高压政策。第三部,昌允被污蔑杀人,迁居龙井附近的大桥洞,以种田和烧砖为生。昌允的弟弟在天宝山矿区被马贼洗劫一空。第四部,二战爆发后,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朝鲜人与清人之间的冲突持续升温,昌允迁居珲春,开了一家冷面店。儿子正守上了新学,昌允也成为抗日团体“重光团”的成员。1919年3月13日龙井发生了朝鲜人集会宣读独立宣言并游行的事件,同年北京暴发“五四”运动。第五部,正守加入独立军并参加了汪清县凤梧洞阻杀日军的战斗。独立军解散后,正守开始了教书生涯。返回龙井后,他到日本领事馆自首,服了五年刑。其间父亲昌允去世。正守出狱后与英爱结婚,不久因参与独立复兴运动再次被捕。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出狱,前来迎接他的妻子英爱说,儿子已经长大了,上学期在班里排名第二。
《北间岛》随着人物的移动轨迹,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延边地区的动荡局势、社会现象、风土人情,包括民间的三皇五帝信仰、地主董凤山家里的过年风俗、妇女裹足的习俗、街道和店铺等等,也记录了包括1920年马贼袭击珲春县城事件、洪范图指挥的汪清县凤梧洞战役、3月13日龙井朝鲜人反日集会等历史事件,刻画了朝鲜人、中国人、日本人的矛盾纠葛。作品中出现了大量中国人形象,有对朝鲜人时好时坏的地主董凤山,袭击珲春城的马贼张江湖,主张“韩国人中国人一样”的革命党人王寿山,接受过新学并同情朝鲜人的进步人士“董凤山的侄子”,集安县中国人学校里的教员王老师(因五四事件从北大退学)等人。作品中也出现了稽查处和延吉厅里的官僚和巡捕的丑恶形象,也有怀着救国救亡理想而奔波的延吉道尹、孟富德团长等正面形象。
《关釜渡轮》是一部自传体性质的长篇小说,1968年4月至1969年3月发表于《月刊中央>,共17章。小说的叙述时间从1960年代(序章)开始,通过回忆从主人公刘泰林读小学的1940年代,一直到朝鲜战争时期刘泰林失踪为止。其中第三章描述了主人公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体验。作者李炳注1921年生于韩国庆尚南道,1943年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专科部文艺系,随后进入早稻田大学,不久被征用为学生兵不得不退学,随日军前往中国苏州地区。在这部小说里,第一人称主人公刘泰林于1944年1月20日入伍,28日即与1000多名学生兵一起由韩国大邱火车站出发,经过奉天、热河抵达山海关,再换乘火车经济南、南京于2月5日抵达苏州,历时九天。1946年2月被美军遣送回国,由上海港上船,于3月3日抵达釜山港。考虑到这部作品带有自传小说色彩,可以推测作家李炳注的中国体验长达两年。小说第三章描写中国体验时,由于“学生兵”这一特殊的身份和视角,以及战争末期残酷灰暗的社会现实,作品中有关中国社会环境和风景的描述不多,偶尔出现时也是寥寥几笔带过。作品中的中国人形象也都是在日帝的压迫之下毫无希望地苟延残喘的底层平民,或者战争的牺牲品。如1944年刘泰林抵达南京时见到的中国人,是一群脸色灰暗、面无表情的人。1944年11月劝说刘泰林逃离军营的战友许凤图,独自一人逃离军营被捕归队后,随即发疯了。据说许凤图为了逃离军营,与附近一户中国人家事先商定协助他逃走。当他按约定时间来到这户人家时,开门的却是日本宪兵。原来是这对中国人夫妇向日军宪兵提供了情报。后来这对夫妇也被日本宪兵杀害。刘泰林通过朋友的转述,听到了日军拿中国俘虏进行活体刺杀练习的事。战争结束后,刘泰林来到上海居住了半年。作品主要围绕抗日运动团体和“韩籍士兵”展开,这群人的规模逐渐达到几千人,其中有不少保持武装的人,也有寻衅滋事被中国当局逮捕的人。作品对国共内战等时局也只作了简单的背景介绍,更多地是关注一个韩籍士兵的个人体验。
李炳注和安寿吉的小说再现的是珍藏在作家记忆里的20世纪初内忧外患、动荡和苦难时期的中国和中国人,同时也是一个朝鲜人反日立场和视角之下的中国,夹杂着共同受害意识、反日同盟意识、文化的异质感、新奇感等等复杂的情绪。
三、结论
纵观这一时期的韩国文学作品,朝鲜战争时期中国元素作为“敌对方”偶尔出现在作品里,之后在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文学作品里很少出现中国元素。尤其是战后韩国作家关注民族分裂的現实、战后国民精神的恢复、国内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导致无暇顾及外部事务,更无心描写冷战的敌对方。拥有璀璨文明的古代中国——尤其是唐朝,在韩国作家的中国认识里作为“理想国度”的记忆得到书写,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与韩国是同样饱受外敌之扰的苦难国家,而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被视为冷战的对立方,朝鲜军队的“帮凶”。即,通过战时文学“现时的敌对”和战后文学“苦难的20世纪”“记忆中的盛唐”之间的对比,可以发现当代中国和古代中国作为“现实与记忆”的二元对立结构,而苦难的20世纪相同的处境,即韩国作家中国认识变化的时期,三者形成了五六十年代韩国作家的中国认识的切入视角。
[责任编辑 全华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