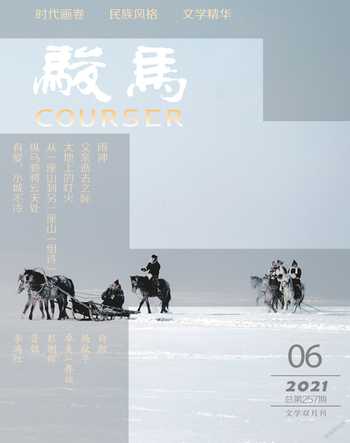葛湾人家
2021-01-22于博
于博
崂山脚下的葛湾是个屯子,现在并入了长岭村,归王哥庄镇管辖。葛湾有三十多户人家,清一色的二楼,红瓦白墙,蔚为壮观。别墅式的建筑错落有致,在崂山脚下,一边扯着崂山的云雾,一边踩着黄海的浪花,如诗如画。
我们驾车穿过崂山隧道,过仰口收费站,一条蜿蜒在崂山脚下的公路把黄海和崂山切割开来,这条路叫滨海公路。路两边挺立着塔柏,像一个个端庄的迎宾小姐,又像一轴轴绿色的屏风。崂山像个端庄秀丽的女人,含情脉脉地注视着大海。她的怀抱里,各式各样的石头像顽皮的孩子撑破了绿色的衣衫,眨着调皮的眼睛,惊奇地窥望着这个世界,一切对于他们似乎都是新奇的。海浪发出哗哗的响声,仿佛在对崂山说着呢喃的情话。
我们要去吃一次开在山海之间的农家宴,就在葛湾。农家宴的主人叫林仪正。因为时间早的缘故,我们在离葛湾不远处的一个山崖上停下,几步下去,就是一面斜坡,斜坡上长着桃树,树上结着青色的果实。树空间,有类似榆树钱一样的东西,同伴纠正我,说这就是崂山绿茶。我很惊讶,原以为崂山的绿茶应该长在崂山深处,长在崂山最神奇的地方,最接近云朵和太阳。同伴说,崂山绿茶遍布崂山,山顶、山腰、山脚都有。当然,山的深处茶品应是好的。
从坡上踏过几块巨石,就踩到了柔软的沙子上。当然,这里的沙子比起青岛海边浴场的要粗粝许多。走上十多米,就踏入到海水中,水很清凉。没过几秒,那清凉就传遍全身,一下子舒服许多。此時是下午三点多,海水有些不安分了,开始向岸边拥挤。远处几艘渔船在游弋,并不是欣赏海景,而是渔民在出海。向远处望去,海水和浮云连在一起,就把天与地缝合了。我们几个人攀上水中一块巨大的礁石,仰面躺下,一面青山为屏,三面海水荡漾,身边清风徐徐,头顶白云悠悠,耳边鸥鸟喁喁,顿觉天地悠悠,但绝没有怆然而泪下,只觉得自己依附在一块仙石之上,有超然物外的感觉。
大约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同伴叫我,说涨潮了。我们便下了礁石,却见来时只没了脚背的海水已经没过了脚踝。等我们坐在来时坡上的石头时,海水开始发威了。滚滚的海水一浪推着一浪,翻卷如雪,一排排地涌上来,冲上礁石,发出吼声,然后变成无数泡沫。海水如同冲锋的战士,前仆后继,一浪高过一浪,终于将我们走过的沙滩悉数占领。这时,一位老者拿着渔网从远处走来,腰间挎着一部小型收音机。他边向水里撒网,边听着评书。我想这位老人一定是住在葛湾的。我这样想,也回身向葛湾望去,却见一幅人间仙境图——崂山起雾了。
崂山的云雾气势恢宏,大片流云在毫不顾忌地飞走,如千军万马在搏杀,在驰骋,让人心旌摇曳。看这场面,我在猜想,是不是崂山道士在作法?无数个道士伸出双手把浓云撕碎,又轻挥浮尘,将碎云化成粉末、化成气,漫过崂山,继续向西北方向疾奔。
崂山的雾又像一幅水墨画。水墨画是变化的,是无数崂山道士正在现场挥毫点厾。这些道长画累了,就在原地烹茗煮茶,那缕缕水汽氤氲,弥漫了整个天际。葛湾就在这汹涌翻腾的雾气的笼罩之下,红瓦白墙愈加分明,和琼楼玉宇相仿。科学证明,崂山的云雾对于茶叶生长大有裨益。云雾多,空气湿度大,有利于茶叶中含氮和芳香物质。崂山绿茶,闻名遐迩,品质优良,崂山云雾功不可没。
一边是海浪汹涌,一边是云蒸雾卷,山海奇观中,我们向葛湾走去。大家爬上满是翠绿的慢坡,绕桃树,过茶墙,来到一栋绿树掩映的别墅下。主人从大门里奔出来,一件白色背心,黑色短裤,剃平头,脸上绽放着真诚的笑容。他就是林仪正,这栋别墅是他的家,也是他们夫妻开办农家宴的地方。农家宴的名字叫山海湾,和地理位置很匹配。
走进林家二百多平米的楼房,我对生活在海边山下的农民有了艳羡。进门是一个宽敞的庭院,一面照壁上写着一个大大的福字,让我感到一阵和谐与温暖。墙角几株耐冬翠绿挺拔,茂盛葳蕤。耐冬,学名山茶花。崂山里有很多这种植物,传说是道教祖师张三丰带来的。他曾三上崂山,最后带来了耐冬。这种植物抗寒,经霜叶尤翠,斗雪花更艳。如今,耐冬已成为青岛的市花。
林仪正家有四株耐冬,已有二十余年的树龄了。林仪正说,有人曾出价每棵5万元买走,他没答应。不是因为他现在条件好了,而是以前生活的痕迹只有耐冬能记住了。那所老宅被崭新的别墅取代,整个葛湾已经融入现代化的生活当中。看到耐冬,林仪正就回到了从前,也让他格外珍惜现在。
进入一楼,是个宽绰的大厅,两边是四个房间。除了主人住一间外,其他都做了客房。客厅中间摆放一张很大的圆形餐桌,足以容下十多位客人就餐。林仪正说,没有单独设餐厅,主要是想给客人家一样的感觉。大厅外侧有一块绿石引起了我的注意。一问,果然是崂山绿石。宋代就有关于崂山绿石的记载。崂山绿石就出产在葛湾坐落的仰口海湾。仰口海湾有两条颜色各异的石脉蜿蜒入海,海水退朝后,绿石裸露,便可采石。采石的地方叫海坑。海坑产的绿石称为水石。水石经海水亿万年的浸透,光润莹泽。相反谓之旱石。旱石虽未经海水洗礼,但风蚀日剥,满是沧桑之感,古朴厚重。无论海坑和旱坑,出产的崂山绿石极具观赏价值,随着崂山绿石的禁止开采,崂山绿石也越发显得名贵起来。
经过木制楼梯,我们来到二楼,二楼的格局和一楼一模一样,只不过中厅的餐桌要比一楼的大得多。从二楼推门出去,是一个平台,站在台上,左望是苍茫的大海,右看便是青翠的崂山。海,就在脚下歌唱;山,就在眼前起舞。我说,这真是一个不错的观景台。我们站在观景台上,如同在一幅山水画卷之间。这时,林家嫂子端来一壶茶,热情地招呼我们品一品崂山绿茶。她特意强调茶是自家种的,除了她亲手采摘的,还有南非美女摄影师采摘的呢。
“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崂山绿茶不仅有解毒排毒、降脂减肥、提神养神的功效,还有抗癌作用,是我国绿茶中的经典茗品。崂山绿茶于1959年才引种成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茶叶种植面积只有60公顷,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现在达到800公顷。林仪正家有三亩茶,年收入几万元。让林家嫂子高兴的是,茶园不仅为他们家带来了收入,也是来崂山的客人主要的游玩项目之一。山海之中,观赏一株株茶树、采摘一片片嫩叶,体会一下当茶农的感觉,让游人心旷神怡。说到这些,林家嫂子总是不能忘记一个南非朋友,她叫Catherine。凯瑟琳?我说。林家嫂子点点头。凯瑟琳是一位摄影师,她来到崂山,被这里的景致所陶醉,对这里的绿茶情有独钟。不但拍不够,还和林家嫂子学采茶,乐此不疲。凯瑟琳说,她要把崂山带到非洲,要把崂山绿茶带到非洲。听罢,我喝了一口茶,不仅品到了浓浓的茶香,也感受到了国际友人对崂山的满满爱意。
坐在观景台上,看黄海,观崂山,品绿茶,阵阵微风吹过,带着大海的气息,带着花草的香味,真让人有说不出的惬意。这时,主人喊我们吃饭,我们依依不舍地从二楼下到一楼,但见中厅的餐桌已然摆满了菜肴,海鲜自是不可少,山野菜也非常醒目,但有一道菜是主人力荐的。这道菜叫崂山凉粉,是青岛名小吃。据说,崂山凉粉起源于道家,有上千年历史了。崂山凉粉主要原料为石花菜,是生长在海底礁石上的海洋植物,加上崂山的山泉水,以慢火熬制而成。崂山凉粉滑溜溜,加以蒜泥、香菜末、红油辣椒,咬之有韧性,口感清凉爽滑。青岛人对崂山凉粉钟爱有加,登崂山途中,身体乏力,吃一碗崂山凉粉,顿觉精神百倍。所以,登崂山不吃崂山凉粉等于没来崂山——这话是青岛人说的。
来青岛不喝青岛啤酒也等于没来青岛。青岛啤酒确实让人倾倒,尤其是散啤。青岛大街上有一道风景,就是来来往往的行人中你会见到不少人都提着一个塑料袋,内装颜色橙黄的液体,上面浮着白沫,雪一样。黄色和白色几乎各占一半。那就是青岛散啤。喝一口麦香浓郁,沁人心脾。
当然,我们丰盛的晚宴就是从喝青岛散啤开始的。
林家嫂子大名叫孙玉芝,老家是青岛即墨的。她说原先生活条件也很艰苦,两三亩山地,连吃饭都成问题。后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葛湾人家都过上了好日子。
孙玉芝透着幸福和喜悦,但随着我们交谈的深入,我对葛湾人家有了新的印象。我想,居于山海之间这样的位置,岂不要家家搞农家宴吗?但是,葛湾只有三户人家在做这个项目。我一下子对葛湾人家肃然起敬。如果大家都把目光盯到这块蛋糕上,势必会造成僧多粥少的局面,也会带来无序竞争。四十户左右的葛湾人家都有自己的事业,不是在经营茶园、茶店,就是开民宿、超市,再就是在青岛市区开厂子,开绿石观赏店,开海产品店,在崂山山里做旅游生意,总之,都干得风生水起。倘若都挤到农家宴这条道上来,道路就会越来越窄。
林仪正脸上始终挂着真诚的笑容。他过来敬酒,说他要早点休息,明早还要去打工。我很诧异,这个农家宴一年收入几十万,還要去受累?林仪正笑了,他说湾里比他有钱的人家多了,平时都要挤时间去崂山风景管理区打工,清理死树枯枝和活动的石头。林仪正说,除了增加收入外,也是为崂山的发展做贡献。我一下子干了杯中的啤酒,为了他这番话,为了勤劳淳朴的葛湾人家。
屋内灯光灿烂,向外望去,滨海公路的路灯蜿蜒着直达天际。渔港灯火辉煌,高高的灯塔发射着耀眼的光芒。海,睡了;山,睡了。一天的喧嚣终于在夜的帷幕下归于沉寂。但崂山里有许多人在静静地期盼,静静地期盼明天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在崂山看日出,那是多么美妙的景色啊。可是等我们早早醒来,打算等待日出的时候,外面已经是大雨滂沱了。我们多少有些遗憾。但是,生活中有点遗憾,才会让我们充满希望和期待,才会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
我们吃过早餐后,告别了林家的山海湾农家宴,告别了葛湾,沿着滨海公路过仰口,从山水画廊一下子闯入到了繁华都市,一路上我的脑海里出现的都是海和山的画面。崂山像个仙女似的含情脉脉,而黄海就如同热情奔放的小伙子,两个恋人幸福地依偎在一起。让我们感到最幸福的应该是葛湾,是生活在葛湾的普普通通的林仪正们。同样是葛湾,同样是山与海的依偎,但只有改革的春风吹来时,葛湾人家才真正体验到幸福的滋味。
葛湾,我们还会回来的,为了一朵黄海的浪花,为了一块崂山绿石,为了一杯崂山绿茶,为了一碗崂山凉粉,为了激动人心的日出时刻,为了葛湾人家的幸福生活。
责任编辑 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