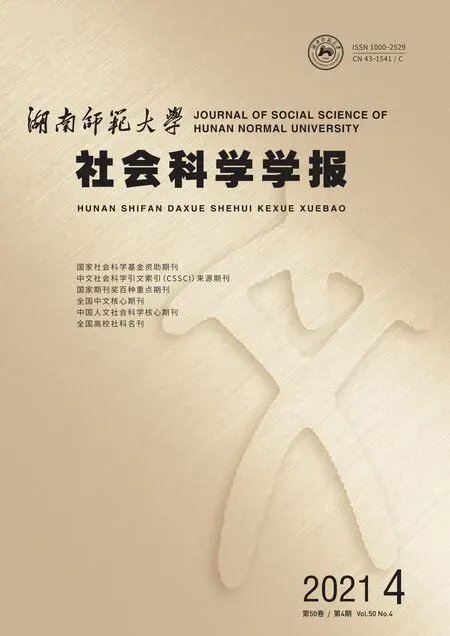善与恶的双重悖论
——论马洛悲剧中的“恶棍英雄”
2021-01-17常远佳赵炎秋
常远佳,赵炎秋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处于从传统戏剧向现代戏剧过渡的时期。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在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他是英国悲剧的奠基者和创始人,对英国悲剧的繁荣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尤为值得重视的是,马洛首创了一类被称为“恶棍英雄”的悲剧角色。这类人物极具影响力,在英国文学史上形成了一类重要的类型角色,同时由于其矛盾性和复杂性在学界引起了长久的争论。本文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特别是恩格斯对道德和善、恶的论述分析解读这类角色,为理解这类角色提供新的维度。
一、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和马洛笔下的恶棍英雄
英国传统戏剧与现代戏剧差别巨大。英国本土戏剧起源于教堂礼拜仪式,最初是为了更生动易懂地向教徒宣讲《圣经》。因为这一形式大受欢迎,戏剧逐渐脱离教堂走向市场。但英国传统戏剧形式受《圣经》影响很大,主要为神秘剧和道德剧,神秘剧基本脱胎于《圣经》;而道德剧则是在《圣经》基础上的寓意化的延伸。总而言之,英国本土戏剧形式较为单一,内容较为单调,单靠本身的发展必然极其缓慢。之所以有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的繁荣,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受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戏剧的影响。没有古典戏剧的影响,“英国戏剧会如何发展难以想象;奇迹剧和道德剧的发展必然极其缓慢”[1]。
英国戏剧首先并未受到古典戏剧的影响,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带来了古典悲剧的范本。有相当长一段时期,英国戏剧都处于模仿古典戏剧尤其是古罗马戏剧的阶段。这一时期有一些悲剧和喜剧上演,但成就和影响并不大,直至马洛的出现。如何其莘所言,“1558年伊丽莎白女王登基标志着英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随之而来的是政治上的相对稳定和经济上的繁荣,这都为英国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英国舞台上并没有出现惊天动地的变化,直到八十年代后期马洛开始为伦敦舞台撰写剧本,才揭开了英国戏剧文学发展史上新的一页。”[2]
马洛是“大学才子派”中成就最大的一个,被公认为莎士比亚之前最重要的戏剧家。他的剧作得到高度评价,任生名认为“他的四大悲剧《帖木儿大帝》上下篇,《浮士德博士的悲剧》《马耳他的犹太人》《爱德华二世》,可以说是英国悲剧在莎士比亚之前最辉煌的成就”[3]。由于马洛对英国悲剧的巨大贡献,瑟芒兹(John Symmonds)称其为“英国戏剧之父和创始人”[4]。马洛不仅被誉为英国悲剧之父,同时也被认为是极具开创性的戏剧家。他第一次将戏剧情节集中于单个人物[2],在《马耳他的犹太人》中首次将喜剧因素应用于悲剧[5],他对悲剧的创新有目共睹。
尤为值得重视的是,马洛的悲剧中出现了一类新的悲剧英雄,这类人物既有英雄人物的特质,又有违反当时主流道德标准的一面。比如《帖木儿大帝》中的帖木儿,一方面具有非凡的诗才、勇气和魄力,另一方面又手段残酷,杀人如麻;而《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的浮士德,一方面智力超群,另一方面又将灵魂卖与魔鬼。这类人物被评论家称为“恶棍-英雄”(villain-hero)①。马洛以恶棍英雄作为悲剧主人公,由此 “开创了英国戏剧史上的一个先例”[2]。因为一般而言,悲剧英雄由好人来充当。亚里斯多德谈到悲剧英雄的时候强调:“第一点,也是最重要之点,‘性格’必须善良。”[6]这一观点影响深远,因此马洛突破这一传统也显得尤为可贵。
马洛创造的恶棍英雄给英国戏剧舞台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为表现人性的复杂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恶棍英雄人物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数位剧作家所效仿”的对象[2],其中也包括莎士比亚。罗根(Robert Logan)认为马洛创造恶棍英雄所用的新的戏剧手法、非传统的表达方式大大影响了莎士比亚[7]。在马洛恶棍英雄的影响下,莎士比亚创造出麦克白、理查三世这样的经典人物。经由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们尤其是莎士比亚的发展和再创作,恶棍英雄成为英国文学史上著名的类型人物,从弥尔顿的撒旦,拜伦塑造的曼弗里德、该隐、路西弗等“拜伦式英雄”,雪莱的普罗米修斯,直至《呼啸山庄》中的希斯克利夫身上都清晰可见这一类人物的影子。
对于马洛的恶棍英雄,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多。最先研究恶棍英雄的波伊尔(Clarence Boyer)将“恶棍”定义为“为着一个自私的目的,肆意违反了观众或是读者认同的道德标准”的人。当“恶棍”在戏剧中充当中心人物时,这种戏剧就是以恶棍为主角的戏剧(The Villain as Hero)[8]。后来的评论者们虽然沿用了波伊尔创造的这一指称,但都承认恶棍英雄角色的英雄特征。Hero“英雄”的含义逐渐取代了其“主角”的含义。如赫丁(Nancy Kaye Hedin)认为恶棍英雄是“赫拉克勒斯和阿特柔丝的奇怪的混合物”[9]。布林(Allison Breen)则将恶棍英雄描述为“具有超乎常人的能力和潜力,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与道德或法律发生冲突,但他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完全邪恶的人。事实上,他通常是一个伟人,具有很多英雄的特质比如勇气、智慧和力量……当他违反了行为标准时,成了恶棍”[10]。凡·埃克(Van Eck)认为恶棍英雄是哥特式英雄的前身。他们的“恶”来自人性的黑暗,他们显示了个人与“传统、规则、秩序和信仰”之间的冲突[11]。
由于恶棍英雄人物的复杂性,学界对马洛笔下的恶棍英雄人物也一直存在争论。如浮士德,一方面有学者认为他本性堕落,贪恋财富美色和权力[12],是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其悲惨结局完全是罪有应得[13];另一方面却有学者将其视为文艺复兴的英雄,或是普罗米修斯式的勇士[7]。对于帖木儿,一方面他被视为杀人如麻的残酷征服者,另一方面他也被视为英勇的战争英雄。巴拉巴斯虽一度被称为“恶的化身”[14],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对他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但他英雄的一面得到肯定;他追求财富也不再被学界视为贪婪,而是被视为追求超越自我的力量。
波伊尔的贡献在于指出恶棍英雄人物与古典悲剧人物的不同,但他仅仅强调了恶棍英雄“恶”的一面。后来的研究者逐渐认识到这类人物的英雄特质,但基本停留在将恶棍英雄视为简单的“恶棍与英雄”“善与恶”的混合体。凡·埃克认识到这类人物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但并未阐明其主体诉求的历史进步性。具体到浮士德、帖木儿和巴拉巴斯,评论者则多从善或者恶单个维度进行分析,没有认识到其善恶的双重性。事实上恶棍英雄人物除了性格的矛盾,其悖论性还与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现实状况有着深刻的关联,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历史与道德之间的二律背反。只有引进历史的维度,深刻剖析这类角色身上存在的双重悖论,才能充分阐明恶棍英雄角色的英雄本质和历史进步性。
二、恶棍英雄的第一重悖论
恶棍英雄的第一重悖论在于从道德的一般角度来看,这些人物既有“恶”的一面,也有英雄的一面。善恶主要以道德的标准进行判断。道德“就其最一般的意义来说,总是被理解为调整人和人之间的行为规范的总和”[15]。道德用来维护人与人之间正常的关系,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帖木儿、巴拉巴斯都有严重的恶行。帖木儿为了维护战时的纪律,亲手杀了临阵逃脱的儿子;因为敌方投降的时间错过了他设定的时限,帖木儿实施了屠城令;因为无力挽救自己的爱人,他一怒之下烧了他们停留的镇子。巴拉巴斯则设计挑起总督儿子和女儿情人之间的争端,使二人在决斗中同时丧生;对于违背自己意志皈依基督教的女儿,他亲手熬毒粥毒死她,同时毒死了修道院的所有其他修女。他们都违反了通行的道德规范,所以从道德的角度来判断,这样的角色是“恶”的。
在“作恶”在这一点上,浮士德这个人物不同于帖木儿和巴拉巴斯,即便在他获得了非同一般的魔力之后,他也没有干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只是戏弄了一下教皇。以一般意义的道德标准来判断,浮士德的所作所为算不上真正的恶。但浮士德还是被许多评论者视为犯下万劫不复之罪,这是因为他背叛了上帝。这涉及另外一重 “罪”,本文将在下一节中详细讨论。
帖木儿的情形有些特殊,因为他是一个征战英雄,他所处的并非常态的社会环境。一般来说,通行的道德标准并不适合作为他行为判断的标准。但他杀子明显违背了人伦关系;他屠城和纵火烧镇子则都是不必要的杀戮行为。即便以战时标准判断,也明显有违正义原则,所以帖木儿常常被谴责为残酷、嗜血的。
传统悲剧理论反对将这样的角色作为悲剧英雄,因为这会妨碍悲剧情感的产生,达不到悲剧目的。亚里斯多德认为悲剧的目的在于“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6](陶冶的原文是“卡塔西斯”(Katharsis),也常被译为“净化”)。亚里斯多德认为只有好人遭难才会引起怜悯和正义的同情,坏人遭难实属活该,不会引起怜悯;而恐惧则是由于观众害怕剧中人物的厄运降临自己头上而引起的,但恐惧只在观众觉得自己跟悲剧人物“相似”的情形下才会发生,倘若是与普通观众相差甚远的大奸大恶之人,也不会引起恐惧之情。因此在传统悲剧中,这种道德上有明显缺陷的人物一般不会成为悲剧的中心人物。
但马洛赋予恶棍英雄人物典型的英雄特征,并且将其作为悲剧中心人物。无论是帖木儿、浮士德还是巴拉巴斯,都具有超乎常人的智慧和能力、非凡的气度这些典型的英雄特质。帖木儿气度非凡,勇气超群,具有无往而不胜的信念和决心,在战场上所向披靡,即使在面对强敌时也毫无惧色,从容迎战。帖木儿不但具有非凡的军事领导能力,还具有非凡的诗才;巴拉巴斯不但具有非凡的商业才能——他是马耳他的巨商,拥有全城一半的财富——而且极具胆识和才能,他在财产被总督强权剥夺之后,靠一己之力将财产夺回;浮士德聪明博学,无人能比,年纪轻轻便“荣膺博士头衔”,并且“一切喜欢辩论和崇尚玄理的人/都远非其匹”[16],不仅如此,他的医道也十分精湛,他开的方子“被视作千金良方”,他曾“让全城逃过瘟疫的灾害”“使成千的凶症消除于无形”[16]。
值得注意的是,恶棍英雄都有作恶的行为,但其行为的根本动机都与作恶无关。他们作恶并非为了狭隘的个人利益,而是出于偏执的性格或者不可违逆的个人意志。比如帖木儿之所以杀子是因为无法容忍自己的儿子临阵逃脱——本来应该像他一样在战场浴血奋战结果却躲在帐篷里避险——这样胆小和怯懦的后继者被帖木儿视为对自己荣誉最大的侮辱;比如在他的爱人赞鲁克莱特去世的时候,也因为极度悲伤和愤怒无法宣泄,而迁怒于她去世时所在的镇子,将其付之一炬。而巴拉巴斯之所以亲手毒死女儿是因为最爱的女儿竟然皈依了他最为仇视的基督教,这在巴拉巴斯看来是无法容忍的背叛。与时时处处盘算个人利益、挑拨离间的伊阿古或者油滑怯懦又贪婪的福斯塔夫稍微比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恶棍英雄的作恶与普通意义上为了狭隘的个人利益而损人利己的行为有大区别。他们的动机和主要行为并非作恶,也并非为了名利或者个人享受而损害别人。
同时,恶棍英雄的最大魅力也是来自无边的个人意志——这一恶棍英雄本质的特征。帖木儿、浮士德和巴拉巴斯三者追求的具体目标虽有所不同——帖木儿追求无限的政治权力,浮士德追求知识带来的无穷力量,而巴拉巴斯追求无限的财富,但三者都共同执着于追求超越自我的力量,共同的特征都在于拥有无限的自信和无边的自我。这一共同特征可由帖木儿极具代表性的宣言来表达,“我用铁链锁紧命运,/用手把住方向。/ 只要太阳不脱轨,/ 帖木儿就不会被打败”[17]。帖木儿由于具有非凡的个人意志,勇气超群,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他甚至凭借这非凡的胆识和能力,在战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爱丽丝-费莫(Ellis-Fermor)盛赞《帖木儿大帝》把“自信提高到令人炫目的高度”,使“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樊篱被推倒”[18]。浮士德和巴拉巴斯莫不如此,他们都是凭借超强的个人信念和能力克服了各种看起来无法克服的阻力。这样的形象在当时具有非同一般的魅力,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强调人的价值能力以及人的无限可能性有十分重要的关系。
表面看来,马洛的恶棍英雄既有善的一面,又有恶的一面,其性格似乎相互矛盾。但实际上,他们作恶的行为和英雄的魅力都来自其本质的性格特征——无边的自我,意志至上,以及横扫一切障碍(包括任何道德规范)的决心。因此,恶棍英雄看似悖逆的性格其实具有某种内在一致性。恶棍英雄都是典型的叛逆者,如果为了符合所谓的“好人”要求而弱化其性格,那才是真正损害了角色性格的一致性和表现力。马洛这样表现恶棍英雄是否会损害其英雄性?从研究的结果来看,这样非传统的人物形象虽然引起了争议,但其英雄性得到了一致公认。
目前既有的研究基本停留在认为恶棍英雄是善恶皆具的悖论英雄。但本文认为恶棍英雄的根本特质是其英雄性。这并不仅仅因为他们都被马洛赋予了英雄形象,而是因为从历史的维度来看,这类人物代表了社会进步的方向。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都具有悲剧英雄的根本特质,那就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只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变化,他们为之牺牲的目标也与传统悲剧英雄的目标有所不同。
三、恶棍英雄的第二重悖论
恶棍英雄的第二重悖论在于他们的另一种“恶”本身体现了历史的进步。他们的“恶”有两种:一种是纯粹的道德的恶,如帖木儿、巴拉巴斯犯下的人伦之罪,一种则是体现了历史的进步的“恶”。这种“恶”从当时主流价值观的角度看的确是恶,但从历史的进程来看,它们又具有进步的意义。恩格斯指出:“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独立中运动的,所有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19]正因为道德都是具体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所以道德总是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比,总有一定的滞后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在一定的经济状况下产生的道德便必然会与正在发展的经济基础拉开距离,成为维护落后的现存秩序、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这时违反道德标准反而会成为一种历史的进步。关于这点,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的道德观时有过深刻的论述:
在善恶对立的研究上,他[费尔巴哈]同黑格尔比起来也是很肤浅的。黑格尔指出:“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但是,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20]
正是由于道德具有特定的阶级和历史局限性,当现有的道德意识阻碍历史进步的时候,历史的进步常常表现为对原有秩序的悖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善”;然而从持有原主流道德的人来看,便是“恶”。这就是恶棍英雄身上存在的第二重悖论,是更深层次更复杂的悖论。
这一点在浮士德身上体现得非常清楚。浮士德并没有什么伤天害理的行为,他之所以被斥责为万劫不复的罪人,是因为他背叛上帝,将灵魂卖给魔鬼。从基督教道德来看,这是最严重的“罪”。然而浮士德将灵魂卖给魔鬼是为了获取知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英勇进步的行为。
浮士德追求的是知识,但这一追求被基督教污名化为“巫术”,教廷当局常常借着打击巫术的名头迫害科学家。剧中浮士德追求的是魔力,但实际上在中世纪,“魔术和科学之间并没有清楚的分界线”[21]。魔术被教会分“善性魔术”和 “邪恶魔术”。 “善性魔术”指“通过自然哲学或超自然智慧控制元素”[21],无伤大雅,并不被教会禁止;而“邪恶魔术”指与恶魔勾连,是教会严厉禁止的恶行。实际就是,不对教会统治构成威胁的就被列为“善性魔术”,反之则为 “邪恶魔术”;而魔鬼不过是与上帝对立的一个隐喻指称而已。浮士德将灵魂卖与魔鬼,显然就是“邪恶魔术”,也被称为巫术(necromance),为教会严厉禁止。教会禁止科学研究常常以打击巫术的名义进行;而科学家也常常被诬蔑为巫师而被处以极刑,“宗教审判突然又在各处流行起来,并把医生们当作亵渎神明的人或幻术家来惩罚或烧死”[22]。西班牙学者迈克尔·塞尔维特(1511-1553)正要发现血液循环的时候,教会便烧死了他。因此浮士德追求的魔术,其实质就是被教会污名化了的科学。
为什么基督教要阻止知识的传播?因为知识与权力是联系着的。福柯说:“真理从不在权力之外,或缺乏权力。”[23]关于真理的斗争“也不是‘代表真相’的问题,而是一场关于真理的地位的战斗以及它所承担的经济和政治的角色”[23]。基督教统治的基础是蒙昧无知,科学的发展、知识的更新往往会造成对基督教权威的质疑。比如教会宣扬地心说,而哥白尼发现日心说,这无疑会削弱教会的权威; 比如宗教改革家路德宣扬“信徒皆祭司”和“因信称义”,宣称所有信徒有直接跟上帝交流的能力和权力,这就意味着教士和教廷不再拥有作为普通信徒和上帝之间的“中介”的特权,也意味着教廷很多敛财手段失去了理论基础,例如著名的“赎罪券”。
基督教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阻止知识传播,残酷迫害科学家。这导致中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非常缓慢,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缓慢。浮士德冲破这一残酷阻力,为追求知识不惜背叛上帝,挑战基督教的权威,具有非常进步的意义。肖明翰盛赞他的行为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浮士德代表了文艺复兴人对知识的渴求,是‘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的化身。他在似乎穷尽一切知识后,不惜以灵魂做交易,与撒旦立约,宁愿下地狱也要获取凡人所不能得到的知识。这种在基督教世界前无古人的气概,表现了文艺复兴人追求知识、追求人的力量、追求人的发展的不可阻挡的决心。”[24]浮士德对知识的渴求代表了历史进步的方向,但在当时的宗教权威看来,无疑是对基督教权威的极大挑战,是不可饶恕的“恶”。
巴拉巴斯追求无尽的财富。这在传统基督教价值观看来,是贪婪和罪恶的金钱欲。传统基督教观念并不主张追求财富,《圣经》上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25]《圣经》上还说:“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25]贪婪被列为基督教七大重罪之一,贪财无疑也被基督教严厉谴责。巴拉巴斯贪求财富,所以从传统基督教价值观来看,他是“罪恶”的。
但从历史进步的角度来看,巴拉巴斯却代表了新的经济力量。处在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巴拉巴斯所代表的形象具有非同一般的进步意义。伊丽莎白时期英国处于资本主义飞速发展时期,伊丽莎白一世大力施行重商主义政策,她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大力发展国际贸易。其政策大大促进了海外贸易,使贸易额迅猛增长,为英国带来巨大的财富。巴拉巴斯富可敌国,拥有一支航行世界各地的国际商船队,他代表的并非普通商人,而是这一时期为英国创造了巨大财富的跨国商人。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巴拉巴斯代表了资本主义这一先进的经济力量,正是这一力量,推动了文艺复兴后英国社会的发展。马洛对于恶棍英雄巴拉巴斯的塑造非常成功地传达了这个人物的英雄性。虽然一度这个人物被误解,但其正义性,伟岸的形象,以及对文艺复兴中“自我”观念的宣扬都符合历史进步的方向。
巴拉巴斯的形象非常复杂,他形象上恶的一面,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的“犹太性(Jewishness)”[14]。科克说:“巴拉巴斯作为犹太人,自动继承的坏名声有囚犯、伪善者、吝啬者、背叛者和不知悔改的魔鬼。”[26]另一方面,可能与他代表的早期资本主义商人地位低下相关。韦伯指出:“在现代开始的初期,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态度的唯一或主要的代表者,决不是商业贵族式的资本主义企业家,而主要是正在兴起的地位较低的工业中产者阶层。”[27]
但更值得重视的是马洛赋予巴拉巴斯这一形象的英雄性,这一特征是传统犹太商人不具备的。同时,马洛颠覆了传统的犹太人代表“恶”,而基督徒代表“善”的对立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正义化了巴拉巴斯反抗总督的斗争。总督费南兹利用强权收缴犹太人的财产来缴纳马耳他拖欠土耳其的贡赋,这本身就是不义的,是对犹太人赤裸裸的歧视和压榨。更重要的在于,费南兹将巴拉巴斯的所有财产全部收缴,使巴拉巴斯失去经商的基本条件,破坏了新的正在茁壮成长的经济力量,成了阻碍历史进步的旧势力。巴拉巴斯因此与之斗争便具有无可否认的积极性。巴拉巴斯这一形象既包含了传统基督教价值观对金钱欲的谴责,又反映了新的经济力量的进步性。这一矛盾的人物形象非常传神地折射出了在历史过渡时期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态。
帖木儿则挑战了传统的政治秩序。中世纪人们相信君权神授,实行长子继承制。中世纪社会是等级严明的社会,人们相信社会等级由上帝安排,因此神圣不可侵犯。帖木儿出身卑微,只是一个牧羊人,但却追求王位,这颠覆了中世纪的政治秩序和传统等级秩序。任何想要改变自己社会等级的企图都是对神圣秩序的扰乱,对上帝的不敬。因此帖木儿想要超越自己的出生追求王位,这样的雄心“被看作是最可怕的罪”[28]。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却是一个进步。君权神授的问题在于以出身决定王位,而不是以能力、气概来决定王位。如果正好王位继承人是懦弱无能之人,这对国家来说就是巨大的灾难。帖木儿的第一个对手波斯王米塞德斯,虽然是命定的王位继承人,但是他懦弱无能,无法平服众臣,给国家带来巨大的危机。帖木儿依靠过人的能力和气度获得王位, 获得其将领的爱戴,所向披靡,他显然比一个无能的继承人更加胜任王位。帖木儿的形象大获成功。说明这一形象符合当时人们的期待,代表历史进步的方向。
另一处深刻的悖论就是如何看待“自我”,它究竟是道德的“恶”还是历史的进步?表面看来,无论是帖木儿、巴拉巴斯还是浮士德,其行为动机都出自“自我”。这与古希腊悲剧中悲剧英雄为了民族大义而行动有本质的差别。波伊尔就此认为,恶棍英雄都出于“自私”的动机。但“自我”放在当时的具体语境,具有非同寻常的积极意义。因为“自我”是被基督教观念一直压制的对象。传统基督教主张原罪说,认为人类自主向善的能力自亚当夏娃偷吃禁果之时就已经被损坏。如果背离了上帝,人的意志会由魔鬼控制。通过强调人的原罪,基督教定义了罪性和渺小的“自我”。“自我”一直是被压制的对象。这一负面的“自我”观念很大程度上压抑和束缚了人的本能,限制了人的发展,也是造成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的基础。文艺复兴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对于“自我”的观念经历了一个觉醒的过程。具有代表意义的是皮科的观点,他在《论人的尊严》的演讲中称赞人具有无限可能,能“成为在天父的孤独飘渺中与上帝为伍,超乎万有,迈逾群生的一个神灵”[22]。这一观点相信人具有发展和完善自我的能力,甚至具有超越自我,与上帝为伍的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布克哈特称文艺复兴为“自我”的发现。
因此马洛剧中的恶棍英雄为“自我”而行动,呼应了文艺复兴的进步要求,是对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丑化和矮化“自我”的一种强力对抗。看起来恶棍英雄是为了“自我”而行动,但由于这一“自我”长期被基督教压制,所以恶棍英雄通过追求和彰显自己的个人价值反抗基督教对“自我”的压制具有特别的意义。马洛通过正义化恶棍英雄的世俗追求和自我价值,“将个人的需求升华为一种广泛的‘善’”[29]。也就是说,通过恶棍英雄追求和彰显自己的个人价值,反抗了基督教对人的世俗要求的压制。恶棍英雄对自我的肯定和追求象征着人们个人意识的觉醒,是对自身价值的寻求和独立人格的追求,体现了个体对生命意义的极限追求,是历史的进步。
四、恶棍英雄——马洛人文主义世界观之体现
恶棍英雄虽有缺陷,但马洛主要体现的是其英雄形象。如果和原型相比较,这一点会更为明确:浮士德和帖木儿都被马洛极大地美化和英雄化;巴拉巴斯虽没有确定的原型可与之比较,但他远比一般的犹太人类型角色更具英雄性。帖木儿的历史原型是一个野蛮的侵略者。他“是一个征服世界的梦想者,以亡命徒的身份啸聚群众,浸假称霸一方,东征西讨,所向无敌,而贪求无魇,手段残酷,使人闻之丧胆,欧洲人目之为强权黩武残酷嗜杀的象征”[30]。他不但名声令人恐惧,腿也是瘸的,形象欠佳。而马洛悲剧中的帖木儿,“身材高大,身姿挺拔”,具有“阿喀琉斯”般的“完美构造”[17];不仅具有超凡的气度、能力和智慧,形象俊美,且具有非凡的诗才。而浮士德的形象脱胎于《浮士德博士传:受诅咒的生活和应得的死》(TheHistoryoftheDamnableLifeandDeservedDeathofDoctorJohnFaustus),这本书一般被称作《英国浮士德书》(EnglishFaustBook)。浮士德的原型生性邪恶,为追求世俗享乐背弃上帝;他获取魔力之后,常去偷酒盗肉,左拥右抱众多美女,利用魔力实现种种低俗的物质享受;在得知会下地狱之后,变得万分恐惧。原型浮士德胆小怯懦,愚昧低俗,根本没有马洛剧中浮士德的勇气、抱负和能力。马洛剧中的巴拉巴斯也超越了传统的犹太人形象。马洛不但赋予巴拉巴斯过人的勇气、智慧和能力,还颠覆了传统的善恶结构,将与之对立的基督教总督丑化和恶化,使巴拉巴斯的行为具有正义色彩。
帖木儿象征无边的意志,浮士德象征追求知识的决心和魄力,巴拉巴斯象征追求财富的野心,无论野心、追求知识还是财富,都为传统基督教强烈反对,具有这些象征意味的形象在当时英国本土戏剧中都是被极力丑化的形象。比较马洛的帖木儿、浮士德的形象与其原型,或者巴拉巴斯与传统的犹太人定型角色,我们不难得出结论:马洛对恶棍英雄的英雄化,完全属于个人的有意创造。马洛为什么要将传统基督教贬低的形象英雄化?因为他们都代表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强调个人价值,重视知识和教育,相信人的理性,肯定人的世俗追求的精神;他们三者极力强调大写的自我也是对基督教压制自我、贬低自我、罪性化自我的强力反抗,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对人类的信心和信念的肯定。马洛将代表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形象极大地美化和英雄化,表达了他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
马洛恶棍英雄人物身上的悖论特征是对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社会现实状况的生动体现。马洛的恶棍英雄创作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当时英国正处于一个不同的价值观相互激荡冲撞的时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仍然是传统基督教价值观,这一观念反对人们追求世俗幸福,反对自我实现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认为人生活的中心是荣耀上帝。但随着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兴起,人们的个人意识逐步觉醒,人们渴望追求知识,追求荣誉,追求自我实现。人文主义观念是对传统基督教观念的反抗。马洛的恶棍英雄,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精神,也同时挑战了传统基督教价值观。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恶棍英雄形象所代表的要求是进步的;但是,因为恶棍英雄挑战他们身处其中的价值系统,“而必然被他们挑战的对象和身处其中的生存状况所界定”[24]——恶棍英雄因为挑战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在当时的语境下总是被判定为“恶”,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他们挑战了传统价值观中不人道和有碍历史进步之处而代表着一种普遍的“善”。马洛恶棍英雄人物身上的悖论特征正是文艺复兴时期新旧价值观冲突的体现。
恶棍英雄人物生动地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社会变化,为我们理解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新旧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激荡和冲撞提供了非常好的素材。恶棍英雄人物之所以具有矛盾的形象是因为他们既有道德的“恶”,也有历史的“善”。表面看来,恶棍英雄是善恶不明或者善恶兼备的人物,但这类人物的实质是其英雄性。他们虽然由于背离了传统基督教主流价值观而被判定为“恶”,但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恶”正是代表了历史进步的方向。
注释:
① villain-hero最初被译为“恶棍-英雄”,本文认为去掉中间这个连字符更能体现这类人物的复杂性和悖论特征,故在下文中称为“恶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