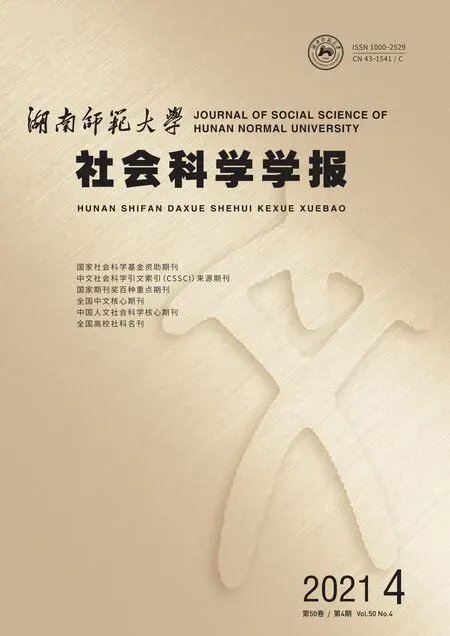自我的再认:《乘风破浪的姐姐》中年女性形象的重构
2021-01-17曾一果王可心
曾一果,王可心
一、引言:父权制下中年女性的身份焦虑
父权制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性结构,渗透到社会组织的各个角落,其特征正在于“是在家庭单位中制度性地强化男性对妇女和子女的权威”[1]。因此女性长久以来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成为“被统治”“被管理”“被凝视”的对象。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似乎迎来了改善的转机:全球化将原本身处男性依附地位的女性整合进市场之中,使其成为家庭经济来源的一部分。养家糊口不再是男性独有的职责,女性在家中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与自主性。伴随着女性受教育和接触媒体信息机会的增加,其群体身份逐渐走向多元,并按照各个年龄阶段所承担责任的不同产生分化。当然,女性通过劳动获取报酬这一社会行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地位。因此,相较于还处于人生初级阶段的青年女性,承担着父权制下更多附加责任的三十岁以上的中年女性群体更加值得关注。中年女性面临着“配偶之间的人际关系、家庭成员的工作和生活、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联系、家务劳动、子女照顾、性欲和情感寄托”[1]等诸多现实问题,需要在同一时间范畴内扮演多重角色,并根据日常生活场景的转换而不断变化。霍尔也明确提出,个体身份“在当代逐渐支离破碎,”它是“建构在许多不同的且往往是交叉的、相反的论述、实践及地位上的多元组合。它们从属于一个激进的历史化过程,并持续不断地处于改变与转化的进程当中”[2]。组建家庭、繁育后代和发展事业……多元身份中搭载的多元责任将中年女性置于更为复杂与压抑的社会语境之中,被动接受着来自父权社会的“全景敞视”。
福柯基于对监狱的研究看到了视觉背后权力话语的运作机制,当代数字科技与视觉监控体系的完善则进一步加强了父权制的社会控制力。相较于屹立在环形监狱中心的瞭望塔,信息时代的权力运作以更加多样、隐匿的形式展开,例如微博、微信、短视频和人脸识别系统,都将个人行为纳入社会治理结构。在父权制审美框架的制约下,电视和网络节目多将镜头与麦克风聚焦于青年女性的身体表演与话语表达,长期“失语”的中年女性则处于弱势地位,她们在承担更多物质压力的同时,精神需求也难以得到回应与满足。
正是在女性群体普遍“失语”的状态下,中年女性被迫接纳父权制的审美规训,“保持青春”“保持身材”“保持美丽”等标准迫使其向青年女性看齐,努力营造属于自己的“不老神话”。对“冻龄美人”等幻想自我的追寻正是父权凝视下的审美框架与消费主义合谋的产物,就像海德格尔所担心的“人之人性和物之物性,都在贯穿意图的制造范围内分化为一个在市场上可计算出来的市场价值。这个市场不仅作为世界市场遍布全球,而且作为求意志的意志在存在的本质中进行买卖,并因此把一切存在者带入一种计算行为之中”[3],在自我凝视、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过程中,中年女性的“本我”逐渐被异化和扭曲,曾经依赖与构建的精神世界难以为继,最终走向西蒙娜·薇依所警告的“匮乏”状态。薇依认为,人的灵魂具有各种需求,但灵魂经常处于未得到满足的匮乏状态[4],“灵魂的匮乏”所强调的不仅是精神需求难以满足所带来的自我压抑,更在于其持续地将中年女性置于身份焦虑的轮回中,使之难以脱离。
二、反抗规训:中年女性的多重身体展演
相较于《妈妈是超人》《婆婆和妈妈》《妻子的浪漫旅行》等以家庭为叙事核心的“她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的突破点在于跳脱父权规训下的女性定位,将媒介制码的重心放在中年女性对父权凝视的身体反抗实践中。弗兰克指出,“身体”事实上是在由制度、话语和肉身组成的等边三角形交叉点上形成的。话语用来表示身体的可能性和局限的“图绘”,能为身体“理解”自身提供“标准的”框架;制度则是这些话语实践发生的地点和语境;最后肉身性指一种肉身的、物质的身体[5]。
(一)话语反抗:彰显独立的女性意识
语言作为一种传播符号体系流动于整个人类社会,人们借助语言表达自我、再现世界、创造价值与认同。正如迈克尔·豪格所说,“语言是文化的媒介,是认同或身份的象征符号。”[6]因此,无论是报刊书籍还是电影综艺,其所挑选与应用的编码语言都严格对应编者/创作者的核心思想与文化机制,以更好地指认明确群体身份认同。
1.“自我”为中心的女性话语叙事
在传统话语框架中,“以自我为中心”的叙事话语一般与“自私自利”“利己主义”等贬义词语相联系,从而背离了“无私奉献”的主流话语形态。因此,在大部分“她综艺”节目中,中年女性一直以为配偶、为父母、为儿女“服务”的姿态出现,处于较为被动的话语地位。但《乘风破浪的姐姐》并没有延续这一趋势,而是展现女性以“自我”为中心构建的话语模型,每一位参赛选手都尽可能充分地表达个人想法,例如郑希怡和蓝盈莹在歌词分配上的“没有客气”,宁静直言“我想赢”,每一位成员“毫不犹豫”地选择自己喜爱的歌曲。女性并非天生便是沉默的,在权力的面前可以利用话语“包含的那些被说出来和被掩盖的东西,那些所需的和被禁止的阐述;利用它隐含的变体和不同的结果”[7],以将其作为反抗的工具,打破父权对中年女性“隐忍”“宽容”的道德规训。把握话语即把握权力,只有直接表达自我思想、自我意愿和自我选择,中年女性的声音才有被大众听见的可能。
2.“去依附性”的文本主题
与以往女团选秀综艺不同的是,《乘风破浪的姐姐》对表演曲目的选择与改编都表现出强烈的“去依附性”,即弱化男性在场,着力凸显女性的独立与自由精神。相较于《创造101》等倾向于打造“温柔可人”等传统意义上女性形象的青年女性选秀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则以更为激进的方式反抗两性关系中女性所面对的不平等压迫与教条主义,例如《Gentlewoman》中“女人要像个女人,什么时代留下的老梗”等歌词对父权规训的直白反击,《相爱后动物感伤》《女孩儿与四重奏》中女性对爱情的“冷处理”,文本的情感重心从以往对甜蜜爱情的追寻转变为聚焦历经风雨后女性的成长与蜕变,对女性主导自我情感加以鼓励。
在强化男女平等意识、淡化爱情必需性的同时,彰显女性自立、自由、自爱的“去依附性”文本主题是贯穿节目始终的核心话语。例如最初的公演曲目《兰花草》“不愿居暖房,迎风晒月光,我慕天地广,花语意铿锵”表达女性人格独立的呼声,第二次公演的《仰世而来》“明白人生去日无多,别摇摆别闪烁,我要我属于我”唱响了“活在当下”的自由之音,以及复活赛团战中的《玫瑰少年》“哪朵玫瑰没有荆棘,最好的报复是美丽,最美的盛开是反击,别让谁去改变了你”则重在树立自爱自信的独立女性形象。从以上种种文本书写中可以看到其始终将女性作为具有完全自主性的个体进行论述,与男性意志彻底剥离开来,实现文本与心理上的双重独立,为之后身体和权力的反抗奠定情感基础。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给教育教学带来巨大冲击,给课程改革注入强大动力。近几年对微课程的应用研究已成为教育的热门话题。综观国内对微课、微课程的研究,应用前景看好,在微课程的概念、内涵、定位、功能、应用模式等方面可谓是百花齐放;但不同的定位、不同的表述,对内涵理解不清晰、不准确,影响微课程开发模式的科学建构。
由此可见,中年女性与青年女性的女团综艺之差异便在于借由文本与语言搭建出了不同的话语体系:青年女团重在“迎合”男性审美,强化父权社会对女性形象和性格的规训;中年女团则将“反抗”的符码编织在语言、文本、实践的各个角落,营造全方位的“去依附性”话语,强调“凸显女性价值”的思想内核。
(二)制度反抗:屏蔽“他者”的凝视
女性对自我权力的争取与反抗从未停止,但不可避免的是,当代女性的自我认知依旧受到父权话语的制约和男性目光的全面凝视。福柯认为,“权力的无处不在,并非因为它有特权能使一切统一在它战无不胜的整体之下,而是因为它不断地产生出来,在每一点中,或更确切地说在点与点之间的每个关系中。权力的无所不在,不是因为它包容万物,而是因为它来自所有的地方。”[7]从“超级女声”开始直到如今的女性选秀节目乃至相亲节目都将男性作为其权力的掌控者,包括男性评委、男性嘉宾、男性导师等等,同时也将受众目标瞄准男性群体。由此,来自男性的凝视得以对女性进行合围,迫使其接受男性所制定的一系列价值标准。《乘风破浪的姐姐》对男权制度的反抗最直接表现于对现场观众的选取与设置,其参与节目录制的500名观众由身处各个年龄阶段的女性构成,在屏蔽男性受众审美视角的同时,将投票权也完整地赋予“她者”,从而在表层意义上实现女性对女性形象的评估与界定。
对“她者”权力的去蔽除了对女性观者权力的赋予外,还在于对节目中参赛者的权力去蔽。《乘风破浪的姐姐》中各位姐姐对表演曲目的改编与歌舞内容的编排都有独到的理解,自我态度与风格品味的融入在比赛过程中获得了充分的尊重,例如钟丽缇为演出特意设计了凸显女性线条美的舞台服装,郁可唯等人将京剧元素融入歌曲演唱中等行为,都将原本僵硬的规则变得生动且贴合每位姐姐的个人气质,中年女性的个体价值与个体存在得到了双重释放。
面对“他者”的凝视,劳拉·穆尔维强调这种行为所带来的快感,即她认为男性观看女性的过程“是一种‘物化’的过程,或者说是把女性转变为欲望对象的过程。这样一来,女性就不再是一个具有自由意志、自身欲望以及能够说‘不’的人”[8]。节目对“他者”凝视的屏蔽并不能完全掩盖男性目光,而是在节目内部竭力营造与坚持女性视角。虽然节目中的音乐制作,舞台秀总监和成团见证人都由男性担当,但是其话语、行为和权力都被相应弱化,从以往的“评审人”角色更改为“辅助者”,以“帮助、支持和鼓励”姐姐们的表演为使命,最大限度上减少男性对女性偏好的投射与规制,坚持打造女性心目中的中年女性应有之形象。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节目所采取的对“他者”凝视的屏蔽措施仅仅是从表层意义上进行的有限反抗,而对中年女性,乃至整个女性群体的凝视更是来自“大他者”的凝视,即拉康所说的“对象a”——“主体对他自己的分裂所产生的兴趣与规定了这一兴趣的东西,即一个获得特许的对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对象出自某种原初的分裂,出自某种自我切割,而这种自我切割乃是因为真实(the real)的逼近而造成的;在我们的代数中,这个对象的名字就是对象a”[9]。父权制切割了女性的政治经济权力,使其长久处于求而不得、无以弥补的匮乏之中。《乘风破浪的姐姐》通过改良节目机制、转变人员职能和营造文化语境等方式弥补了中年女性所匮乏的发声机会,试图为女性营造一个自由抒发和平等交流的乌托邦空间。
(三)身体反抗:男权审美的“祛魅”
在弗兰克看来,生理或更特定意义上的肉体是作为身体构成的第三维度而存在的[5]。肉体性是身体的基础属性,没有生理机能和肉体承载,各类反抗性实践及其意义也就无从谈起。布莱恩·特纳在对人体进行社会分析时发现“20世纪增长的消费文化和时尚产业特别重视身体的表面。消费社会重视强健/美丽的身体,即因为审美目的而强调对身体表面的操控”[5]。从将女性形象进行肢解,追求如“锁骨放硬币”“A4腰”等割裂整体性的身体美感,到今天以“白幼瘦”为代表的审美准则,女性的肉体管理与时尚重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持续演化,但难以撼动的是这种身体规则对女性的“一视同仁”,即不论处于何种年龄阶段的女性都被置于同一个“标准”中进行测量。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作为父权凝视的主要载体,普遍传播和吹捧“少女感”等“同一性”审美框架,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年女性竭力保持姣好的容貌和纤细的身材,认为如此才能够获得男性长久的青睐与社会的认可,但这种标准的建构实际上是将女性置于男性的附属地位,通过制造外貌焦虑以达到控制与物化女性的目的,形成文化霸权。
《乘风破浪的姐姐》则意在打破这种“统一标准”,颠覆男权的审美霸权。为此,节目不仅在选择参赛者方面进行多样化风格搭配,同时也着重引导和帮助参赛者不断突破自我,尝试视觉性地展现多元美感的女性身姿。极具“中性风”的李斯丹妮和许飞、主打民族风歌曲的阿朵、想做Y2K(千禧风)女团的朱婧汐等人的加入,带来了丰富多彩的音乐和舞蹈艺术,更加全面地展示了中年女性的多样化才能和美丽形象,例如节目提供的电音、国风、宅舞、非洲舞等不同种类的艺术,让人欣喜地看到现代中年女性的“全面发展”。
不过,相较于以往一味强调“竞争”与“排名”的女团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在呈现女性的岁月美与进取美的同时也将“人至中年”的种种力不从心剖开来置于屏幕前,宁静常备的速效救心丸,万茜等人的带伤上场都表现出中年女性身体面临的自然损耗以及男权审美标准的强求与不公。因此,从整体性视角出发,无论是“无限可能”的自我挑战还是年龄带来的无可避免的伤痛,节目中每一位女性对自我身体的管理都可被视为肉体上的反抗,来自制度和话语的双重保护与权力的赋予促使她们得以更为坚定地贯彻自身意志,在综艺节目这个平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三、中年女性的共情关注与情感唤起
中年女性的身份焦虑并非受单一影响因素所致,年龄焦虑、职场焦虑、家庭焦虑和身体焦虑等多重要素的杂糅与重叠才于实质上促使其形成对自我的身份焦虑。正是此类消极心理对精神空间的挤占,才使得身份认同问题成为当下中年女性亟待重视与解决的主要任务。
(一)共情关注:节目与观众的情感沟通
《乘风破浪的姐姐》虽然力图简化各位姐姐在节目中的身份,以更好地凸显中年女性表达自我、勇敢追梦的理想特质,但是在排练、采访等过程中既有的家庭和社会身份会不时跳出,将参赛者与受众一同拉回现实,伊能静对女儿的担忧,张雨绮、吴昕因拍戏主持等本职工作的需要而无法完整参与排练,都强调了中年女性不得不同时担负家庭与社会责任。凸显女性反抗行为、营造女权崛起的乌托邦固然夺人眼球,但基于现实的“真人秀”才能更全面真切地反映大众呼声,进一步搭建受众共情的现实基础。
“共情”作为类属于心理学范畴的概念,研究者认为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情绪感染、观点采择和共情关注[10]。如果将节目所构建的一系列身体反抗实践视为抒发女性话语的身份乌托邦,那姐姐们所面对的现实选择与考量便是唤醒受众情绪的突破口,即同为女性,人至中年都需在兼顾多重身份的同时平衡家庭和社会中的各种复杂关系,行为的一致性使得明星和普通民众之间情绪体验的一致性逐步形成。在情绪感染的基础上,受众开始“从他人视角或他人所处的情境出发,想象、推测和理解他人态度与感受的心理过程”[11]。从“受众”到“粉丝”所经历的不仅是个人喜恶的改变,更是对他者行为的情感肯定与感同身受,从而产生共情关注,以投票、拉票、弹幕留言等方式帮助“爱豆”成团出道。正是基于中年女性们相似的生活经验,节目中60位女艺人舞台上和生活空间中的多样身份展演得以引起女性受众的共鸣。正如巴特森等人所说:“共情能搭建起自己同他人之间的情感体验以及与他人幸福感的普遍联系,它是助人行为的源泉。”[12]需要警惕的是,女团综艺作为真人秀节目的一种,节目内在从根本上包含着一定“作秀”的成分,其展现的明星生活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伪真实”,即“通过文化设施和大众传播媒介构筑起的一个弥漫于人的日常生活中的‘伪世界’”[13]。节目与受众之间情感沟通的意义在于引起广泛意义上的群体共鸣,从而促进现实生活中女性的反思与认同,而非使受众进一步沉溺于景观世界,幻想构建一个如女明星般“完美”的自我。
(二)自我肯定:中年女性“新情感结构”的确立
受众共情的建立并非自我认同形成的目的,而是通过感受与反思当前文化实践中女性问题的不足与缺陷以进行调试,并力图创造出契合时代意涵的情感结构。“情感结构”作为威廉斯的核心思想之一,贯穿其整个研究脉络,也为探究女性思想演变开辟了新方向。威廉斯在分析工业小说的过程中发现,作者的观察和写作无法超越所处历史阶段的人在同等问题上所共有的情感结构。随后在《漫长的革命》中,威廉斯继续对这一概念进行深化,提出“情感结构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它是一般组织中所有因素带来的特殊的、活的结果”,并作为文化有机体随物质实践的改变而持续发展,“新的一代以自己的方式对它所继承的那个独一无二的世界作出反应,在很多方面保持了连续性,同时又对组织进行多方面的改造,最终以某些不同的方式来感受整个生活,把自己的创造性反应塑造成一种新的情感结构。”[14]由此可见,当代中年女性的情感结构重建并非像《乘风破浪的姐姐》所形塑的激进女权主义般完全打破常规、抛弃一切束缚、以强目的性为导向的竞争与展演,而是在节目所唤起的共情基础上对传统情感结构加以扬弃。
传统中年女性的情感结构建立在对父权的依附与顺从之上,“男主外女主内”等严格按照性别分工的社会意识并未因女性经济基础的稳固而产生根本上的改变。守旧且固化的社会分工秩序与男女性别地位的不平等使得“隐忍”与“坚强”成为中年女性在家庭、职场等多方场域潜移默化地共同遵守的道德训诫,对“自我”的考量被置于后排。但《乘风破浪的姐姐》所打开的情感突破口让中年女性开始直面自己的付出与努力,个体价值被放在聚光灯下进行讨论,“三十而骊”“最好的年龄就是现在”“每个年龄的女生都有自己的魅力”等“自我肯定”的认同借由网络媒介平台的传播拓展为共享式的群体意识。但就像黑格尔所说的:“当‘精神’脱却它的生存皮囊时,它并不仅仅转入另一皮囊之中,也不从它的前身的灰烬里脱胎新生。”[15]这是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过程,即“扬弃是否定并且同时又是保存”[16]。以《乘风破浪的姐姐》为代表,关注中年女性的节目实质上既没有明确反抗父权的目标,也没有完全贯彻自身意志,仍受限于男性社会文化框架,因此以“自我肯定”为基调的情感结构继承与延续了中年女性的传统社会地位,于反抗的过程中寻求与父权的协商,即在遵守社会规制的前提下对女性的个体价值予以肯定,重视与支持中年女性对自我目标的追求,使其从以往“被沉默”和“被忽视”的压抑语境中解放出来。
因此,中年女性情感结构的重塑一方面否定了女性的“失语”状态和父权凝视带来的年龄焦虑,一方面依然认定女性在当代政经关系结构中仍处于弱势地位。从整体性角度来看,情感结构的反复建构所呈现的是螺旋式上升的状态,正是在不断的“扬弃”中,女性“自我肯定”的群体意识得以崛起,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年女性认识到年龄并非自我发展的限制性条件,即使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需要平衡与维系多重身份之间的转换,人生仍有“无限可能”。同时,中年女性情感结构的重新搭建也为身份认同提供了具有“共同的起源或共享的特点的认知基础”,反过来也正是因为“这些起源和特点是与另一个人或团体,或和一个理念,和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自然的圈子共同具有或共享的”[2],中年女性的“自我表达”才得以积累,并持续强化群体内部的彼此联动与共同在场。
四、认同重构:中年女性身份形象的再确认
从以“青春女性”到以“中年女性”为主的节目叙事变奏,“她综艺”节目拓宽了对女性群体的观察范围,将目光聚焦社会忽略的中年女性群体。但无论是代际关系的探讨还是价值观念的交锋,中年女性所要寻找的并非具体问题的解决方式,也绝非心理上的一时安慰,而是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明确自我价值的渴求,以期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身份建构。
霍尔用“身份”来指接合点,即两个方面的连接之处:一方面是企图“质询”、责令或欢迎我们作为特殊语篇论述的社会主体的语篇论述和实践;另一方面是产生主观性的过程,建构我们认为能被“表达出来”的主体的过程[2]。由此,从实践的角度出发看以中年女性为主体的女团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会发现其在本质上已偏离了传统女团的定义,即年轻化、统一化、扁平化的成员要求和整齐划一的基本表演要求。节目将多种年龄阶段、多种文化背景、多种职业经历的中年女性组合在同一舞台之上,意在尽可能营造中年女性群体的媒介缩影,着重强调每一位团员的个人魅力和能力优势,因此其最终效果并不在于成团出道,而在于凝聚最广泛意义上的受众共鸣,对中年女性群体展开自我反思、自我审视,并拒绝盲从于男性社会的审美法则和道德规训。究其本质,“人们的要求和目标是生命,它被理解为基本需求、人的具体本质、潜力的实现、可能的满足。它是不是人们希求的乌托邦,这不紧要,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真正的斗争过程”,即使中年女性对父权凝视的反抗与斗争是潜移默化的、并未形成一定规模的,但其焦点始终在于生命而不是法律,“所追求的是对生命、肉体、健康、幸福、需求的满足的‘权利’,不顾所有压迫与‘异化’,去重新发现自己是什么,自己能成为什么的‘权利’”[7]。
从主观性建构的角度来看,“30+”女艺人的媒介展演通过对中年女性群体的文化治疗,帮助其开展进一步的自我叙述化。学界对文化治疗的论述普遍集中于文学领域,认为“文学作品对于他人具有明显的精神治疗功效,这种功效如同宗教信仰,具有跨文化传播的潜在能量”,其治疗的关键就在于“文学能够给灵魂带来欢乐,因为它通过虚构和幻想足以唤起对抗精神疾患的力量”[17]。在媒介迅速发展的当代社会,文学作品借由电视、电影等媒介技术实现了“再创作”和视觉化呈现,以更为直观的形式影响着受众对世界的想象与认知。作为文字的技术延伸,影视作品也由此具备同文学作品类似的治疗效果,能够“帮助人构成一种与现实生活相逆反的环境,有助于传播幻觉感受,促使人们用主观经验去取代客观经验”[17],在快感的满足中达到精神舒缓放松的治疗目的。节目中各位姐姐舞台下迥异的性格、事业的挫折和对家庭的难以割舍,无不照进现实,映射出每一位中年女性艰难的生活体验,在满足受众对明星日常的“窥私欲”后继续凭借舞台上华丽而炫目的演出刺激观者的视觉和听觉,并迎合与满足受众的精神需求。值得注意的是,《乘风破浪的姐姐》将一种积极向上的话语表达贯穿节目始终,在营造娱乐快感的同时注入积极的心理暗示与引导,以帮助女性受众在想象中构建理想自我。让女性在身份认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自我形象有了先行的价值设定和理想期待,但这种“必然的杜撰性绝不会破坏它的推论的、物质的或政治上的功效,即使是归属性,即使是身份得以产生的‘缝合进故事’部分地处于虚幻假想状态(也处于象征符号状态)”,因此身份认同作为表现内部的构建“总是部分地构筑在幻想中,或至少构筑在幻觉领域里”[2]。而这也是中年女性搭建主观精神世界的一种手段。
综上,面对中年女性的“身份焦虑”,《乘风破浪的姐姐》为其提供了一个情感释放的出口与自我再确认的机会。女性受众通过观看“她者”的表演与形象呈现而对自我现实生活的行为实践进行反思与批判,力图从传统情感结构中“脱嵌”。借助视觉快感带来的文化治疗,中年女性群体在获得精神抚慰的同时得以正视自身需求,积极开展身份形象的认同重构。虽然仅凭借一部综艺并不能确定其对中年女性身份认同的社会影响程度与实际效果,但其构建的新中年女性形象确实引起了大众的高度关注,现实生活里中年女性所遭遇的身份困境或许也会由此得到社会的正视。
结语
《乘风破浪的姐姐》打开了中年女性群体对外共同发声和对内相互勾连的渠道,为中年女性身份形象的重塑提供了可能。该节目在以父权凝视为主导的社会秩序中开展了一系列的反抗性实践,有效地宣扬与传播了中年女性群体的自我价值。然而,中年女性的反抗实践并非一帆风顺,综艺节目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文化产品不得不面对资本和父权制社会并做出必要的妥协与牺牲,例如微商化妆品广告的植入,为了获得更好的分数而迎合青年受众劲歌热舞的偏好,等等。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在其《后现代文化》中曾提出,“妇女运动的内在同一性问题应当通过妇女运动内部的文化自我理解来解决,并通过与男性文化的对比来定位。”[18]传统意义上展现中年女性形象的影视作品已无法满足和承载当代女性的精神需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变相地成为父权制的“帮凶”,企图借助继续施加年龄焦虑、外貌焦虑、家庭焦虑等外部凝视以维护原本的道德守则,但是反映中年女性群体现实状态与利益呼声的文化作品,如《三十而已》《乘风破浪的姐姐》等已若“星星之火”,并随着受众参与度与作品讨论度的提升渐成“燎原之势”。就像齐格蒙·鲍曼所说的,“身份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个体的任务进入现代思想和实践的。它取决于从不确定性中发现逃避的个体。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社会创建的问题要被个体的努力解决。”[2]中年女性的身份形象也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而不断流动,从未停止,也从未完成,对其的考察与研究仍是未来值得思考的问题。
总之,《乘风破浪的姐姐》诞生必然受到时代的局限,但它依旧不失为当前社会语境下关注中年女性群体价值的优秀节目。值得警惕的是,未来此类节目的制作仍“应当探求力量关系过程的根本性质所隐含的限制形式”[7]。为女性在父权制社会寻求发声提供舆论和平台支持,同时还要避免商业资本成为遏制女性自我发展的某种经济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