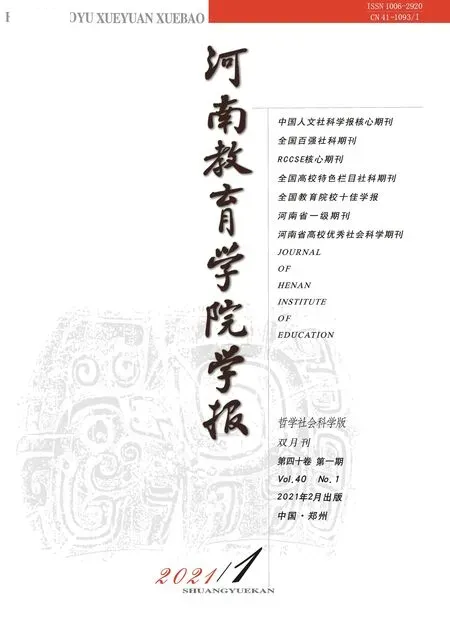21世纪前20年平儿形象研究综述
2021-01-17刘聪儿
刘聪儿
自《红楼梦》小说流行起始,平儿形象就被纳入红学研究的范围,是红学人物形象研究中的一个关注点。本文以中国知网收录的64篇论文为对象,将21世纪前20年的平儿形象研究归纳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形象性格研究、文化内涵研究、人物对比研究、悲剧意蕴研究、当代启示研究。
一、形象性格研究
21世纪前20年的平儿形象性格研究,通常会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继承,比如对色、才、德的“全人”观点的继承。对平儿色、才、德的夸赞,最早见于清代红学家涂瀛的《红楼梦论赞》。在《平儿——集色、才、德于一身的“全人”》这篇论文中,王人恩集中论述了平儿的色、才、德,并从这些方面肯定、赞扬了平儿,同时,也表达了对平儿悲剧命运的同情与惋惜。在这篇论文中,平儿是一个委曲求全的、具有多种女性优点的、聪明的女奴形象。“女奴形象”这种说法是20世纪50~80年代常见的写作用语。王人恩明显继承了前人的观点,这在他的论述中一目了然:“这就是出身寒微、位卑知足的平儿,一个充分了解自己身份、处境的平儿,一个按照女奴身份立身定位、行事为人的平儿,一个很识相的平儿,一个人见人爱的平儿。”[1]
付善明的《论平儿》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这篇文章从平儿与琏、凤之间的关系,平儿的色、才、德等方面集中分析了平儿的形象性格。他从琏、凤与平儿的关系出发,论述了平儿在琏凤关系中的艰难处境及平儿在处理这种关系时游刃有余的能力。他提到了宝玉对平儿的评价:“忽又思及贾琏惟知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又思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姊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帖,今儿还遭荼毒,想来此人薄命,比黛玉尤甚。”[2]593除此之外,他也继承并发扬了清代《红楼梦》评点家涂瀛的观点,认为平儿集色、才、德于一身,“其才不在凤姐之下,其德不知高凤姐几多矣”[3]!他的论文集中表达了对平儿的赞赏之情。
此类文章中,对平儿形象的研究也一如既往地带上了道德评价色彩,对平儿的评价也充满了溢美之词。自《红楼梦》评点出现开始,对人物形象的道德评价就从未停止过。21世纪前20年的《红楼梦》人物形象研究也概莫能外。比如,《夹缝中艰难生存的善良女性——试论〈红楼梦〉中平儿的形象》一文从平儿艰难的生存环境出发,总结了平儿能够在“夹缝”中求得生存所具备的优点与才能:花容月貌,身世凄凉;头脑聪明,能力突出;品德善良,体恤他人。[4]这几个方面是平儿身上最集中、最为人认同的优点。这些描述平儿的词语带有强烈的个人好恶色彩和道德评价的特征。
在纪建秋的文章中,这种溢美之词似乎更多了。在《论〈红楼梦〉中的平儿形象》一文中,纪建秋从品德、容貌、性格、悲剧命运四个方面分析平儿的人物形象。[5]平儿的品德、容貌及性格都有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比如她的善良和能干、她的温柔和仗义,所以平儿的悲剧命运更加让人感到惋惜。这些对平儿形象的赞叹与惋惜,在纪建秋的论文中得到了同样的表达。这是现代研究对传统人物评点方法的一种继承。
《清代〈红楼梦〉评点论平儿及其“薄命犹甚”》以清代《红楼梦》评点派的视角,对平儿的名字、性情、才识、结局进行了评点。[6]这篇文章算是对清代评点派论平儿的总结归纳。
所幸的是,也有试图突破前人视野,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来评论人物的文章。这种新的研究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以现代人的思维来论述平儿的性格特点;另一种则是通过比较文学的方法来发现平儿形象研究的亮点。《论平儿》[7]《浅论〈红楼梦〉中的平儿形象》[8]《平和善良 人之所美——对〈红楼梦〉中平儿性格的思考》[9]《俏平儿之“俏”与不平——〈红楼梦〉中平儿形象研究》[10]等文章从现代人的角度对平儿的形象进行剖析,但也有对清代评点派的借鉴。这些文章都认为平儿的性格及才干很适宜于她在艰难的环境中存活,是在“贾府”这个特殊环境中锻炼出来的。另外,这些文章也对平儿的结局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同时,这些文章都充分认识到了平儿身份的悲剧性,认为平儿也是“薄命司”的一员,后四十回“平儿扶正”不一定符合曹雪芹的创作意图。通过比较文学的视野来对平儿的形象性格进行研究的只有一篇论文,即《平儿形象在霍译〈红楼梦〉中的定向重塑》。该文通过奴才身份的弱化、活泼自主性格的强化、夹缝生存环境的淡化这三点集中展示平儿在霍克思译本中变化了的形象。[11]文学翻译经常会流露出文化隔膜,然而这种隔膜也会对小说人物形象进行重新塑造。这是21世纪前20年唯一一篇在平儿人物形象性格研究方面有所突破的论文。
简而言之,进入21世纪后,平儿形象性格研究呈现出一种旧与新相交织所产生的色彩与样式。这种色彩与样式稍稍背离了20世纪的平儿人物形象研究,开始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二、文化内涵研究
《红楼梦》所创造的人物形象都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土壤中形成并成长起来的。平儿作为《红楼梦》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她的形象也包含着中国封建文化的因子。
平儿的身份代表着封建社会的某种映射。段江丽在《〈红楼梦〉中平儿之家庭角色论》一文中指出,平儿作为通房丫头的这一身份,与古代媵制婚姻有关。“媵”是指女方陪嫁之女,与“妾”并称,都是“半主半奴”的身份,与“妻”不能相提并论。但是,段江丽在文中又写道:“在封建社会,养在深闺的贵族小姐与自幼一起成长的心腹丫环之间很容易产生深厚的情感,她们朝夕相处,知己知彼,既是主仆,又是闺中密友。当小姐出嫁、丫环陪嫁之后,从某种意义上主仆已结为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阶级分析的视野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她们之间的等级差别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平等待遇;从人性的角度,则有可能更多地看到她们在既有制度之下所表现出来的特殊的情感关系。”[12]这段话主要是论述平儿与凤姐之间的关系,平儿之所以能在凤姐面前立足,靠的不仅是智慧与能干,还有她与凤姐之间的感情。从段江丽的论述中,可以窥见平儿的身份本身就具有封建文化的某些特质。而且,平儿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所用的方式方法也都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征。
这不仅在段江丽的文章中有所表述,在其他文章中也有研究。《安分守礼与逾分违礼——“平儿”形象的文化解读》一文认为,平儿通过灵活运用儒家礼仪体系来获得自己的生存地位,并在“逾分违礼”的同时展现自己的美好品德。该文紧紧围绕一个“礼”字,有力地阐述了作为儒家生存哲学符号的平儿是如何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游刃有余”的。“《红楼梦》中,平儿这个人物形象具有相当大的人格魅力与文化内涵,她是儒家温柔敦厚的理想人格的化身,其言行符合儒家礼教规范,安分守礼。”[13]平儿的处事方法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征。王燕的《〈红楼梦〉里平儿的为人处事法》一文认为,平儿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儒家人际关系学,才在贾府这个封建大家庭中“周全妥帖”的。其中,儒家人际关系学是指孔子提出的“恭、宽、信、敏、惠”。[14]这两篇文章均指出了平儿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所运用的方式方法及其中国文化特征。
将这种特征联系得更为紧密的论文是《儒家情理文化的艺术载体》。张向荣在这篇论文中提出,平儿是按照儒家情理文化生存的艺术载体,是儒家情理文化的一种符号。他认为,平儿的生存价值是在儒家情感与理性模式中完成的。平儿形象的文学价值在于平儿生存价值所形成的文化土壤,以及这种生存价值带给《红楼梦》的文化氛围。[15]这种论述,将平儿与儒家文化嵌套在了一起。
除此以外,也有论文认为平儿与佛教思想有密切联系。这些论文也阐述了平儿形象所蕴含的中国文化因子。例如,杨芳认为,《红楼梦》中的平儿是具有佛教善生思想的典型。她从交友待亲、事师、事夫、为主为仆四个方面分析了平儿的佛教善生思想。她认为,从这四个方面可以看出平儿具有四亲可亲、忠诚敬顺、以五事恭敬于夫、能威能役的佛教善生思想。[16]
在21世纪前20年的研究中,平儿不仅仅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更是儒家文化或者佛教思想的符号或载体。这也充分说明,作为《红楼梦》所创造出来的人物形象,平儿具有中国文化中的许多因子。平儿这个人物形象,是在中国封建文化的土壤中萌芽并成长起来的。
三、人物对比研究
在21世纪前20年60多篇研究平儿形象的论文中,平儿与其他人物形象的对比研究也占了相当的比例。这些文章,有的是将平儿与《红楼梦》中其他女性作比较,有的则是把平儿与其他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作比较。
把平儿与其他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作比较,常常能够发掘一些新的视野与观点。比较具有特色的文章是王敏娟的《平儿和春梅——〈红楼梦〉对〈金瓶梅〉的人物塑造的继承与发展举隅》,这篇论文从文学继承与发展的角度出发,列举了平儿和春梅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并论证了曹雪芹继承兰陵笑笑生对人物塑造的方法的观点。[17]通过文本分析,王敏娟认为平儿与春梅最大的不同在于道德品质的不同,认为二者命运的变化也是因为“争宠”的方式不同而导致的,并且隐约透露出曹雪芹的思想情趣、艺术审美水平高于兰陵笑笑生。
沈绍芸的《18世纪中法文学中的侍女形象比较——以平儿、苏珊娜为例》通过比较平儿与《费加罗的婚礼》中的苏珊娜的形象,阐述了18世纪中法两国女性生存状态与时代思想上的不同。作为18世纪法国文学作品中的侍女形象,苏珊娜具有与平儿类似的艰难处境、权力地位、性格品质,但是她们又有很大的不同,最鲜明的不同之处就是反映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平儿表露出来的更多的是作为“半奴半主”的委曲求全;而苏珊娜却敢想敢做,生机勃勃,表现出了作为人而存在的尊严与自由。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18世纪中法两国正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18]这篇文章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究了平儿形象在世界文学史中的价值,为平儿形象研究甚至《红楼梦》研究拓展了新的视野。
在与《红楼梦》中的其他女性作比较的论文中,将平儿与赵姨娘进行比较的文章值得一提。在《〈红楼梦〉中姨娘命运的解读——赵姨娘与平儿、袭人的比较》一文中,作者以充满悲剧意识的人文关怀视角,指出了赵姨娘、平儿等人作为姨娘身份的悲剧性。此文通过赵姨娘与平儿等人的比较,指出了平儿等人处事的智慧,贬责了赵姨娘立身处世的愚昧与狠毒。但是,文章并不是停留在道德评价上,而是升华为对芸芸众生的深切关怀与同情,表达了对赵姨娘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认为赵姨娘的性格品质也是由她悲剧的身份地位造成的,是封建社会必然没落的趋势的象征。[19]卢佳佳的《“得人心与讨人嫌”——观平儿与赵姨娘的为人处事看二者身份命运的变化》一文从处事的角度对平儿提出了赞赏,对赵姨娘发出了贬斥的声音。[20]
将平儿与《红楼梦》中“四大丫鬟”作比较的文章比较多。乐铄在《〈红楼梦〉的女奴主人公》中,将平儿与鸳鸯、袭人、紫鹃、晴雯作了对比。论文以意识形态为视角,从这五位丫鬟的性格、品质、为人处世等方面展开论述,赞扬了鸳鸯、晴雯、紫鹃这样的反叛者,略含贬义地论述了平儿与袭人的奴性。[21]有趣的是,《同为温顺 实质有别——平儿、袭人比较谈》一文强调了袭人的奴性,而赞扬了平儿敢于反抗的精神。[22]在平儿究竟有没有奴性这一点上,学者们出现了分歧。
总而言之,21世纪前20年的平儿形象对比研究,继承了传统人物评点的方法,并与文本分析相结合,开创了别开生面、异彩纷呈的平儿形象研究新局面。
四、悲剧意蕴研究
随着人文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深入人心,在21世纪前20年的红学研究中,使用悲剧精神来分析《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已经是一种极为常见的思维导向了。学者越来越觉得,悲剧的主题是《红楼梦》主要想表达的思想内涵。因此,在涉及人物分析的时候,这些人物几乎都被蒙上了悲剧的色彩。学者们一致认为,封建社会残害人的本质导致了这些人物的悲剧。在这种思维模式与意识形态的引导下,几乎所有涉及平儿人物形象分析的文章,都表达了平儿作为一个封建社会悲剧人物而存在的观点。
《平儿通房身份的悲剧性》一文从奴隶身份的长久枷锁、侍妾身份的尴尬处境、封建制度下的顺从与反抗这三个方面论述了平儿的悲剧性。“归根结底,平儿的悲剧是封建奴隶制与媵妾制混合的产物。封建社会的媵妾制度将阶级带进了家庭、带进了夫妻甚至手足之间,强行将家人分成了压迫和被压迫的两类,这本身就是对人性莫大的嘲讽。而男尊女卑、夫为妻纲,女性卑弱、甘愿服从的依附人格几乎是千百年来女性地位的典范模式,这使得女性独立自主人格的尊严被无情地否定。”[23]《平儿:一个时代悲剧的牺牲品》一文同样怜惜平儿的悲剧处境与悲剧命运,也将平儿的悲剧命运归咎为封建社会奴隶制与媵妾制的残酷与不合理性。[24]这种千篇一律的悲剧性的认同与赞美不仅没有提高平儿形象研究的学术水准,反而使平儿形象研究受到了限制。
五、当代启示研究
关于平儿形象的当代启示研究的论文数量颇为可观,但仍然具有相似化的趋向。
关于平儿形象最多的当代启示是职场中的启示。《浅谈平儿的秘书之道》一文从“了解领导、贴心服务”“摆正位置、参谋服务”“把握技巧、维护领导权威”三个方面指出了平儿形象对秘书工作的启示。文章从职场的角度,对平儿的秘书之道进行了透彻的论述与分析[25],在作为“职业参考书”方面,这篇论文颇有可取之处。此外,《学习平儿做内审》[26]《〈红楼梦〉“平儿行权”中的司法伦理》[27]《〈红楼梦〉中平儿的逆向领导力及其现代借鉴》[28]分别以会计、司法、领导等现代职位为参照分析了平儿为王熙凤工作的可圈可点之处,并指出了平儿的处事方法、工作方法等对现代职场的启示。
人际关系中的启示也是平儿的当代启示研究的内容之一。《平儿的处世艺术》一文从“用心做事、低调做人”“善良忍让、坚持原则”“着眼全局、协调关系”三大方面论述了平儿处理人际关系的艺术能力,并在文末点明平儿为人处世的艺术不仅有利于个人事业的成功,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29]《论平儿的生存艺术》一文从直面挑战、进中求存、顽强适应三个方面论述了平儿的生存能力。[30]
随着文化、政治、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与《红楼梦》中人物生活所处时代的思想观念大相径庭,但是《红楼梦》中的人物给我们的启示仍然可以在现代寻求应用的途径。这说明,《红楼梦》这部经典小说具有生生不息的伟大艺术魅力。
六、总结
总体而言,21世纪前20年的平儿形象研究成果可能因为研究者过于苛刻的缘故而有诸多缺点,但仍然有可圈可点的地方。其中,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平儿形象研究与比较文学的互通、以现代思维来研究平儿形象的新视角这两个方面。在比较文学的视野中,平儿呈现出与原著形象稍微不同的风貌;在现代思维中,平儿则具备了现代人生活中的风格与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