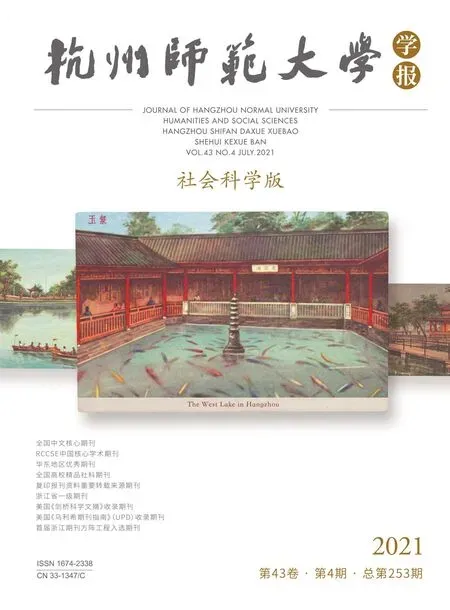人生路向与文明类型:梁漱溟历史哲学中的“人”“文”交构
2021-01-16陈赟
陈 赟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上海 200241)
西方近代通过一套世界历史哲学将共时性的不同文明编织到历时性的历史进程中,以此确证西方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它催生了中国文明之静态性与停滞性的论述,而甲午战争之后西方文明在中国内部的全方位介入,又使得以上论述获得了社会接受的基础。这一论述剥夺了中国文明的未来意义,而将之归属于过去,世界历史的前行则是与西方遭遇的现代化历程,然而欧战提供了世界范围内反思西方文明的契机,这使得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思考走向新的不确定。作为“中国文明之子”的梁漱溟,在1921年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不仅完成了个人生命从出世到入世的由佛归儒之转变,而且,结合自己的人生历程,从人生态度与文明类型的互构出发,重思中国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
一、人生问题、人生态度与文明类型
既然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那么作为其基础的则是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不同的文化文明本质上乃是生活方式之不同,而人生态度最根本的乃是人类心理。故而梁漱溟说,写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他已经“看清楚近代西洋和古中国和古印度三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实代表着人类文化发展的三阶段;断言:在世界最近未来,继欧美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近代西洋文化之后,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并指出其转折点即在社会经济从资本主义转入社会主义之时。所有这些见地主张从何而来?一句话:要无非认识了人类心理在社会发展前途上将必有的转变而已”[1](P.135)。对人心的思考是人生态度的关键,而不同的人生态度又与文明类型关联起来,成为文明类型的基础。
特定的人生态度乃是出于对特定的问题的回应。对问题的学术性处理,其发生发展总在于“问题的督迫”,“问题是学术的源头”[2](P.377)。而人生态度或生活方式又是由问题所引发的,不同的人生态度原本针对不同问题。“人类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有三不同;人类生活中,人所秉持的态度(即所以应付问题者)有三不同;因而人类文化有三期次第不同。”[3](P.73)三种具有典范意义的基本问题,对应三种基本的人生态度,三种基本的人生态度又进一步生出三种文化-文明类型,三种文明类型次第展开,即构成了世界历史的秩序。梁漱溟所谓的人生三大问题:“第一是人对物的问题;第二是人对人的问题;第三是人对自己的问题。”[2](P.377)人生三大问题之说,始发之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1)与《中国文化要义》(1949)各书中被不断丰富。以上三种问题导致三种态度——解决人对物问题的向前进取态度、直面人对人问题的持中态度以及针对人对自己的问题的向后态度,三者并非处在并列的齐等位置,而是有一种由浅到深、从低到高的梯度,这种梯度在个人层面或许并不固定,但在人类文明整体的层次,三大问题的次第与相应的人生态度与文明类型互构,成为世界历史次第展开之序。“依其次第适当以进者,实为合乎天然顺序,得其常理。人类当第一问题之下,持第一态度走去,即成就其第一期文化,而自然引入第二问题,转到第二态度,成就其第二期文化;又自然引入第三问题,转到第三态度,成就其第三期文化。”[3](P.74)
梁漱溟自己的人生历程经历了三个时期的变化,而三个时期被他提炼为人生三条路向:第一路向“肯定欲望,肯定人生,欲望就是人生的一切”;第二路向“否定欲望,否定一切众生生活,从而人生同在否定之中”;第三路向“肯定人生而排斥欲望”,因为“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有卓然不落于欲望窠臼之可能”。[4](P.183)从第一路向到第三路向,是梁漱溟思想历程的三个阶段:从西洋近代功利主义转变为佛家的出世思想,最终归本儒家,以儒家义利之辩、理欲之辩严格分辨人禽两路。梁漱溟将其本人所经历的三种路向,置放在文明论高度加以理解,三种路向遂成为三种文明的精神原则:“正是由于我怀人生是苦的印度式思想,一朝发现先儒这般人生意趣,对照起来顿有新鲜之感,乃恍然识得中印两方文化文明之为两大派系,合起来西洋近代基督教的宗教改革下发展着现世幸福的社会风尚,岂不昭昭然其为世界文化文明三大体系乎。”[5](P.185)只不过,对梁漱溟而言,他本人思想的演变历程中的第二期被视为人生第三条道路,对应着印度佛教文化;第三期发展则被作为人生第二条路向,对应着儒家的肯定人生而扬弃欲望的哲学。通过这样的关联,他一生的思想转变过程,就是在三大文明之间的游弋过程。人类文明的第一路向“向前面要求”,以近世西洋文明为代表;第二路向“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以中国的孔学为代表;第三路向“转身向后去要求”,以印度佛教为代表。[6](P.382)三条路向中,第一条是入世之路,第三条为出世,第二条则可视为前两者的调和或平衡,因而是中道之道。
二、西方文明与第一路向
第一路向是原初的“本来的路向”,其核心是通过奋斗努力的态度以满足人生的要求,“遇到问题都是对于前面去下手,这种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这是生活本来的路向”[6](P.381)。这一路向又被简要地概括为“向前”[7](P.751),它在近世西方文化中有显著的表现:(一)征服自然,对于自然向前奋斗,对于环境进行改造;(二)科学方法,变更现状,打碎、分析来观察;(三)民主异采,对于各种权威反抗斗争。这三点展现了近世西方文明“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人生路向。[6](PP.382-383)就西方文明的历程而言,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洋近世文化走的正是这第一条路,在西洋文明的古希腊罗马阶段,它走的也是这一条路,只不过在中世纪,西方文明转入第三条路。梁漱溟从罗伯特生(Frederic D.Robertson)对希腊思想的如下四个特征的提炼——即无间的奋斗、现世主义、美之崇拜、人神之崇拜——得出希腊人是以现世幸福为人类之标的,属于向前要求的道路。而西方文明引入出世的希伯来文化收拾希腊罗马之向前意欲带来的问题,遂转向第三条路,漫长中世纪重天国不重现世,文化归入宗教,而生弊端,故而又转回第一条路向。宗教改革使得基督教性质发生巨大变化,从本来意在出离世界的第三路向转而“全成了第一路向的好帮手”,“无复第三路向之意味”。“总而言之,自文艺复兴起,人生之路向态度一变,才产生我们今日所谓西方文化”,而“考究西方文化的人,不要单看那西方文化的征服自然、科学、德谟克拉西的面目,而须着眼在这人生态度,生活路向”。[6](PP.382-385)
西方人在古希腊罗马世界走上第一条路乃是无意的,未经反省的,更多由于外缘;既然可以偶然得之,也就可无意中失之。而近世西方重回第一路向,则是“有意选择取舍”,“经过批评判断的心理而来的”,已经不再是偶然,而是内在于其文明本质之中的文化自觉,它意味着西方文明对自己的重新理解与定位。[6](P.390)就任何一种文明而言,其文明的风土性并非一开始就被固定化地给予,而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彰显的:“大约一时代一地方,其思想起初发展的时候,实是种种方面并进的,没有一准的轨向;不过后来因为种种的关系,影响结果只向某一方向而发达,而这种思想就成了这一地方这一时代的特异面目。”[6](P.402)随着文化的演进,到了后来各种可能性并不是得到均衡的发展,而是某些方面被突出,遂成为该文明的底色。“到了后来西洋只有偏于向外的,对于自然的、对于静体的一方面特别发达,而别种思想渐渐不提,这就因为西洋人所走是第一条路向。在一条路向本来是向前看的,所以就作向外的研究;前面所遇就是自然,所以对于自然研究;自然乍看是一块静体,所以成静体的研究。”[6](P.402)向前要求的路向,要求对自然的控制,而对自然的控制则需要偏重理智而非理性的科学。“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即在其站在静的地方去客观地观察,他没有宇宙实体,只能立于外面来观察现象,故一切皆化为静;最后将一切现象,都化为数学方式表示出来,科学即是一切数学化。一切可以数学表示,便是一切都纳入科学之时,这种一切静化数学化,是人类为要操纵控制自然所必走的路子;但这仅是一种方法,而非真实。”[8](P.129)通过科学达成对世界经验的静态化约,甚至将不同质的理则予以同质性的量化,这构成数学化的本质,而这种近代科学之所以出现于“宗教障弊最深的欧洲而不出于理性开明的中国人”,原因就在于向外向前的观看,化生意盎然的世界为静态的物质,“化宇宙为空间”,以此方式,“理智活动自己产生了适于他自己活动的地方、环境,适于计算分析画圈的作用”,但其结果却是极大地加剧了生命的机械性与盲目性,遮掩了人的生机。[9](P.1019)的确,近代西方莱布尼兹、赫尔德、洪堡等人有机性的“花园模型”与以人造钟表所体现的“机械模型”之间的长期拉锯中,机械性的宇宙图景不断凯旋深入,甚至最终倒向了“人是机器”的观点。
重回第一路向的结果是近世西方发生的“人之发见”与“世界之发见”。所谓人之发见即“人类自觉”,“中世教权时代,则人与世界之间,间之以神;而人与神之间,间之以教会;此即教皇所以藏身之固也!有文艺复兴而人与世界乃直接交涉。有宗教改革,而人与神乃直接交涉。人也者,非神之罪人,尤非教会之奴隶,我有耳目,不能绝聪明;我有头脑,不能绝思想;我有良心,不能绝判断。此当时复古派所以名为人文派也。”[6](P.387)“世界之发见”与“人之发见”,正意味着对“向前要求”的人生态度之肯定:一方面,所谓人的发见或觉醒,意味着人认识了自己,而自我肯定,对于“自己”“我”的认识肯定,本身即是一种理智活动,正是这种太强太盛的理智活动,构成近世西方显著的特点,创辟近代科学、哲学,“为人类其他任何民族于知识、思想二事所不能及其万一者”[6](P.391);另一方面,既然人有了“我”,“就要为‘我’而向前要求,向前要求都是由为‘我’而来,一面又认识了他眼前面的自然界。所谓向前要求,就是向着自然界要求种种东西以自奉享。这时候他心理方面又是理智的活动”,这种理智活动将在直觉中本来浑然一体的“我”与“物”、乃至“我”与“宇宙”“打成两截,再也合拢不来”。[6](P.390)在第一种态度中,“‘我’对于自然宇宙固是取对待、利用、要求、征服的态度,而对于对面旁边的人也差不多是如此的态度”[6](P.390)。换言之,不仅物被作为满足欲望的材料或手段,即便是人也被作为物来对待,这就是人的物化或客体化。
第一路向偏重理智而非理性,由此而造成了西洋哲学是“偏于向外的,对于自然的。对于静体的一面特别发达,这个结果就是略于人事”。这一方面使得人生哲学并不构成其哲学的正题,另一方面人生哲学又被披上了“尚理智”“主功利”崇计算“主知识”的特征。[6](P.482)进而造就了西方文明中工具理性之发达:“最近的什么实际主义、人本主义、工具主义、实验主义,总是讲实际应用,意思都差不多。”[6](P.484)这种人生路向背后隐藏着的原则仍然是欲望或本能,梁漱溟借用罗素对“占有冲动”与“创造冲动”的分类,前者追求名利美色之类,占有是从外面获取;后者“则是从自己这里的劲头、才能、力气要使用出去”,“一切好的行为皆出于创造冲动”,但正如罗素所云,西方近世的“资本主义社会鼓励人们的占有冲动,发展了人的占有冲动,而抑制着人的创造冲动,已经到了可怕的地步”[1](P.133)。
但问题是何以“向前看”的近世西方文明能够主导世界历史的现代纪元?梁漱溟将其原因归结为科学、民主:“西方化有两样特长”,“一个便是科学的方法,一个便是人的个性伸展,社会性发达。前一个是西方学术上特别的精神,后一个是西方社会上特别的精神。”[6](P.349)科学指向一种不必讲求运用的纯粹求知,这使由“术”而“道”,由于强调“求公例原则”以及可证实性原则,故能“一步一步脚踏实地,逐步前进”,“今胜于古”。[6](P.355)近代科学的实验态度与实证精神,“把许多零碎的经验,不全的知识,经营成学问”,与依赖个人体验的“手艺”完全分开,放逐了神秘体验,而对一切人开放,由此导致了以科学态度而非“手艺”方式应付一切、解决一切问题的科学精神,其特点是“一定要求一个客观共认的确实知识”,正是这种科学成就了西方近代文明。[6](PP.354-355)梁漱溟以为,中医和西医是两条不同的路向:西医本质上是科学,其根本方法与视角“是静的、科学的、数学化的、可分的”;而中医则是“手艺”,其“根本方法与眼光是动的、玄学的、正在运行中不可分的”。中西医所体现的两种路向,虽然在未来结果将是中医的方法最终优胜,但“无奈现在还是没有办法,不用说现在无神仙之流的高明医生,即有,他站在现代学术的面前,亦将毫无办法”,中医的出现就整个世界历史进程而言是纪元性的错位,在当前西方主导的世界历史纪元,中医“不能说明自己,即说,人家也不能了解,也不信服”,“中西医学现在实无法沟通”。但中西医的真正沟通,“亦须在较远的将来始有可能。而此可能之机在西医,在其能慢慢地研究、进步、转变,渐与中医方法接近,将中医收容进来;中医只有站在被动的地位等人来认识他。所以从这一点说,西洋科学的路子,是学问的正统,从此前进可转出与科学不同的东西来;但必须从此处转,才有途径可循。”[8](PP.131-132)中医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呈现的早熟之象,西医作为科学,它有一套方法步步踏实,不断进步,它有一套理论自己解释自己,因而构成“学问的正统”,中医必等待未来的西医来认识,到了一定纪元它则会大放光彩。近代科学只是对动态世界的静态化约,仅是一种方法,而非宇宙人生之真实;它是有效操纵控制自然的手段,当人类处在以第一问题为主导的时代,科学可以很好地解决人类的基本问题。西方主导的现代纪元,恰恰是第一问题主导人类问题的时代,科学因控制操纵自然的非同寻常的能力,而适应了时代的要求。(1)《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将西方文化长处概括为三点:一是社会与政治上的民主精神,二是思想学术上的科学方法,三是征服自然的物质文明。后来梁漱溟认为民主精神可以归入团体组织,至于科学方法与征服自然,只是一事之两面。见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91-192页。
近世西方文明的另一奇迹是由民主制度带来的个性伸展:“西方社会与我们不同所在,这‘个性伸展社会性发达’八字足以尽之”,这“便是‘德谟克拉西(democracy)’”。[6](P.369)梁漱溟将民主的合理性分为两层:“第一层,便是公众的事,大家都有参与作主的权;第二层,便是个人的事,大家都无干涉过问的权。前一项,即所谓公民权;后一项,即所谓个人之自由权。在这种制度,大概都有所谓宪法,所以又称立宪制度;在宪法里面,唯一重要的事,即关于这两项的规定。”这一制度设计的巧妙性在于使人“为善有余,为恶不足,人才各尽其用,不待人而后治。其结构之巧,实在是人类一大发明。”(2)梁漱溟《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梁漱溟全集》第5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4-135页。早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就将民主精神分为两层:“第一层便是公众的事大家都有参与做主的权;第二层便是个人的事大家都无过问的权。”他指出:“必要有了‘人’的观念,必要有了‘自己’的观念,才有所谓‘自由’的。而西方人便是有了这个观念的,所以他要求自由,得到自由。大家彼此通是一个个的人,谁也不是谁所属有的东西;大家的事便大家一同来作主办,个人的事便自己来作主办,别人不得妨害。所谓‘共和’、‘平等’、‘自由’不过如此而已,别无深解……这种倾向我们叫他:‘人的个性伸展’。因为以前的人通没有‘自己’,不成‘个’,现在的人方觉知有自己,渐成一个个的起来。”见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65页。就公民权而言,它保证了“人人都有分预闻政治”,参与作主的方式不仅有选举,而且有议会制度与代表制度,以保证“大家出钱,商量着来办大家的事”;就自由权而言,它保证了对个人自由的尊重,宪法规定了个人的财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在私人领域,国家权力并不介入,从而可以有法律上不受限制和干预的自由空间。此两种权力确保了“人的个性伸展”。[10](PP.135-137)民主制度的结构之巧妙表现在,它采用立法、司法、行政分立的原则,“无机会给你舞弊,只有一条路让你走——好好安心尽你职责”,官司各有其分,各有监督,哪怕是上握政权之人,亦受国会制约。“妙处在使人为善,在才智之士,得尽其用,在政权从甲转移到乙,平平安安若无事。”在传统政治中,大权集于一人,“无限制,且不分;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托于他,一国兴衰存亡托于他;他稍为一动作,关系影响不知道多大。而一人的耳目,如何能够用?一人的心思,如何能够用?他作事实在太危险了。无心为恶,而遗祸为害,已不知有多少”;更何况,“日久了,总在一种空气之下,一个方向之下,没有不陈腐的,没有不出毛病的”。所以,“如何救济从国家权力机关所生出的危害,腐败,偏弊,实政治制度里面第一大事。然而,在此直无法救济。只有暴力革命,实在牺牲太大,太可怕!”民主政治的巧妙,正在于以制度化方式解决了这一问题,“免除这样可怕的牺牲,而救济了上说的弊害,能有政象常新,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人竞于为善的机会。此其妙用,盖都在他的政党”。在梁漱溟看来,这一套制度的发明,“莫妙于替他开出路来,使之自由竞争,则不但不致为乱,而且尽得其用,食其利”。为政者提供平台,听任各种人才、各种团体自由竞争,“听其自相磨荡,自为酌剂,自寻出路;而在我无所容心,无所用力于其间”。如果不让人们如其所量的有发挥自己才情的余地与条件,社会亦无以安。然民主体制恰恰以统治者“无所容心,无所用力”的“无为之治”原则达到“不待人而后治”,克服传统的治乱循环而达到长治久安。[10](PP.137-140)后来,梁漱溟进一步认识到,民主以及它所带来的个性伸展其实根植于西方的团体生活形式,由于这种团体生活形式而有一种社会的自觉。所谓的社会自觉,“不是从大社会里面,意识到自己这一小份(一身一家一阶级一部份),而却是离开自己,意识到整个大社会”[11](P.647)。
在梁漱溟看来,西洋近代性虽然引领人类走到了世界历史的时代,并最终成为第一纪元的主导者,但作为世界历史的第一纪元,它的问题在于“不免有三层缺憾:一层,是对外肆行侵略,以旁的民族供其牺牲;二层,是在其国内,亦有以此部分人供彼部分人牺牲之势,或至少是幸福不平等;三层,是表面幸福,未必真快乐——这是罗素所为再三叹息的”(3)梁漱溟《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66-167页;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259-260页。。民主不能扩展到国际政治,相反,对外的帝国主义与对内的民主相互伴随,而民主国家内部不平等不能在国家内部实质解决,结果反倒依赖殖民扩张以应对国内危机,而且对幸福的理解被功利主义的控制欲望所主宰,而不能在心性秩序内部解决幸福问题,这种西洋近代性的危机关联着欧洲文明的病理结构。梁漱溟以为:“欧洲的文明,实一病态的文明,其中人生乐趣,究有几许,诚属疑问。所以这三层缺憾;大概是不能否认的。然何以致此?试究其故,则以当初本从个人为出发点,而以现世幸福为目的地;——质而言之,便是中国所谓私欲或物欲——其不免于有己无人,而损人以利己,逐求外物,而自丧其天然生趣,固必致之符也。”(4)梁漱溟《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67页;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259-260页。梁漱溟在当时蒸蒸日上而处于全球扩张期的欧洲文明中,看到了文明本身的危机,而欧战不过其特别表现,其病因则在个人主义之“私”。
西方无论是个人本位还是团体本位,都无法超越“私”,个人主义重“私”容易理解,它本来就是对团体本位的社会之反动,然而即便西方的团体本位,也不过是“私”的放大而已。西洋人“小不至身家,大不至天下,得乎其中,有一适当的范围,正好培养团体生活。但因此西洋人每此疆彼界,度景狭隘,不能一视同仁。因自护其团体而不讲公理者恒有之,反不如中国人养得一片公平心理。盖在团体一面为有所合,则一面必有所分;一面有所爱,则一面必有所不爱。中国人无所合,因亦无所分,其好说天下自是当然的了。故知西洋人之公,只是大范围的自私,不是真公,真公还是中国人”[12](P.194)。梁漱溟敏锐地观察到,西方文明的团体生活,无论是教会,还是国家,都是在此与彼的对立中立身的,利吾国则未必利他国,于我教会为公者于彼教会则可能为私,西方社会的组织构造由于始终处在要么将团体、要么将个人置于本位的原则下,那么,其所谓的团体本位亦无法真正做到大公,而只能是个人单位的移植,内在于其中的仍然是团体为单位的“私”,西方近代所谓的“公”不过“大范围的自私”。
私的核心是欲望。“欧洲近代政治,实是专为拥护欲望,满足欲望,而其他在所不计或无其他更高要求的;我名之曰‘物欲本位的政治’。其法律之主于保障人权,即是拥护个人的欲望,不忍受妨碍;其国家行政、地方行政(尤其是所谓市政),无非是谋公众的欲望之满足。”(5)梁漱溟《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67页;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260页。相对于中世纪的禁欲,近代欧洲政治承认个人的欲望,黑格尔甚至以个人特殊性的满足作为现代的法权性要求,正是这一点使得现代市民社会有别于古希腊伦理生活形式。梁漱溟深刻认识到,“此其精神,本是从禁欲主义的宗教之反动而解放出来的”(6)梁漱溟《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68页;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261页。。然而,它却使得欲望的承认变得公开化,并得到体制化的支持与鼓励:“自近世西洋人个人本位、契约观念盛行,乃认定没有私,公即无从来。团体无论如何重要,亦不过为的是个人;因团体之故,个人自不能不受到一些限制干涉,而只于维持公共秩序所必要者为限。前所谓个人行事,但不妨害公众不侵及他人则国家权力过问不到者,其根本即在公私界划之确立。然而其所谓私是什么,不过是个人的欲望要求;所谓公,亦就是大家的欲望要求已耳。其拥护自由亦即是拥护欲望。”(7)梁漱溟《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68页;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260-261页。
欧洲的问题实际上意味着世界历史的现代纪元的危机,这一危机与政教的非连续性不无关系。历史上的“欧洲宗教凭藉国权,武力相争,为祸既烈;则信教自由,析宗教于国家,早为人心所渴求。公私界立,政治乃与宗教分家,法律乃与道德分家。——欧洲人之道德原与宗教相裹混的;此裹混实种下摒道德问题于国家外之因”(8)梁漱溟《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68页;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261页。。政教分离本来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一旦走向极端就会为文明总体层面上的统合带来问题,从而造成文明体内部的结构性张力,当这一张力以系统性矛盾的方式作用于个人心灵时,就会间接地促成人格之统一性的解体。梁漱溟所面对的近世国家,已经撇除了伦理与教化的功能,也不再作为文明的承担主体,而是“只管人的生活,不复问其生活之意义价值”(9)梁漱溟《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68页;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262页。,而生活本身又被降格为生存需求与欲望的满足。梁漱溟并非不明白政教分离在西方文明中的历史合理性:“我岂不知政教分离,不独在欧洲当时有其事实上及理论上的必要,而且在[任]何时均不失为最聪明的办法;夫我岂不知天地间没有比以国家权力来干涉管理人们的思想信仰行为再愚蠢而害事的”;然而一旦视野拉长到足以超出现时代的纵深时,就会发现政教彻底分离而不再谋求新的更高层次上的连续性的主张其实是一种短视,它“不足以语人类文化变迁之大势”:在传统社会,国家的统治阶级妨碍个人太甚,而后才有近代专求消除这种妨碍而树立个人自由疆界的建制化态度之反动,“然而这自是一个消极目的。文化更转进一阶段时,则单单不妨碍是不算的,必须如何积极地帮助顺成个人种种可能的发展”;进一步地,“在人的生存问题未有一社会的安排解决,则人生向上的要求亦不能有一社会的表现。换言之,其表现为社会的要求,而社会尽其帮助个人为人生向上无尽之开展的任务,固必待经济改造后。尤其不可不知者,现在一般国家所行之法律制裁的方法,实以对物者待人,只求外面结果而不求他心与我心之相顺,粗恶笨硬,于未来社会全不适用;非以教育的方法及人种改良的方法替代之不可。”(10)梁漱溟《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70-171页;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269-270页。
人性的进一步上达的要求需要通过社会来表达,而这一表达本身又需要国家承担更大的责任:人们之间的彼此之不相碍乃是国家的基本责任,但绝非最终目的;如果符合人性的秩序必须让人们彼此之间自行地达到各不相碍,但这种不相碍的自发到来依赖于人们对是非的自觉,那么,国家唯有推进人们对是非的自觉,在更本质的意义上才能作为人的国家——即人之所以为人者在其中生成的国家——而存在。“人类之所以可贵,就在他具一副太容易错误的才能;人类之得充实其价值,享有其价值(人而不枉为人),就在他不甘心于错误而要求一个‘对’。此即人类所以于一般生物只在觅生活者,乃更有向上一念,要求生活之合理也。”(11)梁漱溟《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69页;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263页。然而,现代文明却以“大范围的自私”替代“公”,以一国之是是人类之非,以一己之非非人之是,则其所是者,必然下落为私欲,而是非不彰。“使人类历史而不见有此[向上要求]于其间,不知其为何种动物之历史也!奈何今之人必一则曰人类求生存;再则曰人类求生存……以生存利害解释社会之一切,而不复知人心有是非,几何其不相率入于禽兽之途也!”[12](P.263)现代纪元的危机就在于等人于物,其所谓自由、法权、平等等等,不再是成就人之所以为人的方式,只是将人以价值动员方式组织到某一共同体中的意识形态,(12)关于意识形态及其西方近世起源,参见陈赟《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深层逻辑》,《南国学术》,2020年第2期,第241-260页。只有明白这一道理,才能了解何以在现代以自由平等民主进行自我界定的共同体内部,却同时出于帝国贪欲而对于共同体外部的人们实施暴力、殖民与征服,人类社会已经面临着变质为动物性丛林世界的威胁。
三、中国文明与第二路向
第二路向可简称为“持中”[7](P.751),中国文化堪为这一路向的代表,“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6](P.383)。梁漱溟也曾将这种态度表达为“郑重”,同时将第一种态度表达为“逐求”,而将下文所谓的第三种态度表述为“厌离”。所谓“郑重”的态度,可分为两层来说:在人向外用力时,“自觉地听其生命之自然流行,求其自然合理耳。‘郑重’即是将全副精神照顾当下,如儿童之能将其生活放在当下,无前无后,一心一意,绝不知道回头反看,一味听从于生命之自然的发挥,几与向前逐求差不多少,但确有分别。此系言浅一层”,好似“儿童对其生活,有天然之郑重,与天然之不忽略,故谓之天真。真者真切,天者天然,即顺从其生命之自然流行也”;在向内用力即回头看自家时,“郑重”的态度才意味着“真正的发挥郑重”,“此种人生态度亦甚简单,主要意义即是教人‘自觉的尽力量去生活’。此话虽平常,但一切儒家之道理尽包含在内;如后来儒家之‘寡欲’‘节欲’‘窒欲’等说,都是要人清楚地自觉地尽力于当下的生活。儒家最反对仰赖于外力之催逼,与外边趣味之引诱往前度生活。引诱向前生活,为被动的、逐求的,而非为自觉自主的;儒家之所以排斥欲望,即以欲望为逐求的、非自觉的,不是尽力量去生活。此话可以包含一切道理,如‘正心诚意’‘慎独’‘仁义’‘忠恕’等,都是以自己自觉的力量去生活。再如普通所谓‘仁至义尽’‘心情俱到’等,亦皆此意。”[8](PP.82-83)这种生活态度的核心是关切当下,自觉地充实当下,既不向前逐求而丧失当下,也不超离当下而指向目的论或末世论的未来,而是即当下即生活,当下地向上奋起,当下地享用当下。
这种生活态度之所以又被叫做“持中”,乃是因为它在第一种生活态度“逐求”与第三种生活态度“厌离”之间采取中道原则。“逐求是世俗的路,郑重是道德的路,而厌离则为宗教的路。将此三者排列而为比较,当以逐求态度为较浅,以郑重与厌离二种态度相较,则郑重较难,从逐求态度进步转变到郑重态度自然也可能,但我觉得很不容易。普通都是由逐求态度折到厌离态度,从厌离态度再转入郑重态度,宋明之理学家大多如此,所谓出入儒释,都是经过厌离生活,然后重又归来尽力于当下之生活。即以我言,亦恰如此。在我十几岁时,极接近于实利主义,后转入于佛家,最后方归于儒家,厌离之情殊为深刻,由是转过来才能尽力于生活;否则便会落于逐求,落于假的尽力。故非心里极干净,无纤毫贪求之念,不能尽力生活。而真的尽力生活,又每在经过厌离之后。”[8](P.83)如果说世俗的向前逐求(入世)与超越的彻底出世构成人生的两种极端,那么第二条道路便是一种持中调和。孔学不同于第一条道路的入世,也不同于第三条路的出世,而是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取中道态度。[13](PP.609-610)在西方的历史哲学家沃格林那里,人并不仅仅是一个世间或时间之内的存在者,而是生活在世间但又向着永恒开放的具有超越性维度的存在者,古希腊人通过智性意识的活动(哲学)奠定了生存论意义上的人学真理(anthropological truth),它注重的是人与神之间的结构性居间张力体验中的人性极;而以色列人则通过启示,通过对神性极的关切,而确立了救赎真理(soteriological truth)。(13)沃格林关于两种真理的讨论,参见沃格林《新政治科学》,段保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81-82页。两种真理差别表现在对居间性的生存张力结构的极点的不同关切上。在生存结构的神、人两个不同体验极点的张力中,希腊式的哲学探究侧重人神两极中的人极(生存极)的一面,也就是人的智性探寻(zetesis)的一面;而救赎真理则侧重超越性极点(非生存极),尤其是来自超越性的牵引(helkein)的一面。相对而言,中国文明则关切的是生存体验中的人极(生存极)与神极(超越极、非生存极)的平衡或“居间”(metaxy,in-between),也就是说,它给出的是生存论意义上的中道真理。
梁漱溟如是概括第二条路向:“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譬如屋小而漏,假使照本来的路向一定要求另换一间房屋,而持第二种路向的遇到这种问题,他并不要求另换一间房屋,而就在此种境地之下变换自己的意思而满足,并且一般的有兴趣。这时下手的地方并不在前面,眼睛并不望前看而向旁边看;他并不想奋斗的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他所持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意欲的调和罢了。”[6](P.381)这种态度不是首先去改变环境与对象,而是朝向主体的自我转化,即以自我转化的方式适应或平衡与外部的关系。如果说第一路向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那么,第二路向则“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6](P.383)中西文化本来不是历史的纵向演化中的先后不同阶段,而是文明类型的不同,各有自己的态度、原则与精神。“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而绝没有提倡要求物质享乐的;却亦没有印度的禁欲思想(和尚道士的不娶妻,尚苦行是印度文化的摹仿,非中国原有的)。不论境遇如何他都可以满足安受,并不定要求改造一个局面”[6](P.392),因而不会发生征服自然、驾驭自然的态度。
第二条道路成就了中国文明。中国的形上学完全不讲静体,其“根本思想”在于如何面对流动的变化本身,由于“动体”的“活动浑融”,故其方法则不可能采用刻画静体的呆板的理智化概念,而是注重直觉,强调“体会玩味”[6](PP.442-443);其精神内蕴在《易经》中,“中心意思,就是‘调和’”,“大意以为宇宙间实没有那绝对的、单的、极端的、一偏的、不调和的事物;如果有这些东西,也一定是隐而不现的。凡是现出来的东西都是相对、(成)双、中庸、平衡、调和。一切的存在,都是如此”[6](P.444)。生存体验中的天人两极在中国的形上学中不会被实体化,因而不会产生作为实体化与现成化的绝对者,而是一切都保持在持中或平衡的动态过程中。这就意味着关系的优先性:“一切东西都在这(宇宙)大流中彼此互相关系”,“一切都是相对,没有自己在那里存在的东西”。[6](P.445)这一形上学超出了利害关系,也非理智可及,而是达到一种“无表示”,即对来自主体的因素做减法,以“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因而这种形上学包含着对“生”的赞美,“以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使全宇宙充满了生意春气”。梁漱溟以为代表儒家道理的是一个“生”字,正如代表佛家道理的是“无生”。[6](PP.445-448)
“生”的意思,是儒家仁的概念的最基本内涵,而仁又是一个最能标识儒家思想的概念。“儒家完全要听凭直觉,所以唯一重要的就在直觉敏锐明利;而唯一怕的就在直觉迟钝麻疲。所有的恶,都由于直觉麻疲,更无别的原故,所以孔子教人就是‘求仁’。人类所有的一切诸德,本无不出自此直觉,即无不出自孔子所谓‘仁’,所以一个‘仁’就将种种美德都可代表了。”[6](P.454)仁的核心是“要求得一平衡”,“要求得一调和”,“直觉敏锐且强的人其要求安,要求平衡,要求调和就强,而得发诸行为,如其所求而安,于旁人就说他是仁人,认其行为为美德,其实他不过顺着自然流行求中的法则走而已”。[6](P.454)自然流行的法则并不追求意欲,也不排斥意欲,“孔家本是赞美生活的,所有饮食男女本能的情欲,都出于自然流行,并不排斥。若能顺理得中,生机活泼,更非常之好的;所怕理智出来分别一个物我,而打量、计较,以致直觉退位,成了不仁”,“仁虽然是情感,却情感不足以言仁。仁是一个很难形容的心理状态,我且说为极有活力而稳静平衡的一个状态”。在梁漱溟看来,仁所意味着的生活指向合乎分寸的“恰好”,“‘生活的恰好’不在拘定客观一理去循守而在自然的无不中节。拘定必不恰好,而最大的尤在妨碍生机,不合天理”,“恰好的生活在最自然,最合宇宙自己的变化——他谓之‘天理流行’。在这自然变化中,时时是一个‘中’,时时是一个‘调和’——由‘中’而变化,变化又得一‘中’,如是流行不息”[6](PP.454-456)。
梁漱溟认为仁的一个意思是持中、调和、平衡,另一个意思则是生机、活力、活泼。《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期的梁漱溟似乎更强调持中或调和,他以为“‘仁’与‘中’异名同实,都是指那心理的平衡状态。中即平衡、归寂,即以求平衡,惟其平衡则有不合此平衡者就不安,而求其安,于是又得一平衡”[6](P.456)。与仁相联系的是直觉,直觉使人敏锐,使人与人、人与物之间获得感通的可能性:“能使人所行的都对,都恰好,全仗直觉敏锐,而最能发生敏锐直觉的则仁也。仁是体,而敏锐易感则其用;若以仁兼赅体用,则寂其体而感其用。若单以情感言仁,则只说到用,而且未必是恰好的用,故言仁者不可不知寂之义。”[6](P.455)与仁相违的是理智,后者表现为基于工具理性的计较、盘算、算账,总而言之,是一种深陷在利害关系中的生活样式。“最与仁相违的生活就是算账的生活。所谓不仁的人,不是别的,就是算账的人。仁只是生趣盎然,才一算账则生趣丧矣!即此生趣,是爱人敬人种种美行所油然而发者;生趣丧,情绪恶,则贪诈、暴戾种种劣行由此其兴。算计不必为恶,然算计实唯一妨害仁的,妨害仁的更无其他。”[6](P.461)
理智的算账“把时时的生活都化成手段”,“将整个的人生生活打成两断截;把这一截完全附属于那一截,而自身无其意味”;“不以生活之意味在生活,而把生活算作为别的事而生活了”。相比之下,“仁”的生活方式则抓住了生活的本真,“生活是无所为的,不但全整人生无所为,就是那一时一时的生活亦非为别一时生活而生活的”,而“‘无所为而为’是儒家最注重用力去主张去教人的”。[6](PP.460-461)生活的意味只是此时此地的当下,并无别的目的,以理智方式去“追究人生的意义、目的、价值等等”[6](P.461),只是当下生趣情趣丧失的后果,当下是自然活泼流行的,是生生之意灌注的时刻。仁的活泼泼的生机与生意,无以脱离每一个当下,脱离当下,必然导致生趣丧失,尤其是机械化。“麻木是死,生命的本性是活,不活是负面,是机械,不是正面”,负面只是正面的缺失,恶与错并没有自身的实在,而只是善与对的缺乏,“仁就是活、觉,不仁就是机械、麻木”,“宇宙间没有旁的,只有此两面。而两面又为一面,故宇宙间只有一回事。恶没有根据,错误没有由来,有由来有根据就对了,就不是错误了”。[9](P.1025)仁之所以富有生机或活力,正是由于当下地体会了生活的意味,不再外求,不再去他处寻觅。而当下的意味使人超越了利害关系与目的性,因而构成自得的人生之根基。孔子作为自求自得人生之典范,“原不认定计算而致情志系于外,所以他毫无所谓得失的:而生趣盎然,天机活泼,无入而不自得,决没有哪一刻是他心里不高兴的时候,所以他这种乐不是一种关系的乐,而是自得的乐,是绝对的乐。”[6](P.464)孔子的乐与其生趣盎然之仁关联在一起。
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将孔子所体现的儒家人生态度与中国社会结构关联起来。虽然“孔子最初所着眼的,倒不在社会组织,而宁在一个人如何完成他自己”[14](P.137),但中国社会的构造本身又支持并鼓励了孔子式的人生态度:“中国式的人生,最大特点莫过于他总是向里用力,与西洋人总是向外用力者恰恰相反。盖从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两面所构成的社会,实无时无刻不要人向里用力。”[14](P.194)伦理本位、职业分途是梁漱溟对中国社会构造的经典理解。梁漱溟所谓的伦理,始于家庭,但又不止于家庭,伦理关系的核心是情谊关系,即相互间的责任或义务关系,这与团体本位或个人本位的社会中尤重权利不同。“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由是乃使居此社会中者,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相当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联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14](PP.81-82)这种社会构造就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在这里,一方面,“人情为重,财物斯轻”,于是,“各国法典所致详之物权债权问题,中国几千年却一直是忽略的”;另一方面,“伦理因情而有义”,于是,“中国法律一切基于义务观念而立,不基于权利观念”。[14](PP.83-84)与此相应,整个国家被视为“一大家庭”,“自古相传的是‘天下一家’‘四海兄弟’”的理想:“不但整个政治构造,纳于伦理关系中;抑且其政治上之理想与途术,亦无不出于伦理归于伦理者”;“中国的理想是‘天下太平’。天下太平之内容,就是人人在伦理关系上都各自作到好处(所谓父父子子),大家相安相保,养生送死而无憾。至于途术呢,则中国自古有‘以孝治天下’之说。”[14](PP.82-85)对于普通中国人而言,家庭的绵延与伦理生活,构成宗教匮乏的替代品,它“融合人我泯忘躯壳,虽不离现实而拓远一步,使人从较深较大处寻取人生意义”,可谓“伦理教”。[14](PP.88-89)《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所说的持中、调和、平衡的人生态度,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获得了其体制化形式,这就是伦理生活:“相对论是真理,是天下最通达的道理。中国伦理思想,就是一个相对论。两方互以对方为重,才能产生均衡。而由于不呆板地以团体为重,亦不呆板地以个人为重,而是一活道理,于必要时自能随其所需而伸缩。”[14](P.95)
伦理本位的社会的一个核心内容是道德代宗教。宗教问题被梁漱溟视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人类文化都是以宗教为开端;且每依宗教为中心。人群秩序及政治,导源于宗教,人的思想知识以至各种学术,亦无不导源于宗教”,而这在西方文化乃“基督教实开之”有典型的体现,相反,“中国之路则打从周孔教化来的”。[14](P.97)周孔所代表的儒家教化,其唯一的“教条”,“便是教人反省自求”,“除了信赖人自己的理性,不再信赖其他”。这已经不再是宗教,梁漱溟意义上的宗教,本质上“是一种对于外力之假借,而此外力实在就是自己。它比道德多一个湾,而神妙奇效即在此”,但“中国自有孔子以来,”“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这恰恰与宗教之教人舍其自信而信他,弃其自力而靠他力者相反”。[14](PP.107-108)在梁漱溟看来,“道德与宗教之别,正不外自与他、内与外之别”,而法律与宗教一脉同源,都是“以组织笼罩个人,从外而到内”,因而,“法律或以义务课于人,或对人而负义务,总之,义务是从外来的”;但道德却重自律,当然,单纯道德只是内在的良心,它必外化在礼俗中,形成客观的伦理,“礼乐揖让固是启发理性,伦理名分亦是启发理性。其要点,在根据人类廓然与物同体之情不离对方而有我的生命,故处处以义务自课。尽一分义务,表现一分生命,而一分生命之表现,即是一分道德。道德而通俗化,形见于风尚,即成了礼俗”[14](PP.205-206)。但道德-礼俗的回环交互,却不同于宗教与法律的回环交互,前者构成的是交往化社会,社会关系是人格彼此之间的关系;但后者导向的却是组织化社会,法律的规约与宗教的动员结合在一起,这就使得人格与人格之间的关系被中介化了,或者以神或教会为中介,或者以体制性事实为中介,这些中介化的机制本身都是把人组织到一个焦点化空间中的方式。
宗教被替代,并不是仅仅在思想层面,而是在社会层面,有两种方式使得道德代宗教得以渗透在社会构造中:“一、安排伦理名分以组织社会;二、设为礼乐揖让以涵养理性。二者合起来,遂无事乎宗教。此二者,在古时原可摄之于一‘礼’字之内。在中国替代宗教者,实是周孔之‘礼’。不过其归趣,则在使人走上道德之路,恰有别于宗教。”(1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10页。梁漱溟指出:“礼乐或简括为一礼字,它是人类社会自古早于法律而普遍存在的事物。溯其原始,盖起自上古宗教的敬神;同时,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亦需要一些礼数来维持其等差尊严。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中国,一方面固不能大异乎世界他方,即是它的礼原非和宗教和封建没有关联的。但另一方面在周孔教化中其精神面貌却为之大变特变。其变也,即是把礼归本于人心情理而一以情理为衡准。”见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梁漱溟全集》第4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65-466页。由于内蕴在礼中,道德不再是抽象的观念,而是具体的礼乐,“抽象的道理,远不如具体的礼乐。具体的礼乐,直接作用于身体,作用于血气;人的心理情致随之顿然变化于不觉,而理性乃油然现前,其效最大最神”[14](PP.110-111)。在《中国文化要义》中,第二路向已经被概括为理性主导,理性“实为人类的特征,同时亦是中国文化特征之所寄”[14](P.122),它不是抽象的理智,而是融化到伦理与社会中的情理。由此,伦理本位的社会的特点是:“纳国家于伦理,合法律于道德,而以教化代政治(政教合一)。自周孔以来二三千年,中国文化趋重在此,几乎集全力以倾注于(这)一点。”(15)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37页。在梁漱溟看来此中一个关键环节是,“法律不责人以道德;以道德责人,乃属法律以外之事,然礼俗却正是期望人以道德;道德而通俗化,亦即成了礼俗。——明乎此,则基于情义的组织关系,如中国伦理者,其所以只可演为礼俗而不能成法律,便亦明白”。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21页。
中国社会结构的另一构造特色是职业分途而非阶级对立。“假如西洋可以称为阶级对立的社会,那么,中国便是职业分途的社会。”[14](P.139)阶级发生的经济条件是对他人能进行剥削,政治条件是土地等资源均各被人垄断。就此而言,“阶级不是理性之产物,而宁为反乎理性的。它构成于两面之上:一面是以强力施于人;一面是以美利私于己”[14](P.141)。阶级社会之反理性,正在于它不合乎人之情理要求。但阶级社会又似乎可以催生理性,“它虽不从理性来,理性却要从它来”[14](P.141)。因为阶级“当于经济政治之对立争衡的形势”[14](P.141),从而把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分离开来,以政治制度化方式形成社会分工,从而突出一部分人的理智等各自作用,有助于文明之发展:“凡一切创造发明,延续推进,以有今日者,直接贡献固出自一班人(引者按:譬如统治阶级);间接成就,又赖有一班人(引者按:譬如被统治阶级)。设若社会史上而无阶级,正不知人类文明如何得产生?”[14](P.142)但通过阶级而催生的文明进步,又是以阶级现象的不合理性为代价的,阶级现象内在地要求“经济上之剥削”与“政治上之统治”,这种剥削与统治以一个集团对另一方集团的形式表现出来,只要它存在,人们就无法获得通过自己的努力公平地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因而,人类文明的理性发展只能是:“先形成社会阶级,然后一步一步次第解放它。每一步之阶级解放,亦就是人类理性之进一步发展。末了平等无阶级社会之出现,完全符合于理性要求而后已。”[14](P.144)在这个意义上,阶级社会又非理性化的社会,而中国社会作为理性的社会,则是非阶级性的。也即是说,中国并没有采用阶级这种方式来组织社会。
社会构成的环节包括个人、家庭、国家、天下,中国文明所特重者在家庭与天下,而西方所重者在个人与国家。西方社会构造本来是团体生活为本位,后者有个人本位之反动。但国家、教会与阶级等等都是团体化的组织方式。在这种社会构造中,被突显的是个人对团体的关系,即将个人组织到团体的空间中去;而在中国社会的构造中,家庭与天下都是松散的、非组织性的,最终都落实到人与人的关系。由此而形成了两个文明中对品德的不同理解。西方之所谓德性,重在个人对团体之关系,德性本身则具有凝聚与团结的功能,人与人的关系要么间之以神,要么间之以团体,这很容易导致人与人关系的非人格化现象,即梁漱溟所讲的“机械性”。而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人伦之学的核心,并没有被神或团体所中介化,也没有被卷到某种空间中,这就使得人伦构成秩序与意义的中心。根据梁漱溟的说法,西方重视的是个人对于社会的道德,即所谓“公德”,这种公德展开在个人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等的关系上,而不是具体的此人对彼人的关系,因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家庭、社会、国家、世界等体制性事实中介化了;而中国文明所重则是具体的这人对那人的道德,即所谓“私德”,所谓的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都是这人对那人的关系,而不是个人对某种团体的关系。[6](P.369)这就造成少年陈独秀虽有君臣概念,却不知道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国家的现象。中国文明的道德伦理不是用以组织国家和社会,而是一种在人与人之间建家的“里仁”方式。[15]
中国社会是以职业分途方式获得文明发展所赖以支持的社会分工的。职业所形成的差别,有“形势分散而上下流通”[14](P.156)的特点,这一方式既没有形成土地和资料的集中,也没有形成因职业造成的地位固化,极大削减了阶级形成的条件;与此相应的政治构造是“对内松弛,对外亦不紧张”的“无为而治”,这是一种以“不扰民”为最大信条、以“政简刑清”为最高理想的消极性政治方式,当其“太平有道之世,国与民更仿佛两相忘,则是中国真情”[14](P.158)。此与阶级社会中以阶级意识进行动员、或者积极参与共同体公共事务的“积极政治”形成鲜明对比。梁漱溟常引吕坤《呻吟语》如下表达述说中国的政治理想:“为政之道,以不扰为安,以不取为与,以不害为利,以行所无事为兴废除弊。”[14](P.158)此种政治类型的后果是中国人缺乏国家观念,总是爱说天下,个人似乎缺乏对国家的责任,相反,“他所积极表示每个人要负责卫护的,既不是国家,亦不是种族,却是一种文化”,梁启超也以中国先秦诸家言政治,虽然种种不同,但“莫不抱世界主义,以天下为对象”。这些都传达一种事实:“国家消融在社会里面,社会与国家相浑融。国家是有对抗性的,而社会则没有,天下观念就于此产生。”[14](PP.162-163)这样的中国社会以其消极相安而没有发展出高效而集中的国家组织动员能力,而其“制度似乎始终是礼而不是法”,于是,“其重点放在每个人自己身上,成了一个人的道德问题,它不是借着两个以上的力量,互相制裁,互相推动,以求得一平均效果,而恒视乎其人之好不好”[14](P.185)。同时,由于“政治上经济上各种机会都是开放的。一个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初无限制,尽可自择。而‘行行出状元’(谚语),读书人固可致身通显,农工商业亦都可以白手起家。富贵贫贱,生沉无定,人人各有前途可求”,“所以进取心,在这里恰好又普遍得到鼓励。伦理本位就是这样藉职业分途为配合,得以稳稳行之二千余年,得以通行到四方各处”。[14](P.191)所有这些,都促进了“向里用力之人生”。
而作为中国文明的担纲阶层的士大夫,乃是教化的主体,其功能正在“启发理性,培植礼俗,而引生自力”。在道德、礼俗、教化的辗转循环中,贯穿其中的就是“理性”,中国的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秩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统治者所握有之权力依从于士人所代表之理性”。在一人高居于上而万民散处于下的社会里,士人在君主与万民之间承担了如下的功能:“对君主则时常警觉规谏他,要约束自己少用权力,而晓得恤民。对民众则时常教训他们,要忠君敬长,敦厚情谊,各安本分。大要总是抬出伦理之大道理来,唤起双方理性,责成自尽其应尽之义,同时指点双方,各自走你们自己最合算最稳妥之路。”这上下两者之间做调停引导工夫的士人,“究竟理性唤起到怎样,且不说它,但彼此消极忍耐,向里用力,却几乎养成了中国人第二天性”,以至于形成了一个“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伦理社会。[14](PP.206-209)钱穆先生曾卓有见地地指出:“国史自中唐以下,为一大变局,一王孤立于上,不能如古之贵族世家相分峙;众民散处于下,不能如今欧西诸邦小国寡民,以舆论众意为治法。而后天下乃为举子士人之天下。法律之所不能统,天意之所不能畏,而士人自身之道德乃特重。”[16](P.653)士人之修身成德,在传统中国看似独善其身,其实却亦深有补于世道人心,只不过其感人之深、化人之渐,人所不知耳。“修身为本”“向里用力”都指向个人的“自得”:“中国的人生无他。只是自得——从自己努力上自得——而已;此即其东别于印度,而西异于西洋者。此‘自得’二字可以上贯周孔精神,而下逮数千年中国社会无知无识匹夫匹妇之态度,虽有真伪高下浅深久暂千百其层次而无所不可包,此实为一种‘艺术的人生’,而我所谓人生第二态度,其所以几于措宗教于不用者,盖为此。”[3](PP.78-79)礼乐制度、周孔教化、伦理本位为这种“自得”的人生路向提供了体制化条件与教化性条件。对于梁漱溟而言,整体上第二条人生路向中也含有一些消极的层面,而“自得”则是其积极成分:“在这条路向中,数千年中国人的生活,除孔家外都没有走到其恰好的线上。所谓第二路向固是不向前不向后,然并非没有自己积极的精神,而只为容忍与敷衍者。中国人殆不免于容忍敷衍而已,惟孔子的态度全然不是什么容忍敷衍,他是无入不自得。惟其自得而后第二条路乃有其积极的面具。亦惟此自得是第二条的唯一的恰好路线。我们说第二条路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一切容让忍耐敷衍也算自为调和,但惟自得乃真调和耳。”[6](PP.480-481)调和之路并不是没有原则、各方面讨好的折中主义,而其核心在“自得”之“德”,这种自得,修之于身,而后为真;其以自用为实,自得为真——这才是真正的持中调和。
四、印度文明与第三路向
第三条人生路向简称为“向后”[7](P.751),以印度文化为代表,“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6](P.383)。如果说西方文明所代表的第一路向是肯定欲望,并以欲望构筑人生,那么第三条路向则“根本否定人生,而要人消除一切欲望,达于无欲之境。因为觉悟到人生所有种种之苦皆从欲望来。必须没有欲望,才没有苦”,与第一路向虽然方向相反,但“却同样从欲望来理解人类心理。不过前者以欲望为正当,后者以欲望为迷妄耳”[1](PP.132-133)。通过否定欲望,意在引导众生走出迷妄,然而对欲望的否定,同时连带着“否定一切众生生活,从而人生同在否定之中”[4](P.183)。梁漱溟又将这种人生态度概括为“厌离”。“当人转回头来冷静地观察其生活时,即感觉得人生太苦,一方面自己为饮食男女及一切欲望所纠缠,不能不有许多痛苦,而在另一方面,社会上又充满了无限的偏私、嫉忌、仇怨、计较,以及生离死别种种现象,更足使人感觉得人生太无意思。如是,乃产生一种厌离人世的人生态度。此态度为人人所同有。世俗之愚夫愚妇皆有此想,因愚夫愚妇亦能回头想,回头想时,便欲厌离。但此种人生态度虽为人人所同具,而所分别者即在程度上深浅之差,只看彻底不彻底,到家不到家而已。此种厌离的人生态度,为许多宗教之所由生。最能发挥到家者,厥为印度人。印度人最奇怪,其整个生活,完全为宗教生活。他们最彻底,最完全;其中最通透为佛家。”[8](P.82)
“厌离”实即彻底的“出世”。而“出世”又是一切宗教的特征。所以,印度的思想尤其是佛教,在梁漱溟看来,乃是最彻底的宗教。印度文化中“具无甚可说,唯一独盛的只有宗教之一物。而哲学、文学、科学、艺术附属之。于生活三方面成了精神生活的畸形发展,而于精神生活各方面又为宗教的畸形发达,这实在特别古怪之至!”[6](P.393)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看来,哲学与宗教乃是两大门类,而哲学又分为形而上学、知识、人生三部,西方文明中知识论甚盛,有掩盖一切之势,为其哲学之中心问题,而中国文明则以形而上学为中心,印度则以宗教为中心。[6](PP.401-407)宗教是以超绝于知识的事物,谋情志方面的安慰勖勉,也就是它以超越者的信仰解决安身立命的问题。而所谓超绝本身意味着超离现有世界之外,就是超越感觉及理智所统的世界,因为使人情志不宁的正是现有世界,故而宗教以超绝者实施对这个现有世界之超越,这就注定了真正的宗教都具有出世的特征,“‘超绝’与‘出世’实一事的两面,从知识方面看则曰超绝,从情志方面看则曰出世”[6](P.419)。然而,宗教之存在的必要并不在人类自己勖勉自己而假借一个虚构出来的上帝,而是在于对于无常世界乃至生活本身之真正脱离,这是彻底的宗教之所以为宗教者。[6](P.429)印度的佛教之所以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就是因为它对出世的执着,出世不再是手段,而是目的本身;出世的需求成为一种真诚的人生要求。
梁漱溟认为,欲望的人生无以脱离动物式生活,禁欲的人生则是神佛的生活,[12](P.262)其实质是以神佛代人,人生的终极之境走上人生的自我取消,以取消问题作为问题之解决方式。印度文明之所以走上“无生”,乃是第一条路向之颠倒,第一条路向是人生本来的道路,人生而有欲,不能不向外向前寻找,然而由于欲望无穷,一时一地的欲望之满足不过激发了更多的欲望,故而“欲求愈进必愈苦”。人类通过发明种种乐境作为欲望彻底满足的符号化思辨形式,“如文明、进化、大同、黄金世界以及种种理想之社会”,然而“此不啻与富贵同一妄惑,并且彼时之苦必过于今。因人站在欲望上,一欲望得达,他欲望又将起来了。所谓欲望得遂者,要不过从第一个问题揭过去,到第二个问题耳。未揭过去时,以为彼处有乐,但既揭过去则无所谓乐了。故此说不但与富贵同一妄惑,进一层说其苦且过于今。根本的意思就是人类愈进化则愈聪明,愈聪明则愈多苦。章太炎‘俱分进化论’亦曾驳希望进化者之误,而谓苦乐是并进的”。[17](P.905)对梁漱溟而言,如果以构建美好的环境以救人,则不过是由第一问题引到第二问题。梁氏在其本人的出世阶段,以为出世之理“确乎不易”,“所谓解决世间问题之大圣大哲均是胡涂。而唯一救人之路,只有让人根本去解脱生命。凡有生命的,欲有乐而无苦,既绝做不到,并且明是苦多于乐。你要拒绝苦,则非解脱你的生命不可,此是根本解决”。[17](P.905)梁漱溟以为对于欲望只有两条道路,一是满足欲望的向前态度,一是取消欲望的向后态度。民国五六年间,当他发现儒家既不否定欲望也不肯定欲望,而以生生之仁自然而然地消弭欲望时,他发现了另一种人生态度,进而他将三种态度与人类文明三大系对应起来:“正是由于我怀人生是苦的印度式思想,一朝发现先儒这般人生意趣,对照起来顿有新鲜之感,乃恍然识得中印两方文化文明之为两大派系,合起来西洋近代基督教的宗教改革下发展着现世幸福的社会风尚,岂不昭昭然其为世界文化文明三大体系乎。”[5](P.185)
第三种人生态度回应的是“人对自己——自身和自心——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中,构成意欲之违碍的既不在外物(如第一问题),也不在别人(如第二问题),而是我自己——“我自己的身心有违乎我的要求”,而“自己身体亦是一物,那是在向外看时如此。若在内省自觉中的我身,便和我相连为一事,有异乎外在之一物。至如向外不可得见而只存乎内省自觉中的我心——我的生命——更与发为主观要求之我不可分。所要求与能要求的均不在外,是第三问题的特征”。[2](P.383)这一问题与态度中内蕴着对生老病死现象中所折射出来的人生无常的深切体验:“人谁不有病?谁不有老,有死?更总括一句话:谁不有烦恼痛苦?问题原早有,时时有,不过你不理会其问题在自己罢了。”[2](P.383)每个人都会面对这种无常,但通常人们都不是直面问题,而是转移问题:或则把它当做第一问题(物的问题)来处理,或者将其作为第二问题(人的问题)来对待,总之不能去直接面对无常。[2](P.383)但这是每个人无论如何都将面对的切己性问题,人们之所以没有直接面对,乃是因为人类还受困于人对物的问题、人对人的问题,总是优先地去面对后面这两种问题。一旦后面两种问题在社会化层面上解决了,这一人对自己的问题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换言之,它成为问题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人们是永不会把他自己当成问题的,除非待到外面问题——自然界问题、社会问题——被人类解决得差不多,而同时又发见问题正有不在外者。质言之,这将必在人类社会文化发展到极高乃始是其时机的。”[2](P.383)
虽然人对自己的问题需要条件,但是古印度人却较早地开启了这一问题,其文明的核心便是奠定了这一人生态度的基础:“虽从人类社会前途看去,这问题尚远在未来,但在个人感触亲切上说,却又明明就在眼前。于是聪明的古东方人——特别是古印度人竟以社会一时风尚集中其心思力气于此,从而成就得其特殊修养之学,有如佛学及其他种种。古印度人所特别敏感的,似乎从生死无常而深深厌恶这生命本身的机械、被动、不自在,其为违碍者恰就在能要求的我自己这一面而非在外。这可说是第三问题的核心问题。与此第三问题相对应的人生第三态度便是根本取消这一切,不要这样不自主不自如的生命。佛家所谓‘出离生死’,所谓‘解脱’,盖非独其一派的思想,而是那时不同教派的共同思想。又非徒思想而已,而是以行动实践出之。只有这样出以行动实践,乃具见其要求真切,有不容已。正唯其要求真切有不容已,而后其在解决问题的实践功夫上乃踏实深入,终于产生出真学术,收到问题解决之效而不虚。故我们可以说正同乎前此之例:此特殊修养之学成功固在人生第三问题而尤在此第三态度。”[2](PP.383-384)换言之,正是对于人对自己的问题进行追问而不放松,在学术上步步踏实,在践履上直接面对,才成就了印度的文明。印度文明基于上述问题与人生态度,因而在整体上具有出世的性质:“此第三态度亦曰出世的态度,对人世间生活是消极的。人在解决第三问题时(在解决对自己身心问题时),总或浅或深地有此倾向。这大抵看其问题浅深而定。譬如问题止于在自身就浅。因自身是自己生命比较靠外的部分,愈向内愈深,而深的则包括浅的。像生死无常这种问题正是‘一包在内’了,便彻底消极。”[2](P.384)
当然,第三条道路虽然由古印度人发展起来,但走第二条的中国也会以某种方式涉及第三问题:“从第三问题所引发出的学术亦就依此而浅深不等。具体点出来说,如中国道家养生之学,就是从自身病痛老死问题引出人们在其机体生理上、在其起居生活上如何自己调理以适应天地(大自然)变化,而求得某种自主自如的一种修养之学。与此相联相通的,或说于此植其根基的还有中国传统的医学、体育、拳术等等。这许多学术皆在身体上做功夫,对于机体生理从内里有所认识,从而多少取得生活上某种自主自如,在表面上已完全看不出其消极倾向,而其实脉路上、体系上同道家原是一回事。而道家不单于世间生活著有消极色采,更且在功夫实践上是逆着生物所有生殖倾向的,所谓‘顺则生人,逆则成仙’是也。所以道家虽不像佛家那样彻底圆满地解脱生死,而从道家进入佛家却十分自然而容易。因此,正不妨以一系列浅深不等的学术看待他们。”[2](P.384)梁漱溟以为道家思想也是回应第三问题的,只是佛教在第三问题上比较彻底,其所修者是“无为法”,“而中国道家和印度那些外道所修统属‘有为法’,二者绝不可同语”[2](P.385)。在梁漱溟看来,道家之学“介于世间法、出世间法之间”,之所以被称为“有为法”,乃是因为“其对于人世间显示消极,近乎出世矣,而仍处在生灭迁流中,终未超出来,属于佛家所谓有为法,非所谓无为无漏者。无为无漏的无为法唯于佛家见之”[18](P.341)。梁漱溟将道家之学与佛教共同囊括在人生第三问题与第三态度之下,视之为只有粗浅与深彻的程度之别,或取得自主自如、有限与无限之层级不同,而不是本质路向与态度范式的不同。当然,第三路向究竟以佛教为最为典型,而如何判断佛法与非佛法的区别,梁漱溟以为关键在三法印,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18](P.349)而这正是从世俗生命中解放出来,破我法二执,断能所二取,不再沉沦于生死轮回中,即一切法而空一切相,回归圆满清净之体。
与孔学一样,佛教作为早熟的思想,因不得其时,虽然在第一问题尚未解决的时代就已产生,但毕竟不能大行。佛法在释迦牟尼说法四十余年后卒归衰落,“其影响于环境社会者终不敌其所受环境之影响”,在各宗教彼此辩论之盛大的时代,而佛教本身亦归于头脑思辨之业,而丧失其根本精神,当理论之精妙与圆融为其所尚,则其根本之出世间之实践,则不得不式微。[18](P.351)此其所处的世界历史纪元不得其时,然后方有此问题。梁漱溟写道:“人对自己问题的学术,是打通世间出世间的学问,即是澈究乎宇宙生命的学问。世间一切众生的生命均有很大机械性、盲目性,十分可怜悯。进至人类,自一面说仍不异于其它生物,而另一面却见有反观内照之可能,亦即有脱出机械性、盲目性之前提条件。当人类生活困扰于第一问题下,是颇难自反的,转入第二问题较能自反了,仍处在调整人间彼此关系,实现协作共营生活之期中。大约在此期中和期末,将见此第三问题的学术亦即古道家古佛家的学术复兴起来。换言之,古道家之学、古佛家之学各为将来世界学术之早熟样品。”[18](P.363)古道家与古佛家的取向之复兴,是世界历史的最后纪元,但这一纪元本身是否是对中国纪元的超越,则有待进一步探讨。[19]
梁漱溟以人生路向与文明类型的互构,将对世界历史秩序的理解从西方近代的基督教神学背景下解放出来,但是在他那里,历史哲学的架构仍然受制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哲学,这表现在,他虽然对黑格尔的世界历史从东方世界(一个人的自由)开始,经过古希腊世界与罗马世界(一些人的自由),最终到日耳曼世界(一切人的自由)进行了翻转。这一翻转重新赋予了中国文明以世界历史的未来意义,但他仍然与黑格尔一样,将同时性的多元文明编排在一元性的历时性文明进程的叙述中,而未能敞开儒家传统对人类文明之多元一体格局的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