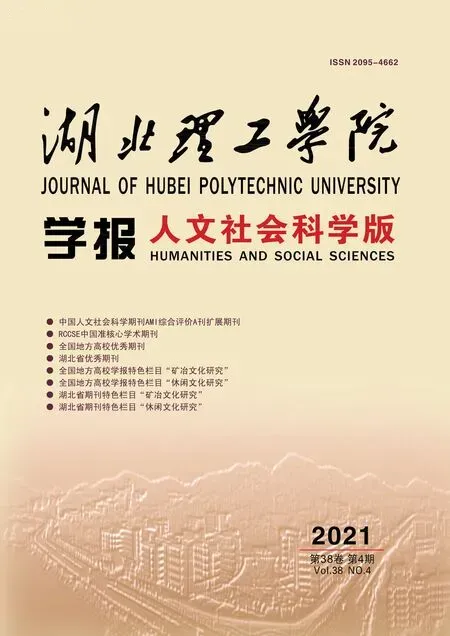日常生活的贫乏与超越
——论萧红《呼兰河传》对“后花园”意象的建构
2021-01-16杨增艳程娟娟
杨增艳 程娟娟
(1.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92;2.华南师范大学 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006)
茅盾在《呼兰河传·序》中指出,因缺乏所谓构成小说的基本要素,故而其并非一部遵循传统小说样式的严格意义的小说。值得注意的是,恰恰去除了“中心”“主题”等思想的介入与统摄,让日常生活以自身而非创作主体预设和建构的既定框架和模式展开,日常生活中人们真实的存在状态开始浮现。通过如实描述人在日常生存境域中的存在常态与状况,可以对日常生活中人的基本处境有个真实而贴切的理解,进而引人思考“如何更好地生活”等难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萧红笔下的呼兰河小城的日常生活就跨越了特定时空区域的限制,凸显出存在论意义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非本真的存在状态。寓居于世,人或显或隐地受制于日常生活的基本图式。“后花园”作为一个与呼兰河小城整体卑琐、庸常、沉沦的日常区分开来的生活世界,可视之为人从日常生活内部思考克服乃至超越非本真存在状态的一种尝试。
一、只是活着:对非本真日常生活状态的展现
日常生活是我们身处其中且每天都要面对、经验的世界。诸多作家的作品里都有丰富的关于日常生活与经验的写作。《呼兰河传》也摒弃了对宏观历史的渲染与描摹,反倒围绕着呼兰河小城里人们的日常生活,聚焦于微小人物的生存状况而展开。有意思的是,同样都是描写日常生活,《呼兰河传》退出了主体某种过于统一的创作意图,不将诸多观念凌驾于日常生活之上①,不惊扰日常生活本身真实的显现。如前所述,《呼兰河传》偏离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且作者在文末也言明自己创作的缘由不过是那些幼年的经历深埋在记忆中,无法忘却。回忆意味着将自身放置在一段过去了的时空之中,这种对已然消逝的事物的再次唤醒,可能会因时空的差异而产生种种的加工、错位乃至变形。尤其很多人、事都是在作者一次次的“看”中丰满起来的,这些幼时常见的场景与画面,几经回味,难免会有疏漏。若抛开对记忆是否真实的辨析,仅仅着眼于作者对那些日常场景不厌其烦的“看”,这种观看悬搁了种种先入为主的前见,现象世界与作家之间的中介便暂时消失,感官在此时成为作家最重要的依托,现象以如其所是的本来面目一一展现。正因如此,日常生活才能剥离宏大历史叙事的遮蔽,琐屑的日常生活和每个鲜活生命经历着的微末细节在作家的“看”之中逐渐清晰起来。
就《呼兰河传》的篇章结构来看,第一、二章围绕着大泥坑、染缸房、扎彩铺、买麻花、买豆腐、跳大神、放河灯、看野台子戏、逛娘娘庙大会等意象与场景,呼兰河城里人们的一日三餐、一年四季的日常生活变得生动立体。而从第三章开始,作者开始将自己的目光聚拢到自己的“家”,从后花园里的祖父、祖母、父母,再到生活在院子里拉磨与漏粉的人们、小团圆媳妇一家、有二伯、冯歪嘴子一家,作者花费大量的笔墨书写着呼兰河人的日常生活,不知疲惫地看着那些冗长而驳杂的生活现象。毋庸置疑,作者看到的生活细节是丰富多彩的,每个人都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经历着生活给予人的悲欢离合与生死变幻,演绎着截然不同的人生命运。正是每个人面对的生活有着巨大的差异,假借作者之眼,读者也体会到了不同的人生况味,看到了呼兰河小城里的人生百态。问题在于,纵使每个人所展现的生活的面貌各自不一,若将日常生活的诸现象放置于一个客观如实的视野之中,则生死悲欢间的差异也开始消弭,一天总是稀里糊涂地过,“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1]724,活着却不过是“为了吃饭穿衣”,死了便也死了。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中现象虽是繁多,却能带出构成日常生活的最为本质的东西。
在海德格尔看来,在世界之中存在乃是此在(Dasein即人)的基本结构,此在以日常生活的形式与他人共在于世界之中。但此在首先“通常是非本真的,即常人自己。在世总已沉沦。因而可以把此在的平均日常生活规定为沉沦着开展的、被抛地筹划着的在世,这种在世为最本己的能在本身而‘寓世’存在和共他人存在”[2]210。亦即,日常生活中的人通常不是作为自身而存在,日常此在脱离了本真状态而消散在常人中。这个常人是指一切人而非特定个体,常人有力地规定着此在之日常存在方式。庸碌无为、均质状态是常人的存在方式,使此在的个性及差异被抹平。常人以卸除每一个此在责任的方式,让此在既无需为自身的存在负责,也不用为自身需要独自判断和决断而烦忧,由此获得对日常生活的统治。通过对此在之在世现象的整体性分析,“海德格尔把此在日常借以在此的基本方式称为‘沉沦(Verfall)’。沉沦的基本样式是闲谈、好奇与两可”[3]84。
以海德格尔的视野观之,闲谈是一种包含了平均且可理解性的话语,人们并不对自己所言谈的内容做深入的了解,甚至根本不关心言谈本身所传达的内容与实质,而是只在乎自己将这些“言谈”言谈了一番。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呼兰河小城的日常生活是喧闹而丰富的,生活在这里人们也多是良善,总会同情不幸者,但是他们“也颇敏感而琐细,芝麻大的事情他们会议论或者争吵三天三夜而不休”[1]702。而泥坑子给当地居民的福利之一就是“常常抬车抬马,淹鸡淹鸭,闹得非常热闹,可使居民说长道短,得以消遣”[1]717。除此之外,此在的好奇并非为了切近存在的本质,也并非为了达到对存在的知,而不过是一种为了趋向所见之事的观看,仅限于从一种新奇之物到另一种新奇之物上。正是对新鲜事物的不断窥探,好奇为闲谈提供了可资谈论的资源。在《呼兰河传》里,当小团圆媳妇因病而请来跳神赶鬼、看香、扶乩的人时,他们家竟被前来看热闹的人所挤满,只因他们家跳神的形式超出了当地人们见过的花样,可谓开启了跳神的新纪元。若错失了这次机会,人们会认为一来失去了谈资,二来会因此落伍,甚至是此生之不幸。如此看来,似乎小团圆媳妇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个体,其生死并不能进入“看热闹者”的视域,大家只是着迷和醉心于看本身。而闲谈和好奇的联合,便引出此在沉沦的第三种样式,即两可。两可作为一种知的方式,其并不去深究事物之实质,仅仅限于对事物之浅层的理解。概言之,此在在日常生活中与常人的共在是依靠闲言、好奇与两可作为引导的,此在沉沦于世即是个体消散于这种共在中,常人的沉沦在引诱着此在加入其中的同时,也给此在一种安定之感,却将此在引向异化。
在这种无根基的以非本真存在的状态中,均质无差异的常人牢牢地掌控着日常生活,那么“此在这种存在者在其日常生活中恰恰丧失了自身而且在沉沦中脱离自身而生活着”[2]207。因此,呼兰河城里的人们每一天都在不断重复着前一天的生活,有热闹时看一通热闹,之后的日子照例波澜不惊地过着。在繁琐零碎的日常生活中,即便是与普通日常生活区分开来的“节日”,与往常也并无不同,甚至还令人生出无端的空虚来。人们“一年柴米油盐,浆洗缝补。从早晨到晚上忙个不休……只不过咬着牙、打着哼,一夜一夜地就这样过去了”[1]724。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活中好像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欣喜与悲伤的,生死不过是稀疏平常之事。通过对日常生活中人们真实的存在状态的发掘,萧红勾勒出呼兰河小城庸常、单调、贫乏的日常生活状态。
二、追根溯源:日常生活基本图式对生命的禁锢
在《呼兰河传》中,只有日常细碎的每一个瞬间构成了生命最为重要和实在的东西,呼兰河人有着自己特定的生活方式、集体认同的价值理念,这些都在维持和推动着人们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如果说人作为能思的主体,通常都会生发出超越自身去寻求生命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依据的渴望,何故在现实中却顺服沉沦在重复杂芜的日常生活中,依照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经验习惯思索与生活,成为缺失反思自我之生存境域的无思的个体?根本原因就在于日常生活的基本图式对于日常主体的支配与禁锢。
呼兰河小城的日常生活以特定的节律发展着,卖麻花、卖凉粉、卖杂货、卖豆腐的人总是在每一天特定的时刻到来,等傍晚的乌鸦飞过,一天就过去了;人们在夏天的时候穿上单衣,在冬日里穿起棉衣,一年也便消逝了。一天之中发生的平凡小事、一年四季的交替变换,构成了呼兰河小城平凡稳定的日常生活。从这个角度来看,呼兰河小城里人们的生活整体是依照着自然规律运行的,这种遵循着固定自然规律的重复不断的日常生活,一方面使呼兰河小城的生活呈现出某种统一化的特性,另一方面也为生活于此的人们建构出一个相对稳定和自足的生活空间。于是乎,尽管每天的生活显得重复又单调,在日常中必得承担起劳动的重负,会遇到诸如想吃豆腐而买不起的窘困时刻,也需时刻面对生老病死的临近,但是发生在大泥坑里的趣事、看野台子戏时发生的争吵、跳大神的精彩瞬间、看小团圆媳妇治病和洗澡等微末的日常小事又在不断地调剂、充实和平衡着相对枯燥的日常生活,让体验着日常生活的主体感受到一种切实的心理满足,进而使人们生发出足够的忍耐力和承受力去面对这充满艰难困苦又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以此能够让卖豆芽的王寡妇在丧子发疯之后,尽管无法忘却自己的哀伤,在大街或庙台上痛哭之后仍旧记得吃饭、睡觉、卖豆芽。有二伯和老厨子在参加完小团圆媳妇的葬礼之后,可以自如地谈论着当天宴席上的饭菜是否可口。
诚如海德格尔所言,此在通过将自身融入与常人的共在之中,建立起与他人及其世界整体性的统一,以便使自身安住于此稳定的生存境域之中。此在在与常人共在的人云亦云中,会形成一种一般化的思维模式。同样,日常生活中的个体顺应着天地自然的循环节奏,在斗转星移的时光变化中生命不断地繁衍生息,日常生活作为一个先在的、给定的生活世界成为生命得以栖居发展的居所。这个此在日常共在的生活世界,蕴含着这个群体的习俗传统、生存智慧以及体认世界的方式。由是观之,在日常生活世界中“自然主义的立根基础和经验主义的活动图式从两个方面共同决定着日常生活的自在性、重复性和类自然性”[4]55。可以说,重复性的思维与生产实践是稳定自足的生存空间得以产生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并且经验源于对经历的总结,含藏着个人或群体的智慧。但是以一种过去了的固定化的思想来指导、作用于每一个鲜活的日常时刻,其必然会有诸多局限。因此,若生命依照着日常生活强大的基本图式运行,其弊端也显而易见。
其一,鲜活的生命主体被降解为生物性、自然性的存在。人以物质性的形式存在,需要借由物质来保障生命的正常运行。日常生活涵盖了人类生活与生产的方方面面,在很大程度上为生命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人的需要层次是一个立体多维的结构,包括物质与精神等多个方面。倘若人停留在生存材料的获取之上,将物质与生理的满足视为生活全部价值和意义的实现,则人无法从较低层次的生存需要过渡到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的提升,生命停留在生物性与自然性的层面。进而不难理解,为何在呼兰河城里人们凡买东西都要讲究个实用、耐用,最大的心愿是可以吃饱穿暖,若问起生活的意义,也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不过是吃饭穿衣”。若是每天都能够吃上一块豆腐,则日子便能充满欢喜,“破草房有上半间,买上二斗豆子,煮一点盐豆下饭,就是一年”[1]725。
其二,对主体意识与创造性的抑制与削弱。在海德格尔看来,时间或时间性是切近此在乃至存在问题的关键,甚至可以说此在即是时间性的,只有时间性使得此在之在世以及超越自身成为可能。必然性(被抛)、可能性(筹划)和现实性(沉沦)作为此在现象的统一体,此在并非只能以沉沦的形式与他人共在于日常生活之中,此在可以先行领悟和走向死亡而复归本真的能在。因为意识到自身存在的有限性,此在忧心于自身的存在,于是不断地在有限的时间内调整和筹划,来延展与实现自己可能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性使得人与其他的存在者区别开来,也使得此在不断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而出离非本真的存在。但“日常生活的内在结构和一般图式具有自在性、稳定性、惰性和保守性,具有凭借着传统、习俗、经验、常识等自在的文化因素而自发地运行的特征,即‘以过去为定向’的特征”[4]266。于是乎,尽管日常生活构成了生命存在之境域,也为主体提供了一个可凭借意识思维来实现自身存在价值和意义的空间。然而日常生活主体更多地还是会下意识地以现成的可供借鉴的经验去应对日常生活,这种不证自明、无需反省的思想经验已然固化成一种统一的思维模式,深深地支配着日常生活主体的思考和行动,使得个体很难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极少产生创新性的思维,遑论生发出审理反思当下生存境域的超越之问。故而可知,为何生活在呼兰河城里的人们不用广告招牌都能准确地找到“李永春药店”和其他的布店、粮店,却对不合常规的牙医生的招牌充满了恐惧;遇到事情,尽管也会热热闹闹地议论上一番,但是需要解决问题时,不外乎一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可以说,“他们过的是既不向前,也不回头的生活。是凡过去的都算是忘记了,未来的他们也不怎样积极地希望着,只是一天一天地平板地、无怨无尤地在他们祖先给他们准备好的口粮之中生活着”[1]767。
概言之,循环有序的日常生活在为主体营造出一个安稳居所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整体性的意义机制,于是日常生活能够长期不断地运转。然而生命一旦耽于重复性的日常生活,困囿于日常生活的一般图式,那么生命也便沉沦于单向化、一维化、同质化的生活平面,成为丧失否定、反思以及超越的常人,很难想象或思考开启另一重生活的可能性。
三、探寻出路:后花园世界的建构
“本真的生存并不是任何漂浮在沉沦着的日常生活上空的东西。”[2]208那么,寻觅一种本真的日常生活,就不是指以一个外在的本真生活世界来观照与统摄非本真的生活世界,以此疗愈和拯救日常生活的沉沦和异化,而是沉潜到日常生活之中,从日常生活内部发现生命存在的另一种可能性,以便使生命超越驳杂单调的日常生活而趋向本真之能在。正因如此,“后花园”作为一个充满自由与爱的生活空间,使作者能够暂时从日常生活图式的桎梏中抽离出来,在呆滞循环的日常生活中获得一种真正的“在家”之感。
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重复性的思维和生产实践,但是日常生活的基本图式又在束缚和禁锢着生命主体意识的勃发和超越。故而,要“在日常生活中开辟出一块可给予人性人情的自由空间,从而缓解一般行为图式给生活主体制造的压力”[5]。在“后花园”世界里: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蝴蝶随意地飞……我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1]758
如果说,统摄在自然时序中的呼兰河小城的日常显得庸常、滞缓而缺乏明亮的色彩,那么,与之相对的后花园世界,植物恣意地生长,动物轻盈自在地飞翔,“我”惬意地玩耍,祖父自由自在地闲着,一切事物都显得轻快而鲜活。作者也用了“健康”“漂亮”“宽广”“繁华”“鲜绿”“热闹”等词语来描述后花园。
若言植物、动物与人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生命存在系统,那么作者借由植物的繁茂、动物的灵动、人的清闲愉悦,展现出的这一幅鸟木草虫生机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就可以发现后花园是一个能让生命舒展的自在空间。万物在此空间里的勃勃生长,也预示着生命自身蕴藉的无限的活性和可能性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反观生命在看似平稳的日常生活中,只受生存本能的驱动时,生命的潜能与活力就被淹没和沉寂了。因此,尽管后花园也受到时节的限制,会在寒冷的冬季封冻,“我”也时常被祖母训斥,但是在后花园里无拘无束的生活已然与呼兰河的日常生活世界隔离开来,让生命体味到一种本真的自在与自由。
诚然,适宜的日常生活给予主体一种安定的“在家”的舒适和怡然。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就日常生活带给主体一种因物质性生存得到保障而产生的一般性满足,以及人们在这种相对平稳安全的生活氛围中获得的心理感受而言,而不是指生命内在精神的安顿。呼兰河小城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固定的生活空间,是呼兰河人世世代代生长的“家”。但是为何这样的生存境域却始终让作者感受到无处不在的“寂寞”和“荒凉”,乃至让无数的解读者认为萦绕在作者心间的是一种“无家的寂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个供人居住的空间,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心灵之安稳居所,没有令人产生一种真正的“在家之感”。而家园之所以蕴含着让人无限神往、留恋的情感,也是人类丰富情感得以产生和寓居的空间场域,就在于“‘家园’意指这样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唯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己要素中存在”[6]15。那么后花园会成为一个独特的生活世界,也在于这是一个被爱所充满的生活空间,关涉主体之精神得以实现真正的归依。
可以说,《呼兰河传》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者真实的成长历程——从小父母便对自己很冷淡,偶尔的恶作剧还会引来祖母拿针刺手指的“惩罚”,这一切都很难让人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家所带来的温暖和爱。作者用“极小”“极黑”来形容祖母和母亲的住房,这样的意象引出的是家庭给自己的真实的心理感受。但祖父是一位截然不同的家庭成员,当“我”出生的时候,祖父便感到由衷的高兴,在成长过程中也是始终笑盈盈地对“我”。与父母和祖母遇事就非打即骂的态度不同,祖父对于作者表现出了更多的包容和爱,以因势利导的方法让她去体认外在世界。于是,在作者心中,只要有后花园,只要能和祖父在一起生活玩耍,就能够抵御住所谓“家”带来的寒凉。故而可知,后花园是对真正“家”的空间的隐喻,而祖父则是让“家”之温暖得以产生的主体。从这个层面上看,后花园对作者而言就具备了某种形而上的意味,成为滋养生命的基石。所以,和祖父在一起读诗、烤猪肉的场景都是生活中的快乐源泉。看似简单的铲地除草、采摘果蔬、追赶蜻蜓蚂蚱、重复的取帽子把戏都透出无尽的乐趣,在平凡的生活琐事之中也能心生无限的欢喜。而这种体现出生命丰富意趣的日常生活,也让作者深深地感受到一种真正“在家”的舒适和惬然。以此,让作者在不停地“看着”呼兰河小城日常生活的同时,也要不断地返回到自己的后花园中。
四、结语
“后花园”是萧红创作中的一个常见意象,而“后花园”意象的建构也通常与对人的生存境况、存在状态的描述紧密相连。抽离概念化的对人之生存状态的宏观把握,让日常生活能够较为鲜明地展现出人的真实处境。萧红看到:寓居于日常生活中,沉沦成为人们无法摆脱的命运。鉴于萧红对这种生存经验的体认,筑造一个自由的“后花园”世界,一定程度上使她从贫乏琐屑的日常生活中脱离而出,同时也让她不断生发出内在的力量去经受住这庸常的生活世界。
注 释
① 诚然,有研究者通过“大泥坑”的意象,认为萧红对《呼兰河传》的创作仍旧是继承了鲁迅以来的“改造国民性”的传统,这种解读也不无根据。“改造”预示着作品中植入了作者强烈的主观意图,有一种统摄性的叙事声音,故而就会有完整的故事结构。而《呼兰河传》作为一篇不像小说的“小说”,就在于作者舍弃或淡化了让人物和故事趋向自己预设的既定模式,现象剥离掉附着于自身的臃肿的观念,不为主体的强大意志所支配塑造,由此日常生活的诸面貌得以一一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