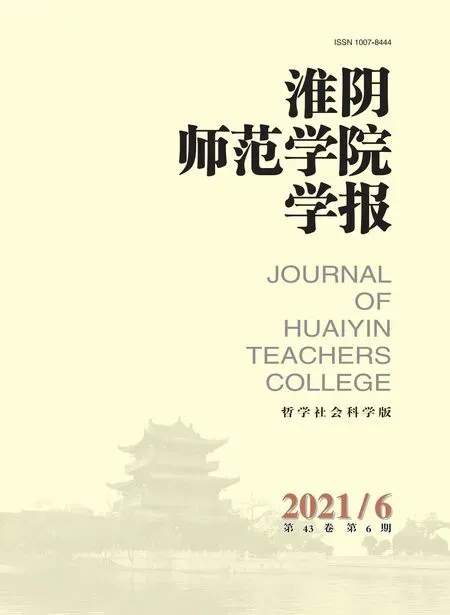中国运河学研究的扛鼎力作
——评张强教授的《中国运河与漕运研究》
2021-01-15李强
李 强
(淮阴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 江苏 淮安 223001)
1998年的时候,张强教授“准备写一部大概40万字的运河与城市研究作品,但写着写着,规模就越写越大了”。20多年过去了,从基本文献整理到历史梳理再到理论建设,一步步拓展运河研究的疆域,一笔笔绘制中国运河学的宏大蓝图,原本40万字的著作升格为5卷本270余万字的皇皇巨著《中国运河与漕运研究》。该书在运河研究所涉及的诸多方面都有开拓性的建树,她的正式出版标志着中国运河学的研究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展。
张强认为,运河学是一门以运河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学问,通过研究运河与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城市等之间的关系,可以充分认识运河在历史进程中的价值以及它对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具体地讲,运河学研究至少有十个方面的重点:第一,重点研究运河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开挖的历史;第二,重点研究运河与古代交通的关系;第三,重点研究运河与古代城市的关系;第四,重点研究运河与古代政治的关系;第五,重点研究运河与漕运的关系;第六,重点研究运河与经济、人口的关系。第七,重点研究运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第八,重点研究运河与中外交流的关系;第九,重点研究运河沿岸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第十,重点研究运河与自然水系、区域地理及环境的关系。[1]以上十个方面其实就是张强教授设计的有关中国运河学的学术版图,代表着张强教授建构中国运河学的学术勇气与学术“野心”,而这十个方面也在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实践。
该书分为先秦两汉卷、三国两晋南北朝卷、隋唐卷、两宋卷、元明清卷,以此来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运河开挖的情况,重新梳理中国运河史,绘制各个时期的运河网络。该书不仅在历史的纵向上大大地开拓了运河史,即将运河史上溯到大禹治水时代,对上古时期的运河开挖的时间进行了梳理和考辨;更是在历史的横向上极大地细化了运河史,将各个时代的运河开挖情况尽可能地落实细化,下大力气考证辨别,弄清了很多之前不清楚、不准确的运河历史,为中国运河学研究取得了新进展。比如,关于鸿沟的开挖时间与建成的时间、历代称谓的变迁以及所利用的自然水系,张强都通过仔细的考辨,得出了可靠的观点,让鸿沟的前世今生、来龙去脉都原原本本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运河最早的使命就是打通水运,便于交通,规模也只是区域性的。渐渐地,运河发展成全国性规模,在国家治理与社会生产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影响力也逐渐深入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该书以大量的史料和事实对中国运河发展的这一总的趋势作了呈现:中国运河首先是区域性的运河,在不断连接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后世的规模。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开启了运河开挖的历史。汉代以后,区域性的运河被逐渐连接起来,初步形成了贯穿南北东西之势。隋朝,在前人的基础上,建成了以洛阳为中心、向不同方向辐射的运河。作者放开手脚,以宏阔的学术视野,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立体地呈现出运河在中国古代社会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如何深入探讨运河在古代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影响呢?作者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即把运河和漕运结合到一起研究,这也是该书最大的特色和亮点。应该说,官方开挖运河的主要意图就是为了漕运,而漕运又关乎政治、军事、经济等国运命脉,所以,抓住了漕运就抓住了运河研究的根本。作者始终以漕运的视角从十个方面考察历代运河:第一,考察历代是如何利用漕运调集租米及赋税入京,保证京师地区的粮食安全和政治稳定的;第二,考察历代开拓疆土及平定叛乱是如何以漕运的方式向边地运粮及军用物资的;第三,考察漕运通道作为商贸往来的大通道,在稳定国家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等方面负有的特殊使命;第四,考察因漕运建造的水次仓即沿岸建造的中转仓,在国家战时就地运兵粮至前线以及灾年就近赈灾放粮中的作用;第五,考察作为漕运重要组成部分的盐运,在国计民生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第六,考察漕运在改朝换代中负有的特殊使命;第七,考察有“海漕”之称的海运在元明时期的国家漕运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第八,考察漕运与屯戍的密切关系;第九,考察水陆联运中的漕运;第十,考察历代漕运管理制度与措施。这十个方面几乎涵盖了漕运研究的全部领域,既标志着作者在漕运研究上的航标式成果,又集中代表着作者为漕运研究设计的基本框架与方向,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多种路径。
除了大刀阔斧地开疆拓土,为运河与漕运研究建构体系,指引大的方向外,作者还通过深入考察运河与漕运,获得了一把解剖历史的利器,从而得以透过表面层层的迷雾直抵历史的真相,得出更本质更精准的历史判断,在很多具体的问题上取得不少新的发现。比如,作者通过研究唐宋时期的运河与漕运情况,发现唐代安史之乱后到北宋,漕运主要依靠江淮即淮南,此时征收的江淮漕米数量超过江南。这表明在经济中心从黄河流域向江南转移的过程中,中间有个江淮兴盛的时期。淮河流域的兴起经历了从淮北到淮南的历史,淮北兴盛始于汉代。淮南及江淮地区到了隋代,其经济发展水平已领先于黄河流域,为安史之乱后唐代重点征榷江淮打下了基础[2]。此论打破了人们惯常的认知,揭示了更真实的历史进程。这样的例子在《中国运河与漕运》一书中比比皆是。
书中还广泛涉及运河与古代城市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通俗文学的发展等多方面关系的具体研究。这些既是作者为运河学拓展的新领地,也是作者给古代城市研究、商品经济研究以及通俗文学研究等领域带来的新视角和新方法,激发出了这些领域新的活力,促进其研究的深化。正是因为有了运河研究这个视角,作者对古代城市的选址与兴衰的原因,有了更本质的认识。作者认为运河改变了原有交通布局,也改变了原有的城市格局,运河沿线的航段节点成为人口密集的繁华都市,具有一定层级的行政建制也向运河沿线迁徙或者运河沿线低层级的城市成为高一级的行政建制,可以说运河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原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同样,从运河研究视角切入,作者找到了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大运河的拉动作用。作者认为大运河参与商品流通,在一定范围内打破了旧有的生产方式,带动了周边城市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动摇了原有的社会基础,使一些城市因缺少运河水运便利而走向衰落,而以苏州为代表的运河城市却得以迅速扩张壮大。商品经济的繁荣与运河城市的壮大又带来了市民阶层的崛起,影响到思想与文化领域,就是启蒙思想的发生与通俗文学的兴盛。这一系列的变化,因作者抓住了运河这一关键而使得一切纲举而目张,层层推进而不失其根本。
总之,《中国运河与漕运研究》是运河与漕运研究的力作。她体大思精,既有宏观上的架构,又有具体问题的深入。可以说,该书重构了中国运河与漕运史,多学科多层面的综合研究展示了运河研究的基本范式,拓展了运河研究的疆域,绘制出了中国运河学的学术版图,称得上是中国运河学研究的扛鼎力作。作者以一人之力,完成如此宏大的建构,实属不易。尤其是近些年来,作者有恙在身,却仍能坚持研究,在中国运河研究领域树立一座巍峨的里程碑,期间所付出的艰辛实非常人所能想象。有念于此,笔者在捧读她时,更感其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