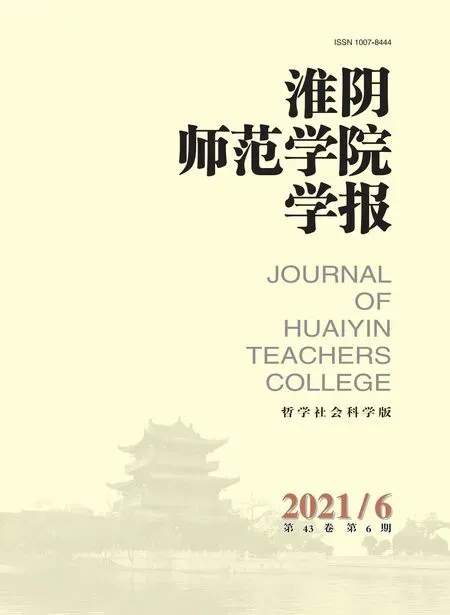论韩少功散文的乡土情结与文化诉求
2021-01-15苗珍虎
苗珍虎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韩少功从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寻根”,到新时期身体力行地“回退”乡村,展现出知识分子少有的干涉现实的悯农意识与乡土情结。他的散文在探索现代化语境下人的心灵困境、民族苦难与文化蜕变等方面表现出特定的民族文化思维方式与审美精神,善于将现实生活的矛盾与社会心理的变迁融入对乡村命运的关注和文化冲突背景中,从而呈现文化碰撞下的乡思之旅与身份认同。这既体现了韩少功对现代化资本原则的清醒抵制及其对本土文化精神的确认,更为可贵的是韩少功能够“转换着自己的思维模式和创作方式,在对现实社会与现实文化的关切之中,突出了知识分子的实践品格”[1]167。
一、精神疗伤的乡土情结
“高楼大厦”为代表的城市生活带给韩少功现代性的生活体验和审美视野,他自述“被城市接纳和滋养了三十年,如果不故作矫情当心怀感激和心存思念”[2]3。但同时城市化的节奏与生活氛围又令他感觉到“挤压”“烧灼”和被“拘押”[3]126。因此,当带着田野气息的清心雅趣越来越稀罕与遥远,乡土逐渐成为精神疗伤的家园,越加令韩少功牵肠挂肚。背井离乡之时,人们会通过脱离权利关系之外的自然来抒发对故国和家园的感怀,比较而言,乡村显然“更能构建一种与精神相对应的物质形式”[4]217。而文学艺术则是“隐含着人生经验和精神取向,是叩问人心和唤醒人心的声波信号或者图像符号”[5]85。因而韩少功的散文不仅反映出他对现代性的反思,更多的是源于作者对遭受现代文明冲击下乡村命运的现实关注和对乡土文明的眷恋。
韩少功既是乡村景观的旁观者,同时他每年有半年时间回到湖南省汨罗市八景乡进行乡村调研,并参与乡村劳作,这使他能够贴近农民、贴近土地,成为乡村文化的参与者。这样的双重身份赋予了韩少功特殊的时空感知角度。他认为中国乡村是“一个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撞击和融合的交错部位……站在两种文明的夹缝里,左看乡村,右看城市,可以有更多的比较和辨别”[6]79。因此能够带着对现代文明的疑惧和对乡村人道主义的忧患意识,更加清晰地感受到城乡一体化过程中以城市理念来建设农村导致的乡村文化传承的断裂。对于选择半年“农民”的生活方式,韩少功称之为“进步的回退”,同时指出回归乡村并不是要对抗现代化,而是因为自己“得到了心境的宁静、劳动的乐趣、人际关系的和睦、时间的自由安排等等”[6]2。
韩少功选择“回退”乡村的生活方式,与乡村相对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相对简单而和谐的人际关系、相对淳朴的民风与文化信仰,以及相对纯净平实的权力色彩有关,本质上是韩少功努力缓解自身与城市文明的紧张关系、消解城市文明戾气的精神抉择,是自我对生存价值的整体观照与人格确认,体现出不随波逐流的文化人格与价值取向:“关切劳动者的世俗生存,恰恰是道德的应有之义,是包括审美活动在内的一切精神活动的价值支点。”[6]118
韩少功的散文展现了鲜活的乡村民俗被城市文明的逐步改造。比如,他的《山南水北》中提及的相关变化,不单是乡民衣着方面的时尚变革:农民穿着蒙上灰尘与污垢的皮鞋,而韩少功则脚穿简单方便的黄鞋子。而且乡村传统美德也遭遇着新的生活规范的挑战,乡民们不再崇尚节俭,很多青年人沉迷于电脑游戏,追求炫耀式的生活消费理念。因此,回到湖南乡下的韩少功总会有一些怅然:“哪怕是在一个偏僻的山寨,我听到立体音响里轰轰扑来的,不是记忆中的唢呐和山歌,而是我在海南、在香港、在美洲和欧洲都能听到的电子流行音乐。”[3]69不过,韩少功没有因为对农耕文明的诗意化讴歌而否认现代文明的便利性,没有在对比中寻求非此即彼的文化批判或者道德评判,而是力图实事求是地展示现代化大潮中,乡村不可避免的命运变化和潜移默化的价值理念更新。
乡村寄托着韩少功的生活理想和社会理想,他关注自己的心灵时空,关注乡村生命个体与精神品质,力求在精神和行动上切合乡村生存状况,突出自己亲近乡村生活的审美诉求。因而韩少功更善于通过普通的乡土风情挖掘乡村生活中的诗意,寄托自己的生活理想与文化诉求,展现农民坚韧顽强的生命力和自在状态下的自足意识。那种淳朴原生态的自然美与人情美蕴含着韩少功对民族性格的理解和对理想人性的向往。他的散文记录民间形态与个体记忆,不但是对刻意讴歌乡村的想象式写作的批判,同时也是谱写着最为真实的乡村民俗史与文化史,并以此抵抗城市常见的外在的喧嚣与阴暗,追求明净自由的生命时光,守护着尽量少被干扰的乡村朴实的自然氛围与良知传统。
韩少功的散文既有对村庄风土人情和民间文化的诗性讴歌,也有对村庄生存艰难和精神困境的书写,同时更饱含一份对乡村在淳朴的文化传统和物质的现代化之间文化困境的展示。他将对乡村的生命关怀化为一种精神信仰的执行力。是寻求精神舒适的隐蔽所,也是支撑自己作为文化人的自由理念与公民意识,充实和滋润自己作为社会人的价值观。他的这种“进步的回退”意在坚守着文学的“民间品格和批判精神”。[6]5
韩少功诗性地寻找心灵净化的创作灵感以及生存状态的选择,蕴含着几份知识分子的诗性想象和有意识体察民生疾苦的良知情怀。正如韩少功在文中所言,他是把自然当作十分重要的“文明符号”,“借以支撑自己对文明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以及自我改进……更重要的,是补救自己的精神内伤”[4]218。
二、“次优主义”的文化怀乡
韩少功从“文化寻根到皈依自然”[7]不只是单纯的创作转型,更体现了“次优主义”[8]332的文化诉求。韩少功曾经明确表示乡土“是民族历史的博物馆”[9]186,乡土中所凝结的传统文化能够更多地显示生命的自然风貌,使得民间文化形态能够提供给作家足够的心灵养分与诗性思维。作家在文本中阐述它们的丰富与精彩程度也常常会成为考察作家是否能够真正深入人民群众、了解民众疾苦的关键所在。
城市日常生活的符号化的生产与消费,满足于模式化的生活与流行化的思维观念,很可能“使我们丧失一种价值清理和价值重建的定力”[1]186。韩少功的散文突出了城市精致文化的喧嚣与虚伪,衬托出乡村粗犷文化的自然随性,民俗民风之淳与知青情怀下的乡村诗性,既蕴含着韩少功渴望回归乡村的自我省察,也反映了韩少功有意识地抗拒城市文化的制约、构建打破城市文明病态的文化思索。
在抒写民俗民风的淳朴方面,韩少功以最真实的生命个体体验来巩固自己乡村召唤的诗性元素,渴望对生活在厚重土地上的具体单个的生命及其生存状况做一个现场的目击者与感受者,实实在在地感受大地的疼痛和人物苦痛,将无视乡村的诗性讴歌转变为为农民和农村多少尽己所能的身体力行,将印象式回忆转化为确认乡土气息的直观体察。这既是一种感知乡村落后贫穷的物质扫描,更多了一份饱含精神和情感的人文主义的触摸,是踏实对待农民、融入农村的方式,而不是看待农民的方式。这也使得韩少功的散文多了细节和内涵,增加了暖心的细腻和情感。
在韩少功的散文(如《山南水北》)中记录了农民生活的诸多层面信息,诸如农民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具体到怎么盖房子、怎么节约原材料、怎么通讯、怎么现代化而不得。同时也写了农村存在的偷情行为,却没有猥琐的成分;写了农民式的狡猾,却无恨的成分;写了极端的懒,却能升华为哲理的高度。即使涉及乡村的恶,也是那种一眼望穿不带任何遮蔽的恶,是值得同情的、道德上又是没法指责的。
乡村有乡村的价值判断与处事原则,在描述乡村大事件时,特别是乡村干部宣传国家政策集中农民进行开会时,韩少功更是写出了乡村特有的思维逻辑。在乡村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乡村干部只能借助特殊情境的触发和偶然的契机,才能彰显民主集中制的优势。原本开会现场吵吵闹闹、无法正常进行,可是当有人涉及宗庙式的骂娘时,则是乡村干部博得同情进而顺利解决民主无法解决的问题的契机。乡村干部一经掌握话语权,常常借题发挥,以道德的制高点压制民意、拉拢人心,体现出颇具乡村风情的农村干部形象。他们只有熟悉农村的话语体系与民俗特点,才能有效地开展政治工作。乡村是以道德来引领一切,而不是靠宏观的口号。《山南水北》中的不可“骂娘”这一乡村话语体系的神圣逻辑,是让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村民得以信服的最佳切入点,并迅速成了公意的代表和良知的化身。乡长带着捍卫个体祖先的凛然正气与道德优越感带动群众的感同身受与怜悯共鸣,而且乘胜追击“从禁码说到封山育林,再说到计划生育和宅基地收费,把所有可能引起争议的话题统统扫荡”[2]95,从而顺利有效解决了乡村存在的政治说教的难题,实现了上传下达的政治任务的有效开展。这一带有喜剧色彩的画面,其背后蕴含着的是乡村世代相传的孝行文化与宗庙意识。韩少功呈现了乡村最低线的道德监控与道德共鸣,展现了传统文化中的“平民传统”。
韩少功的“文化怀乡”是与乡土亲密接触的,而非单纯的心理运思。他对乡土有着更为确实的生命感触和更为宏观的文化视野,他不只描绘了映像中的乡土记忆,更展现了与乡土的现实文化关联,而且在彰显民俗文化的质朴淳厚时,也展现了作者难以排解的人文忧思。如工业发展拉开的城乡鸿沟,导致优质的农村资源,特别是温柔漂亮的女人,她们当然“流向富庶的地方,流向城镇,流向工业”[4]150。城市物质文明以直观的视觉冲击逐步摧毁着农民对家乡故土的深沉依恋与厚重感情,城镇楼宇“虽然不太适用,但能预支一份荣耀”[2]245而成为农民快速模仿的形象工程。在乎“尊严最大化”的“豪宅”带有融入城市节奏的强烈渴望,显示出物质文明的巨大感召力,同时也正在逐渐覆盖泥土的芬芳和农耕文明的传统记忆。
韩少功深知城乡之间存在着知识体系与文化理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别,如城市习惯用公历“记录太阳之历”,农村习惯用阴历“记录月亮之历”[2]46。对雷电已经没有概念的城里人,对乡下人在打雷时暴露在茫茫旷野的现象是永远无法想象的;对于农民式的自我宽慰的心理想象:“不做坏事就不怕遭雷打”[2]80,自然就会觉得是无视科学、盲目迷信甚至愚昧可笑。当农民被想当然地认为是淳朴、善良、忠厚等多层面讴歌的代名词时,衣食无忧的城里人(如韩少功《月下桨声》中提及的大学系主任),对于农民逐渐接触与融入现代化气息的功利性取舍,难免会表现出惊讶和抨击,从而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经济来源相对单一的农民进行脱离乡村实际生活状况的指手画脚。他们一边享受着农民捕来的鱼,一边谴责农民觉悟之低,没有一点“环境保护意识”,居然用密网捕鱼;而当汽车陷入坑中,农民不给钱就不帮忙时,又认为“民风实在刁悍”[3]206。就农村的生活状况而言,农民有权利选择自己认为合情合理的平等交易,就像韩少功文中提到的“红衣女孩”和她的弟弟,宁愿费时费力地折返,退回多收的“一块钱”鱼款,在没有退足一块钱的情况下,宁愿再多跑一趟送上“一大把葱”作为补偿,这种追求心灵纯净和道德无瑕的“执拗”显然是不曾领略乡村艰辛的城里人难以理解的。
韩少功将众多城里人的向往或者守望化为脚踏实地的劳作,从沾满泥土气息的土地中散发出自己劳作的自由声音,本着不卑不亢的行为准则回答了貌似归隐的生存姿态,多了一份坦荡和真诚,以每年长达半年之久的乡村体验的决绝抵御城市文明的惯性纠缠,散发着理想主义者生活的倔强。这是韩少功价值信仰的选择,它受驱于一种健康的生活态度和悯农亲农的文化理念。他将原本属于个人的行为拓展到了属于乡村书写者的集体无意识的价值取向,在常识性的劳作中捡起普世意义的精神愿望,将灵魂的责任与民生的义务结合在一起的生命行为,彰显着知识分子良知意识的外化与责任意识的拓展。这也使得他的散文创作能够在更为广阔的生命范围里找到更为实在的服务对象和独立操守,展现了韩少功“看重文化,更看重文化后面的灵魂”[8]335的艺术诉求和自由愿望,在增强自身生存意义的同时创造出一份文化价值。
三、文化碰撞下的身份认同
韩少功的乡村视野与生活体验是他有意识地在维护尚存的优良乡村秩序与文化传统,是对意识形态下的惠民政策上传下达的隐性监督,同时也是他力求造福一方百姓、服务地方文化乃至扩大地方知名度甚至发展旅游业、增强地方文化自信的身份言说。而韩少功外出交流的国际视野,则进一步反衬出了他对乡土的眷恋之深,在两种文化视野的对比中,韩少功深切体会到了作为农耕文明的特有价值重心的乡土家园蕴含着的“游子悲乡的伤感情怀”,“落叶归根的回迁冲动”,“显示出祖居地或原居地的强大磁吸效用”[5]168-169。
这种文化碰撞与对比集中地体现在韩少功的《人在江湖》散文集中。文学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能够将主体意识升华为灵动的艺术境界,有效地传达出主体的文化素养和价值判断。韩少功一方面指出了异域文化的长处,但另一方面也越发感知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涵和维护民族文化尊严的必要和艰辛。因此,韩少功虽然感受到了法国男人的优雅风度,激赏的却是“中国士大夫传统的闲适、飘逸、超脱和虚静”[10]18。他反感在巴黎的演讲厅里迎合西方人知识胃口的某位中国作家,“宁愿暴露自己的平庸和笨拙,也不愿意哗众表演”,表现出“从精神上保卫一个民族”[10]34的自觉与自尊。中国人是一个爱笑的民族,在巴黎的中国书展上“中国较少西方礼仪的规训,笑起来大多任性而为”,但韩少功认为这种“天然的笑容”是难能可贵的心理表现和生理形态。西方“更多的笑容正在由好莱坞一类霸权媒体批发”[10]74而呈现出明显的商业化气息。
韩少功有意识地将异国他乡与乡土家园进行比较,呈现的是西方社会的工业文明与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传承的人伦亲情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是他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9]184的文学观念的确认。由于作者感知的异国他乡是孤独的、忧伤的,同时也领略到了繁华之中的悲凉,因此当作者理性的思索与现实的孤独变成一种悲悯,联想到哪怕是“贫瘠而脏乱的”故乡时,作者文字的流淌显示出了坚定不移的意旨——眷恋故乡:
我的故乡没有繁华酥骨的都会,没有静谧侵肌的湖泊,没有悲剧般幽深奇诡的城堡,没有绿得能融化你所有思绪的大森林。故乡甚至是贫瘠而脏乱的。[10]22
故乡虽然贫穷,却很温暖。韩少功的这种审美情感是对客观物象的主观情感投射,是一种民族情感体验的动态呈现。抒情需要理性的制约才能避免非黑即白的片面性,韩少功没有因为眷念故乡就完全否定异域的风景,而是基于对现实生活的经验拓展,在想象层面突破现实时空的限制,将西方印象与本土记忆进行了非讴歌式的对比加工。这是比较高明的抒情言志,寻求的是一种不容置疑的“身份”认同感:“文学积极地与民族或国家联系在一起,从而有了‘我们’和‘他们’的区别……文化这时就成为身份的来源。”[11]
在异国他乡对于“突然涌流的想象”的故乡,韩少功在选取意象上具有典型的民族乡村风情:“小径”而非宽阔的马路,“月夜”而非霓虹灯,“草坡”而非楼房,“小羊”而非宠物,“犁头”而非汽车……这些意象具有明显的“去城市化”的倾向,也间接地肯定了乡村劳作的艰辛与光荣,这与韩少功在散文《山南水北·扑进画框》中抒发的渴望“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是一脉相承的。韩少功通过“夕阳”到“月夜”的时光流转感喟思乡情怀,选取“小径”“草坡”“小羊”“犁头”等农耕文明的典型意象,由二胡的悲怆联想到故乡的悲怆,清晰地认识到任何旅游景区的美不过是“失血的矫饰”,每个个体不过是匆匆的生命过客;而养育自己的故乡则是“美中含悲”,艺术家是“痛”并眷念着故乡的诗意的栖居者。因为故乡是生命的发源地,故乡“存留了我们的童年,或者还有青年和壮年,也就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10]22。
故乡农耕文明传承的淳朴民风及其故乡发展的滞后现状,对于游子而言始终是一种心灵的召唤。故乡的“血、泪,还有汗水”蕴含的“美”,对应的是游子的“悲”“痛”“怜”,故乡越是残破衰败,游子越是难以释怀,这里既有对家园故土培育游子的艰辛不易生出的感恩意识,也蕴含着游子不忘本,可又暂时无力回馈家乡、反哺家乡的愧疚情怀。这种深切的家园意识是韩少功、贾平凹、刘亮程、刘醒龙等当代乡土作家的集体无意识。
对故乡的现状韩少功在《人在江湖》中进行了以点带面式的呈现,认为故乡尚有诸多让人“失望”的地方,诸如“浮粪四溢的墟场”,“拥挤不堪的车厢”,“阴沉连日的雨季”……[10]20这是欲扬先抑的手法,不过叙述得客观而真实。乡土作家正是“通过表现村庄生活基本生存欲望的艰难”,从而能够深入“思考人的自然属性在社会属性制约中的艰难挣扎,表达了人的生命意识的自觉”[12]。
韩少功对故乡表示“失望”,是对自己奔涌的思乡之情有节制的理性制约,从而避免了无视故乡贫穷与苦难的田园牧歌式的歌颂,避免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情感的宣泄。但游子的这种“失望”是“不同于对旅泊之地的失望,那种失望能滴血。血沃之地将真正生长出金麦穗和赶车谣”[10]22-23。两类“失望”的不同之处在于作者对故乡是满怀回归的眷恋与触目滞后的惆怅。这种惆怅而又依恋的家国情怀追求的是一种文化归属感,是游子触摸故乡的脉搏、融入本土文化氛围的诗性显现;而源于厚重的土地、贴近普通民众的“金麦穗和赶车谣”的文学意象,则具有“物质丰盈”与“精神鼓舞”的双向发展寓意,表现出游子渴望通过“劳动”和“奉献”使故乡繁荣富强及其对乡土文化未来前景的坚定信心。
在全球化的今天,移民已经司空见惯,这使得“异国他乡的身份认同显得尤为迫切”[13],是否移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事人对某种价值观的追寻,无论是追求个人发展还是旨在探求精神信仰,韩少功都明言对于移民“好像是缺乏勇气也缺乏兴趣”。不想移民是一种明确的文化“确认”,它“意指对一种特殊身份——国家的、性别的、种族的、地域的——确认而不是超越……”[14]标榜发达、自由、民主的金钱社会多少存在残酷的权力之争、利益之争,以致引发诸多人性的沉沦(如作者在文中所言的“文化盲流”),而作者显然不愿意将自己的生命浪费在人情的纠葛与时代的病态上,只愿意静守故国家园、感受生命之花与艺术之花的自由绽放。不想移民强调是“民族的自我”,这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与价值观的熏陶下知识分子坚守民族文化阵地、构建民族文化信仰系统的“回归”姿态,应该说韩少功是一直秉承这种民族文化特质的:“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9]188
民族文化的担当意识落实到了踏实而熟悉的“家园”故土上,它“寄寓着熟识、亲近、眷恋、舒适等情感性因素,诱发着人的乡情、亲情和思乡感、归家感”[15]。韩少功的散文巧妙地将思乡恋家转化成为主体合情合理的文化需要,使漂泊的灵魂找到了真正的心灵栖息地。在中外文化碰撞下,充沛的个体生命与“虚空”般的外在环境产生了不能言说(首先是言语障碍)的冲突,使得作者更为明晰地转向关注自身的生存状态与感性体验,以培养自己不会迷失的精神诉求与独特的生存风格,韩少功的散文抒写了浓郁的乡土情结与明确的文化诉求,以知识分子特有的人文情怀,彰显出对乡村文化观念与价值体系的深情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