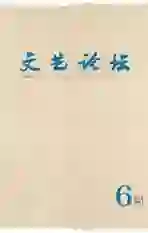被困扰与渗透的情动主体
2021-01-13陈嘉莹
陈嘉莹
摘 要:后电影状态常被批判为加速主义与情感资本主义的附庸。影像透支着个体情感,使主体沦为无生命力的倦怠主体。然而疫情印证了后电影状态也有着孕育情动主体的可能。维维安·索布切克提出的观影具身体验为情动主体提供了条件。劳拉·馬克斯对触感影像的分析表明:触感影像的流通为跨文化观影者提供了共同参与的空间,使主体得以触碰他者,为他者而情动。结合朱迪斯·巴特勒在《战争的框架》中对战争影像的论述,我们试图阐明触感影像之衰朽在事件中的情动效应,指出影像能够对主体造成挥之不去的困扰,使其成为可渗透结构的一部分,体认生命的必朽性与脆弱不安的现状,从倦怠主体转化为为他者负责的情动主体。
关键词:倦怠主体;具身体验;触感影像;触觉主体;衰朽;情动;
《后电影状态》(The State of Post-Cinema)曾在开篇指出,由于运动-影像(moving-image)的技术与文化发展,电影研究者们提出“后-电影”以指称媒介特性与本体论都与传统电影截然不同的电影状态。①的确,我们已然进入后电影的时代。电影因为电视机的出现失去了掌控权、因家庭影院的普及丢失了有着迷影(cinephilia)②情结的观众、因媒介的数字化丧失了原初影像的本真性(authenticity)。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趋势似乎决定了新媒体电影的发展,这意味着资本不仅左右着电影技术的生死也操纵着电影的情感生产。出于这些原因,后电影状态时常被批判为加速主义与情感资本主义的附庸。主体似乎注定过着被追捕的、无生命的生活(haunted un-life)③,他们的情感因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而被透支殆尽,恰如韩炳哲(Han Byung-chul)所说的无生命力与伦理能力的倦怠主体。那么,当下的电影及其折射出的主体图景是否全无希望了呢?或者说,我们还有重新获得本真的影像体验或某种主体性的可能吗?弗朗西斯科·卡赛蒂(Francesco Casetti)曾指出,电影尽管经历了一次次的“死亡事件”,但是它都能够幸存并实现真正的重生④。这也提醒我们,电影有着化危机为转机的可能。2020年正揭示了电影在“死亡”之中孕育新情动主体⑤的能力。疫情无疑是一次断裂性的“死亡”事件,它不仅撕裂了我们的生活世界,也让社会近乎停摆。电影院的观看空间被彻底取消,流媒体与短视频的观看形式全面替代了传统的观影体验,观影者的身体似乎无一不被抛入去中心化、弱时空化与去身化(disembodiment)的状态。但随着疫情的发展,与后来在全球发生的“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后电影凭借关注有限的身体召回了有着情动能力的主体。
维维安·索布切克(Vivian Sochack)提出的体验影像的具身主体可以说为情动主体提供了雏形,结合劳拉·马克斯(Laura U. Marks)对触感影像(haptic image)及主体性的分析,我们将发现:从表面上看,因疫情被隔离在家中的孤立主体,似乎被切断了情感联结,但与此同时,触感影像的流通却为主体打开了参与性的空间,使主体得以与一个个他者真切相遇。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战争的框架》(Frames of War)中论及摄影能够激发观者的情动,这正呼应了触感影像在事件中的情动效应。当疫情将生活世界切分为一个个隔绝空间时,是流媒体与短视频的传播为主体构筑了情动的网络与异托邦式的情感空间。影像通过触碰身处在孤立空间的主体,舔舐着人类脆弱的身体,并为主体重获伦理能力提供了可能。而这些都是传统影像体验所无法给予的。
一、观影的具身体验
电影学者奥梅·金(Homay King)曾借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中的叙述,将太空计划诠释为人类摆脱具身知觉(embodied perception)的尝试。现代化驱使着人们“从他的周围环境与对周遭事物的关心中抽身而出”⑥,并带着测量的目光看待世界。此般去身体化的欲望,在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的梦想中得到了延续。早期“虚拟现实”概念的提出者,借笛卡尔点明了虚拟现实的真相,它裹藏了人们想要摆脱空间与物质环境,作为一种思想实体存在的愿望⑦。基于这些,奥梅·金将当代人对数字媒体、网络与虚拟世界的迷恋,归于摆脱身体、感官与物质空间束缚的愿望,并将此命名为数字笛卡尔迷梦(digital Cartesian dream)⑧。
她显然并不看好去身体化的倾向,并指出许多当代艺术家与影像实践者对这一梦想的拒绝,他们虽然使用数字媒体,却积极地关注世俗的与有时限的物质,企图颠覆数字媒体带来的去身化。例如阿涅斯·瓦尔达(Agnes Varda)用数码摄像机拍摄的第一人称叙事纪录片《拾穗者》(Des glaneuses),就是一部借数字技术制造反差的唯物主义电影⑨。受米勒(Jean-Franois Millet)的绘画启发,瓦尔达将拾穗者的形象移置到了当代拾荒者身上,并聚焦他们所捡拾的社会“剩余物”。她时而让自己年老的身体出现在镜头中;又时而隐没,通过在镜头前伸出自己的手,揭露镜头之眼所依赖的摄影者身体。奥梅·金试图表明,即使电影已经逐渐被数字媒体化,但具有反思精神的创作者们仍关注着与身体息息相关的老化、记忆与可朽等具身观念。借此,她尝试回应后电影状态中的一个显要张力,即去身体化与具身化之间的张力。显然这是当下的电影理论者们无法回避的一个课题。
索布切克就在《肉身之思》(Carnal Thoughts)中急切地问道:当数字媒体允诺观众一个“弥散具身(diffusely embodied)的状态”⑩时,或当我们认为身体的有限性是一种禁锢而非感知、思想与行动的先决条件时,我们将失去什么?随后她给出她的判断:当我们对人类身体与在世行动越来越缺乏具体明确的兴趣与投入时,价值的自由浮动与饱和的当下瞬间,很可能让我们失去未来11。出于这样的担忧,索布切克试图借“身体现象学”应对数字笛卡尔迷梦潜藏的危机。以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为代表的“身体现象学”旨在克服笛卡尔遗留下来的身心二元论,他指出人的知觉是从身体出发展开观察的,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取决于“活生生的身体”(lived body)。生命不是一个简单的意识对象。如果不参照被感知的自然(perceived nature),我们就无法思考生命与外部自然。“活生生的身体”意味着身体不仅感知自然,它也居于其中。因此我们不能从纯意识或反思的角度来描述身体,而应从身体的变形(metamorphosis)来描述,在此,身体不应被化约为纯粹物质的身体,而应被理解为“精神的身体”12。索布切克借此重新阐发观影体验,结合唐·伊德(Don Ihde)的技术现象学,她将影像体验的动态过程描述为:影像通过具体的物质条件影响着观者的微观感知(microperception),使观影者沉浸着、制作着、回应着社会;同时通过其表征功能影响着观者的宏观感知(macroperception),经意识与文本参与着观者的感官。13这样说来,影像既是经验的主体和对象,也是我们感知和表达的积极参与者。而在影像面前活生生的身体则既是一个客观的主体,又是一个主观的客体14——一个兼有物质性与能动性的、不可还原的感性集合。
这般对影像体验的现象学描述指出,在观影过程中,具身主体能够与所有人和物建立亲密的、物质上的联系。索布切克认为,具身的影像体验实际上为新的社会主体提供了条件,因为这些体验是集体性的,虽“外在”于自我又調动着自我的深层结构15。这使得这一新社会主体能够发现活生生的身体的脆弱性和可朽性。简言之,索布切克借身体现象学提醒我们不应该将观影者与周遭的物质性分离开来,而是需要仔细观察观影的物质环境以及我们对世界和他者的感觉与反应,并认识到不仅是技术与文本还有我们的肉身,都既有着重量也有着超越的可能。这样做有助于我们理解观影具身主体的伦理意义。索布切克很可能是对的,她十分敏感地指出,影像和观影者都应被理解为具身存在,但是她似乎过早否认了数字媒体的具身可能。事实上,在后电影状态下,尤其在疫情制造的极端时空中,我们的身体看似被迫移出了影像的传统观看空间,但它们没有被真正取消。我们将在后文关于马克斯的论述中看到,数字媒体不等同于去身体化与无行动。数字媒体不仅仍有着具身可能,还能够唤起触觉关系,并通过感染激发倦怠主体的能量。
二、触感影像及其衰朽
马克斯的“触感影像”概念为数字媒体的具身性提供了可能,也激发了一种新的主体性,即触觉主体性。在她看来,观影体验充盈着触觉关系,这样的触觉关系与“平滑空间”(smooth space)的概念息息相关。德勒兹与瓜塔里(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将传统意义上的度量化空间解释为层化空间(striated space),并提出与此相对的“平滑空间”(向量的、投影的或拓扑的空间)。前者作为视觉的空间(像欧式几何的层化空间),为线性的和固态之物划定了封闭空间;后者则是一种接触的空间,充盈着物-流(chose-flux)的分布,它们不断进行着微小的(触觉的或手的)接触活动。16借此,马克斯指出,平滑空间是一种不断流动的共享空间,在其中,观影者不再是“外在静止的观察者”,而是能够与影像、观影环境或其他观影者发生触觉关系(tactile relations)的人。总之,通过平滑空间的概念重构观影空间,马克斯提出观影不再是一种具有控制性(mastering)与层级结构的体验,而是一个与触感影像保持互触的流动体验。只有通过物-流的持续接触,我们才能够真正感受到影像流变的独特性与无可仿效性。
如上所言,观影体验充盈着影像物质性、感知者与所表现物之间的触感体验,所以马克斯说电影是一种皮肤。借此转喻,她试图将影像激发的触觉体验拓展至影像的流通过程中,并赋予后电影状态以积极意义。她认为,观影激发的触觉关系不仅停留在单次的观影体验中,还充盈在影像的复制与传播中,在此过程中,影像为观者带来的触感体验恰如“一系列互相留下痕迹的皮肤接触”17。事实上,触感影像的论述是基于跨文化电影(Intercultural Cinema)的特性提出的:与传统商业电影不同,跨文化电影在内容上包含实验性的短片电影与叙事性的长片电影,在展示空间上指涉电影院、美术馆、画廊等等剧场空间,在观念上则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流动(这包括来自不同文化的影像内容和观影者)18。就此而言,跨文化电影是机械复制时代特有的电影类型,因为可复制性,它得以在不同文化间传播,触及各异的观众并在多元语境中延伸其意义。电影作为皮肤,既意味着影像体验充盈着触觉关系,也暗示它与超个体的主体性相关,因为影像体验将涉及不同具身环境与主体的相互接触,主体因此能够介入到情境甚至参与到群体性的事件中。这种接触经由触感影像的流通不仅在共享空间中实现,也通过时间的推移建立起一种“变革的联盟”(transformative coalitions)19。在瞬息万变的具体网络——从八卦、电子邮件到社区、大学和机构,当然还包括如今的互联网,触感影像通过接触(contact)、偶然发生的(contingent)影像体验与感染(contagion)20标记着自身的在场,并不断促进联盟的流变。
通过提出跨文化电影,马克斯将更多元的影像类型与体验纳入触感影像的范围内,并指出跨文化电影与网络结合可能具有的积极意义。因此当我们看到马克斯开始为数字媒体辩护时,或许不应该感到惊讶。在论及触觉与电子学时,马克斯表示,许多评论家(如上述索布切克的观点)都认为数字媒体似乎完全存在于一个象征性和非物质的领域,但事实上,数字媒体和我们是相互包含在物质过程中的。的确,对数字化的工具性使用造就了虚拟世界的外观,但数字化的笛卡尔空间(或“数字笛卡尔迷梦”)只是特定实践的产物,而非其本质。数字媒体看似构建了一个个非实体的独立主体,但正如奥梅·金所言,艺术家通过数字媒体实现的创作仍然可能是具身化的,并且用马克斯自己的话说,它们也都是具有触感的,网络上的影像作品远非虚拟的,它索引(index)了不同的物质层面与相互关联的生活21。
数字影像的具身性首先体现在它和传统影像一样都经历着衰朽(decay)。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就指出数字影像会因为有损压缩出现信息丢失与画面受损的衰坏状况。因为比特(bit)是数字通信中最基本的信息单元,所以吉布森将这样的状况比作“比特-腐烂”(bit-rot)22。但事实上,衰朽也带来了生机。黑特·史德耶尔(Hito Steyerl)在《捍卫贫乏影像》(In Defense of the Poor Image)一文中辩证地谈论了影像因衰朽而导致的“贫乏”。她认为虽然衰朽后的贫乏影像普遍分辨率不高,但它们能够以极低的画质复活被时间淘汰的老电影,消解影像因画质差异带来的阶层关系。并且,因为低清晰度的影像便于传送,所以贫乏影像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图像的流通与共享23。不仅如此,马克斯还指出,机械复制时代的影像随着衰朽也再次迎来了“灵韵”(aura),因为物质实体的细微变化将使影像在每一个时刻都呈现出独一无二的效果。其次,数字影像因为其自身发生的错误透露着具身性,一些数字影像作品通过模仿数字错误(error)以激起数字影像的停顿和崩溃并释放电子的随机效果。例如专事“故障艺术”(Glitch Art)的艺术家通过破坏电子设备的数据或实体进行的艺术实践。另外,现场影像表演也通过一次性的视听实践以强调数字媒体的转瞬即逝(ephemerality)。表演者的在场以显明的方式提醒我们,数字影像如同表演者的身体一样也有着其本真性与具身性24。
综上所述,触感影像不仅通过平滑空间实现了人与物的种种共享体验,也在流通中延伸着触觉关系,数字媒体则积极地参与其中。如果说索布切克的观影具身主体还对数字媒体保持着警惕,那么马克斯的论述则揭示了数字媒体孕育全新主体性的可能。马克斯将此主体性命名为“触觉主体性”,以反对统一的“主体性”观念。她认为看似浪漫的统一主体性,实际上暗含着对他者的暴力和孤立。触觉主体性则强调与他者的互触,并让主体在这些真实接触中承受因衰朽带来的逝去。这样的主体性不会为求自保而让自身免于伤害,而是将自身变为可渗透结构(permeable constitution)的一部分。25在马克斯看来,触觉主体性带给我们的将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变革联盟而非一个个破碎的主体。同样在面对影像与主体性的问题时,巴特勒与马克斯一样都将关注点转向了影像与衰朽的关系。并且,巴特勒将这些分析落脚于战争影像,使我们更易把握触感影像的情动潜能。结合二者的论述,我们能够进一步探究影像之衰朽及其激发潜能的机制。她们将为我们指出,影像能够对主体造成挥之不去的困扰,如同触感影像对主体的渗透,“它不仅作用于情感层面,也能启发人们的理解”26,促使我们面对生命的可朽性与脆弱不安的(precarious)现状,成为可被渗透的、始终被困扰着的情动主体。
三、战争影像及其情动的潜能
马克斯指出,当我们观看影像时,影像实际上一直在我们眼前死去(dying)。因为承认影像的物质性,意味着我们将意识到它们无时无刻不在消逝,如同我们承受着自身的死亡27。在这样的描述中,影像之衰朽不仅指的是“比特-腐烂”式的物质性损耗,还涉及被摄主体生命的逝去与观影者的自我指涉。这些都可以在巴特勒对战争影像的分析中找到依据。借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明室》(Camera Lucida)中的论述,巴特勒指出摄影有着将面孔与生命推入将来时态的力量,它总是同时指涉着过去与将来两种时态。巴特在谈论一位等待绞刑的人物摄影时,写道:“我同时看到将要发生和已经发生的”死亡,由于生命的必然有限性,所有的摄影都显示了这样的灾难(catastrophe),而发现此般灾难的普遍性也刺痛着观者28。这样说来,战争影像可以说是这种灾难的极端呈现,因为它总是与群体性的死亡有关,且这种死亡不仅包括肉身的摧残,还包括本体地位的损害与侵犯。另一方面,巴特勒认为战争影像将使观看者“看到自身”。她认为我们在观看战争影像时,将看到我们与拍摄者共享着框定影像意义的规范(这決定了哪些影像可以被公开与流通,哪些影像应该被拥护或指责),因此我们看到的其实是我们自身。29在此,她暗示这种“看到自身”的过程,能够引发观者的情动。但事实上,这个过程是通过我们与拍摄者(而非被拍摄者)的认同实现的,由于拍摄者与被拍摄主体仍可能存在着远距离的观看关系,所以这种认同并不能保证观影者与被拍摄者的真实接触,因此也不能保证情动的触发。在此,马克斯的“触感观看”(haptic look)正可以补充这方面论述的缺憾。
值得注意的是,巴特勒在《战争的框架》多次提及影像对观者的情感作用。在论述影像的复制与传播时,她虽然表现了与韩炳哲一样的担忧,指出影像的流通确实可能扩散战争的恶果,并让人们对战争引发的震惊产生倦怠,以致将战争氛围认作生活的寻常基调。但她也认为,数字世界的战争影像可以超越任何人的掌控,以全新的方式塑造意图。将影像暴露在新的具身环境中,有可能引导我们理解生命脆弱不安的处境,向我们提出伦理责任的要求。巴特勒借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理论,为当下的影像状态重新赋予了“灵韵”。她认为机械复制时代的影像能够脱离影像原本的创作情境,并且不断突破与划定新的情境,随着时间触发情动的可能性与轨迹30。正如触感影像的流通随着时间不断构建着变革联盟,战争影像也让事件延续到了未来。在此,“触感观看”的概念能够更具体地解释影像对情动的触发以及对生命脆弱性的揭示。在马克斯看来,清晰的影像不需要观者靠近,只有模糊的影像才要求观者切近的目光,并且如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分析的,低清晰度的冷媒介(cool media)要求观者调动多种感官的配合与想象力(以及如马克斯所说的“记忆”),因此观影者的参与程度更高31。显然,战争影像通常模糊不清,它因衰朽产生的颗粒感、模糊性与弥散性,极有可能引起观者的注意,吸引着观者用目光去触摸。这使观者得以与一个正在受苦与衰亡的自我产生认同,并唤起爱的关注,而不再漠不关心32。因此,目光的“触”不像“看”那样要求观影者识别对象并与对象保持距离,而是邀请观者贴近并与影像的衰朽发生认同。只有我们能够与影像发生真实的认同,情动的主体才是可能的,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通过影像真正体认到人类普遍的脆弱特质,以及人与人之间唇齿相依的生存状况。
因为触感观看不仅仅关乎死亡,还关乎对一个活着的、与己无关的人的爱。这让触觉主体在面对他者时得以让自身成为可渗透结构的一部分。这意味着,触觉主体不拒绝承认影像或他者的衰朽,也不从死亡的议题中退缩,而是接受他者的苦痛并承认死亡是我们普遍存在的一部分。事实上,巴特勒与马克斯一样,认为统一的“主体”观念隐含着对他者的化约,并常常沦为了民族主义与战争的借口。以美国发起的战争为例,美国总是千方百计“将自身塑造成固若金汤的主体,使自己永无遭受侵犯之可能,即便面对恐怖暴行仍然无懈可击”33。因此,911事件后美国的疯狂报复可以被理解为是对这一统一主体的补偿性修复。巴特勒认为如此统一的主体只是政治的虚幻神话,并常常沦为实施暴力的手段,因此她也提出“边界的可渗透性”(permeability of the border),并指出如果没有可渗透的边界,如果没有打破边界的可能,我们就无法想象主体。因为主体实际上总是互相依存并彼此暴露于各自的生存处境之中,主体同他者的接触构成了存在的根基。34存在的边界从来都不完全属于一个主体,因为这个边界总是与外界保持着持续的互触,因此也总是在互相渗透。如果如马苏米(Brian Massumi)所说,情动是先于个人的(pre-personal)情感的非意识方面(nonconscious aspect of emotion),那么始终在互触、互渗的观影者正是有着情动可能的主体,他们试图取消个体与环境、机体(观影者)与媒介(影像)、主体与世界之间的边界。
这样的主体在后电影状态下有着其特殊的伦理意义。桑塔格在《论摄影》中谈到,每一个被拍摄物都有可能成为愧疚感的对象,因为它已衰朽或可能不再存在,同巴特一样,她也指出,所有摄影都“使人想到死”。因此摄影实际上参与了他者(或他物)的必朽性、脆弱性与流变。因此她说:“摄影与死亡之间的这种联系,始终阴魂般困扰着人们的照片。”35如果结合触感观看重新理解这番话,那么摄影与死亡的联系就不仅仅困扰着照片与摄影者,也同样困扰着被摄影触动的观影者们。就此而言,人像摄影有着其独特之处,因为它们呈现的是他者的面孔。对此,巴特勒援用了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的论述指出,影像中的他人面孔要求着我们作出伦理回应。而触感观看让我们即使没有在现实中遭遇他者的面孔,也可以通过影像与他者照面,通过目光的“触”,他者的痛苦面容仿佛近在咫尺,困扰着你,让你产生移情,进而做出行动。因此,巴特勒才认为战争影像的呈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能否作出义愤、反对、批判等回应。因为人只有在此冲击下才有可能从冷漠的不情动状态转化为他者负责的情动状态。让我们回想一下疫情期间,那些受苦的面容是如何困扰着我们的吧。正是因为触感影像的传播,让我们能够在行动受限的情况下仍然与他者触碰,并最终转化为为他者负起伦理责任的行动(如民间组织的各种捐款与救援行动)。
除此之外,非裔美国影像艺术家亚瑟·贾法(Arthur Jafa)在“黑命攸关”运动中实施的一次影像实践,可以为触感影像对主体的困扰与渗透提供绝佳的范例。作为一个针对黑人暴力和系统性歧视的国际维权运动,“黑命攸关”运动因2020年5月发生在美国的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遭警方暴力致死的事件,发展成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抗议活动。这次抗议后来蔓延至全世界,以至于受到比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遇刺案更多的国际关注。在事件持续发酵的期间,贾法与全球13个艺术机构联合实施了一场48小时的线上放映活动,播放他于2016年创作的影像作品《爱是信息,信息是死亡》(Love Is The Message, The Message Is Death)。在这被《纽约时报》称之为数码时代的“格尔尼卡”36的作品中,贾法通过对电视新闻、监视录像、网络视频以及电影片段的剪辑,回溯了黑人的创伤性历史。总长七分半钟的影像以低清、模糊与弥散的片段集结了黑人群体的生命经验,并通過线上重复播放的形式与世界各地隔离在家的人照面。与剧场式观看的具身环境不同,这次放映的观众几乎身处个人的私密空间中。那些在暴力事件中受伤的身体、在赛事中或迸发或受挫的躯干与在舞台上随音乐起舞的身影,不仅绵密地诉说着黑人脆弱不安的生存处境,也邀请观众在私人空间中触摸这些陌生的面孔,以此感受“他们”与“我们”的切近。在其中,马丁·路德·金的形象凝结了影像中所有将要发生和已经发生的死亡,困扰着观影者。《爱是信息,信息是死亡》无疑是一个道出了黑人群体之脆弱性的死亡/衰朽-影像,它促使人们对弗洛伊德以及所有同样遭受厄运的黑人生命进行哀悼(grieving),如马克斯所说,这构成了一种集体性的经历,当语言和视觉再现都几近饱和时,“意义就会渗入身体和其他密集的、看似无声的记录中”37。这或许就是这个影像不仅让黑人群体深有体会,也让非黑人群体感同身受的原因。48小时的放映不仅仅是为了让触感影像向跨文化群体逐渐渗透,也以时间的跨度在网络世界中打开一个无边界与种族的异托邦式的情感空间,让不可化约的情感得以在流媒体的传播中积聚力量。后电影状态让这场集体触发的情动变为可能。
桑塔格曾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一书中呐喊道:“让残暴的图像困扰我们吧(Let the atrocious images haunt us)。”38在巴特勒看来,这一呐喊在如今仍有其力量。巴特勒试图指出,这句话实际上暗示了桑塔格对摄影重新燃起的希望,虽然这一希望显得暧昧不清。在《论摄影》中,桑塔格似乎判定了摄影对主体的无能为力,并指出煽情的图像不再能够让人作出伦理回应,“照片创造了多少同情,也就使多少同情萎缩”39,显然被情感资本主义裹挟的影像更是如此。然而,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桑塔格再度思考了这个问题,并承认摄影仍需要甚至有义务继续“煽情”,因为摄影让人们知道我们与他人共享的世界仍存在着无穷苦难——“这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善”。但除此之外,摄影还需要催生某种切近关系。除了远距离观看痛苦的方式外,影像存在着其他观看方式。如果说影像制造的“震惊”已经丧失力量甚至沦为陈词滥调,那么触感观看引发的情动或许是一种更可能催生切近关系的影像体验。
综上所述,笔者论述了后电影状态下的倦怠主体危机,也指出了情动主体的可能。索布切克提出观影的具身体验,揭示了电影之体和观影之身对等的具身存在,而马克斯关于触感影像的论述表明,网络时代的数字媒体不仅仍可以提供观影的具身体验,也能够以索引的方式召回身体。通过触感观看,我们不仅能够意识到媒介物质性的“腐烂”,还得以真切体认到他者生命的衰亡与自身终将面对的死亡。这些影像之衰朽对我们带来的困扰促使我们对承受苦痛的他者产生认同,并最终意识到脆危处境的普遍性。只有让触感影像持续地困扰着我们,倦怠主体才能够直面他者的苦痛,让自身转化为可渗透结构的一部分,对他者产生认同,并最终生成具有伦理与行动潜能的主体。
注释:
①③Malte Hagener, Vinzenz Hediger, Alena Strohmaier (eds.): The State of Post-Cinema: Tracing the Moving Image in the Age of Digital Dissemina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3, p.4.
②桑塔格在论文《百年电影回眸》中说道:“也许没落的不是电影,而是“迷影”。电影所激发的爱消失了。” Susan Sontag: Where the Stress Fall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1, p.117.
④Francesco Casetti: The Lumie?re galaxy: seven key words for the cinema to com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4.
⑤依照《情动理论读本》的解释,情动是在主动与被动之间(in-between-ness)产生的一种能力。它是对瞬间或持久关系的冲击或挤压,也是力量或强度的传递。它存在于身体与世界圆融循环的共振(resonances)之中,在人类、非人类、部分身体和其他身体之间传递,等同于力与“力的相遇”(forces of encounter)。因此,情动主体指的是有着生命力(vital forces)的主体,与无生命力的倦怠主体不同,他们有着行动、思考和延伸的潜能,这种潜能因力的相遇而被激发出来。Melissa Gregg, Gregory J. Seigworth: The Affect Theory Reader,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2.
⑥[德]汉娜·阿伦特著,王寅丽译:《人的境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
⑦⑧⑨Homay King: Virtual Memory: Time-Based Art and the Dream of Digitality,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7, p.10, p.73.
⑩11131415Vivian Sobchack: Carnal Thoughts: Embodiment and Moving Image Culture, Berkeley /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153, p.159, p.138, p.2, p.6.
12Maurice Merleau-Ponty: Themes from the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52-1960,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28.
16[法]德勒兹、加塔利著,姜宇辉译:《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上海书店2010年版, 第519页、第533页。
1718192037Laura U. Marks: The Skin of the Film: Intercultural Cinema, Embodiment, and the Sens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xii, p.5-10, p.20, p.xii, p.5.
212224252732Laura U. Marks: Touch: Sensuous Theory and Multisensory Media, Minneapolis /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p.xx, p.157, p.159, 弗洛伊德曾对哀悼(mourning)与忧郁(melancholia)作出区分,指个体面对“逝去”呈现出的两种不同状态。哀悼后的个体虽然经历了痛苦,但能够恢复自由的自我(ego),而进入忧郁状态的个体,则可能拒绝承认失去,因此出现自我的分裂从而实现主体的转向。马克斯则指出触感观看既与持久的哀悼相关,也与拒绝死亡的忧郁相关。因此,弗洛伊德的区分在此并不适用。触觉主体性则意味着主体既能够让逝去的痛苦渗透自身,也能够在此过程中实现主体的转向。p.xix, 91, p.xix, p.105.
23Hito Steyerl: In Defense of the Poor Image, E-flux, Journal #10 - November 2009.
2629303334 [美]朱迪斯·巴特勒著,何磊譯:《战争的框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0页、第182—183页、第50—52页、第106页、第108页。
28Roland Barthes: Camera Lucida: Reflections on Photography, Hill and Wang, 1982, p.96.
31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Cambridge / Massachusetts / London: MIT Press, 1995, p. 22-23.
35[美] 苏珊·桑塔格著,黄灿然译:《论摄影》,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第71—72页。
36格尔尼卡(Guernica)是毕加索最著名的绘画作品之一。作品描绘了经受炸弹蹂躏之后的格尔尼卡城。
383940[美] 苏珊·桑塔格,黄灿然译:《关于他人的痛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第96页、第105页。
* 本文系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曙光计划项目“身—言—像:当代法国艺术哲学的三个主题”(项目编号:12903—412221—17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